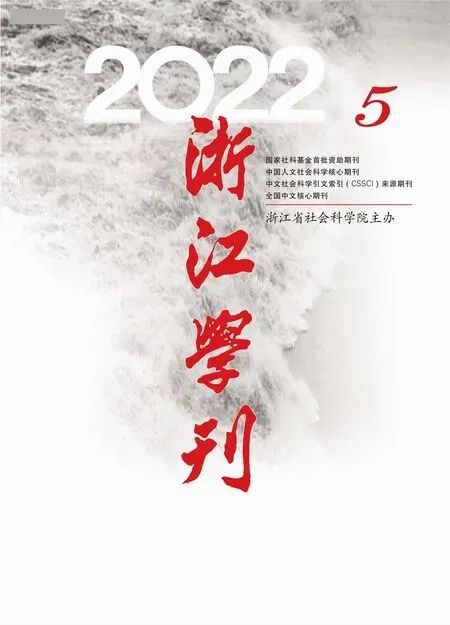叙事与历史:宋代“废罢《仪礼》”的话语空间
2022-11-19陆敏珍
陆敏珍
提要:“废罢《仪礼》”是朱熹对熙宁四年贡举改制的高度选择性解读,这一叙事后成为中国礼学史分期的关节点。事实上,若重建“废罢《仪礼》”话语形成中的事件群,可以发现,在科举制度的各项变革之中,很难看出有针对《仪礼》这部经书的特别考量,唐宋时期,它一直是九经中的中经,亦从未进入任何五经的序列之中,只是在考生“去难就易”的心态下,《仪礼》渐为举子所弃。朱熹“废罢《仪礼》”的叙事与其说是对历史事实的确认,不如说是对知识体系与知识传承的反思。
“废罢《仪礼》”是指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北宋熙宁年间科举改革,罢诗赋而用经义取士,朝廷令试以《诗》《书》《易》《周礼》《礼记》,兼以《论语》《孟子》,而无《仪礼》这一科目。到了南宋,朱熹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将之称为“废罢《仪礼》”,又因科举改制正是王安石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亦称之“王安石废罢《仪礼》”。
这一明显从历史时间中单独分割出来的事件,后来成为礼学史分期的关节点。废罢《仪礼》之前,关于《仪礼》学过去的模样可能并不清晰,但废罢《仪礼》之后,朱熹对礼学的式微进行了具体描述,由此亦构成了他通解《仪礼》的历史语境。由宋至清,学者重复并运用着朱熹“废罢《仪礼》”的叙事,并以此来结构《仪礼》学史,尽管他们所使用的“废罢《仪礼》”之后的时间标尺与朱熹有了很大差别。然而,若把宋代科举考试中关于《仪礼》的一连贯事件排列起来,我们会发现,“废罢《仪礼》”这一糅合了朱熹关于礼学的思考与具体事件的叙述,有时却和历史事实并没有那么融洽。因此,有必要重建“废罢《仪礼》”话语空间中的事件群,以便确立该话语生成过程中所要陈述的主题与观点。
一、“废罢《仪礼》”的叙事
熙宁四年(1071)二月,中书言:
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十,神宗熙宁四年(1071)二月丁巳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5334页;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308页。
此次改制是在“追复古制”、“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的呼吁下展开的。诏令颁布之前,围绕着是否要变革贡举之法以“一道德而奖进于人材”,什么样的考试科目才能获得有为于世的才俊等问题,神宗要求“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僚,各限一月内,具议状闻奏”,在此要求下,吕公著、韩维、苏颂、苏轼等均有建言,最后神宗采纳王安石所议。(2)《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一、四二,第5307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293页。可参见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五《议学校贡举状》,中华书局,1986年,第723-725页;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卷四二《乞改科条制札子》,中华书局,2021年,第702-703页;赵汝愚编,邓广铭等校点:《宋朝诸臣奏议》卷七八《儒学门·学校上》收吕公著《上神宗答诏论学校贡举之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51-853页。下诏废罢明经科,诸科改应进士科业;进士罢诗赋,考试试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五经。从熙宁四年诏令的主旨以及诏令颁行前后的各项议论来看,它并不是关于考试经典的争执,更不是专门废罢《仪礼》的诏令。一百二十多年后,朱熹从礼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次改革,他在《乞修三礼札子》中讲:
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诸生又不过诵其虚文以供应举,至于其间亦有因仪法度数之实而立文者,则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议,率用耳学臆断而已。(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乞修三礼札子》,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87页。
这份札子因“会去国,不及上”(4)王懋竑撰,何忠礼点校:《朱熹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第259页。,然而,对于有意修具三礼书的朱熹而言,它无疑是一份重要的思想表述。在这段文字中,朱熹至少指出了宋代礼学的三个面相:第一,科举考试中的三礼、通礼、学究等诸科的设置,是保证礼学知识传承的重要途径,三礼虽未能行用于世,但其学说却在科考士人中间诵习而得以流传;第二,熙宁四年变法中,存《礼记》而无《仪礼》,等于将《礼记》由传上升为经,并在事实上废罢了《仪礼》的礼经地位,这一遗本宗末的做法是礼学史上的一大过失;第三,礼学知识的传承出现割裂与断层,考生诵读礼文不过是为了应举,以仪法度数作文之人,所议多出于臆断,其学更莫知源流。
除了这份未及上奏的札子外,朱熹在与学生的对话中表达过相似的观点:
《仪礼》旧与《六经》《三传》并行,至王介甫始罢去。其后虽复《春秋》,而《仪礼》卒废。(5)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四《礼一·论修礼书》,中华书局,1986年,第2187页。
祖宗时有《三礼》科学究,是也。虽不晓义理,却尚自记得。自荆公废了学究科,后来人都不知有《仪礼》。(6)⑦ 《朱子语类》卷八七《礼四·小戴礼·总论》,第2225页。
荆公废《仪礼》而取《礼记》,舍本而取末也。⑦
祖宗时有开宝通礼科,学究试默义,须是念得《礼》熟,始得,礼官用此等人为之。介甫一切罢去,尽令做大义。故今之礼官,不问是甚人皆可做。(7)《朱子语类》卷八四《礼一·论后世礼书》,第2183页。
或许,可以将这些言谈视作是上引《乞修三礼札子》的注脚。在这些讲述中,朱熹对废罢明经科、诸科以及《仪礼》之前与之后的礼学稍作勾画。王安石废罢《仪礼》之前,六经是一个体系;废罢《仪礼》之后,《仪礼》从六经中抽离了出来。废罢学究科、通礼科之前,礼学虽不晓以义理,但学人熟记礼文,礼官亦是专门之官;废罢学究科、通礼科之后,礼官只做大义,不晓礼文,后人从此不知《仪礼》。总之,在朱熹看来,废罢《仪礼》与诸科,这一事件背后所包涵的意义以及所造成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
朱熹关于熙宁四年诏令的高度选择性解读,也为后人所接受,他们重复、化用着“废罢《仪礼》”的说法,用以作为礼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魏了翁列举三礼历史时讲:“至金陵王氏又罢《仪礼》取士,而仅存《周官》《戴记》之科,而士之习于礼者滋鲜。”(8)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卫正叔礼记集说序》,《宋集珍本丛刊》第77册,线装书局,2004年,第258页。熊禾曰:“自王安石废罢《仪礼》,但以《小戴》设科,与五经并行,自是学者更不知有周礼之书。”(9)熊禾:《重刊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三《刊仪礼通解书》,《宋集珍本丛刊》第91册,第287页。林駉也说:“自王氏废罢《仪礼》,独立传记……自是而后,儒生之诵习者知有《礼记》,而不知有《仪礼》;士大夫之好古者知有开元以后之礼,而不知有《仪礼》。”(10)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五《朱氏之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4页。最激烈的议论来自陈普《礼编》,他在自序中列举历史上“人伦尽废、丧纪扫地”的诸种事件,将“王安石废罢《仪礼》”与“七国争王之日,秦人坑焚之余,东西两汉知力把持之末,魏晋齐梁老佛之余,唐人室弟之妻、父之妾、子之妇,强藩孽竖恣睢凭陵之极”等相为联贯,用类比的方法,释其为“生人之祸,皆蚩尤以来所未有者”的烈性事件之一。(11)朱彝尊著,汪嘉玲等点校:《点校补正经义考》卷一六六《通礼四·礼编》,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1997年,第5册第458页。
明代,何乔新讲:“自王安石废经用传,士大夫知此经者鲜矣。”(12)何乔新:《椒邱文集》卷十八《书仪礼叙录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9册,第297页。史鉴说:“《仪礼》一书……自王安石废罢,后世不复讲。”(13)史鉴:《西村集》卷六《题司马御史与祝秀才书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9册,第812页。逮至清代,《仪礼》学达于兴盛,研究著作的数量远超前代。在述《仪礼》学史时,人们普遍将王安石废罢《仪礼》一事当作是《仪礼》学式微的转折事件。顾炎武讲:
“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是则《仪礼》之废,乃自安石始之。至于今朝,此学遂绝。(1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七《九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54页。
顾炎武被认为是清人校勘《仪礼》的“嚆矢”,“为《仪礼》之功臣”(15)彭林:《论清人〈仪礼〉校勘之特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他所叙述的《仪礼》学史,前部分文字来自朱熹,末句则将《仪礼》之废的历史从朱熹叙述的时代延长至明代。换言之,顾炎武将《仪礼》衰息的时代从熙宁年间覆盖至清代以前,在这一漫长的时间段中,固然有朱熹及其弟子们致力于通解《仪礼》,但其功并不足以挽回《仪礼》学衰息的局面,因此,四库馆臣称:“宋自熙宁中废罢《仪礼》,学者鲜治是经。”(1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经部·礼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159页。又在《仪礼经传通解》的提要中讲:
自王安石废罢《仪礼》,独存《礼记》,朱子纠其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因撰是书,以存先圣之遗制。分章表目,开卷了然,亦考礼者所不废也。(17)《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二《经部·礼类四》,第179页。
显而易见,此处对《仪礼经传通解》的评价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叙述逻辑,即,以朱熹本人的讲述作为线索,强调其在《仪礼》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将经、传分解清晰。秦蕙田则跳出文本,重新释读朱熹之于《仪礼》的意义。他讲:
自熙宁改制以后,《仪礼》久不立于学官,士子所习者惟《周礼》《礼记》耳,以经文较之他经为繁,习者寖少,故有是命。至《仪礼》,乃礼之本经,汉、魏以来专门讲授,代有其人。自王安石废罢《仪礼》,迄于南渡,遂不复立。朱子虽有《乞修三礼札子》,当时亦不能用,非朱子、勉斋、信斋诸公力扶绝学,礼教何由大明乎?(18)秦蕙田撰,方向东、王锷点校:《五礼通考》卷一七四《嘉礼四十七·学礼》,中华书局,2020年,第8198页。
秦蕙田引入更多的历史事实来解释《仪礼》之废,它既有制度设计的因素,亦有因考生偏选而触发的连带影响。在此政治与社会背景下,朱熹与弟子们通解《仪礼》,就不能简单视之为一本礼书,而应从更广的视域来提炼其价值。在对《仪礼》学史的整体观照中,源于朱熹的洞见,熙宁四年被视作是《仪礼》学史上的重要时间节点,同样地,朱熹与弟子们在《仪礼》上的努力也应视为是对熙宁以来废罢《仪礼》事件的重要修正,是力扶绝学,礼教得以大明的关键。
从《仪礼》或礼学的角度来解读熙宁四年的诏令,我们得到了“废罢《仪礼》”这一叙事。不过,如果循着熙宁四年诏令针对贡举进行改革的事实,从科举考试中去考索《仪礼》存废的历史时,我们会发现,“王安石废罢《仪礼》”这一概括的背后可能过滤了许多信息。
二、“废罢”前后:科举制度中的《仪礼》
朱熹从熙宁变法的系列诏令中抽出“废罢《仪礼》”、“王安石废罢《仪礼》”的叙事,将熙宁变法作为《仪礼》学衰息的源头,而将一件事的源头追溯到哪里显然对后来的解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关联的不只是《仪礼》学的叙事,同时,还有意无意地将历史信息作了某种导向。比如,上引“介甫一切罢去……故今之礼官,不问是甚人皆可做”,“至王介甫始罢去……而《仪礼》卒废”,“至金陵王氏又罢《仪礼》取士……而士之习于礼者滋鲜”,“自熙宁改制以后,《仪礼》久不立于学官”等表述中,在过去与今日的对照之中,在“始罢”诏令到“卒废”的结果中,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即自熙宁四年之后,科举中不再继续使用《仪礼》这部经书。这一让人误解的历史信息显然与叙事者只呈现某几个要素、而非完整的讲述有关。在“废罢《仪礼》”的叙事中,有开始,有结束,却并没有呈现中间的过程。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废罢《仪礼》”这一叙事背后的涵义,需要将原来作为背景的科考制度中的《仪礼》置于前景,以免这一被删滤的历史事实再次被遗忘。让我们将历史进程的时间尺度稍稍拉长些,以便将试图解释的问题的一些关键因素纳入关注范畴。
科举制度中,《仪礼》曾列入哪个序列之中?从唐代科举“分经授诸生”起,有九经、有五经。九经分大、中、小三类,《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1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1160页。五经博士以“《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为五经”(20)《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第1266页。。唐初,曾诏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令天下传习”。(2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1页。综合来看,如果我们要在这些概貌中拎出一条关于《仪礼》的简要线索,大致可以这样表述:作为考试用书,《仪礼》为九经的中经,五经不列《仪礼》。
宋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22)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科目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3604页。。九经至明法,这是考试的科目,也即是文献中所谓的“诸科”。熙宁以前,诸科考试中的场次、试题数、试题形式、判定合格的标准可能发生变化,但作为考试用书的九经、五经与唐代并无差别。比如,仁宗庆历四年(1044),宋祁等准敕详定贡举条制,规定:
诸科举人,九经五经,并罢填帖,六场皆问墨义。其余三礼、三传已下诸科,并依旧法。九经旧是六场十八卷……今作六场十四卷……第一场《春秋》《礼记》《周易》《尚书》各五道(为二卷),第二场《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各五道(为四卷),第三场《毛[诗]》《孝经》《论[语]》《尔雅》各五道(为二卷),第四场《礼记》二十道(为二卷),第五场《春秋》二十道(为二卷),第六场《礼记》《春秋》各十道(为二卷)。五经旧是六场十一卷……[今]作六场七卷……。第一场《礼记》《春秋》共十道(为一卷),第二场《毛诗》《周易》各五道(为二卷),第三场《尚书》《论语》《尔雅》《孝经》各三道(为一卷),第四场、第五场《春秋》《礼记》逐场各十道(为二卷),第六场《礼记》《春秋》共十道(为一卷)。(23)《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七、二八,第5299页。
从上引内容来看,用于考试的《仪礼》也与唐代一样,列于九经,不入五经。嘉祐二年(1057),别置明经科,同样将九经分为大经、中经、小经,“以《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穀梁传》《公羊传》为小经”。很明显,大、中、小经的具体设置与唐制亦无差别,不过,在大、小经配选上作了具体规定,“习《礼记》为大经者,许以《周礼》《仪礼》为中经;习《春秋左氏传》者,许以《穀梁传》《公羊传》为小经”。(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六,仁宗嘉祐二年(1057)十二月戊申条,第4496页;《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三四,第5302页。
神宗熙宁四年(1071),科举变革最为明显。首先,诸科改应进士科业,作为考试科目的九经、五经、三礼、学究等罢废;其次,进士“令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这五部经书作为一个整体,是新出现的经书系列,它与唐代所设五经博士与《五经正义》中的“五经”,明显不一,其中,《诗》《书》《易》《礼记》四部经书相同,《周礼》替换了《春秋左氏传》。不过,此条诏令执行十几年后,到了哲宗元祐时期,复诗赋,与经义并行。元祐四年(1089),将九经由此前的大经、中经、小经的三分法变为大经、中经的二分法,“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周易》《公羊》《穀梁》《仪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即不得偏占两中经”。同时,又对经义进士与经义兼诗赋进士的本经与兼经分别规定,经义进士需并习两经,“《左氏春秋》兼《公羊》《穀梁》或《书》,《周礼》兼《仪礼》或《周易》,《礼记》兼《书》或《毛诗》”。经义兼诗赋进士听习一经,但考虑到“若将《公羊》《穀梁》《仪礼》为本经专治,缘卷数不多,即比其余六经未至均当。所有兼诗、赋进士,自合依元条,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内各习一经”(25)《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一,第5312-5313页。。这样,被后人称为“元祐法”的兼诗赋进士考试中,由熙宁时期的五经变为六经,《春秋》重新进入习经范畴,《仪礼》则不再列入。(26)《仪礼》虽不列为科考经书,但九经的名称仍因袭如旧。据王应麟记载:“今所谓九经”者,即,《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六经,以及《孟子》《论语》《孝经》三小经。(王应麟:《玉海(合璧本)》卷四二《艺文·经解·总六经》,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年,第827页。)不过,元祐四年规定执行的时间较短。到了绍圣元年(1094),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各专治大经一、中经一,愿专二大经者听。(27)《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五,第5314页。南渡后,又兼用经、赋取士,除了个别年份,诗赋进士不再习经义。
从一个较长时间段来梳理科举考试中经书的使用情况,同样可以看到,在科举制度的各项变革之中,很难看出有针对《仪礼》这部经书的特别考量,唐宋时期,它一直是九经中的中经,亦从未进入任何五经的序列之中。相比而言,其他经书或由小经升中经,或由中经变大经,其中,变化最明显的是《周礼》,它首先成为熙宁四年诏令中的五部经书之一,后又上升为元祐法中的大经。由此来看,如果要由一部礼书的变化来解读熙宁贡举改制,显然,立足于《周礼》可能会得到一些更为直观的印象。尤其重要的是,王安石以《周礼》作为制度改革的依据,他将《周礼》与《书》《诗》并为“三经”,编《三经新义》颁于学官以“一道德”。王安石与《周礼》之间的密切关系显然要远甚于他与《仪礼》之间的不契,然而,朱熹却抽出了诏令中所缺席的《仪礼》作为主线,而不是将被废罢的所有经书视为一个整体,显然,朱熹本人的立场在“废罢《仪礼》”的叙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三、《仪礼》之废:举子的选择
如上文所言,在“废罢《仪礼》”“王安石废罢《仪礼》”的叙事中,朱熹以及后来者对废罢之前的《仪礼》并无着墨,但废罢之后《仪礼》的相关历史却是清晰的,“自荆公废了学究科,后来人都不知有《仪礼》”(28)《朱子语类》卷八七《礼四·小戴礼·总论》,第2225页。;“《仪礼》既废,学者不复诵习,或不知有是书”(29)《文献通考》卷一八十《经籍考七》,第1552页。;“自是而后,儒生之诵习者知有《礼记》,而不知有《仪礼》”(30)《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五《朱氏之学》,第64页。;“自王安石废罢《仪礼》,迄于南渡,遂不复立”(31)《五礼通考》卷一七四《嘉礼四十七·学礼》,第8198页。。然而,熙宁年间虽是科举大变动的时期,《仪礼》也一度废罢,但不久它又复归考场,如此一来,学者与儒生之“不复诵习”、“不知有《仪礼》”这一结果显然还有其他因素。为了避免偏离论题,我们仍立足于科举考试这一视点,从考生与经书的互动上去略补一些缺失的历史事实。
唐宋以来,学者对《仪礼》一书的书名、作者、成书年代、篇章、内容等问题,有过许多讨论。比如,围绕着《仪礼》是否为周公所作,人们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贾公彦认为此乃“周公摄政大(太)平之书”(32)郑玄注、贾公彦疏,王辉整理:《仪礼注疏》卷一《仪礼疏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页。,魏了翁、熊朋来等沿袭此说,后者甚至认为《仪礼》“乃周公制作之仅存者”(33)熊朋来:《经说》卷五《仪礼礼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4册,第308页。;乐史则认为“《仪礼》有可疑者五”, 其中之一即“非周公之书”(34)章如愚:《群书考索》前集卷九《经史门·仪礼》,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77页。;张淳也说:“若曰周公作之,则非淳之所知也。”(35)张淳:《仪礼识误》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册,第3页。十分有意思的是,阅读《仪礼》的观感,这一出于不同个体对于文字符号的理解,本应具有多样性与丰富性,士人们却给出了一致的说法。很多学者指出,《仪礼》难读、罕读。韩愈曰:“余尝苦《仪礼》难读。”(36)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读仪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3页。欧阳修讲:“平生何尝读《仪礼》。”(37)王应麟著,栾保群等校点:《困学纪闻(全校本)》卷五《仪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88页。朱熹也说:“《仪礼》人所罕读。”(38)《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记永嘉仪礼误字》,《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90页。陈汶《仪礼集释序》中讲:“自汉以来,礼日益坏……所谓颂貌威仪之事,仅存此书,世亦莫有知者……其节目之繁,文义之密,骤而读之,未易晓解,甚或不能以句。”(39)李如圭:《仪礼集释》卷首陈汶《仪礼集释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册,第35页。到了清代,四库馆臣在述三礼时说:“古称议礼如聚讼。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40)《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九《经部·礼类一》,第149页。
当一本难读、罕读的经书列于科举考试科目,尤其是制度设计存在着选择可能时,应考诸生遇难而退的现象就较为常见了。唐开元八年(720),有人上言:
今明经所习, 务在出身, 咸以《礼记》文少, 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 《仪礼》庄敬之楷模, 《公羊》《穀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41)郑樵:《通志》卷五八《选举略一·历代制》,中华书局,1987年,第708页。
唐代明经考试中,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通二经者,大、小经各一,或中经二。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通之。(42)《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第1159、1160页。对于参加科举的考生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唐人说:“务在出身。”因此,在考试配选中,作为大经的《礼记》因其文少,“人皆竞读”;作为中经的《周礼》《仪礼》与作为小经的《公羊》《穀梁》却在国子监与州县学校中“独学无友”,此处,所谓“四经殆绝”是对举子择选经书的描述。
唐人讲:“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宋人也说:“举子之取名第,止问得失而已”,既问得失,则“去难就易”、“趋时所尚”就成为必然的选择。(43)毕仲游:《西台集》卷一《理会科场奏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2册,第4页。熙宁贡举改革,进士令各占治一经,不久之后,有人就抱怨说,举子之中“为《书》者不为《诗》,为《诗》者不为《易》,为《易》者不为《礼》,为《礼》者不为《春秋》,是亦知一经而四经不知也”(44)《西台集》卷一《理会科场奏状》,第6页。。南宋时,诗赋、经义分科,诗赋不试经义,因此,学子竞习诗赋,习经义者较少。绍兴二十六年(1156),高宗就此提出:“举人多习诗赋,习经义者绝少。更数年之后,恐经学遂废。当议处此。”(45)④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三一,第5333页。同年,王晞亮也上言:“国家取士,词赋之科,与经义并行。比学者去难就易,竞习词赋,罕有治经。至于《周礼》一经,乃绝无有。”(46)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五,绍兴二十六年十一月癸巳条,中华书局,2013年,第3358页。
在“去难就易”的心态下,《周礼》渐绝,《仪礼》更无踪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朝廷有意调整经义与诗赋的取士数额,“稍损诗赋而优经义”④。不过,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庆元元年(1195),朱熹提出了分年考试的主张,他说:
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然欲其一旦而尽通,则其势将有所不能,而卒至于不行。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则亦若无甚难者。故今欲以《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之《礼》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为当世之用矣。(47)⑧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九《学校贡举私议》,《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59-3360、3360页。
在朱熹看来,为当世所用之士,应是“无不通之经”,但当下学者治经“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如此,便不能尽通天下之事与天下之理,而分年考试,则让举子有充分学习的时间,“三年之间,专心去看得一书”(48)《朱子语类》卷一百九《朱子六·论取士》,第2699页。,如此一来,解决经学寖废,“亦若无甚难者”。在这份“议未上闻,而天下诵之”(49)《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考五》,第301页。的《学校贡举私议》中,朱熹也指出了科举考试中经学的状况,他讲:
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主司不惟不知其缪,乃反以为工而置之高等。习以成风,转相祖述,慢侮圣言,日以益甚。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不可坐视而不之正也。⑧
科举应试之下的经学,在举子与主司的有意推动下,不仅没有带来学术的繁盛,反而成为“经学之贼”,朱熹所谓“不可坐视而不之正”,亦非出于一时之愤慨,他自己便起而行之。而“朱子于经学中,于《礼》特所重视”(50)钱穆:《朱子新学案》第四册《朱子之礼学》,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19页。。因此,将“朱子治经重礼”与朱熹“废罢《仪礼》”这一叙事结合起来观察,或许叙述者背后的意图才能渐次立体起来。
四、叙述者的立场:罢《仪礼》与废《春秋》
上文从宋代科举制度中关于考试用书的规定以及举子对通经之书的选择两个层面略补从“废罢《仪礼》”到“《仪礼》卒废”的叙事过程,在对熙宁四年贡举改制的解读中,叙述者的立场与态度十分重要,它决定了在书写过去的事实时,叙述者所密切关注的当下与其中的诉求。早在朱熹“废罢《仪礼》”的叙事之前,曾有人将熙宁诏令释读为“废《春秋》”,彰显这一提法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胡安国,他讲:
近世推隆王氏新说,按为国是,独于《春秋》,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读,断国论者无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适。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乱华,莫之遏也。噫!至此极矣。(51)胡安国:《春秋胡氏传·春秋传序》,《四部丛刊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b页。
胡安国从意义上去解读王安石不立《春秋》的后果,《宋史》本传在追溯胡安国致力于《春秋》的立意时,也是从《春秋》作为经典的意义上去强调胡安国的学术关怀,曰:
自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官,安国谓:“先圣手所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故潜心是书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52)《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传》,第12916页。
除了胡安国外,罗汝楫也因《春秋》学而得到皇帝的褒赞,称:“自王安石废《春秋》学,圣人之旨寖(以)不明。近日(世)得其要者,惟胡安国与卿耳。”(53)洪适:《盘洲文集》卷七七《罗尚书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45册,第507页;《宋史》卷三八十《罗汝楫传》,第11724页。
与“废罢《仪礼》”不同的是,废《春秋》的叙事结构并没有展开。在时间轴线上,熙宁贡举改制中不列《春秋》,元祐时,《春秋》重新列入举子的习经范畴。因此,人们叙述“王安石废《春秋》”时,往往作为一个片段来处理。比如,与上引胡安国的例子一样,许多人以此作为追溯学者致力于《春秋》的写作缘起。楼钥为高闶《春秋集注》所写的序中称:“自顷王荆公废《春秋》之学,公独耽玩遗经……其说粹然一出于正。”(54)楼钥:《攻媿集》卷五一《息斋春秋集注序》,《四部丛刊初编》,第5b页。此外,当人们将“废《春秋》”一事与《春秋》学同列时,亦非用以指涉《春秋》学寖废的起点。绍兴十年(1140),汪藻为张根《春秋指南》作序曰:
本朝自熙宁以来,学者废《春秋》不用,数十年间,笃学而好之者,盖不为无人,然一时章分句析之学胜,故虽《春秋》亦穿凿破碎而不见圣人之浑全。(55)汪藻:《浮溪文粹》卷八《吴园先生春秋指南序》,《宋集珍本丛刊》第34册,第414页。
这里,汪藻虽以“废《春秋》”一事展开叙述,但所指的是《春秋》学研究在不同阶段学术取径的不同。
除了片断处理外,“王安石废《春秋》”亦没有获得较为一致的叙事主题,反而意见纷纭。上引胡安国所论,是从经典不可废的角度去讲述王安石废《春秋》之失,胡寅则从尊经的角度接续这一说法:“自王安石废黜《春秋》,天下学士不知尊尚,一旦乱臣贼子接迹乎四海。”(56)胡寅撰,容肇祖点校:《斐然集》卷十一《论遣使札子》,中华书局,1993年,第229页;亦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七《炎兴下帙六十七》,绍兴五年五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207页。还有人试图寻找王安石废《春秋》背后的故事,道:
王荆公欲释《春秋》以行于天下,而莘老之书已出,一见而有惎心,自知不复能出其右,遂诋圣经而废之曰此“断烂朝报”也,不列于学官,不用于贡举,储积有年。(57)周麟之:《海陵集》卷二二《跋先君讲春秋序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2册,第174页。
“莘老之书”系指孙觉《春秋经解》,在这一叙述中,废《春秋》似乎皆出于王安石的一时嫉妒,而他以“断烂朝报”毁诋《春秋》一事,虽有苏辙、胡安国等人特别指出,认为此种毁诋“使天下之士不得复学”(58)苏辙:《春秋集解》卷首《颍滨先生春秋集解引》,《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废之不列于学官”(59)《斐然集》卷二五《先公行状》,第552页。,但后来亦有人为之辩说:“和静曰:‘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和静去介甫未远,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之语为荆公之罪,亦冤甚矣。”(60)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八《学记》,《宋集珍本丛刊》第83册,第628页。枝蔓的猜测、假托以及辩说使得“废《春秋》”的叙事主旨不明,线索纷纭。
朱熹使用与“王安石废《春秋》”,“不立学官”等几乎相同的遣词来构建“废罢《仪礼》”的叙事,其目标并非是要在“废《春秋》”之上再叠加一个可供考察的历史证据。“废罢《仪礼》”与其说是对历史事实的确认,不如说是对知识体系与知识传承的反思。在朱熹看来,熙宁改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变乱旧制”,废罢诸科,以及进士“令各占治一经”的做法,不仅割裂了原有的知识体系,而且真正将科举变成了蕃篱知识传承的工具。
比如,与礼学密切相关的学究科,他曾细讲该科的沿革,说:
此科即唐之明经是也。进士科则试文字,学究科但试墨义。有才思者多去习进士科,有记性者则应学究科。凡试一大经者,兼一小经。每段举一句,令写上下文,以通不通为去取。应者多是齐鲁河朔间人,只务熟读,和注文也记得,故当时有“董五经”“黄二传”之称。但未必晓文义,正如和尚转经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礼,亦不与进士等。进士入试之日,主文则设案焚香,垂帘讲拜。至学究,则彻幕以防传义,其法极严,有渴至饮砚水而黔其口者!当时传以为笑。欧公亦有诗云:“焚香礼进士,彻幕待诸生。”其取厌薄如此,荆公所以恶而罢之。但自此科一罢之后,人多不肯去读书。(61)《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第3079-3080页。
朱熹从学究科的历史脉络中去呈现该科目的考试形式、弊端以及针对该科目的各种嘲笑,他认为王安石废学究科,虽有归因,但是,王安石所废的不只是人们的厌薄,同时废的还有最基本的读书方法。他在对比明经科与王安石所编的科举考试用书时讲:
旧来有明经科,便有人去读这般书,注疏都读过。自王介甫新经出,废明经学究科,人更不读书。卒有礼文之变,更无人晓得,为害不细!如今秀才,和那本经也有不看底。朝廷更要将经义、赋、论、策颁行印下教人在。(62)《朱子语类》卷八五《礼二·仪礼》,第2200页。
在朱熹看来,王安石新经作为统编教材以“一道德,同风俗”,使学者有所据守,是值得肯定的。他讲:
王介甫《三经义》固非圣人意,然犹使学者知所统一……当时神宗令介甫造《三经义》,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学不正,不足以发明圣意为可惜耳。(63)《朱子语类》卷一百九《朱子六·论取士》,第2694页。
熙宁改制打乱经学的知识体系,追究之下,皆因主持这场改制的王安石本人的学识不足以让他承担起这样的改制。朱熹在很多场合评价王安石时讲:“荆公德行,学则非”,“学皆不正”,认为以“荆公学术之缪,见识之差”这一评语来论之,是的当之辞。(64)《朱子语类》卷一三十《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第3097、3099、3100页。同样,对于赞美王安石学问的说法,他则一一辩驳:
陈后山说,人为荆公学,唤作“转般仓,模画手。致无嬴余,但有亏欠”!东坡云:“荆公之学,未尝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己。”此皆说得未是。若荆公之学是,使人人同己,俱入于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说“未尝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说话!若使弥望者黍稷,都无稂莠,亦何不可?只为荆公之学自有未是处耳。(65)《朱子语类》卷一三十《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第3099-3100页。
“道德一于上”本就是王安石贡举改革的要旨,因此,“人人同己,俱入于是”、“使弥望皆黍稷,都无稂莠”,正是“一道德”的呈现。而苏轼等人脱离这一宗旨,以“不合要人同己”来论王安石之非,以“荆公之学,未尝不善”来虚化问题,在朱熹看来,皆“说得未是”。荆公之学“未尝不善”,而是自有“未是处”。《朱子语类》记载:
先生论荆公之学所以差者,以其见道理不透彻。因云:“洞视千古,无有见道理不透彻,而所说所行不差者。但无力量做得来,半上落下底,则其害浅。如庸医不识病,只胡乱下那没紧要底药,便不至于杀人。若荆公辈,他硬见从那一边去,则如不识病证,而便下大黄、附子底药,便至于杀人。”(66)《朱子语类》卷一三十《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第3097-3098页。
朱熹以庸医不识病而下药作为比喻,来描述王安石之学用于社会变革之时与之相类似的特征:“正如医者治病,其心岂不欲活人?却将砒霜与人吃。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67)《朱子语类》卷一三十《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第3098页。王安石以《周礼》作为改革之理据,但事实上,“他却将《周礼》来卖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国强兵,然后行礼义;不知未富强,人才风俗已先坏了”(68)《朱子语类》卷七一《易七·无妄》,第1799页。。在科举考试中,他以《礼记》作为重要经书,但是熙宁元年(1068),当神宗要求王安石在经筵讲《礼记》时,王安石进言说:“《礼记》多驳杂,不如讲《尚书》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闻也”,于是,神宗从王安石所言,罢讲《礼记》。(69)朱弁撰,孔凡礼点校:《曲洧旧闻》卷九《神宗从王介甫言罢讲礼记》,中华书局,2002年,第208页。于《仪礼》上,王安石同样无识见,朱熹曾评说:“王介甫废了《仪礼》,取《礼记》,某以此知其无识。”(70)《朱子语类》卷八三《春秋·经》,第2176页。在朱熹看来,王安石的学术与见识决定了他在社会变革中的格局,他在解读熙宁诏令时,始终以王安石之学作为言说的对象,以展开其个人的学术思考。
总之,“废罢《仪礼》”这一论题,就事实范畴而言,朱熹对本朝制度的有意解读与历史事实颇有不相契合之处,不过,若将之当作是朱熹对事实进行理解和描述而得出的结论,借由废罢《仪礼》的叙事,朱熹所要指明的是,熙宁贡举改革在事实上割裂了经学的知识体系,也是礼学不明的主要根源。在科举成为“经学之贼”,礼学传承出现断层、礼官却不知礼的多种语境之中,朱熹在评说士大夫所书写的家礼礼书时,倡导“《仪礼》为本”的原则,希望借由“家礼”这一传统形式,以《仪礼》作为知识框架来书写新的社会秩序。如此一来, 以“废罢《仪礼》”为破题,以“《仪礼》为本”为立意,由破而立,构筑出朱熹治礼“以社会风教实际应用为主”(71)《朱子新学案》第四册《朱子之礼学》,第120页。的关怀。至于“《仪礼》为本”的话语如何生成、朱熹怎样重塑《仪礼》的礼典地位,那又是另一个知识考古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