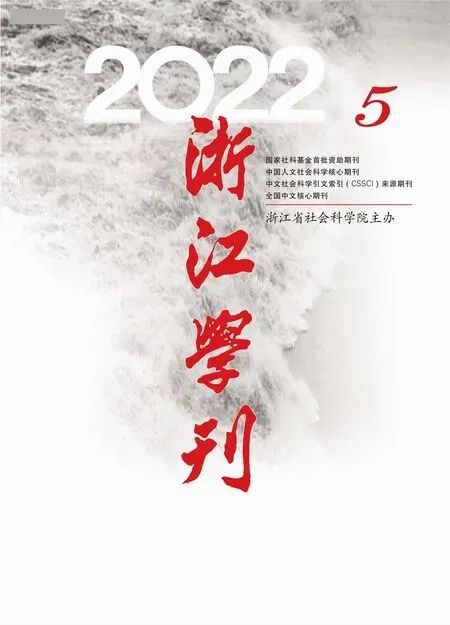论艾米莉·狄金森的“家园”诗学
2022-11-19向玲玲
向玲玲
提要:狄金森以矛盾歧义的方式谈论“尘世天堂”“死亡家园”“天国异乡”,以超前的现代意识应对宗教危机与父权统治,建构起一个灵魂自主自治的“诗歌家园”和开放的“家园”诗学。其中“尘世天堂”观体现了19世纪美国世俗思想的萌芽,即从神性永恒到世俗永恒的蜕变;“天国异乡”观揭示了她对基督教“天国家园”观的继承、反讽与解构;“死亡家园”的诗意构建,被其诗歌叙事揭示为“不可能的故事世界”。这些“家园”在活的语言中诞生,构成了无限可能性的诗歌家园,印证了狄金森“家园”诗学的开放本质。
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美国诗歌的奠基人之一,被称为“阿默斯特的修女”。她从二三十岁开始严格意义上的“隐居”,即不再离家、不再见客,也拒绝发表。但另一方面,她与亲友、包括文朋诗友保持着频繁而炽热的书信联系,并在长达三十年的创作期内写作了近1800首诗歌——其中约800首由本人誊抄、缝制成40册诗歌小辑(fascicles)(1)Cristanne Miller, Emily Dickinson’s Poems: As She Preserved Them,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31-413.,还有一些“诗信”,将她亦诗亦信的文字与自己栽培的鲜花一起,寄赠给众多亲友——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私发表”。
她以“家园”为线索,将尘世、死亡、天国三种语境串联起来,在宗教危机时代重建了某种意义的延续性。但这些“家园”诗歌神秘、晦涩、含混、歧义,充满了悬而未决、无可化解的矛盾冲突。19世纪新英格兰宗教、社会转折时期的多重观念、立场被并置在一起,彼此对话、对抗、沉默。从神学到世俗的“家园”理念被一一辩驳,却未得出一个调停或解决的方案。各种“家园”构建,如“尘世天堂”、“死亡家园”、“天国异乡”,也各执一端,不能满足理论闭环的结构需要,反倒形成一种以分裂与对抗,而非协调或妥协为特征的“家园”诗学。
一、狄金森家园诗歌的创作背景
狄金森家园诗歌的产生,既有时代的烙印,也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她的家乡新英格兰,是19世纪美国宗教“大觉醒”运动的源头与中心。身边亲友纷纷皈依,踏上回归“家园”之路,孤独的诗人在深受冲击与保持诚实之间挣扎,寻觅永恒的家园。正如她对自己创作动机的描述:“我有一种恐惧——自九月以来——无法告诉别人——所以我唱歌,如同男孩经过墓地——因为我害怕”(L261)(2)文中夹注(L261),表示引文来自约翰逊编辑的《艾米莉·狄金森书信集》(Thomas Johnson, 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中第261封信。下同此例。“我依靠恐惧生活—/……仿佛那是—灵魂上的马刺—/一种恐惧会敦促它前往/有绝望在挑衅的地方”(J770, F498)(3)文中夹注(J770, F498),表示引文来自约翰逊编辑的《艾米莉·狄金森诗集》(Thomas Johnson, 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MA: The Belknap P of Harvard UP, 1955)第770首诗、富兰克林编辑的《艾米莉·狄金森诗集》(R. W. Franklin, 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MA: The Belknap P of Harvard UP, 1998)第498首诗。狄金森诗歌没有标题,故以编辑加注的诗歌编号作为标识。下同此例。这里,狄金森用“terror”、“dread”、“fear”三个词反复描绘她的恐惧,“仿佛灵魂上的马刺”不时来袭,使灵魂带着新鲜的伤口而处于敏锐易感、寝食难安的创作状态,不会堕入麻木和迟钝。
国内外学者对狄金森的家园诗歌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总结了至少五个层面的“家园”:(1)诗人自我幽禁的现实的家园,即“父亲的家宅”;(4)Roger Lundin, Emily Dickinson and the Art of Belief, MI: William B. Eerdmans, 1998, pp.63-64.(2)由神圣化的家宅、私家小花园和大自然组成的“尘世伊甸园”;(5)Wendy Martin,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Emily Dickins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pp.86-96.(3)借以摆脱尘世煎熬的“死亡家园”;(6)Joan Kirkby, “Death and Immortality,” in Eliza Richards ed., Emily Dickinson in Context,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66-167.(4)拒绝皈依、无缘于“上帝选民”身份的诗人渴望而否认的“天国家园”;(7)Jane Donahue Eberwein, “Is Immortality True? Salvaging Faith in an Age of Uphearals,” in Vivian R. Pollak ed. A Historical Guide to Emily Dickinson,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76, 79.(5)使诗人实现灵魂独立与自治的“诗歌家园”或“语言王国”。(8)黄超楠:《艾米莉·迪金森:诗歌意象群及原型意象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7-108页。狄金森描绘了从尘世、死亡、天国到语言本体意义上的家园,揭示了她强烈的家园意识。但同时,这些家园诗歌中又充斥着“无家可归”或“此家非家”的强烈感受,使每一个家园建构都变成矛盾的、可疑的。
首先,“尘世天堂”是一个“家”与“非家”的矛盾体,因为它既是神圣的庇护所,也是权力结构、代际创伤、身份障碍等的代名词。在19世纪的美国从神学统治向世俗社会转变的历史语境中,狄金森以“尘世天堂”的世俗永恒取代玄学、神学的先验本体、真实家园,有其时代的特色。格里菲斯认为,狄金森长期火山喷发式不竭的诗歌创作源于“某种形而上的困境”,即由于宗教不确信而引起的恐慌与意义系统的崩塌,如上帝可能不存在、人类经历可能不再具有连续性和意义等形而上的恐惧。(9)Clark Griffith, The Long Shadow: Emily Dickinson’s Tragic Poetr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75-81.这种恐惧也是时代的困境。
狄金森“尘世天堂”的原型,是一个典型的由“男性权威”与“女性美德”构成的“父亲的家”(J824, F796),其中母亲身份、女性力量的缺失,以及代际身份认同的错位,使她时常感到“在家而无家可归”(J1573, F1603)。父亲在求偶阶段就已向未来伴侣再三申明过自己对“性别美德”的诉求,且如愿以偿地娶回一位安静、顺从、勤劳、节俭的妻子:她拥有家庭妇女的所有美德,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从未“篡夺他的发言权”,只是以独特的方式保留了自己的所有意见,如沉默、不回信、不沟通、不行动、长期反复因病卧床、“无力、不愿或拒绝离开她的椅子”、经丈夫允许后离家疗养等。(10)阿尔弗雷德·哈贝格:《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艾米莉·狄金森传》,王柏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38、282页。正如狄金森在致友人希金森的信中所说:“您能告诉我家是什么吗”,“我从没有过母亲。我以为,母亲是你遇到麻烦时匆匆奔向的人。”(L342b)在勇猛的父亲与无力的母亲之间,诗人倾向于认同前者。这种身份认同的错位与不可实现,带来的是匮乏、卑微、自我否认与无家可归的真实感受,以及敏感、凌厉、倔强的挑衅、矛盾的对抗,正如狄金森诗歌中频繁采用的孩童面具,借不谙世事的孩童面具说出令人绝望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也拒绝了社会意义上的成长与成年女性的身份。
这种矛盾冲突,既与诗人的个性特质有关,也来自文化的冲突。当“美国精神的先知”爱默生在《论自立》中用man(男人)指称“人”,在《论诗人》中用he(他)指称“诗人”,在《超灵》中说“对于接受新的真理,所有的人(all men)都会感到一阵激动”时,我们无法判断他是在轻巧地沿用古老的性别化词汇,还是在严肃地执行文化上的“限制继承权”。(11)Ralph Waldo Emerson, Emerson: Essays and Lectures, Joel Porte ed., NY: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83, p.392.但对狄金森来说,超验主义的“God-in-him”(“上帝在他心中”)新神学,无疑再次提醒了她作为“一个不能继承公爵头衔的女人”(12)萨克文·伯科维奇:《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李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499页。,即被文化与社会权力资源排除在外的女性身份,所以也必将迎来她的拆解与反击。
二、“天国异乡”与“尘世天堂”:永恒的失落与蜕变
正如17世纪清教经典中所训诫的,“你要经常思索,仔细思索‘永恒’这个词”,(13)里查德·巴克斯特:《圣徒永恒的安息》,许一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7-48页。狄金森一生都在沉思永恒,并试图在信仰危机时代为去象征化、去神圣化、赤裸裸的生命与死亡重新赋义,以实现某种意义的延续性。“家园”兼具时空物理特征与超越性象征意义,正是她借以实现这种连续性的重要媒介之一,也成为贯穿其诗歌的一个核心词。
(一)“天国异乡”:神性永恒的失落
狄金森诗歌中有对基督教“天国家园”叙事传统的继承。例如,对死亡的淡然、对“回家”的欢欣鼓舞:“旅人迈步回家/鞋也欢腾—”(J7,F16)又如,对上帝的爱、天国的空间物理特性的呼应:“我希望天上的父/会抱起他的小女孩—/老式—顽皮—不一而足—/翻过那‘珍珠’的台阶。”(J70,F117)诗中,第一人称叙述者称神为“天上的父”,珍珠台阶意象则呼应《启示录》(第21章第21节)对天国“珍珠门”的描绘,各要素基本符合传统“天国家园”叙事的特点。
但更多的是她对基督教“天国家园”观的戏仿、反讽与解构,即以模仿者的身份隐藏在话语裂缝之间,以一本正经说荒唐事的仿文本博得读者会心一笑,从而以看似柔弱、实则具有元叙述性质的方式解构了《圣经》文本中描绘的天国家园。
1.对“天国家园”空间矛盾性的戏仿与反讽
狄金森曾在诗歌中模仿过以空间或场所形式呈现的传统天国意象,甚至半真半假地将天国描绘为“一座设备完善的维多利亚家居式上帝的宫殿”(14)⑤ Cynthia Griffin Wolff, Emily Dickinson, Cambridge: Perseus Publishing, 1988, pp.323,337.,但这种戏谑的滑稽模仿很快让位于“严肃戏仿”。如:“撤退—没有希望—/身后—一条封死的路线—/永恒的白旗—在前—/上帝—在每扇门边—”(J615,F453)全诗以看似传统的方式描绘了“天路之旅”的种种磨难,并在结尾处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意象。沃尔夫注意到这一意象对空间维度的摧毁:“上帝在前方这座十二门之城的每一扇门边,他的存在的威慑就是无可逃避的终局。该诗的超现实主义地理学准确无误地排除了天国作为一个‘地方’的可能性。”⑤情绪不明、意图不明的上帝“候在”或“挡在”每一扇门边,也隐含了神人对峙的危机。
“天国”被称为“家园”,却不具备“家园”的空间结构,这是狄金森不能接受的。她曾强调“家”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他们说‘家是心所在的地方。’我认为它是房子以及所有附属设施所在的地方。”(L182)具体说,就是一个有结构、有形式、有边界的空间,向内可提供封闭的场所,向外可打开沟通的路径,才能为“我”在混沌无边的世界中提供一个界限清晰的、稳定的所在。“天国”不具备这样的空间特征,无法令人产生“居留感”,因此不能被称为“家”或“家园”。
2.对“天国家园”故事中的人物身份与关系的戏仿与反讽
“天国家园”观借用了世俗“家”的概念,狄金森就从“家”的伦理、情感、生活痕迹等结构要素出发,指出这一概念的矛盾与荒谬。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上帝是一位远方的—高贵恋人—”(J357,F615)一诗对“圣婚”隐喻的戏仿与反讽。它通过模仿朗费罗的叙事诗《迈尔斯·斯坦狄什求婚记》中的人物与情节——女子爱上求婚的使者而非求婚者——反讽了基督教“圣婚”隐喻中含混歧义的人物身份、关系及其背后的“三位一体”教义。从神圣角度看,质疑“圣婚的新郎是父亲还是儿子”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渎神的,而狄金森提出这个疑问,无疑受到了盛行于19世纪新英格兰知识分子中的“一神论”思想(只有一个神即上帝,耶稣与人是兄弟关系,是人间“领袖”和“楷模”)的影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了“圣婚”与“三位一体”隐喻中的文字游戏与伦理逻辑的困境。
3.对天国故事中去身体化的人物特性,即“灵的肉体”概念的戏仿与反讽
在狄金森看来,“灵的肉体”实则是对个体性、肉身性的否定。所谓“灵的肉体”,是与“血气的身体”相对的复活永生者的身体(《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42-44节),其特征是轻盈的、纯粹的、“更容易、更轻巧地服从灵魂并满足保证其不朽的上帝的意志。”(15)黄裕生:《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神圣文本复活语境中的灵性身体,往往忽略了感官、肢体、部位等个体的、肉身的特征,只保留了作为身份象征的面孔、名字、年龄等抽象特征,或仅限于集体意义上的言行。
狄金森通过叙述者或主人公的言、思、行、甚至是戏剧性的表演,来揭露这种身体观的荒谬性。如:“我想在我被‘宽恕’的时候—/我的形体该会怎样升起—”(J237,F252)诗中,叙述者“百思不得其解”:“灵的肉体”到底是不是身体?在被宽恕而升天的时候,“我的形体该会怎样升起”?无处问询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只能以“科学实验”精神对自己的身、心各组成部分一一检测、探索,试图给出答案。又如:“我用双手摸我的生命/看看它是否在那里—”(J351,F357)这首诗歌,以夸张戏仿的方式将西方传统心身二分法的灵肉割裂本质推演到了极致:“我”将自己“新生命”的每一部分单独取出、分别观测甚至计量,正如科学家对待自己的实验对象,最终使生命被割裂成可视的、可度量的物理学意义上的碎片。
4.对基督教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基督(徒)的得胜”话语的戏仿与反讽
所谓“得胜”,指虔诚的基督徒“经由基督的胜利而得胜”,即基督战胜撒旦及其“堕落世界”,“属耶稣的”基督徒则因此战胜死亡、涤清罪孽、获得永生。“得胜”话语遍布经书各处,给予信众莫大的安慰和鼓励。但换一个角度看,激动人心的“得胜”话语背面,却是被杀伐者的悲惨命运。
经启蒙理性与浪漫主义熏陶的狄金森,无法接受表面辉煌的“得胜”话语背后的残忍“真相”。而使她向“思想殉道者”行列更迈进一步的是,她不仅拒绝“得胜”话语,而且选择了站在话语背面的“被战胜者”一方,作为“失败者”发声:“今天—我命中注定被战胜—(J639,F704)在这首“失败者之歌”中,主人公坦然接受了自己选择的命运,并以一种简陋、随意的措辞自我调侃着:“我”这个被战胜者“纸糊的运气”当然不能和铠甲般结实、镀金般辉煌的“胜利”相比,“没什么凯歌”、“少了点钟声”。与《启示录》中无所不在的、更高处的主语“我”比起来,这首诗中只剩下一个宾语的、自下而上的“声音”——通过“喇叭们向空中宣告它”——虽然远离话语中心,却不容小觑,因为它不惜付出牺牲的代价,也不愿接受“得胜”话语的威压:“如果要得胜,那还不如/死—更满足—”
(二)“尘世天堂”:从神性永恒到世俗永恒的蜕变
“想家”或“乡愁”是狄金森诗歌中的一个高频词,也是一种与西方玄学、神学传统背道而驰的“逆向乡愁”。众所周知,从形而上学到基督教传统秉承的是对先验本体的“怀乡”情结,即人们怀着“乡愁”在这个转瞬即逝、虚幻不实的现象世界流浪,等待重返纯粹、不朽、真正的家园——“理念世界”或“天国家园”。狄金森以孩童面具与天真口吻,将这种形而上的追求称为“最疯狂的梦”或“对那矢志不渝蜂蜜的乡愁”。她在诗中以诱人的蜂蜜喻天国理念,以“引诱者”蜜蜂喻上帝或信仰本身,替人类这个“天真的孩子”发出呼喊:“啊,酿造这珍奇品种的/蜜蜂不要走!”(J319, F304)可以说,她对“天国家园”理念颠覆得多彻底,痛惜就有多深刻。
狄金森在诗中描绘了一个“尘世天堂”。在这里,家是乐园、天堂、坚不可摧的诺亚方舟,自己亲手培育的花园就是鸟语花香的伊甸园。例如:“在家里—在乐园”(J1335, F1361)“人间是天堂的事实—/不管天堂是不是天堂”(J1408, F1435)“洪水掀翻了天—/却饶了父亲的家—”(J824, F796)她赋予花鸟草虫各种象征意义,如以蜂蝶喻情人、上帝,以白雪喻无差别的死亡,以球茎植物的蛰伏与萌芽喻生命的循环、重生等,以致她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感慨;“假如玫瑰花没有谢,冰霜不曾来,我叫不醒的人没有倒在这儿或那儿,那就没有必要在人间天堂之外再来一个天堂——假如上帝今年夏天来过这儿,看见了我们所看见的景象—我想他会认为他的乐园是多余的。”(L185)
因此,在她的“乡愁”诗歌中,神圣文本中的“天国家园”就变成了疏离、陌生的“异乡”,清教先辈的天路旅思则被置换成了逝者、永生者对“尘世故园”的思念。主人公在死后会想家(J935, F1066),在“地下村镇”等待复活时会想家(J529, F582),升入天国后会在“永恒以后思念家园”(J900, F1074),在对天国这个“新家”充满质疑,或对自身的存在产生怀疑时,只能用对“老家”的怀想来宽慰自己:“我告诉自己,‘鼓起勇气,朋友—/那—是从前的一段时间—/但我们可以学会喜欢天堂,/就像对我们的故园!’”(J351,F357)
这种看似背道而驰的“逆向乡愁”叙事,并非对西方传统“乡愁”情结的单纯否定,而是一种自觉而复杂、清醒而痛苦的现代意识的体现。这也正呼应了博尔赫斯在《永恒史》中关于神学永恒崩塌后人类不得不寻求“次类永恒”,如世俗永恒、回忆永恒等“没有上帝的可怜的永恒,而且没有其他拥有者,没有原型”的替代品的哀叹。(16)博尔赫斯:《永恒史》,刘京胜、屠孟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24页。
三、“地下村镇”与“诗歌圣殿”:词语的可能性之旅
神性永恒已失落,“尘世天堂”又时常令狄金森感到“在家而无家可归”。但她还有“词汇”这个“唯一的伙伴”(L261):这些陈旧的、沉睡的、甚至是死的词语,在成为狄金森极端隐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同时,也被一次次唤醒,并在种种突破常规的语言实验中获得了自己丰富、含混、变幻的生命。
(一)“地下村镇”:建构一个“不可能的故事世界”
狄金创作了一组独特的墓园主题诗歌,并塑造了一个比“尘世天堂”更为独特的“死亡家园”——叙述者亲昵地将墓园地下世界称为“地下村庄”“古怪的镇子”“地下都城”,墓园居民也被视作生者“邻村”、“邻镇”的“乡亲”。也就是说,她模仿人间社区的方式描绘了一个“仿家园”及那里“乡亲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她又以反常的、非自然的叙述方式,即“在物理上、逻辑上、记忆上或心理上不可能的叙述”(17)J. Alber, et al., “Unnatural Narratives, Unnatural Narratology: Beyond Mimetic Models,” Narrative, Vol.18, No.2, 2010, pp.113-136.颠覆或消解了自己塑造的故事世界,使其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故事世界”。
1.非自然的、不可能的叙述者
这些诗歌中最常见的叙述者有两类:一类是从故事内部讲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即逝者或颇富哥特色彩的“墓室中的未死者”。但这类叙述者的“自述”不仅揭示了故事世界的非自然属性,也容易造成叙述话语与故事之间的矛盾。例如,“太阳落呀—落—还在落”(J692,F715)一诗中“叙述自我”与“故事自我”之间的断裂:叙述者“我”先以否定语气勾勒出一幅悖论式的、非自然的故事场景——太阳落山,但庄户里依然是正午笼罩;暮色降临,但露水不在草上,只在“我”的额上、脸上——建构起一个不可能的村庄或家园故事背景。接下来,在对“我”的种种生命体征,如对露珠的感知、疲惫、知觉等进行描述之后,“叙述自我”突然跳出故事的情境,对受叙的“我”发出疑问:“但为什么—我自己/对貌似我的这位—发不出多大声音?”叙述者改用更严格的Myself来指称自己,而用my seeming来称呼故事中所描述的我。明显,这里的叙述自我与故事自我发生了断裂:叙述自我突然超越于故事中的“我”之外,以俯瞰的视角审视着自己所构建的故事世界及其主人公,也顺带把沉浸于“死亡家园”情境中的读者一起叫醒,跳出了这个故事。
第二类,是墓园外的旁观者。这类叙述者可能是第三人称单数,也可能是特殊的第二人称叙述者,甚至可能是一种极端化的叙述者,即无实体的“问话者”或“对话者”,只以声音出现——多重叙述声音交织在一起,出现一个叙述声音对另一个声音的“拷问”,从而使诗歌的叙述话语溢出故事的边界而具有了转叙的功能。例如,下诗中无实体的“问话者”A与“审视者”B的声音交织:“它死了—找到它—/声音以外—视线以外—/‘快乐吗’?哪个更明智—/你,还是风?/‘有意识吗’?你不想问问—/低洼的地面?//‘想家吗’?很多人见过它—/即便通过它们—这/无法证明—/它们自己—哑口无言—”(J417,F434)”“问话者”A热切地想要了解逝者是否还有感知:“快乐吗?”“有意识吗?”“想家吗?”紧随A的每个好奇之问后,是“审视者”B的冷嘲热讽:“哪个更明智—/ 你,还是风?”“你不想这样问—/ 低洼的地面?”直到A执着地问出最后一个问题“想家吗?”,B不再讥讽,而是沉郁地表示:这个问题不会被提供任何证词,因为那些见过“它”的证人们,也已成为缄默不能言的“它们”。与沉浸在故事世界中的“问话者”A不同,“审视者”B采取的是外部的视角,即从现实世界的角度审视故事世界,但其声音却出现在故事世界的情节中,与沉浸者A发生了对话,从而模糊了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
2.非自然的、不可能的人物
“死亡家园”故事世界的人物,往往以一种悖论的形式出现:有人类的语言、思维和感知,却没有人类的身体性;同时,不具备足够身体性的“人物”,却被置于“家园”的物理结构中。狄金森为此刻画了两类特殊的身体意象:一、与墓穴环境融为一体的金石身体意象。例如,“大理石的脚”(J510,F355)、“花岗岩般的嘴唇”(J182,F210)、“钢铁的耳朵”(J300,F191)、“钢铁的筋肉”(J666,F752)等等。金石材料当时常被用作特殊身份者的墓穴或棺椁材料,且与逝者身体具有一定的物理共性,因此金石身体意象本身并不显得突兀,但以无生命的身体作为认知、思想的载体,却是反常的、非自然的。二、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身体意象。例如,“我活着—我猜—/我手上的枝杈/长满了牵牛花—”(J470,F605)一诗的开篇,叙述者与自然环境的边界消失,处于一种物我不分的混沌状态。但指尖被刺出的一滴鲜血,却使“我”的身体被触发、意识突然涌现,开始寻求自己生命的证据:“如果我把一面镜子/对在嘴前—它就使镜子模糊一片—/医生以此—证明还有呼吸—”(J470,F605)这无疑是一个悖逆常理的故事,也以非自然的叙述揭示了诗人对身体性的强调。
3.非自然的、不可能的事件与场景
人物的非自然性,导致其行动与事件的非自然性。例如:“自从最后一面后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辛勤忙碌吗?/太多的问题要问他们/我急不可耐//要是能抓住他们的脸”(J900, F1074)叙述者如此急不可耐,以致想要“抓住他们的脸”来问个究竟。该举动如此突兀而不可思议,即使以“提喻”(以局部喻整体)修辞来看,也不能消除其侵犯之感。所以更为合理的解释是狄金森对“灵性的身体”概念的戏仿与反讽,即此处的“脸”并非确指,正如“灵的肉体”并非实际的身体。
同样不可能的,还有各种非自然的场景与物什。例如,“地下村镇”的“居民”待客的“大理石茶”(J1743, F1784)、“绸缎的房椽”(J216, F124)、“长毛绒的溪流”、“锦缎的河岸”、“珍珠人群”(J457,F684)等,一起构成了这个故事世界不可能的日常。
4.非自然的、不可能的时空
这个故事世界的时空是非自然的:时间有时段而无时刻、有流逝而无速度;内部可以比外部大,意念可以穿越时空而化为行动,支离破碎的事件穿梭在现在时的“死亡家园”故事和过去时的“尘世故园”故事之间。尤其是无时态的中文译文,极大地增加了阅读难度。例如:“长长的—长长的一觉—/人所共知的—一觉—”“在石垒的堤岸上/晒太阳打发千年—/却从未抬眼—看过正午?”(J654,F463)时间凝滞、静止,千年和一日并没有区别。又如:“一座坟墓—是一块受限的尺幅—/但广阔胜过太阳—/和他殖民的所有海洋/还有他垂顾的陆地万方”(J943,F890)空间的大小、内外等各种维度相互矛盾。再如:“没有围栏将它圈住/意识是它的田亩,而/它把一个人的灵魂存贮。”(J876,F852)到底是墓穴为人提供“家园”,还是意识为墓穴提供“发生场”?物理空间与人类意识之间的从属关系出现分歧。又如:“我常从村旁经过/在放学回家的时候—/纳闷这里的人在做什么—/村子为何如此静默—”“请相信地下/那亲切的许诺,/喊一声‘是我,’‘带上多莉’,/我就会拥(你)入胸怀!”(J51, F41)开篇时,旁观者“我”讲述着自己对这个“地下村庄”的好奇与揣测,但结尾的祈使句却显示她正是这个“死亡家园”的一员,在对读者发出先行者的邀请和呼唤,从而呈现出一种时空叠加的不可能现象。
5.转叙(metalepsis)
“转叙”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指的是一个或多个文本的不同叙述层或故事世界之间的相互越界,其中包括本体论意义上的转叙,或曰“实体越界”,即故事层面上的“人物或叙述者跨越故事层并有实质的移位行为”,以及修辞学意义上的言语的越界,即“人物或叙述者的视角和声音出现在另一叙述层之中,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移位。”(18)张进、于方方:《论转叙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多样呈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这种叙事策略贯穿于狄金森的“死亡家园”叙事中,例如前文中提到的“太阳落呀—落—还在落”(J692,F715)与“它死了—找到它—”(J417,F434)两首诗中,时而在故事中、时而在故事外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或无实体的声音。前一首诗中的叙述者穿梭于故事世界和现实世界,使自我发生了裂变、一分为二,最终叙述自我跳出故事世界来到现实世界,而将故事自我留在里面;后一首诗中的叙述声音,则彻底模糊了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
(二)“诗歌家园”:无限可能性的王国
语言的虚构与超越,在狄金森的家园诗歌中展露无遗。她说:“自然是一座鬼魂出没的府邸—而艺术—在竭力招徕鬼魂。”(L459A)文学艺术的目的,不是像科学理性一样消除“鬼魅”,而是领略自然与世界的混沌与神秘,并召唤寓于其中的“鬼魅”或精神启示。因此,她将诗歌创作视为一种“自我启示”,以“源于梦和幻觉的潜意识世界”的诗歌言说来置换匮乏的母爱,并与父亲或上帝“搏斗”,(19)Marietta Messmer, “Dickinson’s Critical Reception,” in Gudrun Grabher et al. eds., The Emily Dickinson Handbook,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8, p.308.直至突破现实的局限,“把自己培养成—一名木匠—”,亲手修筑起一座矛盾统一的“圣殿”(J488,F475),即“诗歌家园”。
但狄金森“诗歌家园”的构成方式,就像是“用一种瞬间而且明显矛盾的表达方式在原地画了一个圆”(20)萨克文·伯科维奇:《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李增译,第461页。,将各个瞬间锋利的意识碎片拼贴在一起,以互不兼容的材料与结构形式共筑了这座“诗歌圣殿”,也体现了狄金森“家园”诗学矛盾冲突的本质。在这座圣殿中,“尘世天堂”以父亲的家为原型重新搭建,伸张自己的主权;“死亡家园”作为仿家园,既是凝滞的、无生气的,也是温情的、体贴的、安全的;天国是“家园”还是“异乡”的争辩,则把有关死亡、永恒的终极话题转换为生存论意义上的讨论,以“乡愁”置换了对未知深渊的恐惧。虽然这些矛盾歧义的“家园”,并未使诗人达到和平与宁静,但却让她在无限可能性的“诗歌家园”“语言王国”中,实现了灵魂的自由与自治。
这个“诗歌家园”,是自由的心灵家园。这种自由直观地体现在狄金森诗歌从形式、语言到题材内容的逾矩、越界、不受限。她以粗砺、怪异、不合文法的语言形式与深刻的思想内容、震撼的艺术感染力之间的巨大落差令人不解,也以自主的写作方式宣示了自己的主权。她的诗歌曾作为导火索,在早期英美两国评论家中引发一场关于英语的纯正性、规范性要求与美国文学语言创新、独立精神之间的价值之争。(21)Willis J. Buckingham, Emily Dickinson’s Reception in the 1890s: A Documentary History,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9, pp.3-10, 75-82.但曾长时间受过修辞、文体学训练和古典文学的熏陶,并作为公认的才女为校刊长期供稿(22)阿尔弗雷德·哈贝格:《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艾米莉·狄金森传》,第131, 156页。的狄金森,不至于不了解最基本的语法和文法,所以与其说她“遗忘”了这些教育经历,不如说她是在以自由写作的方式宣示对这个“诗歌家园”的主权。
这个“诗歌家园”,也是无限可能性的家园。正如狄金森诗中所说:“我居住在可能性里—/一座比散文更妙的屋舍—/更多的窗户—/更优质的—门扉—//房间如雪松密林—/目光难以穿透—/作那永世屋顶的/是几处错落的苍穹—//访客中—最美好的—/栖于—此间—/张开我窄小的双手/把乐园收罗—”(J657,F466)“诗歌家园”是比“散文日常”更妙的可能性之屋。这里的房间多如雪松密林,穹顶直通无限和天堂,诗人在这里张开双手就能“把乐园收罗”。在现实生活中,狄金森与外界仅保持着“见字如面”的文字联系、或门窗内外有限的“沟通”;但在这个无限可能性的家园中,她渊思寂虑、心鹜八极,因为“这个世界不是结论”(J501, F373),而只是接近意义真相的一个过程。
结 语
从不同语境看,狄金森的“家园”诗歌充满含混、歧义与矛盾。她既称尘世家园为“天堂”“乐园”或“故园”,又为逝者建构了一个更为温情、体贴、安全的“死亡家园”,作为已失去的尘世故园的替代品。但“地下村镇”诗意建构反映的其实是叙述者对“尘世天堂”的依恋,所以并不能成其为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家园”。她既排斥“天国家园”观,称天国为“异乡”,又依恋“天上的父”、向往教徒式“回家”的欢欣,通过将永恒还是湮灭的终极话题转换为生存论意义上的“乡愁”之争,回避了对虚无深渊的执着与恐惧。这种矛盾冲突的状态,与19世纪美国宗教转型期的特殊语境,即从神学统治向世俗社会转变、多重观念竞争的影响有关,也体现了狄金森在父权文化统治下的复杂心态。
她在宗教思想与现代意识的夹击下寻觅心灵的栖居地,将不同语境下的“家园”共置于无限可能的诗歌圣殿。同时,她也十分注重自己的诗歌及其语言“是否是活着的”(L260)。正如刘晓晖所说,狄金森“倾其一生所作的就是不断地赋予词语以生命”,而“文字生命力的源泉”正来自“文字与真理之间……不断缩小却无法消除的距离”。(23)刘晓晖:《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9-210页。她没有因为建构稳固的“家园”而拒绝语言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反而十分珍视它独立于作者的生命力,即词语一经使用后的意义自我更新、自我生成的能力:“一个字一经说出也就死去,/有人说。/我说它的生命从那一天起/才开始。”(J1212, F278)。
因此,狄金森“家园”诗学以矛盾、歧义、分裂、对抗为本质特征,始终处于一种意义生成状态而不能到达结构的圆满与完结,并最终呈现为一种只揭示、不解决的过程诗学。但也正是这种理论的开放性与拒绝结论的特征,使她的“家园”诗学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具有了现代甚至后现代诗学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