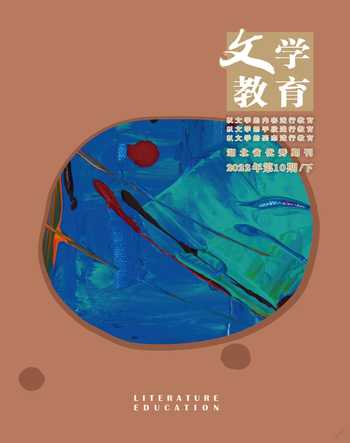城市怀古视角下《板桥杂记》中的遗民认同
2022-05-30孙莉
孙莉
内容摘要:余怀于暮年写作《板桥杂记》,透过城市怀古刻画秦淮繁华景,在今昔对比中展现明清易鼎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明遗民曾经的地位与身份被打破,自我价值重构成为普遍难题。余怀作为明遗民之一,在“今”与“昔”之间重新寻找自己的身份,并通过传承“道”来体现身份价值,实现身份认同。
关键词:余怀 《板桥杂记》 城市怀古 明遗民 身份认同
《板桥杂记》是作者余怀于康熙三十三年完成的作品,采用笔记体的形式,分为上卷雅游、中卷丽品、下卷轶事三个部分,其中中卷所用笔墨最多,勾勒出了众多江南名妓的形象。写作完成时的余怀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他借城市怀古,回忆往日秦淮繁华的景象,通过今昔对比哀叹江山易代的沧桑,在“今”与“昔”之间重新寻找自己的身份,实现自我身份认同。
一.追忆往昔繁华景
易代之际的文人常常回忆往昔繁华。靖康之变后,北宋皇朝覆灭,东京往日的繁华落尽,人们渐渐淡化了对东京的记忆,再度回忆时难免失于事实。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欲在人们心中复活故都盛景,记录北宋都城东京的一景一物,形成“梦华体”叙事的传统。《武林旧事》创作于宋末元初,“及时移物易,忧患飘零,追详昔游,带入梦寐,而感慨系之矣”[1],同样是记载往日繁华,借盛世之景抒发对故国及往日生活的思念。《武林旧事》《梦粱录》《板桥杂记》等作品均沿襲了“梦华”的传统,在物是人非的背景下神游故地,既留存过去生活的绝妙图景,又哀悼繁华的消亡,抒发黍离之悲。
《板桥杂记》中的景物描写主要集中于上卷,详细展示了旧院、贡院、长板桥、秦淮灯船等标志性地点和景物,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繁华热闹的人文画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秦淮灯船的描写,他透过这一焦点还原秦淮河曾经的盛况。“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2]灯船数量多、参与人数多、声响大、持续时间长,往日的欢腾景象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作者笔锋一转,由乐转哀,发出了一声长叹:“嗟乎,可复见乎!”[3]昔日盛况今日却无法再见,余怀在对比今昔的秦淮灯船时感到无限悲凉。
秦淮灯船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意象。如“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消。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罢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4]“阑干浸在波涛底,画船那得出游遨。夷船骤至连天涨,夷船退后江不浪。”[5]秦淮灯船的消失标志着美好时光的消逝,文人心中的哀痛不言而明。秦淮灯船代表着繁华,也代表着富贵。孔尚任《桃花扇》中提到:“你看人山人海,围着一条烛龙,快快看来!(众起凭栏看介)(扮出灯船,悬五色角灯,大鼓大吹绕场数回下)(丑)你看这般富丽,都是公侯勋卫之家。”[6]公侯勋卫之家才能乘坐富有装饰的灯船,于秦淮河上尽情游乐。余怀在《板桥杂记》上卷中着重提及从前秦淮河上灯船毕集的场景,不仅仅是追忆前朝,同样也是追忆当年的富贵生活。
明清朝代更替,作为明遗民的余怀在感叹秦淮景物不可复见的同时,又何尝不是痛心于往日生活不可复来。吴伟业在《满江红·赠南中余淡心》中称赞余怀:“问后生、领袖复谁人,如卿者?”[7]余怀年少时期生活安逸,家境殷实,且欲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而明朝的灭亡给他的人生带来极大的转折,家产遭清军洗劫,妻子受惊而亡,余怀自己也只能在多地辗转漂泊。在清政府的镇压下,抗清势力被摧残殆尽,复明无望,余怀移居苏州终老。他自称“旧京余怀”,成为不仕清朝的典型遗民文人。但就像余怀在《板桥杂记》中所说:“以上皆伤今吊古、慷慨流连之作,可佐南曲谈资者,录之以当哀丝急管。”[8]故国风光已消失殆尽,随之逝去的也有曾经的个人财富与风光,空留下遗民们心中的哀与伤。余怀意气风发的时光也已不可再现,巨大落差之下的他将自己定位为明遗民,仿佛是滞留在了往日的繁华当中。但遗民的身份终究无法让余怀得到心灵上的安定,他要做的是真正认同这一身份并重新寻找到自我价值。
“灯火游船,鼓吹名场。秦淮一水,阅尽兴亡。”[9]余怀追忆秦淮昔日风光中的具体城市景观,带有浓厚的怀古色彩,不仅表达对前朝的百般留恋,也借秦淮风光之变映射自己的身世变迁、命运遭际,余怀寻找着自己在新环境中的地位,寻求自我身份认同。
二.哀叹秦淮名妓悲剧命运
名妓也是当时城市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晚明狎妓之风盛行,江南才子大多喜欢以风流自居。鲁迅于《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故伎家故事,文人间亦著之篇章。”[10]《板桥杂记》中卷记述了多名名妓的风姿与事迹,她们容貌姣好、眉眼如画,且经由艺苑培养,拥有才艺专长,如知书、善画、懂琴等等。余怀笔下的她们与文人的交游中交易性质往往不明显,更多的是情投意合,很多名妓最终也嫁与文人名士。但是在政治动荡的大背景之下,名士或壮烈献身,或退隐沉寂,而这些女子们的命运也颇为坎坷。她们中的许多人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香消玉殒,结局凄凉。透过秦淮群艳的悲凉遭遇,可以看到明清易代之际百姓生活的悲剧色彩。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相似,作者借群艳之凋零言明清之际名士们地位巨大转变产生的苦痛。
作者详细描写了近三十位秦淮名妓,其中必定带有缅怀当年南京浪游生活的成分。“据余所见而编次之,或品藻其色艺,或仅记其姓名,亦足以征江左之风流,存六朝之金粉也。”[11]将昔日名士与美人的交游与今日各自飘零的凄凉局面对比,生发出无限叹惋。余怀并没有像许多文人一样,单纯写作“狭邪”之文,“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狭邪之是述,艳治之是传也”[12]。秦淮佳丽们不只有色与艺,余怀打破时人的固有看法,在容貌及才艺描写之外记述表现名妓们的德行与大义的言行。比如甲申之变时,葛嫩被执,面对清军主将的凌辱,葛嫩大骂,嚼舌含血喷其面,最终被杀。柔弱的女子能迸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尽显其侠肝义胆、柔情傲骨。
秦淮群艳的情与义侧面表现了余怀与清政府势不两立的决心。在他的笔下,从前的秦淮河风光是美妙绝伦的,曾经文人雅士与佳丽们的交往是情谊深厚的,生活有着说不尽的乐趣与雅趣。而清军的入侵使一切化为泡影,他对此深恶痛绝。在清政府严苛的“文网”之下,余怀借看似“狭邪”的题材倾吐真实想法。他作诗书不写清朝年号,隐居吴门,以卖文为生也拒不出仕,执着地固守着明遗民这一身份,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念。
与将女性描绘成男子附属物的文章或才子佳人模式的文章相比,余怀在《板桥杂记》中描写的秦淮名妓更为客观真实。然而,在某些方面仍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的情感偏向及过于美好的想象。他笔下的这些女子基本都容貌才艺双绝且兼具德行与品格,个个都美好出众。吴伟业曾言:“江左全盛,舒、桐、淮、楚衣冠人士避寇南渡,侨寓大航者且万家,秦淮灯火不绝,歌舞之声相闻。”[13]晚明秦淮相闻的歌舞声中又有多少余怀笔下才貌双绝、真情厚意的名妓?又有多少是兼具才思与民族大义的文人雅士?余怀似是有意挑选部分女子的命运加以突出,试图描写名妓们面对国破家亡时的情与义,对她们进行道德评判,作证自己固守“遗民”身份的行为,追逐着道德与政治方面的“正确”,在她们身上找寻身份认同。作者有选择性地突出明朝的繁华,着力书写文士佳人风貌才情与大义,这种自我身份认同的方式是带有幻想色彩的。
三.遗民的价值探索与身份认同
明清易代,山河沦丧让名士们痛苦不堪,他们陷入身份焦虑之中,迫切地想要重构自己的身份以获得自我认同。余怀就是其中之一,对故国深切怀念并强调自己的“遗民”身份,拒绝出仕清朝。然而明朝已经覆灭,他与当下的清朝格格不入,因此产生了理想身份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志士选择以身殉国,表明忠诚不渝的品格。比如张煌言曾在诗中说过:“大厦已不支,成仁百事毕。”“宁进寸,毋退尺。宁玉碎,毋瓦全。”[14]死节是壮烈的,在当时似乎演变成“忠”的象征。同时,也有心属故国却不死节的人,他们提出了对死节的别样看法,如陈確《死节论》:“死合于义之为节,不然,则罔死耳,非节也。人不可罔生,亦不可罔死。”[15]然而在社会普遍观念中,与死节之士相比,在新朝生活下来的明遗民在一定程度上是“应死未死之人”。因此,他们不仅需要表明自己对故国的赤诚之心,更需要为自己在“夹缝”中的生存寻找理由。就余怀而言,虽然在明朝时有为国效力的志向和才能,但作为明遗民,为新朝效忠显然是不现实的。黄宗羲曾说:“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16]明遗民们不与清政府合作,以此保持对前朝的归属感。有志于政治的志士仁人面对这一局面会感到生不逢时,无处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身为精神上的明朝人为何容忍自己生活于清朝?继续生活下来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板桥杂记》下卷讲述了很多曾经潇洒风流的名士或贵族,在明亡后生活陷入困顿。张魁乱后还吴,最后竟穷困而死。中山公子徐青君乙酉鼎革后沦落至为人代杖。“余之缀葺斯编,虽以传芳,实为垂戒。”[17]余怀虽然说下卷的主要作用是垂戒后人,但其实仍是借这些人的遭遇突出今昔强烈对比。明朝灭亡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前尽享地位、财富的人们面临着失去原有高贵地位及财富的境况,如何謀生成为了大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走向民间,行医、经商、卖画以维持生计,但用“平凡”的方式谋生,心中的志向与当前的生存状态相差甚远,如何能体现出“明遗民”这一独特身份的价值?这使得他们越发急切地要寻找自身价值,实现自我身份认同。
清初,统治者施行暴政,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圈地导致民众流离失所,颁布“剃发令”,强制民众服从异族风俗。在这种情况下,明遗民们普遍担心本民族文化与“道”将在强制或潜移默化中消失殆尽,民众会被异族统治者的思想体系同化,失去汉族人特有的品格。因此,他们力图通过著述等方式恢复“道”与“礼”,强调汉族道德标准,维护儒家伦理纲常、价值体系。明遗民们拒绝与新朝合作,便无法从政治的高度上传播“道”,转而将目光转向民间,以求“正人心”,移风易俗。明遗民们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路径之一便是传“道”,通过这一方式实现自我的安顿。
余怀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途径便是留存过往美好记忆,在作品中将“道”传承下来。无论是赞美秦淮旧风光,还是追忆曲中佳人,余怀记录下来的都是曾经的美好,他心中的故国情怀得以安放,也勾起广大明遗民的回忆,向后世的读者展现如梦似幻的明朝。同时,余怀也不忘在作品中传承“道”,拥有“大义”的名妓就是承载“道”的载体之一,余怀在群艳事迹中偏偏择此一种来写,足可见他对道义的重视,通过社会地位并不高的女子们身上折射出的“道”,反映坚守“忠”的重要性,以此坚定自己的信念。
整部作品充满了作者对明朝的怀念,体现了繁华与凄凉转换时巨大的落差感。余怀不时在文中发出叹息:“嗟乎!俯仰岁月之间,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黄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18]“观此,可以尽曲中之变矣,悲夫!”[19]余怀也有意将作品的效仿对象定位于《东京梦华录》这样的怀古城市笔记,而不是青楼小说、“狭邪”笔记,并不将立意局限于展现旧时秦淮声色。从这一点来看即可以明确其在《板桥杂记》中的深沉寄托。
暮年的余怀追忆秦淮风月,通过城市怀古,刻画秦淮一带繁华景象,充分描绘景与人背后的文化内涵,并在今昔对比中展现明清易鼎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文人的地位与曾经的身份被打破,余怀试图通过深切怀念旧朝来证明“遗民”身份,传承“道”以体现身份价值,实现身份认同。
注 释
[1]周密:《武林旧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2]余怀:《板桥杂记》,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3]余怀:《板桥杂记》,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4]孔尚任:《桃花扇》,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70页。
[5]魏源:《魏源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版。
[6]孔尚任:《桃花扇》,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33页。
[7]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08页。
[8]余怀:《板桥杂记》,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9]缪荃孙:《缪荃孙全集笔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99页。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页。
[11]余怀:《板桥杂记》,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12]余怀:《板桥杂记》,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3]吴梅村:《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4]张煌言:《张苍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5]陈确:《乾初先生遗集》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3页。
[16]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二,康熙二十七年刊本。
[17]余怀:《板桥杂记》,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18]余怀:《板桥杂记》,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19]余怀:《板桥杂记》,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参考文献
[1]李瑄.《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
[2]周晓琳、刘玉平.《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3]钟继刚.《艳冶之游与文化情怀——论〈板桥杂记〉》[J].《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03期.
[4]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节义观念及其行为抉择》[J].《明史研究》,2014年第00期.
[5]齐钰.《〈板桥杂记〉在青楼轶事小说中的典范作用研究》[J].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