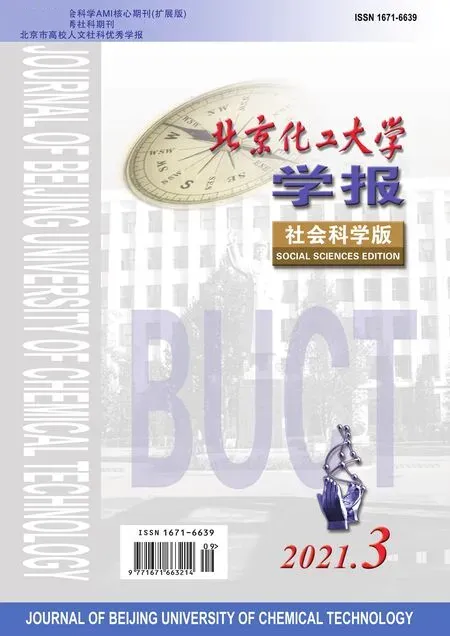李东阳《拟古乐府》新变
——兼论对明清咏史乐府的开启
2021-11-28张煜
张煜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谥号文正。明朝长沙府茶陵州(今湖南株洲市茶陵县)人。明代中后期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诗人、书法家、政治家。他历任弘治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为官50年。据《明史》记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1]他一生著作丰富,今有《怀麓堂集》《怀麓堂诗话》等著作传世。在众多创作中,李东阳乐府诗创作成就尤高,最为引人瞩目,围绕其乐府诗汇聚古今议论最多,如明胡缵宗(1480—1560)赞其乐府说:“我明元老西涯,……拟乐府百篇。举世珍之,不啻隋珠赵璧。”[2]明崔廷槐(1499—约1560)也看到并指出:“西涯乐府优于诗。”[3]清朱庭珍(1841—1903)更是赞曰:“茶陵在明,自是名家,与李何王李并立无让,其乐府自成一格,非七子所及。”[4]由此可见,世人特别将他的乐府诗单独提出评价,对其乐府的珍视程度非同一般,此处提到的乐府,其实是指其创作的一组拟古乐府诗。李东阳将这些乐府诗自命题为“拟古乐府”,诗评家也尊重并袭用李东阳本人的说法,如朱彝尊(1629—1709)评价其乐府说:“其拟古乐府,因人命题,缘事立义,别裁机杼,方之杨廉夫李季和辈,似远胜之。至或刚而近虐,简而似傲,文之佳恶,文正盖自得之矣。”[5]由此,学界评价李东阳也大多用“拟古乐府”名之。“拟古乐府”与“拟乐府”同义,在中国乐府诗的历史上,大略始于两晋文人,如陆机(261-303)已作有《拟乐府》,这一传统在中国诗歌史上时断时续,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至明代李东阳继之大力创作拟古乐府,并直接明确以拟古乐府名之,受其影响,明清诗人创作拟古乐府不断发展,终于蔚为大观。
本文以岳麓书社版《李东阳集》第一卷中收录的“拟古乐府”101题101首为研究对象,这百首乐府,成编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时年作者五十八岁。据《李东阳年谱》“弘治十七年”条可知:“宾之《拟古乐府》百篇,非一时之作,弘治二年与杨一清书中即言及欲拟作乐府,意者此百篇即作于自彼之后数年间,至本年初成编。”[6]本文拟在其拟古乐府诗的创作动机、命题特点、题材选取以及声律体式特点等相关研究基础上,重新界定其拟古乐府之实质,并从乐府诗史的角度揭示其对明清咏史乐府诗产生的影响,以期对李东阳乐府诗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反对摹拟的初衷
每一位作家的创作动机都值得特别注意,这直接关系到作品的风格特点。李东阳创作拟古乐府的初衷是什么呢?翻开他的乐府诗,在《拟古乐府引》中可以看到如下明确的表示:
予尝观汉魏间乐府歌辞,爱其质而不俚,腴而不艳,……嗣是以还,作者代出。然或重袭故常,或无复本义,支离散漫,莫知适归,纵有所发,亦不免曲终奏雅之诮。唐李太白才调虽高,而题与义多仍其旧,张籍王建以下无讥焉。元杨廉夫力去陈俗而纵其辩博,于声与调或不暇恤。延至于今,此学之废盖亦久矣[7]。
根据以上引文中“予尝观汉魏间乐府歌辞,爱其质而不俚,腴而不艳……然或重袭故常……多仍其旧……此学之废盖亦久矣”等语,可知诗人喜爱的是汉魏乐府之朴拙。同时他也注意到汉魏之后的很多乐府诗人“重袭故常”,从乐府诗题到内容都一律沿袭旧有的乐府创作,故不足取。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认为像“唐李太白才调虽高,而题与义多仍其旧,张籍王建以下无讥焉”,如李白这样的天才诗人的乐府诗的题目和内容亦难免因循守旧,中唐以乐府著称于世的张籍、王建之后,更是不值一提。故此,李东阳认为“延至于今,此学之废盖亦久矣”,意思是乐府这一专门的学问,至明代可谓荒废。至此,李东阳在诗序中要表达的核心意思很明确:即乐府创作忌沿袭故常,无论是题目还是内容,反对摹拟、力求新变正是诗人一脉相承的文学观念。他曾说:“今之为诗者,……‘必为唐,必为宋。’规规焉,俯首缩步,至不敢易一辞,出一语,纵使似之,亦不足贵矣。”[8]这就与传统的拟乐府或者拟古乐府的观念截然不同了。众所周知,两晋以来的拟乐府,形式是袭用乐府古题而创作的乐府诗,内容大多以借旧题抒古意发己志为主。李东阳反对“重袭故常”的提法,注定他的拟古乐府从根本上与传统的拟古乐府相背离。对于李东阳有意追求的乐府之变,人们也确实注意到了,如清人田雯(1635—1704)评价说:“香山讽喻诗乃乐府之变,《上阳白发人》等篇,读之心目豁朗,悠然有余味。后李西涯乐府,又变于白。”[9]具体看李东阳构思创作的这一组拟古乐府诗,无论是新的诗题,还是新的取材方式,表达的主旨,都是发前人所未发,且与他这一诗学思想保持一致。
总而言之,统观李东阳创作拟古乐府的初衷,是有意突破摹拟的传统,他要创作的是名为“拟古”的新的乐府。其新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因人命名的新题
关于乐府诗的命题原则,李东阳在《拟古乐府引》中这样说:
或因人命题,或缘事立义,托诸韵语,各为篇什。长短丰约,惟其所止;徐疾高下,随所会而为之[10]。
众所周知,汉乐府“缘事而发”,乐府古题也是缘事而立。乐府诗题与内容的关系或者完全相合,如《战城南》写战争,《孤儿行》叙孤儿苦状,《妇病行》状病妇惨景;或者诗题与内容不合,然而与本辞或古辞有一定的联系,如《豫章行》古辞写豫章山上白杨被砍伐运走,曹植的《豫章行》则借以抒发受曹丕父子猜忌打击的郁愤;或者诗题与内容不合,同本辞或古辞完全没联系,如曹操、曹丕的几首《秋胡行》,有的写神仙丹药,有的咏明君吟相思,和“秋胡戏妻”故事不相关。然而这些乐府诗题都是缘事而立,毋庸置疑。自唐代以来的新乐府的命题,或如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中所说的“因事立题”,或如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评价杜甫诗所说的“即事名篇”,显而易见,也都是以“事”为中心的命题原则。至李东阳,他在《诗前序》中明确地提出了“因人命题,缘事立义”命题方式,首次将“人”置于“事”前,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如同历史散文的纪传体,这样咏史叙事描写更加灵活自由,人物形象突出,无疑是一大新变,正如同纪传体的历史散文相对于编年体的历史散文的进步,这无疑是具有创造性的。从乐府诗题目来看,这一百零一首乐府全为新题,无一首沿用前人古题,确实是李东阳“因人命题,缘事立义”之新作。限于篇幅,从百首中选取几题列举如下:《易水行》《鸿门高》《新丰行》《淮阴叹》《臣不如》《殿上戏》《宜阳引》《颍水浊》《数奇叹》《文成死》《牧羝曲》《问喘词》《冯婕妤》《汉寿侯》《五丈原》《东门啸》《南风叹》《闻鸡行》《晋之东》《伯仁怨》《氐带箭》《五斗粟》《燕巢林》《宁毛狗叹》《长江险》《奸老革》《太白行》《曳落河》《睢阳叹》《河阳战》《令公来》《司农笏》《养儿行》《问中使》《昆仑战》这些新诗题一经传世,即引人瞩目,同时代的作家顾元庆(1487—1565)评价说:“乐府尤妙,其题与句篇自有新意,古人所未道者。”[11]特别指出了李东阳拟古乐府在命题句篇上的创新性和独特性,超出前人。又如王士禛(1634—1711)同样看到了李东阳乐府诗的新变,他评价说:“则乐府宁为其变,而不可以字句比拟也亦明矣。”[12]王士禛指出,读者视角不应局限在字句是否比拟上,言外之意,其妙处体现在字句之外的新题目上。这些评论,都敏锐地注意到李东阳乐府诗的与众不同之处。
三、取材历史的题材
除了题目的创新,李东阳拟古乐府的新变还表现在诗歌题材方面,他创作的是一组记述历史的乐府诗歌,具体来说,有以下两方面的创新。
首先,相较于前人取材现实,描写社会生活,反映民生疾苦,李东阳乐府诗侧重歌咏历史故事、史事。他的乐府作品取材于正史,而传统的乐府诗历来大多歌咏当下的社会时事,这是李东阳乐府的特别之处。对此,学界褒贬不一,引起古今学者广泛关注[13]。如王世贞早年评价李东阳这组乐府诗的时候说:“李文正公为古乐府,一史断耳,十不能得一。”他认为李东阳的这一组取材历史的乐府诗是“史断”,十首里面挑不出一首佳作,这是他早年出于对以乐府的形式咏史的成见。王世贞晚年毫不隐讳地匡正了自己早年提出的看法,他说:
向者于李宾之拟古乐府,病其太涉议论,过于翦抑,以为十不得一。自今观之,奇旨创造,名语叠出,纵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若使字字求谐于房中铙吹之调,取其字句断烂者而模仿之,以为乐府如是,则岂非西子之颦邯郸之步哉……,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而已[14]。
由上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世贞修正了自己的观点。经仔细品读,他甚至认为李东阳的乐府诗“奇旨创造,名语叠出”,更为其没有“被之管弦”,感到深深的遗憾,认为仍不失为“天地间一种文字”,肯定地认为他自成一家,给予很高的评价。就连王世贞本人后来创作的拟古乐府,诸如:《顶生王》《阿修罗》《琉璃王》《无忧王》等等,无疑与李东阳拟古乐府如出一辙。王世贞一人即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评断,从侧面反映出李东阳拟古乐府带给世人的冲击和影响,引发了广泛持久的思考。
又如清贺贻孙(1605—1688)称:“近日李东阳复取汉唐故事,自创乐府。余谓此特东阳咏史耳!”[15]可见李东阳以乐府诗的形式咏史这一典型的做法,的确是乐府诗发展历史上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
李东阳以乐府诗写历史人物故事,究其实质是欲以诗纪史。仅举一例,如其首章乐府诗《申生怨》云:
十日进一胙,君食不得尝。谗言岂无端,儿罪诚有名。儿心有如地,地坟中自伤。儿生不如犬,犬的死君傍。天地岂不广,日月岂不光。悲哉复何言,一死以自明[16]。
诗题下明何孟春(1474—1536)引《左传》为此诗本事作解云:
《左传》:晋献公烝于齐姜,生[太子]申生。晋伐骊戎,骊戎女以骊姬,生奚齐。骊姬嬖,谋欲立其子奚齐,乃谓申生曰:“君梦齐姜,必祭之。”申生寄予曲沃,归胙于公。值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姬泣曰:“贼由太子。”太子奔新城,缢死。
根据何孟春注解可知,《申生怨》一诗歌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晋国骊姬设计陷害太子奚齐,逼迫其自杀一事。李东阳百首乐府诗,都是从正史中选取诗歌素材,以诗纪史,主旨鲜明。这一写法,前无古人,称得上是创举,为明清诗坛上涌现出大量的诗史互证的新乐府组诗开创了先河,如明清之交的万斯同明史新乐府六十首、胡介祉的明史新乐府五十首等等,都继承了李东阳拟古乐府创作的这一传统。
其次,李东阳《拟古乐府》作为一组大型连章体咏史之作,歌咏的历史人物从春秋战国直至元代,从内容上看相当于一部通史,非断代史。他视野开阔,贯穿古今,乐府诗囊括了社会各阶层众多历史人物,世间万象,尽收笔下。这是其乐府诗题材的一大突破和创新。后人继之所创作的新乐府,基本上歌咏的都是一个或者两个朝代,如洪亮吉(1746—1809)的《拟两晋南北朝史乐府》,徐宝善(1770—1838)的《五代新乐府》,朱一新(1846—1894)的《咏南史新乐府》,万斯同的《明史新乐府》等等,题目一目了然,皆为断代史,相比之下,可见李东阳创作乐府的大手笔,不但在当时的诗坛掀起不小的波澜,而且开启了后人咏史乐府诗的创作之路,然而后来者无一人超越他的成就。
以诗歌咏史最迟在东汉出现,如班固的《咏史》诗。然而以乐府诗咏史,且以百篇规模出现的咏史诗,李东阳可谓历史第一人。正因为李东阳这一大规模的乐府诗创作无论从内容形式,还是在数量上,都大大超越世人,成就如此突出,一时众说纷纭。如明嘉靖诗人和诗学理论家徐泰给出了毁誉参半的评价:“长沙李东阳,大韶一奏,俗乐俱废,中兴宗匠,邈焉寡俦。独拟古乐府,乃杨铁崖之史断,此体出而古乐府之意微矣。”[17]清代诗人钱良择(1645—?)说:“李茶陵以咏史诗为乐府,文极奇而体则谬。”[18]反面的意见如李调元在《雨村诗话》中说“李东阳工明史乐府……皆可备史料”[19]等等,显而易见,以乐府咏史在当时得不到人们广泛的认可和接纳。如上所述,连王世贞这样的大家,初始也是抱着批评否定的态度,然而其立场最终转变,向世人正面宣告了李东阳乐府创作的成就,此间经历了十数年或数十年,李东阳乐府终于被认可接受,虽然长路漫漫,然而他还是成功地站在了时代的制高点上。
四、音韵和谐的声律
李东阳对诗歌声律十分重视,曾在《麓堂诗话》中这样说:
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于诗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和。又取其声之和者,以陶写情性,感发之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俳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则古之教何必以诗律为哉[20]?
又云:
而比之以声韵,和之以节奏,则其为次,高可讽,长可咏,近可以述[21]。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李东阳对诗歌声律的重视态度,他认为若无音韵之美的文字不能算作是诗歌,诗歌一定要有声律之美,简言之,是要有音乐性,乐府诗当然也不例外。他论诗注重诗歌的格律音韵,认为这是诗歌区别于六经之所在,故而在诗歌创作中追求合律。他要求自己的诗作要合乎乐律,自己写诗,“凡有得意处,则令善歌者歌之,以定是之高下”,对“诗有五声,全备者少,惟得宫声者为最优,盖可以兼众声也”[22]之说颇为赞同。因此,在其拟古乐府诗前序中,对自己明确地提出要求:“内取达意,外求合律”,表明其创作伊始就要追求乐府诗的音乐之美,这与他的诗歌音乐理论是统一的。《拟古乐府》中的 101首拟古乐府,正是其实践的产物。因此,明人黄周星(1611—1680)在读了李东阳乐府诗之后,在《〈陶密庵诗〉序》中慨叹:
余尝读《西涯乐府》,而酷爱之,不独怀古论世,有功劝惩,而音节鏦铮,激越顿挫,此案间第一绝妙下酒物也[23]。
黄氏认为《西涯乐府》不仅内容充实有意义,并且其音节有顿挫之美,即声律之美。清人潘德舆(1785—1839)在《养一斋诗话》中也称赞李乐阳的乐府说:“此翁于音节最留神,且其振起衰靡,吐纳众流,实声诗一大宗。”[24]潘氏认为东阳乐府“于音节最留神”“实声诗一大宗”,也是从音乐性的角度评价东阳乐府,认为其具有独特的声律之美。胡缵宗在《可泉拟涯翁拟古乐府》卷首《拟古乐府序》中说:“孝庙时,宰相李文正公因之为拟古乐府,凡二卷若干篇。……其调诘屈而谐节。李公虽鉅望盛才,以文章鸣一世,而是编尤为士林所脍炙。然自今观之,其声格合处,可与唐人并驱尔。”[25]
五、备受推重的新体
就体制而言,李东阳的乐府诗句式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兼有,一百零一首乐府诗中杂言体占据多数,最短的诗歌如《尊经阁》只有十七字,最长的如《花将军》长达二百八十多字,充分体现出乐府诗原本是歌词的形式自由的文学特征。这些乐府诗被时人名为:新体新调新乐府。据《浙江通志》卷一八○记载:
冯兰,字佩之,成化己丑进士,选庶吉士,仕至江西提学副使。其在京师,与李东阳谢迁雅相好。迁既归田,与兰唱和无虚日。间书之以寄东阳,东阳亦一一和之。是时东阳为一世宗工,而于兰则敬为老友。各有乐府咏史诗,号为新体[26]。
这段记载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李东阳与好友冯兰互相作乐府咏史诗唱和,十分著名,在京师传为美谈。人们纷纷将其乐府咏史诗“号为新体”,说明乐府咏史诗广为人知,确实新天下人之耳目,也正如田雯在《古欢堂集杂著》卷一中所云:
李西涯以论事作乐府,别辟新调[27]。
更有人其实早已抛开其“拟古”的面纱,独具慧眼地指出:
若元杨维桢明李东阳各为新乐府,古意寖远[28]。
又有云:
永乐以还,崇尚台阁,迄化治之间,茶陵李东阳出而振之,俗尚一变。但其新乐府,于铁崖之外,又出一格[29]。
这里前人将李东阳与杨维桢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创作的名为古乐府其实是新题新体新意的新乐府,与古题古意古体的古乐府相去已远。而同为新乐府,李东阳似更胜人一筹。
六、承前启后的地位
众所周知,乐府诗最重要的特点是采用乐府歌词的形式反映现实民生、追求理想政治,是中国古代诗人艺术理想与政治理想的完美结合,得到历代士人的高度认可。乐府诗自汉代起,跨越数千年,至明清易代之际发展至鼎盛。而李东阳的乐府诗在中国乐府诗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当今学界尚认识不足。
在李东阳《拟古乐府》问世之后,明清两代就接连不断地涌现大量效仿李东阳拟古乐府组诗的形式创作咏史乐府诗的专集。对此,笔者做了较为详细的文献梳理,有较多发现,兹列举如下:尤侗(1618—1704)有《拟明史乐府》100首,其序言说:“拟乐府百首,未敢窃比西涯,庶几存咏史之一体。”[30]王士禛评价说:“长洲尤展成侗……仿李西涯作《明史乐府》百篇,佳处殆不减李。”[31]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也评说:“李东阳工《明史》乐府,近尤西堂效作。”[32]李东阳对尤侗的影响有目共睹。明胡缵宗说:“读公《拟古乐府》而有感焉,篇拟之,亦百首。”特命名为《拟涯翁拟古乐府》。如此成规模的拟作仿作有力地证明了明清诗人学者对李东阳乐府诗的广泛认可与接受。除此之外,尚有吴炎(1623—1663)、潘柽章(1626—1663)作有歌咏明史的《今乐府》200首;胡介祉有(1627—1664)《咏史乐府》60首;万斯同有《明史乐府》68首;张符升(1725—1786)有《绥舆山房分和李茶陵咏史乐府》100首;洪亮吉(1726—1809)有《拟两晋南北朝史乐府》120首;《唐宋小乐府》103首;舒位(1765—1815)有《春秋咏史乐府》140首;谭莹(1800—1871)有《咏史乐府》98首;袁学澜(1804—1879)有《续春秋乐府》100首;程燮有《咏史新乐府》203首等等。这些乐府诗虽然题上与“拟古乐府”不完全一致,但是可以发现,其形式和内容都是以乐府咏史,这和李东阳的做法相一致,李东阳对后人创作乐府诗的影响不可小觑,体现在以乐府诗咏史和大型组诗咏史这两个方面。明清人对李东阳以乐府咏史全面接受并深度学习效仿,别开生面。这些诗人不约而同地创作乐府诗,这些优秀的讽喻历史和现实的诗篇反映近史、反映时事、为民请命,总结一代之兴亡经验教训,展现了诗人的艺术成就和社会良知,具有极高的历史与文学价值。
综上所述,李东阳拟古乐府诗的创作初衷、命题方式、以诗纪史以及音乐性和体式特点等等都清楚地表明,其乐府诗名为拟古乐府,实质为新乐府,非传统意义上的古乐府,这一新变深为后人激赏并广泛仿效,由此开启了明清乐府组诗咏史的先河,明清涌现大量乐府诗人,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史和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现象。乐府诗从汉代到清代这一发展脉络因之更加清晰完整,其创作主题较唐代元白以诗讽谏天子、写当下史有进一步开拓,尤其清乐府多歌咏历史故事、总结前代经验教训,视野也更加开阔,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