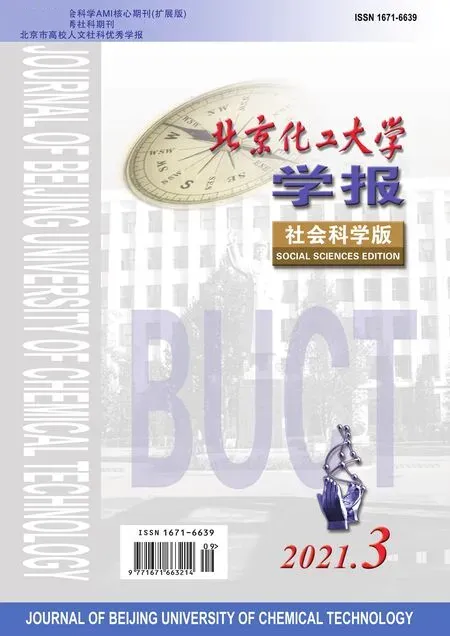近代中国的“少年论述”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2021-11-28郑晓岚
郑晓岚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少年”一词自古有之,常见于中国古代诗词中:如李白《少年行二首》、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王维《少年行》等诗词描绘了朝气蓬勃、勇武豪迈的少年形象;杜秋娘的“劝君惜取少年时”、岳飞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朱熹的“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等诗词劝说“少年”珍惜时间。“少年”与“老年”相对,主要指向个体生命的特定阶段,尤其指向十几岁的男子(1)受到日本文化影响,“少年”一词在近代文学文本中可见“少年女子”,这个偏正结构的语义重心落在“女子”,“少年”成为修辞性词语,指向女子的年龄阶段;在现代语境中则可直接用“少女”指称“少年女子”,与“少年”构成一对反义词。,多在生理学意义上使用,未曾与国家形象发生联系。
“少年”一词流行于近代中国,逐渐成为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修辞符号。当然,关键的问题不是“少年”在中国历史哪一个阶段出现,而是这个概念在近代中国有什么特定的内涵,为何及如何与国家形象产生联系。本文将“少年”置于近代政治文化权力网络中,勾勒“少年”在近代中国的修辞涵义,探讨“少年”如何被发现与重视,又如何成为近代文学文本的书写对象,研究近代有识之士参与近代中国“少年”的精神世界建构和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过程。
一、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少年论述”的兴起
1900年,梁启超首次将“少年”作为国家形象的一个修辞符号置于晚清民众视野,发表了《少年中国说》[1]。文章将过去中国称为“老年”,欧洲列邦为“壮年”,未来中国为“少年”,以“人之老少”喻“国之兴衰”,从生命有机体角度,把生命体的自我修复视为民族复兴喻象,以“少年”喻“老大帝国”涅槃重生、重获民族的青春活力,表达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
梁启超自认《少年中国说》受到龚自珍《能令公少年行》一诗的影响,然而后者并未将“少年”与国家形象联系起来。梁启超主要从域外思想资源提取“少年”意象及其蕴含的政治文化内涵。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当时日本受到欧洲少年运动的影响,已经出现各种“少年论述”,如尾崎行雄的《少年论》和德富苏峰的《新日本之青年》。日本的社会政治风气和思想文化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梁启超“少年论述”的形成(2)具体分析参见:梅家玲.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与晚清“少年论述”的形成[A].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71.。进一步追根溯源的话,梁启超的“少年论述”则主要源于欧洲各国的“少年论述”。在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中,欧洲文艺复兴前并不存在“儿童”这个群体,“儿童”被视为“成人的预备”,只是活在人们的头脑中。在清教主义的原罪观念里,“儿童”是布道的对象,是需要改造心灵、需要被拯救的群体。可以说,17世纪以前欧洲没有“儿童”,自然也就没有“少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欧洲从中世纪的宗教黑暗、神优于人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人们开始发现“人”,发现“儿童”,发现“少年”。18世纪以后,西欧各国掀起民族独立运动,德国、意大利等国成为新兴民族国家,爱尔兰和苏格兰也相继开展民族独立运动。在此背景下,“少年”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先锋,地位日益得到重视。此后,少年运动逐渐兴起,“少年论述”也随之兴起。这类论述普遍在国家名前冠以“少年”一词,例如“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等,由此开启“少年”与民族复兴的渊源。“少年论述”突显于西欧,然后传播到亚洲、美国和非洲,并逐渐成为一种全球现象(3)20世纪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年轻人崇拜现象。具体研究参见:GILLS,JOHN R. Youth and History: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European Age Relations, 1770-Present[M]. New York and London:Academic Press,1974. SPRINGHALL,JOHN. Youth, Empire and Society: British Youth Movements, 1883-1940[M]. London:Croom Helm,1977. LAQUEUR, WALTER. Young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M]. New Brunswick, N. J.:Transaction Books,1984.。
受到西欧、日本等国“少年论述”的启发,梁启超在论述中也经常使用“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少年日本”等语词,并创造了“少年中国”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文化符号,将“少年”与国家形象联系起来,在《少年中国说》中富有预见地指出,过渡时代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中国“少年”手中。“少年”冒险奋进、锐意进取、独立自由、文明进步,代表一股全新的政治文化动力,表征新的世界文明秩序,一改“东亚病夫”的老大帝国形象,隐喻一个朝气蓬勃、革新进步的“少年中国”。“少年”逐渐成为中国自我命名的一种修辞符号,与“新民”“新国”“竞争”“进取”“启蒙”“文明”“民族主义”等语词密切相关,体现“民”与“国”结合的视域,呼应近代身体国家化和军事化的尚武思潮(4)具体研究参见: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黄金麟.近代中国的军事身体建构,1895—1949[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43):173-221.作者从政治、经济、思想、教育等方面论述了中国近现代身体如何参与国体建构。,“负载着深厚的文明、革命、启蒙等深刻涵义,也暗合着‘少年中国’的沉睡与觉醒、衰落或兴盛”[2]。
梁启超身体力行,通过不同方式继续推动“少年论述”:1902年在《新民丛报》翻译刊载日本学者志贺重昂的文章《少年日本之歌》,挖掘“少年日本”与“少年中国”的关系;在《论进取冒险》结尾处用英文附上西方流行诗歌《少年进步之歌》,歌颂“少年”的冒险进取精神[3]。晚清时期由于中国和意大利的历史处境相似,两国都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外国列强压迫,于是梁启超大力介绍意大利,在《新民丛报》上翻译刊载《玛志尼少年意大利约》,介绍青年意大利党的各项主张;翻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叙写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这三位志士的少年时代以及玛志尼创立“少年意大利党”的过程,展现这些开国英雄的勇武气概,说明国家的建立犹如“少年”的成长,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磨炼,希望中国像意大利一样,不断涌现出少年英雄,实现民族复兴[4]。此外,梁启超还翻译了冒险小说《十五小豪杰》,创作《新中国未来记》,进一步推动“少年论述”。梁启超甚至将自己命名为“中国之少年”,以自身影像为近代中国注入了一个有力的少年形象。
二、“少年论述”热潮:近代中国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
传统中国讲究老幼秩序,奉行父权专制,以长者为本位,是一个“长老统治”的乡土社会[5]。年龄是确定一个家族或国家统治者身份的重要依据,整个社会“重老轻少”,“‘老人’拥有特殊的权威。老马识途,‘老朽’并非谦称而是包含了显而易见的矜持甚至威严”[6]。包括“少年”在内的儿童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他们被看做“缩小的成人”或“不完全的小人”[7],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由于“少年”在传统社会中长期遭到忽视,中国古典著作中几乎很难找到少年特性论述,即使出现少年形象,也没有专门为“少年”创作的小说[8]。对“少年”的一般印象大多散见于外国人的论述中。美国著名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描述道:中国少年必须安安静静地坐着,显得老气横秋[9]。传统中国“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10],“少年”若是老成必然得到嘉奖,若是轻狂、张扬则必然遭到责罚,整个社会“希望塑造一个个沈静好读的儿童……这种好静而不好动的模范儿童,最为当时士人家长所称许”[11]。传统中国“少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安静、顺从、墨守成规、缺乏活力与生气,也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长者本位下的大清帝国老态龙钟、落后保守,是《狮子吼》中的混沌国、《新石头记》中的黑暗之国,是《老残游记》中那艘遍体鳞伤、随时可能倾覆的破船,又是《黄绣球》中那座即将坍塌的老房子。
与传统中国不同,西方国家对“少年”则重视有加,正如严复在《天演论》中所揭示的:“然彼其民,好然诺,贵信果,重少轻老,喜壮健无所屈服之风。即东海之倭,亦轻生尚勇,死党好名,与震旦之民大有异。”[12]西方国家“重少轻老”,推崇“壮健”,崇尚“无所屈服之风”,因而国力强盛,说明“少年”事关国家盛衰。就思想层面而言,西方国家对“少年”的重视,主要源于进化论思潮,这股思潮推崇“进步”“竞争”,由《天演论》介绍到近代中国后在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对近代中国“少年”的影响尤其深远。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道:“《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13]进化论思潮甚至“构成了一种西方人士昵称为清王朝没落年代的‘少年中国’的政治和知识倾向”[14],颠覆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启引改造国民奴性的强劲思潮,也引发民众发现“少年”。
对人才的重视,是近代中国发现“少年”的根本动因。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攻击下摇摇欲坠,民族生存遭遇严重危机。近代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不在于器物或制度,而在于人才,应形塑新民,弘扬勇武之气,改造懦弱、阴柔、保守的国民性。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揭示民强与国强的内在关系,为重视人才、形塑新民提供了强有力的行动纲领[15]。1896年,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写道:“举国之人,与国为体。填城溢野,无非人才。所谓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虑虑,三代强盛,盖以此也。”[16]人才与国家密不可分,不论古今中外,人才都事关国家盛衰。1897年,梁启超在《论中国之将强》中再次强调人才的重要性:“有才千人,国可以立;有才万人,国可以强。”[17]一个国家只有依靠人才才能建立,人才越多,则国家越强盛;在《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中则揭示了国民与国家的密切关系:“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殆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有丝毫不容假借者。”[18]民强则国强,民弱则国弱,国民强弱事关国家盛衰。1901年的《光绪政要》中提到:“中国不贪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19]整个社会开始重视人才,呼唤人才。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对人才的呼唤成为中心议题之一[20]。以“少年”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也乐于接受新思想,他们身上体现的希望、冒险、革新、竞争、进步、独立、自由等修辞内涵,“不论是作为政治或社会实体还是象征符号,都成为怀抱革新社会、振兴国家志愿之时人反复论及的对象”[21]。
学生群体在甲午战争之后成为“少年”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早在1872年,为了培养国家有用人才,清政府首次将目光聚焦于学生,开始实施幼童留学计划(5)有关留美幼童研究,参见: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美]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M].刘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李书纬.少年行:1840—1911晚清留学生历史现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从书名可以佐证“少年”与留美幼童的密切关系,也反映当年“少年论述”热潮。,向美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希望他们日后学成归来,担负起强国保种的大任。这批平均年龄不到12岁的“幼童”将足迹探出国外,丈量更为广阔的世界,在世界地理版图中重新定位“老大帝国”的位置,并积极发现自我、想象自我,开启对新兴国家的美好想象。“幼童”的海外之旅冲击了中国既定的社会文化秩序,也引发民众重新审视“少年”的社会价值。
甲午战败后,社会各界纷纷提倡为学生创办新式学堂。1897年,“中国高等教育之父”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宣称设外院是“仿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校之法,别选年十岁内外至十七八岁止,聪颖幼童一百二十名,设一外院学堂,令师范生分班教之”[22]。清政府也开始实施教育新政,兴学堂、废科举、修订学制,进行近代化教育改革。1901年,清政府颁发“兴学诏”,提倡为学生大办新式学堂,甚至将办学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鼓励民间力量办学。全国由此兴起办学热,教育会团体数量日益增多。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教会学堂、军事学堂、公私等各类新式学堂逐渐取代传统私塾,获得了长足发展:全国学堂总数1904年为4222所,1905年为8277所,1909年则高达52348所。学堂数量急剧增加,学生数量也极速增长:1902年为6912人,1909年为1638881人,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23]。
社会各界还开始重视教科书的选择。传统中国只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启蒙读物,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教科书。然而,“这些读物,有的没有教育的意义,有的陈义过高,不合儿童生活,而且文字都很艰深,学时除了死读、死背诵之外,也不能使儿童们明了到底读的是些甚么”[24]。1860—1910年居住在中国的英国汉学家麦高温评论道:“中国的课本,也许是学生手中最枯燥、最陈腐、最古怪的东西了。书的作者恐怕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学生们的兴趣爱好。”[25]随着国势危急,加上新式学堂数量、学生数量急剧增长,传统教科书和传统启蒙读物无法满足救亡启蒙的需要,于是近代有识之士提出了“学堂宜推广以小说为教科书”[26]。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被译介作为教科书。1903年6月21日,上海《新闻报》刊载“希腊名著伊索寓言译英文本出版”广告,将林译《伊索寓言》视为“少年绝妙之教科书”[27]。1907年3月14日,上海《时报》刊载“商务印书馆高等小学教科图书表”广告,将林译《伊索寓言》列为“高等小学教科书”[28]。1906年6月17日,上海《新闻报》刊载广益书局“再版正则东语教科书”广告,将冒险小说《绝岛英雄》列为“教科书”[29]。1909年2月3日,上海《时报》刊载“学部审定商务印书馆各种教科图书”广告,将林译《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林译《鲁滨孙飘流记》、《澳洲历险记》等小说列为“学部审定教科图书”[30]。上述不同图书广告都将小说视为教科书,强调小说对“少年”的启蒙教化作用。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社会各界对“少年”的启蒙教育重视有加,希望通过新式教科书形塑新民。
出版机构也开始大量出版少年儿童读物。近代出版界巨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少年丛书》《儿童文学丛书》《世界儿童文学丛书》《儿童文学读本》《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小学生文库》《新小学文库》等少年书系。1908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林万里主持的《少年丛书》系列,并于1909年1月13日在上海《时报》上刊载出版广告,指出编译、出版丛书旨在鼓励“少年”以“中外名人”为榜样,激发“少年”的英雄之气:“本书杂採中外名人,足为少年模范者。将其事迹编为一传,并详加批评插入图书,以引起少年之注意。……诚十余岁学生校外之读本也。”[31]该系列又名为《中外伟人的传略》,“少年”与“伟人”的修辞关联体现编者的修辞意图:“出版者的初衷就是要为当时暮气沉沉的古老中国,培养一批充满活力的少年,改变中国的命运。”“在二十世纪初期,这一套书不知影响过多少青少年的命运”(6)参见:团结出版社编辑.编辑推荐[A] //孙毓修等主编.少年丛书[C].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近代有识之士也积极进行少年话语实践,强调为“少年”翻译或创作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教育小说等作品,主要介绍欧美少年关注的英雄人物或少年冒险故事。根据欧阳健的不完全统计,1875—1915年间,近100名近代小说家为“少年”创作或翻译文学作品[32]。不少书名直接凸显“少年”一词,如《少年军》《少年侦探》《少年旅行谭》等译作,以及《少年军》《少年机械师》《少年场》《少年镜》等创作(7)这些译作和创作的具体出版信息参见:[日]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M].贺伟,译.济南:齐鲁书社,2002:623-624.。就文学翻译而言,“译者按语以至评论者评语所表达的主题,十居其九是西方人那种一往无前的冒险精神”[33]。不少译者在序跋中明确表示,译作旨在以西方“少年”的冒险精神,激发中国“少年”的勇武精神。1905年《云中燕》书首“叙言”中写道:“是书述法国少女蝶英大冒险之事,情节离奇,叙事委婉。……是书亦足为振起少年精神之一助。”[34]1908年3月27日,东京《夏声》第二号开始连载《萍雪缘》,标“冒险小说”,篇首揭示译者的翻译动机:“见书中那两个人的所作所为,虽算不得什么大事业,然将一种英杰气概实可作少年榜样。”[35]这些序言都揭示了冒险小说于“少年”的精神激励作用,为救亡启蒙、强国保种服务。
近代中国从发现“少年”到重视“少年”,从派出留学生到创办新式学堂,从新式教科书到少年儿童读物,从文学翻译到文学创作,社会各界纷纷表达对“少年”的期盼与呼唤。“少年”甚至变成近代小说家自我命名的修辞符号,从《近代小说著译者及其作品一览表》可以发现,由“少年”参构的笔名共10种:“少年”“跛少年”“老少年”“少年中国之少年”“百钢少年”“大陆少年”“涤骨少年”“山门少年老”“无知少年”“侠少年”(8)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在‘跟着少年跑’已成为时代风尚的语境下”[36],整个社会出现铺天盖地的少年形象,形成一股强劲的“少年论述”热潮,这股热潮反过来又推动“少年”启蒙教育,对近代中国“少年”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深层意义上说,“少年”所具有的朝气、冒险、革新、竞争、进步、革命、独立、自由等修辞内涵,成为改造国民性的一部分。近代中国在倡导新民、想象新国家时,“少年”作为未来国民的重要地位被发现,一跃成为国家主体,被寄予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国民改造等政治期待,进而置身于近代革命话语中心,代表一股新生的社会变革力量,成为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修辞符号,参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三、近代中国“少年论述”与近代文学文本中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到,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在形成和认同过程中,文化特别是文学作用重大,甚至可以说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是通过文学书写完成的。“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为‘重现’(re-presenting)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37]。小说和报纸也成为近代中国想象民族国家的重要载体,有了这些共同的想象,才有缔造民族国家的基础。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一种文类,小说成为想象中国的一个重要方法:“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38]小说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表征,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体现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引导读者对国家、民族产生认同,并将其内在化。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揭示社会的深层意识和权力关系,反映并参与社会意识形态建构,影响人们对世界文明新秩序的想象,有助于建构一个新的民族国家[39]。小说为近代有识之士想象一个政治共同体、实现民族认同提供了重要渠道。他们以“少年”为言说对象,在文学翻译或创作中探索中国在世界新版图中的坐标,展开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美好想象,形塑新的集体认同与民族认同。
文学翻译引进新观念、新范式,在近代中国有助于形塑民族文化[40]。在外国文学译介热潮中,近代有识之士翻译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教育小说等外来文类,建构冒险奋进、勇武革新、独立自由的少年形象,表达对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的追慕,希望建立一个富强文明的现代民族国家。西方冒险小说注重空间场域转化,空间开拓超越了纯粹的文学形式,成为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秩序观念的表征,承载着近代中国民众对新兴国家的美好想象,是近代有识之士展开救国行动的想象场域。冒险征途凶险,少年主人公冒险奋进、勇武爱国,勇于开拓海外殖民地,正是近代中国民众期待的新民形象,他们的冒险经历有助于发现自我,唤醒以“国家”为主体的救亡启蒙意识。他们言说世界文明新秩序,形塑新的民族气质,承载着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希望,也寄托着近代中国民众的期盼:期盼“少年”成为“少年中国”的追梦人,以冒险求新的现代精神,以文明奋进的姿态,告别“老大帝国”,迈向“少年中国”。西方冒险小说以文学话语的形式启引了思想文化的现代性,成为折射五四时期“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影像,两者共同成为新中国与新世界想象中的关键一环,引发“少年”在传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反差中重新认识自我,重建民族文化认同,在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文明想象中批判传统中国,表达对新兴国家的期盼。
“少年”作为国家形象的一个修辞符号,是中国现代文学不断书写的对象。民国时期,“少年”依然是社会有识之士想象现代民族国家的叙述策略。文学作品塑造的少年形象,并非指向现实社会中的年龄群体,而是被历史、政治、文化建构起来的形象,“往往与民族和国家的革命、历史等宏大叙事联系起来”[41]。郭沫若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凤凰涅槃》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气息,期待旧中国在烈火中毁灭、新中国像凤凰一般在涅槃中重生。郭沫若翻译的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展现了“少年”反抗封建等级观念和封建制度的共同烦恼。蒋光慈《少年漂泊者》召唤革命与浪漫的少年先锋,鼓励“少年”献身于革命事业,缔造一个真正的“少年中国”。叶绍钧《倪焕之》书写少年主人公的成长与历险,展现“少年”改变旧中国的种种努力,弘扬“少年”乐观的革命精神与理想。巴金以大家族中的“少年”为题材创作的《激流三部曲》,讴歌民主、平等、自由与独立,反映“少年”与旧世界的抗争,引发许多“少年”参加革命。这类书写往往塑造少年革命者形象,反映一个时代的革命精神,见证时代主流价值观念的变迁,表达对“少年”的角色期待和意义规定,抒发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美好想象。可以说,对“少年”的反复书写,成为想象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方法。
然而,“中国现代启蒙思想虽然也呼唤‘人的觉醒’和‘人的发现’,但这里的‘人’之所以被呼唤出来,乃是为了最终被否定,被改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所需要的‘国民’,而非个人”[42]。就“少年”而言,“少年是因‘现代性’的来临而成为西方文化的中心象徽”[43]。“少年”象征“革新”“进步”“革命”“独立”“自由”“文明”的开端,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坚力量。矛盾的是,“少年”只有打破传统才能缔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少年”有时代表一种不成熟与不稳定,“少年论述”总是伴随着解构与重构,这种矛盾性正是现代性的典型体现。“少年”“作为现代性的特征被反复强调”[44],但他们的个体生命价值都是基于他们对国家或社会的意义,他们的个人价值只能体现于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之中。长者本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政权仍然掌握在老一辈精英人士手里,诚如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所揭示的:“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45]“少年”以理想主义冲击现实社会,其结局已在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交锋中得到了最好的脚注。即使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君主专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但依然未能缔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少年中国”;即使五四青年为了建立“少年中国”而热血沸腾,发动革命,但依然未能如愿。但“少年”又有着不甘屈服、不断探索、勇于斗争的精神,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见证一个“少年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或许只有在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刻,才能告慰无数为“少年中国”奋斗而牺牲的青春灵魂,他们以自己的青春热血谱写了一曲真正的青春之歌,永恒地奏响在天安门广场上。
四、结语
历史沉淀于词汇(9)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在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中,本文讨论的“少年”是一种政治、思想、社会、文化建构的话语体系。从“少年”的发现到“少年论述”热潮的掀起,“少年”本质上不再是一个年龄范畴,而是一个历史、政治和文化概念。该概念通过《少年中国说》广泛传播开来,与新民、新国、民族复兴等意象联系起来,产生、形塑、影响时人政治和文化的想象范式,也推动、重塑关于新兴国家的论述。近代有识之士以“少年”为书写对象,在文学文本中探讨传统中国在世界文明新秩序中的坐标,深入思考国民性改造与国家形象的内在关联,对现代民族国家展开文明想象。这类想象冲击传统老幼秩序,被赋予政治文化等意义,成为缔造一个新兴国家的历史驱动力,参与近代中国“少年”的精神世界建构。
“‘少年’所拥有的这一似乎是‘天然’的进步属性,使它成为现代中国政治与文化历史上一个不断复现的主体,一个错综复杂、充满冲突与歧义的话语网络,一个各种意识形态、理论论述竞争对话的平台”[46]。近代中国的“少年论述”突显了“老年”与“少年”、“过去”与“未来”等二元话语对立,体现社会进化论思潮,强调“少年”必定优于“老年”,“未来”必然胜于“过去”。然而,这多少掩盖了少年身份的暂时性与永恒性:生理学意义上,“少年”的年龄阶段是暂时的;政治文化意义上,“少年”的修辞涵义是永恒的。“少年”成为新兴事物、前驱力量的代表,参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作为国家形象的一个修辞符号,永久地镌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