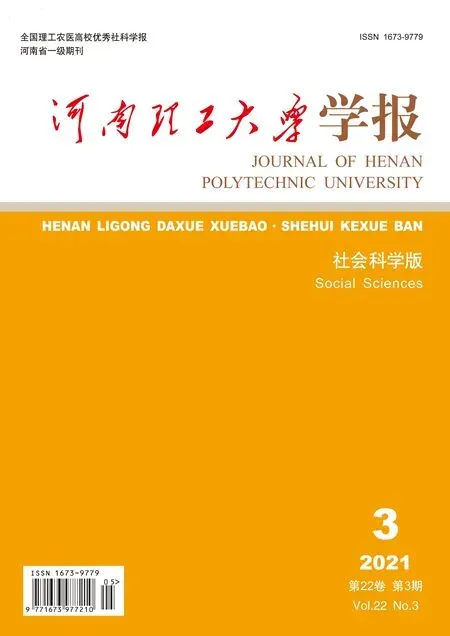《农政全书》贵州粮署本刊印者任树森考述
2021-04-29熊帝兵
熊帝兵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农学经典文献,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平露堂本(有学者简称为“平本”)首刊之后,产生了十多个不同版本,贵州粮署本(有学者称之为“黔本”)就是其中一个出现较早,且具有代表性的版本,在《农政全书》的流传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此本系道光十七年(1837年)贵州通省清军粮储兼巡道任树森所刊。学者在梳理或者研究《农政全书》的版本时,常言及此本[1],然而其刊印者任树森,以及该本的刊印过程及其价值却多被忽略。石声汉在《农政全书校注》之“附录”中收录了平露堂本的5篇原序和贵州粮署本之《任树森序》,但是并未对任树森施注,因此未涉及任氏生平信息[2]1811-1812。故此,本文拟以此序为线索,结合地方志的记载,略考任树森其人以及其在贵州任职期间推广棉业技术、撰写、刊刻农书的事迹,兼述贵州粮署本《农政全书》的历史地位。
一、任树森家世生平考
由贵州粮署本《农政全书》之《任树森序》落款时间可知任树森约生活于清代嘉庆至道光年间,其在落款署名前冠以“新息”二字,“新息”乃河南省息县之古称。由于自身的历史影响力有限,大型文献和重要典籍对任树森的生平事迹均无载录,相关信息主要存于地方志中。光绪《续修息县志》中存有任氏小传,称任树森,字季兰,号芗圃,息县白里人。任树森的父亲、任氏本人及其长子皆举进士[3],可谓当地名门。
任树森的父亲任泽和,字恊子(《续修息县志》称其字介子),号蕙堂[4],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曾官浙江新昌令、嘉善令、海盐令等,所至一方,多施善政,光绪《续修息县志》载:“选浙江新昌令。或言:‘新昌官贫,奈何?’笑曰:‘官宜求富乎?’为治一年,民乐其政。旋权嘉善令,移海盐令。”[3]为官浙江期间,任泽和曾减漕费、苏民困、兴书院、赈灾害、浚城河与湖泊等,颇受百姓爱戴,官至严州知府,后移守嘉兴。卒年七十。
任树森自幼随父任,“读书聪颖过人,举进士,签分户部主事”[3]。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其名列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庚辰科三甲143名之中[5]。任氏性极孝,“居父母丧,皆哀毁,庐墓。服阕后仍官户部”。后历任陕西、云南、福建等地,曾简放贵州粮储道。为官贵州期间,“平反冤狱甚多……仁怀县穆逆聚党破县城,即率五百人扼贼去路,得扑灭焉。以军功加随带二级,又以边俸加按察使衔”[3]。但是,后因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每忤抚宪意,遂引病归”。归里以后,尽自己所能,服务乡里,“值荒乱,出家资以济乡闾,议团练以御贼匪”。深受息县知县赞赏。任氏长子任为琦由进士官广东肇庆知府,升任福建汀漳龙道[3]。
任树森虽为进士,但是相比于清代同时期的林则徐、魏源、龚自珍、贺长龄等社会精英来说,其学识、仕历与政绩并不显赫,或许正因为如此,学者论及其人者甚少。《中国古今工具书大辞典》收录《种棉法》词条,言其撰者为任树森,以30余字介绍了《种棉法》[6];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著录了任树森《种棉法》一书,并撰写了百余字的简短提要,对任树森生平事迹言之甚少,重点亦在论书[7];王永厚在介绍褚华的《木棉谱》时,顺便提及道光十八年(1838年)任树森的贵州重刊本,约二百余字,几乎没有述及任氏生平[8]。
王达先生的《中国明清时期农书总目(续)》中“大田作物”类第425条为:“植棉解惑 清·任树森 1837 存 与褚华《木棉谱》合刊。”[9]王达说任树森所刊的褚华《木棉谱》年份为1837年,即道光十七年。除了王达此说之外,尚未查到该年的这一刊本。任树森刊褚氏《木棉谱》刻于1838年,即道光十八年。《中国农业古籍目录》著录了国内现存的褚氏《木棉谱》的10个不同版本[10]67-68,外加藏于日本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墨海金壶本[10]274,其中没有王达所说的道光十七年本,但是在上述11个版本中,含有道光十八年本。
任树森刊道光十八年本褚氏《木棉谱》,首置三篇与植棉相关的文论,其中第一篇无标题,以文代序,为任树森所撰,版心题“种棉法”三个字,文末未署时间。第二篇有标题为“辨惑”,版心亦作“辨惑”,该篇末署“道光十七年冬新息芗圃氏任树森识”。由此可见,两文的标题分别应该为《种棉法》和《辨惑》。而且多部贵州地方志都收录了上述两文,题名皆为《种棉法》和《辨惑》(具体详后)。第三篇题为《劝邵武属四县民种木棉说》,系青浦籍在闽官员陆我嵩于道光十五年在闽重刊褚氏《木棉谱》所撰,该文之后,任树森手署“道光十八年正月立春日督理贵州通省清军粮储道新息任树森重刊以示黔民[11]”。综上,王达很可能误把《辨惑》篇的撰写时间认定为整部书的刊刻时间;而且,王达所说的“植棉解惑”不知所从何据,很有可能是王达综合《种棉法》《辨惑》两文另取的书名。总体上,就现有学者所言及任达的文字来看,显然还存在不少问题,而且未能清晰地揭示出其主要贡献。
任树森虽然历任多地,但是主要事迹却集中于任职贵州通省清军粮储道期间,任树森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担任此职,贺长龄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巡抚贵州,二人多有往来与协作。贺长龄在《现办桑棉纺织各情形折》和《试种桑秧木棉教民纺织折》等多份奏折中都论及任树森在贵州推广棉桑的事迹,贺长龄还曾应任氏之约,撰写《任芗圃观察重刻棉花图记》一文,而任树森在《农政全书》贵州粮署刻本序中亦盛赞贺长龄在贵州的政绩,以及推荐《农政全书》之功,可见二人关系密切。但是光绪《续修息县志》纂修粗糙,仅言任树森在贵州平反冤狱和扑灭仁怀县穆逆聚党之事,其它则以“凡教养有利于民者,务捐廉以成其事”一言概括之[3],未能全面总结任树森在贵州的主要事迹。
二、任树森在黔推广技术事迹考
任树森到任贵州时,发现百姓“谋衣艰于谋食”。当地虽然也有棉花生产,但棉花质量较之内地相去甚远,“土产木棉色黄而绒薄,为绵不暖,为布不结。殷实家所用白绵多来自远方,贫者莫办焉”[11]。《种棉法》贺长龄也曾得出类似认识,他说:“黔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贫,女红不勤,谋衣艰于谋食。”[12]贺长龄还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臣惟桑棉为衣被之大利,而黔省向不多种者,一则土棉之种不佳,但能织成粗布……故民间谋衣艰于谋食。一则种植未能如法,以致木棉或花而不实……辄为土地而不宜,因所畏难中阻。”[13]164指出了阻碍贵州棉花生产的三个关键性因素为:一是棉种不佳;二是种植技术不得法;三是土地不宜的观念根深蒂固。
任树森通过考察之后,对贵州地方流传的地土、天时不宜观念进行了反驳,在其《辨惑》一文中引用了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驳风土不宜之的内容,结合棉花种植已经遍布福建、陕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等数省不同土壤、不同气候的事实,提出了贵州棉业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地土不宜,而是棉种不佳所致。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的确提到过棉花因地域不同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异,但同时也指出,这种变异对棉花技术的推广影响不大,可以通过定期更新棉种的方式加以克服,“嘉种移植,间有渐变者;如吉贝子色黑者渐白,绵重者渐轻也。然在近地,不妨岁购种;稍远者,不妨数岁一购。其所由变者,大半因种法不合;间因天时水旱;其缘地方而变者,十有一二耳”[2]961。任氏在引述并肯定徐氏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应对可能性变异的办法,“若隔岁而变,则岁购种他方;数岁而变,则数岁一购种他方”[11]。
为了解决土棉棉种不佳的问题,任树森从棉花种植发达地区引进优质种源。道光十七年(1837年)秋,“驰书同年刘芾林(名荫堂,贵州清平人,现官河南光州),嘱购木棉子送黔”[11]。以供其试种,据贺长龄的《试种桑秧木棉教民纺织折》奏折可知,任树森所引进的棉种达二万六千一百余斤[13]153。依据相关史料记载,任树森的此次试种的结果颇为成功。此后,任树森又进行了大力推广,贺长龄在另一份奏折中说:“该道又以土棉之种不佳,因于楚、豫两省购回棉子,散给各属,择其地之相宜者,教民栽种。并于附近郭地雇人种植数亩,教以按候锄治之法,数年以来,开花结果与楚豫等省无异。”[13]165
为了克服种植技术不得法的难题,任树森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贵州重刊了褚华的《木棉谱》。此书乃是清代棉花生产的代表之作,棉花种植与加工的关键技术尽收其中,涉及辨种、选种,棉田耕作、壅粪、播种,轮作、换茬、种植密度等技术细节;采花、轧花、弹花、纺纱、织染等加工工序以及所涉工具论述亦详,为当时棉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的植棉技术总结。此书在贵州的重刊,对促进当地的棉业生产无疑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褚华原书,“辞繁而文,愚氓不之省也”。并不适合当时文化还欠发达的贵州百姓阅读,为浅显起见,任树森“以俗语撮其要附焉,间有所见今俗,与古书略异者参焉”。结合其自己亲眼所见的河南省植棉经验及习俗,改写成了《种棉法》一文。改写后的文字,是一篇近似白话文的植棉技术说明,现摘其句以示:“……种棉的时候,清明前最好,清明后亦可。河南俗语云:‘清明前十天不早,后十天不迟’,这是去年收秋后不种之地,叫作‘春花’。天时、地力、人功都好,每亩可以收三百斤……”[11]
《种棉法》解决了棉花的土壤选择、下种时间、田间管理及天气环境要求等;逐一阐述了棉花生产的各个技术环节,文末附黔中未见之植棉关键工具——锄,绘图配以文字,说明其构造、功能及使用方法。浅显的白话文虽然制约了其本身的学术性,但是对于当时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少数民族聚居的贵州百姓来说,无疑减小了棉业技术推广过程中的语言障碍,技术推广的实效显然优于官样化很浓的文言文。任树森将《种棉法》《辨惑》以及陆我嵩的《劝邵武属四县民种木棉说》三文合刊在褚华《木棉谱》之首,全书包含了上海、河南、福建三个不同地域的植棉经验总结,涉及到思想观念的突破,技术的融合以及工具的使用等诸多内容。另据贺长龄所撰的《任芗圃观察重刻棉花图记》一文中可知,任树森推广植棉技术取得初步成效以后,“又敬镌纯庙《棉华图》勒石贵山书院,以坚民信而垂永利,且属长龄为之记”[13]437。任树森刻纯庙《棉华图》于石上①(1)①纯庙《棉华图》即《御题棉华图》,是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绘制的一套从植棉、管理到织纺、织染成布全过程的棉花图谱,属于“耕织图”的一种,是中国古代特殊形式的农书。,一方面可以使《棉华图》以碑刻的形式被长期保存,另一方面,百姓也可以通过现场观石揣摩,或者制作拓印流传。勒石虽然不能像刊印书籍那样广泛流传,但是对植棉技术的推广也具有一定作用。
三、《农政全书》贵州粮署本的刊刻及影响
《农政全书》在徐光启生前并未刊行,徐光启逝后,在陈子龙、张国维、方岳贡的努力下首次刻印,即平露堂本。据梁家勉先生研究,终明一代,没有另版刊行过,而且历经明清的朝代更替,“撰述者本人著述,横遭统治者明令禁毁,这一书的流传,连带遭受影响”[14]。原刻本愈来愈少,乃至距徐光启时代较近,且足迹较广的刘献廷都曾说:“徐玄扈先生有《农政全书》,余求之十余年,更不可得。”[15]尽管刘献廷最终于无意中得到此书,但求之十年,足见其在清前期的难得程度。多种因素导致从清顺治初年到道光中期的约两百年时间内,除了《四库全书》本以外,未闻有过《农政全书》之另版刊行。而且原来的版片失传,甚至藏书家也藏者甚少[16]。可见,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农政全书》极不易得,从而影响了其在更大范围的传播。
道光十七年(1837年),《农政全书》一本难求的状况发生了改变。贺长龄巡抚贵州,在社会治理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向同僚出示并推荐了《农政全书》。其在《通饬民事宜勤札》中强调了该书的价值,并要求贵阳府将其刊印,分发给各地不同级别的官员,让他们向借助各种机会,向当地百姓讲解书中的内容:“黔省树艺无法,穑事卤葬,尤宜以是书导之先路。有志勤民者,自当案置一编,不时翻阅,遇朔望宣读圣谕之时,即与士民一同讲习;或听讼,或下乡,并当进吾父老,面与解说,使知因地因时,精其具,善其法,勤力以收自然之利,方为无负此官。……凡我臣僚,所宜敬谨服膺,实力从事者也。现饬贵阳府将《农政全书》刷印若干部,发给府、厅、州、县、州同、州判,暨分驻县丞、经历、巡检,凡有地方之责者各一部,俾得加意讨论,与吾民率作兴事。”[13]363
与贺长龄乡呼应,任树森在其刊印的《农政全书》序中则描述了贺长龄“示书”的过程:“道光丙申秋,中丞善化贺公来抚黔,董属吏,勤听断,严缉捕,实仓储,兴学校,仕风骎骎丕变。数月,出此书示僚曰:急则治标,今讼狱稍息,攮窃稍戢,是不可不图其本也,是书尽之。”所谓“此书”即《农政全书》。任树森阅后盛赞之:“诚人人取是书,讲明而切究之,器有必完也,法有必悉也,种有必备也。……中丞出是书,非徒供僚属之览也,其各究心以教吾民,而又师之宽然得自力于农焉,则是书之刻不虚矣。”[2]1811-1812任树森遂将《农政全书》在贵州作序刊行,即贵州粮署本。
任树森所刊的贵州粮署本是《农政全书》在清代较早的版本。此前,尽管《四库全书》中收有《农政全书》(即四库本),但是其并不利于该书的广泛流传。就实际传播而言,贵州粮署本紧列于平露堂本之后,比王寿康的曙海楼刻本早五年。贵州粮署本首载任树森序,次辑平露堂本序及凡例。对比平露堂本和贵州粮署本,其行数、字数都相同,只是贵州粮署本采用的是笔画较粗的楷书体,而平露堂本的明朝字体特征明显。石声汉认为贵州粮署本的刊印依据了平露堂本,而稍有修改[2]6。全书中的“玄扈”皆作“元扈”,想必并非任树森大意,很可能是为了避康熙皇帝玄烨讳。从校订情况看,贵州粮署本不是很好,错字较多,部分插图与原刻有异,且删去了平露堂本文句旁的密点或密圈。
贵州粮署本虽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亦有可圈可点之处,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尽管平露堂本是首刊本,但是由于其篇幅较大,且付刻倥偬,校勘亦有欠详审之处。贵州粮署本对平露堂本中的不当之处,也有所校改,例如:平露堂本之“农本”引冯应京《国朝重农考》之“籍余烈以休养”,贵州粮署本就改“籍”为“藉”;“务本之训,傳自文皇”,贵州粮署本改“傳”为“传”等。
在平露堂本极其难求的情况下,贵州粮署本刊行之后,显然承担了清代中期以后直至民国的通行本角色。同治十三年(1874年)刊印的山东书局本即是据贵州粮署本的重新刻版;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又据山东书局本剪贴影印。195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邹树文等校订的《农政全书》上下二册,“主要依照平本。遇有平本显然错误,而黔本或曙本(上海曙海楼本)的修改较胜的,则依照黔本或曙本改正”[17]。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石声汉的《农政全书校注》,石声汉先生校订的办法是:“用鲁本原书剪贴,以平本为基础,参照其他版本校订。”[2]6石声汉所谓的“鲁本”即同治十三年(1874年)山东书局本。此间,虽然出了祖于平露堂本的曙海楼本,和以曙海楼本为底本的文海书局版及求实学斋版,但其影响均不及贵州粮署本。《农政全书》主要版本关系可以如图1所示。

图1 《农政全书》主要版本关系示意图①(2)①此图参考了梁家勉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其基础上加以改进,删去了其“河北伪燕京道版”之不确定关系,增加了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本,示意方式亦有所改进。梁家勉图见于《〈农政全书〉撰述过程及若干有关问题的探讨》,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编:《徐光启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8页)。
由图1可见,贵州粮署本是清代《农政全书》较早的本子,对《农政全书》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在较长时期内担当了《农政全书》通行本底本的角色。后世《农政全书》万有文库本、中华书局本和石声汉校注本等,虽然未直接以贵州粮署本为底本,但是在他们校勘的过程中亦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四、余 论
事实证明,任树森在贵州的植棉技术推广取得了较大成功,贺长龄说:“该道又督饬贵阳府贵筑县,于省城南门外设局雇匠,教民纺织,并令及幼堂之幼童一体学习,俾将来糊口有资。其尚节堂之嫠妇,则另延女师教之。该道又不时亲往稽查,现在织成之布较之贩自客商者,价贱而易售。小民趋利若鹜,省城纺织者已不下数百家,各属亦闻风兴起。而惟思南府及所属安化、婺川两县,劝办最为踊跃。”[13]165光绪《黎平府志》卷三《棉事》全文收录了《种棉法》[18];民国《都匀县志稿》卷六《农桑物产》之“棉业”转引了其主要内容[19];民国《余庆县志》之“种棉”亦录自《种棉说》[20];民国《甕安县志》卷十四收录了《种棉说》和《辨惑》[21]。诸多贵州地方志对任树森植棉文的收录足以反映出其在当地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除了推广棉业技术,刊印棉花种植书籍与《农政全书》以外,据相关文献记载,任树森任职贵州期间,还积极推广蚕桑技术。贺长龄在奏折中曾简要介绍过任树森推广蚕桑的经过:“(桑树)种植未能如法,以致桑条虽长而不茂。方种桑之始,黔者皆系插条,而蟠根不坚,枝叶未能畅茂,该道(粮储道)因于省城附近之外治地两区,令以椹子试种,破觉根固枝繁,易于长发。计十七年(1837年)至今,共成活三万余株,均陆续令民种于宅畔山边以普其利。”[13]165贺长龄在另一份奏折中说:“十八年春间先于省城附近隙地试种桑秧数万株,长至二三尺时,听民移种。”另外,据贺长龄称:“臣于道光十七年督同藩司庆禄、粮储道任树森刊发《蚕桑编》《木棉谱》,通颁各属,教民栽种,以冀渐知纺织。”[13]153从中可见,任树森在贵州推广蚕桑技术的同时,还刊印了《蚕桑编》一书,但是未能考证出其具体为哪部著作。
相较于同时期的封疆大吏和历史名臣来说,任树森的职位与影响都不高。但是通过史料梳理和深入研究可见,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在很好地履行其自身职责的同时,与贺长龄这样的社会精英产生了合作的机会,形成交集,乃至在《农政全书》传承的特殊历史节点上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学界的视野在关注徐光启、《农政全书》、贺长龄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其中次要历史人物存在的价值和作用。次要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有限,制约了学界对此类人物的关注度,但是史籍既然对其有所载录,说明其还不至于小到应该被历史遗忘的程度。学界对此类历史人物可以不重视,但不应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