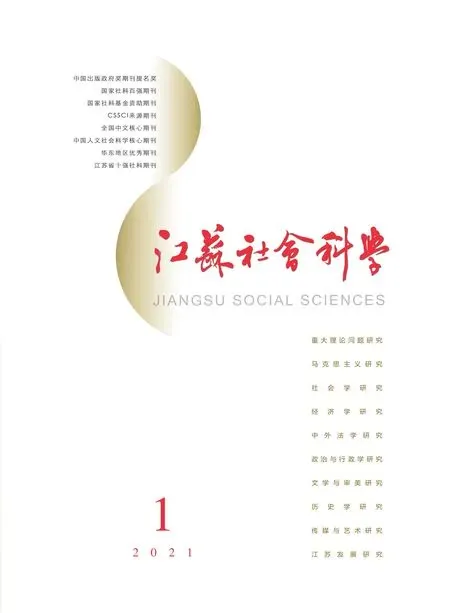任道与任情共生
——审美现代性视域下泰州学派的“身”“道”两难
2021-03-20
内容提要 在明代“身”与“道”崩裂的时代难题下,泰州学派标举知行合一、践履儒家道统、突出士人之“身”的自觉反思意识,在“身”“道”互动中重塑士人主体的审美感知经验——自任于道的担当意识、恃道持道的自尊自信以及觉民行道的极致乐感。而越是自觉地践履儒家审美理想的“身”“道”一贯性,则“身”“道”两难带来的风险累积越盛,“任道”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害身”“杀身”。在对“任道”后果无法回避的自觉体认中,泰州学派反向强化了“爱身”“保身”的私性自主意识,从而加速了任情纵欲等自然情性话语的“旅行”,促成了中国审美现代性独特的双重指征:任道与任情共生。
近年来,学界对明中叶泰州学派由王艮开启的身本论思想已有诸多讨论,讨论中一直存在着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自然情性说,即蔑弃礼法、张扬自然人性。清初大儒如黄宗羲、顾炎武,现代学者如嵇文甫、吕思勉等持此观点。因其类似禅宗心性自由和顿悟一途而有过之,故曰“狂禅”。另一种是弘道笃行说,即身肩儒家道义理想、在做事上笃行超迈。明末学者如顾宪成,当代学者如左东岭、邓志峰等强调这种观点。因其类似侠的狂放雄豪而更有过之,故称其“狂侠”。对此分歧,有识之士敏感地意识到,泰州学派的身本论充满矛盾:“最可怪的是中国史上为真理而杀身的人少之又少,而这几个极少的人乃出在这个提倡‘安身’‘保身’的学派里——何心隐与李贽!”[1]胡适:《胡适日记全编》3,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6页。但仅仅指出现象,缺乏进一步的阐释。
那么泰州学派是开创了布衣士人以身任道的豪杰作风,还是开启了明中晚叶纵情任性的心性自然风气?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对泰州学派“尊身即尊道”的身道观的理解。由于“身”能感知、有欲念、会思考,还能够付诸行动,这一范畴与人的主体能动性密切相关。“身”的主体能动性一旦获得解放,其所蕴含的诸多可能性,比如以身任道或者任情纵欲等等,就会转变为现实性。
笔者拟采用审美现代性的视角梳理泰州学派的身道观,因为审美现代性提供了理解泰州学派身道观的新视域和理论支点——以人的主体性伸张为关切点,结合泰州学派士人以身任道、知行合一的讲学实践解读其身道观。审美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一般认为,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社会性质、文化特征以及观念意识都发生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化。这种使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诸种属性和特质就是现代性。而审美现代性指的是与传统告别的断裂意识、依靠自我的独立思考、朝向未来的进化意识,以及对此形成的自觉感知和审美判断。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在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经验中,确立自我的问题日益突出,因为时代经验的视界集中到了分散的、摆脱日常习俗的主体性头上。”[1]〔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也就是说,就个体肉身层面而言,审美现代性的关键问题是在丰富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发展人的主体能力、意识活动,进而提升人的审美感知经验。泰州学派身道观中隐含的任道与任情的主体性与审美现代性的自我感知较为相契,而这也是推动明中晚叶文艺新思潮到来的一大动因。
一、“尊身即尊道”与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
王艮(1483—1541)在民间广设杏坛,以布衣讲学著称。他针对弟子的疑惑随机加以点拨和启发,其中涉及“身”的言语很多。王艮论及“身”的话语可以归总为三类:一是从正面申说“身”之于家国天下的意义,如“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吾身犹矩”“修身”“立吾身”等;二是强调肉体之“身”的安全是所有一切的前提和基础,需要“安身”“明哲保身”;三是反对流行的错误做法,不仅要警惕“害身”“杀身”“危其身”等对个体生命的漠视和戕害,也反对疏离社会、独善其身的“洁其身”。总之,在流传至今的文本中,王艮在不同场合对尊身与尊道两方面都有所强调:人人皆有“身”,首先要满足肉身的基本物质需求,爱身保身,这是生命保存和延续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满足“身”的精神需求,“身”会感知、能行动、有感情,具有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是践行仁义礼智之“道”的意识和行为主体。否则,“知安身而不知行道,知行道而不知安身,俱失一偏”[2]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换言之,“身”的价值存在于“身”与“道”的关系之中。
可惜的是,王艮存世的文本已然经过了弟子及后人多次编纂加工,早已不复是师门问答的原貌,加之师友问答的话语原境缺失,针对何人、何事,缘何而发?寻觅王艮每次言语行为的原意几乎不可能。泰州学派门下弟子人数众多,遍布社会各阶层,除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员,还有耕、樵、渔、盐、陶、僧、道等各色人等,同一句话是针对布衣学者还是针对官员学者,其语义差别会很大。对于那些惨遭苛捐杂税盘剥、终日为衣食奔波劳碌的平民弟子而言,排在保身安身第一位的就是温饱;但是对于身在仕途的弟子来说,安身保身就不是温饱那么简单了。本文仅以有较为可靠史料为依据的论说展开。
王艮与弟子徐樾(?—1551)围绕“尊身”“尊道”,有过多次讨论。徐樾,字子直,是王艮的弟子,他分别于1528 年、1531 年、1539 年面会王艮,得其口传、心授,数年间书信问道不绝。仕途上他一帆风顺,屡屡获得升迁,《明史》《明儒学案》中都记载了其人其事[3]据《明史》徐樾条下:“历官云南左布政使。元江土酋那鉴反,诈降。樾信之,抵其城下,死焉。”(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册,第7275页)所言较为简略,似有所避讳。另见黄宗羲《明儒学案》(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24页),交代较为详细。1550年元江府土酋那鉴谋反,杀害知府那宪,攻陷州县。朝廷派兵征讨,总兵沐朝弼与巡抚石简会师,分五路进击。那鉴派人到监军佥事王养浩处称愿意投降,王养浩疑其有诈不敢前往受降。徐樾官至云南左布政使,布政使司专责民政事务,且他被派到军中承担的职责是监督军饷,因此受降不是他的职分,但他慨然请行。到达元江府南门外,那鉴没有出迎,徐樾就大声呵问,早已埋伏在此的叛军起而害之。姚安土官高鹄拼死相救,也遇害。那鉴叛乱一直没有平定,1553年那鉴死亡,其他土酋纳贡大象赎罪,嘉靖帝同意息兵。。相对明确的语境对于理解“身”“道”难题非常必要。王艮对徐樾说道:“身与道原是一件。圣人以道济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者身也。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1]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从道尊身尊不可分割的原则性关系论“身”与“道”,看上去既周全又老套,带有理想主义气息。王艮援引《孟子·尽心上》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2]《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影印本),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70页。(作者按:“殉”作“从”讲。)以道从身,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得到张扬,必要条件是天子行善政;反之,恶政横行则以身从道。朱熹顺势推论:“身出则道在必行,道屈则身在必退,以死相从而不离也。”[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0页。指出治统有善政有恶政,“身”之出处进退,伤身害身杀身的风险隐匿其中。王艮对徐樾寄予传承道统的远大期望,故“身”“道”之间不能有任何闪失。随着徐樾在仕途上不断发展,这种担忧愈发明显:“幸得旧冬一会,子直闻我至尊者道,至尊者身,然后与道合一,随时即欲解官,善道于此可见。吾子直果能信道之笃,乃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凡近所能及也。又闻别后沿途欣欣,自叹自庆,但出处进退未及细细讲论,吾心犹以为忧也。”[4]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徐樾虽曾有心脱离仕途,但身不由己,不想后来竟遇害。
可见“尊身”与“尊道”的矛盾焦点集中在治统与道统的撕扯上。“身尊即道尊”赋予“身”的自我理解以崇高的价值感,因为这里的“身”是道统的弘扬主体士人之“身”。泰州学派以讲学著称,讲学是对他们自任为儒家道统的传承者和维护者的士人身份的确认,士人有自身引以为自豪的道德体系和评判标准,仁义礼智信、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些都属于儒家道统的学问。王艮引孟子“以道殉(从)身”,说明“身”是能弘道的士人主体之身,适用于治统与道统关系融洽的政治生态;而“以道从人”,一字之差,差之千里,意味着“身”与“道”都被动地听命于有权势之人,连自己都无法获得自尊自信,如何使别人对自己尊信?如果坚持身与道的主体性,则招致侮辱或危险,“身”之不存,“道”将焉附!
由于泰州学派以行动见长,王艮等人在讲学弘道中践行自己的理想观念,更进一步激化了道统与治统撕扯中的身道矛盾。这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他讲学不论贤愚,广大平民百姓甚至愚夫愚妇,都纳入了弘道之“身”的可能范围,“身”具有了远远超出传统士人阶层的普遍性、广泛性,也就是说“身”具有了复数的内涵外延;二是他出身于盐丁,以一介布衣身份毅然以弘道自任,在民间讲学,取消束缚自我之“身”行动力的名位限制,从自我之“身”的角度,极大拓展了个体的主体能动性空间;三是他没有学而优则仕,没有进入统治集团,依然为地方政务积极建言立策,参与家国大事,赋予“身”以自觉主动地参与家国大事的主体能动性。他认为,当道统被治统挤压时,就明智地选择退隐,但这退隐不是隐士高人的独善其身,而是在治统鞭长莫及的乡村一隅继续践行道统。必须承认,身尊道尊在民间语境中或许有践行的可行性,但稍有逾越则面临两难困境,“身尊即道尊”说无法摆脱治统的干扰和辖制,本身潜伏着害身杀身的极大风险。
王艮开创淮南格物说倡导“明哲保身”,态度鲜明地反对乡民割股疗亲之类极端孝亲行为。但是在其父守庵公93岁高龄无疾而终时,王艮恪守孝道,“天大寒,先生冒寒筑茔埒,由是构寒疾”[5]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因尽孝而伤身,英年早逝。时人李贽称赞他是气刚骨强的“真英雄”。继承王艮气骨的弟子指不胜屈:“山农(颜钧)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波石(徐樾)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心隐(何心隐)以布衣出头倡道而遭横死”[6]李贽:《焚书注》,张建业、张岱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页。。李贽提及的这些泰州学派的“英灵汉子”,因为尊道或不见容于世,或伤身、害身、杀身,而李贽本人亦遭迫害而身亡。清代黄宗羲的评论颇能代表后人的质疑和不解:“人即不敢以喜功议先生,其于尊身之道,则有间矣。”[1]黄宗羲:《明儒学案》,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25页。
面对各种风险的潜在威胁,王艮的尊身即尊道说为何还能赢得广泛拥趸、一度“风行天下”[2]黄宗羲:《明儒学案》,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3页。?因为它恰恰应对了明代社会人心的整体性困惑,即“以道殉(从)人”带来的士人自我价值失落的严重精神危机。众所周知,自朱熹卒后,他生前圈定的孔孟文本被科举采用,儒学在明代已经彻底变质,沦为科举考试的工具。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知识,本应给读书人带来佼佼不群的儒家教养、道德能力,在科举制度下矮化为获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加之商品经济的勃兴,“功利陷溺人心”[3]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集体层面的道德虚伪腐蚀了士人的自我价值。一方面放逐儒家审美中一切崇高的意味,与“道”背道而驰。社会心理被权势和金钱带入穷途,独善其身也不可能:“今人只为自幼便将功利诱坏心术,所以夹带病根终身,无出头处。”[4]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而儒家一旦剥落了真诚的道德意味和神圣的道德象征,就流于苍白贫乏,魅力尽失。另一方面,在儒家伦理道德走向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士人出于唯恐被社会排斥成为异类的肤浅动机,而一味顺应迎合、和光同尘,放弃自觉思考使得士人感知钝化、异化,压抑扭曲自我,士人之为士人的自我价值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总而言之,士人的主体性感知与儒家道德的象征意义脱离,身与道裂变、扭曲和背离,从根基上动摇了“身”的感知、判断和理解。因此,泰州学派弘扬身尊即道尊,具有应对儒家现实困境的意义,即抵抗道统被工具理性化,试图恢复道统的终极性价值地位,激活个体之“身”的主体能动性,在身尊即道尊的关联中,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士人自我价值。
二、身与道“本末一贯”之中的自我本位
如上文所论,在“身”与“道”的关系中,弘道的使命感赋予人自身以意义和价值。千百年来,冒着杀身、灭族的危险,文死谏、武死战之士不绝如缕,“身”成为捍卫道统或维持治统的工具。相形之下,泰州学派弘扬的身道关系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简言之,就是在身与道“本末一贯”的关系中,以“身”为本,确立人“身”的自我本位,重视人的肉身感受和需要,“身”中有情、有欲、有意志,王艮确立“身”的自我本位,也打开了通往自然人性论的关隘。
所谓身与道“本末一贯”,是就以身行道的方法而言。“学问须先知有个把柄,然后用功不差。本末原拆不开,凡于天下事,必先要知本。如我不欲人之加诸我,是安身也,立本也,明德止至善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是所以安人也,安天下也,不遗末也,亲民止至善也。”[5]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学者对此有本体论还是工夫论的不同看法。笔者认为,本体与工夫都统一于践履行动,这是由身道合一的关系决定的。探究身道关系,不是为了谈玄论道,而是为了解决以“身”践履“道”的实际问题,而解决问题必须有个可操作性强的“把柄”好下手,以“身”为本下工夫,见效简易直接。这符合王艮重视践履的一贯品格。他比较强调践履方法而不愿在体用问题上纠缠。后学罗汝芳所论甚是分明:“……阳明多得之觉悟,心斋多得之践履。要之,觉悟透,则所行自纯;践履熟,则所知自妙,故二先生俱称贤圣。”[6]《罗汝芳集》,方祖猷、梁一群、李庆龙等编校整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身道“本末一贯”整合了传统已有的两种路径:一是道德认知上恢复儒家“道”统真诚合法地位,强调审美中“道”的纯正道德象征;二是道德情感上渲染仁义礼智根于心的想象,能知即能行。阳明破解知行分离的难题,由通透高明的觉悟入手,打通道德认知、道德情感与道德实践,将知行合一;王艮则从简易直接的践履入手,打通知行,认为身与道“本末一贯”。
“本末一贯”语出王艮《明哲保身论》:“知保身而不知爱人,……此自私之辈,不知‘本末一贯’者也。若夫知爱人而不知爱身,……此忘本逐末之徒,‘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1]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大学》有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王艮在践履“身-物”或者“身-天下”关系,具体在处理“安身-亲民”、“保身-爱人”以及个人的“出-处”或“进-退”问题上,都秉持以“身”为本的原则。
“本末一贯”包含三层意思:其一,“一贯”者,强调“本”与“末”是浑然的统一体,由本及末,一通俱通。新儒家代表唐君毅深刻地指出:“然心斋亦言安身保身,所以保家保国保天下,则亦不可即谓心斋只为自安自保其身,而言爱人也。观心斋言之本旨,唯在重此身之为本,以达于家国天下,而通此物之本末;遂知此身与家国天下,互为根据以存在。”[2]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本与末互为根据而存在,颇含辩证意味。道之实现不能脱离身之践履,安身保身之价值必须在道之价值实现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否则一味保身安身,就背离了王艮的初衷。
其二,“身-道”又在发生次序上具有本末属性,是含有本末之别的浑融一贯。此处的“本末”,是指关系上有本末之别,遂有知行方面主次、轻重、大小、急缓的若干差别,这种差别若不加约束就会导致“身”与“道”分道扬镳。这里的“一贯”,是指关系上浑融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根据、互为参证。“知‘明明德’而不知‘亲民’,遗末也,非‘万物一体之德’也。知‘明德’‘亲民’而不知‘安身’,失本也,‘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亦莫之能‘亲民’也。知‘安身’而不知‘明明德’‘亲民’,亦非所谓‘立本’也。”[3]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若无本末之别,关系中无主无次、无明无暗,终将走上虚无之途,招致观空证虚之病。若无一贯关系的包容涵摄,“身-道”关系崩裂,则将带来两种后果:或者偏重安身保身,开临难苟免之隙;或者辱身害身,于道无补,招致杀身之憾。王艮以践履道统之身为“本”,以身体力行的道统为“末”,凸显出践履道统过程中以自我为本位的主体性倾向。
其三,由于“身-道”关系浑融一贯又有本末之别,以“身”为本的主体性力量向外部世界辐射。于是,身-物、身-心、身-家-国-天下、学-师友等诸多有着本末之别的事象不断被裹挟进来。身体作为诸多关系的根本原点,由个人安身、保身、修身的良知本性——此之谓不“失本”,向外扩展到家族、社群、国家、天下万物——此之谓不“遗末”[4]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尤其强化了个人与他人的伦理道德关系和伦理道德实践。因此,个人自身的独特价值必须凭借对于群体自觉、天下重任的担当才能彰显出来,服膺“道”的理想信念而不受专制权威的宰制,自我内蕴的良知良能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也就是“道”发扬光大的限度。
概言之,“身”与“道”的本末一贯关系,虽有本末之分,但无主客之别,也即是说,“身”与“道”都是践履行为中的主体,二者构成主体交互性关系。在本末一贯关系中的个人之“身”,是行动主体,具有撼天动地的气魄与潜在能力,能够对儒学在现实中的异化走向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回归孔子为士人确立的“士志于道”;而作为行动对象与价值归宿之“道”,是价值主体,是士人之“身”觉醒的方向,“道”只有在士人之“身”上才能得以现实化。“身”的尊严不取决于外在的富贵利禄,而在努力增进修养、成己成人。在“身”与“道”这两个主体之间,构建起双向互动的主体间关系。
众所周知,心学以“心”为本体,王艮亦然,但他又另立“身”为本——在践履“道”的过程中本末一贯的“本”。那么本体论意义上的“心”与方法论意义上的“身”之间是什么关系?王艮道:“然心之本体,原着不得纤毫意思的,才着意思便有所‘恐惧’,便是‘助长’,如何谓之‘正心’?是诚意工夫犹未妥贴,必须‘扫荡清宁’,‘无意、无必’,‘不忘、不助’,是他‘真体存’,‘存’才是正心。然则‘正心’固不在‘诚意’内,亦不在‘诚意’外,若要‘诚意’,却先须知得个本在吾身,然后不做差了,又不是‘致知’了,便是‘诚意’。……所谓‘正心在诚其意者’,是‘诚意毋自欺’之说,只是实实落落在我身上做工夫。”[1]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这里的“心”本体关联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作为真善美本原以及乐感本原的心体或本心,是建立在感知觉基础上、又不受感知觉限制的主宰;二是指肉身的“心”,古人认为心之官则思,是具有感知觉、能思考的心。王艮所谓正心在诚意,就是“实实落落在我身上做工夫”,即“扫荡清宁”,清除各种外在的人为意见,克服功名利禄的诱惑,恢复人的自然本心,也就敞开了“着不得纤毫意思”的心之本体。由于王艮对“心”这两个层面的含义不加区分,将其混成一团,把本心或良知视同本然的知觉,物来自格、善恶自辨就是诚意工夫,崇尚本然知觉的自然情性观已经萌生。
也就是说,在身与道“本末一贯”关系的践履行动中出现了分叉,在弘扬道统、以身任道的主导价值近旁,生长出对人情人性的本然状态保持宽容甚至纵容的另一价值维度。沿着这一路继续发展的早期代表人物有颜钧。他师承王艮,亦因以一介布衣身份张皇弘道、行侠仗义而著称,同时他主张“从心以为性情”。“性”是人特有的性征,“情”是喜怒哀惧爱恶欲等的发动,将“心”体等同于肉身流露的人性、人情。又自创“神莫”一词,指“心之精神与莫能”,是指寄寓在“性情”之中无声无臭、神妙莫测的驱动力,“性”与“情”具体可感,并且“性情也,神莫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2]《颜钧集》,黄宣民点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如此浑融一气,将本然知觉与良知心体搅打成一团,日后自然情性话语的滋生于此已现端倪,遇到某种合适的契机或刺激就会充分伸展。由儒入禅的邓豁渠倡导佛教的放心说,虽然背离了泰州学派自任于道的入世精神,但是他以出离人世的决绝,主张完全释放自然人性,赋予“情”以高度超越性的本体地位,自然情性话语的“旅行”依靠佛教义理的支撑遂能通行无阻。到了著名学者罗汝芳、杨复所弘扬的“赤子之心”,借助三教合一的力量一发而不可收,“心”本体摇身变化成率性天真的“赤子之心”,更何况后来还有李贽著名的“童心”说。至此,“身”的自我理解逐渐走向私性的自我意识,放大了肉身需要,爱身恋身乃至放任不羁。自然人性晃动了传统道德根基。生命的英雄维度和美善价值虽然渐渐失落,但是在自然情性上获得了更为彻底的解放——尊重人的肉身生命,尊重人的自然情感和欲望,尊重弱者和底层民众。而这正是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的基本伦理,也是构成审美现代性的伦理基础。
三、以身任道的独立人格
综上,士人自身主体性发展的必由之路和终极诉求都离不开对“道”的认同,审美现代性的萌生得益于从道统的传统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泰州学派凭借对“道”的自觉体认和主动承当,获得自我反思与自我认同,显示出不同流俗的独立人格,并且“乐”在其中。他们走出书斋讲学、启蒙,知行统一,“立身行道,身立道行”[3]杨起元:《曾子行孝》,《太史杨复所先生证学编》四,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开拓民间社会文化新秩序,试图建立合理的“礼”治秩序。清新刚健的践履行为方式,塑造出士人自信的情感、自觉的人生态度、独立的人格精神。自身自觉的新天地打开了,“所谓个体自觉者,即自觉为具有独立精神之个体,而不与其他个体相同,并处处表现其一己独特之所在,以期为人所认识之义也”[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这种自觉与世俗庸常化、功利化的价值取向有对立、有差异,凸显出士人之“身”的人格独立特征。在审美主体的意识自觉和行动自觉双重意义上,身与道“本末一贯”有助于唤起士人对于崇高、豪杰等的审美感知。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凸显自任于道的主体自觉担当意识。《孟子·万章下》有云:“自任以天下之重也”[5]《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影印本),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40页。,以一己之身把天下的重任担负起来。“以圣人自任”“自任于学”是“以道自任”的不同表达。“以道自任”是从士人形上理想追求的角度概括的;“以圣人自任”则显得比较张狂,是捍卫道统并富有献身精神的先知式人物的自我期许;“自任于学”则是从讲学践履的角度而言,学以闻道,志以成学,学或者讲学的内容都紧密围绕着道统核心。“自任”建立在人人皆有的良知基础上,是自发显露的道德理性,人应当顺其自我的道德本性而行,在个人与“道”的有机演变之间保持动态的同步关系,可以并且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全责。
泰州学派“赤手以搏龙蛇”或“赤身担当”[1][8]黄宗羲:《明儒学案》,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3页。的自任意识,在继承宋明新儒学所强调的“为己之学”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狄百瑞指出:“这个观念与道德生命中的自发思想相应,也与根植于‘为己之学’的道德行为相关。”[2]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弘祺译,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8页。王艮将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的活力归于人肉身本来具备的、知善知恶的良知。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云:“知善知恶是良知”,把道德创造的根源建立在先在超验的心性上。“有善有恶意之动”[3]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意念一经产生,有时为善,有时为恶,有时无所谓善恶,须经过致良知的工夫,使之皆成为善。而王艮的良知良能是所有人先天具有的超验存在,良知即天理,王阳明那里的“致良知”被他悄悄借用、挪移成为“良知致”,意谓良知自然而然就获致了,凸显了良知自然率性即可获得的便利性。王艮主张:“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则知性矣。”[4]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又云:“‘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5]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天理是形上超越的根源,良知涵泳于人的内在心性,天理良知本是一件,按照身与道“本末一贯”的结构关系推论,身体是良知创生之所,属于“本”;良知先于一切知识和学问而存在,把它向人际、社群、国家充拓开来,实现所谓的“天理”,属于“末”,良知和天理都是不假人为、本来固有、自发而为。从“本”的方面来看良知,就是未尝发动、尚未应物接物时的良知。王栋是王艮的子侄辈,其云:“先师(指王艮)说‘物有本末’,言吾身是本,天下国家为末,可见平居与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应时之良知。至于事至物来,推吾身之矩而顺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6]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173页。可见,良知为本,天理为末。如前文已述,本末对举并没有轻忽“末”的意味,事实上泰州学派尤其强调践履不可“遗末”。因此自任于道的主体自觉担当意识乃是自然生成、自发彰显的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没有丝毫的人力勉强,更无须向外格物致知,只须向自身絜矩,安正自身即可。
其次,确认主体恃道持道、自尊自信的深层次审美感知能力。“道”以其形上超越的内在属性给予士人以深刻的自我确信、高尚的尊严。“若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岂能使彼尊信哉?”[7]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身道一贯,让人体验到作为行道主体强烈的自尊自信,自己是家国天下乃至万物的尺度,体认到自身的自由自在,挣脱桎梏并免于屈辱。赵贞吉曾受教于徐樾,他把读书人不能够自信本心的弊病概括为“五蔽”。蔽者,良知本心受外部世界的闻见道理支配,故而被遮蔽。归根结底,“蔽在不信自心”,病根都出在缺乏对自我本来心性的确信。克服自蔽须对症下药,“必先讨去其蔽,而后可与共学”[8]黄宗羲:《明儒学案》,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51—752页。。
人心容易自蔽,因为只要在世、只要行道,就无法摆脱来自他者的毁誉,“君子反求诸身,委曲尽道,世岂有恶之者哉!但在毁誉上弥缝,则便是媚于世耳”[9]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媚于世”还是“委曲尽道”,前者不善不美,后者尽善尽美,君子必有所取舍。“诚以身莫荣于道义,学莫重于师友。有此师友,则一身有道义,而贵且尊;无此师友,则一身无道义,而卑且贱。”[10]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师友讲学践履成为评判世间善恶、美丑、荣辱的依据,美丑判断中整合了道德的、政治的、社会治理的内涵。自尊自重(“尊”)、真实可信(“信”)是从主体深层次审美意识的角度规定了“身”的内涵。尊身不仅指保全形躯身体,更有维护自我生命尊严与信心的意味,是主体审美意识发展到高度自觉程度的产物,若无“尊身即尊道”、身与道“本末一贯”的强劲支撑,断不可能有此自觉的“尊”“信”意识。
最后,发明士人真体至乐的极致美感在于讲学行道。泰州学派以“乐是学”“学是乐”的传统宗旨著称,“乐”是心体或性体的当下显现,具有浓厚的本体论意味。牟宗三指出,“平常、自然、洒脱、乐,这种似平常而实是最高的境界便成了泰州派底特殊风格”[1]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283页。,道出泰州学派之“乐”的独特性。王襞总结其父王艮的为学三阶段时,把复兴师道与乐之本体绾连为“任师同乐”的思想。这是王艮晚期思想走向成熟的产物,标志着其思想独创性的最终完成。其早期凭借自悟,“以圣人自任,律身极峻”;中期受阳明学启发,明了良知、易简、乐学之妙;晚期“本良知一体之怀,而妙运世之则”[2]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217 页。,著有《大成学歌》。王栋认为,其转向以师道自任,是缘于君道与师道、治统与道统的分离,“后世人主不知修身慎德为生民立极,而君师之职离矣”[3]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156 页。。用道统来规范引导治统,这其实是宋明理学极为重视的一件大事,这是儒家知识分子形上超越的理想在现实社会求取实现的唯一途径。在君臣之伦外另立师友之伦,正是道统与治统相颉颃的一种人际关系架构,因此,“自先师发明任师同乐之旨,直接孔孟正传,而出其门下者,往往肯以讲学自任”[4]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170页,。。以讲学倡明师道者,如王艮、王栋、王襞、徐樾、林春、赵贞吉、韩贞、夏廷美、颜钧、何心隐等人,无论布衣还是官吏,无不倾力于讲学,若没有一腔承接道统、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气概,怕是难以想象。这是一种超越了现世间种种凡庸琐碎,实现万物一体之仁的崇高感,也是一种强烈深刻、令万千平庸肤浅的感官悦乐黯然失色的身心合一之“乐”。
在以身任道的“乐”感中,士人人格独立的自觉意识与儒家伦理的、道德的传统紧紧交织在一起,新锐与陈旧共存,呈现出一种斑驳画面,即伴随士人主体自觉意识发展的,是愈加积极地宣传倡导传统孝悌观念,使得“身”与“道”的矛盾张力进一步加大。如王艮的《孝箴》《孝弟箴》《乐学歌》[5]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54页。、王栋的《乡约谕俗诗六首》《又乡约六歌》[6]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199—200页。、王襞的《青天歌》[7]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270页。、颜钧的《劝忠歌》《劝孝歌》[8]《颜钧集》,黄宣民点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8页。等等大量作品,都是面向愚夫愚妇进行启蒙而撰写的通俗易懂的歌、诗、赋、箴,宣讲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观念。他们憧憬着在恶政之外依靠唤醒士人结成师友关系弘扬儒家师道,发挥“身”的能动性,拯救江河日下、浇薄顽劣的民风世情,实现儒家“政平讼息,俗美化成”的礼治社会。因此,师友之“身”充满英气担当,将个体的自尊自信向群体推广实现。他们留下许多诗歌,流露出自任自信、身道一贯、道由人弘的自在满足感,诸如“但将乐学时时尔,自有生机泼泼然。道在人宏原易简,悟来风月正无边”[9]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199页。“纵横自在无拘束,心不贪荣身不辱”[10]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270页。“悟来吾道足,适意起高歌”[11]《颜钧集》,黄宣民点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负荷纲常只此身,险夷随寓乐天真”[12]《颜钧集》,黄宣民点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等等,诗歌中流露出“自在”“适意”“乐天真”的乐感,践履“道”不是负担,而是自任本心的“乐”与“学”。这其中,不再有魏晋士人在彷徨错乱中寻觅和依附于权势的战栗惶恐,也挣脱了唐宋元明士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拘束格套,自任而不依靠他者拯救、自尊自信而不为他者所惑、自在真乐而不限于自身适用,任道过程充满无畏和担当,笃行道统而不是效忠皇权或金钱,呈现了一种审美现代性萌生阶段士人的独立人格和操守,也是从个体之“身”向家国天下之众生扩展的起点。
余 论
泰州学派自王艮以讲学践履的方式指引了一条士人觉醒的方向,他们努力在“身”与“道”的双向互动中合一,追求“赤子之心”“真乐”的美感诉求。然而在危机四伏的政治生态下,重建儒家美学的“身”“道”一贯性虽然一方面激发出士人不断增强的自觉弘道意识,另一方面来自权力体系的威胁和风险不断累积,刺激士人更为自觉地反思和规避风险。王艮等人守持“身”“道”两全其美的理想,而现实是道统与治统的不可调和。
士人在“身”与“道”之间进退两难。泰州学派践行知行合一、身与道本末一贯的主张,在两难中赢得审美主体性的自觉伸张,但任道风险及其恶劣后果激化了反向的“爱身”“保身”等私性自主意识,在禅悦之风的推动下,加速了任情、纵欲等自然情性话语的“旅行”。“身”“道”在“本末一贯”的关系中产生分叉,在以身“任道”的主导价值中,以“身”为本的践履产生了“任情”的苗头,终至任道与任情共存。它们归属同源同根的本心之“乐”,但是平行发展难以啮合,遂构成中国审美现代性独特的双重平行指征,对后世影响深刻且长久。
审美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多样性,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很大程度上源起于“尊身即尊道”、“身”“道”本末一贯关系中的主体意识觉醒。不安本位、自由独立但积极守持道统,这种独特生成方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士人的普遍可接受程度。于斯时也,标举特立独行之“身”,把抗拒乡愿习气作为道义的担当,审美主体的反思批判力呼之欲出。不依靠他者来拯救而是自任于道主动承当,不为他者所迷惑而是葆有守持道统的自尊自信,不满足于自身受用而是通过讲学行动祛蔽除障向群体扩展。审美现代性的征兆是发现个人的内在自我及其独特价值,用以抵制商品经济加速发展时期道统的工具理性化、国家政治的私性化和个体道德情感的异化。即使“身”存在失之一隅、任情率性的缺陷,只要可堪任道即可,这是对士人主体性的显扬,也是危机时代反思传统、对于审美新变的吁求,有助于重建士人对崇高的审美感知。明中晚叶著名文人如李贽、焦竑、罗汝芳、杨起元、袁中道、袁宏道、汤显祖、徐渭等,对有缺陷但能任道的“豪杰”“英雄”“好汉”的拥护即是明证。这一传统或明或隐地延续下来,从明末以后,在内忧外患、天下兴亡之际独立担当的任道意识重新被激发,介入国家天下的政治践履,爆发出自发自觉的责任感,与所谓的启蒙现代性遥相呼应。
审美现代性的自觉反思意识还表现为与“自任于道”互补的维度,就是反向强化了“身”作为肉身需要有爱身、保身的私性层面,这可以看成是对王艮“尊身尊道”思想中以“身”为本埋下的“身”与“道”两难的一种化解方式。学界普遍认同晚明自然情性的表达与现代性的关联,但褒贬不一:持肯定意见者将人情人性的自然真实表达,归功于泰州学派;持批评意见者将晚明任情纵欲、鱼馁肉烂的末世风习,归咎于泰州学派。笔者认为,泰州学派对中国审美现代性的贡献或局限都要从这两个维度考察,即“任道”与反向平行表达的“任情”。二者同出一源,既大相径庭,又彼此牵制、相互渗透,孤立地强调其中任何一个维度,对于理解审美现代性都可能有失偏颇。比如明末文化思想先驱李贽、袁宏道、袁中道等人身上都体现出“任道”与“任情”的对峙——既彰显放纵不羁的个性自我又旌表压抑束缚自我的孝悌德行。直到晚清以降,受西方文化冲击,启蒙现代性生长,在“革命+爱情”的叙事母题中,“任道”与“任情”改头换面扭结在一块——追求个性解放、摧毁旧道德,投身民族国家革命的大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