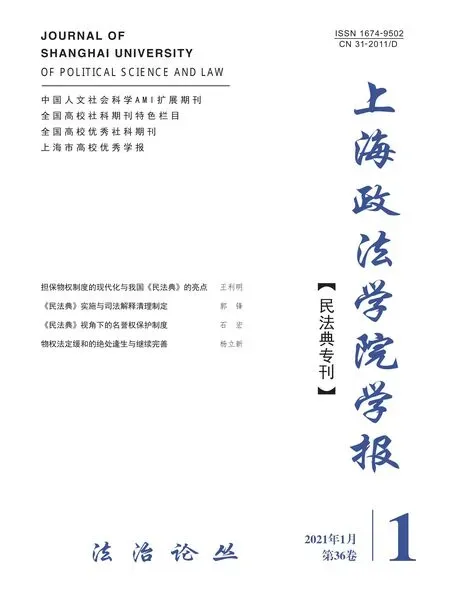分离原则与抽象原则在债权让与制度中之显现
——以债权二重让与为分析中心
2021-01-28陆家豪
陆家豪
一、问题的提出:从2008年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101 号判例展开
众所周知,权利概念之出现与个人主义观念之兴起密切相关,而康德通过将权利概念与人的自由意志相结合从而使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概念得以产生。①参见方新军:《权利概念的历史》,《法学研究》2007年第4 期。而在此之前,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与《论公民》中分别有如下论述:“权利的互相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②[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0 页。“权利的转让既要求接受者的意志,也要求有转让权的意志。如果缺一个,权利都无法转让。”③[英]霍布斯:《论公民》,应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 页。而后世以卢梭为代表提出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和主张都可以在霍布斯的作品中找到源头。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早在霍布斯的理论体系中,权利的转让就必须要有一个合意,而这个合意则必须要通过契约来体现,这也为康德后来采取一个不同进路阐释权利概念并进而影响德国的潘德克吞学派奠定了基础,也为近代私法所产生的极为重要的私法自治原则与契约自由原则④契约自由原则正是私法自治原则在契约法上的体现,所谓私法自治原则,经典定义是:个人得自主决定,自我负责地形成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显然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为表清晰,以下笔者均采用“私法自治”一词进行论述,而不再赘述“私法自治”原则的下位概念,即“契约自由”原则,因为契约自由原则乃私法自治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提供了政治哲学与法哲学基础。⑤关于私法自治的经济学基础,主要以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而契约自由乃古典自由主义在契约法上的反映。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3 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7 页。在英国,私法自治原则受到了从霍布斯、洛克到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的影响;在德国,私法自治原则受到了格老秀斯、普芬道夫、沃尔夫等近代大陆自然法理论以及康德哲学的影响。①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3 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8 页。韩世远教授主要参考了日本学者星野英一教授的观点,但实际上这中间可能存在个别理解偏差。首先,实际上对于霍布斯不能作一个简单的学派界定,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可以得知,社会契约论同样可以从霍布斯的著作中找到源头,而社会契约论正是自然法学派的标志性主张。虽然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以及以奥斯丁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学派的诸多观点,同样可以从霍布斯的理论中找到踪迹,但简单地将霍布斯与功利主义直接挂钩,显然是一种误读。类似地,将洛克简单地归于功利主义学派也是不够严谨的体现。其次,就算是康德的学说也受到了一部分霍布斯理论的影响。所以,区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私法自治原则的法哲学渊源其实意义未必很大。而在德国法上,以萨维尼和温德沙伊德为代表的潘德克吞学派对于权利概念的理解显然充斥着浓郁的“康德色彩”。②参见方新军:《权利概念的历史》,《法学研究》2007年第4 期。埃里克·沃尔夫形容温德沙伊德是“活在康德精神世界的最后晚霞中”。③参见吴从周 :《概念法学、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探索一部民法方法论的演变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 页。潘德克吞学派尤其是萨维尼又基于罗马法从而在其著作《当代罗马法体系》中进一步重构了整个德国民法体系,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德国民法典》的编纂。④有关于萨维尼的理论贡献的论述,参见金可可:《私法体系中的债权物权区分说——萨维尼的理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而《德国民法典》又进一步影响了整个大陆法系的民法典编纂运动,从而致使私法自治原则和权利概念渗透到了整个近代民法体系之中,并且它们在当代民法中仍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债权毫无疑问是最能体现自由意志的一种权利。第一,相比同位阶的物权而言,债权受到的公权力干预的可能性更少,任意性规范在债法中的体现也更高。这点在我国实证法上即可得到印证,当年《合同法》中的任意性规范显然要比《物权法》中多得多。并且从《合同法》被几乎毫无阻力地顺利通过和《物权法》的“持久难产”直到2007年才最终“尘埃落定”以及诸多条文的似是而非来看,债权自由度显然要高出许多。第二,债权奉行契约自由原则,而物权奉行物权法定原则。⑤关于“物权法定主义的松动”现象,笔者在之后会详述,此处不赘。原则上,任意性规范允许当事人基于约定作出与法律相违背的意思表示(当然不能存在法律行为的效力瑕疵事由),而物权的种类和内容都必须由法律规定。⑥德国学说分别称其为“类型强制”(Typenzwang)和“类型固定”(Typenfixierung)。两造相形显然债权自由度要大很多。第三,物权⑦其实不仅仅是物权(行为),处分行为本身都奉行客体特定原则与确定原则,是故在德国学说上,债权让与行为本身属于处分行为(准物权行为),它也一样奉行客体特定原则与确定原则。奉行客体特定原则(Spezialitätsgrundsatz)与确定原则(Bestimmtheitsgrundsatz)。所谓特定原则,是指作为处分行为客体的,必须是一项权利或一项权利之部分,而不得是一束权利(权利集合)。换言之,存在几项权利,就对应几项处分行为。⑧至于如此规定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法律关系的清晰性考虑:一项行为处分一项权利,需要独立观察各项处分行为的效力,有助于准确分析效力瑕疵之所在并寻求针对性的解决之道。转引自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 页。而处分行为的客体特定原则与物权客体特定原则相呼应,后者要求,物权仅存在于确定的一物之上,相应的,每一行为亦仅能处分一物。⑨实际上,物权客体特定原则在大陆更熟悉的叫法即为“一物一权主义”,将这个原则再精确化应当如此展开:物权仅存在于确定的一个有体物上。当然,此原则存在例外,譬如,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转引自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 页。而确定原则是指,至迟在处分行为生效之时,必须明确所处分的具体是哪项权利。⑩Schwab/Löghnig,Einführung in das Zivilrecht,18,Aufl.,2010,Rn.462.转引自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 页。而负担行为不适用特定原则,至于确定性,负担行为虽也有此要求,但比起处分行为,它的确定性要求要低很多。第四,债法是“关系规范”(Beziehungsnormen),物法则是“定分规范”(Zuordnungsnormen)。债权停留在特定主体间的关系,本质上是隐匿的,无关任何第三人,物权则从这样的关系独立出来,而且公开化,变成就特定财物对所有人都有某种潜在规范效力的权利。⑪参见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 页。因而通过比较,债权自由度相较物权要高出许多。进而债权本身就最能体现和贯彻私法自治原则,也是与当事人自由意志结合度最高的权利。
随着市场交易日益自由化和复杂化,交易客体不再限于有体物,交易形式多元化致使债权等无形财产利益开始逐渐可以作为权利客体进行让与交易。而考虑到债法的其他规则日益趋同,在大陆法系尤其是债权让与的优先顺位问题,几乎成为了债法上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⑫参见李宇:《债权让与的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法学研究》2012年第6 期。实际上学界争论不休的以德国法为代表的让与主义(时间在先,权利在先)、以法国法为代表的通知主义,以及以英美法系为代表的复杂的优先权规则①参见方新军:《合同法第80 条的解释论问题——债权让与通知主体、方式及法律效力》,《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年第4 期;申建平:《债权双重让与与优先权论》,《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3 期;张谷:《论债权让与契约与债务人保护原则》,《中外法学》2003年第1 期;崔建远、韩海光:《债权让与的法律构成论》,《法学》2003年第7 期;崔建远:《债权让与续论》,《中国法学》2008年第3 期;徐涤宇:《债权让与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和逻辑贯彻》,《中外法学》2003年第3 期;李宇:《债权让与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法学研究》2012年第6 期;戴建庭:《债权让与制度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合同法中债权让与制度的完善》,《河北法学》2004年第8 期;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3 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57-485 页;崔建远:《合同法》(第5 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225 页。,其实本质上仍然是债权让与行为的定性问题,物权行为理论争论的“余热”扩散到了债权让与这个准物权行为之中,所有试图解决优先权顺位这个问题的学者多少都谈到了债权让与性质的问题。而正如一物二卖最能体现物权行为理论脉络,债权二重让与也让债权让与的定性产生的争议和结论的巨大差异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债权二重让与的处理极其复杂,它涉及让与人、受让人、债务人和次债务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具有研究价值,但对于此问题,我国实证法上却未置一词,仅仅在《民法典》第546 条规定了债权让与之效力,导致了解释论上极大的争议。是故,笔者以“上海锦策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与上海妙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以下称“2008年沪冲民—(民)终字第2101 号判例”)中发生的债权二重让与问题为分析之基本型,进而阐释分离原则与抽象原则在债权让与制度中的利弊取舍。
2008年沪二中民—(民)终字第2101 号判例的法律关系较为清晰,是一个典型的债权二重让与的案例。其中妙鼎公司为债务人,申祥公司为债权人,且为让与人。而锦策公司则为第一受让人,赵文付为第二受让人。申祥公司以妙鼎公司为债务人,处分其对妙鼎公司所享有的合法有效的合同债权,并无不妥。根据《合同法》第80 条规定②《合同法》第80 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让与人申祥公司与债权受让人锦策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对债务人妙鼎公司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关键是债权转让的事实是否已通知妙鼎公司。如果妙鼎公司接到债权让与通知,则本案所争议的债权转让协议对妙鼎公司产生效力,妙鼎公司应向新债权人锦策公司履行,否则仍应向原债权人申祥公司履行。当然,就申祥公司和锦策公司关系来看,通知并非债权让与之构成要件,通知与否并不影响债权的让与。由于本案所争议的债权转让协议系申祥公司和锦策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因此,不论债权转让的事实是否通知到妙鼎公司,该转让协议对申祥公司和锦策公司仍具有法律约束力。
虽然“债权转让协议书”上是仅由郁新龙签名,但依据上述已查明的客观事实可以认为郁新龙作为妙鼎公司的员工,其实施的行为事实上是以妙鼎公司的名义而实施的行为,所以,郁新龙在债权转让合同上签名的事实,可以认为妙鼎公司已经接到了债权转让的通知。况且,将合同权利转让的事实及时通知债务人,并不要求债务人对债权人让与债权的行为作出同意与否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以郁新龙作为妙鼎公司的工作人员就有关款项的确认、转让等涉及公司重大经营活动中所作的签字不具有法律效力为由,认定郁新龙的签字不足以表明债权转让事实已通知妙鼎公司,于法无据,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由于申祥公司与锦策公司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已通知到妙鼎公司,因此,赵文付与景玉祥或申祥公司之间的借贷基础债权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妙鼎公司根据申祥公司的“承诺书”是否实际履行,均不影响“债权转让协议书”对妙鼎公司已产生法律效力的事实。况且,即便妙鼎公司确实已根据申祥公司的指示将欠款交付给赵文付,妙鼎公司应当知道自己此时的债权人已不是原债权人申祥公司,而是新债权人锦策公司,在此情形下,妙鼎公司仍向赵文付履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鉴于本案所争议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不但在申祥公司与锦策公司之间具有约束力,而且妙鼎公司亦受该协议的约束,因此,当事人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虽然妙鼎公司认为其向锦策公司支付转让款之前应该先与申祥公司另外再签订一份合同约定付款时间,但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书”第3 条的规定,在申祥公司与妙鼎公司未就妙鼎公司付款时间重新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妙鼎公司按照其与申祥公司签订的“上海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中约定的期限付款,亦是债权转让协议书第3 条规定的应有之义。因妙鼎公司未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向锦策支付转让款,现锦策公司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书”要求妙鼎公司付款,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违约金,因“债权转让协议书”对此并未约定,故锦策公司该项请求,无事实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的基本见解概括而言:1.由于我国在物权变动模式上采用债权形式主义,因此,我国在债权让与上亦应当采用该模式。又因债权乃是相对权,无需公示亦无法采用交付或登记的公示手段,故在债权让与上,应以意思主义为标准。因此,在两次债权让与中,成立在先的债权让与契约优先于成立在后的债权让与契约,第一受让人取得优先权。2.债权二重让与不适用善意取得,因为善意取得基于公示,但是债权让与没有公示手段,故不适用善意取得,赵文付即使已获清偿,但欠款之清偿仍属于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不得主张善意取得。①参见王屹东:《同一债权双重让与不适用善意取得》,《人民司法》2009年第10 期。
债权二重让与本就为理论和实务上之难题,争论不断。理论界也一直没有定论,而立法上的漏洞要求学者必须在解释论上做努力。如若漏洞实在难以填补,已经穷尽解释,那么必须在立法论视角上做一番努力。笔者试图对这个问题作系统的分析和梳理,从而得以揭开债权二重让与之“普洛透斯”之面,实务上之难题自然也就基本得以迎刃而解。
二、债权让与性质之争
(一)债权的特殊性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债权让与制度的产生原因为何?债权到底怎么了?有学者也提出了所谓的“债权物权化”理论②参见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5 页;李庆海:《论债权物权化趋势》,《当代法学》2005年第4 期。,认为此问题在债权让与尤其是让与担保中也可以体现。对此也存在反对和质疑的声音③参见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6 页;章杰超:《对所谓“物权债权化”的质疑》,《政法论坛》2006年第1 期。,笔者同样不同意这样的说法,理由如下:第一,物权法定主义的确出现了松动之趋势,交易的复杂化使得物权法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需求显得力不从心与捉襟见肘,苏永钦教授即在《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再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可能性》一文中从物权概念、物权法定主义的合宪检验、物权法定主义的政策理由等方面,得出物权法定主义已然松动的理论,从而进一步企图重构现行民法体系,将物权与债权统合进财产权体系,而不再单设物权编。④据笔者所知,苏永钦教授在台湾政治大学讲授的一门课即是财产法。限于篇幅且与本文主题的契合度问题,笔者不可能将苏永钦教授的观点一一展开,具体论述可以参见苏永钦:《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再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可能性》,载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174 页;苏永钦:《物权法定主义的再思考——从民事财产法的发展与经济观点分析》,载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120 页。此种构想并非不可实现。而在此过程之中,债权并不是物权化了,而是债权财产权化了。这两种称谓看似一样,实则差异巨大。债权的财产权化意味着债权从人身关系到纯粹经济关系的一个质变,债权由此失去人的色彩而实现了独立财产化,完成了其从对人的直接支配性到非人格化的转变。⑤参见[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 -49 页。转引自徐涤宇:《债权让与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和逻辑贯彻》,《中外法学》2003年第3 期。在此意义上,债权财产权化实际上就是债权的非人格化,而这个趋势使债权自由让与成为可能,实质上并非债权物权化,而是债权财产化的观念催生了债权让与制度。而同时,债权让与制度本身虽然是在债权财产化的过程中孕育,但又对债权财产化有所助益。这就意味着,欲使债权完全失去人身色彩而表现为纯粹的财产关系,就必须承认债权让与的可能性。换言之,增加债权之财产性质的最重要之点,就是完善其转让的可能性。⑥同注②,第22 页。是故债权物权化与债权让与没有丝毫关系。第二,笔者认为,债权物权化本身就不能成其为一个正确的概念。因为其在逻辑上必然会推演出随着债权物权化,债权物权最终将合为一体,债物二分最终将归于消灭,以之为规范基础的分离原则更没有存在之空间和必要,承认债权物权化,势必将打破整个民法的债物二分体系,恐怕有舍本逐末之嫌。正如苏永钦教授所批判的:“立法者是有意在债物二分的僵硬体系下,让它像冲破寒冬的第一只燕子一样,带来债权物权化的春天。然而在债物二分和债权物权化这两个命题逻辑上即无法兼容的情形下,采此说者更有义务仔细整理其他的民法规定……这一条路未必真的好走。”①苏永钦:《找到漏洞了吗》,载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7-548 页。第三,即使是苏永钦教授所持的将物权和债权同划归为财产权的观点,他也强调必须要坚持债物二分,“因此并非打破债与物二分,如前所述,债权和物权、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二分都不需要改变,只是从更接近社会的,或更功能取向的角度,把不同的关系规范重新整合。说得更好听一点,就是融合《德国民法》的逻辑结构和《法国民法》反映生活的优点于一体”②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 页。。由此可见,债权物权化显然走得太远了些,甚至有些不切实际。因为事实上,物权和债权有很多的差异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如若债权改变了其相对权的性质(尽管这把“法锁”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例外,但相对性原则仍然是债法颠扑不破的原则),物权改变了其绝对权的性质,那么债权不再是债权,物权也不可能成其为债权③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西方逻辑学曾提出的“秃子悖论”:如果一个有X 根头发的人被称为秃子,那么,有X + 1 根头发的人也是秃子。所以,有(X + 1) + 1 根头发的还是秃子。以此类推,无论你有几根头发都是秃子。实际上,债权物权化到底要量化到何种程度才能变成物权呢?美国控制论专家扎德((Lotfi A.Zadeh)运用模糊数学解决了这个逻辑上的悖论,可是这个民法学上的“秃子悖论”,诚值深思。,那又何来债权物权化呢?综上所述,债权让与制度的产生源自债权非人格化而非债权物权化。而要真正理清楚分离原则与抽象原则在债权让与制度中的脉络,恐怕不得不先理清楚债权让与性质的诸多问题。
(二)债权让与性质之再思考
我国理论界针对债权让与性质主要有三种学说:一说为契约说;一说为事实行为说;另一说为处分行为说(也称准物权行为说)。以下分别论之。
1.契约说
持契约说者认为,德国法将债权让与视为一种准物权行为、法国法将债权让与视为买卖合同的观点均有不足之处,英美法将债权让与视为独立的合同的观点更为可取。④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 页。这个观点看似开辟了一条新路,但并不经得起推敲。
笔者认为,首先,我国民法采用的是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虽然有些制度例如《民法典》第563 条第2 项的确借鉴了英美法上的预期违约制度,但是债权让与制度由于必然涉及权利变动,债权让与规则也必须与物权变动模式相一致,无论解释论上是采用以《奥地利民法典》为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还是采用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抑或是采用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意思主义,债权让与的权利变动规则均须与此一致,王利明教授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但回避了如何将债权让与合同与现行的法律体系相协调一致,恐怕略有不妥。
其次,将债权让与视为一种独立的合同,按照王利明教授的观点,似乎将这个合同能够直接发生债权让与的权利变动,并且与德国法上的物权契约不同的是,这个合同本身还具备债权合同的功能,因为王利明教授并不肯认物权行为理论。⑤参见王利明:《物权行为若干问题探讨》,《中国法学》1997年第3 期。显然他不会承认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的分离原则与抽象原则的存在,自然不可能视债权让与合同为物权契约。但同时,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同样也不同于法国法的“一体原则”。持“一体原则”观点的学者认为⑥持此观点者主要有崔建远教授和申建平副教授,笔者之后会详述。,债权让与是一种事实行为,认为债权让与契约直接引起了权利变动,而债权让与行为本身仅是个事实行为,没有意思表示进入的空间。但王利明教授显然也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实际上,王利明教授的观点会导致解释论上的自相矛盾。依照我国《合同法》第80 条第1 款⑦《合同法》第80 条第1 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既然不肯认物权契约的存在,毫无疑问王利明教授的“债权让与合同”是一个债权契约,既然这个债权契约可以直接产生债权移转的效力,但又不承认债权让与是一个事实行为,事实行为论者主张需要债权让与契约与债权让与这个事实行为以及让与通知相结合才能产生债权让与的变动效果(类似于一种债权形式主义的模式)。那么无论采用“通知主义”还是“让与主义”来解释《合同法》第80 条,都无法解释王利明教授的“债权让与合同”。如若采用“通知主义”,通知到达债务人时,债权让与才发生变动,那么“债权让与合同”的订立与通知必然有时间差,它是无法发生权利变动的,又不承认债权让与这一事实行为本身,通知和“债权让与合同”难以发生联结,显然与“通知主义”相矛盾。如若采“让与主义”,则遵循“时间在先,权利在先”规则,“债权让与合同”订立在先,则在先权利人取得债权。但由于“债权让与合同”并不同于德国法上的分离原则,即债权让与契约这个负担行为与债权让与行为这个处分行为的效力需要分别观察,那么尤其是在债权二重让与的场合,第一受让人取得权利后,第二受让人不仅无法取得权利,并且由于转让人在第二次债权转让时是无权处分,这个债权转让合同依照《民法典》第597 条原则上是有效的,但事实上,这个“债权让与合同”在第二受让人这里已经不可能有效,如若有效,必须要产生权利变动的效果,不承认分离原则,自然没有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待定的适用空间,必然陷入一种逻辑上的自我矛盾。
再次,学者对于债权让与的权利变动方式,至少应当与物权变动模式保持前后一致。因为既然不承认分离原则与抽象原则,本身在法律行为体系脉络下,债权让与行为本身即是处分行为。物权行为尚且不被承认,依据“举重以明轻”之当然解释原理,作为“准物权行为”的债权让与行为是不可能被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承认的。故学者在学术观点上应保证前后逻辑一致,而不应该多次摇摆不定易其观点。债权让与的权利变动模式必须与物权变动模式保持前后一致。王利明教授在《物权行为若干问题探讨》一文中主张,“我国民法的规定类似于瑞士法的立法模式。此种模式要求物权之变动,除债权意思表示外,还需以登记和交付为要件”。而更为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在《合同权利让与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其观点发生了转变,其主张:“没有通知债务人的,则债权未被转让,受让人实际并没有取得债权”①参见王利明:《合同权利转让中的若干问题》,载王利明著:《民商法研究》(第6 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20 页。。由此可见他确实保持了与物权变动模式的前后一致,他自己也放弃了之前所主张的契约说的观点,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此观点有诸多不足之处。
最后,承认债权让与合同是一个独立的合同,那它必然要遵循债的相对性,并且债权让与涉及权利变动,只要发生权利变动则必须进行公示,我国《民法典》第546 条规定的让与通知并非不发生公示效力,而是对债务人的一种特别保护手段,此点笔者之后会进行论述。此中原因在于权利客体并不是在一个平行位阶和层次上的,权利的客体是有层次的。②其中,第一层次的权利包括物质客体和观念客体。第二层次的权利是第一层次权利动起来的结果,第二层次客体上的权利原则上是第一层次的权利。第三层次的权利是第二层次权利动起来的结果,其客体原则上是第二层次的权利,其后依此类推。参见方新军:《权利客体的概念及层次》,《法学研究》2010年第2 期。而债权让与在第三层次的权利客体中才能有所体现。第三层次的权利是以第二层次的权利为前提产生的,第二层次的权利(债权)就是第三层次权利人(受让人)的利益之所在。第三层次的权利(债权让与)也是第二层次权利(债权)动起来的结果,而债权让与属于主动的动。而以债权为客体的权利运动过程导致以第三层次的债权为桥梁回到第二层次的权利上来。在此种情况下,作为移转第二层次权利手段的债权的客体就是第二层次的权利。权利的客体就是原先第二层次的权利客体。而作为第三层次的权利客体,第二层次的权利最好能够以一种外部观察的方式表现出来,否则第三层次的权利就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③参见方新军:《权利客体的概念及层次》,《法学研究》2010年第2 期。是故《民法典》第546条第1款规定从文义上似乎以通知作为权利观察的方式(实际上存在规范漏洞)。④当然,对于通知是否具备足够的公示效力笔者在之后会加以讨论。实际上在第三层次的权利上,权利证券化或者登记才是最优的公示方式。同样的,在第四层次的权利客体上,主要体现的制度即是让与担保。同样外部观察的方式是权利证券化和登记。让与担保仍然属于一种广义的债权让与。债权让与担保可以分为特定让与担保与集合让与担保。特定让与担保系指以特定之个别债权为让与担保标的物而言。而集合让与担保系以现在之债权及将来发生之变动多数债权一并为让与担保标的物之担保办法。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修订5 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0-1134 页。而王利明教授的“债权让与合同”显然难以发生公示效力或者说公示性并不足够,对第三人之保护尤其在债权二重让与中的第二受让人和债务人的保护,甚为不利。
2.事实行为说
事实行为说主要依托法国法的“通知主义”。法国法坚持“广义的财产权理论”,其所谓的财产,包括物、物权、债权和无形财产,没有物权和债权的科学划分。⑤参见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 页。转引自徐涤宇:《债权让与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和逻辑贯彻》,《中外法学》2003年第3 期。法国法采“一体原则”,即不承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分离原则,也不区分债权让与行为与买卖、赠与等原因行为。故债权让与发生权利变动之效力取决于债权让与契约,对债权让与契约和抽象的债权让与行为不作刻意区分,视为一体。让与契约成立并生效债权即发生让与之法律效果,但此时债权让与仅对让与人(债权人)和受让人具有效力。要对债务人和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发生效力,必须履行通知义务。而此时的通知属于观念通知,通知行为本身并不具有法效意思。权利变动乃基于债权让与契约此一法律行为而非通知行为。通知行为本身并不构成意思表示。因为意思表示本意是行为人意欲将内心之法效意思表示于外之行为。无论采用新理论抑或旧理论,法效意思均为意思表示构成之不二要素。法律行为系行为人基于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果之行为,属于表意行为。观念通知虽与法律行为一样也属于表意行为。但其效力由法律规定而当然发生,但与法律行为极为相似之处在于:两者均以表示一定心理状态于外部为特征,故学说上称观念通知为“准法律行为”。债权让与通知不过是法律规定与当事人内心之意思产生的一种“偶然的巧合”和“美丽的误会”而已,它的行为基础是法律直接明文规定而非当事人之意思表示。在这一点上又与作为非表意行为之事实行为颇有相似之处。可以这样说,准法律行为介于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之间,但由于其内涵更近似于法律行为,故称其为“准法律行为”,债权让与通知即为典型。在主要包括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民法典中,让与通知不仅是债权让与对抗债务人的要件,亦为对抗债务人以外的其他第三人的要件。立法例上的规定,诸如,《法国民法典》第1690 条第1 款:“受让人,依其向债务人送达转让通知,才对第三人发生占有权利的效力”,《日本民法典》第467 条第1 款:“指名债权之让与,非经让与人通知债务人或经债务人承诺,不得以之对抗债务人及其他第三人。”类似规定在《意大利民法典》第1264 条中同样有所体现。
而我国的规定则与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均不相同。由于我国通说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在物权变动上也不同于日本法与法国法上的意思主义,而是另辟蹊径采用债权形式主义。这一点辐射在债权让与制度中使得我国对于债权让与性质的规定变得也颇具“中国特色”。与物权变动模式相同,我国学说上同样肯认“区分原则”(区分原则不同于分离原则),即区分债权让与和债权让与契约两个范畴。前者只是对债权变动形态的一种昭示,本身并非基于行为人意思而使得权利直接而当然地发生变动,而真正引起债权发生变动的是之后的债权让与契约。因而有学者认为债权让与在性质上是一种事实行为。①持此观点者有崔建远、韩海光、申建平等。参见崔建远、韩海光:《债权让与的法律构成论》,《法学》2003年第7 期;申建平:《债权让与制度研究——以让与通知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108 页。而债权让与契约乃基于行为人意思表示而产生相应法律效果,故而在性质上属于法律行为。它兼有使当事人之间负担相应债法上之义务与产生权利变动的效力。在这点上与法国法上的“一体原则”颇为相似。同样的推理逻辑同样适用于法国法,债权让与同样属于事实行为。
事实行为说论者的经典表述是:债权让与,是指债权自其主体处移转到受让人之手的过程,是债权变动的一种形态,因不承认物权行为制度及其理论,它属于事实行为;同时,它也是债权归属于受让人的一种结果。而债权让与合同则为引起债权让与的一种法律事实,并且,因其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要素,故它属于一种法律行为;因其在让与人和受让人之间产生了债权债务,故它属于债权行为。②参见崔建远:《合同法》(第5 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208 页。逻辑看似合理,但细致分析后不难发现这精美“华袍”之下满藏的“虱子”。事实行为论者多为反对物权行为理论者,一方面,其给出的一个理由即为物权行为理论过于抽象,斧凿痕迹至为明显,将一个行为拆分成几个行为进行分别分析,与生活常理不符。另一方面,通过对事实行为论者论述理由的介绍,“区分原则”的引入使得债权让与也被割裂成两种形态。这同样是与生活常理相违背的,因为按照反物权行为理论者之逻辑,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让与契约这个行为存在,而又为何硬作区分,又多出一个事实行为呢?如若德国法真如其所说的那么违背生活常识,那么“区分原则”何尝不是法律对生活的“强奸”呢?退一步讲,如若遵从所谓“一体原则”,不过是在法律行为框架下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把握,不做分离,债权让与契约兼具债权移转与使行为人负担债法上义务的功能。既然只有一个行为存在,那么这个行为怎么可能既属于事实行为,又属于法律行为呢?德国法上把一个法律行为拆分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是因为将二者的效力作分别观察,从而来对当事人利益做出最佳判断得以保护两造当事人利益与交易安全,即便如此,它也并未违背“一行为不可能同时是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这一基本逻辑,拆分出来的仍然是两个法律行为。而事实行为论者的这个论点毫无疑问比德国法更违背生活常识,同时强做区分也毫无实际意义,可能这才是真正的“看上去很美”,而不是德国法理论。
3.处分行为说
处分行为说主要代表国家即是德国。德国法认为,债权让与契约仅仅是负担行为,而在契约之外存在着一个处分行为,而这个处分行为即是负担行为的履行行为,从而真正产生债权让与的法律效果,而债权让与契约仅仅只是使得双方当事人负担债法上之义务。因而债权让与是一种处分行为,而二者都是法律行为。
法国民法在债权让与的权利变动模式中奉行意思主义,似无疑问。然而,日本法在这一点上并未与物权变动模式一脉相承而对法国法从一而终。不少学说话锋一转,追随德国,认为在债权让与中,存在债权让与行为这一处分行为和债权让与契约这一负担行为,即承认分离原则的存在。①参见[日]:伊藤进等:《民法讲义4:债权总论》,高阳堂1977年版,第242 页;[日]潮见佳男:《债权总论》,新山社2001年版,第516 页。转引自崔建远、韩海光:《债权让与的法律构成论》,《法学》2003年第7 期。但与德国民法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法仅仅承认分离原则而不承认抽象原则②参见崔建远、韩海光:《债权让与的法律构成论》,《法学》2003年第7 期。,即所谓“独立而有因”原则。此处与法国法和德国法均不相同。而日本法中债权让与的性质毫无疑问是一个处分行为。
我国立法对债权让与性质并未予以明确规定。仅仅在《民法典》第546 条有规定债权让与问题③原《合同法》第80 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在解释论上将债权让与通知作为受让人取得债权的条件,实际上是想类推适用有体物上所有权移转的公示方法,但是类推适用仍然应该以事物本质的相似性为前提,正是在这一点上,债权让与和所有权让与存在本质的区别。④方新军:《合同法第80 条的解释论问题——债权让与通知的主体、方式及法律效力》,《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年第4 期。而采处分行为说,显然对交易安全与私法自治之维护,甚有助益。⑤在2008年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101 号判例中,妙鼎公司作为债务人,申祥公司为债权人,且为让与人。而锦策公司则为第一受让人,赵文付为第二受让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债权二重让与基本型,为方便问题之说明。笔者称申祥公司为甲,妙鼎公司为乙,锦策公司为受让人1,赵文付为受让人2。
三、分离原则与抽象原则
(一)分离原则
所谓分离原则(Trennungsgrundsatz),乃因债法义务而变动权利时,变动权利的法律行为与设定债法义务的法律行为相互分离,彼此独立,亦称为独立性原则。⑥分离原则的意义可作此两层理解:其一,效果分离,即法律行为之债法效力与物法效力相分离;其二,要件分离,即产生债法效力者与产生物法效力者分属两项相互独立的法律行为,各有其构成要件。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 页。分离原则在债权让与中的体现主要表现为:债权让与行为(学说上称之为准物权行为)与债权让与的原因行为即债权让与契约(债权行为)要件分离和效果分离。
如前所述,承认债权让与是处分行为即等于承认分离原则的存在。而依照我国合同法,结合徐涤宇教授参与的《合同法(专家建议稿)》来看,依照其立法目的和规范意旨,并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相关条文的立法理由书和学理解释,关于我国债权让与的妥当解释是:(1)债权让与为处分行为,无须通知即生债权移转的效果;(2)在发生双重让与时,应依优先次序原则解决出由谁优先取得债权的问题;(3)债权让与,仅在通知债务人时,始对其发生效力(让与双方以及债务人之外第三人不适用该规定)。⑦《〈合同法〉第80 条第1 款:专家建议稿第80 条》,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 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57-458 页。转引自徐涤宇:《债权让与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和逻辑贯彻》,《中外法学》2003年第3 期。徐涤宇教授通过历史解释与法意解释的方法,从而得出承认债权让与系一种处分行为之结论,并进而承认分离原则。因为在分离原则脉络之下,处分行为引起权利变动,那么必然在双重让与的场合,优先顺序必须依照“时间在先,权利在先”的方式进行,此乃逻辑推演之必然。而以法国法为典型代表,在“一体原则”指导下,债权让与契约一经成立并生效即发生债权让与之法律效果,但未产生对抗效力,即采通知主义,表面上看似也无可厚非。①通知主义的诸多问题,笔者详后分析。
然而,对处分行为说而言,反对的声音络绎不绝,问题也远非如此简单。以申建平老师为代表,她并不赞同处分行为说,也不承认分离原则。理由归纳如下。
1.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尤其是物权变动方面借鉴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更多,由此也无法得出我国《民法典》物权编也采纳了物权行为理论。大陆通说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我国民法不承认物权行为制度及其理论,那么,我国法上的债权让与就不能被随意解释为处分行为。②参见申建平:《债权双重让与优先权论》,《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3 期。
2.《德国民法典》第407 条、第408 条,在二重让与中,一方面强调分离原则,遵循“时间在先,权利在先”规则,另一方面又以债务人未受通知为由否定第一受让人取得债权的效力,事实上是由通知的时间决定何人取得债权。③同注②。
笔者认为,以上两点反驳均不成立,试述如下:
1.我国立法上,物权变动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之观点可以商榷。事实上在解释论上可推演出我国物权法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存在分离原则甚至是抽象原则的空间,这是一种解释论视角,而非立法论视角即可证得。④限于本文主题,具体观点论述可参见葛云松:《物权行为:传说中的不死鸟——《物权法》上物权变动模式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6 期;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以中国法与德国法之比较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朱庆育:《物权行为的规范结构与我国之所有权变动》,《法学家》2013年第6 期;苏永钦:《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载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52 页;苏永钦:《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相关问题》,载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169 页;孙宪忠:《物权行为理论探源及其意义》,《法学研究》第3 期;孙宪忠:《再谈物权行为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 期;徐涤宇:《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目的论解释》,《中国法学》2005年第2 期。诸多学者撰文予以论述。
2.关于《德国民法典》第407 条、第408 条。⑤债权二重让与主要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408 条,它规定:“(1)被让与的债权被原债权人再度让与给第三人,并且债务人向该第三人履行给付,或者在债权人和该第三人之间,某一法律行为被实施,或者某一诉讼出于尚未审结状态的,为债务人的利益,第407 条的规定准用于前取得人。(2)已被让与的债权因法院的裁定而被移交给第三人,或者原债权人向第三人承认已被让与的债权依照法律规定移转给了该第三人的,亦同。”通过准用技术引接到第407 条:“(1)对于债务人在债权让与后向原债权人履行的给付,以及债权让与后在债务人和原债权人之间着眼于债权而实施的一切法律行为,新债权人必须承认其效力,但债务人在履行给付时或者法律行为实施时知道债权让与的除外。(2)在债权让与后在债务人和原债权人之间已经处于尚未审结状态的诉讼中,已经作出关于债权的有既判力的判决的,新债权人必须承认该判决的效力,但债务人在诉讼系属发生时知道债权让与的除外。”参见《德国民法典》(第4 版),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148 页。从《德国民法典》的法条中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在债权二重让与中,通过之前的基本型可知,甲与受让人1 签订的契约后,权利发生移转,随后甲又与受让人2 订立债权转让契约。此时甲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由于负担行为不以当事人有处分权为必要,并且契约只要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以及公序良俗原则,契约即可成立并且生效。如若不发生善意取得问题,⑥关于债权让与的善意取得问题存在争议,通说认为债权让与不能发生善意取得问题,但笔者认为,如若采取登记制之公示方法,债权让与有类推适用《物权法》第106 条有关善意取得规定之空间,之后详述。那么受让人2 恒定地不能取得让与债权,这是分离原则而产生的“时间在先,权利在先”规则的要求。让与人2 的救济途径可以向债权人甲主张违约责任,或者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请求权竞合),请求权基础也可以是《民法典》有关于欺诈的规定从而要求法院宣告合同无效,也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63 条根本违约或预期违约之规定主张合同解除权等诸多救济方式。依据《德国民法典》第407 条、第408 条之规定,为保护债务人之利益,因债权让与缺乏有效之公示制度,依据第408 条第1 款和第407 条第1 款,如若债务人向受让人2 清偿,或者债务人在债权让与后向债权人清偿,那么此处之清偿构成非债清偿,法律为保护善意之债务人,同样规定产生清偿之效果,受让人1 可以依据给付型不当得利之返还请求权请求债权人或者受让人2主张返还不当得利,事实上,此处关于清偿之例外规定,仅仅只是从保护债务人角度出发。但实际而言,对于债权人与受让人1、受让人2 之间的利益变动,除了产生不当得利返还以外,并未产生其他影响,其中债权也终局的不可能让与给债权人或者受让人2(当然即使权利人抛弃权利的除外,即使诉讼时效期间经过,根据“抗辩权发生说”也仅仅是受让人2 和债权人对受让人1 享有抗辩权,本身的实体性权利并未消灭)。所以申建平老师想必是误解了《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债务人未受通知时,第一受让人仍然能够通过不当得利返还请求第二受让人返还让与债权。但如若依照通知主义,第二受让人先于第一受让人通知债务人,一般情况下第二受让人可以先于第一受让人取得债权,此时第一受让人仅能向债权人主张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而对第二受让人没有任何债法上之联结,也没有债之发生原因,故而不能主张不当得利返还之请求,第一受让人对第二受让人请求权基础之有无正是让与主义与通知主义完全不同之处。也不知申老师何以得出“德国法407 条已使优先次序原则无法得以彻底贯彻,事实上是由通知的时间先后决定何人取得债权”之结论。
3.事实上,不论是物权行为,还是如债权让与这样的准物权行为。典型如德国法采用五编制立法体例,借助“提取公因式”(Ausklammerung)之数学技术,用总分则编制体例把法典的形式理性追求演绎得淋漓尽致。①参见朱庆育:《法典理性与民法总则——以大陆民法典编纂为思考对象》,《中外法学》2010年第4 期。诚如弗卢梅所言:“学说编纂体例之主要特征在于前置总则之体例,总则之核心则在于法律行为理论。”而其高徒雅克布斯也有言:“德国法典编纂的体系特点既不在五编制,亦非前置总则体例,而是物法与债法的截然二分。”②朱庆育:《物权行为的规范结构与我国之所有权变动》,《中外法学》2013年第6 期。事实上他们讲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唯有侧重点略有不同,本质上并不冲突。在债物二分体例下,那么必然存在债法上之负担行为与物法上之处分行为,此乃民法上之“任督二脉”③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 页。,由此抽象而来之法律行为理论,故而得以产生提取公因式之可能,从而构成民法总则编之核心。此中逻辑,一脉相承并且缺一不可。相较而言,法国法采取财产权概念而不采用债物二分之区分,那么自然没有分离原则存在之空间与可能。所以,在承认债物二分的体例之下,分离原则是逻辑之必然,如若违背逻辑,后果不堪设想,解释论上也将陷入一种极其困难的自相矛盾。④相关例子,可以观察到《日本民法典》移植德国债物二分的概念体系,但第176 条关于物权变动之规定却改采法国法,采意思主义的变动模式,规范体系出现重大错乱,解释论上也是捉襟见肘,尽管有诸多尝试,奈何效果差强人意。而从我国《合同法》第51 条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 条看似矛盾的规定,如若不承认分离原则,解释论上也将陷入另一种困境。我国民法是效仿德国总则前置之五编制体例,在立法上也采用债物二分体例,那么承认分离原则即是逻辑之必然,否则在债权让与问题中,解释论上也将陷入困境。
4.随着交易形式多样化和交易日益复杂化,简单的“一体原则”可能难以承受“市场需求之重”。在债权让与中,例如,债权保留让与、大宗债权让与或者未来债权让与中,债权让与契约与债权让与行为之间毫无疑问有一个时间差。以债权保留让与为例,依照“一体原则”,债权让与契约成立权利即发生变动,那么当事人已经事先达成了债权让与的保留约定,而此处之债权保留,属于附条件的约定,而能够附条件的,唯有法律行为,所以在债权保留让与中,唯有承认在债权契约中还存在着一个准物权契约,才能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5.分离原则以及基于此产生的让与主义在我国实证法上是可以有所体现的。《民法典》第546条第1 款之立法毫无疑问参考了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97 条第1 款。⑤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97 条第1 款规定:“债权之让与,非经让与人或受让人通知债务人,对于债务人不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97 条是因袭《德国民法典》第408 条之规定,但与德国法略有不同,但立法意旨,都侧重于债务人保护。债权因让与而生效,受让人1 毫无疑问能获得权利,德国法基于债务人之善意而对债务人之错误清偿仍然规定产生清偿效果,系基于债权让与公示制度的不完善,债务人又无从可知其中的权利状况而不得不为之的办法。而我国台湾地区则采取了另一种债务人保护方法:即让与人或者受让人附有通知义务,未经通知,债务人仍可向原债权人清偿,或者向已履行通知义务之受让人2清偿,也发生清偿之效果。但是,这仍然没有超出让与主义的范围,这仅仅是对债务人的特别保护,最终的债权享有者仍然是受让人1,仍可如德国法一样对债权人和受让人2 主张权利,仅仅是对债务人保护之技术手段之区别而已。《民法典》第546 条之规定同样如此,不过从严格的文义解释上看,似乎仅仅只有债权人能够对债务人进行通知,受让人是否要履行通知义务此处存在漏洞,需要进行填补。⑥《合同法》第80 条存在的规范漏洞中的开放性漏洞和隐藏性漏洞之填补,可以参见方新军:《合同法第80 条的解释论问题——债权让与通知的主体、方式及法律效力》,《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年第4 期。但事实上遵从的正是让与主义,那么自然遵从分离原则。
(二)抽象原则
所谓抽象原则(Abstraktionsgrundsatz),基本判断标准是,法律行为之效力是否受其原因(causa,Rechtsgrund)影响。①Astrid Stadler,Gestaltungsfreiheit und Verkehrsschutz durch Abstraktion,1996,S.19.如若处分行为之效力不受其原因行为(负担行为)之影响,即称之为无因性②关于无因性原则的历史,学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萨维尼创设物权合同理论是自由意志理论和法技术构成的结论。具体论述可参见徐涤宇:《无因性原则之考古》,《法律科学》2005年第3 期;但也有学者认为,萨维尼通过对罗马法中traditio(交付)的论理主义的解释而构建了物权契约无因性概念,巴尔通过stipulatio(问答契约)的诠释而创建了无因债务概念。参见陈华彬:《罗马法上的traditio、stipulatio 与私法上无因性概念的形成》,《中国法学》2009年第5 期。,亦称抽象原则。反之则称之为要因原则或者有因性。在债权让与制度中,债权让与的无因性表述如下:债权让与行为并不受债权让与契约效力之影响而受影响。分离原则是抽象原则的前提,承认抽象原则必然承认分离原则。分离原则之下,债权让与契约与债权让与行为之效力在逻辑上可以分为四种形态:1.债权让与契约与债权让与行为同时有效;2.债权让与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而债权让与行为无效;3.债权让与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债权让与行为仍然有效;4.债权让与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债权让与行为无效。债权让与的抽象原则或者无因性仅仅只在第三种情况下存在意义和适用空间。如若说分离原则是债物二分体系下之逻辑必然的话,抽象原则则更多是一种政策选择。弗卢梅即认为采用无因原则无关乎任何先验的“正确性”,而是一种立法目的下的考量。③参见苏永钦:《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载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 页。而有因原则简化原因债权关系所减省的交易成本,比起对第三人(所有潜在的交易对象)所复杂化的估量成本(比如要不要信赖登记),显然会高出很多。④参见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 页。
而债权让与的特别之处在于以债权作为权利客体,该债权所由生的债权行为仍属有因,从而受让的债权虽不因作为让与基础的债权行为失效而受影响,却仍可能因本身所由生的债权行为失效而溯及消灭,是其异于物权处分之处。⑤同注③,第134 页。
抽象原则对保护交易安全确实具有助益,在抽象原则之下,受让人1 在取得权利后不再有后顾之忧,其后手受让人也无须再多考虑前手之交易是否具有瑕疵。尤其是在证券化债权之中,如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票据问题规定》第14 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为体现无因性理论之明证。⑥当然此条有司法解释僭越立法之嫌疑,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 页。而《民法典》物权编也规定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制度(《民法典》第445 条)。毫无疑问在高度市场化的商法之中,为保证交易便捷与资本迅速流通,抽象原则之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在指名债权让与中,笔者认为,要承认抽象原则必须要解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无论是在德国法上还是我国现行法上皆难以解决,如若不解决,承认抽象原则,显然操之过急。
最大的问题在于公示制度。而公示制度对于现代民法而言,地位举足轻重。苏永钦教授即认为,物权行为可以是无因的,也可以是有因的,既非强制无因,也非一律有因,必须视原因是否已经由公示而纳入物权行为去做个案认定,德国法上的物权行为理论,最牵强、最拟制的一部分,或者这样就迎刃而解了。⑦同注④,第168 页。德国法上债权让与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采纳让与主义,让与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欠缺权利外观。在德国通说上也基于欠缺公示公信力而否认债权可以善意取得。⑧Karl Laranz,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Bd.I,Allgemeiner Teil.S.576-577.14 Aufl.,München1987.本身抽象原则否定论者即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令取得人能够从非权利人处取得权利,即便要因原则使得所有权移转随原因行为而无效,善意第三人亦可得到保护,因而,抽象原则实属冗赘。⑨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4.Aufl.,2010,Rn.121;Heinz Hübner,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2.Aufl.,1996,Rn.655.指出善意取得制度与抽象原则产生功能性重叠。⑩当然这个观点未必站得住脚,对此之反驳,可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 页。本来如若债权让与无善意取得制度之适用空间,正是反驳抽象原则否定论者的一个好机会。奈何由于处分行为的抽象性,必须借助一定的权利外观得以观察,并且权利变动必须要进行公示,从而产生公信力,这是公示公信原则的要求。而由于权利外观之欠缺,债权让与行为这一处分行为难以借助一定公示方法予以体现,而依照德国法的规定,首先,通知仅仅只是对债务人之义务;其次,通知本身并无足够公信力;再次,通知也并非债权让与的生效要件;最后,通知仅仅对债务人才具有意义。而交易第三人难以得知债权让与的具体状况,使得债权让与行为这一处分行为陷入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窘迫局面,从而使得在这一层面上,同法国法一样,债权让与契约成立并且生效成为了权利发生变动的判断标志。德国法的这一处理使得抽象原则名存实亡。要使得抽象原则得以真正得到适用,恐怕不得不对到底什么公示方法最契合于抽象原则之适用进行一个考察。
(三)2008年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101 号判例之评析
笔者认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理由存在如下问题,试分述之。
1.如前所述,我国物权变动模式未必一定承认债权形式主义,债权形式主义之变动模式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同时,从解释论上,物权行为并非没有存在之空间,至少分离原则可以从解释论上圆满推出。那么自然不能说,在债权让与的问题上我国也必须遵循债权形式主义。
2.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随后笔锋一转,认为:“债权乃相对权,无须公示亦无法采用交付或登记的公示手段,故在债权让与上,应以意思主义为标准,即债权让与契约完成,债权主体即发生变更。”①参见王屹东:《同一债权双重让与不适用善意取得》,《人民司法》2009年第10 期。以债权无须公示亦无法公示为由而改采意思主义模式,即债权让与契约成立在先,即发生权利变动。这个观点是明显有理解错误的。首先,基于之前的论述,债权并非无须公示亦无法公示。不是基于债权是相对权而无须公示或者无法公示,而是以债权作为权利客体的权利变动必须进行公示,否则将违背民法原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显然混淆了权利本身与权利客体的关系,债权作为权利本身无须公示,但是,当债权作为权利客体进行权利变动时必须进行公示是当然之理。其次,公示方法不仅仅只有登记和交付,通知虽然公示效力不够,但仍成其为一种公示方法。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显然对这个问题也存在误解。最后,既然如若债权让与问题上可以存在通知的公示方法,那么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就存在适用的空间,那么怎么又能改采意思主义呢?不就相当于说债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在债权让与问题上没有适用空间与可能了?在论证理路上也存在问题。
3.从解释论而言,债权让与确实不能适用善意取得,此问题之前笔者已经进行了详尽论述。但是,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一步认为:在本案中,妙鼎公司对赵文付之清偿属于不当得利,不能以善意取得为由拒绝清偿,故申祥公司对赵文付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由于在本案中,法院经审查认为锦策公司已经向妙鼎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那么此时德国法模式与法国法模式的区分度并不大。因为基于德国法和法国法,债权让与契约均是一经成立权利即发生变动,那么只要锦策公司向妙鼎公司完成通知,那么妙鼎公司则必须向锦策公司履行清偿义务,如若向赵文付完成清偿,则自然产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此点自不待言,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分析并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不能基于此即认为,我国债权让与制度就必须采意思主义变动模式。因为问题在如果赵文付率先通知时,德国法与法国法即在此问题上走向分野,如若赵文付先行通知妙鼎公司,依照法国法,则妙鼎公司之清偿行为有效,并且赵文付可以获得清偿,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此时锦策公司对赵文付不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故此时通知为对抗要件而非债权让与的生效要件。而在本案判决书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对此问题的理解存在偏差。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方面认为:“当然,就申祥公司和锦策公司关系而言,通知并不是债权让与的构成要件,是否通知不影响债权的让与。”,另一方面又认为:“本案中,因债权让与涉及债务人妙鼎公司,故通知与否则成为债权让与的构成要件。”这显然是一种前后矛盾的措辞,因为不可能说通知在不同的当事人的关系之间既可能成为构成要件又不是构成要件。实际上仍旧没有理清楚这一问题。如果采德国法模式,赵文付预先履行通知义务,那么此时规定妙鼎公司对赵文付之清偿有效,妙鼎公司退出债之关系,又因为基于让与主义,锦策公司才是权利人,故锦策公司仍然可以向赵文付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而对于债权让与行为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未置一词。如若以其承认的意思主义模式为例的话,那么自然要采的是事实行为说,进而无论如何不可能采用让与主义。但事实行为说的诸多问题笔者已经予以详述,而与意思主义相嵌套的通知主义(无论是通知对抗主义还是通知生效主义)也存在诸多弊端。而此时恐怕不得不对债权让与优先顺序模式进行考察,而此问题,恐怕已经超出了解释论视角,由于我国法律对债权让与问题规定得过于简单,恐怕不得不求诸立法论来得以解决,从而使得理论与实务上之重大争议得以缓解甚至解决。
总结而言,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基本正确,的确,锦策公司作为权利人得以让妙鼎公司支付欠款,但基于笔者之分析,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债权让与的诸多基本问题仍然存在重大的理解偏差,由于本案中锦策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使得本案的法律关系并不那么复杂,也使得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并无问题,但是,如果实务中发生了赵文付率先履行通知义务,恐怕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就不那么尽如人意了。可以说判决结果正确,但判决理由存在问题。
四、债权让与公示制度之考察
(一)让与主义
如前所述,让与主义的最大弊端在于权利外观之欠缺使得公信力保护不足,使得债权让与抽象原则名存实亡,使得在权利变动方面也以债权让与契约成立生效为判别标准,而债权本身属于无体物,又不能类似于动产一样基于占有而产生权利推定之公信效力,所以让与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公示方法,不如说仅仅只是一种“时间在先,权利在先”规则的债权让与优先顺位之解决方法,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公示方法。
(二)通知主义
法国法并不严格采用通知主义。如若依照严格通知主义,那么通知应当为债权让与的生效要件。本身法国法系诸国采用严格的通知主义,但基于实务要求,已经陆续废除,而改采通知为对抗要件。①参见李宇:《债权让与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法学研究》2012年第6 期。故依照《法国民法典》第1141 条与第1690 条②《法国民法典》第1141 条规定:“如果出卖人将标的物再让与给第三人,而该第三人先于前买受人占有标的物,则前买受人不受保护”;第1690 条规定:“受让人,仅依其向债务人进行有关转让的通知,或依其向债务人在公证文书中接受转让的表示,始对第三人发生占有权利的效力”。,在债权二重让与中,原则上债权让与契约成立生效后受让人1 取得债权,此乃意思主义变动模式之要求,而由于一体原则之存在,受让人2 之转让契约应为无效。但如若受让人1 未向债务人履行通知义务,则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即如若善意之受让人2 向债务人履行通知义务,债务人依照让与通知向受让人2 完成清偿,则债务人之清偿有效,并且受让人2 得以终局地取得债权,而受让人1 不得对其主张权利,仅仅得对债权人主张债务不履行之请求权。由此可见,通知仅生对抗效力。在日本法上,如前所述,在债权让与性质上跟随德国,认为债权让与是一种处分行为。但在通知的性质上却又转向法国法,通知同法国法一样产生对抗效力。法律依据规定在《日本民法典》第467 条第1 款规定:“指名债权的让与,非经让与人通知债务人或债务人承诺,不得以之对抗债务人及其他第三人。”可见,日本法对此问题的规定体系略显混乱,法律适用上必然会陷入矛盾。
但通知主义存在诸多弊病。首先,通知本身仅仅是对个别人的通知,本身难以产生对第三人的公示效力,仅仅只是一种人为拟制,第三人对于债权让与之事实只有向当事人查询方可明知,本身当事人也并不负担告知义务,并且这中间还有可能存在欺诈之风险。其次,债权让与权利变动与通知中间可能存在时间差,通知很有可能无法正确传达信息,现如今通知又不再是债权让与之生效要件,当事人没有也不可能对潜在之受让人一一进行通知。再次,在未来债权让与之中,如若债权尚未发生或者债务人根本还未确定,那么根本没有通知的可能。应当说通知主义无法保障交易安全。最后,在新型债权让与例如大宗债权让与中,对债权要进行一一查询,几乎不可能。①参见李宇:《债权让与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法学研究》2012年第6 期。通知虽是一种公示方法,但事实上通知难以称其为一种妥当的公示方法,或者说难以发生公示之效力。
(三)登记主义
之前笔者已经借助方新军教授对于权利客体层次的划分中提到:实际上在第三层次的权利上,权利证券化或者登记才是最优的公示方式。同样的,在第四层次的权利客体上,主要体现的制度即是让与担保。同样外部观察的方式是权利证券化和登记。②参见方新军:《权利客体的概念及层次》,《法学研究》2010年第2 期。由于指名债权之让与多发生在个别交易之中,难以像票据一样进行权利证券化之公示方法。故而登记主义便成为权利观察的最佳方式和手段。而权利本身是一种抽象存在,但当一个权利成为另外一个权利的客体时,它最好能够通过有体的载体表现出来,否则以它为客体的权利的不确定性就非常明显。③同注②。而由于债权本身是一种权利,它不能如有体物一般通过交付来表现权利移转,那么对其有体化最好的方法只能是登记和权利证券化。而无记名有价证券的最佳方式是权利证券化,记名有价证券的最佳方式则是登记。登记主义使得权利得以形成外观,也使得笔者之前所讨论的抽象原则得以产生适用之空间。同时,由于公信力之形成,善意取得制度也具有适用之空间,并且得以适用一些复杂的新型债权让与之要求,如未来债权让与,大宗债权让与以及保理等。而李宇博士则在《债权让与的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一文中,运用“制度内情境分析法”,依次考察让与主义、通知主义、登记主义三种主要制度对各方当事人及第三人的影响,发现登记主义更为公平,更有效率。④同注①。他更进一步主张,债权让与登记制,表明公示原则为适用于一切财产权转让的基本原则,性质上为财产法总则上的原则。⑤同注①。而居于关键的就是财产权关系的公示制度。相对的财产权关系可以不必公示,绝对的财产权关系一定要有效地公示,公示制度越有效能,交易者的选择自由越大,交易成本也越低。⑥参见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 页。到目前为止,最有效能的公示方法当然还是财产权关系的登记制度。⑦同注⑥。
问题到此并未得到最终解决。如何将之前笔者所论述的债权让与的处分行为性、债权让与的分离原则与抽象原则,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让与主义,与登记制度加以无缝镶嵌。同时这种理论是否在我国实证法上具有解释空间,这是基于立法论还是解释论之视角?是否可能会导致法律体系的不协调甚至是错乱?如若采登记制度,是登记对抗主义还是登记生效主义?通知此时是否还有存在意义?如若存在,它在债权让与中承担着何种功能与角色?这均是笔者不得不进一步必须探讨的问题。
五、债权让与分离原则、抽象原则、登记制与我国实证法
第一,基于笔者之前的论述,《民法典》第546 条第1 款是让与主义与分离原则的体现。而笔者之前已经提到,让与主义严格意义上而言不属于一种公示方法,而是一种确定债权让与优先顺序的手段,而登记制则是债权让与的最佳公示方法。那么毫无疑问,登记制不仅不会与让与主义发生矛盾,反而是让与主义的润滑剂,它真正得以疏通了德国法关于债权让与理论的规定,使得抽象原则产生适用空间。而在我国实证法上,尽管通说并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但在债权让与领域并非没有无因性之适用空间,票据行为无因性即为典例。如若引入登记制度,如若采登记对抗主义,分析之路径为:债权让与行为使得权利发生变动,依照无因性理论,如若债权让与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债权让与行为仍然有效,那么权利仍然发生变动,权利人得以请求不当得利之返还。但未经债权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登记对抗主义的最大问题还是在于,抽象的债权让与行为仍然没有被有体化,如若采登记对抗主义,则仍然要走上“债权让与权利变动以债权让与契约之成立生效为判断标准”这条老路上来,故为笔者所不采;而登记生效主义的分析路径则为:登记是债权让与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也是抽象的债权让与行为有体化的体现和标志,未经登记,债权让与不发生效力。故基于登记而产生公信力,第三人得以知晓债权让与中的权利细则,对其中利弊予以审查和取舍。也正如李宇博士所言:“不公示主义之弊,正是登记主义之利。不公示主义之利,却未必是登记主义之弊。”①李宇:《债权让与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法学研究》2012年第6 期。并且这其中的成本问题也需要予以考虑:如若承认抽象原则,那么登记机关仅需要审查登记事项本身,当处分行为的原因抽离于行为时,其行为效力不必考虑其原因时,登记机关对于原因行为相关资料可以完全不要或仅供参考,检验成本当然较低。抽象原则在登记机关的合法性检验成本上无论如何会小于有因原则。②参见苏永钦:《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载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 页。而反之,若采要因说,为保证公示之正确性,登记机关就有理由对原因行为,即债权让与契约进行审查。这样容易使得公法进一步介入私法关系的范围,不利于私法自治原则之贯彻。而反之如若采抽象原则,则不仅节约经济成本,减少审查负担,而且有利于贯彻私法自治原则,使得当事人对自己的利益作出最佳判断,也符合市场经济理论的要求。
第二,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即是通知是否有存在之必要。笔者认为,通知不再有存在必要。因为通知本身就是一种公示制度,依照我国《民法典》第546 条第1 款规定,通知是保护债务人之手段,在我国不属于一种公示方法,因为通过笔者之前的分析,我国债权让与在理论上应沿袭我国台湾地区和德国的让与主义。那么既然让与主义不是一种公示方法,那么登记制在我国毫无疑问有适用的空间。登记制完全可以替代甚至在一种更优的意义上取代《民法典》第546 条第1 款规定。因为债务人基于债权让与登记得以很清晰明了地得知他该向谁进行清偿,而不再需要通知而发生错误清偿也能产生债务人清偿之效果这种人为的立法拟制来保障债务人之利益。因为如果此时债务人再发生错误清偿,例如,债务人向债权让与未经登记之受让人2 进行清偿,而不向债权让与已经登记之受让人1 进行清偿,那么债务人也必须对其过失承担责任,这正是登记簿公信力之要求。逻辑上会产生的另一种可能是:在债权二重让与中,受让人均未履行登记的情况。那么让与人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典》第221 条,基于有效的债权让与契约按照约定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债权人处分债权的,不发生债权让与权利变动的效力。预告登记后,如果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债权让与登记之日起3 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这与让与主义并不违背,因为让与登记此时已然是处分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那么受让人2 如果先于受让人1 完成债权让与登记,那么他也可以基于处分行为成立在先,从而先于受让人1 取得权利,这仍然符合“时间在先,权利在先”规则的要求。而进一步而言,如若受让人均未履行登记,也未在规定期限内进行预告登记,那么先获清偿之受让人得以享有债权。如若均未与清偿或者债务人仍然向债权人清偿,那么债权让与契约成立在先的,优先获得债权。自是当然之理。而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如若采债权让与登记制,能够避免《合同法》第80 条第1 款带来的比如在债权二重让与中带来的如果债务人向并非是真正的权利人清偿,他得以退出债的关系,但是,权利人还得费劲人力物力去向债权人或者其他受让人主张权利这一问题,对真正权利人的保护更为周延,债务人如果基于过失而发生错误清偿,承担责任本为分内之事,也没有不公平之嫌疑。
第三,引入债权让与登记制不仅不会打乱我国现行法的体系,反而会使得现行法的适用在逻辑上更为圆融,体系上更为前后一致。《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45 条规定了债权让与的类推适用方法。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45 条规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合同法》第124 条和174 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权利转让或者其他有偿合同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首先适用《合同法》第174 条的规定,再引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类似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453 条也有体现:“关于物的买卖的规定,准用于权利买卖和其他客体的买卖。”但是由于权利属于无体物,依照现行法的规定买卖合同中所规定的内容也没有参照适用之可能,尤其是在债权让与通知的具体方法和法律效力问题上,这与买卖合同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①参照方新军:《合同法第80 条的解释论问题——债权让与通知的主体、方式及法律效力》,《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年第4 期。而《民法典》第646 条又有相关的规定。②《合同法》第124 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由于债权让与属于无体权利的让与,又缺乏有体化的公示方法,故而使得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45 条《民法典》第646 条的类推③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45 条、《民法典》第646 条采用的措辞是“参照适用”,其规范性质而言均是参引性规范(Verweisungsnormen),但在法学方法论上,对“准物权行为”的适用方法是“类推”。所谓类推适用,指的是将法律明文之规定,适用到该法律规定时未直接加以规定,但其规范上之重要特征与该规定所明文规定者相同之案型。在类推适用上,最引起争执之问题为:如何认定拟处理之案型与法律明文规定之案型,分别所具之规范上有意义的特征为相同,亦即其规范意旨。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5 版),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92-495 页。适用顺序模式变得名存实亡。一方面,煞费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番苦心。另一方面,债权让与行为作为准法律行为而不能类推适用法律行为的有关规定,那么又何谓“准法律行为”呢?
第四,更进一步而言,引入登记制甚至可以完成与《民法典》物权编的贯通。权利本身就是物权的客体,然而我国物权法除了规定应收账款质押制度,将债权让与制度规定在合同法中,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因为基于债物二分体例,即使是德国法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德国法将债权让与规定在债法总则中,实际上仍然混淆了债权让与本质上是一个权利变动问题,涉及的其实是物权法中权利变动的问题,它仅仅因为客体是比较特殊的债权,而权利本身就是物权的客体,而不应当被规定在债法之中,而更应当规定在物权编之中。这一问题,也希望将来民法典编纂者们予以关注,这样才能让权利这一物权客体找到“真正的栖息之所”。引入登记制之后,关于债权让与这个准物权行为的诸多问题也有了类推的空间。比如争议颇大的善意取得问题,则因为具备足够的权利外观,而产生公示公信主义的要求。则可以类推适用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与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④当然对于我国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这一立法,学界批判甚巨,因为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我国台湾地区,都只有动产适用善意取得,而不动产如若要发生善意取得问题,也是基于登记错误,那么,基于不动产登记簿之公信力,善意之第三人仍然可以获得不动产所有权,而本身的权利人可以让登记机关或者侵权人承担责任,根本不需要再刻意创造出一个所谓不动产的善意取得,纯属画蛇添足。对此比较精彩的批判,可参见朱广新:《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限度》,《法学研究》2009年第4 期。当然在解释论上也不乏优秀作品来支撑第106 条关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规定,参见叶金强:《物权法第106 条解释论之基础》,《法学研究》2010年第6 期。从而在债权二重让与中,如若发生登记错误,例如本身应当登记给受让人1,却错误登记为受让人2。那么受让人2 即可基于善意取得或者公信主义取得债权,并且受让人1 不得向受让人2 主张不当得利返还。另外,有关于物权编中关于登记的规定均得以有类推空间。从而彻底解决了债权让与的类推适用之难题。当然,有关于债权让与契约这一原因行为的规定,也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从而真正使民法体系实现逻辑的圆融与体系的自洽。
六、结 语
我国民法学界似乎有一种“反智主义”倾向,而不承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分离原则与抽象原则其实如果能够自圆其说,也能够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只可惜从现行法上笔者只看到对于债权让与问题的含糊不清与逻辑错乱。法律应当具有形式理性,否定一种法律逻辑,应代之以另一种法律逻辑。⑤参见李宇:《债权让与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法学研究》2012年第6 期。民法研究者多受过良好教育,我们不应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落入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之泥潭,这种反智倾向让人不禁想起被绑在火把上的人,无论见到真正的现实世界的那个人如何诉说和描述,火把上的人根本无法理解。诚如佩雷尔曼教授所言:“真理并未给理性选择留下空间,因为在此意义上的所有选择都意味着对真理的无知。”⑥Perelman,Justice,Law,and Argument,p.166.转引自朱庆育:《意思表示解释理论——精神科学视域中的私法推理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 页。
解释论的确对于我国目前的民法学研究甚有助益,但如若过于强调解释论,则容易落入概念法学的窠臼,这对我国民法学的长远发展而言并没有帮助。必须要有更多基于立法论视角的讨论,尽管工程浩大,前路漫漫。但这并非是不为之努力之借口,理论也是基于多元化才能够百花齐放,法律人对这一问题的心态上更应该开放包容,尤其是在《民法典》编纂这一热潮的节骨眼上。苏永钦教授多年前研究我国民法典编纂问题时说过的话一语惊醒梦中人,尽管时光荏苒,但这段话对于现今之大陆,甚至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值得大陆民法学者反复咀嚼、回味与思考:“民法典追求的是合理、可行的市场规范,以及逻辑、方便操作的规范体系,不是民族主义的宣言书,立法者若能以全球的视野,把目光梭巡于内外之间,多方比较,深入考察,所谓中国特色即可自然浮现,无必要的强求不同,只会降低体系的理性,升高运作的成本,最多换来一点精神胜利,实在不值。”①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