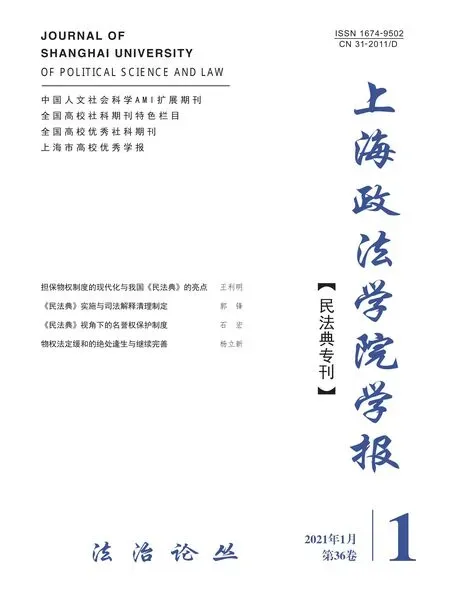论债务免除行为的性质
——以类型化为视角
2021-01-28孙文桢
孙文桢
一、问题的提出
债务免除,乃是债之关系消灭的一种原因。本文标题所谓“债务免除行为的性质”,系指债务免除行为到底属于契约抑或属于单独行为。关于此问题,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议,迄今尚未平息。我国《民法典》①本文中所称“我国《民法典》”或“《民法典》”,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5 条规定:“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债权债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但是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拒绝的除外。”该规定在“单独行为”和“契约”之间的摇摆不定,充分表明对债务免除行为的性质问题进行研究实有其必要性。同时,为能真正地发现问题并有效地解决问题,本文的研究从类型化的角度进行。此所谓“类型化”,系指按研究的需要而对债务和债务的免除进行类型区分。
此处需预先说明两点。其一,债法理论对“债之关系”的含义历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债之关系,系指个别的给付关系,而广义债之关系,则指包括了数个债权和债务(即数个狭义债之关系)的法律关系②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 页。。各国民法在处理债务免除问题时,对“债之关系”均取其狭义。故此,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对“债之关系”亦取其狭义,并在此狭义基础上使用“债”“债务”“债权”等相关概念。
其二,本来,按债法理论,“债务免除行为的性质”并非仅指债务免除行为到底属于契约抑或属于单独行为,而是亦包括其他方面,诸如债务免除行为属于有因行为抑或无因行为、属于无偿行为抑或有偿行为、属于要式行为抑或不要式行为,等等。但是,鉴于此处的“其他方面”或者已有定论,或者未见争议,而学界近些年来在提及债务免除行为的性质问题时,如无特别情况,亦均指债务免除行为属于契约抑或属于单独行为这个问题,故此,为保留共同的交流平台,为使学术观点能够有机会发生碰撞交锋,本文所谓“债务免除行为的性质”,其意仅指债务免除行为到底属于契约抑或属于单独行为。
二、已有立法模式的瑕疵
迄今为止,关于债务免除的立法,共有三种模式,即“契约模式”“单独行为模式”“单独行为修正模式”。与此相应,关于债务免除行为的性质,亦有三种学说,即“契约说”“单独行为说”“单独行为修正说”。鉴于此三种学说和三种立法模式内容分别对应,且相互间结合紧密而难以截然分离,为叙述方便,本文拟从立法模式的角度展开论述,而对相应学说的内容则在论述过程中适时提及。
深入研究即可发现,这些立法模式或者无法适用于所有债务,或者制度设计有违科学,从而均暴露出了其各自不同程度的瑕疵。
(一)契约模式
契约模式认为,债务免除应当通过债权人和债务人成立契约的方式进行,债权人的单方意思不足以免除债务。债务免除属于处分行为,故而此处的“契约”属于处分性质的契约,即所谓“准物权契约”①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4 页。。从法制史角度观察,契约模式的最早立法例当推罗马法。罗马法上关于“免除”的规定主要有两种方式,即“正式免除”(acceptilatio)和“略式免除”(acceptilatio Aquiliana)。正式免除系市民法上之免除方式,略式免除为万民法上之免除方式。正式免除的方式,因各个契约成立方式的不同而不同;易言之,以某种方式成立契约债务,亦应以该方式免除之而后方可发生债务免除的法律效力。略式免除不像正式免除那样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而只需债权人和债务人达成简单的口约(pactum de non petendo)。该口约亦称为“不索债的简约”。凭此简约,债权人允诺不向债务人索债,于是在效果上即相当于免除了其债务。②参见丘汉平:《罗马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396 页。
罗马法以契约免除债务的做法影响深远,后世大陆法系的普鲁士、法国、德国、瑞士、保加利亚、苏俄等国,皆以债务免除为契约③参见《普鲁士邦法》第一部第十六章第379 条、第380 条和第388 条,《法国民法典》第1285 条、第1287 条,《德国民法典》第397 条,《瑞士债务法》第115 条,《保加利亚债和契约法》第108 条,《苏俄民法典》(1922年)第129 条。。其中,德国的规定简洁明了,堪称契约模式的典型代表。《德国民法典》第397 条共两款,其第1 款规定:“债权人以契约对债务人免除其债务者,债务关系消灭。”其第2 款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订立契约承认债务关系不存在者,亦同。”④《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 页。除这些大陆法系国家外,英美法系诸国亦将债务免除视为契约。⑤参见邢建东:《合同法(总则)——学说与判例注释》,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 页。
综观学者们的论述可知,契约模式的确立系基于三方面的理由。其一,债之关系具有特殊性,不能无视债务人的意思。如果仅凭债权人的单方意思即可发生债务消灭的效果,则正是对债务人意思的无视⑥参见胡长清:《中国民法债篇总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602 页;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9 页;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 页;江平:《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1 页;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 页。。其二,债权人免除债务人的债务,是给予债务人以恩惠,但恩惠不得强加于人,否则就损害了债务人的人格独立。通过契约免除债务,在给予债务人以恩惠时首先征得债务人的同意,这正是尊重债务人的人格独立。⑦同注①,第873 页。其三,债权人免除债务人的债务,必有一定的动机或目的,因而不能断定该免除必定不会有损于债务人的利益。为避免债权人滥用权利从而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应当对债权人免除债务的方法和效力有所限制,而以契约免除债务即可实现此目的。⑧参见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下册),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845 页。这三方面理由,亦构成了“契约说”的内容。
不可否认,衡诸债务免除千姿百态的实际情形,契约模式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堪称合理。诚然,债务人的意思不能被无视,从而债务免除无论意味着给予债务人以恩惠(例如贷款人免除借款人的还款债务),抑或意味着在给予债务人以恩惠之同时亦损害债务人利益(例如,公司免除为学手艺而向公司提供有偿服务的学徒工的债务①周枏:《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14 页。),抑或意味着损害债务人利益(例如,公司免除为学手艺而向公司提供无偿服务的学徒工的债务;又如,甲为使马得到运动而借用于乙,乙免除甲的债务②这个关于马的借用的例子来自我国台湾地区戴修瓒教授《民法债篇总论》(下册)(会文堂新记书局1947年版)第530 页。戴修瓒教授举此例意在说明“债之关系固多为债权人之利益,然为债务人之利益者,亦或有之”。问题在于,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借用合同系实践合同,因而在其生效时,出借人已无债务,更遑论债务被免除。所以,笔者认为戴修瓒教授的这个例子欠恰当。不过,按照我国《合同法》和《民法典》合同编对赠与合同的规定并衡诸法理,借用合同这个无名合同完全可以被视作赠与合同,从而借用合同就成了诺成合同。基于此种认识,笔者在文中就依然使用了这个例子。另,关于借用合同可以被有条件地视作赠与合同,可参见史尚宽先生所著《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 页上的论述。),均应当征得债务人同意即采契约模式,其间理由或在于尊重债务人的人格独立而不对其强加恩惠,或在于保护债务人的利益。不过,在这三种情形之外,债务免除尚有第四种情形,即该免除既不会损害债务人的利益亦非给予债务人以恩惠。此种情形下,契约模式就难称其为合理。试举一例予以说明,甲公司与乙贫困户达成赠与合同而承诺赠与乙贫困户五万元。乙贫困户如果拟免除甲公司的债务,那么,该免除就既不是给予甲以恩惠(乙这时只是不愿意接受甲的恩惠,而并非在给予甲以恩惠),亦没有损害甲的利益。该免除如果采取契约模式,则在甲不同意免除时,乙就必须接受甲的恩惠,而这显然违反了“恩惠不得强加于人”的生活常理,有悖于尊重他人人格独立的人权观念。换言之,契约模式此时暴露出了瑕疵。
(二)单独行为模式
所谓“单独行为模式”,系指债务免除无须债务人的同意,仅债权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产生债务免除的效力③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4 页。。换言之,单独行为模式并非指债务免除必须采取单独行为方式,而是指可以采取单独行为方式。从法制史角度观察,单独行为模式的产生晚于契约模式,乃是作为契约模式的反对物而出现的。采取单独行为模式而规制债务免除的立法例主要有《奥地利民法典》(第1444 条)、《日本现行民法典》(第519 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43 条)和《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415 条)。其中,日本民法典比较特别,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公布的民法典(史称“旧民法典”),由于深受法国民法典的影响,规定债务免除为契约即所谓“合意上的免除”,而以债务人之承诺为必要(日本旧民法财产编第504 条至第507 条)④张谷:《论债务免除的性质》,《法律科学》2003年第2 期。。由于那场著名的“民法典论争”,该旧民法典被无限期推迟施行。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施行的新民法典即日本现行民法典,在债务免除问题上,摒弃了旧民法典的契约模式而改采用单独行为模式,其第519 条规定:“债权人对于债务人表示免除债务的意思时,其债权消灭。”⑤参见《日本民法典》,王书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96 页。日本民法的做法堪称单独行为模式的典型代表,为其他采用同样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所追随。
支持单独行为模式的观点可称之为“单独行为说”。该说认为,权利可以自由抛弃,债权人可以单方面抛弃自己的债权⑥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第1 版,第281 页。,而债务人被免除债务,不过是债权人抛弃债权的间接结果,债务人既因此而受利益,当然就没有征得其同意的必要;并且,如果免除必须征得债务人的同意,那么在债务人不同意免除时就会发生债权人不得抛弃债权的结果,这显然违反事理⑦胡长清:《中国民法债篇总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603 页。。在笔者看来,此等说法难以服人。
在法治社会里,债权作为权利之一种固然可以抛弃,但该抛弃却不能由债权人任性为之,而是必须顾及债务人的利益,此为私法诚信原则之应有之义。同时,债权人免除债务人的债务,并不必然就意味着债务人因此而受利益。前文在分析契约模式的瑕疵时指出,债务免除亦可能意味着损害债务人的利益。在此情形下,债务免除采取单独行为模式就难称其为妥当。退一步讲,即使债务免除意味着给予债务人以恩惠,衡诸“恩惠不得强加于人”的生活常理和尊重他人人格独立的人权观念,亦应征得债务人同意。“赠与”被包括我国在内的多国规定为契约而非单独行为,即为该常理和观念的突出体现。至于说如果债务人不同意免除自己的债务,则会发生债权人不得抛弃债权这种结果,这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都可谓正常,而并无违反事理之处。
笔者对前述诸般支持单独行为模式的理由作如此批驳,意在揭露该模式的瑕疵,即该模式在债务免除的绝大多数情形下都无法适用,而只能适用于极少数情形。在前文所举甲公司和乙贫困户之间赠与合同的事例中,乙免除甲的债务既非给予甲以恩惠,亦不会损害甲的利益,因而就没有必要征得甲的同意。换言之,该免除可为单独行为。衡诸生活经验和常识,这种债务免除情形应为极少数。
(三)单独行为修正模式
鉴于在单独行为模式中,债权人可能滥用权利损害债务人利益,因此有必要对债权人的免除行为进行限制。具言之,原则上债权人可以单独为债务免除,但是如果债务人对免除表示反对的,则不发生免除的效力,是为单独行为修正模式。采用该模式的民法有《意大利民法典》和我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第1236 条规定:“债权人免除债务的意思表示的通知送达债务人时,发生债的消灭,但是被通知的债务人在适当期间内不愿接受该意思表示的,不在此限。”我国《民法典》第575条规定:“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债权债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但是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拒绝的除外。”
单独行为修正模式在域内外均不乏支持者,这些支持者的观点可谓之“单独行为修正说”。柳经纬教授认为,契约模式和单独行为模式各有利弊,不可一概肯定或否定,而应在这两种模式之外寻求“债的免除之第三条路”,即将此两种模式结合起来。①柳经纬:《感悟民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 -266 页。我国台湾地区的戴修瓒教授则认为:“由立法论言之,免除方法,固不必采用契约,而单独行为,似可稍加限制。例如规定免除不得违反债务人之意思,又如债务人得抛弃免除之效力等。”②戴修瓒:《民法债篇总论》(下册),会文堂新记书局1947年版,第530 页。日本学者小池隆一先生亦说:“免除虽为债权人单独行为,然不得违反债务人之意思为之。”③[日]小池隆一:《日本债权法(总论)》,第383 页。转引自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4 页。
该修正模式的“修正”,表现在前述《意大利民法典》第1236 条和我国《民法典》第575 条的“但书”部分。该“但书”部分表明,该修正模式的确立者意识到了单独行为模式对债务人意思的无视,于是为尊重债务人的意思而将该意思纳入了考虑,从而展现出了向契约模式靠拢的态势。鉴于该修正模式既有别于单独行为模式亦不同于契约模式,本文将其单独列出而与其他两种模式并列。
该修正模式的根本瑕疵在于对债务人的意思处置失当(关于对此“处置失当”的详细论述,可见本文第四部分,此处略去)。该修正模式对债务人的意思处置失当,势必导致债务人滥用反对权,即在无资格拒绝债权人免除债务的意思时却表示拒绝,在无资格表示不愿接受债务免除的意思时却实施了此等表示;势必导致该修正模式尊重债务人意思的这个初衷被架空,最终成了挂羊头而卖狗肉——挂着尊重债务人意思的羊头,但却卖着债权人单方意思的狗肉。④应予指出的是,尽管同属“处置失当”,但意大利和我国民法在此“失当”的程度上尚存差别。《意大利民法典》将“赠与”规定于其“继承”编,而非“债”编。刘家安教授认为,《意大利民法典》此举既表明赠与被作为财产取得的原因看待,亦表明赠与契约的效力是财产权的直接变动而非设立债之关系。笔者赞同此观点,并据此而进一步认为,既然如此,则《意大利民法典》第1236 条(位于“债”编当中)所说的“免除债务”,就不包括免除赠与人的债务。换言之,在《意大利民法典》中,债务人得以放纵自己意思的机会就少些(只存于其他与赠与合同相类似的合同中)。相比之下,在我国《民法典》中,这种“放纵”的机会就多些。关于刘家安教授的观点,参见刘家安:《赠与的法律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5 期。
该修正模式的上述瑕疵,表明其制度设计有违科学,同时亦使其成为关于债务免除的三种立法模式当中最差者。三种模式当中,契约模式的瑕疵较小,单独行为模式的瑕疵较大,而该修正模式的瑕疵最大,可谓失败的立法模式。有鉴于此,在后文,除为批判目的之外,笔者将不再提及该修正模式。
三、债务免除的类型化
前文分析了三种债务免除模式的瑕疵。三种模式当中,单独行为修正模式因为其制度设计有违科学,导致该模式成为失败的立法模式。其余两种模式即契约模式和单独行为模式,其瑕疵均在于无法适用于所有债务而只能适用于部分债务。造成该瑕疵的根本原因在于思维上的以偏概全,即无论是契约模式的确立者和支持者,抑或单独行为的确立者和支持者,都认为各自所赞同的那种模式可以适用于所有债务,而前文所举诸例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究竟哪些债务适用契约模式,哪些债务适用单独行为模式?这其中有没有规律可循?如果有,这规律是什么?笔者认为,欲寻出此等问题的答案,需要从类型化的角度考察债务免除。
债务免除的类型化需以债务的类型化为基础。债法理论上并非没有债务的类型化,所有债务被划分为合同之债务、侵权之债务、不当得利之债务、无因管理之债务和其他债因所生之债务,此种划分即属于债务的类型化。凡债务的类型化,必须服务于特定的目标,而该目标则决定了债务类型化的特色。为服务于债务免除的类型化目标,债务的类型化亦必有其自身的特色。
(一)债务免除视角下债务的基本类型
前文在考察债务免除立法模式的瑕疵时指出,债务免除究竟是适用契约模式还是适用单独行为模式,取决于该免除之是否给予债务人以恩惠或者是否会损害债务人利益。如果债务免除意味着给债务人以恩惠或该免除将会损害债务人利益,则为表达对债务人人格独立的尊重或为保护债务人的利益,该免除就应当征得债务人同意,即采取契约模式。相反地,如果债务免除既不意味着给予债务人以恩惠亦不会损害债务人利益,则债务人对该免除就没有资格表示反对,债权人亦没有必要征得债务人同意,而完全可凭己方意思予以决定,即采取单独行为模式。借此倒推,本文对债务作如下两种基本划分。
第一种,依债务之目的而将其分为填补型债务和增益型债务。填补型债务的目的在于填补债权人的某种利益空白,而增益型债务的目的则在于使债权人的利益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只要抱有“填补”目的,即属于填补型债务,而不必要求用以填补的利益与将被填补的利益这两者间完全等同,超出或不足亦可。大多数债务都属于填补型债务,例如侵权之债务、不当得利之债务、无因管理之债务都是。就合同债务而言,双务合同和有偿合同中的债务均属于填补型债务,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的债务是交付标的物并移转其所有权,该债务的目的就在于填补买受人在价款利益上的空白(失去价款);买受人的债务是支付价款,该债务的目的就在于填补出卖人在标的物利益上的空白(失去标的物)。不仅如此,在某些无偿合同或者单务合同中,亦会存在填补型债务,例如自然人间借款合同中的还款债务即是。
增益型债务比较少见,其典型代表为在某些赠与合同中赠与人所承担的债务。此处之所以说“某些赠与合同”,乃是因为并非所有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债务均属于增益型债务。在有的赠与合同中,赠与人承担债务,其目的在于报恩、支付报酬、偿还人情债等诸如此类,此时的债务不属于增益型债务而属于填补型债务。例如,张三为报答李四曾经的救命之恩,与李四达成赠与合同,承诺赠与李四豪华别墅一套,张三的债务即属于填补型债务。虽然生命至高至贵,而一套豪华别墅的价值无论如何都不能与人命的价值相提并论,但张三的债务既然具有填补目的,即仍不失为填补型债务。在有的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之债务,其目的却不在于“填补”,而在于增加受赠人的利益,例如奖励、扶贫等,此时的债务即属于增益型债务。在前面所列举的甲公司与乙贫困户达成赠与合同而承诺赠与乙五万元的情形,甲的赠与债务即属于增益型债务。①按《意大利民法典》第770 条和《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2433 条的规定,赠与被分为“奖励性赠与”和“报酬性赠与”两类。此种划分可以给我们以启发。笔者在文中将赠与人的债务分为“填补型债务”和“增益型债务”两类,即有受此启发的因素在其中。不过,比之《意大利民法典》和《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笔者在对赠与人的债务进行分类时根据研究的需要作了深化拓展:赠与人的“填补型债务”在支付报酬之外,尚有其他目的(例如报恩),而赠与人的“增益型债务”在奖励之外,亦有其他目的(例如扶贫)。
在债务免除的视角下,对债务做这种类型划分的意义在于:债权人免除填补型债务意味着给予债务人以恩惠,但免除增益型债务却只意味着债权人不愿意接受债务人的恩惠,而不意味着给予债务人以恩惠。
第二种,依债务本身是否附有债务人的利益而将其分为自利型债务和非自利型债务。债务对债权人而言意味着利益,此点已属常识,自不待论。与此同时,我们还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情形,债务本身亦附有债务人的利益于其上,例如工人以练习为目的,在工厂服务;又如学徒工为学手艺,而为企业提供服务。①此处所举“工人”和“学徒工”两例,分别来自戴修瓒教授的《民法债篇总论》(下册)(会文堂新记书局1947年版)第530 页和周枏教授的《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14 页。这种附有债务人利益于其上的债务,即为自利型债务,而其余那些无债务人利益附于其上的债务则为非自利型债务。
在债务免除的视角下,对债务做这种类型划分的意义在于:债权人免除自利型债务将会损害债务人的利益,而免除非自利型债务则不会损害债务人的利益。
(二)债务免除视角下债务的综合类型
前文在划分债务的基本类型时,采取了两个不同的标准,这就决定了两种划分的结果存在着重复交叉。衡诸数学上排列组合之原理,二二得四,这种重复交叉共有四种情形,从而产生了四种综合类型的债务,即填补兼非自利型债务(例如,借款人的还款债务、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债务)、填补兼自利型债务(例如,学徒工为学手艺而向公司提供有偿服务的债务)、增益兼自利型债务(例如,学徒工为学手艺而向公司提供无偿服务的债务、为使马得到运动而出借马的债务②此处所举“马的借用”事例,来自戴修瓒教授的《民法债篇总论》(下册)(会文堂新记书局1947年版)第530 页。)和增益兼非自利型(例如,甲公司与乙贫困户达成赠与合同而承诺赠与乙五万元的债务)。这四种综合类型的债务,正是考察债务免除行为的性质时将直接面对的债务类型。
为叙述方便,后文将这四种类型债务中的第一种即“填补兼非自利型债务”称为“纯填补型债务”,将最后一种即“增益兼非自利型债务”称为“纯增益型债务”。
(三)债务免除的类型化
上文通过分析归纳,将债权人免除债务人债务时所可能面临的所有债务划分为四种综合类型。债权人如果免除的是前三种类型的债务,就不能任由己方单独决定,而应当征得债务人的同意即应当采取契约方式。这三种类型的债务中包含有填补型债务(第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和自利型债务(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免除填补型债务(例如免除借款人的还款债务)意味着给予债务人以恩惠。鉴于恩惠不得强加于人,为尊重债务人的人格独立,此时的免除就应当征得债务人的同意即应采取契约方式。同时,免除自利型债务(例如,免除学徒工为学手艺而向公司提供服务的债务、免除出借人为使马得到运动而出借马的债务)将会损害债务人的利益。为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此时的免除亦应征得债务人的同意即应采取契约方式。
对于第四种类型的债务即纯增益型债务(可参考前文所举甲公司赠与乙贫困户五万元的事例)而言,一方面,其免除并不意味着债权人给予债务人以恩惠,而只意味着债权人不愿意接受债务人的恩惠;另一方面,其免除亦不会损害债务人的利益,因为这种类型的债务属于非自利型,并无债务人的利益附于其上。既然此种情形下的债务免除与债务人的利益毫无关涉,则债权人就没有必要征得债务人的同意。换言之,此时的免除,通过债权人的单独行为即可实现,而无须采取契约方式。
对于纯增益型债务的免除,如果法律规定必须采取契约方式,会发生怎样的后果呢?纯增益型债务对债权人而言实系恩惠,如果其免除必须采取契约方式,则在债权人欲免除此债务而债务人不同意免除时,此债务即无法免除。这实质上是债务人在强迫债权人接受其恩惠,而恩惠不得强加于人,乃属生活常理,亦为尊重他人人格独立之必然结论。
观诸民事生活的丰富实践并衡诸债法理论可知,通过单独行为而免除(纯增益型)债务这种情况只发生于赠与合同和其他诺成单务无偿(即诺成、单务、无偿这三者俱备,下同)合同中,赠与合同堪称诺成单务无偿合同的典型代表③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上),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46 页。,通过考察赠与合同的原理即可寻找到问题的答案。在赠与合同中,作为债务人的赠与人享有一项特权即任意撤销权④关于此任意撤销权所受限制,各国(地区)间并不相同。按我国《民法典》第658 条(相当于《合同法》第186 条)规定,在“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享有任意撤销权。。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任意撤销赠与,该撤销系单独行为而无须作为债权人的受赠人同意。债之关系的双方之间相互平等,应能相互制约,方称合理。在笔者看来,受赠人仅凭自己的单方意思(单独行为)即可免除赠与人的债务,此权利正与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对称匹敌,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双方间的相互制约。
(四)契约在债务免除方式中的主导地位
在前述四种综合类型的债务中,可以通过单独行为予以免除的债务只有纯增益型债务这种类型。从该现象观之,似乎可通过单独行为而免除的债务在所有债务中的占比达到了四分之一,但事实并非如此。纯增益型债务只存在于赠与合同和其他诺成单务无偿合同当中。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背景下,有偿合同和双务合同的数量最多,单务合同和无偿合同的数量较少,至于诺成单务无偿合同的数量就更堪称稀少。即使在这稀少的诺成单务无偿合同中,债务人的债务亦并不总是纯增益型,还可能是其他类型,例如赠与人的填补型债务。由是观之,纯增益型债务在所有债务中占比甚微,堪称极少数。如将所有债务比作海洋,则纯增益型债务就只不过是其中几朵浪花而已;如将所有债务视为森林,则纯增益型债务就只不过是其中几株小树罢了。既然纯增益型债务在所有债务中的占比如此微小,而只有纯增益型债务才可通过单独行为予以免除,那么,在债务免除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者就不能是单独行为而只能是契约了。换言之,在债务免除方式的王国里,契约占据着绝大部分天下,而单独行为只是偏安于一隅。
在债务免除行为的性质问题上,“契约说”和“单独行为说”截然对立。如前文所述,“契约说”认为任何债务的免除都应采取契约方式,而“单独行为说”则主张任何债务的免除皆可通过单独行为来完成。显而易见,这两种观点均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契约说”没有意识到契约在债务免除的世界里只是居于“主导地位”这个事实,企图以契约横扫债务免除的整个世界,结果是费力不讨好,而“单独行为说”竟然亦抱有同样的企图,那就更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四、关于《民法典》第575 条的修正
关于债务免除,我国《民法典》第575 条规定:“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债权债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但是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拒绝的除外。”该条规定虽然位于《民法典》合同编通则,但根据《民法典》第468 条的规定①我国《民法典》第468 条规定:“非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适用有关该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本编通则的有关规定,但是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除外。”和参与《民法典》编纂的权威学者的意见②参见王利明:《论民法典合同编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法学论坛》2020年第4 期。,合同编通则发挥着债法总则的功能,因此该条规定所谓“债务”,即涵盖了所有种类的债务,而不限于合同债务。
不难看出,《民法典》第575 条规定的债务免除模式属于本文第二部分已经否定过的“单独行为修正模式”,而同属于该修正模式的尚有《意大利民法典》第1236 条。在前文,笔者只是简单地指出该模式的根本瑕疵在于对债务人的意思处置失当,而未展开论述。现在,可以通过分析《民法典》第575 条的瑕疵而展开相关论述了。
(一)《民法典》第575 条存在的问题
《民法典》第575 条最显著的特色在于以单独行为为主导,而辅之以债务人的拒绝权。前文的分析表明,在债务免除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并非单独行为,而是契约。据此,《民法典》第575条将单独行为作为主导即因缺乏事实依据而难称其为科学。
《民法典》第575 条的“但书”部分表明立法者有意尊重债务人的意思,这无疑值得肯定,因为绝大部分的债务免除都离不开债务人的意思。但是,与债务免除的实际相互比较即不难发现,该法条在具体安排债务人的意思时却处置失当。此“处置失当”包括“放纵”和“无视”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有的情形(见前文所举甲公司和乙贫困户之间赠与合同事例),债务免除(乙贫困户免除甲公司的债务)既非给予债务人以恩惠,亦不会损害债务人的利益,因而债务人就没有资格对此免除表示拒绝,债权人亦无必要征得债务人的同意,而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单独行为完成债务免除。但是,按照该第575 条,只要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免除意思在合理期限内表示了拒绝,该免除即告破产,其结果就是债权人(贫困户)不得不接受债务人(甲公司)的恩惠。这显然难以称其为妥当,既违反了“恩惠不得强加于人”的生活常理,亦有悖尊重他人人格独立的人权观念。在债务人没有资格表示拒绝时,法律却允许其表示拒绝,是为对债务人意思的“放纵”。该“放纵”的存在,势必导致债务人滥用拒绝权,从而侵害债权人的行为自由。
另一方面,在有的情形(见前文所举贷款人免除借款人的还款债务、公司免除为学手艺而向公司提供服务的学徒工的债务、马的借用人免除出借人的债务诸例),债务免除或者意味着给予债务人以恩惠或者将会损害债务人的利益。此时,或者衡诸“恩惠不得强加于人”的生活常理和尊重他人人格独立的人权观念,或者为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免除债务均需征得债务人同意。但是,按照《民法典》第575 条,只要债务人没有在合理期限内对债权人的免除意思表示拒绝,该免除即告成功。此处的问题在于,“没有在合理期限内表示拒绝”并不总意味着“同意”。债务人之“没有在合理期限内表示拒绝”,固然可能意味着同意,但亦可能意味着从来就不知道债权人免除债务的意思(例如,债权人将该意思发到了债务人的电子邮箱,但却没有通知债务人,而债务人亦一直没有打开过邮箱),还可能意味着在是否拒绝这个问题上一时拿不定主意。此处的后两种情形均属于“没有在合理期限内表示拒绝”,但却均不属于“同意”。在需要债务人同意才能免除债务时,法律却任由债权人以其单独行为而免除债务,是为对债务人意思的“无视”。该“无视”的存在,势必导致立法者尊重债务人意思的初衷被架空,而出现“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挂着尊重债务人意思的羊头,但却卖着债权人单独意思的狗肉。
除上述两个重大瑕疵之外,《民法典》第575 条还有两处小的瑕疵。其一,“但书”部分中的“合理期限”如何确定,颇费思量。究竟多长时间为合理?依据何在?该期限应当自何时起算?自债权人免除债务的意思表示发出时起算?自该意思到达债务人时起算?自债务人知悉该意思时起算?抑或自债务人了解该意思时起算?等等。此等问题不得到合理解决,势必使《民法典》第575 条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依笔者之愚见,将来修正《民法典》第575 条时,此“合理期限”应予删除。其二,“债权债务部分或者全部”的表述问题。诚然,债权人免除债务人债务时,既可能免除部分债务亦可能免除全部债务。就此而言,《民法典》第575 条明确提出“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堪称周到合理。但是,紧接于其后的表述“债权债务部分或者全部”,却显得罗嗦而且拗口。
(二)对《民法典》第575 条的修正
鉴于《民法典》第575 条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建议修正如下:
“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被免除的债务消灭。
债权人免除债务人的债务,应当经过债务人同意,但该免除同时具备下列两项条件的,则不必经过债务人同意:
(一)该免除不会损害债务人的利益;
(二)该免除并不意味着给予债务人以恩惠,而只意味着不接受债务人的恩惠。”
关于该修正,特作如下四点说明(为叙述方便,下文将该修正后的法条统称为“修正后法条”)。
说明之一,关于修正后法条的结构。修正后法条共两款,第一款规定免除是债之关系消灭的原因,部分免除则部分消灭,全部免除则全部消灭;第二款规定债务免除行为的性质。两款之间,第一款系“一般”,第二款系“特别”,合乎立法的技术规则。
说明之二,关于修正后法条的第一款。修正后法条第一款的前半句即“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若仅从文字表述而论,“债权人”实施“免除”行为,而此行为的对象又是“债务人”的“债务”,这似乎表明债务免除属于单独行为。不过,从联系角度观之,结合修正后法条第二款的内容作综合考察即可看出该前半句中的“免除”并非单独行为。同时,从历史角度观之,该前半句源自《合同法》之第105 条,与《合同法》第105 条之前半句完全相同。关于《合同法》之第105 条所谓“免除”到底系何种性质,可从权威著名学者的论述中获得答案。在《合同法》颁行11年之后,合同法权威崔建远教授论及奥地利、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在合同债务免除问题上采取“单独行为模式”这种做法时,特意说了一句:“我国《合同法》也应如此。”①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80 页。这个“也应”,表明在合同法权威崔建远教授看来,《合同法》第105 条中的所谓“免除”并非单独行为。著名民法学者孔祥俊教授认为《合同法》第105 条只是从免除系债的消灭原因这个角度规定免除的,而并不能从该法条中看出免除到底系何种性质。①孔祥俊:《合同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383 页。
修正后法条第一款的后半句即“被免除的债务消灭”,比《民法典》第575 条相应部分的内容更简洁明快,不但将《民法典》第575 条中的“终止”改成了现在的“消灭”②关于此种情形下到底该用“终止”还是“消灭”,学界有争议。笔者认为,“终止”和“消灭”在债之关系领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宜相互替代,而应严格区分。限于本文主题,文中此处仅表明观点,不展开论述。,而且用“债务消灭”表达“债之关系消灭”这个意思。用“债务消灭”表达“债之关系消灭”这个意思,其重大意义不在于简洁明快,而在于准确地揭示了债的本质。在探求债之关系的本质问题时,现代民法学的先驱者萨维尼先生曾论及债的本质。他说:“在这些紧密联系而不同的关系中,我们按照哪一个来确定债的本质呢?毫无疑问,依据债务人的关系,因为存于债务人方面的行为必要性构成了债的真正本质。”③Savigny,A Treatise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and The Limits of Their Operation in Respect of Place and Time, Translated by William Guthrie, 2ed., T.& T.Clark: Edinburgh, 1880, Sect.XXVI, Pp.194 -195.笔者赞同萨维尼先生的这个见解,认为债的本质在于债务而不在于债权,故而在此以“债务关系消灭”表达“债之关系消灭”这个意思。
说明之三,关于修正后法条的第二款。该款中“但书”前面的内容,明确规定债权人免除债务人的债务应当经过债务人同意,从而恰当地反映了契约在债务免除方式中的主导地位。至于“但书”中的那两项条件,表达的其实是本文在第三部分所论述过的“纯增益型债务”的免除,而整个“但书”部分的内容,正反映了前文已经论述过的原理,即债权人免除纯增益型债务,通过单独行为即可完成,而不必采取契约方式。同时,该“但书”中“不必”一语,亦系对债之双方间契约自由的承认。该“不必”表明:对于纯增益型债务的免除,固然可任由债权人以其单独行为来完成,但如果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愿意以契约方式来完成该免除的,则法律亦不禁止。④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4 页。
说明之四,关于实践与理论的一致。科学的认识论认为,实践乃理论之源头,而理论则指导实践。据此,具体到立法领域,立法实践就应接受法理的指导。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指出,契约在债务免除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适用于绝大多数债务免除情形,而单独行为方式只适用于极少数情形即纯增益型债务的免除。修正后法条正是这种理论的再现,两者完全一致。修正后法条以契约为主导,并辅之以单独行为,而建立起债务免除的机制。基于此,笔者将上述修正后法条处理债务免除问题的模式称为“契约主导模式”,而将与此模式相对应的理论称为“契约主导说”。
在债务免除的性质问题上,有学者先是明确主张债务免除应为契约,表明赞同“契约说”,接着详细地论述了债务免除之所以应为契约的诸多理由。其立场之鲜明、文采之飞扬、目光之犀利和征引之广博无不令读者佩服有加。但是,出乎读者意料的是,论述完诸多理由之后,该学者却突然扭转笔锋而认为《意大利民法典》第1236 条(即前文否定过的“单方行为修正模式”)亦值得借鉴。为了打消读者心头的疑虑,该学者给出了解释:“理论上如何圆融无碍是一回事,立法上如何适应现实,又是一回事,必须要极高明而道中庸,不可偏废。”⑤张谷:《论债务免除的性质》,《法律科学》2003年第2 期。对于此等放任实践与理论相脱节的做法,笔者实不敢赞同。萨维尼先生有言:“法学所探索和寻求的,乃是一种统一谐和、循序渐进的法理,找出适当的手段,而这可能才是整个国族所真正共通共有的。”⑥[德]弗里德里希·卡·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 页。
(三)第三条路究竟应当怎么走?
在债务免除的立法模式问题上,柳经纬教授认为,“契约模式”和“单独行为模式”各有利弊,不可一概肯定或者一概否定,因而最好的办法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走“债的免除之第三条路”⑦柳经纬:《感悟民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266 页。。笔者赞同此观点,但问题在于:这第三条路应当怎么走?
走这第三条路时,要将“契约模式”和“单独行为模式”两者结合起来,那么,这种结合应当是怎样的结合?是“契约模式”和“单独行为模式”两者平起平坐的结合,还是有主有次的结合?如果是有主有次的结合,那么何者为主何者为次?为什么?《民法典》第575 条就是对这第三条路的一种走法。该走法以单独行为模式为主而以契约模式为次。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在债务免除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契约方式而非单独行为方式。由是观之,《民法典》第575 条的走法就违反了事物的真相,而前述修正后法条的走法就合乎事物的真相。①此处可借用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鼻祖莱昂·狄骥的观点予以说明。狄骥认为,客观法先于制定法、判例法、习惯法等实在法而存在。在他看来,立法活动所产生的法律只有在符合客观法时才能真正发生效力。关于狄骥的相关观点,可参见(法)狄骥:《宪法论》(第一卷),钱克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6 页、第381 页。对“契约模式”和“单独行为模式”进行结合时,还有个怎样对待两者各自利弊的问题。既然各有利弊,那么在结合之前就应当先剔除各自的“弊”并同时保留各自的“利”。如前所述,两种模式都认为自己适用于所有债务。这显系错误的认识,因为契约模式适用于除纯增益型债务之外的其他债务,而单独行为模式则只适用于纯增益型债务。《民法典》第575 条无视两种模式各自的适用范围而贸然地将其结合,显系错误的结合,而前文指出的“放纵”和“无视”即为该错误的突出表现。相形之下,前述修正后法条所展示的结合就是科学的结合,因为该结合明确了两种模式各自的适用范围。
五、结论和余想
迄今为止,所有关于债务免除的学说和相应的立法模式,皆错误地未对作为免除对象的债务作具体分析,从而皆未认识到不同的债务,其免除乃具有不同的性质。本文认为,在纯填补型债务、填补兼自利型债务、增益兼自利型债务和纯增益型债务这四种类型的债务中,前三种债务的免除应采契约方式,而第四种即纯增益型债务的免除则可采单独行为方式。换言之,债务免除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形属于契约,在极少数情形(即纯增益型债务的免除)可为单独行为。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将自己的这个观点称为“契约主导说”,基于此“契约主导说”,本文对我国《民法典》第575条作了修正。修正后法条在处理债务免除问题时,以契约方式为主导,笔者因此而将该模式称为“契约主导模式”。
在以上结论之外,笔者尚有两点余想。
余想之一,否定之否定规律。
从法制史角度观察,在债务免除问题上,已有诸立法模式的产生顺序是“契约模式→单独行为模式→单独行为修正模式”。初看上去,该顺序貌似事物发展中的否定之否定,然细究之后则发现不是这回事。按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原理,事物发展中的否定应当是合乎事物内在逻辑的自我否定,而不能是外在而人为的点缀。“单独行为修正模式”即为此种点缀。若将该顺序中的“单独行为修正模式”代之以本文提出的“契约主导模式”,则事物合乎其内在逻辑的自我否定即得以实现。比之“契约模式”,“契约主导模式”仿佛回到了“契约模式”这个原点,但实际上它又不同于此原点,从而完成了债务免除方式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循环,通过“扬弃”实现了债务免除方式上的质的飞跃。
余想之二,赠与合同背后之人的尊严。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曾数次考察赠与合同。正是在赠与合同那里,笔者才发现了典型的“纯增益型债务”,并进而以此发现为基础对债务免除行为的性质问题做了全面观察分析。与此同时,笔者亦深感学界对赠与合同的研究有待深化。由于赠与合同不像双务合同或有偿合同那样反映交易关系②我国合同法理论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个观点,即合同法是调整交易关系的法律。例如,崔建远教授在其主编的《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 页)中说:“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的法律。”笔者不敢赞同此观点,因为合同法所调整的关系并非全是交易关系,亦包括了单向的财产或劳务的移动关系,例如在赠与合同、无偿委托合同、无偿保管合同等合同中,就只有财产或劳务的单向移动,而根本不存在交易。,研究者对它似乎兴趣不大。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其表层问题,诸如任意撤销权、法定撤销权和拒绝履行抗辩权(《合同法》第195 条)之类,而对于其深层问题尤其是其背后之人的尊严问题却几乎缺乏关注。在笔者看来,“赠与”之为合同,此事实本身即向社会传递了这样一个强烈的观念:即使是给予他人以恩惠,亦必须征得他人同意。该观念承认并力倡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不但契合了私法的精神,而且鞭挞了所有与现代人类文明格格不入的等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