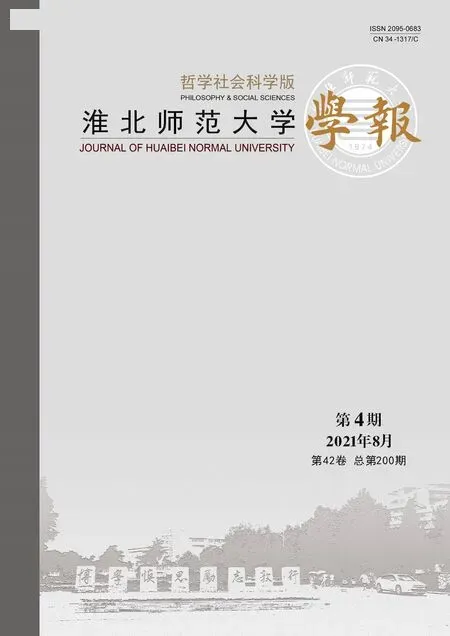现实政治境界的政治修辞基本原则
2021-01-14吴礼权谢元春
吴礼权,谢元春
(1.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2.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政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也是“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建立以暴力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利用法律这种强制性的手段来调节利益分配,解决社会冲突的活动。”[1]1政治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权术。至于什么情境下是艺术,什么情境下是权术,这要视从事政治活动的主体(政治人)的人格而定。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政治既然是一种社会活动,那么不论它是艺术,还是权术,都跟修辞有密切关系。因为从事政治的主体(政治人)要想实现其社会活动的目标预期,势必就要有效地阐述或表达其社会活动的诉求,从而赢得全体社会成员或特定社会群体成员的认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治人就不能不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有一番经营努力,这便是政治修辞。”[2]44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政治跟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每一个人都不是自然的人,而是社会的人,都具备一定的人格。政治人作为一个社会中具有独特身份的人,自然也有其政治人特有的人格。这种特有的人格,反映到政治活动中,就必然对政治境界的形成产生影响。就政治学的视角来看,“无论是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看,政治都是有境界之别的,可以将之分为理想政治境界与非理想政治境界两种”[3]18。理想政治境界,就是《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模式,汉人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还作了具体的人事描写,但毕竟只是一种按照儒家学说所构拟的“大同社会”的模式所作的图解而已。虽然“理想的政治境界,是古往今来所有人都向往的。但是,它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中,是善良的人们在精神上的一种寄托。而非理想的政治境界,亦即现实的政治境界,则是人类社会的真实状态,是一种连续性的、‘写真’式的常态。”[4]1
虽然现实的政治境界不像中国古代先哲所描绘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理想政治境界那样美好,而是充斥着尔虞我诈、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等等丑恶的现象(这在近现代西方社会中尤其典型)。但是,既然生活于其中,那么,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政治人都必须直面现实,适应这种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尤其是政治人,更要对现实政治境界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政治交际活动中自觉遵循现实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的三个基本原则:“知人论事”“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唯有如此,才能适应政治交际活动的需要,顺利实现其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
一、知人论事
知人论事,作为现实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的一个基本原则,其涵义是指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在政治交际活动中,为了实现其特定的政治修辞预期目标,必须对政治修辞的受体(包括政治人与自然人)进行研究,包括对其身份背景、职业、生活经历、文化程度、性格爱好与心理倾向等等予以深入了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政治修辞受体的认知水平、心理状态,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或政治主张等清楚、准确地传达出来,让政治修辞受体能够听得懂、听得进。简言之,就是要求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必须见人说话,看对象论事,准确把握政治修辞受体的心理,投其所好,根据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亦即日常我们所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将话说到对方的心坎里,使其在愉悦的情感主导下欣然接受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理念、主张等。
关于这一点,早在先秦时代,韩非子就曾作过精辟的论述: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韩非子·说难》)
韩非子上述所论,讲的是游说国君如何取胜之道,正是跟政治修辞紧密相关的问题。众所周知,战国时代是一个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时代,但同时也是诸子百家各色人等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时代。不同学派的学者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还有很多策士说客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常常都要游说诸侯各国之君。在韩非子看来,游说诸侯各国之君对于这些学者、说客或策士来说并非难事,难的是游说时将话说到被游说对象(诸侯各国之君)的心坎里。他认为,“一个游说者(即交际者)要想让被游说的诸侯国之君(即受交际者)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践行自己的治国安邦理念,就应该首先了解对方的所思所想(即心理),适应其心理倾向,然后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将自己的思想学说或政治主张推销给他,让他欣然接受。但是,交际者(即游说者)必须注意,如果受交际者(即被游说的君主)有沽名钓誉的心理,交际者却以厚利为诱饵来说服他,则必然不惬于其心。因为受交际者觉得交际者将他的境界看得太低了,认为他是贪图小利之俗辈,那么他必然对交际者产生抵触排斥心理,即使交际者的思想学说再怎么高明,政治主张再怎么正确,他也会在不悦的情绪心理作用下断然拒绝。如果受交际者是个贪图厚利之辈,而交际者以虚誉清名来说服他,则必然不合其心意。因为受交际者觉得交际者以虚幻不实的东西来诱骗自己,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那么他必然不愿接受交际者的游说。如果受交际者内心想着的是厚利,而表面却标榜清高、崇尚令誉,交际者不能洞悉其真实心理,而以虚誉清名来游说他,那么他表面虽然会欣然接受,内心则会疏远交际者,绝不会践行他的主张;反之,若以厚利来游说他,受交际者虽满心欢喜,但表面却假装拒绝”[5]154。所以,韩非子认为,对于这种受交际者(诸侯国之君,即被游说对象)尤其要认真研究其真实心理,对症下药,才能保证游说取得成功。可见,韩非子早已看清了当时风行一时的游说活动之本质,将之视为政治修辞的一种典型形式,并且明确强调了在现实政治境界下遵循“知人论事”原则对于保证游说成功(即政治修辞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性。
除了韩非子深谙政治修辞需要遵循“知人论事”原则的重要性外,东汉大思想家王充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他曾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说过如下这样一段话:
苏秦精说于赵,而李兑不说;商鞅以王说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虽尽尧、舜之言,犹饮牛以酒,啖马以脯也。故鸿丽深懿之言,关于大而不通于小。不得已而强听,入胸者少。(《论衡·自纪》)
在王充看来,“苏秦的口才不是不好,但事实上他用精妙无比的言辞向赵国之相李兑推销其‘合纵’之策,最终却失败了;商鞅也是一个能说会道的说客,他以‘王道’游说秦孝公,结果秦孝公昏昏欲睡,不肯采纳他的策略。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就是苏秦游说李兑、商鞅游说秦孝公时都没有揣摸透受交际者的心理。当时赵相李兑的兴趣不在联合山东六国‘合纵’而抗强秦,而是要在赵国弄权,架空赵肃侯。秦孝公发布招贤令,商鞅从魏国出走,远投秦国,厚贿秦孝公宠臣景监,得以晋见秦孝公。但是,第一次、第二次游说,商鞅都没有打动秦孝公,反而让他昏昏欲睡。而第三次再游说秦孝公时,却让他兴趣盎然,一连五日与之抵膝长谈,乐此不疲,从此对商鞅信而不疑,最终决定让他放手在秦国进行变法,终使秦国迅速崛起,成为天下之霸”[5]155。他认为,“商鞅的三次游说,前两次之所以失败,第三次游说之所以非常成功,究其原因,都与交际者(商鞅)对受交际者(秦孝公)的心理揣摸有关。第一次,商鞅以‘古帝君之德’游说秦孝公,不得其心;第二次以‘王道’游说,又不惬其意;第三次用‘霸道’游说,则让秦孝公大为高兴。这是因为这次游说深得秦孝公之心,切合了秦孝公急欲振兴秦国的迫切愿望,所以受交际者(秦孝公)视交际者(商鞅)为知音,从此信用有加”[5]155。正是基于苏秦与商鞅游说成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王充才由此得出结论:“不得心意所欲,虽尽尧、舜之言,犹饮牛以酒,啖马以脯也。故鸿丽深懿之言,关于大而不通于小。不得已而强听,入胸者少”。也就是说,“交际者不了解受交际者的所思所想(即心理倾向),即使表达得再有技巧,说得天花乱坠,也好比是对牛弹琴,难入于其耳。纵然受交际者出于礼貌而勉强听之,也不会入于心,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效果”[5]155。
事实上,在现实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在政治交际活动中若是不自觉遵循“知人论事”的原则,那么其政治修辞的预期目标肯定不能实现。反之,则必然能实现。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战国时代的生动例证。
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妖祥乎?”庄辛曰:“臣诚见其必然者也,非敢以为国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不衰,楚国必亡矣!臣请辟于赵,淹留以观之。”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揜于城阳,于是使人发驺征庄辛于赵。庄辛曰:“诺。”庄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王独不见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饴胶丝,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将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颈为招。昼游乎茂树,夕调乎酸醎。夫黄雀其小者也,黄鹄因是以。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鰋鲤,仰啮菱衡。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射者,方将修其碆庐,治其缯缴,将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缴,折清风而抎矣。故昼游乎江河,夕调乎鼎鼐。夫黄鹄其小者也,蔡圣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流,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而载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己乎黾塞之外。”
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于是,乃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君,[而用计焉],与淮北之地也。(《战国策·楚策四》)
从上述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庄辛劝谏楚襄王是为了楚国的前途命运,话题是劝楚襄王“亲贤臣,远小人”,奋发有为,振兴楚国。很明显,庄辛的劝谏属于典型的政治修辞行为。第一次劝谏时,作为政治修辞的主体(政治人),尽管庄辛也是满怀一腔爱国热情,但是,在实施劝谏的政治修辞行为时,由于没有对当下的政治情势作出清醒的评估,既没有考虑到楚襄王的为人特点,也没顾及其君王自尊自大的心理,因而没能遵循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的“知人论事”原则,对楚襄王不思进取、不理朝政、任意胡为的荒唐行径进行了直言批评,犯了中国封建时代最大的政治禁忌:“批逆鳞”,让楚襄王作为楚国之君的自尊荡然无存,至高无上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结果,不仅导致预期的政治修辞目标(即通过进谏使楚襄王改正错误)未能实现,而且君臣之间温情脉脉的最后一层面纱也彻底被撕去,从此君臣分道扬镳,不再相见,一个继续在楚国胡作妄为,一个去国离乡。第二次进谏时,政治情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政治修辞受体的楚襄王,在经历过几乎亡国灭种的沉重打击后,终于清醒过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体会到了庄辛以前对他进谏的诚心与苦心。而作为政治修辞的主体,庄辛这一次也对以前的进谏方式进行了反省,摆正了君臣之间的人伦关系,并对遭受沉重打击而失去信心的楚襄王予以了深切的理解,知道楚襄王此时心理比较脆弱,最需要的是鼓励,所以在进谏时他特别注意了语言表达的策略,“没有实话直说,而是采取了迂回曲折地表达方法,以讽喻策略循循善诱,八面设兵,最后才点出主旨,从而一语激醒梦中人。庄辛意欲对襄王推销的政治理念,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作为国君应该居安思危,不可贪图安逸而不思进取。’这个政治理念,按理作为国君的应该是明白的,否则根本就不配做一国之君。但是,在那个时代,国君是世袭的,有没有能力,头脑清楚不清楚,根本与能不能做国君是脱钩的。所以,对于襄王这样的国君,庄辛首先只能承认‘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必须正视襄王是自己的国君,楚国是自己的国家这样的事实,同时确定这样的思想:一定要说服襄王振作起来,一定要让他明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和‘居安思危,振作进取’的为君之道。经过第一次进谏失败的教训,庄辛这次在推销他的政治理念,说服襄王时就十分注意表达的策略。他先是引了‘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两个俗语来安慰襄王,给他打气鼓劲,鼓励襄王不要气馁,可以重新振作有为。这是用的‘引用’语言策略,具有特别大的说服力。因为谚语俗语,都是前人一代又一代知识经验的总结,是公认的权威结论。因此,引用前人的经典之言,特别是谚语俗语往往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襄王虽然不争气,但还不至于昏庸到连这个道理还不懂。事实上,后来楚襄王知道认错反省也证明他不太胡涂,智商还算正常。因此,庄辛的第一句话就是十分高妙的说辞,为下面的进一步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庄辛又运用了‘用典’的语言策略,以汤武两明君以百里而昌,桀纣两昏君以天下而亡的历史事实,婉转地告诫了襄王如何做个仁君好王。接着,庄辛一连说了蜻蜓、黄雀、黄鹄自以为与人无争、自以为无患而被人射杀烹食的故事,这是运用了‘讽喻’语言策略。讲这三个临时编造出来的故事,目的是要引出蔡圣侯贪图享乐,自以为与世无争、自以为无患,结果被楚宣王系而捕之的历史故事,从而自然地把话题引入到要真正想说的话上:襄王您整天与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优游享乐,不理朝政,不思进取,结果就是秦王举兵差点把楚灭了,您现在也被逼到城阳流浪。这样,说得自然,道理讲得滴水不漏,让襄王无法辩驳;但道理陈述表达又非常的婉转,给了襄王面子,使他能乐意接受,并深刻反省自己,心灵深处激起巨大的震荡,以致‘颜色变作,身体战栗’。最终,庄辛顺利地推销了自己的治国政治理念:‘人无远忧,必有近忧。国君应该居安思危,奋发进取,国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有所发展’。”[6]106-107由此可见,作为政治修辞行为的进谏,自觉遵循现实政治境界下的“知人论事”原则是多么重要。
战国时代的政治人(政治修辞主体),为了游说与进谏的成功,需要自觉遵循“知人论事”原则,那是因为游说与进谏都是政治修辞行为,必须将话说到政治修辞受体的心坎里,突破其心理防线,或是从心理上、情感上征服对方,才能最终实现其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后世的政治人游走于中国古代官场,不仅游说、进谏需要自觉遵循现实政治境界下的“知人论事”原则,有时甚至在宦海生涯中受了委屈或冤屈需要为自己辩白,也是需要自觉遵循“知人论事”的政治修辞原则,否则就无法在官场生存,甚至还要掉脑袋的。下面我们就看一个鲜活的例证。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号哭。允新妇自若云:“无忧,寻还。”作粟粥待。顷之,允至。(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
上面这则文字记载,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三国魏明帝曹叡执政时期,时任吏部郎的许允,因为所用之人多是其同乡,结果被人举报。魏明帝闻知非常震怒,认为许允这是在假公济私、结党营私,遂派虎贲(即皇宫卫戍部队的将领,汉有虎贲中郎将,魏袭其制)前往收捕许允。许允一看皇帝竟然用虎贲之将来收捕自己,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许家人一见,更是吓得哭成了一团。但是,许允之妻阮氏却从容不迫,一点也不慌神,还安慰家人:“大家不用害怕,更不必担心。”一边说着,阮氏一边命人去熬粥,并信心满满地说,粥熬好了,许允就会回来了。安定了家人后,阮氏又安慰了丈夫一番,临行前告诫他两句话:“明主可以跟他讲道理,决不能跟他求情。”许允牢记妻子阮氏的嘱咐,到了朝廷,见了魏明帝,从容应对,没有丝毫慌张。魏明帝质问他为什么多用同乡之人,他从容回答道:“孔子有言:‘举尔所知。’臣的同乡,臣最了解他们。他们的情况臣知根知底,所以臣多用了些同乡。陛下不能只看臣所用之人多是同乡,也要看看臣所用同乡是否称职。若所用同乡皆不称职,臣甘愿领罪。”魏明帝一听,觉得许允说得也有道理。遂让相关官员一一检视他所用之人,结果发现都官得其人,很是称职,没有职守上的瑕疵。于是,连忙将许允给释放了。许允告别时,魏明帝发现他的衣服被弄坏了,觉得过意不去,乃诏赐新衣,以示恩宠。[5]174
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许允是三国魏明帝时代的吏部郎,是负责官员选拔与考核的朝廷重臣,属于职业政治人。而传唤许允的魏明帝是九五之尊的皇帝,自然也是职业政治人。魏明帝传唤许允到朝廷不是要跟他闲话家常,而是要追究他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的法律责任。正因为传唤的性质如此,这就决定了许允上朝面君的性质就具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其面对魏明帝时所要辩解的一切话语都属于政治修辞的性质。故事的结局告诉我们,许允作为这场君臣政治交际活动中的政治修辞主体,最终成功地实现了其预期的政治修辞目标——为自己洗清了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的冤屈,赢得了作为政治修辞受体的魏明帝的信任。那么,许允何以面对怒不可遏的魏明帝的质问能够几句话就能化解,既为自己所蒙受的冤屈作了辩白,又赢得了魏明帝的尊敬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作为政治修辞的主体,许允听进了其妻阮氏(角色政治人,事实上是最高超、最出色的政治人)“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的建议,遵循了现实政治境界下“知人论事”的原则,面对魏明帝的质问,不说一句求情的话,而是从容不迫地跟他讲道理。因为他“了解魏明帝,知道他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的昏君”,“只要能将道理讲明白,他肯定明断是非,不会冤枉人的”[5]174。正因为如此,面对政治修辞受体的魏明帝怒不可遏的质问时,许允保持了自己作为政治修辞主体的从容与淡定,并不急于为自己多用同乡的事实辩白,而是坦然承认,但是巧妙地抬出圣人孔子作为庇护神,引其“举尔所知”的用人荐才名言为依据,“有力地为自己多用同乡的行为作了辩白”[5]175,让政治修辞受体的魏明帝从心理上为之折服,觉得无话可说。“加上最后检视用人效果的验证”[5]175,更让魏明帝对其清白深信不疑。可见,在现实政治境界下,职业政治人在政治交际活动中遵循“知人论事”的政治修辞原则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二、审时度势
审时度势,作为现实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的一个基本原则,其涵义是指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在政治交际活动中,为了实现其特定的政治修辞预期目标,必须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政治交际的时机,选择恰当的修辞策略,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理念、主张等适时传递给政治修辞的受体,使政治修辞受体能够在最大限度上予以接受,从而实现政治修辞的效果最大化。换言之,就是要求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必须懂得看时机说话,在恰当的时机说恰当的话,让政治修辞受体觉得愉悦、自在而欣然接受,从而实现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
关于这一点,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就曾作过论述:
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
孔子上述这番话,意思是说:“侍奉在君子(即统治者、领导、上司等)身边,陪他说话,有三种过失需要避免:一是没轮到自己说话时,却冒失地先开了口,这叫急躁;二是该自己说话的时候,却错过时机没有说话,这叫隐瞒;三是不看上司的脸色而自说自话,这叫瞎了眼”[5]142。仔细分析一下孔子这里所说的“三愆”,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前“二愆”都是与说话的“时机”有关。可见,在孔子看来,政治修辞(“侍于君子”者必是政治人,其与君子的言语互动自然属于政治修辞的性质)要特别重视“时机”的把握。换言之,就是要求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必须懂得审时度势,见时机说话。否则,就必然会犯错(即“有三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战国时代的例证。
范雎既相,王稽谓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宫车一日晏驾,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馆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沟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宫车一日晏驾,君虽恨于臣,无可奈何;君卒然捐馆舍,君虽恨于臣,亦无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沟壑,君虽恨于臣,亦无可奈何。”范雎不怿,乃入言于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内臣于函谷关;非大王之贤,莫能贵臣。今臣官至于相,爵在列侯,王雎之官尚止于谒者,非内臣之意也。”昭王召王雎,拜为河东守,三年不上计。(汉·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上述故事,说的是王稽游说范雎,希望他向秦昭王推荐自己,以求加官进爵的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出,王稽求托范雎向秦昭王进荐自己是一种政治修辞行为,范雎游说秦昭王而希望秦昭王升王稽官职也是一种政治修辞行为。因为王稽与范雎、秦昭王都是职业政治人,它们谈话的内容涉及到王稽的官职升迁问题,而官职的升迁乃是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在上述这个故事中,无论是王稽求托范雎的一番话,还是范雎游说秦昭王的一番进谏,都是典型的政治修辞。
作为政治修辞的主体,王稽求托范雎之所以取得成功,其根本原因是他自觉遵循了“审时度势”的原则。因为王稽求托范雎之时,范雎不仅官至秦国之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还被秦昭王封了应侯。可见,范雎作为一个外来的客卿此时已经在秦国政坛站稳了脚跟,跟秦昭王的关系也达到了最密切的程度。王稽正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觉得这时应该是范雎说话最有力的时机,也是自己求托他,让他报答自己当初冒着生命危险带他入秦的知遇之恩的最佳时机,所以他选择在此时求托范雎。可见,王稽是一个合格的政治人,也是一个高明的政治修辞主体,深谙政治修辞之道。除此之外,王稽作为政治修辞主体,还有一个更高明的地方,这就是他对世情人心的洞悉。当他作出决定,要前往求托范雎向秦昭王推荐自己时,不是以恩公自居,而是以下级见上级的姿态出现。之所以如此,是他清醒地意识到,眼前的范雎已经不是早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带进秦国的魏国落魄书生,而是位极人臣的秦国权相,眼下他必须直面自己与范雎政治地位悬殊的现实,摆正自己的位置,以下级见上级的心态求托范雎,而不是居功而索求报答。因为“现实生活中受人恩德者,并非都能做到有恩必报,相反还有些人一阔脸就变,甚至翻脸不认人”[5]254。如果王稽果真以恩公自居,直道本心,跟范雎实话实说:“我曾有恩于你,你现在位极人臣,正是报答我的好时机。否则,错过时机,后悔也来不及了”[5]254,虽然于情于理都是对的,相信范雎从理智上也是能够认同的,但一定会有情感上的不快。而一旦产生情感上的不快,即使他迫不得已答应了王稽的请托,也会是不情不愿,这就必然会影响到他向秦昭王进荐王稽的效果。事实上,王稽是一个清醒的政治人,他洞悉了世情人心,在求托范雎时“以下级对上级的态度婉转进言”[5]254,运用“折绕”修辞法,以“三不可知”“三无奈何”这样“曲里拐弯的说辞,婉转迂回地将其真意表达出来,让受交际者范雎思而得之,在赢得面子的同时,愉快地接受其请托”[5]254。由此可见,王稽最终求托成功,获得秦昭王的重用,实在是与其高明的政治修辞艺术有关。而这高明的政治修辞艺术的核心,就是作为政治修辞主体的王稽自觉遵循了“审时度势”原则,在恰当的时机与有利的政治情势下实施了求托范雎这一政治修辞行为。
说到王稽求托范雎的成功,我们还要强调指出一点,这就是政治修辞固然是需要遵循“审时度势”原则,但也不能忽视修辞技巧的运用。事实上,在上述王稽求托范雎成功的政治修辞案例中,作为政治修辞主体的王稽在修辞技巧上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对此,上面我们已经对其“三不可知”“三无奈何”的“折绕”修辞策略的运用所产生的效果作出了分析。如果在政治交际活动中,政治修辞主体既无自觉遵循“审时度势”原则的意识,又无自觉运用修辞策略的意识,那么其政治修辞的预期目标就不可能达到。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诰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新唐书·孟浩然传》)
上面这则历史记载,说的是盛唐诗人王维与孟浩然的故事。众所周知,“王维是盛唐时代的著名诗人,诗、画俱佳,后世学者评价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不仅文学造诣深,少年得志,早早就科举及第,做了状元,而且还特别会做人,深得唐玄宗信任,历任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等要职。玄宗天宝年间,还官拜吏部郎中、给事中等职。同样是盛唐时代的著名诗人,堪称盛唐一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也是王维好友的孟浩然,跟飞黄腾达、一路顺遂的王维相比,人生境遇就显得相当窘迫了。他的诗虽然写得好,连李白都写诗推崇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赠孟浩然》),但跟才华横溢的李白一样,因为没有走通唐朝科举取仕这条体制内的正规晋升之路,只能落魄失意地颠沛流离”[5]222-223。不过,“在唐代,如果没有走通科举之路,还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依靠朝廷重臣向皇帝举荐。如果获得皇帝青睐,也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走上治国平天下的为官之道。应该说,孟浩然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位好朋友王维。王维才学好,在朝廷中非常得势、深得唐玄宗倚重,自己‘居庙堂之高’,却没有忘记‘处江湖之远’的朋友孟浩然”[5]223。《新唐书》的上述记载,说的正是王维心系好友孟浩然功名前程,意欲向唐玄宗举荐孟浩然,希望他也能得个一官半职的故事。然而,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王维刻意安排孟浩然晋见唐玄宗,唐玄宗也给了他求官的机会,但是孟浩然却侍对不当,得罪了唐玄宗,结果落得个被放还的结局,终生无缘官场。
从政治修辞学的视角看,孟浩然虽然在见到唐玄宗时尚未走上仕途,算不得是一个政治人,但却是当时文坛上的著名人物,连王维与李白都十分推崇并引以为友,而且唐玄宗也是久闻其名。以孟浩然如此优越的文坛地位,完全可以在见到唐玄宗后瞬间就可以转变为一个政治人的角色。可惜孟浩然没有政治人的潜质,在与唐玄宗的政治交际活动(“侍对”)中没有自觉遵循“审时度势”原则的意识,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未能尽情展露自己的才学,运用恰当的修辞策略,向唐玄宗表达自己愿意效力国家而一展长才的意愿。正因为孟浩然在侍对唐玄宗的政治修辞活动中没有自觉遵循“审时度势”原则的意识,也未有自觉运用恰当修辞策略的努力,因而就错失了良机,不仅未能获得唐玄宗的青睐而加官进爵,实现由一介书生向朝廷命官的身份转换,而且还让唐玄宗为之震怒,最终落得个被“放还”的结局,从此永远失去了进入仕途的机会。如果孟浩然具备政治人的潜质,有自觉遵循“审时度势”原则的意识,那么一定会充分利用好友王维给他创造的面圣机会,在与唐玄宗侍对的特定时机主动作为(歌颂唐玄宗文治武功的成就,表达效力国家的意愿),选择恰当的修辞策略,诵出诸如他写给宰相张九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两句:“欲济无舟揖,端居耻圣明”,那一定会让唐玄宗龙颜大悦,立即可以由一个“角色政治人”迅速转换为一个“职业政治人”,进而开创一个美好的人生境界。事实上,孟浩然在侍对唐玄宗的政治交际活动中没有遵循“审时度势”原则的自觉意识,也没有选择恰当的修辞策略以实现修辞目标的自觉意识,因而非常情绪化地诵了一首不合时宜的旧作《岁暮归南山》:“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结果,让唐玄宗听了感到非常不爽,从心底不予认同,当即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在诬他英名。因为从政治修辞的视角看,孟浩然在侍对唐玄宗的政治交际活动中事实上是一个“角色政治人”,是政治修辞的主体,需要适应政治修辞受体唐玄宗的心理特点,主动恭维歌颂其治国安邦的成就,强调其知人善用的英明。这样,才能逼近自己所要实现的政治修辞的预定目标(求取官职,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然而,孟浩然作为政治修辞主体完全不懂政治修辞,其即席诵诗的修辞作为完全与其政治修辞的预定目标背道而驰。就他对唐玄宗已然诵出的三句来说,“句句都是不得体的,接受效果极差。第一句‘北阙休上书’,在朋友面前玩清高时可以说,但当着皇帝的面这样说,就让人觉得非常矫情,显得为人太虚伪。因为此时此刻面对皇帝诵诗,事实上就是在‘北阙上书’。第二句‘南山归敝庐’,直承第一句而下,给人的印象好像是说自己向往归隐南山、居于敝庐的生活。这样的表达,明显与即席求官的当下情境格格不入,让受交际者莫名其妙。至于第三句‘不才明主弃’,表达就更加糟糕了。因为这句诗,就交际者孟浩然本人来说,是想在当下情境中赋予它这样一层意思:‘自己由于无才,所以至今尚未仕进,难一展才华为国效力、为君王尽忠’”,好像是在表达谦虚之意。但这样的表达事实上让听者唐玄宗“觉得这话是在发牢骚,在埋怨自己。因为听者认为对方所说‘不才’是中国人的谦逊之言,因而‘不才明主弃’的实质含义是说像他这样有才的人君王至今未能任用。这样,听者自然而然地由此推导出对方的实质话语核心是骂自己不圣明,是昏君。其实,唐玄宗之所以说孟浩然‘诬’他,正是按照我们上面所分析的思路来进行的。尽管我们都知道孟浩然没有这样的意思,但事实上却给唐玄宗造成了这样的误解”[6]9-10。相反,如果孟浩然深谙政治修辞之道,有自觉遵循“审时度势”原则的意识,有自觉朝着预定政治修辞目标(逢迎唐玄宗而求取官职)努力的意识,以“折绕”修辞法诵出诸如“欲济无舟揖,端居耻圣明”这样的句子,结果肯定大不相同,“当场就会被唐明皇加官进爵的,自然一生风光无限、前程似锦。因为‘欲济无舟揖,端居耻圣明’两句,就说者来言,尽管实质上是要求个一官半职,但却打着是不辱圣明帝王的旗号,同时还吹捧了对方是圣明的君主。这等巧妙的措辞不能打动对方之心,那是不可能的。而就听者而言,虽然明知对方是在求仕,但其表达十分婉转、巧妙,言语之间透着才学,且又称自己是圣明之君,这对于唐玄宗这样颇是风雅且自以为圣明的主子来说,是再中听不过的了。”[6]10
从上述中国古代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我们足可以清楚地见出,在政治修辞中自觉遵循“审时度势”原则,往往是实现政治修辞预期目标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
三、因地制宜
因地制宜,作为现实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的一个基本原则,其涵义是指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在政治交际活动中,为了实现其特定的政治修辞预期目标,必须根据政治交际活动当下特定空间的政治人文环境特点,选择恰当的修辞策略,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理念、主张等恰切地传递给政治修辞的受体,使政治修辞受体能够在愉悦的情感情绪状态下最大限度地予以接受,从而实现政治修辞的效果最大化。换句话说,就是要求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必须懂得见场合说话(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因地制宜,即景生情,配合特定空间的人文环境,选择恰切的修辞策略表情达意,最大限度地迎合政治修辞受体的心理,使其在愉悦的情感情绪状态下欣然接受,从而实现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
关于这一点,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和墨子都曾作过论述: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
孔子上述这番话,意思是说:“在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家,人们可以有话直说,正道直行;而在一个政治错乱的国度,人们不仅行为要端正,凡事小心,而且说话也要格外谨慎,切不可实话实说,更不可直言批评统治者”[5]146。孔子这里所说的意思,用今天的俗话说,就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意在提醒政治人游走于不同的诸侯国要注意分场合说话,不要碰触政治禁忌而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其中的“邦有道”“邦无道”,所指就是“场合”(“有道”“无道”之邦,就是最大的“场合”[5]146),也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特定空间的人文环境”的概念,指的是“诸侯国的政治氛围”[5]146。孔子要求政治人游走于不同的诸侯国,言行要有所不同,这实际上要强调的正是政治修辞必须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的重要性。由孔子的这番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是深谙政治修辞之道的。作为政治人,他是一个“非常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并不是那么书生气,为人还相当世故,深谙处世之道,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有用之身,以便日后干大事”[5]146。
比孔子稍晚的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生于春秋末战国初的乱世。为了宣传墨家学派的政治主张如“非攻”“兼爱”“节用”“非乐”等思想,他亦与孔子一样,一生都在周游列国,到处游说诸侯各国之君,是一个典型的说客,当然也是一个深谙政治修辞之道的政治人。正因为如此,他对政治修辞需要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的重要性有着切身深刻的认识,因而对此问题的论述也更为详细: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君子,子则将奚语?”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墨子·鲁问》)
上面这段文字记载,是墨子回答魏越的话。魏越问他如果见到诸侯各国之君,准备怎么游说他们。墨子就回答道:“大凡进入一个国家,一定要选择最急迫的事情来游说国君,以便帮助他治国安邦,解决民生问题。但是,游说国君首先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这就是要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如果那是一个政治混乱的国度,那么就要跟国君谈尊重贤良之才、加强内部团结问题;如果那是一个经济窘迫的国家,民不聊生,那么就要跟国君谈节约开支、丧事从简问题;如果那是一个好乐好酒成风的国度,那么就要跟他们的国君讲沉溺于音乐的害处,讲反对天命的意义;如果那是一个民风淫僻无礼的国家,那么就要跟他们的国君谈敬畏上天、虔诚事鬼的道理;如果那是一个好战成性的国度,就要跟他们的国君讲兼爱、非攻的道理。所以说:‘游说一个国家要选择最急迫的事。’”[5]147
从墨子跟魏越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出,墨子所强调的“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的观点,从政治修辞学的视角看,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游说作为一种政治修辞行为必须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的重要性。因为墨子这里所说的“凡入国”的“国”是指他所要游说的诸侯国,跟孔子所说的“邦有道”“邦无道”的“邦”是一个概念,也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特定空间的人文环境”的概念,指的是“诸侯国的政治氛围”[5]146。在墨子看来,进入一个诸侯国,要想游说其国君取得成功,只有“适应了游说的‘场合’(即所要游说的诸侯国的现状背景与政治氛围),然后再对症下药,选择最急迫的事情予以游说,才能收到好的效果”[5]146。可见,墨子是非常重视政治修辞中“因地制宜”原则的贯彻。
中国古代的政治人(诸如孔子、墨子)深谙政治修辞必须重视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的道理,现代的中国政治人对此也有深刻的认知,并且有不少成功的实践。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南洋爪哇有一个财产超过千万的华侨富翁。一次他外出访友,因未带夜间通行证,怕被荷兰巡捕查获,只得花钱请一个日本妓女送自己回家。日本妓女虽然很穷,但是她的祖国很强盛,所以她的地位高,行动也自由。这个中国人虽然很富,但他的祖国不强盛,所以他的地位还不如日本的一个妓女。如果国家灭亡了,我们到处都要受气,不但自己受气,子子孙孙都要受气啊![7]18
上引这段文字,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年在海外宣传革命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一段话,至今读来仍让人心灵震撼,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之所以有此独特的政治宣传效果,是因为孙中山先生作为政治修辞主体在面对海外华侨这一特殊的政治修辞受体时,自觉遵循了政治修辞的“因地制宜”原则,即景生情,就地取材,以南洋富翁与日本妓女的故事为例证来说明自己所要宣达的主旨,让广大南洋华侨有亲切感与确凿感,因此说服力自然就大大加强了。如果孙中山先生不遵循政治修辞的“因地制宜”原则,不就地取材,以南洋富翁与日本妓女为例,而是以理性的语言宣示其所要表达的意旨:“祖国是你们华侨的坚强后盾,如果祖国不强大、很疲弱,你们即使在海外他人的国度挣了钱,经济上是富人,但仍然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政治和经济上不能与其他人有平等权的化外之民,生命和财产也不能有保障,不仅自己,甚至子子孙孙都永远摆脱不了受气还要受侮辱的悲惨命运。只有祖国强了,我们的华侨同胞才能在海外他人的国度有地位,挺起腰板做人。因此,我们华侨同胞应该深明大义,支持我们国内的同胞和革命党人革命,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推翻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建设民主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8]7-8虽然这样的表达也能将道理说得很透彻,让广大海外华侨明白其用意,但未必能够深切打动他们的心,激发出他们强烈的爱国之心,进而愿意慷慨解囊,将自己在海外辛苦打拚的血汗钱捐献出来支持国内革命。事实上,孙中山先生并没有跟听讲的海外华侨讲空洞的道理,而是因地制宜,从他们身边就近取材,以南洋富翁与日本妓女的故事为例,通过近代中国与日本国力强弱的对比,以事实说话,从而以不可辩驳的说服力征服了广大海外华侨的心,最终赢得了广大海外华侨对国内革命的有力支持。可见,孙中山先生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人,也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治修辞主体,深谙在宣传革命这一特殊的政治修辞活动中自觉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的重要性,而这也恰恰是他长期在海外从事革命宣传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结语
相对于日常修辞,政治修辞是一门更具挑战性的语言活动。尤其是在现实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所具有的挑战性就更大。它不仅需要政治修辞主体具备高度的政治智慧与娴熟的修辞技巧,还要具有自觉遵循现实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基本原则的意识。唯有如此,才能适应复杂的现实政治情势,面对政治场域瞬息万变的突发情况,游刃有余地进行语言文字的经营,使所欲传达的思想情感或是政治诉求最大程度地为政治修辞受体所接受,从而实现政治修辞效果的最大化。
政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跟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有着密切关系。人有人格,政治人有政治人的人格,反映到政治活动中,就有了政治境界的高下优劣之别。事实上,政治从来都有理想与非理想两种境界。政治境界不同,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所要遵循的政治修辞原则也有所不同。在理想的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遵循“坦诚相见”“友善合作”“慎言其余”三项基本原则,即可顺利实现其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而在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则必须自觉遵循“知人论事”“审时度势”“因地制宜”三项基本原则,才能顺利实现其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