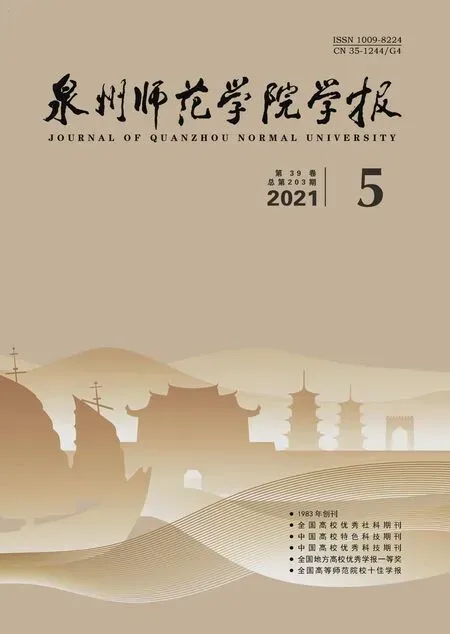沈曾植的碑派书风及其书法批评的再认识
——以《沈曾植寐叟题跋》书法为例
2021-01-03王守民
王守民
(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2016年,由艺文类聚金石书画馆编纂的《沈曾植寐叟题跋》正式出版。在此之前,关于沈曾植书法风格研究的文章很少,立足于题跋墨迹全面进行研究沈曾植书法风格的文章只有日人菅野智明的《〈寐叟题跋〉的书法》(1)(日) 菅野智明著:《〈寐叟题跋〉的书法》见《福岛大学教育部论集人文科学部门》六十一号,福岛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32页。一篇。其他的文章在分析沈曾植书法风格时,限于材料的缺乏,均无详细深入地梳理,更没有按时段上的分期,沈曾植的书法风格一直以来都是模糊的。
一、沈曾植书法渊源及碑学思想的形成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又号寐叟,吴兴人,光绪进士,官至布政使。沈曾植生活上是不幸的。他早年丧父,生逢太平天国运动、八国联军入侵,生活十分艰辛时,不得不将家传的《灵飞经》宋拓本拿去典当,换取米面度日;同时,沈曾植又是幸运的。他的周围有一批如王国维、郑孝胥、康有为、陈衍等友人;也有包世臣、韩泰华、愈功懋、黄绍箕等师长。沈曾植是“同光体”诗派的代表,李慈铭、袁昶、文廷式、王仁堪、黄绍箕都是其座上客。同光诗派的雅集,更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书法交流。
马宗霍《霎岳楼笔谈》中对沈曾植的书法渊源有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寐叟执笔,颇师安吴(包世臣),早岁欲访山谷(黄庭坚),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決不能得势;中拟太傅(钟繇),渐有入处;暮年作草,遂尔抑扬尽致,委曲得宜;真如索西征(索靖)所谓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极缤纷离披之美。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不仅安吴为出蓝也。”[1]244
可见,马氏把沈曾植书法分为三阶段:初段师法黄山谷、包世臣;中段师法钟太傅;暮年取法章草,融碑入帖,渐入化境。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笔者从《沈曾植年谱》中得知沈曾植早年师从舅父学习书法。笔者通过整理沈曾植的早期书法作品,确实发现了有黄庭坚书风的痕迹。韩泰华博学多才,在书画方面的造诣颇深。在收藏、评骘书画作品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当代研究韩泰华的学者很少关注韩泰华的书法风格。实际上,韩泰华《玉雨堂书画记》一书中有对于黄庭坚书法的记述与评价[2]77。
笔者通过整理沈曾植的书法作品后发现,黄庭坚风格的书法作品集中出现在光绪戊寅(1878)年就出现了,属于早期的书风,此时沈曾植二十九岁。因此,笔者推断是舅父韩泰华影响了沈曾植的早期黄山谷书风。
当然,此书中还有关于唐宋写经书法资料的记载,这些评价都对于沈曾植写经方面思想的形成有启蒙作用.早期沈曾植楷书就是从写经书法里汲取营养的。具体说,沈曾植对魏晋人写经十分用力。根据沈曾植弟子王蘧常说:“先生于唐人写经,《流沙坠简》亦极用力……摹《流沙坠简》,当悬臂拓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3]19足见写经与简书对沈曾植书法风格形成的意义重大。沈曾植书法中黄山谷风格的作品、写经风格的作品下文有专论,这里不作赘述。
沈曾植书法除了受韩泰华的影响,受张廉卿书法的影响亦可见一斑。陈柱在《书法詹言》中说:“沈子培初师包安吴、张廉卿,并略兼黄山谷。暮师《流沙坠简》及魏晋人写经,以之入章草。遂驾清二百年以上。”[4]53陈柱对沈曾植的书法师承的评价一针见血,可以视为最为权威的评说。沈曾植早期师法包世臣书,然而包世臣书法却没有成为他最终的选择。包世臣柔美的帖派书风,尚不能满足沈曾植审美的需要。张廉卿书风对于沈曾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楷书方面。张廉卿楷书笔法的规范化,在沈曾植书写对联、大字立轴时就显现出来了。沈曾植在造形上变化丰富,用笔上又不失谨严。如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立轴《一上高楼》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作。而在沈氏的对联大字上看,张廉卿的影响还是在的。倘若从外形上去寻求,恐怕也不那么容易被察觉。
影响沈曾植书法最大的就是包世臣了。后世学者对于沈曾植取法包世臣,都没有异议。除了马宗霍,金蓉镜、王蘧常也都明确了沈曾植取法包世臣书风这一点。
沈曾植受包世臣影响最大的还是在笔法方面。他继承包世臣的用笔理论,如用指的“中实说”等。但是沈曾植不是僵化地继承,而是有自己的思考。譬如他对于“中实说”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他认为:“惟小篆与古隶,可极中满之事。”[5]572
在他看来,真正做到“中实”的只有篆书和古隶,因为这两种字体在书写过程中,运笔都保持匀速平实的状态。于是,沈曾植在选择篆隶书碑刻时都兼顾其特征。如隶书他最推崇《校官碑》。这块碑篆意十足,是篆初变隶的典范。
不可否认的是,沈曾植追求包世臣笔法的“中实”也是经过了一番思考的。当他看到刘墉的书法后,幡然醒悟。一则题跋如是写到:“晓起睹石庵书,忽悟笔迹流美之说,因知中画圆满,仍须从近左处圆满求之。”片面的追求中实圆满,也会产生稚拙之感。在书写实践中对于“笔画中实”的思考,换来的是沈氏在用笔上的顿悟。沈曾植包世臣风格的作品都是出现在早期。这一时期的小字题跋中,总会融合碑派的方笔。光绪之后的沈曾植书法中,纯粹的碑派书风成为主流,与包世臣的倾向于帖派的书法风格是有不同的。
沈曾植的碑学思想,无疑也是植根与包世臣的书学土壤之中的。沈曾植的碑学思想主要是“以帖证碑,融碑入帖”。这种辩证的、宏观的碑派书学思想,是在包世臣碑学思想影响下的升华,是清代末期碑学生态中的重要导向。
沈曾植不像同时代的碑学家康有为走向“尊碑抑帖”的纯粹化道路,而是尊帖与崇碑并重,他影响了后世的碑派书家如陆维钊、郑孝胥等,成为海派书家的巨擘。他延续包世臣用其他时期的碑刻来论证北碑的方法,在比较南北刻石差异中寻找共性与个性,融南北书法为一炉,包世臣碑派书法在沈曾植的碑学思想下的推波助澜又得到了新发展。沈曾植学古能化古,先钟繇贯穿其学书的始终,再从魏晋楷书、简牍书法中获得灵感而登堂入室,堪称清末书学的智者。
二、沈曾植书风类型、分期与碑派书风的再认识
马宗霍把沈曾植书法划分为三阶段,三种书风取向。笔者对沈曾植的《寐叟题跋》书法墨迹和《沈曾植遗墨》中的作品进行梳理、辨析、分类,其书法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但是有却七种书风取向:早期(1870-1910)黄庭坚与欧阳询、北碑书风;中期(1882-1909)钟繇与写经书风;晚期(1902-1922):章草书风与倪元璐书风。王蘧常认为沈曾植书法晚年书风的转变,得力于唐人写经和流沙坠简;笔者认为晚期沈曾植的章草、今草的锤炼和变化不为人注意。尽管马宗霍先生有提到沈氏晚年的草书乃第三阶段的主流,但是没有这么详细的划分和分析。
(一)早期黄庭坚书风
根据沈曾植现存作品统计,从时间上基本可以断定,沈曾植的帖派书风,约在同治年间开始,至宣统二年(1910)。帖派书风的取法的主流是宋代黄庭坚。沈氏在运笔与结构上比较靠近黄庭坚的特点:纵笔放逸,结体又紧收。
如果说沈曾植前期书风是以帖派书风为代表的话,那么黄庭坚风格的行书就是典型。而且这一时期的书风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笔者根据《寐叟题跋》和《沈曾植遗墨》《沈曾植年谱长编》中的作品与记述,正如马宗霍先生所言,黄庭坚书风是沈曾植早期的取法方向。沈氏早期取法黄庭坚书风的书法作品有10幅,约开始于同治末,但在光绪庚戌(1910)以后就不见踪影了。嘉兴博物馆藏有一幅沈氏的行书墨迹《曼陀罗寱词手稿》,是纯粹的黄庭坚书风,可惜没署书写时间,想必也是此段时间的作品。沈曾植纯帖派黄庭坚书风的作品占一定比例,影响到了好友陈衍。陈衍与沈氏交往甚密,其书风也接近。两个人于戌戊年(1898)订交。此时沈曾植专致于黄庭坚书法时期,陈衍受其影响也很大。陈衍有一通《致虞虎手札》,与沈曾植如出一辙。不得不承认,陈衍受沈曾植书法影响还是很大的。
(二)欧体书风
沈曾植在学习欧体书风方面汲取了欧阳询内擫的势,偶尔还看到一两笔隶书的“波发”用笔,很是有趣。他的欧体书风主要集中在1901年至1904年四年间,共有6幅作品。欧体书风的作品自1908年的《跋墨池堂帖》以后,就销声匿迹了。这一时期沈氏崇尚唐楷,强调以唐楷入碑。
他的观念与康有为“尊碑卑唐”观是相斥的。譬如沈氏崇唐。他认为颜真卿的书法源于北朝,同样可取法。他说:“鲁公书源出殷氏父子,后得笔诀,嗣法河南,所谓厌家鸡欣野鹜者耶?然如此碑结体固不能与《裴镜民碑》绝无瓜葛也。”[6]375由于沈氏推崇唐碑,其楷书取法广泛,而后由唐学习北魏、至魏晋书风,实现了复古。
可见,民国崇尚北碑的碑学思潮下,学习唐人书风早已被忽略。唐初书法中具有碑派书法的影子,也可以作为取法的对象。所以,沈曾植在取法上实在是有过人的眼光和明智的取舍的。没有学习唐人书法的基础,沈曾植也不会有后期碑派书法上的突变。唐代书法的重要性在后来的许多碑派书家创作中就可以凸显看出来了。
(三)北碑书风
沈曾植北碑作品取法广泛,最后导致他的北碑风格的作品多融合在诸书体中。他学习北碑书法,时时看到黄庭坚、钟繇书法的影子。沈曾植学习北碑,并不是关注那些奇诡的造型,而是更注重其内涵。他既有唐碑的谨严,又不乏写经与北碑的势与韵,并不是一般书家所能望其项背的。如他在选帖时选东魏《敬使君碑》《崔敬邕》。他在一则题跋中写出自己对北碑的看法:“北碑楷法,当以《刁恵公志》《张猛龙碑》及此铭为大宗,刁志近大王,张碑近小王,此铭则内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兰亭者,可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庾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7]52可见,沈曾植不着眼于造像题记之类的民间题刻,始终保持传统的学习路径,自己的书写风格便迥于常人。含蓄蕴藉,意味悠长的北碑是其理性思考后的选择。沈曾植北碑在大字书写方面有自己的主张。北碑可壮其骨,作为大字,沈曾植从大字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一些摩崖经典之作入手,拓展了其碑派书法的新境界。他追求质古之美,楷书参隶法,隶书参篆法;他追求变通,楷法、篆法、隶法与草法之间都是可以相同的。因此,找到已经在笔法上做到浑融的碑刻,显得尤其重要。
沈曾植眼中的北碑是与别人不一样的,他不是孤立地去看或写一块碑,而是找出些碑与其他碑或墨迹的联系,最后达到碑帖融通的目的。如他以为北魏《寇治碑》可作写经来学习。此碑这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四)小楷书风
马宗霍、王蘧常关于沈曾植楷书的讲法都一样,都认定他楷书在早期学习晋唐书家,后期从写经体、流沙坠简上突变出来。实际上,笔者发现,沈曾植学习写经,并非是在晚年,1899年的《追怀诗跋》就是纯粹的写经之作。此时沈氏只有50岁。此后,写经体始终与唐楷、魏碑、草书融合,出现于沈曾植的书法创作中。
笔者进一步对题跋、墨迹梳理分析后发现,沈曾植早期以钟繇、黄道周小楷为基础,后面再转向敦煌写经小楷、流沙坠简的学习,这应该是在暮年的突变期。沈曾植小楷书风大致有三个阶段:早期钟繇、黄道周书风阶段、中期写经体阶段,后期写经体与钟繇、黄道周渗透融合阶段。
沈氏写经体融合黄道周书风代表作《追怀诗跋》《李壁墓志跋》于戊戌年(1898)出现,在宣统甲寅(1914)年以后集中出现,成为沈曾植晚期书风的主流。
我们看上去像钟繇风格的作品,大部分是他从魏晋写经上学到的。写得比较纯粹的两件作品是《明拓阁帖跋》《文征明画跋》,都集中在光绪末宣统初。此后有约八年题跋较少使用钟繇或写经体写作品。宣统乙卯(1915)至去逝前七年的时间里,题跋中又集中出现一批经典作品,足以代表沈氏书写风格和楷书方面的最高成就。如《集明拓大观帖跋》《金世宗西冷探梅图》《跋兰亭刻石》《七言古诗》《宋刻兰亭刻石跋》《跋徐季海帖》《宋拓绛帖跋》《明拓大观帖跋》《题画跋》等。
可见,这些类似钟繇的写经风格的作品是沈曾植晚期书法作品的主要风格之一。小楷书风在后期的融合中,可以看到隶书的笔意与魏碑的方笔笔意。
(五)章草书风
这种书风的作品集中出现在沈曾植晚年的宣统年间。如果说楷书作品中是沈曾植借助敦煌写经实现的创作突变的话,那么章笔意草书风则是沈曾植融合写经楷书、隶书、北碑笔意实现的书写上的升华,属于自己对古法与创新认识。
光绪癸卯(1903)有一件《题右军诗帖》、可作为沈氏章草的代表作品。宣统年间集中出现一些优秀作品如《易庵画跋》《李子健画跋》《更生院长诗》《潘氏阁帖跋》《怀素小楷跋》《宋拓四种小楷跋》《陈老莲画跋》《跋祝允明草书》《跋兰亭诗》《博古堂诗跋》《残本大观帖跋》等。
《残本大观帖》的题跋是在他去世当年写的,此跋可以代表沈氏章草之最高水平了。沈曾植在章草上刻意用功,独出新意。陈柱先生认为他是以《流沙坠简》及魏晋人写经入章草,故能领标清人书法[4]34。此说法很有道理,沈氏的章草中有许多夹杂着魏晋楷书、甚至魏碑的写法,足见功夫之深才能其浑融一体。沈氏的创新之处也显而易见了。按陈柱先生的说法,章草的学习分四个时期:先临皇象、晋二王诸章草帖得其法。其次是临明代二宋以上诸章草帖。再者就是写《流沙坠简》与魏晋写经,可得古趣。最后融汇诸家再回到皇象索靖源头处去索求。陈柱作为民国时期书家之代表,他这种思想也代表了沈曾植一派的章草书家的学书理路,这是十分有益于后之学书者学习与研究的。
(六)倪元璐章草、行书书风
明清书家是清末许多书家学习的首选。沈曾植也不例外。大家只知道沈氏学习黄道周,却没有人提过沈氏学习倪元璐。沙孟海说:“我一向喜欢他(沈曾植)的书迹,为其多用方笔翻转,诡变多姿,看到他《题黄道周书牍诗》‘笔精政尔参钟索,虞柳拟焉将不伦’给我极大启发。由此体会到沈老作字是参黄道周的根,直接临习钟繇、索靖诸帖,并且访求前代学习钟索书体有成就的各家字迹作为借鉴。”[8]110
沙孟海认为,沈曾植晚年取法黄道周、倪元璐,并没有死学两家,而是把功夫用到了钟繇、索靖身上去,所以变态才多。从现存有纪年作品的题跋来看,沙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沈曾植在学习过程中,增加了方笔与翻转动作,帖派书写中融合了碑派笔法,别具风格。
沙氏认为沈曾植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根据笔者统计有纪年的题跋看,最早的有倪元璐书风的作品是光绪壬寅年(1902)的《宋芝山晴江列岫卷跋》,这是他五十九岁时所作,属于晚年作品。此后至宣统己酉年(1909)共7年间,沈曾植写了一批重要的的题跋。沈氏晚年,几乎看不到倪元璐风格的作品。倪元璐书风逐渐被章草风格与钟繇书风所湮没了。
沈曾植早年受家学影响,楷书从欧阳询和唐人写经入手,行书主攻黄庭坚,是创作上的准备期;中年在北碑、墓志方面的接受较好,是创作储备期;晚年以遗老自居,潜心思考,是厚积薄发期。自1912年后的十余年,是沈曾植书法创作的突变期。这十年间的交往与题跋多集中在与书法相关的事上。这段时间,他开始研究敦煌写经、北朝墓志造像,并运用到创作中来。题跋集中在写经小楷、《流沙坠简》、简牍章草、《阁帖》的碑刻上。
沈曾植晚年学习魏晋人写经与章草,最后实现了创作上的突变。多数人不知道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字与大字作品的分别。魏晋小字要转变为条幅大字,是很难的。沈曾植就面临着这个问题。所以,他参考明清人的高堂大轴的章草,完美实现了自己在书写上的突变。
可以说,晚年时期的沈曾植,在眼界上大大拓宽了,创作思路也被打开。如果是前期、中期的创作是有步人脚踵的话,那么晚期十年他则突破窠臼,达到了自我蜕变实现创新的高峰期。沈曾植在碑派书法上的成就斐然,主要是由于他能把碑派的书学思想渗透到诸书体的学习中,进而获得更多的创作灵感。只是他的创新阶段来得太迟了,倘若岁月假以时日,沈曾植的碑派书法在诸体中的融会与发展方面,还会开拓出新的境界。
三、对沈曾植碑派书法的批评之反思
沈曾植的书法批评者主要有曾熙、向燊云、沙孟海等人。他们对于沈曾植的书法批评,主要集中在沈氏的书法创新上。他特立独行的书写,使其赫然成为清末民国时期碑帖结合的杰出代表,后世不乏对于他创作的学习与研究者。
首先,在曾熙看来,沈曾植书法的长处在于生拙与不稳。这当然是相对于馆阁体而言。形上的不稳,实际上是稳的另一种高级形式。曾熙评曰:“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寐叟于前两义逊谢。至后语不晓。髯曰:翁覃谿一生稳字误之,石庵八十后能到不稳。蝯叟七十后不稳,惟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故不稳。愈不稳则愈妙。寐叟避席曰:不能至此,但奋吾老腕为之。未知能到不稳处否。”[1]244汉隶、北碑的用笔,对于塑造生拙的美感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是楷书还是行草书,用笔结体上都会融合汉隶、北碑的笔意。
向燊云集中于他的草书创作上,章草的成就,沈曾植肯定是那个时代承前启后的一面旗帜。他说:“书学包慎伯,草书尤工,纵横驰骤,有杨少师之妙,自碑学盛行,书家皆究心篆隶,草书鲜有名家者。自公出而草法复明。殁后书名更盛。惜其草迹流传不多耳。”[1]244可见,对于沈氏草书的创新度,近现代书坛上都是认可的。章草取法《流沙坠简》中的章草,其中有草稿体书风,用笔结体上都与汉代章草有别。沈曾植章草的创作实践,充分说明他在复古通会方面的成功。复古方面的取法点,是决定创作水平高低的关键。
可是,沙孟海在评价中表现出疑惑:沈曾植是如何实现创作上的突变的?他说:“他是一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奥秘‘一旦豁然贯通了’。”[9]17沙孟海的怀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沈曾植在创作上的创变,很多人都是很好奇的。沈曾植创作的秘密究竟何在?
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记载可以权作一注脚:“冒鹤老尝遇寐老(沈曾植)曰:‘君笔诚奇纵矣,然不过以方笔为包安吴耳。寐叟老拍其肩曰:‘此安可为外人道。’”[10]117
沈曾植以碑派的方笔改造包世臣书法,且自成家数,可算是一个善学的聪明人了。包世臣对沈曾植影响是很深的。沈氏晚年变法,用碑派的线条来表现包氏笔下的帖派书法,出于蓝而胜于蓝,获得门径且登堂而入室,非善学精思者莫能致之。用碑派笔法书写诸帖,实现笔法的融通,是实现碑帖结合的捷径。沈曾植碑帖融合能从质变走向量变,绝不是像沙孟海所说的那样一朝一夕实现的,背后的功夫少人看到而已。
光绪庚子(1900)以前,沈曾植书法以黄庭坚、包世臣书法为主要效仿对象,此后,取法日渐宽泛,书风也丰富起来。可以说,沈曾植在光绪庚子之前的交往,基本上以“同光体”诗人的身份参加雅集聚会,这是很长的时期,可以看作是沈曾植书法及书学思想的积淀期,而易见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作品中有郑孝胥碑派书法用笔的影子,这不足为怪。
沈曾植碑派书法与康有为碑派书法相比,虽然同是碑帖结合确是有区别的。
沈增植与康有为交往的时间并不长,在政治立场、艺术审美观念上存在着明显不同。光绪乙未年(1895)康有为中进士,之后举办强学会,黄绍箕、沈曾桐参加,沈曾植则没有加入,却也不反对康有为,可见他们在政治上持不同立场。
沈曾植在庚子年以后的二十年间,以前清遗老的身份,矢志于书法研究。在缪荃孙、罗振玉的帮助下开始研究敦煌写经、《流沙坠简》。他在民国三年(1914)时已经六十五岁,这时他向罗振玉问及《流沙坠简》中是否有章草与今隶一事。也是这一年,罗振玉把《流沙坠简》后半段寄给沈曾植;郑孝胥把《黄石斋尺牍》放在沈曾植家达半月之久(10月29——11月13日)。根据粗略统计,从民国四年(1915)至民国五年(1916),沈曾植书法中章草数量剧增,写经体融合黄道周、钟繇书风的作品大量出现了。
晚年除了在字体上的取法有改变之外,沈曾植在创作上给我们的启发很大。
首先是他用碑派的用笔去改造前人的书法,实现碑帖融合。沈曾植首先用碑派用笔改造包世臣。他大概看到包世臣用笔缺乏筋力,少骨气。楷书上又继续寻找内敛且极具个性的黄道周、倪元璐书法。他能把碑派运笔、简牍的用笔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笔墨语言。他的行书条幅翻转运笔颇有明人书法的个性特征,沈曾植在碑帖结合方面的探索还是比较成功的。沈曾植的创作方法,对于民国以后乃至当代碑派书法的创作都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次是异体同势,相互参照,最后达到诸字体在创作上的通变。沈曾植认为,篆书要参隶书法才会姿态生动,隶书要参楷书法才会灵动;篆书参籀势,才会质古;隶书参篆势才会质古。沈曾植对于邓石如取法玺印文字、瓦当文字的方法表示赞同。他自己最喜欢《校官碑》,因为此碑有篆书笔意。沈曾植的有些行书、楷书中有明显的隶书笔意。如横画,就是隶书的写法。以隶书笔意参入其他书体,是沈曾植书法创作上的突破。
最后,沈曾植写大字用小字法。我们可以看到,沈曾植的大字,是与其小字结构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笔法的改变而已。把小字放大书写,是六朝时期摩崖写经刻石上就已经出现的书写形式。如北齐《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就可以看作是放大的写经体作品。沈曾植能把钟繇、写经小字放大书写,并加入碑派的运笔,这是他在创作方法上的突变。
因此,在书法创作上,沈曾植给我们很多启发。尤其是在碑派书法创新上,更是让我们获得许多灵感。现以康有为作为对比说明之。
沈曾植强调的碑派帖派书风融合,碑的外延大,含汉碑,而康有为则只限于魏碑与帖学的融合。沈曾植与康有为的碑学观念、创作方法迥异,在碑帖融合方面的创作方法也有明显的不同。那么,创作出来的作品也自然不会相同了。康氏同样是以碑派线条去写帖,其气韵与风度仍可以看到帖的影子,或者说,其气势已够但骨力稍弱,这是应当注意的,而其弟子梁启超的书法,其中碑的成分又强调过多了。似乎已经没有办法体现出帖派的书写性。于右任强调写字“无死笔”,书写中也有生拙的美感,这与沈曾植是殊途同归的。
从明清书家入手,复归晋唐。崇唐碑,甚至是隋碑。沈曾植与康有为的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崇唐与卑唐的观念上。在同光年间,帖派书家崇尚唐碑如欧阳询、虞世南等人的书法。但是,陈振濂先生认为:“这些碑并非碑学里提倡的碑,而是‘帖’。因为它不具有碑在镌刻过程中的独立的美学价值”[11]101。沈曾植并不能算是纯粹的碑派书家。换句话说,他的碑学实践中,其碑与帖的概念都比康有为、梁启超、郑孝胥等人的要大。他把隶书的笔法融入到章草里面来了,把北碑的用笔与包世臣、黄道周、倪元璐等人的书法融合,写出自己的新意来了。他并没有像后来的书家一样纯粹用魏碑笔法来表现魏碑。
碑帖互证、互参,碑、帖的外延增大了,这与康有为碑帖观念不同了。沈曾植给我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以隶书或碑派的线条写简牍、以碑派笔法写行草、以碑派笔法写古今楷书等,可以说,沈曾植的碑帖结合的概念,涵盖更加广阔。
四、结语
不可否认,我们以往对于沈曾植书法风格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参考《寐叟题跋》书法和现存的墨迹的比对分析,沈曾植书法的全貌基本上呈现在我们面前。沈曾植书法的风格类型和字体类型的多样化,都和他的创作手法分不开的。通过文章对沈曾植书法的风格再认识,更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沈曾植书法创作价值的深入思考和再认识。
沈曾植碑派书法方面的创新,是碑派书法在康有为碑学理论上的新发展。康有为与沈曾植在碑学观、创作观上的不同,表明了碑派书法在清末发展存在的不同发展路径。沈曾植“尊唐崇魏”和“碑帖并举”的书学观,是碑派书法创作很重要的导向。从创作上看,沈曾植的确拓宽了碑派书家在创作上的思维界域,开阔了创作视野,丰富了创作成果,与后世的碑派书法发展很有裨益。
文章通过对沈曾植书法创作批评的分析,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沈曾植书法复古与创变的方法。沈氏强调复古,回归晋唐,兼用多种笔法,融会贯通。康有为的碑派书法虽也属碑帖融合的范畴,但其书法作品在审美效果上与沈曾植迥异。客观上讲,沈曾植碑派书法创作实践给后世的启发性会更大些。
沈曾植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达到了书法创作的鼎盛时期,完成了碑派书法的转型、蜕变。对于以沈曾植为代表的清末碑派书家的书学渊源、创作思想、审美批评层面的梳理、研究与深入发掘,是当代碑派书法创作现象与碑学审美流变研究过程中的关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