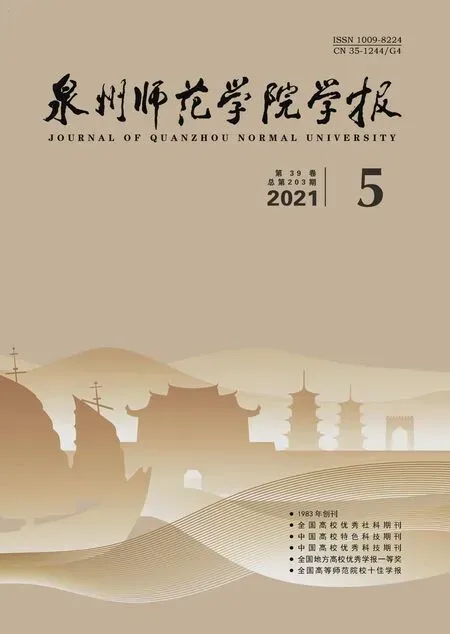泉州开元寺“飞天”造型世俗化、本土化过程及成因探究
2021-12-11陈晓萍王庆兰
陈晓萍,王庆兰
(泉州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两汉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了中国。随着印度佛教的传播,其文化艺术与中国本土思想艺术文化发生了碰撞,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中国本土化佛教文化。“飞天”(1)本文提到的“飞天”包括佛教的飞天、妙音鸟和迦陵频伽。飞天指佛教中天帝司乐之神,每当天上举行佛会,便凭借身后的飘带凌空飞舞,抛洒鲜花,以作歌舞,用歌声、舞姿、音乐、鲜花、食物供养诸佛;“妙音鸟”梵语是“迦陵频伽”,出自印度神话和佛教传说,是半人半鸟的神鸟,被作为佛前的乐舞供养。三者的功能和造型有着很强的联系,为了叙述的方便,三者在本文中被统称为“飞天”。艺术是中国佛教美术中的杰出代表,它的形象来源于古人渴望离开地面,翱翔于天空的浪漫幻想。现今,飞天是宗教艺术中最受人们喜爱的形象之一,它既满足了人们对仙境的浪漫幻想,又体现了人们对理想中世界的美好追求。
通过 “丝绸之路”传入泉州的“飞天”艺术,历经了一个外来艺术本土化、宗教艺术世俗化的过程,从人物造像、动作特征等都在发生了显著变化。飞天与佛像不同,其没有严格的规则制度,艺术家在对飞天的艺术形象的创造上,拥有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因此泉州飞天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极为显著。
一、泉州开元寺飞天不同时期的造型
泉州以多元包容的文化思想和独特的地域性,孕育出了精妙绝伦、造型多样变化的“飞天”艺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泉州飞天的造像呈现不一样的造型特征。泉州开元寺现存的几处不同时期的“飞天”形象,完美地展现出这个衍变的过程。泉州开元寺始建于唐垂拱二年,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庙。开元寺已知现存最早的飞天艺术形象是曾经位于佛寺大殿前庭的南唐保大四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1]535-536,在经幢的宝盖石上刻着四尊浮雕飞天(经幢现已经是残片,保存在泉州博物馆)。飞天(见图1)头戴宝冠,面庞丰满,耳垂及肩,上身右袒僧衹支,颈带项圈,飘带绕肩膀、臂飘扬,双脚裸露,腰系长裙,体态轻盈。从雕刻上看,其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总而言之,飞天形象呈现出唐朝特有的丰腴圆润的审美风格,是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传统唐代飞天浮雕形象。

宋元时期,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海运商业贸易发达,佛教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直接传入泉州。这个时期的泉州飞天艺术,以开元寺大雄宝殿上的妙音鸟以及甘露戒坛上的飞天伎乐最为独特、最为出彩。大雄宝殿上的妙音鸟共二十四尊,造型上与印度神话中“迦陵频伽”极为相似, 皆是人身鸟翼。妙音鸟坦胸露臂,神态优雅生动,头戴宝冠,项挂缨珞,臂束钏镯,背上两翼舒张——妙音鸟们在翅膀上有一些区别,分为老鹰翅膀和蝙蝠翅这两种形象,羽毛灿烂。她们分别捧着文房四宝、瓜果、南音乐器,侍奉在五方佛前;甘露戒坛的飞天伎乐(见图2)与大雄宝殿的妙音鸟不同,造型上更偏向中国传统的飞天艺术形象,它没有翅膀,造型上完全以人身的姿态,大多赤裸上身,或穿小件背心,手持“南音北管”乐器在空中表演大型的乐舞,身后飘带飞扬。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大大阻碍了泉州海运的发展。《明史·职官四》中以“倭寇祸起于市舶”描述了嘉靖二年的日本“争贡事件”。在当时,海边倭寇的兴起,让统治者加大了锁国的政策,减少了对外的交流——泉州从一个国际性港口沦落为了一个地方性港口。这个时期泉州开元寺的飞天形象演变成了藏经阁木雕迦陵频伽造型(见图3):迦陵频伽有着乌黑的头发,头戴红色的宝冠,身穿红色璎珞背心,腰系金色腰带,着绿色下裙,翅膀缺失。飞天的面部雕刻极为细致,单眼皮,长脸,嘴角上扬,似笑非笑,除了厚重的大耳垂与佛教造像有联系之外,面部带有本地人典型的长相特征。与宋元时期的飞天斗拱相比,其形象清瘦雅致,少了几分异域的风情,更有一种真实、世俗之美。
二、泉州开元寺飞天造型的衍变
从前述三种不同时期飞天来看,随着朝代的更迭,飞天造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佛教和佛教美术一进入中国,就表现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民族化的趋势,但直到隋唐,中国飞天艺术才逐渐拥有成熟的形象。在泉州,虽然唐代便有飞天形象,但其造型衍变的高峰期却是宋代——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交流,使得泉州“飞天”的形象更加成熟且独特,明代的“飞天”也只是在宋代的基础上,形象更加地域化。分析泉州开元寺“飞天”形象造型,可以看出当时飞天造型受本土化与世俗化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发展与变化。
一,从人物造型本体来看,泉州开元寺南唐飞天是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形态,其造型继承了盛唐一贯的审美风格,脸庞端圆、体态轻盈、身材圆润,但表情较为庄严肃穆;宋代的飞天脸庞端圆、高鼻通额、两耳肥厚,这种造像手法与当时泉州佛像造像的手法一脉相承(2)参考陈晓萍的《泉州木偶头造型艺术考述》(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级硕士毕业论文)第一章“木偶风格探源”,可知泉州继承了河洛地区成熟的宗教雕刻样式,而这和泉州现存菩萨造像和古老的提线木偶如出一辙。,飞天体态曼妙婀娜,裸露的身体和上肢做了几何的概括,较为浑圆丰腴,有一种雍容华贵的韵味,既有神佛的端庄,又带着世俗的明媚;明代的飞天则体现出了较为强烈的地域化和世俗化倾向,人物脸庞拉长,鼻子为蒜头鼻,眼睛睁大,嘴角上扬若微笑状,带着闽南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其庄严肃穆的表情已经被温柔亲切所替代。
二,从装饰来看,宋代开元寺大雄宝殿妙音鸟的翅膀除了常见的鹰翅,还出现了与传统造型完全不同的样式——蝙蝠翅(见图4),这种翅膀形式,在其他地区的妙音鸟上并未发现(3)关于开元寺大雄宝殿飞天的翅膀,另一说为“火焰翅”。参考穆宏燕的《泉州开元寺大殿妙音鸟翅膀造型溯源》(《美术研究》,2015年第4期)一文,提到“火焰翅膀可能是泉州艺术家在波斯细密画影响下创作性发挥。”但从翅膀外缘来看,有一个明显的倒勾,是为明显的蝙蝠翅。。在我国,蝙蝠形象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在史前时期,人们就开始使用蝙蝠形象了;而根据出土西汉时期的一件文物——蝙蝠形柿蒂座连弧纹镜,在镜上镌刻着“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的铭文,可见这一时期蝙蝠形象就和吉祥文化有所挂勾了[2]11;宋代时期吉祥文化开始兴盛,蝙蝠形象在宫廷和民间的推动下有着新的发展。大雄宝殿有着蝙蝠翅膀的妙音鸟极大的可能,就是源于当时人们对吉祥文化的喜爱推动蝙蝠形象的进一步发展。并且,纵观历代的蝙蝠形象,不管其艺术风格有着怎么样的变化,其在翅膀造型都有着一个明显的倒勾,这也是妙音鸟的蝙蝠翅膀形象所符合的。

图4 大雄宝殿带蝙蝠翅膀的“飞天”
三,从色彩来看,南唐的飞天是单色的浮雕,而宋代“飞天”斗拱和明代的“迦陵频伽”,择色极为鲜明大胆,飞天的头发皆为黑色,羽翼、宝冠和衣带的颜色为蓝绿色和红色,首饰耳坠、臂钏、腕钏处采用了金色,而“飞天”的皮肤选择了较深的黄棕色。这种肤色的“飞天”可谓绝无仅有。
四,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南唐的飞天浮雕作为建筑的装饰,是当时流行的样式。而开元寺宋代及明代的“飞天”,不仅是重要的装饰,还更具有实用功能——作为斗拱,起承重的作用。宋代的迦陵频伽“在艺术方式上,突破了绘画和线刻画等平面艺术形式,开始以建筑构件的形式大量出现在建筑屋脊之上”[3]。而泉州宋代的妙音鸟并非作为屋脊的装饰,而是作为建筑承重的斗拱,兼具美观价值与实用价值,这种设计意识与印度文明早期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有着莫大的关系,“从古希腊站立的、以头承重的石质女郎柱,到中国于空中横出的、以头托拱的木质妙音鸟的演变过程,其中的文脉(包括对人体的热爱) 源自古希腊,经古印度的融合过渡,在中国得到发展。”[4]现在的印度建筑中仍可见到以承重形象出现的飞天状构件,这也间接说明了泉州宋代飞天形象很可能从海丝之路传入。
五,从所持器物来看,开元寺宋代的飞天手持全套完整的“南音北管”乐器,包括“南管”的南琶、洞箫、三弦等乐器,和“北管”壳仔弦、北管笙、北琵琶、双清等乐器[5];或手持文房四宝、青素瓜果等。南音北管是泉州本土的传统乐器,与其他地区的飞天相异。此外,飞天手持文房四宝、素青瓜果,削弱了飞天作为神所有的神性,并以强烈的生活气息打破了宗教的氛围,也是飞天形象进一步中国化的展现。
综上所述,泉州开元寺飞天造型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种种变化表明了飞天形象在长期的演化中淡化了其作为神的存在,同时也代表了每一个时期泉州人的审美倾向。
三、开元寺飞天艺术世俗化的成因
“从人类学和古代社会的研究来看,艺术和美是怎样起源的呢?并不是起于抽象概念,而是起于吃饭穿衣,男婚女嫁,猎获野兽,打群仗来劫掠食和女俘以及劳动生产之类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极其平凡的事物。”[6]艺术与人有着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宗教艺术作为艺术分类的中的一个枝干,同样也是如此。虽然“宗教艺术本是以表现宗教观念,宣扬宗教教理,跟宗教仪式结合在一起或者以宗教崇拜为目的的艺术。”[7]7但在其作为人与神之间沟通的媒介时,常常在符合各自宗教观念和精神情感的基础上,不断贴近世俗的生活,贴近当地的习惯,使人们更加能接受宗教文化,便于宗教传播。
一,“飞天”造型世俗化的内因。飞天艺术世俗化和本土化是必然的,其最终的服务对象归根结底还是生活在不同地区世俗中的人。飞天这个艺术形象在宗教中本身就带有着世俗化的意味。实际上,佛与天部诸神也要享受伎乐,飞天这种艺术形象就是以此而出现——在佛前侍奉歌舞,轮流为诸天作乐,是供养佛的“伎人”,它的存在让庄严的佛国多了一番人世的色彩[8]。飞天这种艺术形象的出现,也表现了即使是在庄严的佛教中,人类也始终不会放弃对快乐本能和自身欲望的追求。
开元寺“飞天”造型是随着时代和人们的审美观念的转移而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恰恰反映了宗教艺术与世俗生活直接的关系。特别是明清时期,此时是中国传统佛教的衰落期。即使是在闽南这块“好信、乐信、善信”的土地上,这时的宗教生活,实际上更多的是演变为群众乐于参与的一种风俗习惯。这一时期,人们去参加庙会和法会,更多的是渴望通过对神佛的信仰,让自己的功利心能够得到“有求必应”的满足,寺庙的一些宗教活动也渐渐演变成了风俗节日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泉州飞天的形象出现了新的发展变化,其不再有南唐、宋元时期的圆润富贵形象,反而透露出一种清瘦娴熟的美。这个时期飞天形象的人性甚至已经超过了神性,更多的是为人们视觉审美而服务,其形象表现更多的是世俗的传统审美观念。
二,泉州开元寺“飞天”造型本土化的外因。创作“飞天”是泉州惠安的木雕师傅,文化水平不高,作为土生土长的艺人,他们在进行创作时,除了沿袭前人的程式之外,还会受到本土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前述提到开元寺宋代“飞天”手中所持泉州传统的演奏乐器“南音北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虽然历代“飞天”或双手合十,或手持乐器,但如此大规模完整地呈现本土乐器的飞天依然罕见;大雄宝殿妙音鸟的蝙蝠翅也是泉州“飞天”独有的符号。因“蝙蝠”与“遍福”谐音,蝙蝠纹成为闽南民俗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符号意向,其被广泛运用于泉州的建筑、日用器具的装饰中——如建筑装饰、永春漆篮、刻纸、家具等等。特别是在建筑雕刻中,蝙蝠纹更是比比皆是。泉州的木雕艺人创造性地将蝙蝠纹样融入妙音鸟翅膀的造型中,既是一种创新,更寄托了美好的寓意。
三,开元寺“飞天”斗拱色彩的运用,也具有浓厚的民俗色彩。开元寺木雕彩绘飞天其他部位多采用金色、红色、绿黑色这些颜色进行装饰,“闽南地区用色喜用红色、金色和黑色,按当地人的俗语云:红喜气、黑大方、金富贵。以红色作底子象征着喜气,金银色,从质地和视觉上都能感觉到财富的重要性”[9]。其中,最引人侧目的是开元寺飞天的皮肤为棕黄色(4)吴荣鉴在《敦煌壁画色彩应用与变色原因》(《敦煌研究》,2003年第10期)中提到:“敦煌壁画中主要用朱丹来叠晕染人物肤色凹凸部(即凹凸法),或阱朱丹加白色调成肉色,用量较大……隋代中期到中唐期间,敦煌壁画及彩塑同样长期在强光、高温、高湿度下,却变成了褐色”在全国不同地区的飞天形象来看,其大部分是皮肤白皙。敦煌石窟壁画中出现了不少皮肤黝黑的飞天形象,这些并非飞天本身的着色,而是因为颜料中的橙红色的铅丹和白色的铅白颜料经过上千年的老化变为黑色。泉州妙音鸟木雕以漆着色,由于古代所用天然漆这种涂料的稳定性,并未存在颜色氧化变深的这一说法。。关于这种肤色的设定,原因可能有三:其一,在寺庙众多的柱子上,飞天斗拱所占比重不小。妙音鸟的肤色与大殿的柱子颜色比较接近,更能使寺庙内部空间的整体色调取协调。在漫天神佛中,飞天是出于陪侍而存在的,如果其是跳跃的浅肤色,会抢了主佛的风采;其二,离不开当地文化的熏陶,地处亚热带海洋气候的泉州日照很强,当地居民皮肤呈棕黄色,而当时来泉州中亚人的皮肤颜色也是棕黄色;第三,其造型直接受到印度的壁画的影响,印度壁画中人物的肤色也是较为深色的棕黄色,这也是泉州开元寺飞天从海丝之路直接传入的一个间接证据。
宋元时期,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对外贸易高度繁荣,多种文化在泉州和谐共处。泉州宋代飞天形象跟从路丝之路传来的南唐飞天比较,从内到外都发生了变化,其棕黄色的皮肤、蝙蝠羽翼,手持“南音北管”和文房四宝、素青瓜果,并作为承重结构出现在殿堂中,种种变化表明了“飞天”形象明显淡化了作为神佛的身份,代表了当时泉州人们的审美价值倾向。
四、结语
历经几度发展与变化,佛教由外来宗教变成了中国本土的宗教,由虔敬的信仰膜拜到世俗的民间风俗。而在佛教美术中,也出现了相应的易变。从佛国走向人世间的“飞天”,也正是中国佛教艺术,从宗教化逐步走向世俗化的象征。从更深远的视角看,泉州开元寺飞天的艺术形象是宗教性和世俗性、异域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神性和人性的完美结合。同时,泉州开元寺飞天造型世俗化过程,也是宗教文化不断使自身适应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相的过程。
总而言之,向着世俗发展,是宗教艺术必然发展的总趋势,也是宗教艺术最终的归宿。不同时期开元寺飞天形象,凝固了当时一段段历史文化,使人们可以透过时间的长河,窥见千年前古人的审美和追求的变化。随着宗教的远去,泉州飞天作为宗教性质的部分不断消逝。现今,人们更多的是将它当作一件极佳的艺术品来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