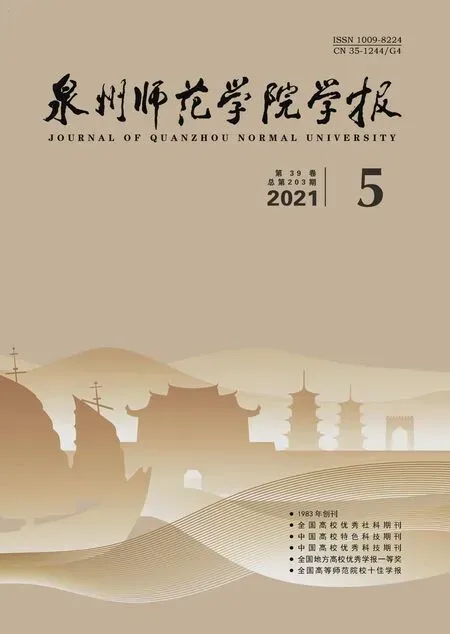从陆维钊碑帖互补思想看其行草书风的形成与演变
2021-01-03徐宇
徐宇
(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一、陆维钊学书经历及碑帖的互补思想
陆维钊(1899—1980),浙江平湖人,字微昭。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曾跟随王国维先生任助教,后协助叶恭绰先生编纂《全清词钞》,于诗词、书法、绘画等领域均有造诣。
陆氏早年随家邻潘锦甫习书,从《多宝塔》入手,后转学于六朝碑刻,尤得力于《三阙》《石门铭》《石门颂》《天发神谶》《爨龙颜》《爨宝子》,中年之后,融会贯通,独创“陆氏蜾扁体”,尽管陆氏以碑入手,但其书法思想观念有别于其他部分碑学书家“崇碑抑帖”观点。如陆氏对于碑帖选择的认识就与之不同,初学时他认为”临摹之范本,如为墨迹,必易于碑版;如为清晰之碑版,必易于剥蚀之碑版:即由推想窥测易不易之程度,此三者有不同尔”[1]5。
碑学自经历阮元、包世臣的推崇以来,乘着帖学发展的靡弱势态而走入书家的案桌视野,这本是书家寻求突破的一种倾向,但经由康氏早期书学观念的推波助澜,导致后起的书家们取法非碑即帖,而陆维钊秉持着“碑帖互补”的书学观念,以回归魏晋为导向,碑刻和墨迹书法作品均为其所取,即“碑可强其骨,帖可养其气”[2]82。
碑刻和墨迹对陆氏来说只是他学书的补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化古为我。陆氏的这种碑帖互补观念实是对沈曾植的“南北互证”观的继承与发展。
王守民曾论述沈曾植与陆维钊的书学观念。康有为对包世臣书学观念的继承发展成极端的认识,沈曾植则对包氏观念的继承较康有为更缓和辩证。沈氏承继包世臣碑学观点,将碑学放置在广大视野下,使帖学成为其参考,这是对包氏碑学观原意的进一步深化阐释。王守民将沈氏这种方法称作“南北互证”当为精辟之语。
陆维钊生于沈曾植书法辉煌时期,早年陆氏在清华随王国维先生任助教,据笔者考证,民国三年(1914)冬王国维与沈氏结识,时年沈氏正六十四岁,王国维音韵学、元史研究等方面均受沈氏启发。王国维对沈曾植书法的推崇,或为陆氏的学术观念转变埋下了种子。
沈氏的碑帖互证,王守民释为“在碑帖学习过程中,用笔、结体、风格上相似的碑帖可以相互参考、比较”[3]。而陆维钊则在沈氏的基础上,对碑帖各自优点进行区分,陆氏认为“选择碑之长处,在其下笔朴重,结体舒展,章法匀净绵密;帖则用笔精熟,气韵生动”[2]82。
与康有为的卑唐观、沈曾植的尊碑不同,陆维钊对待碑刻有独特的理解。“时人好尊魏抑唐,或尊唐抑魏,一偏之见,不可为训。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原可并行不悖,正如汉学、宋学不必相互攻讦也”[1]20。陆氏辩证看待魏碑与唐碑,认为其偏向哪一方都会失之平衡,只要取其长处吸收即可。
陆氏推崇唐碑的实质是借唐碑溯源魏晋。“窃尝谓唐之真书乃集汉魏六朝融合而贯通之者……唐人气息可几魏晋”[1]35。唐碑集汉魏以来于大成,规矩林立,守正方整,于整齐之中蕴含变化,陆氏从此处入手,便取得上溯魏晋的“钥匙”。
在陆氏的书法创作中,碑帖互补思想始终起着指导作用。从篆书方面来看,陆氏蜾扁体字型结构虽偏扁,沿用许慎旧文篆法,篆隶融合,却又非篆非隶,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陆氏的部分蜾扁体作品中可窥见一些行草书笔意。从行草书方面来看,碑派笔法与帖学笔法时或可见,而且并不受拘束,任意挥洒,整幅作品或碑派气息占主导、或帖学精神较强、或两者兼容,平分秋色,风神骨气自然流露。
二、陆维钊碑帖互补思想在其行草作品中形成及演变
笔者梳理陆维钊的行草书作品,以为陆氏行草书风形成与演变可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行草书以1958年篆书《心画》作品落款为代表。篆书《心画》的行草落款“古人有书心画也一语,其心画易画哉名在青推其心之所之而已”,此幅作品主要部分内容由篆书书写,落款用行草三行结尾,笔者选取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陆维钊著《书法述要》收录的篆书《心画》分析。
据考证,邢秀华在“陆维钊的书法艺术及其历史地位”一文中指出“这种书体(陆氏蜾扁体)在先生的翰墨生涯中,最早面世的作品世作于1958年,其代表作是‘心画’”[4]84。吴玉璋在“陆维钊书法艺术解析”一文中称“(陆维钊)六十一岁还在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时所书篆书《心画》的行草款”[4]116,吴氏在同一文中的后半段总结陆维钊的作品时,又称“六十四岁的篆书《心画》”[4]126。吴氏对篆书《心画》的年代前后存矛盾的说法,而邢秀华则称最早的“心画”作于1958年,笔者根据鲍士杰先生的《陆维钊年谱》[5]统计发现陆氏存在同一种内容在不同时间多次反复书写的情况,故吴氏和邢氏分别见过不同时期的作品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从《书法述要》所载的篆书《心画》来看,此时陆维钊书写的篆书字体修长,篆隶笔法能自然融合在创作中,下笔厚重中实,字法沿用许慎说文,与吴昌硕风格气息近似,纯然一幅外拓肆意的状态。行草落款用篆隶笔法书写,“古人”“一语”“画哉”“其心之”等字的笔画之间有意作出连带的连带与牵丝,“易”“哉”“所”字等纵向笔画伸展拉长,“于”等字部分笔画颤抖书写,从后期书写的行草作品来看,此时陆氏的行草以篆隶笔法为主,在创作上只是有意识的将行草书特点融入其中,但似乎还未融入明显的帖学笔法。
第二阶段以小字行草作品《先大父同邑画友手札》《毛泽东沁园春》《十二铜盘照夜摇》为代表。与《心画》落款对比,这部分作品可以看出陆氏已对宋人墨迹书法与近人书法有所临习与关注。章祖安先生在“陆维钊书法论”一文中谈到“陆先生于艺事,从无门户之见,于书法上也不喜言讲碑学与帖学之别。他曾向我道及马一孚曾言碑学与帖学之纷争是无事生非,庸人自扰”[4]8。
陆维钊认为宋人之书是集唐人之大成,宋人书法作品蕴含着唐人的气息,这与他辩证看待唐、魏碑刻是同样道理。“窃以为唐之真书乃集汉魏六朝融合而贯通之者,而宋之行书乃集唐之真草融合而贯通之者”[1]35。由此可见陆氏推崇宋人实质上的对晋唐古法的重视,而在宋人之中陆氏最喜欢苏轼。“宋人之书,当以苏轼为第一”[1]35。
这三幅作品整体风格接近苏、黄风,字形横向伸展取势,方圆并用,单字左下角的斜向势态与右边的收敛势态形成强烈对比,整体结构左向倾斜,在此作中完全看不到陆氏篆书《心画》时期行草落款的影子,这部分作品笔法精熟混融自然,不再刻意依靠笔画之间牵带来作书,转而重视字内笔画的连续取势,生动活泼。
笔者参照苏轼的《黄州寒食帖》与吴昌硕的部分行草手札,发现陆氏之所以转变如此快,一方面是对苏轼书法的大力临习,另一方面还极有可能在取法苏轼的时候参照过吴昌硕的手札作品。吴昌硕的行书手札行气绵密,字内的笔画呼应取势,左下角斜撇笔画放纵,这些特点在陆氏的作品中可窥得一二。而吴昌硕与陆维钊书学观念与学术经历存在一定的相似,如两人的书法创作都以篆隶书为主,吴氏从石鼓文中突破而出,陆氏则从汉魏六朝碑刻创“蜾扁体”,两人都以篆隶笔法入行草,且均在诗、书、画等领域有所见解与造诣。吴氏作为陆氏的前辈,必当成为陆氏关注的对象。
《十二铜盘》是陆氏临恽寿平画跋之作,金峥指出“他(恽寿平)同时对黄庭坚、米芾、倪云林多有临仿,有临作和画跋可资证明”[6]66。笔者以为陆氏之所以临恽寿平的作品,正是看到了恽寿平行草画跋中的宋人气息,而陆氏借此临习得以感悟宋人书风并上溯晋唐风骨。其对恽寿平书法的追崇有两方面,一是倾慕于恽氏的画作,另一方面是借恽氏书作入得宋人堂奥。
第三阶段以1977年左右大字行草《天地乘龙卧、关山跃马过》《为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作》《鲁迅先生送增田涉君归国诗》作品为代表。《天地、关山》联可视为陆维钊以碑笔入行草的突破之作,与之前的《心画》行草落款相较,这时陆氏的碑帖融合精进不少,内擫与外拓笔法自然显露,视觉上给人以强烈的冲突感。真可谓“一气呵成,形方势圆,顾盼情生,诗句豪迈,其书也是捭阖跌宕。”[7]282“天”“地”等字的收敛与“卧”“过”的肆意恰到好处的融合,细看既有帖学的精微笔法,远观又有碑学的宏壮气势。“过”字的笔画取之于陆氏推崇的《石门铭》,在另一幅《自书四碑名》作品中,陆氏总结自己的碑学营养。“《三阙》《石门铭》《天发神谶》《石门颂》,余书自以为得力于此四碑。”
小字行草轴《为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作》作品是陆维钊以纯方笔书写行草作品的代表,此作陆氏以《爨宝子》《爨龙颜》等方笔之意创作,以《石门颂》中伸展笔画取纵势,整体风格方正严整,营造出一种庄重严肃的情绪。“逝”“周”“导”“迎”等包围笔画完全从《爨宝子》《爨龙颜》中取法,“年”“华”“酬”“仰”“择”“攀”等竖向拉长则从《石门颂》中借鉴,这些拉长的笔画散布在作品的各个地方,既调整了章法上的单调,又强化了整幅作品的碑刻气息。 陆氏这一时期作品对碑帖的取舍亦在尝试,这种以碑法写行草为主,作品中的帖学气息被弱化,使我们可以窥测出陆氏碑帖互补思想的变化与完善。
小字行草条幅《鲁迅先生送增田涉君归国诗》是陆氏晚期作品,其作品用笔方圆结合,字形随势变化大小,厚重与纤细笔画均充满力量,笔画饱满精熟,碑学与帖学气息并重。整幅作品结合《兰亭序》《爨龙颜》《石门铭》、魏碑之笔意,融合一体,变化多方,细心察之方可从精微处领会。如该条幅作品中的“丹”就与《石门铭》中的“辀”的右半部分如出一辙,“是”与“随”和走之底的一些字就有《兰亭序》和《爨龙颜》的影子。
据笔者考察,陆氏对《兰亭序》曾有过多次临写,其中包括“摹、临、背”多种手段。如1971年陆氏临的《兰亭序》后面就有跋语“第八十八通”,陆氏在与人交流的时候就常感叹学王太晚了,并且他面对学生也经常呼吁其多临《兰亭序》《圣教序》,陆氏自跋早期临习的兰亭序作品时,记录下此语“余临《兰亭》第一百五十通以后稍有所会,此为初学时临写,形神俱失,作为垂戒可也。”
陆氏临写兰亭还会对不同版本进行区分,如他自跋语中就有对其临习的版本进行说明,据有记载陆氏临过虞本兰亭以及冯承素本兰亭。陆维钊的临习不是一昧的单纯模仿,他是怀着创造性的思想进行临习。
第四阶段以1979年左右所书周恩来《送蓬莱仙兄返里有感》条幅、纪念西泠印社七十五周年《水木、亭台》联为代表。《送蓬莱仙兄》条幅是陆氏晚年行草书作品,与中期的行草书相比,陆氏此幅作品充斥着徐文长笔意。起笔的方圆、线条的粗细信手拈来,随字形的需要而生发,碑派浑厚线条在衔接时取方折之势,变化多端;结体冲破常规要求,左右结构或上下错位、或拉开距离,营造出一种奇异险绝、跌宕恣肆的氛围。整体章法气势连贯,动荡连绵,个体的字形服务于整体的需要,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
《水木、亭台》联中,虽是行草书的结构,却参杂了篆隶书的笔势,有意于收缩密集的笔画,而将撇、捺等笔画伸展,甚至将左右结构中的右半部分下移取纵势,质的圆厚内敛与方折爽利转折形成动态冲突的和谐。
陆维钊行草书中的碑帖互补思想,是其篆隶书碑帖结合实践的延续与发展。篆隶书中的碑帖结合方法为行草书融创提供了参考,这使得陆氏可以从大量的碑帖作品中汲取养分。碑刻和墨迹数量众多,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作品是一种能力,而陆氏在篆隶创作中的成功,既培养了他选择碑帖的广博眼界,又增强了其融会贯通的创新突破能力。
从早期行草题跋作品看,陆氏以碑派笔法为主,后逐渐临习帖学墨迹,心摹手追,融汇碑刻与墨迹各自的优点,其行草书中的碑帖互补思想,已经不是单调的碑帖融合,陆氏基于碑帖的深层理解、想象、神采的摄取,在行草书中以“自我”精神为主导,汲取不同碑刻、墨迹的特点融汇自身。用笔上,线条内擫圆厚雄壮与转折的外拓方折爽利形成动态平衡;结构上,笔画收缩紧密连绵与纵逸伸展豪放取势;章法上,单字字内错位独立有序与连贯动势融合,整体风神跃然纸上。在整个过程中,陆氏“自我意识”始终主导着书法作品,碑与帖只是其摄取需要的素材,最终的目的是化而为之己用,形成其独特的风格。
陆氏行草书中碑帖互补思想的形成与演变不是偶然,这根植于他深厚的传统功力,得力于其“书外”功夫的修炼与提升。对于诗词、绘画、印章、音乐、医学,他无所不精,而且能融会贯通,他一生都沉浸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努力拓宽自己艺术实践的深度与广度,这些经历为陆氏行草书的碑帖互补思想形成,提供了可能性与源源不断的能量。
三、陆维钊碑帖互补思想下行草作品的反思与启示
陆氏晚年教导学生要以淡泊的心态做学问,淡于名利,正是由于其生活学习过程中的通达心态,使得他从六朝碑刻入手也未影响其书法观的大局面,在面对前人崇碑抑帖、崇帖抑碑的极端认识时,陆氏继承沈曾植的碑帖互证观念,并衍生出了他碑帖互补的书学思想。
从陆维钊的行草书创作层面来看,早期行草书作品以碑派笔法为主,线条的牵丝连带显得不够自然,自从其关注帖学墨迹之后,转而花费大量精力摹写、临写、背写,终悟得帖学笔法。在碑帖互补思想的影响下,陆氏行草书掺以篆隶笔意,在冲突对比之中营造出个性鲜明和气势磅礴的风神骨气。只叹惜陆氏在行草融合互补的黄金创变期离世,不然其行草艺术上的成就或可超越“蜾扁体”。
笔者纵览陆氏的行草书作品,试指出其碑帖互补思想下行草书风的长处与不足:
首先,陆氏行草书风的长处在于既注重个体,又重视整体风神骨气。在单字中,陆氏采取左右错位的方法,造成字单字字形的险绝,密集的块面与伸展笔画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而单字融汇于整幅章法中时,却显得和谐自然,令人眼前一亮又引人深思。
其次,陆氏行草书在连贯的基础上,注重空间的构建。陈振濂认为,陆维钊行草书成功之处在于能以动势带出丰富的造型结构。这实际上得益于陆氏对魏碑篆隶书的学习,人们关注行草书往往容易局限于整体的连绵气势,而陆氏则在结构空间的舒展中,完成了气势的连贯。
陆氏行草书不足在于,未形成稳定的风格。从陆氏整个生涯时期的行草作品中分析可知,由于陆氏对碑帖的广博吸收,导致其临习过多家作品,尽管他最终的目的是上溯魏晋古法,但在碑帖互补的路上还未将临与创融汇至完全成熟稳定的状态。
古往今来,书家个人风格形成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孙过庭《书谱》有“人书俱老”之语当是其最好的注脚。惜其陆氏晚年行草书风正处于成熟期,却不曾想病重逝世,留下了未竟遗憾。
陆维钊由碑入帖,并得以生发出“碑帖互补”思想,陆氏始终坚守这种观念,并将之应用到书法创作的方方面面,这种“超前”的书法观不仅使他与同时期的其他书家拉开距离,而且陆氏的“碑帖互补”观念对我们现今学习书法亦有重要的启示。陆氏曾言“以隶求隶是写不出来的”[2]86,从此语中可知陆氏早已认识到只注意碑刻是行不通的,必须融百家之长处,化他物为我用,偏颇的看待某一方面是走不远的。只有兼得碑学与帖学之长,方可证得变化,融会贯通。
当今时代“书法热”潮流风气盛行,展览的大量出现既是“书法热”潮流的直接反映。然而在这种潮流下,许多流于形式缺乏实际内涵的展览夹杂在其中,粗制滥造、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成了这些展览的特点,甚至于一些展览入选作品中存在许多错字。在这种评选状态下,投稿的书者也流于形式上的制作,忽略了书法艺术的精神内涵,培训班的“批量制作”使得展览中出现了千人一面的现象,这些书者似乎已经成为了展览中的“投稿机器”,从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丝毫情感的流露。
笔者以为,陆维钊的书学思想与书学经历能给当前书坛的书者们一些启示。
第一,书法学习应具有广博的识见。书家的眼界决定了其书法艺术的高度,陆氏面对碑刻与墨迹,兼收各自长处化为己用,这高超的学书识见是陆氏碑帖互补融创成功的重要条件。
第二,书法创作要具有求新创变的意识。陆氏的创新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将许多相对立的概念融汇于一体。如“蜾扁体”中是篆隶书的字形,却夹杂着行草书的笔意,既雄浑厚重,又有生动自然。行草书中篆隶的线条质感与转折的方硬劲利形成一种“冲突的和谐”,在注重空间的构筑时却又能保持整幅作品的风神气势。用章祖安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极不和谐而极和谐”。
第三,努力提升文化修养。陆氏不仅于书法艺术有所涉猎,其在诗词、篆刻、绘画等其他艺术上均有造诣。他深知各类艺术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所有艺术思想的来源都是传统文化的延伸,学问的高深与否直接决定了书家艺术成就的高低。
陆氏“碑帖互补”思想下的行草书实践已为我们提供可行的方法,这种辩证的书学思想不仅可以拓宽我们的学书视野,亦可作为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
四、结语
陆维钊在近现代碑学理论与创作研究方面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他由“碑可强其骨,帖可养其气”的单一审美观,逐渐转演变涉猎广泛、“碑帖互补”的书学观,在此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笔下的书写形态从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转化。陆维钊行草书中的碑帖审美观的形成与演变,是民国以来碑帖融合过程中的创作典型。
陆氏碑帖互补思想还未得到全面挖掘,应该指出,陆氏在书法艺术上始终坚守“在对立中求得和谐统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求新创变”观念。当其他书家困扰在碑学或帖学的视域时,陆氏则兼取碑帖之长,在冲突中寻求平衡与和谐。
陆氏的“碑帖互补”思想是对清末民国以来“碑帖融合”书学思想的发扬。碑派书法如何在碑学与帖学的对立之中获得发展,陆维钊通过自己的的书学实践为我们指明道路。陆维钊书法中碑帖互补思想与方法,对于我们拓宽民国以来碑派书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系统地进行碑学审美与思潮研究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