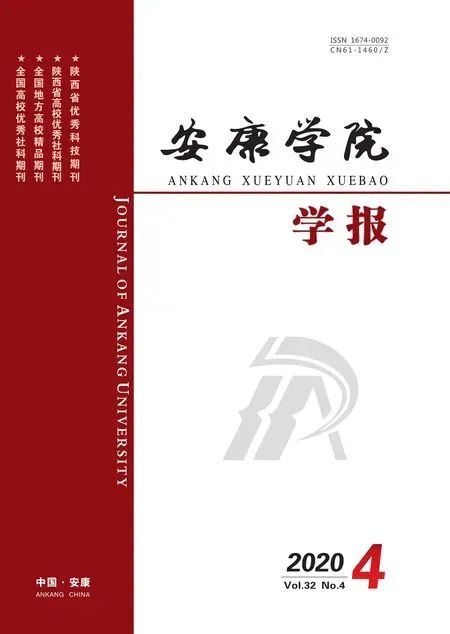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中协商民主的困境、出路与意蕴
2020-12-27茹亚辉刘瑞萌
茹亚辉,刘瑞萌
(辽宁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三三制”政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内容,而在此政权的运行过程中,协商民主又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维度。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作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协调并处理各阶级阶层在政权中关系的光辉典范,使得参与到政权中的各党派人士都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利益,最终实现了团结合作、共赴国难建设宗旨。笔者以“三三制”政权的生成为基础,深入探讨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中协商民主面临的困境及出路,进而分析“三三制”协商民主承载的现实政治价值意蕴。
一、“三三制”政权的生成
1940年3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提出了“三三制”的构想,即“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742。这一构想既是时势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有深刻的理论来源和现实基础。
首先,“三三制”政权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势使然和对国民党企图“一党专政”的严厉回应。一方面,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共产党意识到单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时需要联合其他阶级、阶层和党派共同完成这双重历史任务。在这种背景下,按照此前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同时考虑到中间势力对民主的强烈诉求,中共需要重新设计政权体制,与其他阶级中的进步人士一道团结抗日,共赴国难。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中蓬勃发展,这是国民党不能容忍的。1938年10月,国民党宣扬“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2]的口号,对边区制造一系列反共摩擦,同时颁布法令企图防制和处理异党,实行“一党专政”。国民党不但没有全心抗战,反而还抛弃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遗志。面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毛泽东指出:“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1]741。“三三制”政权就是在这种坚决有力的回应中应运而生的。
其次,新民主主义理论擘划了构建战时新型国家政权的基本雏形。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这一新的国家政权构想就已经初步形成。1936年8月共产党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1937年10月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对这个口号的含义作出明确阐述。正是有了这样的铺垫,1940年1月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此理论擘划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蓝图,不仅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性质,即革命性使其“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1]673,妥协性又使得资产阶级不能承担起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责任,而且还指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1]675,是以“联合专政”的国体与“民主集中制”的政体为基础所构建起来的新的国家形式。但抗战初期中共在根据地所建立的政权显然不符合新的国家政权思想。如何实现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命题,也是对当时“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1]677的现实思考,正是出于这种考量,“三三制”政策得以出台。所以说,毛泽东所阐述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原则既为“三三制”政权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圭臬,又为构建战时新型国家政权指明了方向。
最后,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为中共政权中统一战线的扩大提供了现实依据。苏维埃政权致力于工农革命,无法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而随后中央红军的到来,则改变了陕北原有的发展局面。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时中共从抗日大局出发,作出了从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的重要部署。在政权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共重新核定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资格的阶层。1937年5月中共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法条例》中规定:“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十六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颁布了新规定,进一步保障其人权。新法令摒弃了原有的阶级色彩,给予地主和富农基本政治权利。另一方面,抗日民主政权废除了原有的苏维埃制度,实行议会民主制,同时边区议会改名为参议会,作为边区的民意机关和权力机关,进一步保障公民权得以实现。“三三制”政权思想的产生和制度的推进就是在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的改革实践中发展而成的。
“三三制”政权不仅适应了抗日的需求,而且也符合新民主主义理论对新型政权的诠释,同时也是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过程中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突破了狭隘的阶级观念,建立了这一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新型政权,此等制度设计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大义和首创精神。
二、“三三制”政权中协商民主的困境
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和政治形势的日益严峻催生了“三三制”政权,它的实施旨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同时满足中间势力对民主的诉求。“三三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促进党外人士参政议政,增强协商民主的效力。然而,在“三三制”协商民主实践运行初期,却面临一些困境。
首先,寻求党外人士的工作存在形式化倾向。如何保证“三三制”的比例,成为政权建立初期中共面临的一大难题。毛泽东曾言:“这种人数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4]480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某些地区却采取机械的方式凑出了“三三制”的比例,这种行为为后来的民主协商埋下隐患。由于对进步分子物色程度不够和“左”倾关门主义的干扰,凑数成为极普遍的现象。如在陇东分区,某些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也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可以被当作民主人士列入其中,这种做法深受当地民众的质疑。让一些原本不算进步人士的党外人员进入政权,势必会造成党内外矛盾逐步激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工农的利益,甚至使得政权偏离了其运行的正常轨道。即使寻求到党外人士,某些地区也会出现形式化的弊端。如在庆阳“三三制”选举中,“地方上有威信的进步人士聘请到选委会来,不认真的聘请或聘请了仍把他们当作‘聋子的耳朵’”①参阅《庆阳县高迎区第三乡试选的经验教训(1945年10月14日)》,庆阳市档案馆藏,档号32—10—23。,这说明当时根据地民众并没有深刻了解“三三制”政权的实质,部分地区仅仅将其作为中共下达的指令,因而在实现其对民主诉求的过程中困难重重,这也为日后政党民主协商的运行增添了难度。
其次,党外人士政治表达自由不够充分。“三三制”的初衷是中共不仅要在形式上吸纳非中共人士,还要赋予其一定的职权,从而满足他们对民主的需求,以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但在实际的协商民主实践中,既要顾到这个阶层又要顾到那个阶层,这一目标却是难如所愿。一方面,部分党员干部与党外人士相处存在隔阂。例如“如县府张科长(彦儒)到三区工作,觉得三区区长很自大,看不起他,实际是这样的,区长孙长贵同志不善于接近各方人士,表面上不十分热情致成误会。”[5]69这种生活实际表明部分党员与非中共人士之间仍有障碍,或者说双方还不适应这一新政治模式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进入政权后的党外人士受重视程度不够,“有职无权”现象时有发生。再如党外人士卢振藩会议发言,遭到与会其他人员打断和呵斥,回去后发牢骚说:“撑门面,党外人士不说话,一说话就驳”[6]。这表明部分党内干部受传统思维模式的桎梏严重,他们不会与党外人士共同协商讨论,从而使得“三三制”在协商民主实践中收效甚微。同时部分地区还存在着“党包办一切”的现象,某些党员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思想中也混进了“以党治国”的错误观念,这使得参与到政权里的党外人士“觉得无权,对政府不会有兴趣,因而不会积极”[7]。所以说,“包办”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党外人士的参政积极性,使党外人士从心理就对政治持冷漠态度,这使得协商民主的意义大打折扣。
最后,传统乡村社会实际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张力,使得协商民主效果不尽如人意。从革命冲击与社会变迁的视角考察,我们会发现,1940年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后,民主模式逐渐趋于现代化,但乡村权力结构和传统社会文化却没有完全消散,皇权心理和保守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使得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极大张力,从而影响到民主政治的运行与协商民主的效果。在广大农村地区,乡绅是乡村社会权力格局的核心,他们所信奉的儒家伦理也就自然成为村庄的“乡规民约”。儒家思想核心观念重在人情,其“人情法则”在乡村社会中突出表现为“面子”文化,“三三制”下的协商民主实际就是以传统社会民俗风尚为基石而形成的一种“民主商量”,这种议事的方式,让大多数人感到有面子,心里舒坦[8]。在谈及如何团结党外人士时,冯志国提出:“一般党外人士都是爱好面子的,崇尚客套的,所以我们不可拿党内的作法去对付他们,尤其‘斗他一斗’的办法,是来不得的”[9]。这种“客套”极端化在民主协商过程中同样会造成问题,例如著名党外人士李鼎铭任边区政府副主席时,就造成了一种“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10]的现象。此外,乡村中民众还有着“怕惹人”“不得罪”的心理,这种心理普遍存在于协商民主运行过程中。例如在召开评议会时,人们总认为“大会人太多不好说话,小会易开,自由发言”①参阅《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乡选总结》,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7—2—6。或者“说一个公道话,惹一个人”[11],这种心理的存在成为推行协商民主运行的一个障碍。虽然“三三制”民主使新政治模式与传统社会“面子”文化相契合,但是在乡村这等现代化转型远未实现的地区要实行现代民主制度,民众还需要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因此这也就成为中共推行协商民主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
三、“三三制”政权中协商民主的出路
中共在“三三制”政权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固然会增加民主协商的难度,但是对待这些问题,中共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探寻并实践多种出路致力于解决所面临的困境。
其一,聘请党外人士或党员自动辞职来满足“三三制”的比例。为消减在民主选举时共产党员占多数的现象,进而保证“三三制”原则得以有效贯彻,林伯渠发布的《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中讲道:“各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该自动退出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各县政府还可以选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士,酌情聘请”[12]。这封指示信则为边区参议会第二次民主选举提供了指南。从边区政府组成人员上来看,当选的有18名政府委员,其中7名是共产党员,徐特立立即请求退出,而以民主人士白文焕替补;在选举参议会常驻议员时,共产党员王世泰、萧劲光也主动退出,从而为选举的顺利开展铺平道路。但是在选举过程中,部分群众思想不通导致开明绅士落选的甚多,于是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决定聘请以开明绅士为主的46名非中共人士为议员,从而在人员成分上符合“三三制”的基本原则。这种对策不仅是对“三三制”比例要求的有效遵循,而且党外人士来源之广,也有利于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取得抗战胜利具有重要作用。
其二,实行党政分开,在政府机关中设立党组以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在由苏维埃政权转变过来的“三三制”政权中,部分党员干部依然存在着“把持包办”的惯性思维,要解决这一问题,我党首先实行了党政分开的改革。党政分开初衷就是使党委和政府要有明确的分工,并且要规范“三三制”政权的运行体制。这样就可以打消人们认为我们的政府是“党政府”的疑虑,同时也可以提高党领导的效率。党政分开并不意味着党领导能力的削弱,我党进而采取了在政府机关中设立党组的办法来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三三制”政权是抗日战争背景下各阶层、各党派的联合专政,由于政策主张不尽相同,所以在他们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这就要求党组要认清自己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党组作为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应积极发挥民主作风,团结非党干部,并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非党干部,反对“因党而骄”。在党组运用问题上,“他(党团)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自己党员的努力在政府会议和参议会中,说服非中共人士得到通过,才能发生效力”[13]。同时,“切忌政府和民意机关的一切日常工作都由党团来决定或代替”[5]71。这种合作就充分显示出一种协商民主,是不同意见之间的妥协与协调,同时中共愿意让出政权中三分之二的席位给非中共人士,这也表达中共希望和各党派进行协商的诚意。这种规则从制度上保障了在政权机关中党与党外人士民主协商的有效实施。在与党外人士进行协商时,为了进一步克服“包办”,我党还需要重新定义“领导权”,正如毛泽东所言:“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意见”[1]742。党内要建立一种新型领导观,即党内领导应更加注重对民主方向的引导,而不是对具体事务的包办,同时要牢记党对政权的领导。党的领导责任要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14]。也正是由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民主协商才会健康地运行下去。
其三,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一揽子”会议来解决非中共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某些党员排斥党外人士,不愿和不惯与他们合作共事,这使参与到政权的党外人士变得“有职无权”,这种狭隘性使得民主协商经常事与愿违。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1]743。根据指示,中国共产党设计的方案是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1944年3月1日,毛泽东指出:“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目标之下”[4]90。该论述充分表达了中共愿意与党外人士民主协商的诚意,同时也体现了“三三制”政权下协商民主的广泛性与真实性。党外人士座谈会召开时,各党派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受到了广泛的肯定与赞誉。边区教育厅厅长柳堤就支持说:“我们愿意接受一些政治教育,以后这类报告,我们很愿意听。”[15]于是,陕甘宁边区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作为典范加以推广,这也成为解决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最主要手段。除此之外,中共还以政策法规的形式作了一些硬性规定,从而使得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法治化、规范化。基层政权也相应开创了“一揽子”会议的模式,即决议是一揽子,执行也是一揽子。林伯渠对这种模式赞赏说:“这种方式又民主又集中,合乎三三制精神,能解决问题,能办好事情。”[16]采取党外人士座谈会和“一揽子”会议等形式后,绝大多数党外人士的态度出现明显改观。中共不仅通过制度创新,而且发挥党外人士的示范与带动作用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双管齐下不但调动了党外人士的参政积极性,而且各党派可以团结一致,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之,也因为边区工作的成就与进步,“三三制”民主政权作为抗日救国的大熔炉得到了快速发展。
四、“三三制”政权中协商民主的价值意蕴
“三三制”协商民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后走上了正轨,这种新型民主制度不仅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时民主政治建设承载着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也不无裨益。
首先,从战时角度讲,“三三制”协商民主将各阶级、各党派团结在一起,使根据地内矛盾有所缓和,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对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势如破竹的侵略态势使得中共看到要想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仅仅倚靠一党一派是很难办到的,必须要凝聚其他阶级和党派同仇敌忾,这样才能增强我们抗战的信心和力量,这种想法应用于实践就催生了能够调动其他各方面积极因素、联合抗日的协商民主制度。在抗日民主政权的人员组成问题上,毛泽东又强调:“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1]648。中共包容的胸襟使得政权之门向一切拥护抗日和民主的进步人士敞开,这在最大程度上迎合了党外人士对民主的诉求,也适应了抗日的需要。不仅如此,依照“三三制”原则所建立起来的政权机关从抗日大局出发,制定了施政纲领和具体政策,这极大地缓和了根据地内紧张的阶级矛盾,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抗日积极性。如毛泽东就将协商民主原则确定为“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4]809,周恩来也表示“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17]是“三三制”民主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同时,中共在政治方面还保证地主、资本家和农民、工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与贯彻,将各阶级、各党派团结到一起,使得部分党外人士转为拥护政府和拥护抗日,这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以及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次,从战后角度讲,“三三制”协商民主作为中共在战时构建的新型民主模式,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的创立提供历史渊源,进而奠定了新中国政治基础。“三三制”政权是具统战属性和民主属性为一体的新型政权模式,而协商民主又是该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这种建立在统战基础上的各革命阶级联盟的民主制度为新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18]。抗日战争的硝烟散去不久,中共便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希望实现和平建国的目的,而国民党表面上与中共展开谈判,背地里却积极扩军备战,最终国民党撕毁协定,重开内战。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解散政协,甚至对民主党派进行无情的打压,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其解散。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使得民主人士对此政权大失所望,与此同时,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友好态度使他们将自己的立场逐渐转向中共一边。与国民党不同,中共一方面向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讲述自己的建国构想,并认真与他们沟通,倾听他们的意见;另一方面以极大的诚意和耐心,积极扩大与民主党派的共识面,并对他们“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提出批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表达了筹建新中国的愿景,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作为对此口号的回应,表明了各民主党派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在这样的默契与互动中,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京盛大开幕。会议规定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宗旨、地位和作用,正式确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依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对做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在政府中也安排了职务,作为中共局部执政的第三种力量,在此时也成了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骨干,他们将为新政权的巩固与重建立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至此,我国创造了通过协商民主组织人民政权,成立人民政府的先河,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治基础[19]。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共同纲领》临时宪法作用的消失,人民政协的命运也备受关注。毛泽东指出:“我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20]在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不但保留下来,而且还得到丰富和发展,协商民主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沿着健康的轨道继续前行。
最后,“三三制”政权模式所传达的“民主”“协商”“平等”等理念具有极大的普世价值,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经验与启示。“三三制”民主协商实践可以说是对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的有益尝试与探索,它蕴含的诸多理念对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不无启示,或者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本思想都可以从“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实践中得以窥见。“三三制”政权的本质在于民主,透过其选举制度可以看到这一政权模式的参与主体之广,意图将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从而让人民切实感受到真正的民主在边区,这种“民主”理念与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所要求的“牢牢把握住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21]相一致。又如“三三制”政权提倡协商合作,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抗日问题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他们互相交换意见,讨论协商,在促进抗日根据地民主建设的同时又推进抗战胜利的进程,这其中的“协商”思想与如今人民政协“协商议政、献计出力”的基本方式相契合。再如“三三制”政权坚持平等原则,政权始终奉行党派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这种“平等”理念也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一以贯之的原则。“民主”“协商”“平等”这些理念共同熔铸成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之下团结奋斗的人民政协史。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崭新方位上,我国的协商民主实践不断开辟新境界。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22]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强化委员责任担当”[23]。党和国家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提出这些新要求,使协商民主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贡献更大的制度优势。
五、结语
协商民主寻求的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民主关系,是一种以承认差异性和多元性为前提,以理性与信任为基础,以对话和协商为方式,以容纳和兼容为原则,以利益协调和社会共识为目标的民主形态[24]。这种民主形态发端于中共为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而建立的“三三制”政权中,陕甘宁边区因此成为驰誉中外的民主摇篮,毛泽东更把它称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协商民主经历过一段曲折后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脱胎于此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迎来新突破。回顾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建设实践,不仅能从历史维度中探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源,而且能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