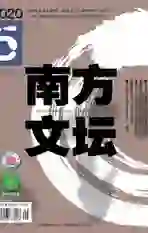时尚、生计与上海女人心
2020-12-24徐炯徐德明
徐炯 徐德明
王安忆为写上海女人而造一座都市,像雨果为冉阿让造一个他的巴黎一样,为王琦瑶造了摩登上海。这上海女人一眼瞄着时尚,另一只眼盯着生计,有一颗摆荡于摩登时尚与生计日常间的上海心。
一、“时尚”与“时间”
《长恨歌》里的上海摩登参差显晦四十年,1946年王琦瑶选美获封“三小姐”,1980年代中她现身各种“派推”、舞会,仍是怀旧氛围中的老摩登。风光过的女人们沾滞于某个高光时间,耽溺那个光晕氛围,时时想回到那个时间点。
(一)海上繁花,上海繁华
王琦瑶的前世,是清末民初吴语小说中“夷场浪”(洋场上)的生活,大量以“海上”命名的小说、游览指南表述了海上繁华的现象①。那海上繁华便是《长恨歌》的时尚生活前奏,映照着1946年的上海王琦瑶,构成半个世纪里的时尚文化的更替循环。韩邦庆《海上花列传》表现海上红倌人沈小红、黄翠凤,上海的近代繁华离不开周身印记着时尚而走红的海上繁花。红倌人在1920年代的《歇浦潮》中,又作兴与政经名流住“小房子”过“人家人”日子,那是王琦瑶与李主任入住的交际花公寓“爱丽丝”的前身。与之区别,王琦瑶是接受现代教育的女学生。她这一辈子烙印多样记号:上海的市井留给她们苏州与宁波的底色,五四年代开启了另一种人生价值,后半生也没有完成社会观念的改造。她的1940年代同代人,秦淮河班子上唱红了的蓝田玉(白先勇《游园惊梦》),嫁给舍不下她的昆腔从上海赶过去迎娶的钱将军,守着猫儿眼、祖母绿在台湾体会繁华消歇、政经流转。王琦瑶也守着李主任留下的装着金条的西班牙雕花的桃花心木盒,带着时尚的流风余韵撑持生计。
王安忆《长恨歌》继续的是自己的主题。此前的《海上繁花梦》采用象征手法,以五个故事写上海繁荣面面观,故事三“玻璃丝袜”是时尚符号。赵钱孙李诸色人等对玻璃丝袜有兴趣,唯老孙通过脚着丝袜、高跟鞋的小李太太而“识得女人了”。小李太太面对打劫的山寨主从容谈论“时下流行的旗袍的款式,并详细解释了那发展的历史,说了旗袍又说大衣、西装、西裤、皮鞋,大王聚神静听,似乎对都市文明有着神往”。其实神往这历史而一往情深的是王安忆,《长恨歌》《天香》《考工记》就是这个情感与认知逻辑。王琦瑶身披繁华,映照都市上海与曲折人生。四分之一世纪后再论《长恨歌》的上海女人,试图回答,这小说的特质可以/何以成为经典?
(二)“们”与“俏”
王安忆这部小说处置了“数”的问题。时尚的基本原理是复数,它必须由多数人群造势而成。时尚由人体现,焦点在女人,聚焦于偶像级别的俏女人,从焦点一圈圈放大出去是不计其数的追随者。她们成了群,以一个上海实有人物比照,那是苏青样的一群人②。王琦瑶选美荣膺“三小姐”,“三”是个“生万物”的数字,是那时尚裹挟着的心同此理的复数人等。所以,在第一部篇首《王琦瑶》一节里,不同情境中或有“一个王琦瑶”、有“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时或是看电影的“一群王琦瑶”。她们是“追随潮流的,不落后也不超前,是成群结队的摩登”。第二部里则有了在弄堂谋生的“形形色色的王琦瑶”。第三部,80年代的时尚轮到王琦瑶女儿一代“薇薇和她的朋友们”与妈妈抗衡。无奈与世界时尚隔绝太久,1980年代的妈妈王琦瑶,已经由复数蜕变为单数了,年轻时的朋友离她远去,活着的吴佩珍早已去了香港,蒋丽莉、程先生则赴黄泉而隔世。
王琦瑶的名字从《长恨歌》中走出来,一时流传耽于时尚的大众和爱好文学的小众口头。当我们带点吴语口音说起这个名字,不由地将“王”姓的韵母发得响亮,而“琦瑶”则轻易滑向了声韵反切,二字快速连读成qi-ao,好像她就该叫作“王‘俏”。不能说王安忆居心寓意,但我们不妨记住:这上海女人,姓王,名俏,字琦瑶。
(三)“箱底”映现“走样”
王安忆写上海女人的私人生活,不仅表述情爱的务虚,更有维持生计的务实。她从民间婚嫁习俗中提炼出一个关键词:“箱底”。这个词包含的不仅是女子陪嫁“压箱底”的细软财物,而且印记过去生命,寄托当下、未来的生计,甚至有生命美学价值。《富萍》中曾表述“奶奶”的箱底事关女人的生存与家族发展,小说让这个从苏北来上海帮工的女人攒下了不薄的箱底,既聚钱为自己防老也给宗族传人孙子娶亲。而王琦瑶的箱底则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装着金条的西班牙雕花的桃花心木盒,放在五斗櫥里锁着,甚至没有在女儿薇薇面前打开过;一是江南梅雨天过去,入伏后家家户户打开箱子晒霉的贮存,王琦瑶的服饰晾在竹竿上,既往的时尚成就再一次展览给自己看呢,那是她傲人的资本与尘封的记忆,时尚彰显与悖晦在这里波澜起伏,一同奔涌而至的是光彩耀目与时光一去不复返。
王琦瑶的箱底可派日常与非常用场:一半可以自己随时改动、不即不离地调整衣着装扮,也适用作女儿薇薇的时尚对照;另一半则是解困,入了旧货行,换来口中食。那些衣服皮鞋并不是为给女儿穿着,却好像要立此存照,映现出80年代新一波时尚的“走样”。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所尚,王琦瑶视1980年代为“走样”当然是捍卫过往风华的价值。选美前的王琦瑶,照片就曾经在杂志上和照相馆橱窗里吸引欣赏与追随者的视线,一路至今而自信风流不减,但无限风光暌隔已久。从50年代到80年代,王琦瑶、严师母侪辈依然故我地一路在服饰发型上暗暗用过劲,同时享用了巴西咖啡、西餐牛排与苏联面包。视王琦瑶为旧时代“箱底”的蒋丽丽是另一派,不说她嫁了个革命军人与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列宁装的新时尚就让王琦瑶看着别扭。旗袍与列宁装掺和,加上有限模仿时下放映的外国电影的角色服装,薇薇一代人的时尚不是文化自信的风华。王琦瑶看薇薇把刘海卷得像个服侍人的“小大姐”(妓院女佣),她的鄙夷不屑何止于“走样”的判断。所以,薇薇那一群里最有时尚感觉的朋友张永红臣服于王琦瑶,妈妈也附带征服了走样的女儿。王琦瑶三十多年间与文化世界里的时尚隔绝,但她领略过当年洋场文化世界里的服饰风华,这就是王琦瑶曾经拥有过的品质,弄堂生活世界里的有限存留,张永红钦羡的“真时髦”。
作为上海时尚符号的王琦瑶,其结局是最大的“走样”!
二、上海的“芯”中“心”
《长恨歌》分三部写,大视野而小生活,与史诗品格及“三部曲”无缘。王安忆在大都市文化世界格局中写生活世界“茶杯里的风波”,目标瞩目上海女人生活的“芯子”,于中处处可以扪及人心,这个取向的中国小说前所未有,比张爱玲多点“芯子”里的暖,较苏青的“结实”有诗的虚无。
(一)“鸟瞰”生活“芯子”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广角视野里的都市上海大世界与弄堂“小生活”芯子,看似一对矛盾,其实的撷取手段基于一致的摄影原理。设想在百老汇大厦天台设置摄影机,先取鸟瞰的广角获取大视野,而后把镜头推上去,这视点便聚焦于一片街坊、一条弄堂、一个公寓房间、一个女学生及后来半辈子场景③。这种切近上海现代都市品格的观察方式,如小说中女学生王琦瑶摄影棚内试镜头,美女在“三面墙的房间”布景中蒙着盖头充新娘,隐秘的也公开。王安忆设想上海是一间大摄影棚,每一户是三面墙的房间,“卸去一面墙的房屋,所有的房间都裸着,……成了一行行的空格子。……想象那格子里曾经有过怎样沸腾的情景,有着生与死那样的大事情发生。”焦点从爱丽丝公寓移到王琦瑶平安里的房间(“那开始朽烂的砖木格子里”),仿佛默片一样:等待李主任,与严师母、康明逊、萨沙的牌局,又接上与这两个男人的暧昧,再后来程先生服侍王琦瑶的月子,女儿薇薇长成……
小说当然不是默片,写上海女人须擅长于无声处“听壁脚”,觅得些隐私的声音。不像那飞在半空、屋脊上的鸽子,地老天荒的,见惯不惊,听见听不见都没有反应。小说是有情表述:那私情的,彼此拨动心弦;这生计的,透出过日子精明。听得那康明逊与王琦瑶两个人反高潮的前戏:“王琦瑶说:我也有求你的,我求的是你的心。康明逊垂头道:我怕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王琦瑶不由冷笑一声道:你放心!”情切切而意悬悬的紧张,并不能阻住接下来的百般缱绻。再听听中产阶级的严师母的生计讲用:“要说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的。……吃是做人的里子……不像面子那样,支撑起全局,作宣言一般,让人信服和器重的,当然,里子有它实惠的一面,是做人做给自己看。”这“芯子”的宣导,内核也就是市井生活哲学“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严师母中产阶级风格让她较一般下层更务虚,“假如完全不为别人看的做人,又有多少味道呢?”她否定下层人糊口唯“吃”是尚,做人“为别人看”的尊严必须把“吃”与“穿”先后掉个位置。她实惠的衣食哲学是弄堂经济基础里的上层建筑,高度认同上海女人务实的生计观。严师母也代表着王琦瑶,生活“芯子”保留了一大截“心”的取向,那是她們“做女人的端底”。
平安里的市井倾向的表述是“众生话语”,专门在生活的芯子里用力,不管它是个多大的社会政治的外壳。过日子的实惠,才是上海人做人的芯子。王琦瑶选美进入爱丽丝公寓与被谋杀之间,有三十多年大段的日常生活,这里面的人生“芯子”是小世界里的小目标,是螺蛳壳里的道场,专属上海女人。从邬桥回来平安里的日子,李主任好像没有存在过一样寂灭无声。“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隙里,互相都被遗忘,倒也安全。”遇上康明逊,即使怀了他的孩子,这个负不起责任来的男人也只能噤声。那个找来装幌子的萨沙,迅速匿迹销声。唯有那个木头般的程先生遥遥地有了回声,让静声啜泣的王琦瑶在产前与月子里有了依赖。爱的浪漫让位于生计的实惠,活着是第一位的,1960年的“吃”上升为生活全部。过这样的小日子也要经得起折腾,小资的男人都化作了虚无,王琦瑶带女儿过日子,“生活在世道的芯子里,凭的是感性的触角。说是自私也可以,总之是重视个人的经验超过理性的思索”。“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④不尽然的是,苏青式的物质生活“芯子”的世俗之外,王琦瑶还有好好做人的“心”之向往。
(二)勾心、斗角听“静声”
中国小说的人物精神情感关系,并不趋向供奉的神祇,而是彼此拨动着心弦,如贾宝玉对林黛玉情急示爱,只说“我的心”。表述彼此勾动心弦,好像抚琴的指法,这是“勾心”的笔法。小说的情/琴韵的美学往往在于乱弹琴/谈情,悲喜剧于焉而生。王琦瑶、程先生、蒋丽莉之间,不是勾错了弦,就是按错了徽位,奏不出知音的《流水》。小说第二部“阿二的心”一节,王琦瑶勾动起阿二的都市向往,阿二撩动了王琦瑶回上海的愿望。
“斗角”原理出在建筑与家具工艺,不是“斗争”,不该完全指向彼此间明争暗夺,各自作为一部分组成矛盾统一体是更重要的内容。中国传统家具八仙桌的桌面,是由四根框料嵌入膛板,四根边框的接榫处皆以四十五度角斗合,严丝合缝;如果做一个三角形的框架,就应该是六十度斗角;六角、八角亭的斗角更其复杂。中国小说是人际关系的文学,“斗角”是人际组合的基本笔法。《长恨歌》的同学、母女、情人、街坊,无不是这“斗角”的组合,彼此依存是一种关系,矛盾长存是她们的状态。
“静声”是《长恨歌》的一个发明,它的价值在与现代文学的对话中才能彰显。中国现代小说的镗鞳大声是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与《摩罗诗力说》中“精神界战士”的“心声”,它是知识分子反抗绝望的承担与抱负;嘈杂热烈的发自市民大众的喧嚣声,张爱玲概括为“市声”,她的朋友苏青身在其中,张爱玲则把自己“包括在外”⑤,于虚无中识得此声真面目;王安忆阐释“静声”是人物嗡嘤啜泣的“渺小的伟大”,“终其人一生”,“以其数量而铸成体积,它们聚集在这城市上空,形成一种称之为‘静声的声音”。因为它是来自众生,汇成一派从静寂中涌出的大声,所以王安忆说“‘静声其实是最大的声音,它是万声之首”。这静声诉说人道、立足民本,终归还是一种“众生话语”。鲁迅的“心声”,张爱玲的“市声”,王安忆的“静声”,声音的并存、冲突、掩映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结构性关系,须无偏颇地聆听而声声入耳。
如果按勾心、斗角的美学倾听《长恨歌》的静声,倾听王琦瑶在平安里躺在床上看月光映上窗帘花影的悄然心动,和王琦瑶一起倾听忙完晚餐收拾停当后程先生离去,身后司伯灵锁的“咔嗒”声撞上心来。如果这一声声“静声”的泛音深入读者之心,就不宜作《长恨歌》问世以来时见的通俗情节解读:风风光光选美的“上海小姐”死于暴力谋杀。小说题目分明提示那个焦点字眼“恨”,偏旁“心”才是作家致力的对象,心之与时俱变,随着风光与失落的情势而心潮起伏,嗡嘤啜泣。作者将心比心地贴着人物写,表述人物之间的知心悉心与勾心、斗角,由是见出上海人心的曲折变化。
汪曾祺屡次讲到老师沈从文:“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⑥唯有贴着心写才产生有真味的人情世故,王安忆善于贴着上海女人写,贴着写才能打捞人心的“静声”。《长恨歌》“‘沪上淑媛这名字是贴着王琦瑶起的”,贴心而散发最强“静声”者,是那勾心、斗角的王琦瑶、蒋丽莉和程先生三者关系。这三人在一起,无处不写心。那第一部第二章,选美过程从“沪上淑媛”而参选“上海小姐”到底定“三小姐”,这三节哪一页不写到“心”字,多到十次左右,至少也有三五处,描摹诉述各色各态的心,心往一处使、心心相印转而心生别念,女儿心在一个时尚向度上就如此丰富。王琦瑶选美,心之波动欲盖弥彰,程先生满心是王琦瑶,蒋丽莉帮助王琦瑶是闺蜜之情,其实真心在程先生身上。要说女人之间的情谊,王琦瑶与同学吴佩珍、街坊邻居严家师母、女儿薇薇乃至其同学张永红,越是勾心,越是斗角离不开。
小说第二部有一段“合掌文章”的“哭”,三个人分两个场面流泪,一个在小酒馆饮泣,两个在蒋丽莉的卧床前抱头痛哭。各自哭的是自己,也是哭另外那两个。三人历经世事变化而重聚,不久蒋丽莉罹肝癌病笃。一生抱憾的蒋丽莉的痛苦拜这二人无端之赐,病榻上的她,前首拒见程先生,后脚与王琦瑶抱头痛哭。程先生黄酒就百叶丝喝到天色暗下来伏在桌子上不起,伴以无声不断的泪。蒋丽莉检视自己活页夹上十多年来对程先生的情诗,先是纵笑,笑诗中的自己,接下来哭自己一生“太倒霉”,触动王琦瑶“更倒霉”的感慨,一同大哭。她们/他们彼此勾动了心弦,回味多年情感纠葛凑斗成的那一角生活,不了自了成虚无。
三、历史的恨憾
王琦瑶作了四十年的繁华梦,没有婚姻并不妨碍她做人,无奈她在做人的起点就踏入繁华而不能抽身,摩登上海给女人划定了一条辙,她就是运行在这都市里的“有轨电车”,行驶在时尚拷贝的现代轨辙中。
(一)无言流水,有轨电车,火烛小心
先从邬桥说起。邬桥在哪里?小说第二部描述的是一个江南水乡市镇,处于苏州、昆山那一方之中,读者经验里的某类地方就是了,它是虚构的。作者在构虚,劈头就说:“邬桥这种地方,是专门供作避乱的。”邬桥是种属概念的一类,仍然是复数,它本非不仕者隐居之地,是老幼男女渔樵耕读的聚居地,桥梁一顶顶,店肆一家家,屋舍俨然,可避秦时乱,也可规避改朝换代。“邬桥这类地方,全是水做成的缘”,镇市与外界的联系,是地老天荒的河流水道,河上的船老大“看不出年纪,是时间的化石”。这水任意沟通太湖、苏州、松江,主流沿吴淞江接黄浦江入海,分岔入方浜、肇嘉浜流进上海县,那一顶顶桥与方浜上的陆家石桥无大差。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开头从陆家石桥上一跤跌下来的赵朴斋,第二日一早就去挨门窥视长三堂子,开了海上时尚之眼。如此转折一想,邬桥竟是过往的上海县,或叫作华亭,徐光启在明朝就称作“海上”⑦。王安忆多年之后接着写这里的繁华,上海县《天香》园女人们的旷世工艺与生计,《考工记》大宅子里过本分日脚的上海男人。王琦瑶到邬桥的空间转渡其实是时间转换。
如果读第二遍《长恨歌》,可将第一、第二部的开场对读,开头都没有人物语言,是无言独白。不像小说,那是散文的文体,一种谈话的文体,有英文絮语体散文风味,却又不离小说街谈巷议的意蕴。用独白来表达时空蕴含,去“布”景、安排宽阔深厚又不避虚无的生命哲学的环境,安排王琦瑶的离去与归来,变化就是对时尚的镜头推拉。第二部的时序承接第一部,但是邬桥之“老”远早于全篇开头王琦瑶的女学生时代。王琦瑶进入邬桥,那是外婆梦回的前现代,现代上海主宰王琦瑶的生命过程与命运,上海的现代化是她的轨道,摩登的动力驱驰王琦瑶这部有轨电车。
《长恨歌》的写实方法必然及物,写既实有却又虚无之物,首推那有轨电车的“当当”响声。小说总是有意无意地插入有轨电车声,如金圣叹所谓“草蛇灰线”⑧,不经意又故意地布置成文章线索与肌理,这分明是王安忆在表态。这当当声总是在虚幻中提示真实,又在真实里透露虚无,它与不同时段、不同身心处境中的王琦瑶们结合,呈现强大的能指功能。第一次始于去看拍电影,王琦瑶和吴佩珍从片厂回家,在车上“懒得说话,听那电车的当当声”,她不自觉地用这声音去抵御电影摄制的虚幻感,其实声音与影像的虚幻只是程度不同。这虚幻与虚无一而再再而三地情景化:一个情景,选举上海小姐的消息传播着,“电车当当地,也在发新闻。这是何等的艳情啊!是夢中景色,如今却要成真。”再一个情景,程先生在咖啡馆等王琦瑶,“电车当当地响过去,是安宁白昼的音乐,……王琦瑶走过来时,是最美的图画了,光穿透了她,她好像要在空气里溶解似的,叫人全身心地想去挽留。”情景三,“那电车的当当声都像是遥远的地方传来,漠不相关的;王琦瑶等着李主任,知道了什么是聚,什么是散,以及聚散的无常。”情景四,王琦瑶百无聊赖去看夜里的第四场电影回来,“候车的人满脸都是夜色,电车进场当当地敲着夜声……”还有康明逊自问:“她(王琦瑶)到底是谁呢?这城市似乎只有一点昔日的情怀了,那就是有轨电车的当当声。”在第二部中这旋律始终在,蒋丽莉和程先生乘电车,“听着电车当当地响。这好像是那千变万化中的一个不改其宗,凌驾于时空之上的声音。”第三部“薇薇眼睛里的上海,在王琦瑶看来,已经是走了样的。那有轨电车其实是这城市的心声,如今却没了。今天,在一片嗡然市声之中,再听不见那个领首的当当声。”王琦瑶的生命动力犹存,她快要不择地而行,如那无轨道的车了。随年轻人去舞会,王琦瑶真不知今夕何夕了,她船行过前现代的水上,心思也曾融入那摩登动力的有轨电车的当当声中,而今再到爱丽丝,耳畔却只有无轨电车声了。
遥远的世代留下一个幽微的警世声音,直到第三部第四章王琦瑶“祸起萧墙”走完“碧落黄泉”之路。小说在此重申“平安里祈求的就是平安,从那每晚的‘火烛小心的铃声便可听出。”摇铃值宿的声音是改良进化了的打更,前现代的更锣换成了外国铃铛,摇铃人丢弃了更夫那音韵绵长而息事宁人的“平安无事”,只留下警告的嘱咐“小心火烛”。平安无事意谓既无小偷也无强盗,然而王琦瑶叫出了“强盗”,骂了“瘪三”,这是她最后的声音。强盗是衙门都头捕快捉拿的对象,瘪三是洋场租界上无业者的贱称,都出自于1986年王琦瑶之口。她的语汇从前现代,到摩登时尚年头,再到后摩登时段,小说家让王琦瑶的语言活得比57岁长,活出了上海城的年龄。
(二)男女,世故
《长恨歌》的时尚与生计融化出上海女人的个人空间,也诉说世道人心。写上海女人,不能没有男人,讨论男人才是完整的作品论,值得说说程先生。他与王琦瑶没有肌肤亲切,却一直是王琦瑶信赖之人,乃至可以托孤。他以耽美的态度在人世走了一遭,其财富是镜头下收获了无数美的影像,弱水三千,他唯一属意王琦瑶。他独身不是缺少感情,而是太专一,一根筋认定王琦瑶,他理解男女绑定在了审美的向度上。他欣赏王琦瑶之美,入迷而全心全意参与选美,他耽于崇尚王琦瑶的美并享受这种感受,也会不出声地哭,痛苦地把自己喝醉,他的爱心散发“静声”。王琦瑶理解他的爱是一种恩义,她与他,没有对等。自打帮王琦瑶拍照、助她选美,他恋一个、被一个恋着,几乎用完了一生余下的二十年时间。他不是情痴,而用足够的理性压抑住感情,甚至从来没有表现出激情,很冤地被王琦瑶认作“呆木头似的”,待到她深陷生活困境时方才悟出他“解人至深”。另一个女人蒋丽莉不够美,她孤注一掷地把感情整趸地卸在程先生身上,这足以吓退他,但是与蒋丽莉来往可以暗度王琦瑶。他可谓上海小男人,玩不转大格局,就是小小的三角关系也不擅处置。他会呵护女人,待在怀了别人孩子的王琦瑶身边忙一日三餐,服侍她到上床后再回到自己的住处。那顶楼的住处就是摄影工作室,他的摄影爱好大于所学专业,最大的愉悦就是看着相纸上的王琦瑶逐渐显影定影,留住那美的瞬间。就是这种小男人,内心装着大尊严,选择从顶楼的窗口走出、像树叶样坠落,那是捍卫人的自尊。革命运动由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王琦瑶身边不虞缺乏男人,她需要男人的欣赏,再需要一个年长于她的成熟男性呵护,更本能地需要和男人在一起的快乐与快活。程先生是第一个来到王琦瑶身边的男人,也是最后一个真爱她的,他无与伦比地拥有前二项,却缺乏表现后项。起初王琦瑶享受他通过镜头的欣赏,她无思虑地享受程先生的呵护,表达出一些自私,这是上海女人在摩登时代赋得的秉性。临产、分娩、坐月子的王琦瑶尽享程先生的呵护,那不是彼此产生冲动的语境,程先生每晚关上身后门的锁声落在内外两人的心上,心更近了,欲望快活远了。王琦瑶没有婚姻,也亲近过几个男人。她不一定需要婚姻,情感生活却总是有差错,时尚文化是酿错的一部分。她最大的错失是程先生,稍一错便过了,死的死了而活的活着,继续往前走,活着的也死了,是个错死。写《长恨歌》的上海必然世故,世故得虚无,世故得给人物设定小目标、过小日子。
上海女人王琦瑶不可重复,《天香》的三代女人小绸、希昭、蕙兰另有一番模样;程先生没有写完,《考工记》里的陈书玉重打锣鼓另开张,他也没有婚姻,连学铁道专业都和程先生一样,他不敢爱女人,而爱上一座祖宅,与这宅子厮守到最后。王琦瑶的四十年是上海女人的私人历史,《长恨歌》《天香》《考工记》这三本书是王安忆上海的生活世界“小历史”。小历史中不表述人所周知的大事件、人物不显山露水,既不如英雄好汉、达官贵人等大人物头面风光,也不是与之对比的小人物的晦暗,如19世纪俄罗斯文學那样。她/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价值,轻易不放弃,社会天翻地覆了,人物却延续些前朝方式习惯,这些人的那点世故是面对世界依然故我,她/他们如前朝人物活在后代,他/她们时时怀旧,也是怀旧的对象。海上小历史的重心在上海女人身上,她们登台唱戏,男人倒成了帮腔。尽管她们有时只是时尚化地热闹一番,有时耽于衣食生计,没有任何使命感,男人们却也乐意陪衬,全心全意的男人要数程先生。
王安忆精读了上海,她为上海城造了个上海女人,王琦瑶。
【注释】
①王安忆把握上海从19世纪开埠起到世纪末的繁华,《考工记》主人公陈书玉家族史就是这一段。对此一时段文学与文化较充分的讨论是《海上倾城:上海文学与文化的转异,一八四八/一九〇八》(吕文翠,麦田出版社,2009,第19-20页)。
②王安忆:《寻找上海·我看苏青》,学林出版社,2001,第197页。
③上海高处鸟瞰视野的街坊、弄堂图景,可参看对照王安忆《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第35页插图“淮海坊俯瞰”、第53页插图“后期石库门屋顶俯瞰”。
④王安忆:《寻找上海·我看苏青》,学林出版社,2001,第193-195 页。
⑤张爱玲:《把我包括在外》(Include me out),见“张爱玲典藏12”《惘然记》,皇冠,2010,第123页。
⑥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见《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465页。
⑦吕文翠的“海上”用法最早见于徐光启题《琴鹤高风诗册》,见《易代文心·绪论》,联经出版社,2016,第12页。
⑧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见林乾主编《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第3卷“水浒传”评点,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第23页。
(徐炯,扬州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徐德明,扬州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20年江苏省“双创计划”、2019年扬州市“绿杨金凤计划”资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