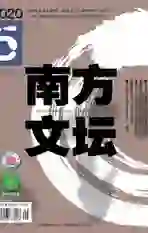不写也可以
2020-12-24康凌
康凌
克罗齐很早以前说,“文学批评”这个词,意思太模糊,好像一大堆各不相同的活动,仅仅因为它们都和文学搭点边,所以就都归到一起来了。
我对文学批评的看法跟克罗齐先生差不多,那就是说,我也不太知道文学批评到底是什么。以批评的名义,我们可以寫个人的读后感,也可以写单纯的书评,可以做高头讲章的文学史论文,也可以搞搞文化研究,兴致来了,甚至可以借题发挥,做点社会批判什么的。但说到底,这些事情是不是一定要在“文学批评”的范畴里来做,好像也不一定。文学批评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正是因为这样,涉及“批评观”的问题就有点麻烦——凡事要涉及什么什么“观”的时候,都会有点麻烦。因为它不仅是在问这件事是什么,还要问这件事“应该”是什么了。而批评应该是什么,我就不太答得上来。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里写“批评”这个词条,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批评已经变成了一个难解的词”。他的意思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批评”总是跟“权威论断”(authoritative judgment)搞在一起。这样一来,“批评”就常常变得假模假式起来:明明只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反应”,却要把自己打扮成抽象、普遍的“论断”,啧啧。
在假模假式方面,我有些经验,但大都和写论文有关系,如果要我谈谈论文观,我大概可以故作摇曳一下子,至于批评方面,可就摇不起来了,这主要是因为我的批评文章实在太少,大山临盆,生个耗子,很不像话。总得先有好的批评,再谈批评观,不然别人就会说你是个骗子,这比假模假式还要糟糕。
在没有批评观这件事上,我还可以说出一个理由。那是从方岩先生那里抄过来的。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专门去学习了《南方文坛》之前登出的批评观,因此读到了方岩先生的文章,他说,“是否要用某种单一、逼仄的写作格局、形式和某种外在于写作的评价机制,去衡量辽阔而复杂的写作,确实成为我的日常焦虑之一”。我没有方岩先生这样的日常焦虑,但完全同意他提出的设问。好的文学批评各有各的好,怎么去“观”它们,是后来的事,也是不大要紧的事。方岩先生还说,我们无须 “喋喋不休地解释”自己的写作,因为“一个人的写与不写对这个世界来说,从来就没有重要过”。
这句话如此准确,我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我看自己写的所谓批评,也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文章或许可以不写。但写了也就写了。声称坚持和声称放弃,都很矫情,声称别人矫情,也很矫情。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作为一个写得很少的作者,我只能老实承认自己没有什么批评观,如果容许我耍个滑头,那也可以这么说,我觉得我的批评观可以是这样:写一些有意思的文章——读后感、书评、文学史论文、文化研究、社会批判——然后管它们叫批评,写不出的时候,不写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