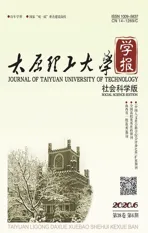“修齐治平”家国叙事的重构逻辑:基于《颜氏家训》的解读
2020-12-20辛昌泽夏当英
辛昌泽,夏当英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颜氏家训》是中国家庭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历来受到学者文人的广泛赞誉和关注,陈振孙即称其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学界关于《颜氏家训》的研究亦成果斐然。具体而言,研究者们一方面聚焦于家训文本的分析,在字词训诂[1-2]、语言音韵[3]、儿童教育[4-6]和家风建设[7-8]等方面进行了翔实的讨论;另一方面则将《颜氏家训》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分析魏晋时期的社会特征,如社会风俗[9-10]、士人心态[11-12]和宗教思想[13-14]等时代内容,但少有家国关系视野下的相关论述。基于魏晋时期的社会动荡背景,士族家国观念必然发生变化,本文正是以家国关系为切入点,探析士族家国意识的变化如何形塑其家庭建构逻辑。“家国叙事”模式肇始于传统社会的家国一体格局,其实质在于“以家喻国”,个体、家庭与国家(王朝)的行动路向具有一致性。在不同历史阶段,家国实践体现为或“殉主弃亲”或“安家忘国”的多元行动选择,并非是“修齐治平”的理想化线性递进方式。这种动态家国叙事投射出士族的家族诉求、忠君意涵和家国观念的变化。自西晋“八王之乱”以来,“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15],儒家伦理相对衰落,胡汉文化冲突与南北地域矛盾也日益尖锐。家庭作为个体在乱世中的安身立命之所,其本体性意义尤为突显。故而,建构一种合乎家族实践逻辑的行为规制,以及调适“修齐”与“治平”、扬名显亲与保身安命的关系,成为魏晋士族所关注的现实问题。颜之推是士族的典型代表,他一生颠沛流离,历经梁、西魏、北齐、西周、隋五朝兴衰,多次幸免于杀身灭门之祸。命途多舛、南北奔亡的遭际使其形成了对政治变迁、家国关系和南北文化的独特创解,并以此写成《颜氏家训》。具体而言,颜之推视野中的家国叙事一方面以儒家“修齐治平”为实践主线展开,另一方面则出现“家”重于“国”的家国地位倒置现象,并影响了士族家庭的制度安排与行动逻辑。
一、“修身”与“齐家”:保障家庭稳定的策略
魏晋时期,以儒传家是士族普遍采取的家庭管理策略,即依据“修齐治平”为实践主轴,并辅之儒家伦理教化,以实现个体扬名与家族振兴的统一,也促成了家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如颜之推暮年的最大心愿即在于光耀门楣[16],并写作《颜氏家训》来提领子孙实现“修齐治平”的治家理念。家训作为儒家义理落地化的日常行为规范,不同于维护官僚统治的庙堂“显学”,而是基于“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现实建构。魏晋时期,儒学相对衰落与士族门阀兴起,使得践行儒家规制的价值意义被压制,其功利化特质更为明显。故而,儒学价值取向与世俗要求趋于一致并不断融会,也赋予了修身实践以道德合理性,修身与齐家的世俗指向由此趋同。家国叙事呈现出“修齐”的功利性因素增强,并以家族兴旺为最终归宿,国家与天下层面的济世意识淡化。
(一)修身:以伦理规范指导个体行动
“修身”是儒家“修齐治平”理想人格实践的基础与扬名显亲的前提条件。前者阐明了“修身”价值目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进而内成其圣;而后者则表明其工具目的在于“立身扬名”,以显门楣。颜之推主要围绕学习教化与言行规范两方面展开,并带有明显的工具性与保身倾向。
1.勤勉治学是修身的必要条件
颜之推非常重视学习教化的必要性,在《颜氏家训·勉学》中(下引《颜氏家训》只注篇名)举例道:“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俗乎”[17]。相反地,他对世家弟子依靠祖荫而不学无术的风气予以批判,痛感其“长受一生愧辱”,当时移势迁,“求诸身而无所得”时,终至“转死沟壑”的下场。在《勉学》中颜之推进一步指明学习的最佳途径为“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颜门在魏晋时期并非望族,难以同高门弟子“平流进取”,勤学读书便成为致仕齐家的唯一途径,如“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勉学》)。除研习上述儒学典籍外,颜之推也强调学习技艺的现实价值,认为“人生在世,会当有业”,例如“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等论述都鼓励后人应习一技之长以触地而安,与传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唯学论不同,他反对士大夫皆“耻涉农商”的刻板偏见,强调修身教化的立足点首先在于“得以自资”,在此基础上,进而“倍须训诱,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勉学》)。可以看出,颜之推将修身方式的外延扩展到所有利于保身的情境,读书不再致力于明理而旨在入仕显家,传统修身的“明德”目的已然弱化。
2.遵守“仁礼”的社会规范
以儒传家是颜氏家风的典型特色[8],儒学伦理也成为规范颜门子弟行为的道德准则。“礼”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所谓“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颜之推也强调“礼为教本”,“礼,身之干也”(《勉学》)。人们唯有遵从“礼”的规范,才能避免因触犯刑律而招致杀身灭族之祸。“礼”在维系家庭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与兄长交谈必须“先着衣帽”;在称呼上则要懂得尊礼避讳,以体现“尊卑之差”;适逢丧葬时期,宾主吊唁的时间、服饰和礼节要求都有着细致的规定等。
“礼”作为“仁”的外在形式,其修身规范深刻体现了“仁”的价值内涵。在颜之推看来,“仁”的践行方式表现为内在修养和社会行动两个层次指向,一方面主张遵从以孝悌为核心的道德伦理约束。孔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相应地,颜之推也将“孝”作为修身之本:“诚孝在心,仁惠为本”,“孝为百行之首”(《勉学》)。他认为“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时益物”(《归心》),亦即儒家所言“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另一方面颜之推也非常重视“仁”的行为导向作用:“为善则预,为恶则去,不欲党人非义之事也。凡损于物,皆无与焉”,“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省事》),呼应了孟子“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思想。除此之外,最高层次的“仁”体现为:“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抿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养生》),从而将“仁义”的价值置于个体生命之上,正是“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真实关照。如张嵊“为贼所害”仍“辞色不挠”,谢夫人“登屋而诟”却“见射而弊”等壮举也被他赞扬。可以发现,“礼”不只是儒家伦理要求,更是约束个体行为,避免家毁人亡的保身策略;而“仁”仅是乡党族人的互助需要。虽然颜之推也提及“杀身成仁”的相关表述,试图兼顾生命与气节、情与礼间的需求,但“仁”与“孝”的济世价值始终隐而不彰,更难以升至国家层面的“忠义”维度。
(二)“齐家”:以亲缘制度管理家族事务
“齐家”作为儒家理想人格实践的第二环节,与“修身”相承接,个体的道德伦理修养主要以家庭秩序建构为导向。亲缘制度指在家族管理中,家族成员以亲缘关系为互动基础,并依据相应规定进行辅助管理的一种非正式化管理方式。具体而言,颜之推非常重视亲缘关系与家族伦理的濡化作用,主张家族成员应各安其分,履行其相应的责任义务,并且对家族的管理原则和具体事宜也予以细致的规定。
1.家庭秩序——人伦为本
家族内部的夫妇、父子和兄弟关系,以及衍生而来的妯娌姊妹、妻妾童仆等家族旁支关系共同筑成了颜氏家族的人伦亲缘网络。颜之推将“三亲”作为家族关系主轴:“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兄弟》)。在《治家》篇首就开宗明义地点明了整合人伦秩序的基本原则是“自上而行于下者也”,即人伦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同族成员基于儒教价值的主体实践与行动自觉。他对如何处理父子、兄弟、夫妻,以及旁系关系皆提供了伦理参照。
“礼”是处理父子关系的核心旨向,“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教子》)。颜之推认为父子相处应恪守礼仪规范,并提出“父子异宫”“抑搔痒痛,悬衾箧枕”等防“狎”祛“简”的具体方法。在夫妻关系中,颜之推并没有超越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伦常规制,认为妇女“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必无牝鸡司晨,以致祸也”(《治家》)。即体现出男权至上的家庭话语。颜之推也强调兄弟团结对家族安定的重要意义,所谓“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兄弟》)。同族兄弟具有共同的家庭记忆与生活习惯,这种先赋性的身份符号明确了他们在困境中应相互扶持的义务。在动荡的魏晋时期,基于血脉联结的亲族互助正是人们得以入世齐家的动力源泉和精神寄托。最后,妥善协调由“三亲”派生而来的旁支关系也对家族人伦建构产生重要影响,如“仆妾之为雀鼠,妻子之为风雨”,“娣姒者,多争之地也”,“妇人之性,率宠子婿而虐儿妇”(《治家》)。这些训文都指出了妯娌子侄、姊妹婆媳等派生关系如若不睦则对家族有危害性。但旁支关系的存在是家族繁衍的现实需要,故而他主张“若能恕己而行,换子而抚,则此患不生矣”即祛除私心,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的仁爱态度善待兄弟子侄。但是,基于伦理义务范畴的濡化自觉并非万能,家族秩序建构也离不开具体的制度实践。
2.宽严适度的家庭制度
家族制度建设是相对于仁爱孝悌等儒家人伦而言的具体家政规范,颜之推分别从治家原则、家族经济、婚丧嫁娶和终制规模等方面予以阐释。治家首先应秉持宽严适中的原则,他通过中书舍人醉酒被杀和房文烈借房被烧为例,告诫子孙治家过严或过宽都会造成丧财破家之痛。在家庭生产方面,他强调参与农业活动的重要性,如“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治家》)。这些论述虽然反映了一种重农务本思想,但这也恰恰是千百年来封建家族得以延续的物质基础,因而具有超越历史维度的价值意义,也是古代“耕读传家”习俗美德的现实参照。涉及婚嫁事宜,他认为应审慎续弦,原因在于“异姓宠则父母被怨,继亲虐则兄弟为仇”(《后娶》)。继母对自家孩童的偏袒往往会引发嫡庶争斗,进而酿成“门户之祸”。此外,他也主张“婚姻素对”,阐述了为攀附权贵而联姻的后果:“或猥婿宰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后娶》)!最后,他提倡节丧薄殓,并叮嘱子孙,待其死后只需“殓以常衣……当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随”,以免“刳竭生资,使冻馁也”。
颜之推在家族人伦秩序与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了事无巨细的规定,如强调长幼间的孝悌礼仪,重视亲族间的仁义互助,但他并非具有移孝作忠的价值自觉,也缺少士志于“仁义而已”(《孟子·尽心上》)的理想追求。“家国同构”格局的显著特色即在于家族伦理和政治道德相统一,故有“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大学》)的论断;而颜之推虽以儒家伦理作为齐家方针,但从未将其上升至国家制度安排,训诫内容始终围绕个体性命与家族兴旺展开,在这方面,修身与齐家的归宿一致。
二、“治国”:实现扬名显亲的必由途径
“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理想人格实践的最终阶段,也是光耀门楣的最有效方式。颜之推一方面鼓励人们在修身过程中通过伦理濡化以协调家族关系,另一方面则经由勤勉学习以入仕治国,保持家道不坠。修身、齐家、治国的归宿都旨在扬名显亲,具有现实层面的一致性。在他看来,“治国”即是指个体在保全生命的前提下,进入官僚系统而巩固家庭政治地位,其不再具有人生意义实现的价值内涵,而是作为“齐家”必要策略,体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家国叙事安排。
(一)入仕目的趋于世俗化
儒家自古有“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仕宦传统,鼓励个体积极入仕,以实现“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与生命意义。颜之推的入仕目的却并不相同,“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顾无常分矣”,“但以门衰……使汝等沈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觍冒人间,不敢附失”(《终制》)。在朝做官仅是乱世中得以保存家族延续的无奈之举,入仕也就具有扬名显亲的世俗化取向,这自然对他的为官原则产生影响。在颜之推看来,仕宦的核心要求即“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基于此,他提出了具体的官阶俸禄规定,如“自今仕宦不可过两千石”,“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止足》)。官阶过低不足以振兴家族,过高则“惧罹谤讟”,唯有官居中品才得以“免耻辱”“无倾危”。官位若超过家规限度,则应“便当罢谢,偃仰似庭”,以免招来祸患。
儒家传统的入仕目标在于济世化民,使天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官阶越高,意味着拥有更大的权力推行“修齐治平”的理想主张,这成为历代儒士为官进取的不竭动力。而颜之推虽然强调“人生在世,会当有业”,但并非向外推展于治国平天下,为官仅是保持家道不坠的途径,也由此缺少谋求高位的行为推力。基于仕宦目的不同,其具体的仕宦方式与儒家传统观念也有所不一。
(二)忠君观念倾向谨慎务实
在儒家传统观念里,进谏是臣子尽忠的表现,所谓“臣所以有谏君之义何?尽忠纳诚也”[18]。而颜之推则对谏诤行为予以强烈反对,认为其旨在“贾诚以求位,鬻言以干禄”,但结果通常却难遂人意,终致“不省之困”“不测之诛”,这表明“忠”的内涵已发生改变,也影响了颜之推的仕宦观念。在他看来,“能守一职,便无愧耳”,“入帷幄之中,参庙堂之上,不能为主尽规以谋社稷,君子所耻也”(《诫兵》)。即为官者应坚守本职工作,多做有益于国家、社会发展的实事,即谓尽忠。魏晋时期,士族享有极大的政治特权,而贵族子弟大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官员比比皆是,而如此为官者也难得善终。故而,颜之推一方面强调仕宦目的在于扬名显亲,另一方面又时刻保持着谨小慎微的心态。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张力,使其形成了一种务实经世的官场行为准则,并弥合了传业理想与谨慎心态之间的矛盾,进而既能在激烈的官场斗争中全身而退,又达到了扬名显亲的世俗目的。
在魏晋时期,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士族权力斗争激烈,“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9]。这种社会背景所塑造的家国叙事则是基于人们对“忠”的世俗新解,如颜之推将谨慎务实作为忠君处世的唯一准则,以既无功亦无过的仕宦方式减少触犯刑律的可能,并不断调适儒家伦理内涵以适应情势变化,其慎道也非旨在提高个体修养,而是出于家族免祸。从“修齐治平”的目标来看,内圣止于保身,外王止于保家,士大夫不曾运用儒学伦理内求于道,也无法凭借政治权力济世化民。家族地位逐渐置于国家之上,家国关系也趋于倒置。
三、家国关系的倒置与价值重塑
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门阀大族势力壮大,不仅寒门庶族无法与其相抗,连皇家贵胄也难以望其项背[20],在东晋甚至出现几家豪门大族先后专权的政局。但皇权依然具有政治与道德合法性,不过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21],如士族子弟谋求官职以巩固家族稳定,皇室也需依靠士族的智能来维持政权,两者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在民间的社会生活中,士大夫不再以仕忠朝堂与兼济天下为己任,“其所关切者亦唯在身家之保全”[22],这种“止知有家, 不知有国”[23]的价值取向表明士人眼中的家国地位发生了置换,并影响了个体与家族的行动策略。其原因是在魏晋时期的社会大背景下,国家不再是人们唯一的价值寄托,士人的价值取向开始重塑,并在家族延续乃至个体生命中发掘了新的价值归属。可以说,传统家国叙事的变化正是魏晋士族的社会心态、个体归属和伦理支持的变化体现。
(一)孝先于忠引起家国倒置
忠孝关系是“家国同构”格局的集中体现,自汉董仲舒将“君为臣纲”作为三纲五常之首,国家君臣之伦重于家族父子之伦,并以此构建忠孝一体的伦理政治。伴随王朝更替频繁,唐长孺指出,“自魏晋门阀制度建立以来,孝道实践在经济与政治上的作用尤为凸显,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也由此形成”[24]。
“孝”的概念最初作为儒学家族伦理的基本维度之一,其实施效力仅限于家族内部,以此指导人们行为和规范家族秩序。自西汉“以孝治天下”(《孝经·孝治章》)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来,“孝”与政治便紧密结合成中央集权统治的手段,由孝及忠也成为官方话语建构的必然途径,并为历朝所沿用。但家族与王朝发展并非完全保持一致,在魏晋时期,由于过度强调孝道的作用,使其走向威胁王权的反面,一些士族豪门的政治地位甚至超越皇权。究其原因,即在于忠孝观念的地位变化。传统儒学强调“忠”的专一性,即“从一而终”式的忠节,这也是由孝作忠的逻辑基础。而魏晋“忠”的内涵体现为官员应坚守本职事务,不越权、不渎职以保全自身,淡化了忠节的道德要求。但是,不论处于任何朝代,“孝”始终源于家族发展的必然,而“忠”的内涵规范之变化使得士大夫不再忠于一朝,由孝作忠的逻辑基础也由此消解,随之改变了传统国家至上的家国关系。此外,“孝”在魏晋时期与自然、名教相融合,所谓“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成器”[25],父子关系成为先天的、原始的最高道德,而“忠”不过是后天发展而来的人为产物,这样,家族在士人眼中的地位逐渐置于国家之上。
(二)家族成为新的价值归属场
自汉董仲舒完善“天人感应”体系以来,君王成为“天意”的代表,其特点在于突出社会群体的作用。个体行动与生活意义唯有在国家主导的集群框架中才得以满足,“修齐治平”成为确立个体价值的主要路径。然而,随着西汉灭亡而导致“天人感应”体系的奔溃,人们处于前所未有的个体归属焦虑和价值迷茫中,这也是造成魏晋社会思想冲突大背景的原因。
具体而言,个体经由一整套修身察举而入世建业的制度设置,将自身融入社会群体、家族依附国家,进而实现人生价值。但伴随“天人感应”体系与察举制度的瓦解,这种良性的入世途径也受到破坏,个人与群体的联结纽带趋于断裂,个体由此丧失了行为依据和价值归属。此外,在“天人感应”系统下,社会具有一套共同的伦理信仰指导人们行为,个体与社会、家族与国家之间维持着一种平衡、稳定的关系;但“天人感应”的崩溃打破了这种平衡,最终引起士族的迷茫与不安。正如颜之推在《序致》中自嘲道:“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国家不再给予人们归属感与稳定感,个体亟须新的价值归属和精神寄托。与国家相比,“士大夫宗族既有不会轻易随改朝换代而转移的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更有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体文化优势”[26],并为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提供了安身立命的避祸场所。这样,士大夫转而向内致力于家族发展,如“此儿必大成吾门”[27],“此儿进利,终破门户”[28]等家庭训诫充分体现出魏晋士族的门第竞争意识。家族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不再纯粹是国家的依附,并积极进入官僚系统以巩固家族发展,家国地位趋于倒置。个体的精神依托也从国家群体转向世俗家族,进而在香火绵延中实现新的人生价值。
(三)自我价值认同的增强
魏晋时期,各国征战连年不休,作为士人行动依据和精神支持的儒学伦理已无力指导个体行为,人们原本被伦理规范所压抑的自然本性逐渐显露出来,并随之对外来学说和宗教思想予以关注,其社会思想展现出对个体生命与人格自由的深切关怀。
儒家认为,通过鼓励人们在现世积极建功立业,将有限的生命融于无限的社会中,以此实现永恒的人生价值,消解死亡的焦虑感。但这种方式在死亡问题突显的魏晋时期已然失去了效用,而佛、道思想则能为个体的精神困顿与死亡焦虑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如道家提倡的精神自由即满足了人们对个体存在价值的需求倾向,颜之推也提出“礼源人情,恩由义断”的判断,反对礼教对人之本性的过度束缚,进而在调适情礼冲突的过程中强调个人存在的现实意义。此外,佛教的诸行无常和轮回思想宣扬世间万物如同人之生老病死,皆是一个无穷循环反复的过程,这便对死亡的形式做出了永恒的消解。佛教学说深刻地描绘出士人在面对死生无常和世事变迁的渺小与无力感,颜之推作为这一时期士族的典型代表,对生命无常的感慨尤为深刻:“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勉学》)。可以看到,由于儒学伦理日渐式微,以及战争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性大为增强,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命运和价值,而道教和佛教义理则为人们纾解生命价值与人格自由的困惑提供了有效途径。个人从群体关系中脱离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自身的某种价值解放,其中也蕴含了“自求诸身”的个体化倾向,促使个体与社会事务相疏离。
四、结语
在传统社会,家族与国家的关系始终是此消彼长、难以协调的两极。基于魏晋时期的动荡社会背景,士族的行动策略虽然以“修齐治平”的实践路径展开,但其核心在于个体生命保全与家族发扬光大。具体而言,颜之推一方面依据儒家伦理指导个体修身、治国与齐家的具体行为,但另一方面他并未将儒学价值上升至“平天下”的高度,修身与治国的最终归宿也止于“齐家”。可以发现,在社会安定时期,“治国”与“平天下”具有同一性,“修齐治平”的实践路向趋于递进上升,家齐则可国治;在社会动乱时期,家国地位逐渐倒置,人们视家族重于朝廷。究其原因,即在于忠孝关系的变化,具有政治意义的“孝”逐渐回归到家族本身,同时,个体归属呈现出一种内返趋势,即倾向于家族利益和个体价值的满足,个人逐渐从国家维度中脱嵌出来,并不断解构着家国同构关系。随着隋唐大一统王朝的建立,社会逐渐稳定,门阀势力退出历史舞台。此外,科举制的推行使得学识取代孝廉,成为做官的唯一标准。与大一统政局相适应,“忠义”思想进入官方话语的中心,国家的首要地位不断被突出强调,进而巩固了中央集权。可以说,这正是千百年来封建社会家国关系互为冲突与调适的阶段性反映,并由此塑构了士族灵活的家庭制度安排,也是传统家国同构模式的文化根源与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