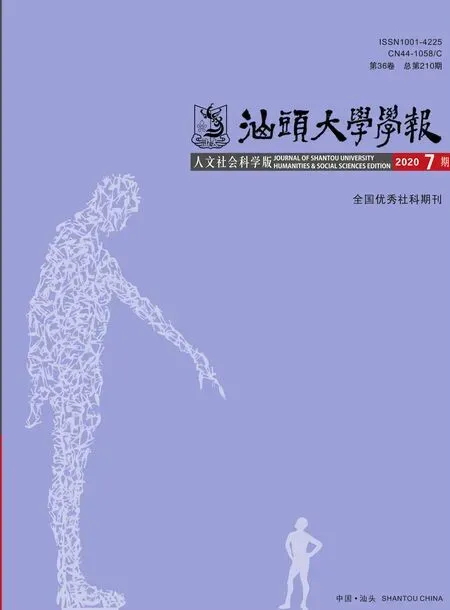论许广平的性别平等意识
2020-12-19陈红旗
陈红旗
(嘉应学院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作为一名民国的“新女性”,青年许广平既有着破旧立新、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坚定理念,也有着勇于践行“放足”“不装饰”“不搽粉”“不带耳环”“婚姻解放”等倡议的强烈诉求,更有着追求个性解放、个体自由的自觉意识。从1910 年代积极关注“反满”“民族振兴”“世界共和”等政治运动,到1940 年代热切倡行中国民主促进会提倡的“民主救国”主张,许广平一直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一员。在这一过程中,她基于敏锐的女性立场和女性意识,一直关注着“人”中的弱者一翼——妇女的命运。许广平对妇女命运的关注既有形而下的具体考察,也有形而上的理论探讨。由于她是从女性本位和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所以男性与女性的性别平等问题一直是她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
一、专制制度下女性的低等地位
在专制制度和旧礼教横行的旧中国社会里,女性被剥削、压迫得极为可怜,可以见得到的社会事业基本上被掌控在男性手中,妇女大多被视为生育工具、家庭成员、孩子之母乃至夫家的财产,男性不但可以利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道德准则和“七出”这类法令来规约女性,还可以依据强大的夫权、政权、神权、族权、话语权和经济权来控制女性的命运。因此,女性根本无法拥有社会权利,更不用提什么性别平等。对于这种情形,许广平非常愤怒,她认为这太不公正了,而儒教起到了对女性加深精神控制的作用,为此她直言批评道:“封建社会思想结晶所形成的一切儒教思想,是屠杀妇女的最残酷的宣言。”[1]113同时,她还专门写了一系列文章来抨击那些剥削、压迫、屠杀妇女的专制制度和旧礼教。
为了充分说明旧礼教对妇女的“屠杀”恶行,许广平专门从她阅读历史上被儒家奉为圭臬的“经书”的感受入手,来解析旧礼教和专制制度的可怕性,以及二者有机结合之后给女性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的余毒和戕害。旧礼教推动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形成了以男性为纲的家长制和“唯我独尊”的统治思想,他们把妇女视为一种完全从属于男性的没有独立性的动物,活动范围只限于闺阃以内的纺绩酒食之事,只要稍微犯错或者违逆男性家长的意志,即可被丈夫逐出家门,并被视为正常和不足为奇的事情,比如连孔子都曾出过妻,这件事情经常被儒生“引道”。《仪礼·丧服第十一》特别指出:“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2]80这意味着被逐出的母亲就算死了,她的儿子连举哀一下都不可能,就更不用说“争辩母亲被逐的是否合理了”[1]114。这无疑违背了人伦天性和天然亲情,显得极不自然和极不人道。
更可怕的是,在旧社会中女性的命运或曰人生轨迹从出生之日起就被规定好了。《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3]171这就等于说,男孩小时应备受器重,要给他玩圭璋,预期他将来会成家立业、称君称王;而女孩小时就备受歧视,只配玩瓦当,预期她将来能够负责好家中饮食、不给父母带来忧虑就可以了。《礼记·内则第十二》:“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凡女拜,尚右手。”[4]539-541这隐喻着男人长大后志在四方、前程远大,而女人长大后只能做些纺绩、搬祭品等浅俗的家庭杂务之类的工作。班昭在《女诫》中说女性应该“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5]29,这就是“妇功”,它合并“妇德”“妇言”“妇容”为所谓的“四德”,它们也是女孩在学校里学习的基本课目,即“妇学”。《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6]20“妇学”专门由“妇官”掌管,“妇官”就是专门教女子学习妇功的女官或曰教师,她们将女孩关在家中、门内所学的正是“妇学”和女红[1]114-116。而女孩们之所以学习妇学和女红,目的就是为了嫁人后更好地为丈夫和男权体系服务,并通过丈夫或儿子的成功来获取存在感、获得感、成就感和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感,即“妻以夫为贵,母以子为荣”,这几乎等于完全否定了女性的主体性、个体价值和精神独立性。
在旧礼教之下,女性无疑是一种人为的制度化的牺牲品。对此,女性难免会产生怀疑、质疑和反抗情绪,为了让女性心甘情愿地受男性奴役和支配,为了维持男权独尊性社会的稳定和长久,男权中心主义者利用旧礼教和诸多歪理邪说对妇女极尽愚弄之能事。许广平说,为了维持封建传统的威严,男权支持者们对男女进行了尊卑之分,并将这种尊卑意识灌输给男性和女性,让他们视之为自然分野或曰从来如此。《易经》中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并强调“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7]374。这就等于把男人当作天和“知者”,把女人当作地和“从属者”。男权社会中的男子为了永远保持压迫妇女的权威,让妇女服服帖帖、不知反抗、更加顺从,就极力强调男女有别和男性的天生优势,并以“礼”的名义将女性“藏娇”和“隔离”。《礼记·哀公问》:“非礼无以别男女、父母、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8]618《礼记·乐记》:“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9]567《礼记·大传》:“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10]557《礼记·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人道之大者也。”[11]552为了强化男女之别,旧礼教规定男女七岁起就不可同席、同食和杂坐。《礼记·内则》:“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4]541《礼记·曲礼上》:“男女不杂坐,不同拢枷,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阃。……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12]429-438这不但将女性与家庭以外的男性完全隔离开来,还人为地阻隔了女性与兄弟之间的交往、交谈和交流的机会。那么,男权卫道者们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将女性与男性乃至外界隔离开来呢?原来是为了“外言不入”。《礼记·内则》规定:“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4]534那么,这些卫道者们为什么如此害怕外言入内呢?为什么拼命宣传“女子无才便是德”和“女人是祸水”等歪理邪说呢?归根结底是害怕女子知晓外事后产生觉醒意识,不愿意再继续接受男性的压迫剥削和欺骗愚弄[1]116-117,他们更害怕女性会因此产生与男性争夺权力的欲望和追求性别平等的合理诉求。
由于封建社会根本不把妇女当作个体的“人”,更不把妇女当作性别意义上的“女人”,所以“五四”先驱者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人积极推动女性解放运动,主张把属于“人”和“女人”应有的东西与固有的气质还给“女人”。与这些先贤相比,许广平的视角与观点要更为具体和富有针对性一些,她知道女性解放运动不仅需要女性群体去努力争取,更需要男性群体的支持和整个社会的认可[13]112,为此她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明确提出和强调了男女性别平等的思想主张,这些主张一方面体现了她的女性立场和先锋意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她的理论洞见和辩证思维。
二、夫权的荒诞性与性别平等的可能性
在中国古代,随着“夫权”的出现和延展,所伴生的自然是女权的旁落和衰落。在奴隶社会时期,由于男性在农业生活中的生产效率更高一些,在畜牧生活中所起作用更大一些,所以男女的社会地位较之母系氏族制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系社会和男权体制得以形成,“夫权”也在新石器时代前期出现了,此后随着封建社会的来临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夫权’日益猖獗,妇女的地位也日益低下”[14]129。“夫权”占优势地位之后,女性受夫权所支配,性别平等根本无从谈起,因为男性比女性占有更多的权利和权力,比如在婚姻关系中,丈夫占有婚姻主导权、优先发展权、家产控制权、家务豁免权、家庭符号权、子女冠姓权、优先出轨权、强行施暴权[15]16-18等。问题还在于,为了强化“夫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儒家学者从古礼中寻找依据,在强化家庭生活中丈夫权力的同时,鼓吹阳唱阴和、男主女从、夫死不嫁、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等,建构了男性至上主义体系,从而使得夫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16]63。夫权强化的结果导致了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和社会资源过度集中在男性身上的不合理现象,导致女性在家庭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公共领域的待遇低下和权利缺失,这无疑延缓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局囿了女性追求个性发展和自我实现的社会公共空间,更消解了女性追求独立人格和个体精神自由的合法性。
对于夫权的不合理性和非人道性,尤其是儒家学者利用《周礼》《礼记》《仪礼》等建构的礼乐文化来强化夫权的现象,许广平用理性的分析、独异的思维方式和富有穿透力的思想,指出了《礼记》《系辞》《仪礼》中诸多说法的不合理和荒诞性。针对《礼记·郊特牲》中“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亲迎,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17]530的说法,她告诉读者,这里的夫妻表面上是“齐同”、平等的,实际上着重在男性之“先”,是有尊卑贵贱之分的。针对《易经·系辞》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7]143的说法,她毫不客气地批评道:“这是多么不平等的待遇!因为有贵贱之分,《曲礼》上甚至‘夫不祭妻’,表示‘妻子如衣服’一样随时可以舍弃,而女人却非从顺不可。于是把女人打入了万劫不复的被剥削了自主权的一种非人境地了。”[1]117女子不仅要“从顺”自己的丈夫、公婆等“上者”,还要“从顺”自己的儿子,只因后者是男性。事实上,在女性出嫁到夫家之前,作为父母是一定要把这种道理或者准则告知乃至“命令”女儿去谨记的。《仪礼》:“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母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6]146这就等于说父母在告诫女儿嫁人后不可违逆翁婆的命令,甚至连庶母也来告诉她,要恭敬遵从其父母的教言,以免到了婆家犯错丢脸,被人家批评没有家教和不懂礼仪。同理,《孟子》:“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18]150《礼记》:“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17]530;“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19]666原来,所谓的妾妇之道就是顺从“夫子”,所谓的夫妇之义就是“顺从”丈夫和夫家的所有男性及“上者”,古人认为“妻柔而顺”这种伦理思想不但可以令家庭和睦,还可以保证家运长久,“故圣王重之”。此后,这种要求女子“顺”的思想更加复杂,进而形成了《礼记》《仪礼》所建构的“三从四德”。“三从四德”等于剥夺了女性在家中的所有“权力”,就算丈夫死后,这种权力也要归到儿子身上。对于这些不合理的教条,许广平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为此她质疑道:“就不知道‘夫死从子’的一句,如果太幼小无知,是否也依从他呢?没有儿子而丈夫死了,又怎样呢?”[1]118这就等于嘲讽了提倡和制定“三从四德”等旧礼教者的荒唐和恶辣,以及那些封建假道学的荒诞和蛮愚。
许广平还发现,这些封建礼教和假道学的信条明明荒诞不经,却被大肆推广,其目的就是为了约束女人和强化男人的绝对自由权。按照人的心理需求特点来加以分析,往往越是缺失的东西就越是想拥有和强化它。因此,为什么那些道学家们千方百计地想把女性固着在家中呢?这是因为他们很无能,是爱情上的软弱者,性欲上的无能者,他们害怕老婆逃离,所以就拼命借助传统观念来愚弄妇女以便维持家庭稳定和保有自己的绝对权威性。他们利用上下尊卑之别来把丈夫比作“天”,丈夫死了被说成“丧所天”,“天”意味着上者、支柱乃至一切,丧夫就意味着寡妇是等死的“未亡人”,是只能去“节烈”或殉葬的烈女节妇。《礼记》:“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17]530女人死了丈夫就得终身不能再嫁,那么男人呢?无论妻子同意与否或者生死与否,他都可以再娶。如果妻子对于丈夫的花心行径不满,丈夫就可以依据“七出”来逐出女人。“七出”是七种休妻的理由,这是在奴隶社会晚期形成的、在封建社会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的律令,按照《仪礼》的解释就是: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这就等于从法律上保障了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绝对权力,于是人世间的无数惨剧都因“七出”而发生。更糟糕的是,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宣传不断强化这种不公平的律令,这使得男女性别平等完全成了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法律给与了男性绝对权力和绝对保护,但由于封建礼教和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所以家庭纠纷不断,且无法解决。许广平分析这原因就在于古代天子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谓“圣贤”或“盛德”者喜欢“三妻四妾”,老百姓自然会学习、跟随和模仿,而不予以清除这种明显不符合现代家庭伦理和基本人道人性人情的旧礼俗和婚姻制度,当然无法解决多妻制之下的家庭矛盾问题。
由于针对女性的专制制度和旧礼俗太过荒诞,难免会引起某些女性的不满、质疑乃至反抗,为了平息她们的愤怒,男权拥护者们给予了女性“一般待遇”——侍奉舅姑(公婆)和做些家庭琐事,但这不过是另外一种“御妇之道”和欺骗手段而已,因为伺候公婆的要求非常多且极为严格。《礼记·内则》中强调妇女侍候公婆要“如事父母”,公鸡初鸣就得入门拜见,“莫敢或后”,要嘘寒问暖、好生侍候,有了“疾痛苛痒”得“敬仰搔之”,出入时要“敬扶持之”[4]532-533。显然,这些举动如果是媳妇愿意去做的还算容易做到,但如果是不愿意去做的又不能违逆公婆之命就会非常痛苦,更过分的是,一旦公婆不喜欢媳妇的做法和做派,就算媳妇再尽职也会被休弃,这是没有道理可讲的。《礼记·内则》还规定:“子妇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饮食之,虽不耆,必尝而待。加之衣服,虽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己虽弗欲,姑与之,而姑使之,而后复之”;“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茞兰,则受而献诸舅姑;舅姑受之,则喜”[4]534-535。许广平认为,专制制度导致家长的权力无限扩大,以致个人没有行动自由,也不能有私蓄,就算有人赠送礼物也要呈送给公婆;而女人根本没有独立人格,就连喜怒哀乐都不能自已,更没有自己的地位。更令人气愤的是,就算已经被贬损到无以复加了,但还是被孔夫子所不满意,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就是稍有小惠也被视为“妇人之仁”,更厉害的是把女人看成“祸水”,而毫不反省男权社会根本就不把女人“当平等的自由人看待,一切教育,都是愚弄她们,埋没她们的智慧,养成服从的奴性”[1]121-122。笔者认为,这是1940 年代初现代女性的理论思维所能达到的最具穿透力的真知灼见。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解放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反对屠戮女性的一切旧礼教、复古思潮和尊孔运动成为女性解放运动的主要意旨,而与此相伴生的另一维度就是追求男女性别平等。许广平认为,这不但非常必要,而且完全可以实现。她指出:“夫妻合力经营共同生活,在家庭上的权利和义务,理应平等。”她以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妇女的存在情状为例,来证明妇女完全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得到真正平等。她强调,苏联妇女不但在宪法上得到了保障,而且实际上都解放了,她们获得了职业上的发展,她们再也不是家庭的囚徒和丈夫的豢养者,而是女性解放的楷模,所以她号召英勇的英国妇女不要接受丈夫给的酬金,要自求独立,让那些鼓吹妇女重新依附男人过活的“甘言利诱”无法实行[20]123-126。她还认为,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国固然以男女平等为一贯方针,法律也规定中国妇女的地位完全与男子平等,但现实生活中并未真正做到这一点,至于“中国妇女的实际生活情形”,不但很多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不太了解,就连很多从事妇女运动的人也不了解[21]129,这意味着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依旧任重道远。
女性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解放和平等权利,就必须接受初等乃至高等教育,对于这一点,许广平完全支持和认可,但她反对当时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学习法西斯主义者的主张,朱家骅希望妇女的教育与男子有别,希望女性能够回归家庭,强调“女子的服务应该以家庭为起点”,认为女子应该去做小学教师、会计、簿记、看护等职务。她批评说,这等于在剥夺妇女与男子教育平等的权利,其目的是要把妇女赶回家庭,让她们依旧作“家庭中的婢女”,如此“骨子里仍旧是要做男女不平等”,依旧是很自私地“不肯把法律上有利于男子的特权放弃”。她坚持认为,当时女性所需要的是教育均等的机会,需要国家建立公共食堂和托儿所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救出来,“把阻碍妇女解放运动的黑暗的门打开来”,需要打破妇女教育的所谓“程序”,根据女性智力、体质、性情的差异因材施教,进而让女性成才并为社会做出应有贡献,甚至成为“抵抗外侮”的有机力量[21]139-140。显然,许广平把教育机会均等视为妇女的生路,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一旦妇女受到了真正的现代教育,她们很难再重新回归传统家庭,她们不但要追求经济独立,更要追求生理本能的解放和个体精神的自由,而只有当她们真正做到从家庭走向社会,并且有了为人、为女的双重自觉时,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22]32,才有可能为女性争取到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三、在斗争与合作中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性别/ 性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系统中,以致于形成了本体论逻辑结构。[23]46性别差异尤其是奴化女性不但带来了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现象,还给女性造成了几千年的深重苦难。今天,男女性别平等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但在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和一段时期内,这种观念还很难被深受旧礼教和男权中心主义思想毒害的民众所接受,因此,追求性别平等的女性解放运动举步维艰。近现代以来,女性解放运动往往是与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绞缠在一起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时而同心同向时而更弦易辙的局面: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与女性解放运动的斗争目标并不完全是趋同和叠加的,有时它们之间会形成合力,有时它们之间也会产生牴牾。加之复古、守旧和反动势力的破坏,因此女性投身政治面临着很多困境。作为一名知识新女性,许广平对此深有体会,但她更知道女性投身政治和社会运动的重要性。与一些主张女性群体自己去争取性别平等权利的高蹈理论有所不同,许广平主张新女性不仅要与男权至上主义者和男权中心主义思想进行苦斗,更要争取进步男性、开明家庭、社会组织乃至政府力量的大力支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男女性别平等。这种思想非常新颖和独到,这也意味着是时的许广平已经站在了女性理论思维的制高点上。
1940 年代,中国社会虽然还有不少封建思想的遗毒,但总算解放得多了,倘若有人要提倡读经尊孔、复古守旧、男权至上,肯定会遭到反对和批判。但在许广平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完成和男女性别平等的实现。她希望妇女工作者能够“从被动转移到自动”,要找到自己适合去做的工作并“实行坚强的学习”,不要害怕自己能力不够或并非自己所长,就算是“硬干”也可以逐渐成为优秀人才或达成目标。她以苏联女性的成功例证来加以说明,很多苏联女性过去不过是小学教师、农村妇女、工厂女工,但她们在国家保卫战中当上了枪手、炮兵、工程师,她们荣膺了很多奖励,也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她们靠的就是主动坚持和永不放弃的竞赛精神[24]148-149。她还以三八妇女节成立的过程和初心——要求男女平等、争取人的合法待遇——来启发中国妇女:要联合自己的父母、兄弟、丈夫、儿女、姊妹、朋友,一起为民主建国而努力团结,要在修改宪法草案时把母亲保障、儿童保障、妇女职业保障等给予明确规定,要把自己真正从家庭中解救到社会中来[25]152-153;要争取受教育权,通过教育获得科学思想、实用技能、学识见识和管理国家的经验;要参加职业部门,不仅要践行宪法规定的妇女有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社会上一切平等的权利,还要彻底实现男女同等待遇;要积极参选国民大会代表,为妇女争取更多的合法权利[26]157;要向刘和珍、杨德群这样的先烈学习,勇于为民族国家的美好未来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27]154;要相信自己,“不要看轻自己的力量”,努力从可以做和应该做的事情做起[28]176,最不济也要尽一份力,“为怎样打发自己生活的人们交换一些生的实况,给大家作为生的参考”[29]164。这些主张是非常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对于抗战背景下的中国妇女,艰苦生活固然给她们带来了新的苦难,但在日寇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中国妇女无疑是抗战队伍中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这是一种社会共识,反过来这种共识也意味着中国妇女遇到了翻身求解放和追求性别平等的最佳机遇。
在全面抗战的社会和历史大背景下,当“救国”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潮和思想主潮时,许广平对于新兴妇女运动和性别平等问题的思索、探寻也在向更深广的层面延展。她认为,儒教思想及其服务的阶级,统治了中国数千年的结果是把妇女视为贱坯,“无才便是德”成了某些人眼中的中国妇女应有的终身命运。即使是她自己,也险些因此被裹成小脚和失去读书机会。然而“自由平等”是人类进展的必要条件和历史洪流,这是时人不惜拿生命血肉去换取的时代使命,背叛这一使命“必然为公众所共弃”。她指出:中国新兴妇女运动早已冲破了“三从四德”的桎梏,也跨越了“五四”前后知识妇女局限于参加政治活动的维度,已经到了参与政权、推动社会改革、发展个性、建造自由、明确担负起争取国家和平民主的重大责任层面了。她以民进领袖雷洁琼和女记者浦熙修等新兴妇女运动先驱者为例,歌赞了她们忍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殴打、下流羞辱却仍然与男子一起携手为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争取民主和平的英勇精神;她们身先士卒,冲在新兴妇女运动的最前列,因为她们明白这是新兴妇女运动必经之途,也是妇女应该担负的无可诿弃的责任。至此,“妇女运动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运动,是整个新兴的社会运动的一环”,妇女完全可以依凭自我健康、沉着的精神担负起“缔造新中国的一份责任”[30]165-170。这里,许广平不但看到了女性身上蕴含的巨大能量,还预言女性终将和男性一样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主人翁。当时代正以特有的方式激发出女性身上潜隐千年的激情和被压抑的能量时,许广平的文字为读者留下了超越性别平等的女权思想理路的历史光影。
如果说,参加女师大学潮时期的青年许广平曾陷入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困境——“无根之‘群’”,即“有关‘群’的理想成为一种缺乏现实根基的抽象存在”[31]193,那么历经了多次妇女运动和全民抗战浪潮的洗礼,尤其是通过民进组织的民主救国活动,步入中年的她已然找到了新兴妇女的精神支柱——“有根之‘群’”,即志同道合的群体已经形成,且正走在推动性别平等乃至缔造新中国的路上。也正是因为感受到了这种“群”的宏大力量,她才会对死于“人言可畏”的影星阮玲玉和死于“做人难……”的名伶筱丹桂表示深切惋惜。人固有一死,但她认为在当时的时代,人就应该好好地合理地活着,“这是真正的人生权利,新的社会下所应争取的,没有到手,就奋斗”[32]171,只要敢于与其他人尤其是新兴妇女们一起奋斗,女人就可以成为连鲁迅都敬佩的那种“勇毅的人”[33]431,甚至可以成为未来新中国的女主人。至此,许广平再次显示了其女性主义思想的前卫性和前瞻性,体现了她辩证的思维方式,凸显了她在“群体”与“个体”或“男权”与“女权”之间所做的斗争与合作相结合的策略背后的智慧,这种智慧对于今天追求男女性别平等、政治平等乃至身体平等的女性主义运动依然具有明晰的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