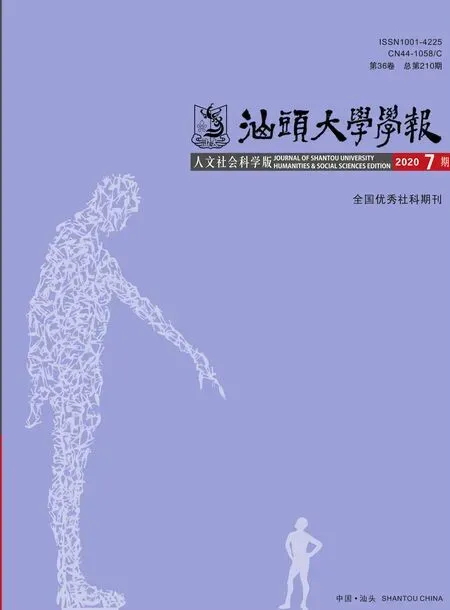林渊液散文论
2020-12-19肖玉华
肖玉华
(韩山师范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一
对于散文写作,林渊液一直在孜孜找寻。
三部散文集:《有缘来看山》(1999)、《无遮无拦的美丽》(2008)、《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2016),差不多十年磨一剑。集中所收作品,从最早写于1991 年的《奶奶》到最近写于2016 年9月底的《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时间跨度是26年。在这26 年间,林渊液的散文无论就题材的选取还是就整体风格的呈现而言,都有了很大变化,而其散文身份也在一直不断变换之中。从篇幅来看,《有缘来看山》收文43 篇,合计不足12 万字,平均每篇文章约2600 字;《无遮无拦的美丽》收文18 篇,18 万字,每篇平均约1 万字;《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收文16 篇,合计16 万字,平均每篇1 万字。当然,文章之篇幅长短不能作为评价其优劣的标准,但对林渊液而言,这种篇幅长短之别还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后两部散文集中的作品明显要优于第一部。早期散文,也就是《有缘来看山》中的多数篇章,其题材的选择很明显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此时的林渊液就像一个采蘑菇的小姑娘,随手摘取身边的人和事,或着眼于现实,或耽于回忆,或纪事,或抒情,但散文写作的逻辑思路多从微观和现实着眼,多由某一个具象(或人或事或物)生发,作者在此基础上予以散点透视,抒发自己的感悟,所抒之情也多偏于感性,虽不失其个性化的“影子”,但相对而言,林渊液对散文题材的过滤与沉淀并不充分,思力之“长”与“厚”明显不足,加之笔力尚显稚嫩,所以反映在文字上,《有缘来看山》中的不少篇章有急就章的痕迹,其力度和长度不足自然也就不可避免成为这些散文的“硬伤”。
《渡》是一篇显得较为生硬的文字。文章从一幅题为《渡》的画作联想到自己读高中时语文老师对茫然的她的“点化”,11 年之后,她又把老师当年的话转述给了一个叫评儿的女孩,由此完成了一个极具禅味的“渡”人的过程。《用心地去发现吧》阐释了罗丹的名言:“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文中最后的呼告也缺乏动人的感染力:“用心地去发现吧!生活无处不飞花,美就在你的身边,在你的眼前,在你的心里。”立意相对浅显,文字也较为直白。
当然,这时期的散文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比较多地表现出了她至情至性的一面。《红氍毹七品》、《沈园遗韵》、《写给薛涛》等散文中对传统女性的书写表现出了对现代女性的审美观照和关怀。青春年华正怀梦,此时的林渊液一方面采撷生活中的感怀与感动,同时也在试图构筑一个古典且不乏诗意的梦境。就像《人,诗意的栖居》中所追寻的,作者借助于对四首古典诗的解读,在诗与文学的世界里完成了一次回归乡村田园和自然之旅。《挑一肩情趣给城市》中对扁担挑着的竹笼里的鸣蝉作了一番遐想,奢望能为迷失的城市生活担回一丝丝情趣。
令人欣喜的是,到了《无遮无拦的美丽》,林渊液的文笔变得成熟且自信了许多。那个曾经多梦的采蘑菇的小姑娘已经不再那么感性。或许是年岁的增长,或许是阅历的丰富,“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我的身体和春草一样复苏了,细嫩而虚弱的细胞迅速地充盈和刚健起来。”[1]她已不再满足于从身边和记忆中的人与事中抒发感怀,分享感动,她有了更为重要而深刻的命题需要关注。以《蒜茸与一个女子的成长史》、《无遮无拦的美丽》、《走过我初恋的狄青》、《一个人的王朝》以及《红颜七绝》为代表的一系列散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延续着前阶段散文创作热衷于感怀与感悟的抒写,但更多融入了作者自我的人生与生命体验。文字的分量也因此变得厚重、深沉起来,其中所蕴含的思考的张力也有所加强,使得其散文创作的境界和格局一下子变得开阔了许多。正如有评论所言:“此时的林渊液,文章中开始伸出了长长的触须,在现实的衣物、潮剧人物的积尘和自己身体的王朝起落间去触摸自己,在对自己的回眸中重建自我,这使得她的散文的取景范围大大拓宽,也使得她的散文成为自我成长史的透视镜,更成为了以文学重塑自我的基石。”[2]《蒜茸与一个女子的成长史》是一篇关于一个女孩到女人的生命变迁史和成长史:居于主流之外多少有些另类的“我”最终“跌回到尘世凡间”,在极为细微的“蒜茸”这种味道上与一直传统道路上走来的妈妈在生命历程中“殊途同归”;《无遮无拦的美丽》通过阅读衣裳来“阅读我自己的断代史”,宣称:“我依然是凡俗中的一个女子,像千千万万凡俗的女子一样,穿戴一些有着某种约束的衣饰。我的穿着和我的思想步调一致,只能在我自己可以坦然接受的限度之内。这个限度并不是一个矢量,它可能成长和改变。”[3]《走过我初恋的狄青》是相当独特的一个文本,它通过“我”与传统戏文中的“狄青”这一人物形象之间互为镜像、双向嵌入式的写法,不仅从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审视了“狄青”这一英雄形象,更由此检视了“我”的成长历程,以及所逐步形成的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和态度;《红颜七绝》选取了古代如鱼玄机、赵飞燕、江南采莲女等七位(类)女性形象,作者试图在“他者”的形象解读中投射自己的生命体悟。同样是写禅意,《落花禅》明显要比《渡》更有文学审美意味。由此可见,《无遮无拦的美丽》一集在林渊液的散文创作历程中有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过渡性意义。
二
如果说《有缘来看山》是对自我性情的抒写,《无遮无拦的美丽》熔铸的是自我的生命体验,那《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则转向于文化,特别是对于潮汕本土文化的反思。
已年过不惑的林渊液对自己早先的创作产生了困惑:“大约是在六年前,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极大怀疑,曾经的那些文字有如枝枝叶叶,风一吹来,便没有了赋形。”[4]林渊液的自我怀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周作人。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周作人发觉自己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写的作品“满口柴胡,殊少温柔敦厚之气”[5],并重新确立了自己在散文创作中的文化身份,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散文史新的篇章。林渊液的这种反思在散文史上的意义自不可与周作人同日而语,但对于她本人而言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同样表明林渊液在散文创作中开始有了一种文化身份的自觉。“做潮汕平原上一棵开花的树”,这是作者对自己在文化散文中文化身份的定位。“树与土壤,向来有一种契阔平生的情谊。当我确立自己关于‘树’的理想的同时,个人写作的生活资源问题也被揭开了。我生在潮汕平原,长在潮汕平原,年少时,我的内心经常会叛逃出去很远,可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她牵扯着走回来。”[4]至此,林渊液开始有了潮汕文化阐释者的身份自觉。
作为潮汕本土作家,潮汕文化进入林渊液创作视野应该始于其创作早期,时间大约是上世纪90 年代末期。《亦浅亦深潮剧缘》(1998)中的潮剧就是潮汕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或者载体。但毋庸讳言,这时期作者尚处于一种自发阶段,到《无遮无拦的美丽》集时,潮汕文化基本上是作为一种人物活动或者事件发生与进行的背景存在着。《走过我初恋的狄青》的主体内容自然是狄青形象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所起到的影响,但是潮州歌册、潮剧乃至于民间文化作为背景铺设其间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处理方式在《蒜茸与一个女子的成长史》、《死亡的栅栏》、《无遮无拦的美丽》等篇章中同样可以看到。直到《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潮汕文化元素才从背景站到了前台,成为散文创作的焦点话题。虽然林渊液视阈中的潮汕文化景观并不足够丰富,但凡是纳入其笔端的文化无论是具体的载体或者符号都具有极强的潮汕文化的代表性,诸如潮剧、潮州歌册、潮汕工艺、女红、嵌瓷以及民风民俗等等。作者以潮汕文化的阐释者的身份诠释着潮汕文化,这种身份自觉无疑与上世纪90 年代文坛弥漫的“怀旧”气息以及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为代表的文化散文的兴盛有一定的关联。“90年代文化界尤其是文艺界,弥漫着一种怀旧气息。实际上,对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呼唤常常体现为对于前代社会的怀恋。对于艺术家或具有艺术气质的思想家,常常有怀旧或反现代文明的倾向,也就是在评价社会的时候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二元对立,或道德的尺度优先于历史的尺度,认为历史的前进导致道德的退化、美德的丧失。”[6]当然,林渊液在这方面的自觉相对较晚,她对潮汕文化的反思似乎与笔者曾经关注的许多作家都不一样。例如在对江南文化的怀旧与反思中,车前子怀旧的时间前沿是“小时候”,叶兆言则是心系民国时期,费振钟的触角伸得最远——六朝,但无论是哪一个时间段,这些作家对现实中的文化景观毫无例外地持批判和否定态度。如果再稍往前看看,余秋雨等人的文化散文的立场和姿态也大抵如是。林渊液则不然,她以潮汕文化为考察对象的文化散文对潮汕文化并不是一味予以批判与否定,当然,批评与批判肯定是必须的,毕竟文化散文的天职就在于它的批判性,并在批判中彰显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小黑屋”这一意象显然是潮汕文化中的狭隘与自闭一面的隐喻表达:“这个小屋子真暗”(《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忍冬草与一座城市的近代史》中在对汕头小公园的欧式建筑做了考察之后,作者发现:
在我们的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中搅拌着的就是殖民化。我们的开放是被动的。我们的美丽是被动的。我们的富裕是被动的。我们的文明是被动的,我们的城市是被动的。(《忍冬草与一座城市的近代史》,《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第150 页。)
但批判与否定并不是林渊液对于潮汕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的全部认知。作者更多的是站在一种相对客观、理性的立场上审视潮汕文化。其中她对潮剧的情感变化堪为代表:小时候喜欢听潮剧,甚至还动手尝试过潮剧的创作,年轻时却“替它露怯了”,“觉得它很村气,也有很多糟粕”,“它最好被埋葬了就像根本没有来过这个世界”,并宣告“我不喜欢潮剧现在!”人到中年之后,“才重新反观自己与潮剧之间的恩怨”,“重新走进剧场,观看潮剧”,“重新珍视起潮剧来”(《私塾、故乡与远方》、《梦因由》)。在祛魅早已成为一种潮流,现代性凸显的时代文化氛围中,林渊液却为潮汕大地上依然盛行的巫术与比比皆是的神祇寻求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能够对其给予人们心灵和精神慰藉作用予以大胆而理性的正视。在巫的世界里作者读出了它的人情味:
巫所给予我们的阴间世界,竟然如此充满人情味。这个阴间是半敞开的,半透明的,可以到达、亲近和改善,可以共勉和相互关怀。这个世界,给活着的灵魂以自由、从容的死亡。(《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第17 页。)
所以它的存在自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真伪判断对于巫来说真有那么重要吗?她只是一个民间的灵疗师,不用药不用石,在伤口上呵气成烟,那血便止了,新的肉芽生长起来,人的元气也便生长起来……如果我们的乡村,还有人需要在红衣婆的咒语中获得安静,获得能量,那么,就让她留在山村的门楼和山墙里吧。(《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第26 页。)
相应地,对潮汕民间信仰中“老爷”存在的认可也就成了应有之义:
我对老爷已经不再持愤激的成见,相反地,我感谢他为我们安顿了许多或者无奈或者无望或者恐惧或者战栗的心灵。这在农村大地,是一个多么重要的精神工程。(《乡神》,《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第35 页。)
总之,林渊液既没有对潮汕文化表现出盲目自信,也没有予以全盘否定。林渊液对于潮汕本土文化在心理与情感上无疑有其矛盾的一面,但她却最终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点去化解这种矛盾。正如有学者所论:“林渊液作为潮汕文化的阐释者和反思者并不安于故土歌唱的角色。相反,她孜孜不倦地探索故乡在遭遇现代化的过程中的复杂精神景观;她也在故乡文化与强势主流文化的对抗中寻求反抗遮蔽的文化主体性。”[7]这或许才是林渊液在潮汕文化散文系列中文化身份的价值所在。
三
散文后面站着一个人。林渊液的散文中有一个鲜活的个性形象在。其实,林渊液散文创作的找寻过程,也是她个性化特征不断外化与强化的过程。
古典诗情与现代理性相结合,在林渊液的散文中达到了一种平衡。如果说有所侧重的话,那就是早期相对偏重于诗意,近期相对偏重于知性。以古典的诗意情怀营造出独特的氛围,并在其中以现代女性的智性视角审视文化,这成为林渊液散文形象的独特之处。
早在1800 年,法国文学史家斯达尔夫人在其《论文学》中就曾经说过,“我觉得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8]。与北方作家常见的粗犷、豪放气质相比,南方作家更趋向细腻、婉约,有一种诗意化的浪漫情怀。翻开林渊液的散文,读者总能感觉到作品中弥漫着一种具有古典气息的诗意氛围。有的是在开篇营造:
那一处远离市声的田园水泽,仿佛一直在遥等着我们。一百年,或者一千年了。是前世今生,也是魂里梦里。因此,当梵和我风尘仆仆来到这座小村庄,我一眼便认出了它,一百年前,或者一千年前,我们也是这样踏着衔草的阡陌走到这里的。(《今生乡野是前缘》,《有缘来看山》,第4 页。)有的则在文末点染:
出得门来,走入夹道的白梅花中。青竹梅的花很小,貌不惊人,单一朵落在衣裙上,也就误以为被积水溅上了。但千朵万朵地站在枝头,千株万株地站在道上,也就有了一种铺天盖地的烂漫和蛊惑……上了车,逶迤而去,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梅花源记》,《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138 页。)
这种诗意化的文字在林渊液散文中随处可见。“老屋瓦松”、“紫藤花开后的小巷”会令她驻足流连;她希望把蝉鸣挑进缺少情趣的城市生活,把自己放逐于山、水与自然天地之间,即使身处凡尘俗世之中她也作此遐想,并一直精心呵护这种诗意氛围以及梦境。不过,保持这种状态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即与现实妥协,一旦诗意遭遇现实的碰撞时,在情绪上需要克制,需保持一种相对温和状态,而不至于有大起大落的变化。这种表现与周作人颇为相近,而与余秋雨、夏坚勇相去甚远。所以,同样面对传统文化,林渊液虽也看到了潮汕文化的负面,也叹惋于潮汕传统手工艺制作所面临的现代困境,但她却始终能够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发现其正面的与合理的一面。而这也正体现出林渊液性格中理性、知性的一面。林渊液力求在散文中达到理性与知性相融的状态,无论是对美的发现还是对存在的理解,都体现了其知性气质。
这并不妨碍林渊液在诗意氛围中以现代女性视角理性地审视着眼中的人、事与文化,这或许才是林渊液散文表达的重点。林渊液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就是“智性”。而这个“智性”特质也曾被有些学者看作是南方文化的质点。[9]林渊液散文很少像北方作家那样重视在散文中表现现代文明带来的道德冲突,既不像余秋雨那样悲愤如苦旅者的行吟,也不像李国文那样充满着愤懑与“刺”,毕竟,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潮汕女性作家,林渊液在审视潮汕文化时要表现得温和而温暖得多。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林渊液的一种宿命,像血液一般流经她身体的潮汕文化的影响并不属意于发现或表现潮汕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就使得她的散文缺少一种大开大阖的力度。而这未尝不是她的个性之显现。相比较而言,她显得含蓄蕴藉,而更善于借助于各种修辞手段,诸如比喻、象征等,使得文化描写达到一种具象化的表达效果。所以说,林渊液笔下的潮汕文化是可感可触的,《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开头颇具象征意味:
有一天,我发现了那间小黑屋。
当然,是在异乡。
一群来路各异的外地朋友,聊着聊着兴致大发,有人想必还喝了点小酒,推波助澜恰到好处。奶奶做的香椿尖炒鸡蛋,童年的核桃,还有雪,各种绵软而又浓炽的记忆和情感,纷纷从他们口中喷薄出来,蔓延,噼啪啪听得见柴火燃烧的声音。我发现自己被囚在一间小黑屋,与这群朋友隔着四壁的墙。周遭黑魆魆的,我似乎站了起来,想去点亮一盏灯,但打火机咔嚓几下,喷出点小火苗就熄灭了。(《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第1-2 页。)
以“黄昏”意象来象征传统艺术、手艺等所面临的境遇,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似乎一度为许多作家共同的选择,而林渊液的《诸神的黄昏》则不禁令我联想到了车前子的散文《手艺的黄昏》。当然,跟车前子文中表现出的落寞感之强烈相比,林渊液则略显温和,而她对“诸神”尤其是嵌瓷艺术所表现出无法放弃的态度则又有一种柔中带刚的执着。
对于传统文化,无论是从整个民族文化层面还是从区域亚文化层面而言,许多作家都会面临着困顿其中的一种宿命感,林渊液也不例外。而面对这种宿命所表现出的矛盾与冲突,对于一个潮汕女性作家来说,或许林渊液所承受的东西要远远大于男性。所幸的是,林渊液正以其特有的诗意和理性在这种宿命中进行文学上的突围,而且一直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