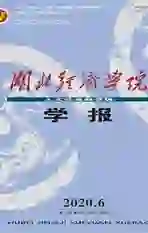海德格尔哲学视域下《美之艺术家》解读
2020-12-07杨奥
杨奥
摘要:短篇小说是美国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艺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之艺术家》是霍桑早期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主要講述一个艺术家在美国工业化文明飞速发展的时代所发生的种种故事。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所阐述的此在生存论分析和他的美学思想来看,艺术家欧文的此在与欧文最终的创作显示了其存在的真谛。
关键词:《美之艺术家》;《存在与时间》;此在;美学思想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是美国19世纪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霍桑所处的时代是美国工业化社会迅速发展的时代,经济之花在美利坚大地上的繁荣盛开,让人们见证了一个新生的、蓬勃向上的美国。在文化层面,欣欣向荣的美国也逐渐摆脱了欧洲的影响,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美国文化。这个时期,各色思潮迭起,美国国内也涌现出一大批如爱默生、梭罗等新时代思想家,霍桑便是其中之一。
在国际文坛上,霍桑颇负盛名的作品当属他的长篇小说《红字》。然而,霍桑最初进入文坛时靠的却是他的短篇小说。霍桑所创作的短篇小说立意新颖,风格迥异,颇具自己的特色。其中一些短篇小说广受评论界的好评,包括:《欢乐山的五月柱》、《胎记》、《会预言的画像》、《我的亲戚莫里克诺斯上校》、《美之艺术家》等等。《美之艺术家》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小说主要描绘的是艺术家这一群体,反映了艺术家们的生活状态。
评论界对《美之艺术家》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该短篇中含混的超验主义思想、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对艺术家群体的关怀、对艺术的分析等等。本文将以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与美学思想为理论基础,分析艺术家欧文的“操心”现象以及欧文艺术创作的本质。
一、海德格尔哲学概述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著作《存在与时间》是哲学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作。该作一出版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成为了20世纪最重要、最具有革命性的哲学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海德格尔详细论证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哲学问题—存在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两千年以来的西方哲学以及传统形而上学把一切事物看做表象,只是在理论层面探讨哲学,从外在研究事物,而忽略了事物的存在。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的主要研究对象便是存在而不是存在者。海德格尔将人这种存在者称为“此在”(Dasein),并以“此在”为出发点来讨论“存在”。他详细论证了此在的生存论要素,此在与其他此在的关系,以及此在的时间性。
此在具有“向来我属”(Jemeinigkeit)的性质。此在的本质是去存在。这里海德格尔所谓的“去存在”并不是萨特宣称的人自由选择的可能性,而是此在的展示性充满可能,即“此”的存在。既然此在是一种可能性,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具有两种存在样式,即拥有自己和失去自己的两种存在样式,拥有自己意味着面对自己本真的可能性,而失去自己意味着逃避自己本真的可能性。海德格尔称其为“本真状态”(Eigentlichkeit)和“非本真状态”(Uneigentlichkeit)。此在的生存论要素的结构整体是“操心”(Sorge)。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操心是他最为重要的哲学概念之一,因为这个术语是统领海德格尔讨论的一切存在现象的基础。操心指的是人的一种规定性。在《存在与时间》中,操心指的是:“先行于自身已经在(世)的存在就是寓于(世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
在海德格尔学术生涯的后期,他研究的重点从此在变成了一种前世界的存在,着重探讨存在本身以及存在的真理。海德格尔对艺术的研究便是从探讨存在开始。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不同于以主客二分法为首的传统美学,他对美学、对艺术的思考主要是基于存在论层面。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对艺术本质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艺术作品的存在。
二、艺术家此在的“先行于自身”
诸多评论家分析该短篇小说时,从一开始就把欧文·沃兰德理所当然地默认为艺术家,这是不准确的。被默认为艺术家的欧文,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概念中,成为了一种“现成存在”(Vorhandenheit)。这个概念是海德格尔用来专指“非人为的事物的存在方式”,如一张桌子在教室中,指的是作为客体而被主体观察的一种呈现。而作为此在而存在的欧文,永远是在去存在,他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因此,只有理解了什么是不断展示自己作为艺术家而存在的可能性,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欧文这个角色。从文中的开篇,我们也了解到,最初的欧文并不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被读者所熟知,而是一个别具匠心、有爱美之心的钟表匠,只是热衷于将艺术赋予在他的作品中。
以创造艺术为己任的欧文,便是一种先行于自身的此在。“先行于自身”指的是人“去存在”的可能性,即人(此在)总是面向他的可能性筹划自身。正如上文所说,此在不是现成存在,而是可能性。在这个意义来说,人永远在向着他的可能性筹划自己,即使他还未是他未来的可能性,他的可能性也已先行于自身。即使他在未来并没有成为他所筹划的可能性,他也毕竟无时无刻地向他的可能性筹划着。“先行于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指的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有选择的自由,人的选择决定了人的存在。人去存在的过程,则是人的本质。换句话说,人的本质就是人永远“是”他的可能性。
最初的欧文,便是为了自己的艺术追求而不断筹划的此在。从欧文手指能握住一把小折刀的时候,欧文便开始展示出对艺术的热情。“有时他会用木头做出漂亮的图形,有时他的心智似乎又用于探究隐藏在机械里的奥秘。”在帮客人修表时,欧文也会自作主张,在客人的表上搭配上他自己喜欢的图案。欧文同时也是一个擅长发现并理解“美”的人。欧文醉心于对美的探寻,以发现事物中的美为目标。对艺术的不断追求,便是欧文面向“成为艺术家”这个可能性做所的不断筹划。这里所说的“成为艺术家”并不是指欧文真的想要成为艺术家,而是指他不断地追求完美的艺术。即使欧文失败了,即使欧文没有成为艺术家,他毕竟也时刻筹划着成为艺术家。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性,便是欧文存在的本质,是“操心”现象中此在的“先行于自身”。
三、艺术家此在的“沉沦”
此在先行于自身指的是此在的可能性,而此在在先行于自身的同时也同样在世存在,它指的是此在的事实性。两者共同构成此在的生存结构,是其生存结构的两个同样的、源始的维度。这种在世存在在此在先行于自身的同时将此在抛入了一个世界,这是此在的“被抛性”(Gewoffenheit)。此在在被抛中认识到了孤独的自己,认识到了自己的无家可归,这是一种“畏”。在对这种“畏”的逃避中,此在开始了它的“沉沦”。“沉沦”是操心现象中的最后一个层面:寓于(世内照面者)的存在。然而这里的“沉沦”,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它不存在伦理意义上的高低。海德格尔特地指出:“这个名称并不表示任何消极的评价,而是意味着:此在首先与通常寓于它所操劳的世界。”此在投身于它所操劳的世界指的则是此在的日常性存在,即消散于世内存在者,隐匿到“常人”(Das Man)中去。在日常操劳中,此在接受了常人的特性,即一种千篇一律的“平均状态”(Durchlichkeit),而遗忘了自己做为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并不是社会大众,而是一种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存方式。它是一种中性的、平均的、被广为接受的价值尺度。“常人”规定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成功的,等等。在常人中,此在得以安心,而不再“畏”,因为一切都按部就班。
艺术家欧文的“沉沦”,便是一种向常人的隐匿。它发生在欧文的“共在”中。共在指的是此在与其他此在一起存在于世界中。“共在是此在的生存论结构,它先天决定了此在要与他人发生关系。”121359文中欧文的存在并不是自己的存在,而是与他身边的人(彼得·霍文顿、罗伯特·丹尼斯、阿涅·丹尼斯)一起存在,他也不得不与他身边的人打交道。海德格尔认为,在世的本质是“操心”,而在世中与他人打交道则是操心的一种方式——“操持”(Ftirsorge)。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说道:“此在首先与通常是在操持的残缺样式中行事的。互相怂恿、互相反对、互不需要、陌如路人、互不关己,都是操持的可能方式”。文中欧文与身边人的操持便是在这种残缺样式中行事的。彼得·霍文顿与罗伯特·丹尼斯都认为欧文追求的艺术没有实用价值,不着边际。欧文则认为他们是不懂艺术的大老粗,他也反对将艺术的价值以是否具有实用性的角度来衡量。文中对欧文如此描述:“他总是要追求优美雅致,从不造访实用的东西,这是一种爱美之心的新发展,它完全摆脱了功利主义的粗俗鄙陋,就好像任何美好的艺术一样。”。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欧文与身边人所打的交道总是在互相反对、互不需要的对立中。在这种样式中,此在逐渐忽视了他最本己的可能性,反而从“常人”中理解自己,用他人的尺度衡量自我。这样的存在样式使得欧文感受到了他与身边人的距离,造成了欧文不稳定、易怒,反复无常的性情。在与他人的操持中,欧文曾前后三次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他身边的人过于注重实用价值,这令欧文异常苦恼。久而久之,欧文在与他人的操持中,不再向着自己的本己可能性积极筹划,而是随波逐流,逃离到了常人中去,接受了常人的价值观。第三次放弃创作的欧文,反而把艺术创作视为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道:“那只是年轻人让自己迷惑的神秘幻想。现在我明白事理了,想起那些都会好笑。”这种遁入常人,对自身存在可能性的遗忘,便是艺术家欧文的沉沦。
四、“向死而生”的艺术家
此在是人的可能性,而人最极端的可能性便是死亡。海德格尔认为,死亡不是现成现象,而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于是,所谓“本真状态”的此在指的就是能够正视自己的终极可能性,即正视死亡。然而,人们通常对死亡的理解,是“常人”的理解,他们只是把死亡看成一个与此在相遇的事件。在“常人”对死的平均理解中,死亡的“向来我属”性被遮蔽了,这使得此在遗忘了死亡才是它最本己的可能性,反而把死亡看成是自身之外的事。这种对死亡的理解,是经验到的死亡,而不是认识到最本己、向来我属的、谁也无法夺走的死亡。海德格尔认为,只有“畏”死,即對死亡的正确理解,才是此在摆脱沉沦,回归本真状态的正确道路。对死之“畏”,指的是认识到死亡不是现象,而是此在向来我属的终极可能性。死亡永远只属于“我”,而不属于任何其他人。
因此,海德格尔呼吁:此在需要先行到死亡中去,直面死亡,在死亡中领悟自身。当此在认识到,死亡仅仅是自己的终极存在可能性,而他人无法代替自己死亡时,此在才能摆脱沉沦,脱离常人的控制。这是因为死亡的向来我属性将此在拉回了自身,使此在认识到它的存在只属于自己。而先行到死亡中去,说的是只有面对死亡,正确理解死亡,此在才能领悟生命的真谛,向着自身最本己的可能性不断筹划自己,而不是逃离到常人中。人终有一死,只有认识到死亡的可怕,才能理解生命的珍贵。
文中的欧文,在第三次放弃自己的创作后,彻底接受了常人的统治。然而他仿佛又突然醒悟,回归了那个充满智慧、对艺术无比热爱的自己。这次转变不同于以往,因为欧文在前两次转变后依旧会受到身边人的影响。这一次的转变,昭示了欧文自身彻底的蜕变,他与身边的环境彻底地和解了,不再受到它的影响。对此,霍桑在文中并未直接指出这次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欧文的转变,来源于欧文对死亡的正确理解。文中对欧文这样的心理状态也进行了描述:“他觉得自己很有力,但有一种迫切感却促使他愈发辛勤地劳作,生怕自己在做活的时候,死亡会突然降临。”由此可知,此时欧文的转变是因为他真正认识到了死亡是自己最本己的可能性。在死亡的鞭策下,欧文认识到了生命的珍贵。正是因为死亡随时都有可能降临,他才意识到了完成艺术创作的必要性。随后,霍桑又列举了许多关于诗人、哲学家的例子,来表明死亡确实可能会突然降临。他说道:“在任何特定的时代,最珍贵的精神体现在个人身上,他却不合时宜地死去。”此刻的欧文,在死亡的鞭策下,彻底摆脱了此在的沉沦,摆脱了常人的统治,从“共在”中的虚假与安宁中醒悟。他转而面向自身筹划自己,面向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并且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并把他的创作当做礼物送给了阿涅。
五、艺术家对艺术本质的理解
欧文最终创造的作品是一只活灵活现的机械蝴蝶,它代表了欧文艺术创作的最高峰。来自国外的学者弗里德利克·纽巴里(Frederick·Newberry)认为:“《美之艺术家》的行文结构便是以欧文蝴蝶的成功为目的。”评论界对这只机械蝴蝶所代表的含义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这只蝴蝶是一种柏拉图式理念的创造,也有学者认为它只是一个毫无实用价值的小饰物。笔者认为,从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出发,这只机械蝴蝶意味着欧文作为艺术家对艺术本质的理解。
海德格尔对美学的认知不同于传统的美学思想。他对艺术的探讨都是基于“存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旭认为:“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回归艺术作品本身,现象学地分析了作为艺术作品之物的世界性,通过它进一步去揭示艺术作品是如何有所庇护地敞开着‘存在的真的。”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的本质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人作品。”这里“存在的真”,在他看来,是通过作品中“世界”与“大地”的争执而呈现的。这里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指的是由艺术作品建立的世界,它揭示了存在着的存在与此在的世界陛。而“大地”则是指“庇护起用具之物所敞开的意义世界并使其持立于自身之中的东西。”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中,艺术作品揭示了一个世界,并由于大地的存在使其立于自身。世界与大地对立统一,在澄明与遮蔽的过程中,存在者的真理被揭示了。
文中欧文最终创作的机械蝴蝶,揭示的就是他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存在。当阿涅仅仅困惑于这个蝴蝶的构造时,欧文告诉她:“是的,阿涅。完全可以说他拥有生命。因为它将我自己吸入了体内,吸入了它的神秘美艳之中,——它的美不仅是外表,而是深入到了它的全部构造——他代表了一个唯美艺术家的智慧、想象力、悟性和灵魂!”这件不起眼的艺术品,之所以弥补珍贵,正是因为它的构造,是艺术家欧文一生的心血所在。蝴蝶的精华,炫丽,象征着欧文的艺术,也是他存在最本己的可能性。然而,当阿涅父亲和阿涅的孩子想让它落在自己的手指上时,蝴蝶却逐渐变得黯然失色,失去光泽。美丽的蝴蝶,在精明干练的人手上黯然失色,这也象征了欧文本人在与他人的共在中走向沉沦。正如欧文所说:“它禀性纤弱敏感,在怀疑和嘲笑中就会遭受创痛,正如那个为它注入了生命的人一样。”而最终,在机械蝴蝶被小孩毁灭而走向了它的死亡之前,暗淡无光的蝴蝶又从小孩的手上飞了起来。这次飞翔则象征了那个经历沉沦而最终又向死而生的欧文。文中对蝴蝶如此描述道:“最终,从孩子手上起来,轻盈灵秀,毫不费力,似乎主人的精神赋予它的灵气驱使它不由自主地舞出这番曼妙的景象,飞向更高的领域。若是没有什么障碍,它可能会一直飞上高空,從此进入永恒。”这个蝴蝶,好像能够提前得知自己的死亡,于是做了最后一次曼妙的飞翔。然而,正如此在最终的可能性是死亡,蝴蝶也经历了它的死亡,就像总有一天,欧文也会经历自己的死亡。
在这个艺术作品中,欧文凝聚了其一生的存在,这就是其艺术所呈现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机括中得以保存,这是将艺术的“世界”庇护起来的“大地”。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中,作品中被置入了存在者的真理。它仿佛就是欧文一生的缩影,表现了欧文对艺术的追求,在共在中的沉沦,以及向死而生的筹划。在故事的结尾,倾注了欧文一生辛劳的蝴蝶被阿涅家一把捏碎了。“欧文·沃兰德平静地看着这场毁灭,这似乎是对他一生辛劳的毁灭,然而又不是,他早已捉住了远比这只蝴蝶更美的东西。”在笔者看来,远比这只蝴蝶更美的东西,便是欧文自己“存在的真”。
六、结语
虽然人首先和通常是“沉沦”的此在,然而通过先行到死,此在还是能够从“共在”中的“沉沦”回到最本真的自己,面向死亡而筹划自身。文中的欧文,虽然最初在共在中沉沦,然而通过先行到死,还是回归了最本真的自己,对自己的存在有了把握,创造出了能够揭示自身存在的艺术作品。从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论角度分析,霍桑《美之艺术家》所探讨的,依旧是人如何存在这一古老的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