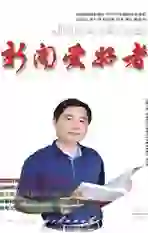新媒体生态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文化再生产
2020-09-22孙英芳
【摘要】新媒体的发展对于当下持续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影响。新媒体改变了非遗固有的生活语境,也改变了非遗的传承主体和传播渠道,同时不断创造着新的语境,形成了新的传播特色。尤其是资本理念下的非遗借助新媒体获得了更大的传播和再生产空间,显示出更深层面的社会文化选择问题。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媒体;传播;文化再生产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革命的产生,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席卷全球,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当,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强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面貌。基于对全球化和“现代性灾难”的反思,人们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因此呼吁维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国际上非物质文化保护运动的兴起,正体现出对日益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化的担忧。中国文化的非物质文化保护运动,也是这个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由于政府强力主导和全社会的参与,非物质文化保护运动声势浩大,其涉及的诸多方面的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探讨和思考,有关非遗保护问题的研究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而当代生活中的新媒体作为信息技术的一种直观显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对新媒体和非遗保护关系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更好地厘清新媒体和非遗保护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从更深层次上理解新媒体生态下的文化再生产问题。
一、新媒体生态下的非遗“新语境”
非遗的语境是非遗产生、发展的生活环境,是由时间、空间、传承人、受众、表演情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根据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所认定的非遗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五大类内容:一是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是表演艺术;三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是传统手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国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发展于乡土性的民间社会,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征,或以口头传承的方式,或伴随着鲜明的行为实践性,是民间社会和地方民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表现形式上,虽然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通过一定的物质形式来呈现,比如传统手工艺等,但大部分还是通过口头传承和行为实践来展现的,因此地方性、实践性、历史性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特点。但是,当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不断加快的城镇化进程,使新的生活方式席卷了传统农耕生活,中国几千年來农耕社会所建构起来的文化体系逐渐变化。作为传统农耕生活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持续进行的城镇化进程中逐渐丧失了原生语境,在社会的急速变化中变得无所适从,因而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
新媒体是信息技术发展在人们生活中最显著的体现之一。在当代,新媒体以其强大的技术支撑、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优越性,形成了无限广阔的网络虚拟空间,为非遗带来了新语境。一方面,新媒体改变着非遗的原生语境。很多非遗即使没有脱离其固有的原生语境,但在新媒体的影响下,其原生语境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非遗的固有生活空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新媒体是把双刃剑,对非遗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另一方面,新媒体建构起非遗的新语境。借助于网络空间,更多的非遗项目实现了跨越时间和地域的传播,从局限的地方社会进入当代都市人群的视野,在新媒体创造的新语境下获得发展。以民间文学为例,民间文学作为一种口头叙事文学,其演述往往需要特定的文化空间,有学者称之为“民俗场”,民俗场的缺失,会使民间文学的传承陷入困境。在近些年乡村社会巨变的背景下,民间文学的发展确实面临着传统“民俗场”缺失带来的发展困境,但新媒体的发展为民俗场的重建提供了新的可能。实际上,不少民间文学借助新媒体手段走向舞台和荧屏,走进更多百姓的生活,获得了新的生机。借助于新媒体创造的传播方式和具体途径,非遗的传承和发展不断与时俱进。
二、新语境下的非遗传播新形态
新媒体改变着非遗的原有生活环境,同时也在不断塑造着非遗的新语境。在新的非遗生存、发展语境下,非遗的传播主体、传播渠道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形成了非遗传播的新形态。
(一)非遗传承主体的改变
非遗作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传承的主体是社区、群体或者个人。非遗作为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文化遗产,承载其历史记忆、社会认知和价值观念。一般而言,非遗传承主体具有地方性特征,往往是特定地域的特定人群或个人。但是在新媒体的语境下,非遗的传承跨域了地域限制,非遗在更加广阔的地域环境里被更多的人所认知,进而在传承主体上出现了不断扩大化的倾向。这样,传承的主体不再仅仅局限于特定地域的特定人群,而是扩大到新媒体语境下的所有人都成为非遗传承的潜在主体。传承主体的边界日益模糊,带来了传承主体的不确定性。
(二)非遗传播渠道的改变
在新媒体环境下,非遗传播渠道的改变是更为直观而显著的事实。在传统农业社会有限的技术条件下,非遗的传播大多依赖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和身体实践,传播的范围和效力都比较有限,也正因如此,很多非遗只能在特定地域的小范围内进行传播。但是,现代新媒体依托先进的技术手段,使得非遗的传播渠道得到质的飞跃。尤其是电视、网络和自媒体的日益发达,非遗的传播形态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状态。在新媒体环境下,利用便利的互联网条件,人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非遗项目,而非遗项目也借助新媒体的技术条件,实现了多渠道、全方位的传播。
三、新媒体影响下的非遗传播与再生产
新媒体生态下,非遗不仅改变了原有的传播主体和传播渠道,从而呈现出新的传播形态,而且,非遗的传播不再是单一的传播问题,而是包含着文化再生产的复杂内容。
(一)资本的介入和资本理念下的非遗再生产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场域”理论的探讨中,曾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资本理论。他把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资本不仅是场域活动中竞争的目标,同时也是竞争的手段。当不同资源以市场为纽带进行整合时,就促使场域内的资本不断进行博弈,不同资本在互相较量、此消彼长的同时,场域本身也随之变化。新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资本,借助现代网络媒体传播技术、包装创新设计以及文化符号的创新等,以资本的运营方式进行再生产,可以产生相应的效益。这样,非遗一方面可以转化为文化产品,通过商品流通领域,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一种特殊方式。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产品的非遗进入千家万户,进入不同人群的视野,也使非遗在新的生活语境下构建起多元文化交融中的新内涵。所以,新媒体生态下非遗的保护和传播需要新媒体的传播手段,同时非遗也能够作为资本,借助新媒体手段进行再生产,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
根据《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重点在于“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由于非遗种类丰富,传承语境、传承方式不尽相同,非遗保护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在非遗保护的现有经验上,对于现实中濒临消亡无法继续传承的民俗事项,人们常常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采制、归类存档保存,如同博物馆保存文物一样保存非遗。但实际生活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不能简单地像保存文物那样保存非遗,解决非遗生存危机的关键在于为非遗找到符合当下的时代意义,把它融入现代文化体系之中,进行功能的转化和发展,使之成为现代民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从根本上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发展。换句话说,非遗的生命关键在于其再生产的能力。
(二)再生产:新媒体语境下非遗传播的延伸
新媒体生态下,知识和信息的迅猛增长和获得方式的变迁导致文化的代际传承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基于数字技术的互联网,让横亘在受众与传播者之间的透明茶色玻璃壁垒瓦解,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在互联网上重新获得生机”[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开展,正体现在新时代和新媒体背景下,非遗在新的知识体系中延续和新变。
在新媒体环境下,当非遗进入生产领域和商品流通领域,以文化产品的身份亮相于各大电商平台,已经脱离其固有的生活语境,成为文化遗产——工业化制作流程——现代商业运营的新型产业链中的一部分。比如,2020年6月13日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阿里巴巴、京东、苏宁、拼多多、美团、快手等多家网络平台在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商务部流通发展司等部门的支持下,联合举办“非遗购物节”。通过举办非遗购物节搭建非遗销售平台,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追求个性化多样化文化旅游产品的需求,有利于推动非遗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让民众在购物体验中,共同参与非遗保护、共享非遗保护成果”。[2]此时进入再生产领域的非遗,它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这个过程,是传播的过程,无疑也是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这种状况,在手工艺类非遗的传承中表现尤为明显。以主要依赖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来说,似乎其进行商品化生产的程度相对较低,但民间文学的口头表演作为人际间的交流互动,参与互动的诸要素在互动中可能形成新的社会结构。语境的研究证明,通过民间文学的演述,表演者与受众之间会建立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可能会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创造新的社会结构。在新媒体环境语境下传承和展演的民间文学,在无形中重塑着新的社会结构,这个过程,也是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所以,新媒体语境下的民间文学,本身也是一种再生产活动。基于此,有学者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性保护”,本质上是要在推动传统文化生活样式的传承、延续乃至创新的同时,寻求民族国家现代文化发展的精神内核,要在文化意义的生产层面推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变迁。[3]毕竟,“传统”的概念是现代性话语的建构,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因此不必把非遗和传统捆绑而固执于非遗的“原生态”。通过传播保持非遗的文化再生产能力,才是非遗生生不息的根本。
四、新媒体背景下非遗传播和再生产的深层问题
非遗传播和再生产从表层上看,是非遗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更深层面上看,是当代社会的文化选择问题。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媒介本身就是信息。但是,决定其最终意义和信息的并不在于机器,而在于使用机器的人们。[4]因此,新媒体不仅带给人们文化选择的便利,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选择,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技术本身也体现出文化的选择性,能够超越小范围的地理空间和时间限制,在更广阔的新语境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离不开新媒体的参与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公众面前呈现出来并激发人们认识、保护和传承,新媒体功不可没。
但新媒体和资本之间有着密切又复杂的关系,因而呈现于大众媒体为众人所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完全摆脱资本对其一定程度上的支配性。所以,非遗的选择中有着资本的动因。但是资本又不是非遗发展的全部支配因素,社会选择的力量不可忽视。保存着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传承和再生产的意义除了融进当代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为之带来便利,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唤起人们对集体记忆的认知或情感认同,因此,步入工业化时代的人们,在传统的思维习惯影响下,会带着对过往历史的情感依恋,对文化传统的心理认同来频频回望非遗传统并期待其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由此保留和历史之间的延续,以调适工业化时代生活带来的种种不适应。
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民族文化发展意义重大,所以,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更是国家或者说社会精英的文化选择。主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坚守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进而在当代社会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中辨识出更有利于民族国家和民众集体的文化导向的有效途径。也正因如此,非遗保护体现出更加深远的意义。这样,资本推动下的新媒体,以显性直观的方式影响着非遗的传播,使新媒体生态下的非遗保护有着多层面的复杂性。交织着资本、新媒体、文化再生产等复杂因素的非遺不再是简单的表层保护和传承问题,而是作为资本的文化与非资本文化之间的博弈,也是整个社会在新的生活语境下的调适和选择。
总的来说,在当代新媒体生态下,在应对生活急剧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应对和调和,力求有新的发展并进行有价值的文化再生产,新媒体也显现出对非遗保护的强大推动力,在非遗保护运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无论如何,在资本、新媒体、文化选择和文化再生产的复杂关系中,非遗保护的未来之路遥远深邃。新媒体会在非遗保护中构建什么样的文化认同,又如何构建新时代的文化认同,都是让人期待的未知数,也正因如此,新媒体生态下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值得继续观察和研究的课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重大委托项目“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研究”的子项目“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课题编号:18@ZH011);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山西村落文化传统功能研究”(课题编号:2019B457)]
参考文献:
[1]姜飞.传播与文化[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208.
[2]中国旅游新闻网,2010-5-12.
[3]胡惠林,王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生产性保护”转向“生活性保护”[J].艺术百家,2013(4).
[4]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9.
(孙英芳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
编校:王 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