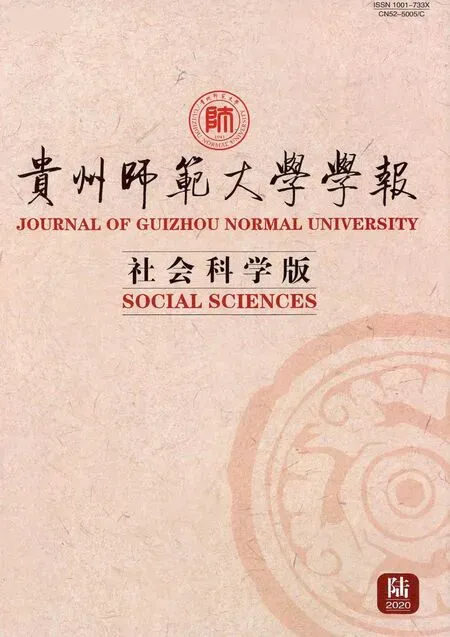性别意识与审美重构
——以郭沫若译《鲁拜集》为中心的考察
2020-03-16咸立强
咸立强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鲁拜集》的日文译者小泉八云谈到Omar Khayyám(郭沫若译为莪默伽亚谟)时说:“奥玛一直受到宫廷的眷爱,始终住在他的小房子里写着关于人生、爱情、酒和玫瑰的诗歌。”[1]鹤西翻译的《鲁拜集》中有这样两个诗句:“让我的手总不和酒杯分开,/我的心总倾注着对一位美丽女郎的爱!”[1]酒与美女,一起为读者勾勒出了《鲁拜集》最为亮丽的风景。《鲁拜集》中与酒有关的字眼比比皆是,美女也经常出现。法国的爱德蒙·杜拉克(Edmund Dulac)、英国的罗纳德·爱德蒙·鲍尔弗(Ronald Edmund Balfour)、美国的爱德华·沙利文(Edward J. Sullivan)等为《鲁拜集》绘制的插图中,美女与酒杯(坛)都是被特别凸显的对象,就画面布局及比例而言,美女似乎更为引人注目。英译者菲茨杰拉德说:“酒和美女是用以彰显他们所赞美之神的意象,而不是遮掩这些的面具(using Wine and Beauty indeed as Images to illustrate, not as a Mask to hide, the Divinity they were celebrating)。”[2]菲茨杰拉德指出了波斯语诗篇中酒和美人这两大意象之于神的关系,但是菲茨杰拉德似乎无意于忠实地再现原诗意象的神意,是以他的英译被人视为将原诗中洋溢着神性的意象世俗化了。神圣化还是世俗化,不同的译者各有其理解和选择,这也就使《鲁拜集》的翻译呈现出迥然相异的审美风貌。
就《鲁拜集》中酒与美女这两个重要意象的翻译处理而言,郭沫若在众多汉译者中别具匠心。推崇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鲁拜集》的郭沫若,非常重视酒之意象的翻译,不仅忠实地对译了原诗中直观的酒之意象,还将原诗隐喻酒而无“酒”字出现的诗句显豁地译成酒之意象,酒之意象在郭沫若的译文中明显得到了强化。与酒之意象的翻译相比,《鲁拜集》中的美女意象或者说女性色彩在郭沫若的翻译中则表现出被淡化的倾向。郭译《鲁拜集》中女性色彩的淡化之所以值得注意,首先是因为郭沫若对女郎这一重要意象的翻译处理体现了译诗与原诗之间的巨大张力,这方面的探讨将有助于深入认识郭沫若的译者主体性及审美建构问题;其次,译诗中性别意识的呈现与现代汉语及白话诗歌形式的建设密切相关,郭译《鲁拜集》在众多汉译文本中非常典型地表现出了白话译诗所具有的现代的性别意识。整体而言,通过对《鲁拜集》中酒与美女两类意象的不同的翻译处理,郭沫若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鲁拜集》某些诗篇的审美。
一、郭沫若译诗中女性色彩淡化的表现
郭沫若译诗中女性色彩的淡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将原诗中女性化的意象转变为男性化的意象;第二,不译原诗中带有女性色彩的意象;第三,以男性代词替换女性代词;第四,将诗中出现的第三人称女性代词替换成第二人称代词。
郭译《鲁拜集》第41首将原诗中女性化的意象转变为了男性化意象。And lose your fingers in the tresses of/ The Cypress-slender Minister of Wine,郭沫若译为:“酒君的毛发软如松丝,/请把你的指头替他梳理。”[3]头发柔软的“酒君”,在原诗中所表现的是一种女性化的气质。单词Cypress一般译为柏树,与松树对应的则是pine。日本译者小泉八云谈到这首诗时说:“在波斯人中间,现在都还常常把美丽的女郎比作柏树,因为柏树高而苗条。”[1]在波斯文化中,柏树代表的却是女性。英译者菲茨杰拉德显然把握到了原语诗篇中的女性意象,故而在英文译本中使用了tresses,这个单词在英文中一般都是指女性的长发。拥有女性长发的苗条的酒君,是一位女性,这两个诗行呈现给读者的是非常明确的女性化的意象。郭沫若将Cypress对译为 “松”。松柏在中国传统诗文中常常并举,代表着坚强挺拔的男性阳刚气质。Slender在原诗中修饰的是酒君,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美女。郭沫若的译诗将Cypress-slender对译为“松丝”“酒君的毛发软如松丝”,实际上就是将原诗中对身材的修饰转变成了对头发的修饰。在连续的转换中,郭沫若消除了这两处英文单词的女性标志。无论郭沫若译诗中的“你”是否可以理解成女性,酒君已经确切无疑地被郭沫若处理成了男性。这首译诗最后一个诗行中第三人称代词“他”的使用:“请把你的手指替他梳理”,表明郭沫若明确地将“酒君”看成了男性。即便郭沫若当时并不知道波斯文化有以柏树比喻女性的习俗,从菲茨杰拉德的英文版中,也完全能够看出诗句中女性化的表述色彩,但郭沫若显然不想在自己的译诗中再现这一女性化的意象,所以他在译诗中进行了一系列的置换,遂使译诗与原诗相比明显呈现出女性色彩淡化的倾向。
郭译《鲁拜集》第24首、第42首没有将原诗中带有女性色彩的意象译出。第24首最后两个诗行:
Dust into Dust, and under Dust to lie,
Sans Wine, sans Song, sans Singer, and—sans End!
郭沫若译为:“尘土归尘,尘下陈人,/歌声酒滴——永远不能到九泉!”最后一个诗行有三个意象wine、song、singer,郭沫若只翻译了原语文本中的前两个意象,却省略了singer这个意象。一般来说,有歌声自然就隐含着有歌者,没有歌者,也就没有歌声。但是英文版诗中三个意象并列出现,也就意味着对于诗人来说,歌声与歌者都是被欣赏的对象,处于相同的位置,而不宜将歌者处理成由歌声被联想到的间接意象。故此,郭沫若译文中的“歌声”只能被视为song的对译,singer在郭沫若的译诗中被省略掉了。Singer这个单词,决不属于郭沫若所说的“难解处”。显豁的意象,没有难度的翻译,此处出现的意译只能是郭沫若特意为之。
原语文本中的singer是谁?要具体追踪诗中的歌者身份固然不可能,但是联系上下文,singer的性别还是可以确定的。《鲁拜集》第12首中有:Beside m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这里的歌者就是女性。第24首诗中的wine、song、singer,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第12首诗中的verses、wine、you,酒、歌(诗章)、歌者(你)构成了《鲁拜集》反复吟唱的对象。醇酒、美人与诗章,这就构成了诗人眼里天堂的模样。但在郭沫若的翻译中,醇酒的意象被完整地保留下来,美女的意象却被尽可能地省略掉了。有歌声自然就有歌者,英文本在song之后紧接着出场的singer,显然是强调歌者的性别,以便构建醇酒、美人与诗章三位一体的审美世界。郭沫若译文在略掉了singer之后,这首译诗的审美就和郭沫若在《读了〈鲁拜集〉后之感想》中提到的刘伶与李白的诗作非常相似了。郭沫若谈到中国传统诗人的享乐态度时,被列举出来作为例证的,都是沉溺于醇酒者,酒是叙述的核心,却没有谈及享乐者在美女方面的任何追求。醇酒、美人意象的不同的翻译处理方式,显示了译者郭沫若的某种主体性诉求,也是进入这一时期郭沫若精神世界的密码。
第42首译诗中,And if the Wine you drink, the Lip you press,郭沫若译为:“倘若你把酒压唇”[3],更准确的翻译应如黄杲炘那般译为:“你喝的酒和你吻的唇”[4]。也就是说,郭沫若似乎将the Lip you press理解成了press your lip,所以郭沫若将其译为自己拿酒压自己的唇,意即自己饮酒。但是,汉语叙及饮酒,一般只说“把酒”,而不说“把酒压唇”。当然,郭沫若的译文也可以读为“把酒、压唇”,即通过阅读上的停顿将其理解为两个分开的动作,“把酒”指的是诗人“把”酒给自己,而“压唇”则是“压”另外一个人的唇。如此一来,郭沫若与黄杲炘两位译者的译诗也就一致了。但是,将“把酒压唇”分读为两个不同的指向有过度诠释之嫌。笔者倾向于将郭沫若译文中的“把酒压唇”理解为“把酒”压自己的唇,而不是原语文本所表达的“你吻的唇”。the Lip you press中的you所指代的对象一般都认为是男性,这位男性所“压”的“唇”便是女性之“唇”。因此,原语文本中这个诗句歌吟的是美酒加美女。但是,郭沫若的译诗却删除了原语文本中的美女意象(女性的因素),只保留了饮者饮酒的意象。
郭译《鲁拜集》第100首中的第三人称女性代词被译成第二人称代词:
Yon rising Moon that looks for us again——
How oft hereafter will she wax and wane;
How oft hereafter rising look for us
Through this same Garden——and for one in vain! (第100首)
郭沫若将诗句How oft hereafter will she wax and wane译为:“你此后仍将时盈时耗”[3]。译诗中的“你”对应的是原诗中的“she”。于是,英文版呈现的“她——我”的诗歌抒情情景转化为“你——我”的诗歌抒情情景,间接性的陈述变成了郭沫若诗歌创作中常见的情感直抒。
And when like her, oh Saki, you shall pass
Among the Guests Star-scatter'd on the Grass,
And in your joyous errand reach the spot
Where I made One——turn down an empty Glass! (第101首)
郭沫若将when like her译为:“你像那月儿”[3]。Her作为代词,指代的就是第100首中的Moon(月亮),郭沫若直接将其译为“月”,就语法逻辑来说,郭沫若的翻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英文版诗句以her指代“月”,月便与整首诗中美女的意象体系相呼应,her的使用让母语即便不是英文的读者也能理解其女性化的色彩。在汉语文化体系中,月亮虽然属阴,常与嫦娥相联,自身却并不必然象征女性,就郭沫若的《鲁拜集》译文中的意象体系建构而言,也没有任何将月这个意象与女性相联系的迹象。整体而言,当郭沫若将“月”这一指代的对象替换her这个代词时,也就去除了原诗中的标志女性色彩的词汇。郭沫若在这一首译诗中选用的字词并不能够让读者见出女性的色彩,从郭译《鲁拜集》整体的翻译选择来看,郭沫若在第100首和第101首诗篇的翻译过程中表现出来女性色彩淡化的趋向。
二、女性色彩的淡化是译者郭沫若有意选择的结果
在《鲁拜集》的众多汉译者中,郭沫若是唯一有意淡化原诗中女性色彩的译者。
按照译诗形式,百年来《鲁拜集》的汉译可以简单地划分为旧体文言译诗和新体白话译诗。旧体文言译诗普遍地不对译原诗中的女性代词,如黄克孙的第100、101首译诗:
100 101
明月多情伴客身, 酒僮酒僮劝客来,
人来人去月无闻, 座中无我莫徘徊。
从今几度黄昏月, 醉翁去后余何物,
遍照园林少一人。 一只空空覆酒杯[5]。
旧体译诗属于文言诗歌系统,而文言第三人称代词不分男性女性,汉译者使用文言的形式翻译西方诗歌时,基本都不对译第三人称代词。黄克孙等人的旧体译诗既没有对译女性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也没有借助其他手段呈现原诗的女性色彩。就译诗与原诗的差异而言,这自然也算是淡化女性的一种表现,但这一现象的造成并非译者个人选择的结果,更多地是旧体诗和文言两者藩篱所致。对于这种类型的翻译,笔者不将其视为有意淡化女性色彩的翻译实践。再如前面所述的《鲁拜集》第41首,旧体诗汉译者似乎都无意改变松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情趣,译诗中也很难见出表示女性的意思,如黄克孙的翻译:“携壶浪迹山林上,/翠柏苍松供酒神。”[5]翠柏成了“供”酒神的事物,而不是酒神本身。与旧体译诗相比,选择自由体翻译的译者除了郭沫若之外都明确地译出了这首诗中的第三人称代词“她”。黄杲炘译为:“让你的手指在她发丝中忘情”[4],鹤西译为:“且把你的手指插入她的卷发,/莫辜负那苗条女郎的劝酒持觴。”[1]“她”字的使用,表明两位译者都明确地将酒君看成女性。
除了《鲁拜集》第41首,其他诗篇中she/her的翻译情况也大多如此,如刘复(半农)从法文翻译的《鲁拜集》第54首:
瞧瞧玫瑰花见到了晨风开放了:
黄莺儿被她的青春闹醉了。
我们喝些酒罢,为的是不知有多多少少的玫瑰花,
又被风吹落在地上化做了灰尘了[6]!
第100首(按照郭沫若译《鲁拜集》版本次序)鹤西译为:
啊,女郎,几时你和她一样
在那草地上群星般的宾客中来往,
请你斟酒时把满满一杯美酒
倾洒在我曾经坐过的地方!
第101首(此处所列译诗顺序依照的是郭沫若译《鲁拜集》版本)鹤西译为:
那边又升起了照着我们的明月——
今后啊她还会不断地圆缺,
今后啊她还会升起来寻找我们,
但在这花园里——有一人将遍寻不得[1]。
黄杲炘将这一首译为:
亲爱的,你瞧那月亮又在升起,
透过颤抖的梧桐寻找我和你:
今后她还将多少多少回升起——
在树荫里空把你我之一寻觅[4]!
上述列举的自由体译诗,都将文言译诗及郭沫若译诗中被省略或抹掉的“她”明确地译了出来。将各种版本的汉译《鲁拜集》放在一起稍加对照,便能确定这样一个事实:《鲁拜集》汉译者众多,真正有意在译诗中淡化女性的只有郭沫若。在其他白话汉译者都将she/her对译为“她”的时候,只有郭沫若将其译为“他”;在其他白话汉译者将酒君译为女性的时候,也只有郭沫若将其译为男性。郭沫若译诗中出现的人称代词“他”,并非是可男可女的传统汉语的混合用法,从郭沫若自身文学创作的实践来看,当郭沫若从事《鲁拜集》的汉译工作时,他已经非常明确地用“他”指代男性,而用“她”来指代女性。
三、郭沫若文学创作中第三人称代词“她”的使用
《鲁拜集》中的诗篇都很简短,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却较为频繁。简短的诗篇使每个字词的翻译都不容忽略,十音节五音步的诗句中第三人称代词频繁出现,这也就意味着译者和读者都需要反复地思考同一原语词汇的翻译和阅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鲁拜集》中的she/her在汉语译文中到底对译的是“她”还是“他”,也就不是译者粗心大意所致,尤其是《鲁拜集》出版后又经过郭沫若的修订,修订后的译文没有改“他”为“她”的现象,故而可以确定《鲁拜集》译文中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不是源于排印错误或翻译时的手误,而是郭沫若自觉的翻译选择。但是,在将《鲁拜集》译文中第三人称的使用与女性色彩的淡化趋向关联起来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郭沫若文字中“她”与“他”这两个人称代词的使用概况。换言之,便是需要确认郭沫若在着手《鲁拜集》的翻译之前,已经明确地区分“他”与“她”并熟练地使用这两个第三人称代词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翻译与文学创作中“他”“她”不分是常态。最早提出创造“她”字的,是刘半农。在“她”字被普遍接受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之前,现代知识分子曾使用“伊”“他(女)”等指代女性。郭沫若最早谈论第三人称代词区别使用问题的文字见于1920年出版的《三叶集》。1920年3月30日,郭沫若在写给宗白华的信中,转述了田汉的一段话:“我要造一新字。近来女性的第三人称用‘她’字而男性仍缘用‘他’,觉得太不平等。男的便是人,女的便不是人了么?所以我想把‘他’字底人旁,改成‘力’,从男省。”对于田汉的观点,郭沫若并不完全认同:“男女平权也不必在这些枝节上讲求。文字只求醒壑敷用,‘她’字底诞生也正符合这个意思。”[7]由《三叶集》可知:第一,郭沫若和田汉交换过“她”“他”等字的区别及使用问题;第二,郭沫若在与田汉通信之前似乎就已经知道“她”字的创造,在使用方面强调“敷用”,而不必过于讲求在“男女平权”等方面的意义;第三,《三叶集》中郭沫若的信用“他”指代妻子安娜,田汉所写信件用“他”指代表妹,这表明《三叶集》时期郭沫若和田汉虽然明确了“他”和“她”区别使用的价值和意义,但在各自的书写实践中却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
1921年8月5日,泰东图书局出版了郭沫若的自编诗集《女神》,其中的许多诗篇在创作时间上都早于《三叶集》中的通信,但是与《三叶集》相比,《女神》中“她”和“他”这两个第三人称代词的区别和使用已经非常明确和娴熟,再也没有用“他”指代男性的情况出现。茲简单列举一些使用“她”字的诗句如下:
1.《别离》(首刊于1920年1月7日《学灯》):“我送了她回来”。
2.《演奏会上》(首刊于1920年1月8日《学灯》):“她那Soprano的高音”。
3.《湘累》(首刊于1921年4月1日《学艺》第2卷第10号),剧中老翁与屈原谈到洞庭湖中歌唱的两个女子时所用代词为“她们”:“她们倒吹得好,唱得好,她们一吹,四乡的人都要流起眼泪”;提到鲧和他的儿子大禹时则说:“我又举了他的儿子起来,我祈祷他能彀掩盖他父亲底前愆。”
4.《序诗》(首刊于1921年8月26日《学灯》):“所以我把她公开了。”
根据表4的分析数据,以台式烤香肠产品的感官评分为指标,通过极差分析可知,各因素对台式烤香肠品质影响的主次顺序为C>A>B,即孜然粉的添加量影响最大,其次分别为大豆组织蛋白、玉米变性淀粉,台式烤香肠加工配料的最佳组合为A1B1C2,即大豆组织蛋白为1.5%,玉米变性淀粉添加量为4%,孜然粉添加量为0.4%,用此配料加工出的台式烤香肠产品的色泽、风味、组织状态、口感良好。
上述所引诗句,首刊本及《女神》各版本中“她”字都没有什么变化。其中,前两个诗句创作和发表时间皆早于《三叶集》通信,说明郭沫若在《三叶集》通信之前已经开始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她”,只是暂时还没有定型,《三叶集》中才会出现用“他”指代安娜的情况。
从首刊本到初版本,《女神》所收诗篇在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修订方面存在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添加第三人代词“他”;第二,改“他”为“她”。添加第三人称代词“他”的诗篇有三,这类的修订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诗中意象的男子类属,而不是通过代词的添加将女性化意象转为男性化意象。首刊本《新阳关三叠》第一节诗句:“眼光耿耿,不转睛地,紧觑着我。”[8]初版本在句首添加了一个“他”字。这个“他”指代的是太阳。首刊本中,这一诗节已经在两个诗行中反复使用“他”指代太阳,所以新增添的“他”所起的主要作用并非是凸显太阳意象的性别。首刊本《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第六节诗句:“慢慢地开了后门”[9],初版本在句首添加了一个“他”字,新添加的唯一的“他”字将这节诗中无性别的工人明确为男性。首刊本《立在地球边上放号》首刊本中的诗句:“无限的太平洋提起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10]初版本在“全身的”之前添加了一个“他”字,新添加的诗中唯一的“他”字将太平洋的性别限制为男性。
从首刊本到初版本再到后来的各个版本,《女神》中的诗篇没有改“她”为“他”的案例,改“他”为“她”的诗篇有二。首刊本《死的诱惑》第一节诗句:“他向我笑道”,初版本将“他”改为“她”;第二节诗句:“他向我叫道”[11],初版本也是将将“他”改为“她”。第一节诗中的代词的指代对象是“小刀”,第二节诗中的代词的指代对象是“海水”。首刊本《无烟煤》第四节诗句:“我悄声地对他说道”[12],初版本将诗句中的“他”改为“她”。这两处代词的修改,若是从《女神》自然意象的性别归属来说,似乎也不用改。《女神》中的海洋固然多为男性,而太阳多为女性,如《日暮的婚筵》中,夕阳明确地被描述成女性,用的代词是“她”,爱恋着夕阳的海水则被描述成男性,用的代词是“他”。夕阳与海水,便是诗人想象中的婚筵上的一对新人,新娘子是夕阳,情郎是海水。但是自然意象的这种性别区分似乎并不确定,如《新阳关三叠》中的太阳从首刊本始就一直是男性。蔡震从德语文化中的太阳(die Sonne)及日本创世神话寻找郭沫若《女神》自然意象的性别根源:“郭沫若创作《女神》时所身处的日本,其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创世诸神许多是女性,日本民族崇拜太阳神,那位太阳神也是女性。”[13]这些固然能够解释《女神》中太阳为女性的问题。但是,《女神》中的太阳、海洋意象同时兼有男女两种性别,有的诗篇用“他”指代,有的诗篇却用“她”字指代,这种复杂的性别纠缠表明了郭沫若文学创作思想的杂糅性。
通过对诗集《女神》中“他”“她”两个代词的考察,可以发现郭沫若将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用之于人时,不存在“他”“她”混用的情况。与《女神》的编纂同时进行的,还有《茵梦湖》的改译工作,有学者将《茵梦湖》视为“最早自觉使用‘她’字并且影响较大的译著之一”[14]。大体上可以肯定郭沫若在编纂《女神》时已经明确了“他”与“她”区别使用的思想意识。《女神》中太阳、海洋意象兼有男女两种性别属性,说明郭沫若乐于接纳外来新思潮,同时也在以自己的意愿强化或修正这些自然意象的性别属性。
《女神》诗集出版一年后,郭沫若开始翻译菲茨杰拉德英文版《鲁拜集》,《女神》中意象的使用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了《鲁拜集》的翻译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是从意象的性别选择来说,《女神》对《鲁拜集》的影响并不明显。《女神》中太阳意象的性别在男女之间游移不定,《鲁拜集》中则是固定的男性;《女神》中海洋意象的性别也在男女之间游移不定,而《鲁拜集》中的海洋则是女性,如第34首中的诗句:“披着紫衣的海洋,/只是哀哭她见弃了的主上”[3]。《鲁拜集》中太阳与海洋意象性别属性的固定化,可以解释为翻译受限于原语文本,但是考虑到郭沫若多处都改换了《鲁拜集》原语文本呈现出来的性别属性,原语文本带给郭沫若的束缚终究只是造成意象性别固定化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还是译者郭沫若自己的翻译选择。
在意象性别固定化的《鲁拜集》译诗中,第三人称代词“她”“他”,体现了译者郭沫若对所指代的对象男女性别的准确界定。就此而言,若英文本中是男性,郭沫若用了女性的“她”,则表明郭沫若选择了将翻译对象阴柔化,或者说强化了译诗的女性色彩;若英文本中是女性,郭沫若却使用了男性的“他”,则表明郭沫若选择了去女性化(女性色彩淡化)的翻译策略。从《鲁拜集》的翻译实践来看,郭沫若的翻译选择带有明显的去女性化(女性色彩淡化)倾向。
四、译者主体的自我建构及审美重构
《鲁拜集》翻译中表现出来的女性色彩的淡化并不意味着郭沫若不重视女性。郭沫若翻译《鲁拜集》时,正值《女神》问世不久,在别人眼里,郭沫若赫然已经是一位女性崇拜者。《创造十年》中记叙高梦旦请客,郭沫若夹坐在女士们中间。郭沫若回忆说:“大约是看见我是名诗集以《女神》,并做过《卓文君》一类作品的人,以为一定是一位女性崇拜者,所以才那样安置我的罢?”[15]高梦旦究竟是如何想的,现已不知。但郭沫若从文学创作出发进行的揣测,恐怕更切近于自身的思想实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郭沫若就是一个的“女性崇拜者”。《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在《女神》中,歌吟“女神”的诗篇,除了第1辑首篇《女神之再生》,便是第3辑第1组诗“爱神之什”。《女神》问世之前,编发郭沫若新诗的宗白华在和郭沫若的通信中赞誉的,主要便是第2辑第1组诗“凤凰涅槃之什”。《女神》问世之后,最受读者研究者们推崇的,也是“凤凰涅槃之什”。郭沫若不以“凤凰涅槃之什”里的所咏之物命名诗集,而以《女神之再生》或《司健康的女神》等篇目里的“女神”命名,这只能说明郭沫若对“女神”抱有别样的感情,说是“女性崇拜”也很恰当,因为就在诗剧《女神之再生》中,郭沫若就以歌德《浮士德》结尾处的诗句作为题引:“das Ewigweibliche,/zieht uns hinan”,郭沫若将其译为:“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16]
郭沫若并不单纯只是女性崇拜者,他也是男性的崇拜者。周海波教授说:“综合来看,《女神》由两个美学向度支撑:一是男性的力量向度,一是女性美的审美向度。二者相辅相成,架构起《女神》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呈现出对时代的男性雄壮力量的赞歌。”至于女性美,既被视为“对男性中心的反思与批判”,又被看作“是对男性世界的反衬,从特定视角写出了女性对男性世界的互补”[17]。男性雄壮的美与女性的美,都是郭沫若推崇和歌颂的对象。有些研究者认为郭沫若真正尊崇的还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宋益乔、石兴泽指出,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中既有“崇拜女性的情感意识”,同时这些女性又是“男性精神的附丽”,“她们是用天使、圣女装饰起来的精神奴役”[18]。张传敏从“一切的一”与“一的一切”推出郭沫若的个人意蕴中,“也包含了他对于男女从分离到合一的憧憬”,而这个“憧憬”又被归结为“郭沫若对自己男性身份认同感非常强烈,即使是男女合一,他强调的也是女性的男性化,强调的是男性的主导地位”[19]。李畅干脆认为郭沫若笔下在的女性形象“从来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真正的自我价值,完全是用男性的价值标准和审美理想打造出来的”[20]。邓芳认为郭沫若笔下的所有女性都被塑造成男性的附属,“没有男性便找不到生存的意义;自我贬抑而崇拜男主人公,自觉服从男性专权的等级关系;为男性利益牺牲生命或因男性已死而自杀殉情,表现出毫无自我意识的对男性的绝对服从”。认为上述这些描写表现了“郭沫若把女性形象的奴性、依附性、工具性等女性特质作为美好品质大加赞美”[21]。男性与女性的特征界定是社会化的结果,不将郭沫若笔下的男性女性置于社会化的历史长河中给予考察,郭沫若的女性崇拜情结很容易被误读为“男性精神的附丽”。
提出郭沫若文学创作中的男性崇拜与女性崇拜问题,就是想要将《鲁拜集》翻译中表现出来的女性色彩的淡化置于郭沫若整个的文学世界中进行考察。当郭沫若在翻译《鲁拜集》的实践中表现出淡化女性色彩的趋向时,译诗中男性的歌唱也就愈加明显,这似乎确证了郭沫若文学创作中的男性崇拜倾向。但是,女性色彩的淡化与男性歌唱的凸显并不就意味着与女性崇拜相悖。笔者以为郭沫若《鲁拜集》译诗中表现出来的女性淡化倾向恰恰是女性崇拜情结的表现形式之一。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崇拜很难摆脱男性精神的浸染,指出郭沫若塑造和推崇的女性身上带有“男性精神的附丽”,无损于郭沫若是现代文学作家中少有的表现出女性崇拜情结的作家这个事实。不同的人的女性崇拜各不相同,在《女神》中,郭沫若崇拜的女性有从神龛上走下来的女神们,有聂嫈、春姑娘那种大义凛然的女性,也有太阳、大海这类女性化的意象,她们所代表的是磅礴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她们的生命虽然也都与男性密切相关,却不是男性世界里花瓶似的摆设。概而言之,《女神》中的女性与《鲁拜集》中的女性大不相同。《女神》中的女性才是郭沫若心目中理想化的女性,《鲁拜集》中的女性却不是郭沫若崇拜的对象。《鲁拜集》中的女性才真的是宋益乔、石兴泽等学者所说的“男性精神的附丽”,与美酒、诗章一样,女性在《鲁拜集》中是男性的服侍者和享用的对象。郭沫若翻译《鲁拜集》时表现出来的淡化女性色彩的倾向,表明那一时期的郭沫若不满意那种沉溺或麻醉于女性的生活,更不愿意将女性作为颓废生活赏玩的对象,而这正是郭沫若女性崇拜的确证。
在《读了〈鲁拜集〉后之感想》一文中,郭沫若大谈诗人与酒,闭口不谈女性。郭沫若的兴趣所在,是饮者“于饮酒的行为之中,发现出一种涅槃的乐趣”。“涅槃”而不是“颓废”才是郭沫若对诗人与酒着迷的根本原因,而指向颓废的醇酒与美人却没有真正进入郭沫若的视野。就此而言,郭沫若理解与接受的《鲁拜集》,与莪默伽亚谟、菲茨杰拉德所追求的诗意并不完全相同。当郭沫若动手翻译《鲁拜集》时,已不再用“他”指代女性,译文中所用代词“他”字所指代的自然是男性,因此这一代词的选择可视为郭沫若在翻译过程中存在去女性化的选择。与去女性化选择相对应的,则是郭沫若明显将《鲁拜集》视为了“心眼睁开”[22]后出现的破坏(颓废)精神的表现,与《女神》所呈现出来的男性化的歌唱相吻合。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女神》开拓的男性化的歌唱,在《鲁拜集》的翻译中愈加分明地被凸显了出来。只是在《女神》中表现出来的是那种在破坏中进行建设的富有创造力的男性化的歌唱,而在《鲁拜集》中表现出来的则是破坏(打破既定藩篱)与颓废,若是在整个郭沫若文学创作的历程中审视《鲁拜集》的翻译,《鲁拜集》似乎便是沟通《女神》到《星空》的一座桥梁,是郭沫若的歌唱从呐喊到彷徨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鲁拜集》原诗中,诗、酒、美女构成了令人沉醉的天堂世界,而在郭沫若的译诗中,诗与酒的意象得到了凸显,相对淡化了美女的意象。郭沫若译文中淡化女性色彩问题,绝非是无意识所造成,而是译者在对原诗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创造再加工的结果。男性的美与女性的美,都是郭沫若推崇和歌颂的对象。郭沫若本身并不是男性或女性中心主义者,惟其如此,《鲁拜集》译文中表现出来的去女性化或淡化女性色彩的趋向就表现得更加明显。究其根源,窃以为与郭沫若个人在这一时期的家庭生活及其对文学理想事业的追求等密切相关。翻译即创作,郭沫若在翻译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以自身当时的审美诉求重塑了原诗文本,围绕着诗酒人生重新建构了《鲁拜集》的审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