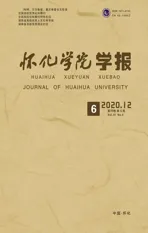明清贵州城市发展历史文献及研究述评
2020-01-19聂雨欣马国君
聂雨欣, 马国君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何谓 “ 城市 ”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次出现关于 “ 城 ” 与 “ 市 ” 的记载,如《汉书》 “ 食货志 ” 载: “ 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 ”[1]《释名》云: “ 城,盛也,盛受国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 ”[2]《吴越春秋》又载: “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3]《宋史》记载: “ 废州(思州) 为城,及务川县,以务川城为名。 ”[4]有关 “ 市 ” 的记载在《易·系辞》有: “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5]而 “ 城市 ” 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其记载云: “ 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 ”[6]可见,古代文献大都是将城和市分开而定, “ 城 ” 主要是作为城堡, “ 市 ” 反映的是货物交易。
明代贵州建省以前,城市数量寥寥无几,且文献记载不详。直到明清,伴随着贵州建省及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贵州城市建设得以快速发展,留下诸多历史文献,对此学界研究颇多。为系统梳理贵州城市史和学界研究成果,服务西南山地城市建设,笔者拟将贵州城市史研究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简称建国前) 贵州城市历史文献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简称建国后) 明清贵州城市研究概述等加以分述之,以求教学界方家。
一、建国前贵州城市历史文献概述
贵州城市发展相较内地而言,是先有城后有市,这样的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朝廷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军事重镇。因此,要了解贵州的城市发展,就很有必要对涉及贵州城市发展的历史文献进行认真梳理,了解其基本情况。费孝通将 “ 传统中国的城市形态分为两种类型:一为城镇,一为集镇。前者筑有城墙,内有衙门与驻军,是区域内的一个行政中心;后者没有城墙,内有商店和作坊,是区域内的一个经济中心。 ”[7]从贵州城市发展情形来看,应为费孝通所提及的城镇类型。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腹地,明以前分属湖广行省、四川行省、云南行省、广西行省统辖。相传明代以前在今贵州境内的城市,有古牂牁郡城,在 “ 思州一百八十里,即汉未伏时所保于此 ”[8],竹王城 “ 在杨老驿东十里 ”[9]等。当时贵州的城市大都很简单,即城市只有军事防御功能和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不突出。
明永乐年间,朝廷基于巩固云南、稳定西南的战略考虑,对思州、思南两土司改流后,就其领地置贵州省,从此,贵州城市始见规模。据资料记载,有明一代,贵州府一级的城市(不包括同城城市)有6 个:即思州府城、石阡府城、思南府城、铜仁府城、乌罗府城(后废,在今松桃县境)、新化府城(后废,在今锦屏县境);县一级的城市(不包括同城城市) 有永从县城、施秉县城、定番州城、麻哈州城、独山州城、瓮安县城等18 个;卫所城(不包括同城城市) 有毕节卫城、龙里卫城、新添卫城、兴隆卫城、层台卫城、偏桥卫城、赤水前所城等48个。以上诸城市,由于贵州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的是府卫同城,有的是州卫同城,有的是卫司同城。如贵阳府城,与贵州卫、贵州前卫同城;普定卫与安顺州同城;镇宁州城与安庄卫同城;永宁州城与安南卫同城;普安州城与普安卫同城;都匀府与都匀卫同城,平越府与平越卫同城,黎平府城与湖广五开卫同城;镇远府城与湖广镇远卫同城;清平县城与清平卫同城;永宁卫城与四川永宁宣慰司同城;乌撒卫城与四川乌撒府同城;乌撒后所与云南沾益州同城。
此时的城市营建,多为防御,以保护城内居民,稳固人心。(万历) 《贵州通志》卷一载: “ 春秋凡城必书城之重也,黔在万山中,为诸夷窟穴,则高城深池以为捍卫,……语曰众心成城,守土者宜深呼之矣。 ”[10]地方志为明代贵州城市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价值,在(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 《贵州通志》、(嘉靖) 《普安州志》中都有营建部分,记载了城墙的变迁和功能,山水、城市间驿道状况以及学校、官署、坊市、寺庙等在城市的分布。我们可以从记载中大致得知明代贵州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状况。郭子章的《黔记》对明代城市的城墙和城市安全性记载非常详细,并且以较为精准的地图绘制了当时城市的形状、城市形胜以及建设的状况。
官修文献对研究明清贵州城市亦具有很大的作用,如《明实录》 《明史》 《大明一统志》等详细地记载了城市行政等级情况,是研究城市行政变化等级的重要资料;《明会典》对城市建设的制度也略有记载,是书卷一百八十七载: “ 凡各处城楼,窝铺,洪武元年,令腹里有军城池每二十丈置一铺,旁近城每十丈置一铺,其总兵官随机应变增置者,不在此限,无军处所有司,自行设置,常加点视,勿致疏漏损坏,提调官,任满得带相沿交割,违者治罪。 ”[11]
游记是研究明代贵州城市的重要补充,如《贵州名胜志》 《广志绎》 《徐霞客游记》等。《贵州名胜志》多侧重于贵州山水的描写;《徐霞客游记》记载了民居以及民间风俗情况。这些典籍对城市的记载较为微观。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诸书所附地图对明代城市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清灭明后,在城市建设方面对明朝制度多有沿袭,但也做出了较大的调整,主要是裁卫并县;改土归流;少数民族地区直隶厅城,直隶州城,厅城的设立;其他省份城市的并入;兴义府城及其下辖城市的调整。通过调整,府一级的城市有14 个,即贵阳府城、兴义府城、安顺府城、大定府城、遵义府城、黎平府城、都匀府城、石阡府城、镇远府城、思南府城、思州府城、铜仁府城、平越直隶州城、松桃直隶厅城;县一级的城市63 个,主要有开泰县城、都匀县城、罗斛厅城、定番州城、永宁县城(雍正八年,割永宁县城归四川)、锦屏县城(道光十一年改县为乡隶开泰县) 等。需要注意的是,清朝通过裁卫并县后,由卫改成县一级城市较多,如龙里卫城裁为龙里县城,平溪卫城裁为玉屏县城,清浪卫城裁为青溪县城等,共计26 座。
同样,清代地方志是研究贵州城市的重要文献。清代地方志相较于明代的记载更为详细,除了有整个省的通志编撰外,还有具体到一个府或县的方志编撰,较明朝更为丰富,对城市的城墙、官署、学校、坛庙、寺观、山水、城市之间的驿道等记载更为具体、微观,而且无论是文字记载还是地图的绘制,都已经具体到城市建筑的内部建设,进而还记载了城市的发展状况。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清实录》 《清史稿》等对城市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清史稿》对贵州城市用 “ 冲、繁、疲、难、要、简 ” 进行标注,可以清晰地了解各个城市的战略地位;《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详细地记载了明清城市的来源,很多已经追溯到隋唐时期,资料弥足珍贵。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较为准确,清晰地绘制了明清贵州的疆域,同时也绘制了城市(治所) 的一些位置,可以宏观地了解整个贵州的城市位置情况。
民国时期文献对明朝和清朝的贵州城市均有记载,且更为清晰和详细,可做研究明清贵州城市史的重要补充资料。如(民国) 《贵州通志》 (建置志) 记载了明清时期贵州城市的来源、变迁、规模、迁址,甚至城市人口,而对于城市内部的微观建筑,如寺庙、学校、公署、牌坊、街道等,已经更为详细和系统。此外,相关的民国文献还有(民国)《八寨县志稿》、 (民国) 《施秉县志》、 (民国)《独山县志》、(民国) 《大定县志》、(民国) 《岑巩县志》、(民国) 《玉屏县志资料》等。
清至民国时期文献都较为精准地记载了贵州明清城市的发展情况,对于探讨贵州城市变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涉及怎样在喀斯特地貌的民族地区选址、考虑后勤补给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多讲究。因此,系统整理并归类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笔者要展开贵州城市史文献梳理的首要原因。正因为有这样的资料记载,再检索建国后有关明清时期贵州城市的研究成果,就能做到理解自如。
二、建国后明清贵州城市研究概述
如前所述,关于明清贵州城市发展的文献资料丰富,建国后引起了学人的关注,刊出成果较多。笔者根据成果研究的对象,将其分为四类,分述于下。
(一) 明清贵州府、州、县、厅城市研究
建国以后对明清贵州府、州、县、厅城市建置之研究成果颇多,主要有蓝勇的《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的地理演变》[12]、杜佳的《黔中喀斯特山区屯堡聚落空间特征研究》[13]、杨光的《中国山地城市空间形态调查研究》[14]、徐毅等的《清代前期西南改土归流地区的城市治理初探——以云南、广西和贵州为中心的考察》[15]、杨永福等的《论元明时期的 “ 入湖广道 ” 与滇、黔政治中心的变迁》[16]、曹端波的《国家、通道与市镇:历史时期贵州的对外交通与市镇分布》[17]、张建的《明清贵州城镇的形成及其对当今贵州民族地区发展的启示》[18]、韩笑等的《论清代遵义复式城市的形成》[19]、范松的《试论明朝时期的治黔方略与黔中城镇建设》[20]、杨旭等的《明代贵州治所城市的修筑及布局刍议》[21]等等。
蓝勇文中以 “ 冲、繁、疲、难、要、简 ” 来规定西南城镇等级,并指出贵州城镇的分布特点,较大的城市只分布在贵州军民府附近。徐毅等一文没有专门对贵州城市进行具体分析,而是对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的总体情况进行考辨,并将三省改土归流地区的城市体系分为三个等级, “ 地区性的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 。张建则从军事战略的视角分析了贵州建城的原因,由于贵州所处军事地理位置特殊,为联结云南以及中原地区之纽带,故建城原因就是为了维护云南地区的稳定。杨旭则是从地理学的视角对贵州城市分布状况进行探究,非平原类城市主要分布于湖泊及河流冲积平原地带,由于贵州省多为喀斯特地貌,故城市为避免地势之不平,主要分布于地势平坦的坝子地带。
此外,关于明清贵州府、州、厅、县城市建置的相关著述有周春元的《贵州古代史》[22]、方铁的《西南通史》[23]、李孝聪的《历史城市地理》[24]、范松的《黔中城市史:从城镇萌芽到近代转型》[25]、罗建平的《安顺屯堡的防御性与地区性》[26]等。李孝聪在其著作《历史城市地理》中提到,明清贵州城市就规模而言,相比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处于落后状态;范松的《黔中城市史:从城镇萌芽到近代转型》对黔中城市尤其是安顺、贵阳、遵义的建设、经济、文化发展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同时整理了明清黔中城市的来源。而建国后的地方志中,如《贵州省志·地理志》[27]《遵义市志》[28]《修文县志》[29]等,在其城镇描述中对明清贵州城市多有提及,尤其是城市的来源和变迁,并且以现代科学的手段论述了城市所处具体位置的地理环境,如河流阶地、河谷平原等。这在明清历史文献中是没有提及的,但现代方志主要论述对象为现代城镇,对明清城市的论述也只是一笔带过,不成体系,也不够详细和完整。
学界对明清贵州城市尤其是城市的建设和选址方面的研究颇多,且对明清以前城市的考证也较为全面,但并没有一个专门和系统的研究。大多数以西南地区为总体宏观对象进行研究,或者是对明清贵州城市某个区域、某个方面进行研究,有的只是在描写近代城市或者现代城市之时一笔带过,城市的行政等级也并没有详细的研究。
(二) 明清贵州卫所城市研究
卫所制度作为明朝首创的一种军事制度,对其军事安全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在明朝,很多地方都广设卫所,贵州也不例外。卫所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城市之性质,只是府、州、县、厅城市相较于卫所城市,商业功能更为显著,而卫所城市以军事防御功能为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涉及明清卫所城市建置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主要有覃朗的《明代贵州都司卫城浅述》[30]、陈国安等的《试论明代贵州卫所》[31]、钟铁军的《释明代贵州之 “ 州卫同城 ” 》[32]、马国君的《明清时期贵州卫所置废动因管窥》[33]、吴才茂的《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形成研究》[34]、汤芸等的《从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看贵州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7]、肖秀娟的《明清贵州卫所变迁及其影响研究》[35]、罗婷的《 “ 一线路 ” 上明代屯田研究——以贵州普定卫为例》[36]等。
覃朗指出明代贵州卫所之建立是为了维护贵州的驿道安全,卫所的分布亦具有独特性,主要在依山傍水的险要之地,或是在控制要道的关键之处,同时也论述了贵州卫所城市的城墙、护城河以及卫所城池内的微型建筑。陈国安提到了贵州卫所城镇以及府、州、县城镇在地理分布、职能以及物质形态方面的不同,卫所城镇之设立位置为贵州驿道附近,其目的为维护驿道之稳定,具有军事性质,而府、州、县城镇的主要职能则是理民和理苗,其分布地在苗区腹地。马国君指出明代贵州卫所的设立是为了防止蒙古,而卫所也改变了贵州的政治形势。值得一提的是, “ 清代一方面在进行‘裁卫并县’,但在一些偏远的地区,清朝还不得不增设‘卫所’以资控制 ” 。吴才茂总结了由卫所变为城池的机制和表现,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由军城演变而来的城池,主要呈现点状和线状的分布;二是卫所开始商业化,从而发展成为具有经济功能的城市。
学界对卫所的研究非常深入,尤其是明朝卫所设置及清朝裁卫并县,包括卫所的选址,但是具体到卫所城市的研究则着力不深,而且对于卫城以及城市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梳理,特别是清朝在疆域调整之时引起的城市变化,对明朝城市或继承、或废弃、或转变几乎没有关注,值得学界注意。
(三) 明清贵州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研究
明清贵州城市史研究对明清贵州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着力较多。研究成果主要有李储林的《明清贵州江西会馆地域分布及形成机制探析》[37]、许桂灵的《秦汉至明清时期西南地区交通发展与沿线城市商业贸易》[38]、朱泽坤的《清代贵州集市研究》[39]、杜莹莹等的《清至民国时期贵州马铃薯的种植与影响》[40]、颜勇等的《发展迅速的清代黔中社会》[41]、黎帅的《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研究(1644-1840 年)》[42]、蒋德学等的《明代贵州建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43]、李婧的《14 世纪中期至19 世纪中期贵州思南府的社会发展》[44]等。
会馆是反映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李储林提到明朝贵州城乡已出现会馆,而到清朝,会馆这种组织已达到鼎盛,作为一种维护同乡关系的纽带遍布贵州各个城市,尤以江西会馆居多。许桂灵一文提到明清时期贵州商业贸易,北部遵义主要与四川贸易;东部地区则主要是湘、赣商人;黔东南地区以两广地区商人居多。朱泽坤认为清朝贵州城市经济相比之前有极大提高,主要体现在集市数量及次数的增多、时间的提前、规模的增大。杜莹莹认为马铃薯这一经济作物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以及经济的发展,如开阳县除自己食用之外, “ 将粉条、淀粉等马铃薯加工品远销贵阳、重庆、四川等地 ” 。黎帅以清代黔东北为对象,梳理了黔东北各府县的建城史以及河流道路等。
明清为贵州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不仅体现在当时经济的繁荣,文化发展亦有明显进步。关于明清贵州城市文化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有:刘淑红的《试论明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书院教育》[45]《明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儒学提学官制度》[46],李伟等的《论明代贵州教育的发展概况》[47],宋荣凯的《论清代贵州义学教育的创建、办学性质及功效》[48],冉诗泽的《改土归流与土司的国家认同研究——以贵州草塘土司宋氏为例》[49]等。
刘淑红在《试论明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书院教育》中提到了明代贵州城市的文化教育,指出王阳明对明代贵州教育有巨大贡献,如将中原文化传播到贵州、创办书院、阳明心学促进了贵州的讲学之风;在《明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儒学提学官制度》中提到贵州建省之初,并没有设立按察司副使来管理学政,其学政由云南管辖,直到弘治十六年(1504 年),贵州自己的提学官才始有规模。李伟着重论述了明代贵州教育 “ 向社会各个等级、各个民族开放,对学生的等级身份限制几乎消失殆尽。 ” 可以看出,明清两代贵州教育逐步发展,不同于前代的精英教育,已经普及到寒门子弟。以宋氏土司为例,冉诗泽指出改土归流之后,人口大量迁入 “ 改变了该地区的人口社会构成,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和经济、商贸恢复与发展,也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繁荣 ” 。
此外,涉及明清贵州城市发展状况的著述主要有何仁仲的《贵州通史》[50]《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教程》[51]、李振纲等的《贵州六百年经济史》[52]、郭长智等的《贵阳城市发展史》[53]等。何仁仲在《贵州通史》一书中的部分章节描述了明清时期贵州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及传统建筑和城堡建筑。他在另一篇著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教程》中强调,明朝贵州交通获得极大的发展,相继开通了多条道路,如关索岭古道、赤水卫乌撒道等,促进了贵州商业的发展,形成了当时较大的城镇,如贵阳、南笼、都匀、毕节等。
关于贵州经济、文化的研究,学界在物产、移民、交通、文化制度、学校等方面都着力较深且详细,但研究主要是针对一个区域展开的,对城市的研究仅仅也只涉及经济层面,其他社会方面,尤其是宗教这类人们精神层面的改变涉及较少。
(四) 其他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研究。如郭渐翔的《贵州城镇史迹一贵阳名称朔源》[54]、李旭的《西南地区城市历史发展研究》、胡振[55]的《明代贵州军事地理研究1368—1644》[56]、高莉娜的《明清古镇的奇葩——贵州省黎平县德凤古城的保护与规划建设》[57]、覃影的《边缘地带的 “ 双城记 ” ——清代叙永厅治的双城形态研究》[58]、严奇岩的《从林木种类变化看明代以来贵阳森林资源的变迁》[59]、贾亭立的《明代筑城的串楼初探》[60]等。胡振指出贵州城池建设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修建卫所军城为主;第二个阶段是在贵州建省之后,城池建设由之前的修建卫所军城为主转化为修建府州县城为主;第三个阶段是万历年间平播之后,贵州的府州县邑城和卫所军城一起并建。覃影探讨明清两朝叙永厅双城的变迁以及插花地问题的解决,从而反映了清朝中央王朝管理体系的脉络以及不断调适的过程。严奇岩论述了明代到民国时期贵阳的森林变迁,其中提到贵阳杉木在清朝时期明显减少,其原因之一就是用于贵阳的城市建设。贾亭立则是对明代串楼的分布及功能进行了探究,认为串楼这一城墙的微型建筑主要分布于南方,贵州亦有, “ 从地理条件来看,串楼分布的地区属山地地形,较少黏性较强、适合筑城的土料。从气候条件上看,这一地区的降水量偏大,年均降水量多在1 400 毫米以上,是全国多年平均降水量(约648毫米) 的2 倍以上 ” 。
从以上研究成果看,学界对明清贵州城市的探讨已涉及环境与城市的关系、同城现象的产生、城市城墙微观建筑诸多方面。研究成果虽多,但并没有形成一部系统的贵州城市史研究专著,故对其展开进行探讨,对于丰富和完善西南史地研究有重要价值。
三、小结
自明朝贵州建省后,贵州开始有规模地建城市,贵州城市发展离不开中原移民的建设,同样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更离不开贵州省广大人民在这片土地上洒下的汗水。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学界对明清贵州城市有诸多研究,并留下了不少著述,这是我们现在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通过对贵州城市史文献即学界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对明清贵州城市的研究呈现出多领域、深层次的特点,尤其是在城市的选址、建设以及经济的发展等方面,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对明清贵州城市并没有一个整体的、系统的研究。要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学界需重视以下几点:第一是需要加强贵州城市史整体研究。学界对明清贵州的某一个城市,或者是以西南地区城市为宏观对象的研究较多,对整个贵州城市发展并没有系统的研究。第二是卫所城市与治所城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界对于此领域并没有进行系统清晰的梳理,缺少对两者间的功能转化研究。第三是历史上的城市发展必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宗教等诸多方面,而从学界刊发的成果来看,对贵州城市的发展状况研究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其他领域的研究显得明显不够,故也难以彰显贵州城市建设在西南的战略地位。第四是贵州处于西南地震带,72%以上的地区为喀斯特地貌,生态系统较为脆弱,且地质灾害频繁,这也是展开贵州城市史研究需要注意的重要方面。明清是贵州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其城市建设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生态背景直接关联,因此展开贵州城市史研究,就需要多角度、多层次,展开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服务于今天西南山地的城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