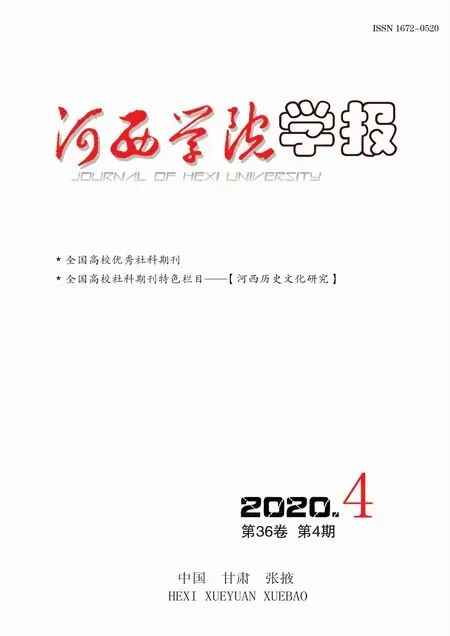《广韵》《集韵》所见河西地名异写考校九则
2020-01-17何茂活
何茂活
(河西学院文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河西地区古代地名异写较多,有的不为学者所知,有的形音关系复杂,令人疑惑。今以《广韵》《集韵》这两部韵书为出发点,选取九例,试作简单考校,借以观察这些异写的形成及传承使用情况。同时,也以此为视角,对这两部韵书的体例特点试作对比。
一、溺水
溺水,即弱水。《广韵·药韵》而灼切:“溺,水名,出龙道山。其水不胜鸿毛。”[1]502《集韵·药韵》日灼切:“溺,《说文》:‘水,自张掖删丹西至酒泉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桑钦所说。’”[2]1484
按:溺,是“弱水”之“弱”的加旁分化字,但后世不从,仍作“弱”。上引《广韵》所释“出龙道山”,“道”为“首”之误。龙首山,位于山丹县西北部,当地人称“龙头山”。清戴震《水地记》:“大通河源,为甘肃凉之祁连、合黎、龙首、焉支等山。”自注:“龙首山,在山丹县西北二十五里边外。”[3]412道光本《山丹县志·山川》:“龙首山:城西北三十里,一名甘凌山,俗名北山。《通志》曰:‘甘凌,又名甘峻。山阴有泉,旱祷辄应。内石洞三,有龙眼石,土人以晦明卜岁焉。’”[4]77-78按:甘凌,实为“甘浚”之讹。①
查《广韵》诸本,“溺”下“龙首山”之“首”皆作“道”,周祖谟《广韵校本》、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及蔡梦麒《广韵校释》等均未出校。这一讹误,影响了后世多种韵书,《五音集韵》《洪武正韵》等均相沿而讹。《集韵·药韵》“溺”字条下引录《说文》,文字无出入。
沉溺之“溺”本作“㲻”。《集韵·锡韵》乃历切:“㲻,《说文》:‘没也。’或作溺。”此义之“溺”与柔弱之“弱”,古音相近,意义相通。汉刘熙《释名·丧制》:“死于水曰溺。溺,弱也,不能自胜之言也。”清毕沅疏证:“《说文》‘溺’即《禹贡》之弱水。然则‘溺’固有‘弱’音,故此以‘弱’训‘溺’。”[5]407可见“弱水”写作“溺水”,不仅是字形上的加旁繁化,而且在字音字义上也有同源孳乳关系。明人田艺蘅的《留青日札·三弱水》说得更清楚:“东海中有弱水,不胜鸿毛,至则必溺,故名。又,西海中亦有弱水。西海,今西宁卫西三百里,弱水在甘州之西。”[6]360
二、潶水
潶水,即黑水。《广韵·德韵》呼北切:“潶,水名,在雍州。”[1]529《集韵·德韵》迄得切:“潶,水名,出黑山西。”[2]1576
按:“潶”字的成因与上条所论“溺”字相同,属加旁区别字,但后世流行不广。《正字通·水部》对此有辨析:
潶 旧注:“音黑,水名,在雍州。”按,《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自郑玄、郦道元,皆不能知黑水所经之处。汉《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未详其地。独杜氏《通典》,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岭百里,方圆七十里,东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东,号曰漾濞水,又东南入会川为泸水。泸水即黑水。本作黑,旧注黑讹作潶,谓水在雍州,并非。[7]40
《正字通》的主要观点有二:其一,“潶”是“黑”的讹字。这一观点大体可取(准确地说应当是加旁分化字,或曰俗字,而不应称为讹字)。该书羊部“”字条下也说:“,俗字。黑羊作,误。与水部黑水作潶同。”[7]281可以参考。其二,认为旧注说黑水在雍州是错误的。这一说法欠妥。《正字通》只注意到了《禹贡》中的“华阳、黑水惟梁州”,但没有注意到《禹贡》中还有“黑水、西河惟雍州”之句。因此说黑水在雍州,并无错误。事实上,黑水所流经的张掖等地古属雍州,与《禹贡》所述是吻合的。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上文所述字书韵书中对“潶”的收录和考辨以外,历代典籍中鲜有对此字的使用。可见在汉字发展过程中,既会通过添加形旁明确义类,从而产生新字,也受趋简求易心理的影响,限制上述新字的滋生与传播。在这种矛盾和制衡中,汉字总量的增长总是有所节制的。
三、甘峻
甘峻,山名。山在张掖,为甘州得名之由。《广韵·谈韵》古三切:“甘,《说文》作,美也。又陇右州,本月支国,汉匈奴觻得王所居。后魏为张掖郡,又改为州,取甘峻山名之。界有弱水、祁连山,上有松栢五木,美水茂草,冬温夏凉。又有仙树,人行山中,饥即食之辄饱,不得持去,平居时亦不可见也。”[1]223-22《4集韵》“甘”字头下注释简略,无此内容。
甘峻,亦作绀峻,今多作甘浚。明李贤《明一统志》卷三七:“甘浚山,在都司城西南八十里,有泉甘冽,因名,又名绀峻。”[8]940清赵一清《水经注释·河水二》:“《太平寰宇记》甘州张掖县下云:‘甘峻山,一名绀峻山。《水经注》云:张水历绀峻山南与张掖河合,即鲜水也。’今本无之。”[9]4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十二·甘肃行都司》:“甘州左卫,本匈奴昆邪王地,汉置张掖郡,取张国臂掖之意,后汉因之。晋仍为张掖郡。西魏置甘州,取州东甘浚山为名。隋、唐因之,亦曰张掖郡。”[10]2973-2974今张掖市甘州区有甘浚乡。
此外,本文第一节所引道光《山丹县志》例,谓龙首山一名“甘凌”,又名“甘峻”。今按“甘凌”实为“甘浚”之讹。乾隆《甘肃通志·山川》载:“甘浚山,在(山丹)县西北三十里,延袤至甘州,一名甘峻山,俗名龙头山。山阴有泉,旱可祷雨。”[11]220清许鸣磐《方舆考证》卷四十对此曾有讨论:“《明统志》:‘甘凌山在山丹卫西北,连亘甘州,中有三石洞,其下有泉,岁旱于此取水,祷雨有应。’按其方位,正古甘竣山也。而《明统志》以为甘凌山,乃别载甘竣山于都司城西南八十里。《方舆纪要》因之并误。”[12]据此可知,甘凌、甘浚实为一山,“凌”当为“浚(竣、峻)”的形讹。
五、番和③
番(pán)和,为汉代所置之县。据《汉书·地理志下》,张掖郡辖县十:觻得、昭武、删丹、氐池、屋兰、日勒、骊靬、番和、居延、显美。其中番和为农都尉治。后世亦名番禾。《辞源》“番和”条释义:“郡、县、镇名。汉番和县,属张掖郡。晋改番禾,属武威郡。南北朝皆置番和郡。北周废郡置镇。唐天宝中改为天宝县。”[16]2809
《广韵·桓韵》薄官切:“縏,番和,县名,在凉州。”按:此条有误,脱漏了“縏”的释义和“番”的字头。余迺永改订为:“縏,小囊。番,番和,县名,在凉州。”[1]126是。
《集韵·桓韵》蒲官切:“番,番和,县名,在张掖郡。”[2]310
《集韵》与《广韵》对“番和”的辖属关系表述不同,但也各有依据。《广韵》依据的是当时的建置情况,《集韵》则重在存古溯源。从这一点看,《集韵》与《广韵》的编辑原则有明显不同。
关于番和为何要改名为番禾,我们暂未找到确切的理据,但关于唐代将番禾改名为天宝县之事,《旧唐书·宣宗本纪》有如下记载:“三月庚午,武威郡上言:番禾县天宝山有醴泉涌出,岭石化为瑞麰,远近贫乏者取以给食。改番禾为天宝县。”[17]218时在天宝年间,如此上言并更名,颇有谀上之嫌。
番禾,亦作蕃禾。《宋史·外国传·吐蕃》:“河西军即古凉州,东至故原州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吐谷浑、兰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界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周回平川二千里。旧领姑臧、神乌、蕃禾、昌松、嘉麟五县。”[18]14155
六、丽靬
丽靬,即骊靬,汉代县名。《说文·革部》:“靬,干革也。武威有丽靬县。”[19]60《说文》中“丽靬”的写法,在《广韵》中未见承袭,但在《集韵》中则有之。《集韵·翰韵》墟旰切:“靬,《说文》:‘靬,干革也。武威有丽靬县。’”[2]1142这种写法在正史中亦有所见。《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傉檀大悦,释其缚,待之客礼。徙显美、丽靬二千余户而归。”[20]3147
但在历代典籍中多作“骊靬”,《广韵》《集韵》亦有存录。《广韵·元韵》居言切:“靬,干革。又骊靬县,在张掖。”[1]115《集韵·元韵》居言切:“靬,干革也。一曰骊靬,县名,在张掖。”[2]281又《脂韵》陈尼切:“骊,骊靬,县名,在张掖。”[2]93
据《集韵》“陈尼切”的注音,“骊靬”之“骊”当读chí。《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骊”下均如此处理。但是此字为何有此读音,令人疑惑。
其实关于“骊靬”的读音,古今学者早有讨论。《汉书·地理志下》张掖郡所辖县“骊靬”下,李奇曰:“音迟虔。”如淳曰:“音弓靬。”④颜师古曰:“骊音力迟反。靬音虔是也。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13]1613岑仲勉先生认为:“读骊如迟,必汉代西北方言如是。师古之力迟反,谅只就唐初音读而为注,不能据以改正李音也。”[21]186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依从《集韵》(亦即信从李奇说),可以算是比较慎重的做法。但是从其异写形式“丽靬”来看,我们认为颜师古之说更为可取,即仍如字读“力迟反”(lí)。再者古人多认为“骊靬”与西域黎靬(又作犛靬)国亦即大秦国有关,如此则更可证明“骊”不读chí。
又有作“轢德”者。清顾炎武《肇域志》卷四二:“觻得县,《汉书》觻作鱳,又作轢德。在郡西九十一里。”[23]1527乾隆《甘肃通志·古迹一》载:“[觻得故城]《地理志》:张掖郡,故昆邪王地,太初元年开,治觻得县。孟康曰:鱳音鹿。按:《汉书》觻作鱳,又作轢得。”[11]600
八、乐㴦
汉代酒泉郡有乐涫县。《说文》:“涫,也。从水,官声。酒泉有乐涫县。”[19]235这一写法后世广有传承。《广韵·桓韵》古丸切:“涫,乐涫县,在酒泉。”[1]125《集韵·桓韵》沽丸切:“涫,《说文》:‘也。酒泉有乐涫县。’”[2]307清顾炎武《肇域志》卷四二:“乐涫县,在卫西二百里,汉置。前凉改为建康郡,唐为军,今名骆驼城,立高台所。”[23]1527
但乐涫之“涫”,或亦讹作“㴦”。《广韵》《集韵》均收录有这一讹字。《广韵·东韵》居戎切:“㴦,县名,在酒泉。”余迺永校注:“《汉书·地理志》酒泉郡有乐涫县。涫字误作㴦而有是音,当删。”[1]25《集韵·东韵》居雄切:“㴦,县名,在酒泉。”[2]27《汉语大字典》引方成珪《集韵考正》:“‘㴦’乃‘涫’之讹。前后《汉志》可证。此沿《篇韵》而失考也。”[24]1831
查古代史籍,确有将“乐涫”讹作“乐㴦”者。唐李林甫《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禄福县]本汉乐㴦县,属敦煌郡。后魏太武帝平沮渠茂虔,改县为戍,隶敦煌镇。孝文帝改为乐㴦县。”[25]对此,张驹贤所作考证以《汉书·地理志》为据,指出“㴦”为“涫”之误。并说:“《广韵》《集韵》两名并收,殊少别择。敦煌宜作酒泉,方与《地理志》合。”[26]1181由此可见,《广韵》《集韵》所收“㴦”字,并非一个简单的形误之字,它也是有一定的文献依据的。当然如果加以“别择”,安排在“涫”字头下作为异体,而不是按其声旁“宫”收列于东韵,那样会更为妥帖。
此外,“乐涫”还有写作“泺涫”者。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二四:“唐于泺涫古城置福禄县,盖从《续志》名也。”[22]396“泺”系受“涫”感染而误增“氵”旁。这种情况,是汉字俗字、讹字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九、燉煌
燉煌,亦作焞煌,今作敦煌。《说文·水部》:“河,水,出焞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19]224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水部》:“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源注海”;“《汉书》云:‘燉煌本酒泉地,《春秋左传》所谓允姓之戎所居瓜州也。发原独至于海,故曰渎。’”[27]213王筠《说文系传校录》认为大徐本作“焞”和“燉”是讹字:“大徐‘敦’讹‘焞’,本书引《汉书》又讹‘燉’。”[28]526其实这样的写法在历代典籍中并不鲜见,不必视为讹字。如《汉书·张骞传》:“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唐颜师古注:“祁连山以东,焞煌以西。”[13]2691-2692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中说:“敦煌在文献记载及金石刻辞中,无作焞煌者(如《裴岑纪功碑》《曹全碑》,敦煌、居延两木简之类)。本文盖为当时别体。”[29]322其中认为“敦煌”在文献及碑刻中无作“焞煌”者,未免失之武断,仅《说文》与《汉书》即可为其明证。
上述异写也存录于《广韵》《集韵》中。《广韵·魂韵》徒浑切:“燉,火炽。又燉煌郡,燉,大;煌,盛也。”[1]117“燉煌”之名在《广韵》中凡12见,除此例以外,其他均见于姓氏及地名用字的释义中。《集韵·魂韵》他昆切:“燉,火色也。一曰,燉煌,郡名。”[2]294又徒浑切:“敦,大也。一曰敦煌,郡名。”[2]296
《广韵》与《集韵》二者比较,前者未见敦煌之名,而燉煌之名出现达12次;后者二名俱见,各有一例。前者对姓氏、地名注解比较详细,而后者这方面内容极为简略。可见《集韵》对《广韵》虽有继承,但在体例方面调整变化很大,对姓氏、地名等不再作详细解释。
以上我们对见于《广韵》和《集韵》的九个地名异写作了简单考校。通过考校,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古代地名,异写纷呈,有必要进行系联比证。通过比证,可以解决音义方面的疑难问题,如通过“骊靬”与“丽靬”甚至“黎靬”的联系,可知“骊”音chí之不可信。
第二,添加类化符号亦即累增意符是产生地名异写的一个主要原因,如:弱—溺,黑—潶,番—蕃,乐—泺,敦—燉。其中后两例,“乐”因“涫”而成“泺”,“敦”因“煌”而成“燉”,系受同词另一音节字形感染而累加意符。
第三,《广韵》与《集韵》虽然都是宋代官修韵书,后者比前者晚出三十年,但是二者之间在编辑体例上有明显的差别。从本文所举诸例来看,《广韵》收列文字的形音义较为精要,所录又音及异体较少,而《集韵》则务求赅广,因此颇显繁细。如“骊”,《集韵》收录的又音“陈尼切”就不见于《广韵》。《广韵》对姓氏及地名用字,尤其是姓氏,注解过繁,显得很不平衡;《集韵》克服了这一缺点。《广韵》释义多采取综合概括的方法,而《集韵》释义以《说文》为依据,保留故训原貌,在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参考价值。当然二者各有特点,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我们注意体会并合理利用。
本文曾于2019年10月在甘肃高台参加骆驼城与五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讨论,承蒙冯培红教授、崔云胜教授等多位学者惠示高见,谨此致谢!文中仍有浅陋疏误之处,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注释:
①详参下文“甘峻”节所引《甘肃通志》等。
②本节讨论中所说的“朴”“扑”,古籍中实为“樸”“撲”。下文“丽”“骊”“泺”,古籍中实作“麗”“驪”“濼”等,恕不一一说明。
③本条讨论的情况与其他各条不太相类。其他各例是见于《广韵》《集韵》的地名“异写”,而本条的“番和”是汉代所设县名的正常写法,“番禾”是后代所改之名,只有“蕃禾”是真正的“异写”。但宽泛地说,也算一个地名的不同写法,所以也放在这里一并讨论。
④如淳所谓“音弓靬”,是说“靬”音“弓靬”(意为弓衣)之“靬”,而不是说“骊靬”读作“弓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