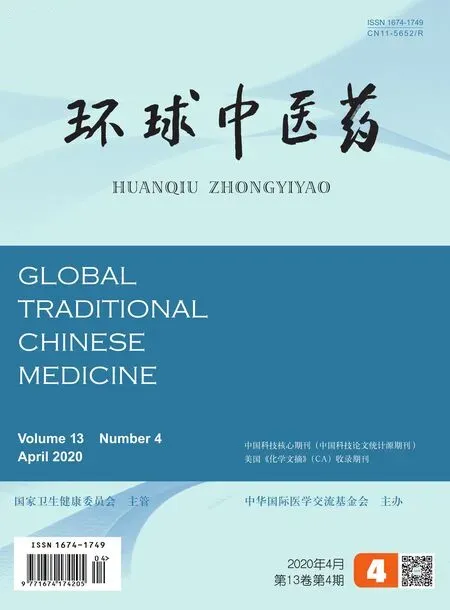脾主运化理论的演变
2020-01-11王启航陈萌
王启航 陈萌
中医藏象理论认为,脾有三大功能:脾主运化、脾统血、脾主升清,其中又以运化功能为核心,其内涵为:脾具有把饮食物化为精微,并将精微传输至全身的生理功能,即脾主管人体对饮食物的消化吸收[1]。而实际上,在中医理论的奠基著作《黄帝内经》之中并无“脾主运化”之语。脾主运化的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秦汉:脾者裨也,脾助胃气。(2)汉唐:脾主消磨,磨而消之。(3)宋元:脾主运化,重脾轻胃。(4)明清:脾主运化,胃纳脾运。随着时代发展,脾功能逐步扩大并整合了消化系统的部分功能,脾与胃肠道的关系发生改变,脾之解剖学基础也变得模糊不清。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整个藏象理论的迁延,也深刻影响了临床治法。
1 脾者裨也——秦汉
秦汉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它不仅在物质文明和疆土领域上为后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精神文明方面也是如此。诸子百家经历了相互抵制和争辩再到相互吸收融合至秦汉终于形成了以“实用理性”为特征的系统论宇宙图式,而中医理论正是这种系统论的最高成就和典型形态[2]。它具有如下特点:(1)形气相合,即不脱离物质探讨功能。(2)系统论,即不抛开联系谈作用。以脾主运化理论为例,这一时期的运化理论,概括而言,即以胃为主导,以脾胃为核心的整个消化系统承担人体对饮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功能。
《黄帝内经》中对此有丰富的论述,笔者概括为四个层面:(1)整个消化系统(脾与胃肠道)共同负责饮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如在《素问·六节藏象论篇》中脾与“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共称“仓廪之本”。《素问·经脉别论篇》则描述了饮入胃后脏腑配合将精气散布全身的过程:“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2)脾胃关系密切,共同构成消化系统的核心,在生理解剖上“脾与胃以膜相连”(《素问·太阴阳明论篇》);在生理功能上“脾主为胃行其津液”(《素问·厥论篇》),故脾胃共同主管饮食的消化吸收,如《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之言“脾胃者,仓糜之官,五味出焉”。(3)整个消化系统又以胃主导,故胃又称“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素问·五藏别论篇》)。后世又有“胃家”一说,以胃代指整个胃肠道,如《伤寒论》中“阳明病,胃家实是也”说的是整个胃肠系统的实证;“胃中有燥屎五六枚”说的燥屎在肠道。(4)虽然消化吸收功能由系统承担,但是落实到临床仍然要回到具体的脏器之上探讨治疗。如《素问·太阴阳明论篇》之言:“太阴阳明为表里,脾胃脉也。生病而异者何也?岐伯对曰:阴阳异位,更逆更从,或从内或从外,所从不同,故病异名也。”虽然脾胃关系密切但是由于其功能不同发病各异,治疗上也应区分清楚,此谓脾胃分治思想。
《难经》明确提出了脾助胃消化吸收饮食的解剖学基础,如《难经》之言:“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脾和散膏分别对应现代解剖学之脾脏和胰腺。现代医学认为脾脏是一个富于血供的实质性脏器,脾的组织中有许多称为“血窦”的结构,平时一部分血液滞留在血窦中,当人体失血时血窦收缩,将这部分血液释放到外周以补充血容量,此为“脾裹血”。而胰腺则是消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无法独立承担消化功能,且与胃的关系极为密切。胰腺同时具有内外分泌功能,其外分泌液为各种消化酶,进入胃肠道中,发挥消化饮食的作用,为各个脏器提供能量,此即“温五脏”之义也。其内分泌液则影响血糖浓度并进一步影响糖原的合成,即影响饮食物的吸收并影响人的食欲,此即“脾气通于口,口和则知谷味矣。”
《释名》之言“脾裨也,在胃下,脾助胃气,主化水谷”[3]很好地概括了这一时期的运化理论。该书虽然成书于西汉,但其原为探求事物名源所著,且去古不远,由此可见,“脾”字诞生之初,就是形容消化系统中一个辅助胃消化饮食的脏器[4]。综上所述,笔者将这一阶段的“脾主运化”理论特点概括为重胃轻脾。
2 脾主消磨——汉唐
汉末至唐,是中国的乱世,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地方武装割据,加之气候变迁冷期来临,瘟疫横行,这种时代条件决定了此阶段的中医学重实践而轻理论,方剂数量大为丰富,而较少有阐发理论的医家著述,如《伤寒论》《肘后方》等著作均能反映这一特点。而此阶段却出现了脾功能的一大演进——脾主消磨。
脾主消磨理论最早见于《金匮要略》“脾伤不磨”[5],它并非创见而是对原有理论的提炼和形象化,即将脾助肠胃消化饮食的功能形象化为“磨而消之”,这可能源于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以水为动力的石磨即产生于晋)[6]。这一阶段脾主消磨的理论特点仍然是重胃轻脾,生理状态下脾要依附于胃发挥其消磨水谷的作用,病理状态下脾胃相互影响。如《金匮要略·黄疸病》中,仲景认为黄疸病的核心病机是脾家湿热波及血分(“脾色必黄,瘀热以行”),但是治疗上兼顾胃家,如茵陈蒿汤及栀子大黄汤中用大黄和栀子。同时认为阳明病也可诱发黄疸如:“阳明病,脉迟者,食难用饱,饱则发烦头眩,小便必难,此欲作谷疸。”张仲景提出的这一理论对学界影响巨大,至宋以前,后学多依此说。如隋朝《诸病源候论》:“胃为水谷之海,脾气磨而消之。”[7]其后唐代之《外台秘要》也有相同论述:“胃为水谷之海,主受盛饮食者也,脾气磨而消之则能食。”[8]同时代的《千金翼方》载言“风入脾则脾不磨,肠鸣胁满”[9]论述了外邪伤脾引起脾主磨的功能异常进而导致的消化不良。
而此时并非只有一种声音,晋代王叔和提出了“脾主水谷”一说,且论述了脾虚可导致水谷不化,在其著作《脉经》之中有如下论述:“脾主水谷,其气微弱,水谷不化,下痢不息。”[10]这种说法在其时并未受到重视,但确为现代脾主运化理论的萌芽。叔和是太医令,医权贵多,其时士族权贵阶层多好“玄学”与“清谈”,与当时的医林风气相去甚远,这或许是叔和之说未受接纳的原因之一。
3 脾主运化——宋元
宋是中医理论的“爆发期”,大量现行的理论是首见于宋朝,诸如现代中医所言之“理法方药”的诊治层次,完整的病因病机学说等都是在宋朝建立完备的。这恐怕与大量士族阶层进入医学行业以及宋朝理学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11],这直接导致了中医藏象理论内核的演进,从重解剖重实践到重功能重思辨,而从“脾主消磨”到“脾主运化”的演变就能反映这种变化。
宋代严用和的《严世济生方》在现存的文献中最早明确出现“脾主运化”的文字,其内涵也与现行的脾主运化的内涵基本相同:“盖胃受水谷,脾主运化,生血生气,以充四体者也。”[12]与脾主消磨对脾助胃消化饮食的具象化不同,脾主运化似乎脱离了解剖实体,它是饮食物在人体的消化过程中经历的消化系统的功能之总和,是行而上之道,与之相对的胃家成为了单纯的装食物的“口袋”失去了消化吸收功能,是形而下之器。换言之,脾主运化整合替代了胃、大肠、小肠的消化吸收功能。故笔者将宋以后的脾主运化理论特点概括为重脾轻胃,以脾统胃。
不同于晋代叔和之言的反响平平,严用和的这一理论在学术界生根发芽,并影响了金元时期的脾胃理论。如张从正用“布化”来描述脾对胃中的饮食所化之精微输布的作用,“布”与“运”同义,与脾主运化十分接近,他在《儒门事亲》中写到“食入胃,则脾为布化气味,荣养五脏百骸”[13]。饮食物进入胃中,其后的消化与吸收功能皆属于脾之布化;朱丹溪亦是对脾主运化的功能论述比较明确的一位医家,其言:“脾土之阴受伤,转运之官失职,胃虽受谷,不运化,故阳自升,阴自降,而成天地不交之痞。”[14]论述了脾运失司所致的痞证。
但也有医家仍遵旧说,如张元素说:“脾者,土也,谏议之官,主意与智,消磨五谷”[15]。再如罗天益仍然强调胃在饮食消化吸收过程中的主要作用,认为脾只是辅助胃来消化水谷,其言“今寒湿之气,内客于脾,故不能裨助胃气,腐熟水谷”[16]论述了寒湿伤脾后脾不能助胃气消化饮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东垣作为重视脾胃理论的医家,在其著作《脾胃论》中仍未言及脾主运化,对脾胃消化功能的认识还是强调脾为胃“磨”谷,胃中化生的精微可转输于脾,其言:“夫脾者,行胃津液,磨胃中之谷,主五味也”;又言:“盖胃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17]。故笔者认为这一阶段虽然出现了脾主运化的理论体系和重脾轻胃的理论倾向,但是脾主消磨仍然是宋金元时期的中医的主流认识。
4 脾运胃纳——明清
明代情况再一次发生了改变,对外贸易的繁荣促进了中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1580年利玛窦来华,拉开了欧洲医学传入中国的序幕。对于十六世纪末的明代医家来说,他们可以接触到大量的欧洲医学知识,如《性学粗述》《泰西水法》中介绍的希波克拉底的四元素论,再如《主制群征》《泰西人身说概》带来的传承自古罗马的西方解剖学[18]。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知识不同于现代医学,它大量沿用古希腊、古罗马的认知,偏重书面理论和哲学思辨,仍然处于传统医学的阶段。因此不同于近代西医传入后对中医造成的巨大冲击,彼时的欧洲医学仅仅是拓宽了明代医家的视野,并使医家著作呈现出理论的系统化趋势。以王肯堂为例,作为利玛窦的好友,王肯堂的著作中吸纳了诸多西洋解剖学与外科法,但是他的本体论仍然是纯中国式的,并且较之前人,更为系统[19]。
这种时代条件使明代成为中医理论演变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其特征正是哲学思辨大量融入医学,中医理论系统化,其代表人物是张景岳。张景岳对阴阳五行作出完备的哲学描述,并以之诠释了《黄帝内经》,提出了完整的以五行配五脏为生理系统核心的藏象理论体系和完备的脏腑辨证方法,其深刻影响延续至今。对于脾藏象,在其著作《类经》及《景岳全书》中对其运化功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明确提出了脾运胃纳的消化吸收模式,如“脾主运化,胃司受纳”[20],再如“胃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21],脾主运化至此成为了学界的主流。清代御医黄元御、龚庭贤等人皆从此说,由于重视五行,重视中道,而脾之五行属土正居五行之中,这又进一步导致了脾功能的扩大。新中国兴办中医学高等教育,四版教材划定了脾的三大功能,并以脾主运化为功能之核心[22],往后的教材都依此说,而脾主消磨似乎无人再提。
5 结语
从脾主运化的演进过程上看,总体趋势是脾消化功能的扩大,从“脾助胃”到“以脾统胃”。这种演进带来了两个层面的影响:其一是治疗上,脾胃混治成为了主流,消化不良者,统以健脾胃之法治之,然用药上是以辛甘温为主,其治在脾。笔者认为治胃之法与治脾之法应当予以区分,即脾胃分治,脾主升而胃主降,其性不同,治中焦当各从脾胃之性。再如从《内经》之言“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可见治胃不用辛温而当用苦味药。《神农本草经》之言“芩连厚肠胃”即为以苦味药治胃之法。其实脾胃分治思想历代名医皆有示范,如仲景之旋覆代赭汤治心下痞硬噫气不除,旋覆花软坚降胃气,代赭石重坠兼去胃中污秽,正是治胃之法。更有半夏泻心汤治心下痞,半夏、黄芩、黄连健胃,而半夏、干姜健脾,是治胃之法而兼顾护脾运。再如东垣《脾胃论》中的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以辛甘化阳之药补脾,并佐用芩连石膏以治胃,是治脾之法而兼顾胃之通降。此二者皆是脾胃同调之法但侧重不同,且脾胃用药各有法度,绝非脾胃混治。故叶天士总结仲景与东垣之心法:“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仲景急下存津,其治在胃,东垣大升阳气,其治在脾。”[23]此思想应当予以挖掘。其二是对藏象理论本身的影响。何为中医藏象?这一问题从西医进入中国后一直持续引发讨论。笔者认为,脱离解剖谈功能是违背中医形气相合的基本思想的,故藏象理论必有其解剖学的脏器基础。实际上大部分中医学者也持有相同观点,因为中医的藏象功能本就与生理脏器功能息息相关,唯独“脾”,现代认为其为免疫器官,而中医却把它看成消化系统。通过梳理“脾主运化”理论的演进,应该不难发现最初脾消化吸收饮食的功能是有其物质基础的,即“脾主磨”的解剖学基础在胰腺,而胰为脾之副脏,常以脾代称,而脾的其他功能则由脾之本脏承担,脾主升与脾统血的功能皆与免疫系统相关,尤以脾统血与脾本脏之免疫功能关系最为密切,故《内经》有“脾生血”“血生脾”之说,《难经》有“脾裹血”之说。从具有生理基础的脾主磨到消化吸收功能总和的脾主运化,这种变化反映了整个中医藏象理论的演进方向,从重实践到重理论,从重解剖到重思辨,原本建立在脏腑、五体、经络基础上的中医变成建立在阴阳五行基础上的中医。笔者不禁思索,脱离了实践的理论是否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哲学思辨下的中医理论是否还能保持其自身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