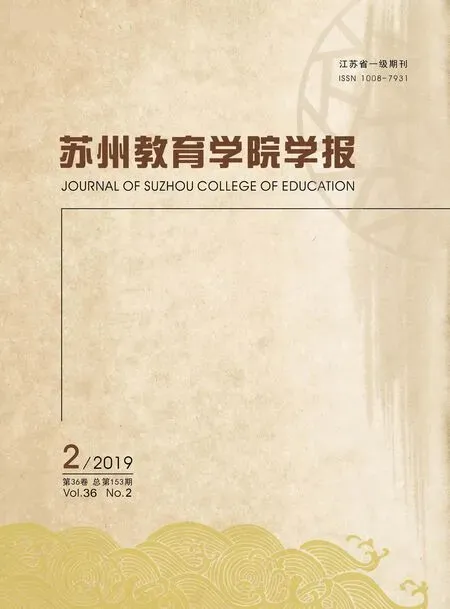明清“申氏家班”闻名吴中之原因探析
2019-02-21刘志强
刘志强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一
明万历、崇祯年间是苏州昆曲的黄金时代,特别万历年间为昆曲之极盛时期,“此时作家亦郁然而起,竞盛一时”[1]。接受和欣赏昆曲的观众,更是囊括了从公卿士大夫到贩夫走卒的各个阶层。市场和利益的驱动,催生了能够满足各个层次的、各式各样的职业戏班,除此之外,热爱昆曲艺术且财富力雄的官、商之家亦喜豢养家班,家班除满足家庭成员的欣赏外,同时为昆剧艺术的交流、发展作出了贡献。本文所述申氏家族昆曲家班即为其中代表。对昆曲以及家班繁荣原因的研究和论述历来颇多,但昆曲家班个案研究相对缺乏。本文试以申氏家班为例,在各家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兴盛原因提出一些看法。
申氏家族之所以成为苏州鼎甲望族,主要得益于既有状元身份又是太平宰相的申时行。申时行几十年青云直上的官宦生涯,奠定了富厚一方的家族地位。申时行谢政后,乃自营今申衙前四大宅、百花巷四大宅等第宅,且遍征梨园、广蓄声伎,创置昆曲家班。“明代家班的组成方式是由主人出资招募艺人,通常是分行当、根据培养前途来招募幼童、幼女,聘请教师进行训练,然后采买行头,适时登场。”[2]闲居苏州的申时行应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亲自参与演员招募、培训以及创置细则等。而创置家班本身,除说明申时行对昆曲抱有浓厚兴趣外,也说明昆曲已成为申氏家族必不可少之娱乐方式。另外,申时行效仿范氏义庄置申氏义庄以赡给族人,也有利于申氏家班的发展。申氏家族的第二代主人乃申时行之子申用懋、申用嘉。申用懋科举顺遂,故常出仕在外。申用嘉却仕途蹇塞,长期居住在家,婚姻湖州豪族董份家族。用嘉为督促子弟举业,曾创立家课。虽曾任广西参政,但因擅自离职归家,被朝廷除名。家族的第三代主人是申用嘉之子、进士出身的申绍芳。申绍芳官至兵部左侍郎,曾娶秦淮著名青楼女子卞敏为妾①“玉京有妹曰敏,……乃心厌市嚣。归申进士维久。……(维久)得敏益自喜,为闺中良友。”参见《清代声色志》卷下,上海进步书局1915年版,第23—24页。。总的来说,申氏家班万历年间始创,直至清康熙初还有演出活动②“申时行创建的申府班在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还应王巢松的邀请,去太仓演《葛衣记》、《七国记》;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赴王府演《万里圆》传奇。根据吴江毛莹《晚宜楼集》赠周铁墩诗句,申府班在康熙初年依然在活动。”参见王胜鹏:《明清时期江南戏曲消费与日常生活:1465—1820》,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138页。,持续了四代人,历时较长,成就较高,虽当时不无煊赫一时的家班,但申氏家班不仅出类拔萃,而且生命力特别坚韧,故而闻名于晚明和清初,位居江南家班之首。
申氏家班“相国家声伎,明季为吴下甲。每一度曲,举座倾倒”[3]150。苏州素有“申《鲛绡》,范《祝发》”[4]之誉,当时申府梨园班以周铁墩所演《鲛绡记》中之看家白面戏而独擅胜场。申氏家班直接和间接培养出了许多艺术成就较高的戏曲人才。“身短而肥”“木强迟重”[5]1450的周铁墩,通过艺术训练,水平得到多方面的提高:“方其蹋鞠、超距,角抵、趯跃,虽俊鹘飞隼莫能过也。……教之歌歌,教之泣泣,教之官官,教之乞乞,昼忖宵摩,滑稽敏给,罔不形容曲中,极于自然。时复援引古今,以佐口吻、资谈笑于相国左右。……观者入其云雾中,啼笑悲欢,动心失志;而铁墩冷眼看人,四筵之情性毕见,擅名梨园四十年。”[5]1450也有通过艺术训练突破身体残疾的障碍,终能擅场于舞台的,如艺人顾伶。顾伶跛脚,“平时行蹒跚,每登场,却疾徐应节,人竟忘其躄也”[3]150。女优沈娘娘,自善度曲,也从事昆曲教学,“(女优)登场演唱,侍御酡颜谛听,或曲有微误,为致意沈娘娘为校正云”[6]。男优“醉张三”,“申班之小旦,酷嗜酒。醉而上场,其艳入神,非醉中不能尽其技。……观其红娘,一音一步,居然婉弱女子,魂为之销”[7]。“申时行家班中的看家小旦醉张三后来加入吴徽州班,成为班中的台柱。”[8]170而苏州派领袖李玉,也是申府家人出身,从小受到申氏家班昆曲实践与理论的双重熏陶,才情和格局皆卓尔不凡[9],著传奇数十种,古今交誉,钱谦益评之为:“于今求通才于宇内,谁复雁行者!”[10]
结合程宗骏《明申相府戏厅家班考》[11]等相关资料,申氏家班之演员、演出作品、戏曲创作人才以及与名家戏曲交流情况大致如下:申府最知名作品乃是周铁墩表演之《鲛绡记》,周铁墩所擅演尚有:《鸣凤记·写本》中之杨继盛,《钗钏记·观风》等折中之李若水等。沈娘娘为钱岱女乐教师时,教习有:《跃鲤记》《琵琶记》《钗钏记》《西厢记》《双珠记》《牡丹亭》《浣纱记》《金雀记》《荆钗记》《玉簪记》《红梨记》诸院本中一二出或三四出。“醉张三”擅演《西厢记》中之红娘、《明珠记》中之刘无双,其他尚有《义侠记》等。另外,申府小班有演《西楼记》最擅场的管舍。申府中班的金君佐顺治十二年(1655)演《葛衣》《万国》,其表演“真使人洞心骇目”[12]795;同年又演《万里圆》,“见者快心悦目,真千古绝调也”[12]796。又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演《望乡台》《汝州春店》[12]802。尤侗创作之《钧天乐》,曾于顺治十五年(1658)在申氏堂中表演。李玉有剧本数十种之多,沈自晋在顺治四年(1647)定稿的《南词新谱·古今人谱词曲传剧总目》之《一捧雪》下注云:“(李玉)所著一笠庵传奇十余种,未尽刻。”[13]康熙六年(1667),李玉自述创作传奇二十余种③“予于词曲,夙有痂癖,数奇不偶,寄兴声歌。作《花魁》、《捧雪》二十余种。”参见李玉:《南音三籁•序言》,《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影印本,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905页。。吴新雷则考出有名目的李玉传奇42种[14]。
二
学界对明清家庭戏班的研究,以胡忌、刘致中的《昆剧发展史》,张发颖的《中国戏班史》《中国家乐戏班》以及刘水云的《明清家乐研究》等为代表,对中国家乐戏班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明清家乐研究》[15],从家乐的正名,到家乐主人类型、演员的来源与培养、演出的形式及场所,再到家乐的艺术审美及影响等,翔实厚重,全面清晰地展示了明清家乐的整体背景。此外,刘召明博士论文《晚明苏州剧坛研究》以晚明苏州整个剧坛为研究对象,家乐戏班的论述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对戏班主人热衷于戏曲的思想和现实原因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8]但在以上著作中,申氏家班只是整体研究的一部分,对发掘申氏家班作为“上三班”与同时期家班的“共性”具有意义,但“个性”发掘深度未免不足,也即对申氏家班何以在激烈竞争中独“名闻吴中”没有作出解释。程宗骏先后写了《明申相府戏厅家班考》、《明申相府戏厅、戏班与李玉出身初探》[16]专门探讨申府家班,但主要着意于申府演出地点、演员及演出节目的考订,“闻名”的原因分析也显得不足。本文即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探析申氏家班“闻名”的深层心理、独特眼光、演员培养方式及物质原因。
在深层心理上,申氏家族三代人都不再停留于纯粹的儒家思想,苏州的商业文化及市民趣味同时对其产生影响。即申氏重要人物的思想中,同时存在着儒家的“谦”“俭”“慎”以及世俗的佻达、奢靡、“声色”[17]思想。站在儒家立场上,与地位低下的艺人交往已事属非常,更不要说在家庭中供养艺人。明末谨慎持重的学者陈龙正即把不与演员交往郑重地写入“家矩”,不但不能蓄养家班,亦且不能延请优人。①《革俗例》:“俗所通用而必不可袭者四事:一曰家中不用优人。优人演戏无非淫耳,岂可令妇人童稚见之?”(陈龙正:《几亭外书》卷二《家矩》,《丛书集成续编》214册,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92页)又《勿畜优伶》:“士夫最忌畜养优伶,每见不好学问者,居家无乐事,搜买儿童,延优师教习讴歌,称为家乐,酝酿淫乱十室而九。……儿女辈习见习闻,十来岁时,廉耻之心早已丧尽,长而宣淫,乃其本分。……延优至家,已万不可,况畜之也。”(陈龙正:《几亭外书》卷二《家矩》,《丛书集成续编》214册,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94—395页。)而对于申氏几代人来说,他们并不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仰者,积极投身科举的同时,也积极拥抱苏州特有的享乐文化。申时行营豪宅、征声色;申用嘉,先是有冒籍参加科举的不端行为②申用嘉万历十年(1582)举于浙。御史李用中、福建按察司佥事李瑖、吏科给事中杨廷兰及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交章劾奏申用嘉冒籍浙江。(朱吾弼:《皇明留台奏议》卷八《乞肃法纪申公论疏》,《续修四库全书》4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0页),之后在广西参政任上擅离职守归家,可以说是相当“任性自由”③“(申用嘉广西参政任上)闻兄病笃,请于台使者,拜疏即行。……广西巡抚以公擅离守地,具疏,旨下,考功议夺官。”(魏禧:《明广西右参政通奉大夫申公家传》,《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03页)。而申绍芳娶妓女为妾,生活上两人互为知音,诗作倡和④《云阳晚憩占赠小妇》:“春风驿路短长亭,乞得仙山梦草灵。懒向修眉拈画本,闲将纤手订茶经。帘前花气迎朝馥,树里莺声媚晚听。入夜一篝方对剪,盈盈自起拜三星。”参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69册《明诗平论二集》卷十四,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70页。,相当自在。相比于同时期苏州儒家氛围浓厚的范氏家族,简直有天渊之别。范氏子弟范牧之才华卓著,因与杜姓妓女交往,遭家族坚决反对,最终导致了范牧之病死、杜姓妓女自杀的悲剧[18]。申氏左右逢源的生活,背后是兼收并蓄的开放思想。陈寅恪曾对善于从新旧道德中取其有利的心理有过分析:“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 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19]申氏兼取两方面好处,而对沉重的责任并不过于在意,可谓是能够适应社会的巧者、能者。申氏勇于也乐于接受新事物,“及至嘉靖、万历年间,法制废弛,贪墨成风,去朴从艳成为时尚。蓄奴也不再犯禁……一些官僚致仕居家为寻求享乐,就搜购儿童,教习歌舞,或招募戏曲艺人”[20]。面对“新社会风气”潮流,申氏家族自然赶在前面。一方面通过科考获得仕途上的权势,另一方面不放弃一切人生的享乐。“不肖者巧者”“善利用”环境,以争取最大的“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自私与享乐成为士人毫不讳言之人生目的”。[21]这应该是申氏数代人抛弃思想负担、专心经营家庭戏班、达到享乐人生目的的深层心理。而其他家庭,可能设置家班之心理与申氏并无不同,只是把握不好发展与享乐的平衡,一味荒耽纵佚,导致家庭迅速沦落。
昆曲本来就转音若丝、流丽悠远,魏良辅加以革新,创“水磨调”,字清、腔纯、板正,使昆曲温润恬和、典雅细腻,遂成就一时之盛,也愈加符合士人的口味。申时行一生,与昆曲改革家、创作家魏良辅、梁辰鱼、汤显祖等前后相去不远,亲自见证了苏州昆曲的黄金时代。虽然汤显祖的政见与申时行颇不相合,但申时行却非常欣赏汤显祖的才华—自然包括其戏曲上的才华,亦有提拔汤显祖的意愿。申时行在朝官高宦达,在野门望显赫,与申时行相似的,还有湖州的董份、太仓的王锡爵等。董份是申时行的座师,两家也是姻亲。王锡爵是申时行的同乡同官兼好友也兼姻亲。董、王、申三人的共同趣味表现在:都十分喜爱戏曲,都创置有家庭戏班;三公皆有文集传世—董份《泌园集》三十七卷、申时行《赐闲堂集》四十卷、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五十五卷,文集都同样缺少论述戏曲的内容,而其实三公对昆曲精鉴博采的程度不亚于专业级别。这种现象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对通俗艺术的态度,认为其重要性不能跟高文大册的文章相提并论。戏曲写作、演出等作为“小人”逐利、“君子”消遣的事物则可,过于沉迷则不可。“君子”应肩负道德责任、建功立业。以申时行等的名望,必持重,不肯把戏曲研究当作严肃对待的目标,更不会在传世的文集里加入戏曲的内容。其儒家思想与实际行为的睽离,唯有知人论世,才能有深切的理解。
申时行在主持会试之时曾对文人与文风在明代的变化有过精到的论述:“臣尝考览当代之籍,观士习之变,大抵国初草昧经始,淳风未漓,士朴鲁而辨于政,武健而怵于法,即有非凡不御之材,兢兢守职救过而已,时则多质而少文。熙洽百年,当成弘之际,文教醲蔚,士皆重博雅、奖恬退,耻不修,不耻不闻;耻不能,不耻不达;时则彬彬,质有其文而不诡于正。又百年而天下之文日盛而入于侈,士乃委蛇其道,繁缛其节,竞斧藻而工鞶帨。其甚也,浮游夸诞,称引夔魑象罔、叛道离经之说而号为奇士,至于好奇而习愈坏,殆孟氏所谓诐行淫词生于心而害于政事者,其为世道病非浅鲜也。”[22]在关系到国家命脉的文章上,申时行郑重其事,以圣贤的“文质彬彬”论为最高准的,对当今的“淫词”颇为不满。如果把申时行正襟危坐的官方文章,与其实际生活中喜爱不乏“淫词”的昆曲,看成其思想的矛盾与分裂固然可以;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正是因为申时行有着正统文人的兴趣和偏好,从而使申氏家班艺人表演带有文人色彩和文学趣味,则显得更有意义。对申氏家班以及家班艺人不吝笔墨加以称赞的,正是各地来往于申氏家庭接触过其家班的文人。戏曲文学的雅和俗之中,偏重“雅”的一方的原因,不外乎戏曲接受者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雅致的兴趣偏好。申时行及其众多子孙的科举家族身份,使家班也染上了文人“雅”的独特色彩和追求。
昆曲的雅、俗是迎合市场需要的两种不同表现。申时行一生喜爱虎丘,曾多次游览,他去世后,申文定公纪念祠也建在这里①“申文定公祠在流化坊,祀明少师大学士时行,万历四十五年巡抚都御史王应麟奏建,子少保兵部尚书用懋参政用嘉祔。一在卫道观东华堂,公少读书处;一在虎丘三泉亭南。”参见《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十六,江苏书局刻本,清光绪九年(1883)。。虎丘是热闹繁华之地,特别是八月半中秋之时,很多戏曲表演家和全城观众汇聚于此,形成戏曲竞赛或是艺术交流的盛会。张岱记述虎丘万人空巷以及戏曲表演盛况云:“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23]申时行对这样的场景应该不会陌生。作为流行文化,昆曲受到广泛的喜爱和追捧,申时行也不例外。苏城长大的申时行,对昆曲的兴趣可能就是由此点燃并保持终生。不用说,所谓戏曲大会,最多的欣赏者还是三教九流的普通人,表演自然倾向于“俗”的一面。而对申时行这样的欣赏群体来说,会对昆曲“雅”的一面有更多的要求。在明代社会,话语主导权及较高的消费能力集中在宦、商阶层,其欣赏品味和创作参与使昆曲始终保持“雅”的一面,可以说,申时行家族及申氏家班的努力使昆曲天平向“雅”的一方倾斜。
申府之家班,知名于吴中的原因是表演人才多、表演艺术高。而人才之发现与教成,则是申府主人之眼光和培养的结果。申时行名气大、交游广,使家班有更多接触戏曲名流的机会,磨练了表演人员的技艺。在第一代家班形成规模、完成程序运作后,家族后代不难维持下去。而家班本身也可以随时间成长并成熟,既有高质量的培养,又可以与最专业的同行交流,甚至可能同戏剧创作者打成一片。著名戏曲家尤侗看来与申府颇有来往②参见程宗骏:《明申相府戏厅家班考》,《艺术百家》1991年第1期,第113—114页。文中引用了尤侗《西堂余集•年谱》。,而戏曲成就卓著的李玉即出身于申府。李玉作品题材之广泛、艺术之精到、情感之深沉,除与李玉身居相府见闻广泛、受到长期艺术熏陶有关外,还应与因感身份低下故写作传奇以抒愤密切相关③李玉的出身或说是申府家人,或说是申府家仆之子,要之与申府密切相关。相关论述参见欧阳代发:《李玉生卒年考辨》,《文学遗产》1982年第1期,第144—147页。。
另外,科举制度实现了社会的跨阶层流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金榜题名”和“出将入相”的梦想成为集体意识扎根于社会,每一个传奇的诞生都为人们津津乐道。申时行科举和官宦生涯的巨大成功无疑具有了进入传奇的资格。退休后的申时行,面对戏台上“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套路型故事,心里大概有着更独特的感受。而申氏子孙,也大概很容易在戏曲故事中回忆起家族曾经的荣耀。自然,申时行本人也免不了成为戏曲创作的对象,申家屡次鼓动官府禁绝搬演申氏故事的《玉蜻蜓》而屡禁不止,根本原因是梦想成真的故事给了渴望荣华富贵的人们以巨大的心理安慰,从而具有难以遏制的生命力。
三
刘召明在《晚明苏州剧坛研究》中将家乐戏班在晚明兴盛的原因总结为:1.吴文化圈对兴于斯、盛于斯的本土剧种的热爱;2.精美清雅的私家园林为演出提供了合适的场所;3.发达的经济、富豪之家的奢侈攀比之风为艺术活动提供了物质支持;4.文人结社相伴以戏曲演出活动。[8]190-195这基本也可以用来解释申氏家族何以能够创置家班的物质因素。家班主要是为了满足享乐需求,是消费性质的,戏班人员的生活、培养费用以及演出活动的支出,皆由申氏提供。在申时行之前,申氏并不显赫,即使家族两代相继出了两位进士,仕途上青云直上,皇帝赏赐丰厚,与富贵之家缔结婚姻,有较多的寿序和墓志铭润笔收入,等等,恐怕也不足以使刚辞官回来的申时行在苏州拥地千亩以上。对此,刘召明对江南缙绅追求货殖、钻营取利之风的论述颇能揭示申氏发家的真正原因:“晚明家乐戏班主人以致仕缙绅为主,而这种江南经济繁荣的‘小气候’,也非常利于他们充分利用经济发达的环境经营产业,获取财富。‘苏松财赋之地,易为经营,江楚旷莽之墟,止知积聚耳。’而且他们善于经营,巧于经营,一般不自己亲自出面,而是交给门生故吏代为经营。‘前明缙绅,虽素负清名者,其华屋园亭,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门生故吏代为经营,非尽出己资也。至于豪奴悍仆,倚势横行,里党不能安居,而市井小民,计维投身门下,得与此辈水乳交融,且可凭为城孤社鼠。由是一邑一乡之地,挂名童仆者,什有二三。’……‘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8]193以科举致身显途的王鏊、申时行等,可以不必亲身过问家庭经营,其声名权势,足以为家人经营生产提供便利。可见,申氏家班是兴趣和爱好的产物,更大程度上却是物质丰富的产物。申府家班培养出了许多知名艺人,促进了昆曲艺术的发展,又刺激了艺术市场中更多作者和剧本的产生。昆曲市场的内在发展逻辑皆与物质和利益息息相关。
因戏班具有消耗性,故家庭戏班兴衰与家族兴衰同步。明清易代之际,家族需要应对生存危机,为节省开支,戏班优先被裁,申班艺人因此流散①“遭逢时变(按:甲申明亡),暴富之客,将奄致之。铁墩蹙然曰:‘承事相国以至今日,乃反颜面事趢趢儿,吾宁甘乎?’遂绝群而往,不复出。逾三四年,相国之后,稍稍整顿旧观,乐承平故事,铁墩始复出。”参见程宗骏:《明申相府戏厅、戏班与李玉出身初探》,引褚人获所撰《周铁墩传》,《中华戏曲》1999年第2期,第142—160页。。安定之后,申氏后人整顿旧观,重新豢养戏班。但是随着家境的今不如昔,戏班规模同样比不上最盛之时。申府家班后期多有出外演出的记录②“引王抃撰,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兄(按:名揆,字芝廛,顺治十二年进士)两日,“申氏中班”演《葛衣》(明吴江顾大典编任西华事)、《七国》(顺治间李玉编孙膑事),金君佐(按:当时申府中班当家老生)方在壮盛时,真使人洞心骇目。’”参见程宗骏:《明申相府戏厅、戏班与李玉出身初探》,引王抃撰,《中华戏曲》1999年第2期,第142—160页。,估计此时家班演出更大意义上已经是家庭经营以获得利益的一种方式了。而当家族缺少重要人物支撑,那么家班也随家庭没落而没落了③“康熙二十三年……申相国之后—第四世长房传世曾孙允荣、允同已殁,‘申府中班’之名亦不复存在矣。”参见程宗骏:《明申相府戏厅、戏班与李玉出身初探》,《中华戏曲》1999年第2期,第142—160页。。但相对而言,申氏家班经过较长时间才逐渐从申氏家族中退出,究其原因,恐怕与申氏义庄制度不无密切关系。
申时行在退休之后开始捐置义田,效仿苏州古老的“范氏义庄”,用义田的公共收入赡给族人。申时行去世后,申用懋、申用嘉兄弟继承遗志,制定规则,正式建立义庄制度④参见申祖璠:《申氏世谱》卷八,赐闲堂刻本,道光辛丑年(1841)。,形成了一个以义庄为核心的家族共同体。义庄虽然主要解决的是申氏族人的物质保障问题,但家族所有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投入,都不能脱离其物质基础。考察申氏家班,特别是考察家班的长久运行,似乎不能不着眼于此。
在家族科第连绵、仕途顺利时期,物质积累丰厚,在家族必要支出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有足够的资金供消费和享受之用。家班属于享乐消费,其水平和影响跟投入的时间、精力以及资金成正比。申氏家族共同体在形成之时,富贵显达,号召力强,因此其家班很快以表演剧目多、艺术水平高且出现多位有特色的表演艺人扬名苏州及士大夫之口。在经历改朝换代和家族衰落时,共同体优先保障族人生活,缩小家班规模甚至停止其活动也是自然之事。申氏义庄并不优先发展申氏家班,却足以使申氏家族能长久延续下去,而一旦家族再次兴盛,则家班也很有可能再次恢复活力。入清后,申氏重新组织家班,是家班的一次死后复生。如果没有义庄维持,那么申氏家族可能彻底衰落,而家班也再没有重新组织的机会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申氏义庄至清乾隆时期尚正常运行①申祖璠:《申氏世谱》卷二,沈慰祖《申氏义庄记》,赐闲堂刻本,道光辛丑年(1841)。,却无义庄直接支持其家班的条例。义庄之设,主要用于赡族众、完国课、供祭祀、建祠堂、修族谱以及饥年捐施乡里。[24]义庄赈济对申氏族人来说是应享的权利,但权利往往与责任相应,必然也需要族人尽一定义务,故往往配合家训、家规对族人进行规训。“义庄”乃申时行仿照“范氏义庄”创置,范仲淹乃纯儒兼名臣,故范、申氏义庄条例皆体现了儒家思想在家族中的实践要求,无论施规训者或受规训者皆受约束。儒家规训首先要培养族人节俭的生活意识,杜绝极端奢侈的非理性消费;其次也会对家班人员培养产生影响。明清之际,申氏家班人员开始四散,其艺人无论德、艺都受到时人好评,如周铁墩的忠厚性格,再如顾伶亦“能存故主之义”:“曹村金相国谢政归里,……素悉顾名,遣其侪招之,顾谢曰:身获事故相,年已老矣。不能更事今相国。遂弃其业,终身不复入梨园。”[3]150除了有意教导,也不排除家族风气的影响,此其“义庄”影响戏班之一处。第二,家班及艺人的供养是高消费之事,巨贾豪宦也往往仅能支持数年,之后“破室败家”“招灾致祸”者比比皆是[15]227-231。以晚明名士张岱为例:“岱累世通显,服食豪侈,蓄梨园数部,日聚诸多名士度曲征歌……。明亡,避乱剡溪。素不治生产,至是,家益落,故交朋辈多死亡,葛巾野服,意绪苍凉,语及少壮秾华,自谓梦境。”[25]张岱的“不治生产”,正与申氏设置“义庄”制度化经营大异其趣,结果是张岱一经患难即不能维持基本生活,以前的家乐繁华也成为南柯一梦,而申氏却能够在易代之际平稳过渡,甚至连家班也保留下来。如果张岱因易代而家破人亡则令人同情,但若因家班挥霍无度的非理性消费而导致家庭破败,就没什么好说了,他们原本就没有为家族谋划长久之计。作为同时代人,袁宏道对此感慨尤深:“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26]很明显,义庄使申氏子孙在享乐消费上趋于理性,经济条件不足时则合理缩小规模,昆曲热度不再时,则自然解散之。家班设置和运行的合理化,不能不归功于义庄规训制度。第三,当昆曲繁盛时,要么群哄而上,以之为性命;要么像陈龙正那样,视之如洪水猛兽,以为世道人心全由优伶败坏,此两者皆是极端行为,往往既不利于家庭的发展,也不利于艺术的传播。而设置了义庄的申氏家族,却能够在长时间内正确对待家班及艺人,无疑在艺术应该如何健康发展方面给人以一定的思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