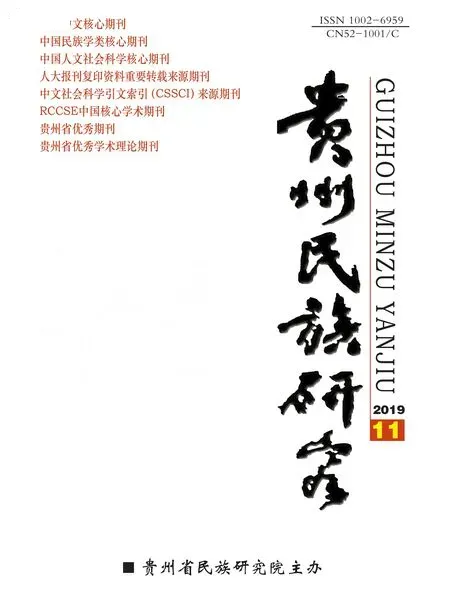民族地区生态环保村规民约的作用机理及其实证分析
2019-02-09舒松
舒 松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 100081)
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民族地区,由于生态系统脆弱,自身调节和恢复能力差,生态保护和建设投入不足,生态环境形势已经变得非常严峻。与此同时,尽管民族地区采取措施对影响和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了约束和规范,但受破坏的先行性和规制的滞后性影响,行政主导型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效率却不高。当前,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亟待优化,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大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治理架构,形成政府主导、市场推动、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新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发掘利用民族地区的传统与民间资源,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以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为例来说明传统乡村法治资源对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作用。
一、民族地区的生态环保村规民约及其作用机理
民族地区生态环保村规民约是指少数民族群众结合本村寨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生产生活实践,以村寨民众合议方式制定的用以维护本村寨生态环境秩序,并有一定权威性和强制性的成文或不成文的社会规范。在我国,民族地区生态环保村规民约大多是作为少数民族村规民约的析出部分而存在,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少数民族的乡规民约。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北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范仲淹“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为当地羌人立条约[1](P10271)。这是有关少数民族乡规民约的最早历史记载。
(一)民族地区生态环保村规民约是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产物
作为一种具有民族性与地方性的规约禁令,民族地区的生态环保村规民约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产物。美国学者吉尔兹曾说:“法律与民族志,如同驾船、园艺、政治及作诗一般,都是跟所在地方性知识相关联的工作。”[2](P222)民族地区的文化多样性突出,地理环境较为偏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造就了极富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的村规民约,这也是民族地区生态环保村规民约价值功能形成的基础。作为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产物,民族地区生态环保村规民约主要通过道德和宗教来引导,具有多样性与分散性的外观形态,体现出地域化的民主性和权威性。
民族地区的生态环保村规民约主要通过道德和宗教来引导。法学家朱苏力曾说:“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在时间流逝中完成,在无数人的历史活动中形成。”[3](P53)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体现了这一特点。我国现有的56个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由400多个族群通过民族识别确立下来的,但中华大地上的华夏各民族却已存在了数百上千年[4]。经历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许多民族认识到自己周遭的一草一木、一虫一兽与自己的生存发展存在密切关系,出于敬畏自然,于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出现了起到类似德治作用的旧式或新式规约。如古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众多封山碑;现代云南省泸沽湖畔的少数民族乡村制定的水源保护专门规约[5](P181)。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有着浓厚的宗教信仰。这些宗教信仰或多或少地渗透到了生态环保村规民约当中,渗透的方式包括图腾崇拜、创世传说以及神山神湖禁忌等,这便使在客观上起到生态环境保护作用的村规民约具有相当程度的宗教性。
民族地区生态环保村规民约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分散性。我国少数民族的村规民约既有成文的,又有不成文的;既有通过石碑、文书传承的,又有通过演唱、讲授传承的。如我国苗族就存在通过“埋岩”程序来进行立约的习惯,而一些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可能更多地诉诸于言传口授,通过向后代讲授各种禁忌来传承保护生态环境的习俗。对于那些能歌善舞的民族来说,歌曲和舞蹈也可能成为表达规约精神的独特方式。这些都体现了民族地区村规民约的多样性。在我国民族地区,许多少数民族村落不具备制定专门的环保村规民约的条件,生态环境保护规约大多被列入某一个综合性的规约当中,或者被融入某一个神话传说、图腾信仰当中,因而生态环保村规民约又具有分散性的特征。
民族地区生态环保村规民约的制定实施具有民主性和权威性。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存在类似于村的基层组织。如苗族的“议榔”、侗族的“侗款”、景颇族的“贡沙”、黎族的“合亩”、瑶族的“石牌”、彝族的“家支”、赫哲族的“哈拉莫昆”、鄂温克族的“毛哄”等,这些基层组织虽然叫法不一,但其性质都与村落有着相似之处。这些基层组织的首领对内维护治安、对外统领防御,在必要的时候召集组织内的民众制定、修改、废止规约。大凡制定、修改或废止规约,尤其是涉及重大公共利益,都会有相应的大会,这些大会的参与者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除了民主性,民族地区生态环保村规民约还体现了相当的权威性。如我国诸多少数民族的规约里经常以罚款的方式来使规约得以遵守,这事实上使得村规民约作为一种习惯法发生效力。正如霍贝尔所说:“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文明社会,法律存在的必备条件是社会授权的当权者合法地使用物质强制。”[6](P5)
(二)民族地区村规民约生态环保作用的形成根源
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之所以能够对生态环境起到保护作用,其根本原因无外乎两个:环境产生规约和环境需要规约。
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为村规民约发挥环保作用提供了内在依据。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有别于汉族。这些特殊环境塑造了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和信念,孕育出特殊的需求,产生出特殊的行为准则。这是村规民约生态环保作用形成的根本原因。例如,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尕海乡的村规民约中规定:“草场虽承包到户,但草场是国有资源。要严格遵守草场合同规定的要求,合理利用和建设草场,每年都要灭鼠治虫,补播种草,严格控制载畜量,不能有过牧、滥牧等盲目短视行为,……对不履行承包合同义务和规定要求……而对周围草场造成影响、损失的牧户,要处以300—500元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要收回承包草场。”[7](P340)这条村规具有很浓的游牧民族特色,而形成这一特色的根本原因是尕海乡的生态环境。尕海乡的海拔在40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只有3摄氏度,这种地势高、温度低的高原气候更适宜发展牧业而不是耕种业,且这种条件下植被相对比较脆弱,需要人工进行维护,比如“灭鼠治虫、补播种草”。于是在高原气候的影响下,一个关于保护草场并具有游牧特色的环保村规就产生了。事实上,不光是尕海乡,其他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村规民约之间也有着类似的联系。这种在民族历史影响下的独特民族地理因素是村规民约发挥环保作用的内在原因。
少数民族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是村规民约发挥作用的外部原因。由于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原因,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如景颇族、佤族、独龙族、畲族等民族依托山地实行刀耕火种;藏族、蒙古族等民族依托草原以牧业为生;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民族依托江河以渔猎为生;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依托山区丘陵地区以农耕为生。当今,不少自然资源丰富的民族地区的发展开始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但这种转变只是改变了少数民族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方式。少数民族对生态环境的依赖,塑造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环保村规民约之间的紧密关系,即生态环境促进环保村规民约的产生,同时也受到村规民约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但粗放型发展方式使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因此,当前少数民族地区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又为村规民约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机会。
(三)民族地区村规民约生态环保作用的实现机制
民族地区村规民约生态环保作用的实现源于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政策、民族自治立法、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业已形成的紧密关系。
首先,国家法律与政策对民族地区村规民约生态环保作用的肯定,使村规民约能够在国家生态环保机制层面发挥作用。作为一种具有正面效益的乡土秩序与法治资源,少数民族地区村规民约的作用得到了当今《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物权法》等不同层次法律的肯定。因为村规民约体现基层村民自治,符合法治精神,是基层民主的体现,也是维护村民个体权利,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需要。基于这种肯定与支持,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被纳入国家生态环保治理体系发挥作用,如2003年环境保护部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评估赋分表》中将村规民约作为衡量法规制度体系健全与否的一个指标。此外,2004年国家林业局在《关于大力开展村屯四旁植树和农田防护林建设的通知》,水利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水土 保持生态修复 促进草原保护与建设的通知》中均肯定环保村规民约在国家环保活动层面的作用。上述都是民族地区环保村规民约在国家层面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
其次,许多民族自治地方将村规民约作为生态环保法制化的重要内容,使村规民约能够在民族地方的生态环保机制中发挥作用。如1991年颁布实施的《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依法治林,加强林政管理,引导和支持各民族群众制定有利于保护森林资源的村规民约。”2008年颁布实施的《云南省文山苗族壮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今冬明春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规定:“要不断完善林区单位的防火负责制、护林人员岗位责任制,以及乡规民约、防火公约、联防协作等制度。”均为生态环保规约产生影响的绝佳例证。
再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化,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无论是涉及水资源保护、森林资源保护、草原资源保护还是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的环保村规民约都具有浓厚的习惯法特征,这使得村规民约已成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重要方面发挥作用。如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制定的《帮家、翁江两村村规民约》承继了瑶族固有习惯法的处罚方式,普遍规定了罚米、罚酒、罚肉的“三罚”方式[8]。又如云南基诺族、东北鄂伦春族出于对森林资源的感恩和敬畏,在村规民约中规定了诸多保护山林资源的内容,这些内容一直在作为习惯法发挥作用。贵州都匀市凯口镇平新村至今保留有一块清朝道光年间流传下来的石碑,碑文中有“山场树木偷者罚银一钱二分”的规定。该村在1984年制定的村规民约沿袭习俗作出规定:“偷砍集体或他人的成柴树、竹,按每寸罚款10元,照此推算。”[9]上述事例充分表明环保村规民约已经在作为习惯法发挥作用。
二、民族地区村规民约生态环保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以黔东南苗族侗族为例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少数民族比例较高的自治州,也是苗族、侗族分布非常集中的地区。通过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调查,笔者发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侗族的环保村规民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研究民族地区环保村规民约作用机理的绝好范本。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上古三代时期被称为荆蛮之地,曾隶属于夜郎国。明永乐年间,贵州正式建制为省,黔东南此时归属于黎平府。清朝时隶属镇远府。1956年7月23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正式成立,州府为凯里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生态资源非常丰富,水能储藏量高达262 万千瓦,森林覆盖率高达62.79%,有“林海”“杉乡”之美称。此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还有种类众多且珍稀的植物资源,以及10多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作为一个生态环境多样、民族文化丰富并且享有诸多殊荣的地域,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保存了众多极富特色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运行着一套独特的维持其内部之间以及与自然环境之间进行良性互动的规则体系,其中便包括了众多出于保障生产效益或维护信仰禁忌而制定的生态环境保护规约,最有代表性的是苗族、侗族制定的村规民约。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和侗族的村规民约包括旧式村规民约和新式村规民约。所谓旧式村规民约,是指在议榔、鼓社、寨老、侗款等组织领导下制定的规约,如苗族古歌中具有法律意义的内容和侗族著名《约法款》等;而新式村规民约,则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苗族、侗族地区设立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以来制定的带有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色的规约。二者相较,新式规约更具规范特色,而旧式规约则更为形象和生动。据中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宣传部的统计,80%以上的村寨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这说明村规民约的普及率已经相当高了。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旧式村规民约,在苗族集中体现于“榔规”,在侗族集中体现于“款约”。榔规即议榔组织订立的规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历代传承而经议榔内部成员所默认的苗族古歌和理词;另一种则是议榔大会通过“埋岩”等仪式而确立的规约。其中苗族古歌和通过埋岩仪式确立的“石头法”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规约,从中也可大致看出其作用机制。
(1)诵唱式规约——苗族古歌及其作用机制。苗族古歌记叙了苗族的祖先是姜央,而姜央又是云雾所生。《开天辟地歌》中记载道:“姜央算最老,他来把天开,他来把地造……姜央生得晚,姜央算最老……哪个生最早?哪个算最老?云雾生最早,云雾算最老。”[10](P2-7)这段歌词以盘歌的形式将人类的起源追溯到了“云雾”这一自然现象,实际上反映了苗族对自然的崇拜。古歌中类似这样把自然物作为崇拜对象的词句还有许多。《枫木歌·砍枫香树》中记载了一个神话故事,讲的是鹭鸶和白鹤吃了池塘的鱼,池塘因为抓不到鹭鸶和白鹤,于是这口叫“香两老婆婆”的池塘请来负责解决纠纷的理老,合谋将责任强加在了鹭鸶、白鹤安窝的枫树身上,并且叫人将枫树砍倒;枫树因为受冤迟迟砍不倒,好不容易砍倒了,便出现了以下歌词:“枫树砍倒了,变作千百样。树根变什么?树根变泥鳅……树桩变什么?树桩变铜鼓……树干生疙瘩,疙瘩变什么?树干生疙瘩,变成猫头鹰……树叶变什么?树叶变叶子……树梢变什么?树梢变鹡鸰……还有枫树干,还有枫树心,树干生妹榜,树心生妹留,这个妹榜留,古时老妈妈。”[10](P182-184)这一段歌词不仅讲述了一桩纠纷,更把枫树的树干和树心当成了人类的祖先“老妈妈”,而且将泥鳅、铜鼓、猫头鹰等都融在“枫树”这一自然物中,传递出很强烈的“天人合一”观念。苗族古歌中所包涵的人与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的观念广为流传,后来逐渐成为一种默认的村规民约,约束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索取行为。而在另一方面,苗族的理老也正是在熟悉这些古歌、古理的基础上再来判断是非从而调解纠纷,苗族古代很多纠纷也正是如此解决的。
(2)埋岩式规约——“石头法”及其作用机制。苗族和侗族的先民在没有文字和没有学会使用汉字的时期,常常在某一地点举行“埋岩”(也叫“栽岩”)的仪式[11],即组织本村寨或者邻近村寨成员聚集到一块,埋下一块半露地面的岩石,并举行一系列仪式和制定一系列口头性规约用以约束族内人们诸如贼盗、婚姻等方面的行为,而这些被制定的规约就是本文所称的“石头法”;之后如果有人违反了规约,将被拉到这里进行调解或者审理,并将此次调解或审理的结果作为一种先例对以后的违法事件的处理进行指导。这时的“石头法”是不成文的,石头仅仅起到一个象征性的作用。随着汉字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被学会和使用,这些不成文的“石头法”逐渐被各种写有文字的石碑所代替,这也是本文所称的“石头法”,只不过是一种成文的“石头法”。这种独特的立法方式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和侗族中曾广泛出现,其组织的主体便是前文所提到的议榔和侗款,而这些所谓的“石头法”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榔规和款约的主要内容。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榔规的运行机制[12]。
(3)法典式规约——《约法款》及其作用机制。《约法款》乃是侗族一部非常珍贵的规约典籍,具有相当高的权威;甚至可以说,这部法典式的《约法款》出现之后,侗款在组织制定具体款约的时候无不以这本典籍为参考性依据。长期以来,由于侗族没有文字,因而这部款约的流传形式基本靠口头传承,这也导致了后世很多不同版本的出现,而笔者所参考的乃是流传于广西三江一带并由学者吴浩、梁杏云等人整理出来的版本。根据这个版本可知,《约法款》全文包括序词、六面阴规、六面阳规、六面威规、尾语五个部分,都以非常形象并且有节奏感的语言进行表述。其中“六面阴规”主要规定破坏龙脉、挖掘坟墓、谋财害命等较重的犯罪行为,对犯这些重罪的人一般都处以很重的刑罚,如处罚金、活埋、沉水等;“六面阳规”主要规定出轨、通奸、盗窃等较轻的犯罪行为,对这些行为一般都以罚款、喊寨等形式进行处罚;“六面威规”则更侧重一种民事方面的规约,比如热情好客、兄弟和睦、村寨治理等行为。在《约法款》中规定的众多行为规范当中,有不少涉及了生态环境保护,但主要用意都是在保护私人产权。比如“六面阳规”中的“四层四部”一节中关于偷砍树林的规定:“偷干柴,砍生树;偷直树,砍弯树。抓得柴担,抓得扁挑。要他父赔工,要他母赔钱。跟随的人罚六钱,带头的人罚六两。”类似的还有同一节中关于保护水源的规定。虽然规约都是为了保护村寨民众的私人权益,但这并不妨碍客观上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13]。作为一部对侗族影响极大的村规民约集,《约法款》关于森林资源和水资源等的零碎保护规约对后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侗族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是具有相当明显之作用的;而且,《约法款》中规约的结构、处罚方式甚至订立规约的模式,都对后世黔东南侗族地区的新型村规民约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变化,黔东南苗族和侗族村寨开始以新的组织和新的价值观来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传统的“鼓社”,“榔规”和“侗款”等组织虽然还存在,但其影响力已经明显不及以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为代表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新型村规民约正是产生在这一背景下。然而,从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情况看,苗族和侗族的生态环保新规约在制定主体、行为模式、保护对象、处罚方式等方面都体现出与旧规约的继承关系。为研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新型村规民约的环保内容,笔者特意对收集到的16份村规民约进行了分析。这16份村规民约分别是:(1)《为维护输变电设施的安全制定的规约》(丹寨县龙泉镇,1983年)[14];(2)《烧茶公社城望大队“以克农”护林乡规民约》(丹寨县城望村、金竹坪寨,1985年)[15](P62);(3)《关于维护西江村吃新节秩序的通知》(雷山县西江镇,1991年)[16];(4)《雷山县报德村村规民约》(雷山县报德村,1994年)[15](P253);(5)《雷山县也利村村规民约》(雷山县也利村,1997年)[15](P239);(6)《雷山县上郎德村村规民约》(雷山县上郎德村,2001年)[15](P245);(7)《羊排村村规民约》(雷山县西江镇羊排村,2002年)[17](P33-36);(8)《报德大寨民约公告》(雷山县,2003年)[15](P233);(9)《雷山同宗两家家谱》(雷山县)[15](P235);(10)《高贵村村规民约》(雷山县西江镇高贵村,2006年)[17](P32-33);(11)《西江村村规民约》(雷山县西江镇西江村,2011年)[17](P36-38);(12)《双井镇铜鼓村村规民约》(施秉县双井镇铜鼓村,2016年);(13)《龙塘村村规民约》(施秉县双井镇龙塘村,2015年);(14)《平楼议款条约碑》(从江县往洞乡,1992年)[18](P78);(15)《报京大寨村规民约》(镇远县报京乡报京大寨,2005年、2008年)[19](P53-57);(16)《洛香村中寨公约》(从江县洛香镇洛香村,2012年)[20]。以上16份村规民约涉及九大类环保内容:
(1)禁止乱砍、偷砍树木规约。有关这部分规约是所有有关生态环保的规约里出现条数最多的,总计有42条。其中《羊排村村规民约》中第二章则是专章规定偷砍树木相关内容的。
(2)森林防火规约。这部分规约出现频率也相当高,总计有29条。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规约不光出现次数多,而吃新节秩序的《通知》且惩罚是最严重的。比如西江镇人民政府、老年协会和鼓藏头联合印发的《关于维护西江村吃新节秩序的通知》就规定放火行为要罚“3个120”,即120斤猪肉、120斤酒、120斤米,另外加罚12000响的火炮;情节严重的还要送交公安机关处理。又比如《雷山县也利村村规民约》中第17条至第19条也规定失火的惩罚是“3个120”;而在《西江村村规民约》中除了规定罚“3个120”,还要加罚120斤蔬菜,外加鸣锣喊寨一年。可以说,苗族村寨在对违反生态环保规约的行为进行处理时,罚“3个120”是最高的处罚。而对侗族来说,虽然没有“3个120”的处罚方式,但是对引发山火、寨火的行为处罚也是相当严厉的,比如《平楼议款条约碑》第7条规定山火、寨火造成2000元以上损失的,罚款5000元,因为迷信而用火导致的加倍;损失在2000元以上的,罚款5000元以上,上不封顶;此外,如果情节严重,还要依国家法律进行第二次处罚。这也可以说是侗族村规民约中最严的处罚方式了。
(3)禁止摸鱼、电鱼、毒鱼、炸鱼规约。这部分总计有12条。这部分规约数量也不少,而且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因为这里针对的毒鱼、炸鱼等行为其范围不光限制在河流、水塘中,而且包括在田中。之所以有关于禁止在田中毒鱼、炸鱼的规约,乃是因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和侗族人们有在田中养鱼的偏好。
(4)保持地面清洁、禁止乱扔垃圾规约。这部分规约总计13条。这类规约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侗族地区的一种城镇化趋势。
(5)禁止割草与放牧规约。这部分规约总计出现了12条。当然,村规民约中并非禁止民众割草或放牧,而是禁止进入别人的林区或田地进行放牧,其初衷还是为了保护村民私人权利。
(6)禁止破坏风景林规约。这部分规约总计有4 条。这部分规约内容乃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许多苗族和侗族地区被国家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并逐渐开发成旅游景点以后的产物。为了维持村寨的风景,村规民约中对破坏风景林的处罚也相当严重。比如《羊排村村规民约》第二节第12条中不光规定破坏和霸占风景林区的民众要被处罚“3个120”,还要附带其他很多处罚;甚至还出现了“发现砍一刀一斧的罚款20元”的严苛条文。
(7)合理使用生产、生活用水规约。这部分规约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仅出现3条。
(8)禁止在斗牛场附近挖沙取石。这部分规约仅出现1条。这条规约的出现正反映了苗族、侗族中的一项风俗,即斗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和侗族自古便有斗牛的风俗。由于斗牛对场地的要求很高,因而禁止在斗牛场附近挖沙取石的规约乃是为了保护好斗牛场地。
(9)禁止盗采药材。这部分规约只有1条。禁止盗采药材的背后可能与禁止割草的规约性质一样,都是为了保护私人权利。
对上述九大类规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环保规约在运作过程中有如下特征:
一是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规约的制定主体和执行主体上。虽然大部分规约的制定主体都是村委会或者村党支部,但是有几份村规民约中还保留着传统苗族的“鼓藏头”“寨老”和侗族的“款”。比如1991年7月西江镇的《关于维护西江村吃新节秩序的通知》其制定主体便包括了鼓藏头以及同寨老组织性质极为类似的老年协会;又比如2003年9月1日雷山县境内的《报德大寨民约公告》便是由报德大寨的3个寨长和13 个酒长共同商议制定的草稿。此外,有两份村规民约规定的执行主体也很有特色,如《平楼议款条约碑》中规定成立护款队,由每村派两人组成,负责执行款内的决定;又如《西江村村规民约》中规定拒交违约罚款的,将会请鼓藏头和寨老出面解决。
二是注重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在笔者搜集的以上16份村规民约中,环保规约总计有101条,而其中有71条是关于保护树林的,包括防止火灾、禁止乱砍滥伐等内容,其比例高达61%。这实际上反映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和侗族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对树林的依赖,这与前文的相关论断是一致的。
三是注重规约的实施保障。例如,所有苗族和侗族在制定规约的行为模式设定基本上都以禁止性规约和义务性规约为主,极少有授权性规约。又如,在苗族、侗族的村规民约中规定了较为详尽的惩罚机制。违反规约的惩罚方式主要有批评教育、鸣锣喊寨、请鬼师护魂、帮全村洗寨、取消享受或暂缓享受村里的各种优惠待遇、没收涉案物品、照价赔偿、交违约金、罚“3个120”、拉猪拉牛抵交罚款等,可以说是花样迭出。但总体来看,这些村规民约的主要处罚方式还是以赔偿或罚款为主,而且大部分村规民约都规定了罚款金额的分配机制。比如《高贵村村规民约》规定违约金分配方式为:“60%归捉拿人,30%归处理人,10%稿纸费。”《雷山县也利村村规民约》规定:“各款罚金均按以下分成比例进行:被盗主人享受10%,检举、捉拿人员享受60%,处理人员享受15%,村集体享受15%。”《雷山县报德村村规民约》规定:“70%给村民,20%将给捉拿者(或举报人),10%交村委会。”此外,一些规约还规定了争端解决机制。如好几份规约中出现了向解决纠纷的村委会上交纠纷处理费的条文。值得注意的是,西江村的规约中对处罚金统称为“违约金”,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内容,这一方面表明了西江村的苗族人民已经认识到村规民约乃是一个“约定”,另一方面则深刻反映除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侗族人们具有较强的民主观念。
四是表达方式具有一定的粗糙性。到目前为止,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和侗族村寨基本都学会了使用汉字,并且也有了本民族自己的文字——苗文和侗文,这意味着苗族和侗族村寨的村规民约可以用成文的形式表达了。但从笔者所阅读的村规民约来看,这些文本不论在整体内容安排还是部分概念表达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诸多瑕疵,比如表达重复、条理不清、含混不明等问题并不少见。此外,部分规约所反映出来的对现代法学理论的认识也显得较为肤浅。当然,这并不影响规约被广大苗族和侗族人们所认可。
三、当前民族地区生态环保村规民约存在的不足及其完善思考
通过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生态环保村规民约的研究,笔者认为苗族和侗族村寨能在大山深处创造出独特温馨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体现自我管理的村规民约功不可没。从甘吾苗寨的“咙当”仪式以及众多村规民约文本来看,这些看似或神秘或粗糙的规约其实是一套为少数民族地区量身定做而行之有效的乡土秩序。村规民约背后所隐藏的这种乡土秩序对于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具有深远意义。
以矛盾分析为轴心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特点。在对民族地区村规民约进行评价时,也需要这种思维方式,既不片面否定看似简陋的村规民约的价值,也不过分拔高其作用,而是力图去粗取精,从中寻找真正有利于生态环保、有利于法治建设的资源。近年来,习惯法、田野调查、生态环保等领域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热点,但仍有一部分人不屑于研究少数民族保留传承下来的民间资源。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少数民族环保规约被认为表达粗陋,实施武断。例如,尽管款约、古歌和其他形式的规约中包含非常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行为模式和制裁方法,但是依然不能掩饰其在文字创造、表达技巧、书写工具等方面的简陋。这种简陋可以让许多人将其直接斥为“落后”。试想,在一个苗族的鬼师念完一句“不要偷钱偷东西,破坏地方环境,反正偷和破坏的行为是不好的”之后,有几个法律人会觉得这句既无生效和失效日期又无严谨之法律逻辑的话是一种有效的环保规则呢?在另一方面,尽管我国上至宪法、下至地方政府规章都有相当多的法律法规明确提出尊重和认可民族地区的习惯法,但直至今日,在我国有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专门法规中,笔者并没有发现明确规定适用民族地区村规民约的条款。事实上,虽然近年来有关民间法的研究逐渐升温,但国家法对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民间习惯法的重视和认可程度并未达到我们期望的高度。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我国整体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构建并不成熟;另一方面,可能正如学者苏力所说:“现代化不仅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首要目标和任务,而且也是主导当代中国制定法实践的基本意识形态。正是在这种历史追求背景下,习惯在制定法中的位置变得相当尴尬。”[21]这种“尴尬”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得这些生态环保规约的法律效力存在含糊性。
如果仔细阅读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中的生态环保条款,我们会发现有许多条文事实上对国家环保法律的制定实施起到了辅助作用。例如,生态环保规约中罗列的破坏生态环境的具体行为就对生态环境法中的一些概念起到了解释作用,而生态环保规约规定惩罚措施对于落实国家环保法律法规中规定的法律责任也大有裨益。虽然如此,我们依然能发现规约在制度架构层面所存在的冲突。例如国家法律并没有赋予村委会、议榔、侗款等基层组织罚款、行刑、强制执行等权力,但少数民族地区的很多成文或不成文的环保规约都规定了违规处理方式,比如“鸣锣喊寨”、罚“3个120”、“拉猪拉牛”进行强制执行等;甚至有些较为偏僻的地方可能还会对违规者处以刑罚。毫无疑问,这些越权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双重处罚风险都与国家法治相冲突。
民族地区的生态环保规约除了具有表达技术的简陋性以及规约本身的效力含糊性等缺点外,其在具体的实施机制上也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实际上,实施机制上的不完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种法律理念上的不完善。虽然民族地区的环保规约具有很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包含着明显的和谐观念与厌讼思想,但其在实施这些理念和规约中所表现出来的宣扬宗教迷信、影响法制统一、侵犯民众人权等行为,无疑与国家主流的法律理念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22](P57)而这种民族基层地区不相同的乡土秩序则正是两者分歧的关键所在。
笔者认为,要解决民族地区村规民约在生态环保方面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的冲突,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首要任务就是要完善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中的生态环保的规定。民族地区村规民约因为本土化和民间化致其具备种种天然优势,但也存在着诸多不适应时代的地方。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若想更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首先对村规民约的内容进行完善。如一些相对开放的少数民族村寨的村委会、党支部、寨老等有影响力的机构可以主动多学习一些立法或司法技巧,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充分发挥网络、社交媒介在规约制定和实施中的作用。实际上,从笔者到过的少数民族村寨来看,手机和电脑的普及率已经相当高,利用现代化手段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
其实,我国民族地区积习流传的许多风俗习惯与国家法的要求并无太多乖违之处。如丽江有一块清朝遗留下的《象山封山护林植树碑》,内容丰富,规定细致而简练,其中有一条规定:“倘敢不遵约束,妄于禁约界内攻凿土石,砍伐树木,纵放牧畜,任意践踏,确有证据者,许看山人役通知绅耆,指名赴地方官衙门禀报究治,决不姑贷。”规约中“指名赴地方官衙门禀报究治”其实便体现了民族地区村规民约对国家法律和处理程序的尊重。因而,国家和民族自治地方在日后对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立法之时,也应当对这些留存于民族地区的、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秩序的村规民约给予法律层面的认可与明确。而实际的情况是,“国家法的制定要考虑法制统一的原则,这就天生具有了无法兼顾各地实情的弱点,对各地的民族风情、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很难作面面俱到的考虑。”[23](P314)正是这种“无法兼顾”,致使民族地区环保规约在被国家认可的过程中遭遇或多或少的阻力。这需要民族地区对规约中的一些行为模式和制裁机制进行完善,尽量避免与国家法发生直接冲突。如西江苗寨的村规民约中将违反规约的责任形式改为交“违约金”,这便是一个值得推荐的做法。再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旧型村规民约和新型村规民约之间无论从形式还是精神上,都存在很大的不同,新规约实现了对旧规约的超越。如果村规民约自身能够不断完善,其实就意味着它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当然,完善是多方面的完善,其中包含对其实施机制的完善。这意味着民族地区在借助村规民约保护生态环境以及推行无讼、和谐、以教化为主等观念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吸收现代法治理念,对现代法治中的程序正义等理念进行充分吸收,以便从具体操作层面实现环保秩序与个人自由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