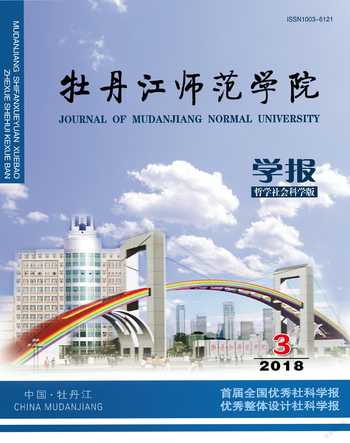《春秋》讳弑君笔法试析
2018-09-10刘春雪
刘春雪
[摘 要] 春秋时期的弑君事件所反映出的通常是此诸侯国的政治不安定、礼乐制度约束的缺失,以及周王室地位的衰微,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社会极度动荡和人民的流离失所。作为礼乐制度的坚定维护者,孔子在修订《春秋》时,对于不符合礼乐的弑君事例采用了讳弑君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春秋笔法。弑君是政治不协调的结果,而讳弑君是维护礼乐制度的需要,它不仅表达了作者的情愫,同时给释者留下无限阐释的空间。
[关键词] 《春秋》;讳弑君;礼乐制度;春秋笔法
[中图分类号]K062 K22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6121(2018)03-0085-07
在《春秋》中,共有39例弑君事例,其中孔子讳弑君的笔法有7例。从讳弑君笔法与明弑君笔法的比例上看,会很自然地生出疑问,即:为什么那几例弑君事例要用隐讳的手法加以阐释?其用意又是什么?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一、鲁国国君被弑与《春秋》讳弑君笔法
(一)鲁隐公被弑及讳弑君笔法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春秋·隐公十一年》)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了解到,鲁隐公于十一月十五日去世了。至于怎么死的,死于何地等却无从知晓。然而,考察后,我们从《春秋》三传中却能得到答案。
《左传》对此的解释是: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从此段记载中能清楚地知道,隐公并非如孔子所记的薨,他是被弑,且死于桓公及羽父之手,是血腥的权力争斗的结果。寪氏是替罪羊,羽父是表面的弑君者,而其身后是隐公之弟桓公。由《左传》可以了解到,隐公只是作为摄政王而当政的,在一定的时机内,正常情况下,他是应该把王位让于桓公,桓公即位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桓公没等到他哥哥把王位传给他就把他杀了。而在这个过程中,羽父只不过是起到引子与桥梁的作用,是他引导桓公使贼完成了弑君的过程。这其中,真正的无辜与受害者是寪氏,他在这场血腥的政治争斗不过又添上了血色。
再看《公羊传》对此的解释:
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系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公羊传·隐公十年》)
公羊家们用自问自答的形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隐公的被弑,且说出了隐公何以为“隐公”的原由,并且让读者可以了解孔子《春秋》的一些书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隐公毕竟是孔子修《春秋》的第一位鲁国国君,而隐公是在太子年幼,且鲁国与当时的强国齐、宋、郑等关系紧张,特别是与宋国正处于战争状态,为应付这种复杂局面的情况下继位的。简言之,他是为鲁国作出过贡献且无大过。此外,弑君的是另外的一位鲁国国君,而且是名正言顺的继承者,孔子怎能不为之讳书。历史虽然无法更改,但作为修书者,将其情感融入其中也是情有可原的。同时,《谷梁传》的解释也指出了“公薨不地,故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等对隐公死的基本看法,且更加明确隐公何以谥号为“隐”。在《公》《谷》二傳中,也可略窥孔子讳书的情感,即为“不忍也”。
在《史记》中,太史公详实地记载了隐公之死的过程及其原因。其原文如下:
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鐘巫,齊于社圃,館于蒍氏。揮使人殺隱公于蒍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 (《史记·鲁周公世家》)
由《史记》的这段记载可更清晰地看到公子挥(即羽父)的小人谄媚嘴脸,子允的弑君之心,以及隐公的不白之冤。
(二)鲁子般被弑及讳弑君笔法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春秋·庄公三十二年》)
从《左传》中,所看到的却是这样的事件:
初,公筑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由上文叙述可知子般被弑的前因及后果。子般的被弑,一是由于与圉人犖结的怨,而又没听庄公之劝,子般的“妇人之仁”为自己的被弑埋下祸根;二是由于庄公在立嗣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又过于刚愎自用,使得各个继嗣的政治集团之间矛盾加剧。而各个政治集团也都是被庄公的弟弟们把持的,也就是说,这属于王族内部的争斗。有关此事的前因及后果,在《史记》中记载得更为清晰明了。其原文如下:
三十二年,初,莊公筑臺臨黨氏,見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圉人犖自墻外與梁氏女戲。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柰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后奉祀;不然,死且無后。”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 (《史记·鲁周公世家》)
这种王族的内部斗争既是鲁国立嗣制度的反映,也是鲁国王族内部亲疏远近关系的呈现。庄公问嗣,同母的弟弟季友就赞同将王位传于自己的侄子般,而异母的弟弟叔牙赞同把王位传于自己的弟弟庆父。需要指出的是,鲁国的传王位制度是传子与传弟都可以的,庄公本身是想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如果这样,庄公就不得不为子般立嗣扫除障碍,这样,庆父叔牙的政治集团必须有所牺牲。史料记载的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叔牙被鸩死,庆父残存。但是,当庄公薨,子般立势未稳之际,庆父立即纠集余党及子般的仇敌进行反扑,其结果是子般被弑,季友奔陈。从庄公死到子般被杀,这中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可谓“孝衣血色”。
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如此看重“孝弟”的孔子是不可能将本国王族内部的兄弟、叔侄之间的不孝不弟的事直白于天下,与人笑柄,让人效仿的。整个子般被弑的过程,将鲁国王族内部的不孝不弟之事呈现得淋漓尽致。而作为传鲁史又极看中“孝弟”之事的孔子,其不得不为之隐的苦衷还是能够让人接受和理解的。
在《国语》中,关于庄公有这样两段记载,其原文如下:
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匠师庆言于公曰:“臣闻圣王公之先封者,遗后之人法,使无限于恶。其为后世昭前之令闻也,使长监于世,故能摄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健而君侈,令德替矣。”公曰:“吾属欲美之。”对曰:“无益于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已矣。”公弗听。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妇觌用币。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对曰:“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夫妇贽不过枣、栗,以告虔也。男则玉帛、禽鸟,以章物也。今妇执币,是男女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不可无也。”公弗听。
(《国语·鲁语上》)
从这两段文字不难看出,庄公做事是有些不顾当时礼法的。他好任性为之,且刚愎自用,这种对礼的不遵守无疑与其君位不称,同时,也会引起臣民不满和对其的不尊重。可以推断,子般之事的发生也可以说是必然,是庄公“所作所为”的直接后果。而闵公被弑也可看为是子般被弑及鲁内乱的继续。
(三)鲁闵公被弑及讳弑君笔法
《春秋·闵公二年》曰:“秋,八月辛丑,公薨。”
对此,《公羊传》却一针见血指出: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公羊传》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真相,即闵公非薨,乃庆父所杀且庆父连杀二君。而《左传》和《史记》则分别陈述了事件的经过。如,《左传》所载: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左传·闵公二年》)
而《史記》记载得更加详实:
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及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尸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 (《史记·鲁周公世家》)
庆父(共仲)立闵公而又弑之,与哀姜有很大的关系。在庄公未死之时,庆父就与哀姜私通。而庄公迎娶哀姜之时,庄公就有许多违礼之事。而反过来,哀姜与庄公的弟弟私通,可说是对庄公的莫大讽刺。于此同时,哀姜与子般与闵公的被弑也有着直接关系。在这两个事件中,哀姜的作用是与庆父等同的,甚至可以说是主谋,同样是弑君的刽子手。从《左传》《史记》的叙述中可知,庆父连杀二君,终于引起了鲁国上下和其他诸侯国的不满,被迫自缢而亡。与他狼狈为奸的哀姜也被齐侯处死。这二起弑君事件的发生,可以说都是庄公所作所为的后遗症,其对立储问题的不坚决,使庆父产生怨恨,又没处死他,于是留下祸根。同时,庄公对礼仪的不在意,也使其内墙出丑,叔嫂通奸,最终导致闵公被弑。对于这一系列鲁国宫墙内的丑剧,作为严谨又有着自己独到见解的孔子,将其避讳起来不无缘由。众所周知,孔子非常注重纲常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人伦大节的思想是本,不应该被破坏。孔子对违背这些人伦纲常的做法是嗤之以鼻的。而鲁二君的被杀,正是对人伦大节的严重破坏,在孔子看来是不值得载入史册的。鲁昭公二年,韩宣子适鲁见易象及鲁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鲁国当时是在人眼中礼仪盛行的国度,而孔子又是对周礼极力推崇、维护的,他怎忍心看自己的国君及王族对礼仪破坏殆尽而将其写入《春秋》呢?但是,作为史家,他对发生的事还得记载,所以只能用隐讳笔法记录。不难看出,孔子的民族情感及民族自尊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鲁子赤被弑及讳弑君笔法
冬,十月,子卒。(《春秋·文公十八年》)
这样简短的一行字很难让人了解其内幕。这里面所传递出的信息,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子”死了。至于“子”是谁,为什么要记录下来等一系列问题都不得而知。然而,再看《公羊传》的解释,就知道了“子”原来是子赤,并了解他是被弑的。其原文如下: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公羊传·文公十八》)
但是,这里的记载仍是粗略的,对于事情的经过及原委还是不得而知。进一步查找,《左传》中给出了答案。其原文如下: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左传·文公十八年》)
《左传》直书“書曰“子卒”,諱之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孔子讳书的解读。由《左传》的阐释清楚地知道,子赤的被弑是襄仲在齐侯的支持下完成的。这次弑君与以往不同,是在外国诸侯的干预下进行的,有大国对小国操纵的味道,并非完全是内部的争斗。同时,作为导火索的宫廷内丑剧也无法遮蔽。孔子为这样的事讳书,主要原因是,子赤的被弑是在齐侯的允许下进行的。自己的国君生死被别国国君操纵,被外诸侯支持的势力所杀,这种整体的国家与民族侮辱,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作为修史书的孔子,怎能把有辱国家与人民尊严的事记录下来?此外,将其隐去的做法也代表着一种愤恨与不满,即:对襄仲的愤恨,对宣公的不满,这体现了孔子对其的蔑视,以及对当权者尊威的一种维护;同时,也体现了孔子修书的一个原则——婉而成章。
上述四例都是鲁国的国君被弑而隐讳阐释的。而在《春秋》中,鲁国也只有四例弑君事件。对鲁国的弑君问题全都隐讳着写,也体现着孔子修《春秋》的基本书法。在《左传》中,君子曰有这样内容:“《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成公十四年)。孔子记载鲁弑君之事的委婉与隐讳,其原因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孔子作为鲁国人修鲁史,一定会考虑当权者的感受,这种王族内的相互杀戮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与展示的。同时,这种兄弟间、叔侄间骨肉相残的事情,不符合孔子的“孝弟”思想的,是对周礼的极大破坏。其次,鲁国作为周公的封地,是礼乐文化相对发达之地,有着传统的礼乐文明,而在这样的地方却多次发生弑君事件,其礼乐文明令人怀疑,也可说是对其文明的一种否定。故此,将其隐去不仅是对本国的尊重,也是孔子自身情感的一种体现。
二、非鲁国国君被弑与《春秋》讳弑君笔法
(一)郑僖公被弑及讳弑君笔法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春秋·襄公七年》)
《公羊传》中,将事件的始末与成因展现了出来。原文如下:
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弒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公羊传·襄公七年》)
从《公羊》传的阐释可知,郑僖公是被其大夫在自己的国土上所弑,原因是他不同意大夫的“亲楚离中”的意见,且郑僖公有逆礼违常之为。而孔子隐是为了中原诸侯国的颜面。中原诸国要会盟,且僖公为了去会盟与大夫子駟意见相左被弑,所以把他的被杀记录下来对诸国也不是光彩的事,这体现了中原势力的下滑。而从整个当时诸侯国政治形势来看,其大夫的意见是正确的,是可行的。郑僖公违礼在先,不听劝在后,终招杀身之祸。而《春秋》“所言如会,未见诸侯。”其意正如《谷梁传》所载:
“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逾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这样的一番阐释就更加清楚了,如会而未见,其实已不是僖公如会,只是郑国的一个象征性的代表,通告各国郑君已无罢了。这时的郑国已经要与中原诸侯国分离而倾向于楚国。郑僖公的逆礼违常在《左传》中有明确记录,且对他的三次“不礼”及侍者谏而被杀僖公的暴虐颇有微词。其原文如下: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左传·襄公七年》)
从整个弑君的过程来看,郑僖公的过错似乎更大些,但也展示了春秋时代出现的所谓的“礼崩乐坏”的局面,体现出一种民主的进步——君不谋其政,废君的作法。僖公的被弑并不值得惋惜,但中原势力的下衰却让孔子担忧。这已不是简单的臣废君,而是楚国新势力的强盛,已经影响到中原新格局的面貌,有夷狄凌驾于诸夏之感了。
(二)楚王郏敖被弑与讳弑君笔法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春秋·昭公元年》)
《左传》将事情的始末记载了下来: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於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左傳·昭公元年》)
在这段记载中,楚公子围要弑君的想法早已被郑子产所料,一来可见子产的深谋远虑及对事情分析的准确;二来也可看出楚子围的野心早已被人所知。
(三)齐侯阳生被弑与讳弑君笔法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春秋·哀公十年》)
《左传》的记述也很简单,事情经过也不是很明了。其原文为: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左传·哀公十年》)
而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这样记载:
“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吳。”
是鲍子与其君有怨,趁吴、鲁伐齐之机而杀了悼公。
考察后两例弑君事件,无论《左传》还是《史记》等资料记载得都很简略,有些地方很难看出孔子的真正用意。但是,从整体讳弑君的事例中能感受到孔子讳的一些原因:为亲者,尊者,贤者讳。同时,孔子在对一些弑君问题上,也极力回收自己的情感,對与本国王族内的骨肉相残的行为,蔑视与痛恨都不足以表达其感情。弑君是政治不协调的结果,而讳弑君是维护礼乐制度的需要,它不仅代表着作者的情愫,也给释者以极大的阐释空间。
附:三十九例弑君事件
一、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桓公完;二、隐公十一年,羽父使贼弑鲁隐公姑息;三、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殇公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四、桓公十七年,郑高渠弥弑郑昭公忽;五、庄公八年,齐襄公诸儿被弑;六、庄公十二年,宋万弑宋闵公;七、庄公十四年,郑傅瑕弑郑子仪庄公;八、三十二年,庆父弑子般;九、闵公二年,庆父弑鲁闵公启方;十、僖公九年,晋里克杀奚齐及君卓;十一、僖公十八年,齊人殺無虧;十二、僖公二十四年,晋怀公被弑;十三、僖公三十年,卫杀其君公子瑕;十四、文公元年,楚成王被弑;十五、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文公十六年,宋昭公杵臼被弑;十七、文公十八年,齐懿公商人被弑;十八、文公十八年,鲁襄仲弑子恶;十九、文公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二十、宣公二年,晋灵公夷皋被弑;二十一、宣公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二十二、宣公十年,陈灵公平国被弑;二十三、成公十八年,晋弑其州蒲;二十四、襄公七年,郑僖公髡顽被弑;二十五、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襄公二十六年,卫宁喜弑其君剽;二十七、襄公二十九年,阍弑吴子馀祭;二十八、襄公三十年,蔡景侯固被弑;二十九、襄公三十一年,莒公买朱被弑;三十、昭公元年,楚公子围弑其君楚郏敖;三十一、昭公十三年,楚灵王熊虔被弑;三十二、昭公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十三、昭公二十七年,公子光弑吴王僚;三十四、定公十三年,薛弑其君比;三十五、哀公四年,蔡昭公申被弑;三十六、哀公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荼;三十七、哀公十年,齐侯阳生被弑;三十八、哀公十四年,齐陈恒弑其君简公壬;三十九、哀公十七年,卫庄公蒯聩被弑。
[参考文献]
[1]刘鹏.春秋弑君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6.
[2]宋秀秀.司马迁笔下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弑君事件[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2):42-45.
[3]吴秉坤.《左传》叙事与弑君凡例之关系[D].北京:清华大学,2006.
[4]孟翔为.从鲁国的弑君现象看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J].绥化学院学报,2016(3):76-79.
[责任编辑]李献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