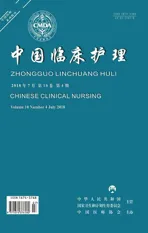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创伤后护理人员的成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2018-07-30王莉莉师晓辉
王莉莉 师晓辉 杜 瑾
工作场所暴力是指工作人员在其工作场所受到辱骂、威胁或袭击,使其安全、幸福和健康受到明确或含蓄的挑战[1]。在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医疗场所,护理人员作为高危人群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发生率可高达64.3%~86.7%[2-3]。暴力事件严重影响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正常工作和生活,影响护理事业长远发展[4-5]。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指经历挑战性的生活危机事件后个体体验到的积极心理变化[6],表现在与外界关系、自我认知、人生观等方面发生正性变化[7]。目前,国内外对护理人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状及影响因素等方面[4,8-9],很少有关暴力事件创伤后成长的研究。本研究旨在调查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创伤后成长水平,探讨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提高护理人员创伤后成长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7年2~6月南京市2所三级甲等医院经历工作场所暴力的340名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工作年限≥1年,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注册护士;②临床一线工作科室护理人员;③身心健康;④知情、同意参加本研究。其中男22名(6.47%)、女318名(93.53%);年龄22~53岁;工作年限1~21年;已婚107名(31.47%)、未婚233名(68.53%);中专48名(14.12%)、大专82名(24.12%)、本科及以上210名(61.76%);护士118名(34.71%)、护师134名(39.41%)、主管护师及以上88名(25.88%);非正式编制人员90名(26.47%)、正式编制人员250名(73.53%)。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称、工作年限、科室、聘用方式、婚姻状况。②工作场所暴力量表(workplace violence scale,WVS) 由Schat 和Kelloway[10]研发,中文量表由王培席[11]参考其条目及计分方式编制而成,量表包含言语性骚扰、威胁恐吓、情感虐待、躯体性骚扰、躯体攻击5个条目,每个条目计0~3 分,总分为0~15 分,分数越高表示暴力频度越高。
频度分级为零频度、低频度、中频度、高频度得分范围分别为0分、1~5 分、6~10 分、 11~15 分,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2[12]。③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由国外学者Tedeschi等[13]编制,汪际等[14]译,包括精神变化、欣赏生活、个人力量、新的可能性、与他人关系5个维度,21个条目。从 “完全没有”到“非常多”采用0~5分Likert 6级法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创伤后成长水平越高,各维度及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611~0.874。
1.2.2 资料收集
为避免二次心理应激,对遭受创伤者进行认知测量不宜于遭受创伤2周内进行[15],因此本调查中所有护理人员的调查时间距离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的受伤时间均在2周以上。由经过培训的调查者发放问卷,填写问卷前对调查目的、意义进行说明,统一指导语,匿名填写。对研究对象提出的问题当场解答,现场回收问卷,核实并确保问卷填写的完整性、有效性。本研究发放问卷340份,回收有效问卷340份,有效回收率100%。
1.3 统计学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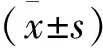
2 结果
2.1 护理人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现状
被调查的340名护理人员中,遭受情感虐待324名,占95.29%;遭受威胁恐吓196名,占57.65%;遭受躯体攻击38名,占11.18%;遭受言语性骚扰24名,占7.06%;遭受躯体性骚扰4名,占1.18%。低频度212名,占62.35%; 中频度103名,占30.30%; 高频度25名,占7.35%。
2.2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护理人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创伤后成长得分比较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的护理人员PTGI总均分为(58.45±16.83)分。不同性别、职称及婚姻状况的护理人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创伤后成长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护理人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创伤后成长得分比较 (n=340)
2.3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创伤后成长预测因素
以创伤后成长得分为因变量,性别、职称及婚姻状况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为:男=0,女=1;护士=0,护师=1,主管护师及以上=2;已婚=0,未婚=1。结果显示,性别、职称及婚姻状况是护理人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见表2。

表2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创伤后成长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调整的R2=0.187;F=4.591,P<0.001
3 讨论
3.1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创伤后成长水平不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创伤后成长总均分为(58.45±16.83)分,表明护理人员在经历工作场所暴力事件后,创伤后成长处于中等水平,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分析原因:工作场所暴力可增大护理人员的职业压力、带来各种负性情绪,致护理人员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甚至引起其行为和目标变化[4]。既往研究[16]表明,大多数护理人员未接受工作场所暴力安全防范培训,相关知识及安全意识的缺乏使护理人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时毫无防备,需要较长时间从创伤的伤害中恢复,且大部分医院缺少完善的暴力事件汇报系统,对暴力事件处理不当,受害的护理人员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17-18]。再者,媒体片面甚至失实的报道,致使社会舆论给予医护人员不公正的关注和评价,把罪恶的源头归结到护理人员身上,致护理人员工作场所暴力创伤后成长水平低。
3.2 不同人口学特征对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职称、婚姻状况的护理人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创伤后成长水平不同。创伤、反思、认知结构的改变有利于个体创伤后成长。女性对创伤事件更加敏感,容易产生焦虑等负性情绪[19],而负性情绪能够调动女性对创伤事件的反思和再认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性通常表现坚强、勇敢的形象,与女性相比男性更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导致创伤事件后男性获得的社会支持与关注比女性少,故女性创伤后成长水平更高。职称高的护理人员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丰富,通过反思、整合自身潜在的资源,比职称低的护理人员有更强的自我恢复、更新以及重塑能力;且职称高的护理人员往往是护理职能结构中的管理岗位,经历了更多的工作磨练,对创伤事件的认知能力、解决创伤问题能力以及控制内心感受的能力较强;而职称低的护理人员往往更多关注创伤事件本身所带来的持续的内心痛苦,故创伤后成长水平低;此外,职称高的护理人员通过继续教育学习获取信息的能力较高,可通过多种渠道发泄不良情绪[20],较快调整创伤后心理;职称低的护理人员由于专业技术不熟练、沟通技巧匮乏,容易造成其身心处于紧张、疲惫的状态,致创伤事件后调整较慢。研究[21]表明,情感支持促进个体创伤后积极改变高于信息、物质支持,更利于创伤后成长。已婚的护理人员能够获得来自配偶更多的情感支持,促进其与社会的接触和情感交流,减少情感和社会退缩,故已婚护理人员创伤后成长水平较高。
3.3 工作场所暴力频度对护理人员创伤后成长影响的分析
Laufer等[22]研究发现,创伤后成长水平受个体对创伤程度评价的影响,个体主观认为创伤越严重其创伤后成长水平越高,创伤频度的增加使个体主观体验到的创伤越严重,故创伤后成长水平越高;但创伤频度继续增加,创伤事件累计的结果过于严重,超出了个体心理承受能力的底线,正性心理资源透支过度,应急能力耗尽,激起个体创伤后应激障碍,故创伤后成长水平随之下降。
4 结论
本研究中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的护理人员创伤后成长处于中等水平,性别、职称、婚姻状况是其影响因素;创伤后心理调适影响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及其工作状态,提示护理管理者应加大对护理人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创伤后成长的重视程度,职业培养中加强工作场所暴力相关培训,以提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创伤后成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