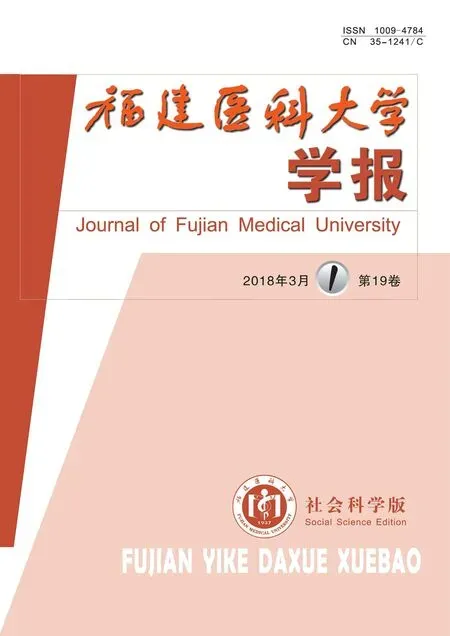“场域-惯习”视角下张爱玲的翻译及其译作接受
2018-04-18游晟
游晟
(福建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张爱玲是华语文坛一位才华出众的女性。1962年,夏志清首开先河,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推举张爱玲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称赞其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曼斯菲尔德、波特、韦尔蒂、麦卡勒斯之流相比[1]。张爱玲小说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而其译者身份却长期为人们所忽视。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张热”的蔓延,译者张爱玲终于浮出地表,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界。目前张爱玲的翻译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方面:(1)《金锁记》的自译研究;(2)张爱玲的女性主义翻译诗学研究;(3)《海上花》翻译研究;(4)多元系统理论下张爱玲的翻译研究。当前“张学”的“翻译转向”凸现了对张爱玲的翻译活动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然而,人们在关注张氏翻译时,往往停留在对其翻译策略讨论的层面上,对影响张爱玲翻译选材及策略应用的深层次原因缺乏深入考察。作为一名才华出众且精通双语的译者,张爱玲用中文翻译的作品在华语地区反响热烈。但在长达40多年的海外生活中,张爱玲用英文翻译或改写的作品却屡屡受挫。笔者拟以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考察张爱玲的翻译活动并分析其译作接受情况迥然不同的原因。
一、“场域—惯习”理论概述
布尔迪厄在社会学研究中受磁场的启发,提出了“场域”与“惯习”两个核心概念。其中,“场域”(field)指“具有自身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2],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由经济场、艺术场、文学场等不同场域组成,各场域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因内部分裂及外部对立而彼此分隔[3]。在各场域内部,行动者(agent)负载着资本(capital),为争夺有利位置或提升现有资本与其他行动者斗争,使场域内充满变革。在各场域外部,权力场决定着资本分配与社会结构,处于支配地位,文学场等其余子场域则处于被支配地位。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惯习”(habitus),它指行动者在成长、教育、工作等社会化的过程中,“经由积累传递而逐渐形成的持久、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4]。一方面,场域中的行动者在长期社会化的过程中,学习并内化场域的规则形成惯习。另一方面,行动者会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身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倾向,从而产生新的惯习并作用于其所处的场域。
“场域-惯习”视角下的翻译场有自己独特的运作规则,由于翻译具有跨文化的特殊属性,翻译场受周围其他场域(如文学场、政治场等)和权力场的影响,并非一个完全独立的场域。换言之,翻译活动不仅在翻译场中发生,它“同时发生在其他场域之中,与相关场域的规则相互渗透、相互影响”[5]。因此,“场域-惯习”视角下的翻译可视作由译者、赞助人、出版商、读者等行动者负载着各自的资本在场域中相互竞争、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活动。其中,译者在翻译场与其他场域的相互作用影响下逐渐形成自己的惯习,从而作用于自身的翻译实践。译者的惯习不仅影响其翻译策略、措辞等微观方面,还在宏观方面影响其对文本的选择。
二、张爱玲翻译活动概览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初登文坛就创作了《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等一批优秀的作品并迅速成名。相较于创作生涯,张爱玲的翻译事业则要平淡许多。1941年,张爱玲摘译了Margaret Halsey的作品《谑而虐》并刊载于《西书精华》第6期。其后几年,她牛刀小试,陆续在当时的流行报刊杂志中登载译作。1952—1955年,张爱玲翻译了以TheOldManandtheSea为代表数量众多的美国文学作品,翻译事业也逐渐步入佳境。张爱玲离港赴美后,不断尝试用英文改写或翻译一些自己的作品,如TheRougeoftheNorth,NakedEarth,Shame,Amah!,LittleFingerUp等,但均反响平平,未能进入主流市场。20世纪80年代后,张爱玲转向吴语小说《海上花》的白话文译介。此后,张爱玲的翻译生涯接近尾声。
张爱玲的翻译活动具有“多维度,多面向的特征”[6]。她曾多次翻译他人及自己的作品,体裁不仅涉及散文、诗歌、小说等多种文体,更囊括了英译汉、汉译英及语内翻译等不同形式。依据布尔迪厄的观点,运用“场域-惯习”进行社会学研究,必须考虑以下三个必要环节:分析与权力场相对的场域位置,勾画出行动者在场域中的客观关系结构,分析参与者的惯习[3]。从“场域-惯习”的视角来看,前两个环节属于与场域直接相关的外部因素,而“参与者的惯习”属于内部因素。笔者分别从外部的场域及内部的译者惯习着手,研究张爱玲翻译文本的选择及翻译策略的使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译作在中美各自文化语境中的接受情况并分析其原因。
三、香港文学场中张爱玲的翻译惯习及其译作的接受
1952年,张爱玲离沪抵港。彼时的香港是美国在亚洲推行冷战政策的重要阵地。为扩大“美元文化”的影响,美国在香港地区设立办事处及今日世界出版社等机构,藉译介大量美国文学经典作品宣传美国思想文化并大力推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1952—1955年,张爱玲受雇于美国新闻处驻香港地区办事处(以下简称“香港美新处”),翻译了大批美国文学作品,这一时期成为张爱玲最为集中且大量进行文学作品汉译的阶段。
(一)香港文学场中张爱玲的翻译惯习
由于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成立背景及其译作的特殊使命,这一阶段的翻译文本由“香港美新处”的文化参赞和华盛顿方面负责,也有些是香港方面挑选[7]。“香港美新处”作为张爱玲留港期间的赞助人,对作品的遴选环节十分重视。这一阶段翻译选材主要体现的是赞助人的作用,译者张爱玲在文本选择上并没有太多发言权。但这一时期张爱玲的翻译活动,仍可看出其翻译涉及的品种繁多、体裁广泛,作品风格也大为迥异(表1)。

表1 张爱玲美国文学汉译作品一览表
上列书单的作者有“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与梭罗、“迷惘一代”的海明威等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译作中既有清新自然的小说,又有浪漫典雅的诗文,还有庄严肃穆的政论。虽然题材内容各异,但上述译介的对象无一不是美国文学史上的巨作,且选择的篇目有意避开了同时期较有影响力的揭露美国社会黑暗面的作品,均为宣扬美国文化艺术与社会价值的作品,“香港美新处”文化外宣的目的展露无遗。
在冷战背景下,香港文学场为有效传播美国文化及价值观,要求译者翻译的语言忠实通顺、风格自然流畅,从而降低中文读者的阅读障碍,达到传播甚至教化的目的。受这一主流规范的影响,张爱玲从事的美国文学译介不是简单的英汉双语转换,而是一项以文化输入为旨归的传播活动。其译作不仅要完整忠实地传达原作信息,还需让读者顺畅自然地接受美国文学与文化,达到意识形态传播的目的。
参照“完整忠实”这一要求,张爱玲没有对原作进行任何的删减或增补,而且十分注重对原作风格的把握与拿捏,有些地方甚至是逐字对应。
例1:But I must get him close,close,close,he thought.I mustn’t try for the head.I must get the heart[8].
译文:但是我一定要把他拉得很近,很近,很近,他想。我千万不要刺在头上。我一定要戳到心里去[9]。
上例描写的是老渔夫Santiago在海上与大鱼搏斗时的心理活动,展现了他与困难抗争的大无畏精神。张爱玲在译作中使用了两个动词“刺”“戳”,准确还原了果敢坚韧、不屈不挠的主人公形象。在句式的安排上,原作中海明威接连使用了三个“close”表现主人公想要制服大鱼的急切心理,张爱玲在译文中严格按照英语的行文句式,用了三个连续重复的短句“很近”将之如实译出,恰到好处地渲染了捕鱼时紧张的气氛,句式安排上与海明威的“电报体”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忠实原文外,因“香港美新处”提倡“译文注重流畅、易读,适合中文读者,读起来没有语法、结构上的障碍”这一翻译理念[7],张爱玲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了大量归化策略。譬如,在翻译TheLegendofSleepyHollow与TheYearling时,她使用了大量中文四字成语,如:兴风作浪、鬼影幢幢、不遗余力、营营扰扰、循私枉法、心猿意马、南征北讨、酩酊大醉、蛮横忤逆、精疲力尽、狼吞虎咽等,将远在异国的故事主人公带进了中国读者熟知的世界。归化策略的使用消除了英汉两语间的障碍,使译文更加流畅易懂,也使译文更容易为中文读者接受。
鉴于冷战时期信息闭塞,多数中文读者对美国文化感到陌生,为了帮助读者更透彻地领悟原作的内涵与真谛,张爱玲在多部译作前补录了自拟的序言或“译者识”,详尽介绍了作家背景与文本主旨,深刻剖析了其阅读和翻译时的心路历程。譬如,在翻译《爱默生选集》时,张爱玲于译者序中系统地梳理了爱默生的生平与创作思想。在译介另一位超验主义大师梭罗的作品时,她同样在译作前补充了一篇类似于随笔性质的介绍文章《梭罗的生平和创作》,将自己对梭罗的独特见解融入文中,称赞其诗作“有一股天然的劲道和不假借人工修饰的美……就好像我们中国古时的文人画家一样,梭罗并不是一个以工笔见胜的画匠,可是他胸中自有山水,寥寥几笔,随手画来,便有一种扫清俗气的风度。……又像中国古时的忠臣良将,平日里就有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凌云壮志”[10]。张爱玲的介绍中没有冠冕堂皇的术语和连篇累牍的文字,仅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梭罗创作风格的大致轮廓。远隔时空的梭罗此刻仿佛化身为我们熟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工笔画家与良将忠臣。由此一来,读者与作者的距离便一下拉近了许多。正是通过增补译者序等副文本,张爱玲在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穿越时间地域的阻隔,把远在大洋彼岸的作者和他的超验主义思想带入中国读者的视界。
(二)香港文学场中张爱玲译作的接受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不断加剧,冷战格局逐渐成型,香港文学场也笼罩在浓厚的冷战氛围中。美国以香港地区为基地,通过书刊、新闻、文化外交等媒介大力宣传美国文化。此时,许多受战争影响滞留香港的优秀作家回归内地,香港文坛陷入沉寂期,文艺刊物寥寥无几,多数文学作品价值不高。处于真空期的香港文学场迫切需要一批高质量作品打破创作贫乏、思想封闭的局面。美国抓住这个契机,聘请大批精通中英文的译者加入其翻译计划,力图扩大其在香港乃至远东地区的影响力。1952-1955年这一阶段张爱玲的翻译实践作为“香港美新处”译介美国文学计划的一部分,服务于美国文化外宣政策,旨在经由文学作品汉译传播并彰显文本中蕴含的美国主流价值观。这一计划的翻译作品由赞助人“香港美新处”指定。在翻译过程中,张爱玲不仅按照规范要求,完整忠实地传达出了原作信息,在此基础上,考虑到译作的流畅性和易读性还运用了归化策略使读者较为顺畅地通读译本。此外,张爱玲还在一些作品前加写了较长篇幅的译者序或前言等附文本,为读者补充作品相关的背景知识。可以说,此阶段张爱玲的翻译惯习不仅契合了当时香港文学场的翻译规范,也满足了读者对作品的阅读需求。这使她的译作不仅在当时的市场上可见度很高,广受华文世界读者欢迎,也成为了“在知识闭塞的冷战时代,香港和其他华文地区接触新知、了解美国文学与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7]。
四、美国文学场中张爱玲的翻译惯习及其译作的接受
1955年张爱玲赴美后,便着手英文写作,希望籍此在异乡崭露头角。然而,张爱玲的英文创作之路却并不像她预想的那样顺畅。TheRiceSproutSong虽获报界好评却销路不佳,另一部TheNakedEarth则找不到一家愿意提供赞助的出版社。两次尝试遇挫后,张爱玲把目光转向了其40年代的成名作《金锁记》。1956年,张爱玲用英文将这部作品改写为PinkTears(此稿现已失散),遭Scribner公司拒绝出版后再度自我改写为TheRougeoftheNorth[11],直至1967年才由英国Cassell出版社出版,但读者反应非常冷淡。而此时,TheRougeoftheNorth的中文版《怨女》已在港台连载,风行一时。1971年,张爱玲再次将《金锁记》译为TheGoldenCangue,收录于夏志清主编的TwentiethCenturyChineseStories中。之后,张爱玲彻底放弃了打入英语世界的想法。纵观张爱玲汉英翻译活动的年表,可以发现在其近半个世纪的海外生活中,张爱玲不断翻译或改写着《金锁记》。这其中时间跨度巨大、涉及过程繁杂,不仅是张爱玲创作经历中的特例,也是中国文学翻译史中绝无仅有的案例。因此,《金锁记》到TheRougeoftheNorth的自我改写是张爱玲现存汉英翻译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笔者就以该作品来考察美国翻译场中张爱玲的翻译惯习及其译作的接受。
(一)美国文学场中张爱玲的翻译惯习
经历了TheRiceSproutSong与TheNakedEarth两部英文小说的失败后,张爱玲急需一部有创见的英文作品在海外立足,早年成就其蜚声上海文坛的《金锁记》成了不二之选。从《金锁记》到PinkTears,由TheRougeoftheNorth到《怨女》和TheGoldenCangue,远离故国的张爱玲在20多年中反复改写与翻译着一个故事,她的文学惯习和翻译惯习在中英文的四度延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张爱玲坦言自己的文学创作受中国旧小说的影响较深[12],从《金锁记》到TheRougeoftheNorth两部小说叙事结构的变化尤其凸显了张氏文学惯习中浸润着的中国传统诗学。《金锁记》中有多处描写借鉴了西方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让小说的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呈现出“错时”结构[13]。相较之下,TheRougeoftheNorth的叙事则严格按照故事时间推进,复归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技法。此外,赴美后的张爱玲遭遇了事业与生活的双重打击,早年“出名要趁早”的壮志激扬已然被磨蚀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平淡近自然”的创作心态[14],这点在《金锁记》和TheRougeoftheNorth的人物设定变化中可见一斑。在早年写作的《金锁记》中,主人公曹七巧受封建制度迫害又疯狂害人,逼死媳妇,破坏子女婚姻,最后孤独终老。其个性极端癫狂病态,充分彰显了人性中恶毒的一面。而TheRougeoftheNorth的Yindi同是封建旧制度的受害者,其害人的程度却轻了许多,最终尚且能儿孙满堂。Yindi作为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不彻底的人物”,其性格平淡内敛许多,展现了中国传统女性在没落的封建豪门中无奈挣扎与最终沉沦的命运。两部作品主人公的对比充分展示了张爱玲文学惯习从“大红大绿”式的对照到“参差的对照”的转变[15]。张爱玲赴美后文学惯习的变化决定了《金锁记》和TheRougeoftheNorth叙事安排与人物设定的变化。
张爱玲在翻译时也承袭了其文学惯习,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从词语、句式到篇章结构都严格按照中文范式,采用了直译的策略。对于TheRougeoftheNorth的英译本中几个称谓,张爱玲采用了汉语发音标注附加英文夹注的形式。如在处理汉语中特有的称谓如“姑爷”“姑奶奶”时,张爱玲分别使用了“Gu-ya”“GuNana” 等威妥码注音,同时为了传达这两种称谓在汉语中的特殊意义,于其后又补充了 “the polite terms for the son-in-law and the married daughter of the house, called Master of Miss and Madame Miss”,详细解释了两种称谓的文化内涵。除人名称谓外,张爱玲在翻译中文谚语时也多采用直译策略。
例2:嫌我丢脸,皇帝还有草鞋亲呢[16]。
译文:So I shame you by coming. Even emperors have relatives in straw sandals[7].
例3:弯弯扭扭尖厉的鼻音,有高有低,像一把乱麻似的,并成一声狂喜的嘶吼,怪不得是红白喜事两用的音乐[16]。
译文:The wiggly nasal squeals at a dozen different pitches blended into a single exultant blare. No wonder the same music was used in both ‘red and white weddings’—‘white wedding’ being euphemism for funeral[17].
例4:她在灯下看着他在红封套上写“长命百岁”“长命富贵”[16]。
译文:She made him write inside the gold bordersLonglife,hundredyearsorLongevity,wealthandinfluence[17].
例2中的“皇帝还有草鞋亲”是汉语的一句俗语,意在表示不能瞧不起穷困潦倒的亲戚。小说里Yindi的哥哥去看望她,兄妹二人拌嘴时,哥哥情急之下说了这么一句。张爱玲并未用“look down upon”或是 “despise”这类浅显易懂的英文表达女主人公内心对哥哥的鄙视,而是颇具创意地用了“emperors have relatives in straw sandals”这样一个意象,将故事中东方话语中蕴含的独特且陌生的意象直接呈现在了西方读者面前。例3中的“红白喜事”在汉语中泛指婚丧,张爱玲没有用直白简明的“wedding and funeral”替代,而颇费周章地使用了“red and white weddings”,严格照应了中文的“红白喜事”,再于其后增加了“白事”一词的解释以方便英文读者的理解。例4中“长命百岁”直译为“Longlife,hundredyears”,完整地保留了汉语中人们对永生及长寿的祈祝。上述3例无不证明了张爱玲的翻译惯习承袭了其文学惯习中浓厚的东方情结,并立足于中国文化,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汉语独特的魅力。
(二)美国翻译场中张爱玲译作的接受
张爱玲在TheRougeoftheNorth的翻译过程中,从文本选择、叙事安排、人物设定及翻译策略运用中均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力求彰显作品中古老的东方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读者从作品能够更真实地体察到旧中国的民俗风貌。这样一部作品在美国为何为读者所不识,此中原因可以从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中窥之一二。“Knoph我记得是这些退稿信里最愤激的一封,大意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如果过去的中国是这样,岂不连共产党都成了救星。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18]张爱玲在TheRougeoftheNorth的翻译中避开了激进的国家主义的渲染,聚焦于旧中国的“荒废、混乱及焦灼不安的个人主义”[12],通过日常生活中婚丧嫁娶等题材的描写揭示了封建社会旧家庭的劣根性。但就彼时的美国文学场而言,这种对中国封建家庭制度“平淡近自然”的描写无法满足其对中国的二元想象,即中国是“由口吐金玉良言的儒家哲学家们组成的国度”或“训练有素的共产党员统治着那批哲学家”[12]。张爱玲的作品既不像林语堂一样能够借助儒家哲学的旷达情怀激发西方读者的兴趣,也不像韩素英的作品一般亲近共产主义,能为西方提供瞭望新中国的窗口。相反,TheRougeoftheNorth中“因国耻而生的自鄙”及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不仅不为美国文学场接纳,甚至被别有用心的出版商视作共产主义的颂歌[12]。此外,彼时美国文学场中的读者主要集中在 “那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了到越南战争中期这段时间,习惯阅读《读者文摘》及《生活杂志》的大学生及中年中产阶级人士”[19]。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他们的记忆仍然停留在赛珍珠对于古老东方的印象中,这一批读者对中国普遍存有好感;加之美国政府在“越战”中的表现让他们开始抨击上一代的文化,“并逐渐在完全陌生的农民文化社会中,找寻‘真实的象征’”[19],此刻的中国成了这批读者急于寻找理想、救赎信仰的地方。然而,张爱玲在改写中秉持的态度却是“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揭穿的……”[18]她作品中对人性的揭露和探索,对社会道德的批判让西方读者“想用如田园诗般和平安宁的中国文化救赎欧洲的精神文化危机”的梦想瞬间成了泡影[20]。张爱玲赴美后与美国文学场主流规范相悖的文学惯习和翻译惯习导致了TheRougeoftheNorth的“滑铁卢”,也让她打入主流作家行列的愿望成为泡影。
五、结语
从“场域-惯习”视角考察张爱玲的美国文学汉译及其中文作品英译这两个阶段,可以发现以下两个特征。一方面,张爱玲译介了大量美国文学作品,因彼时处于冷战时期的香港文学场受制于权力场,张爱玲在翻译时充分传达了源语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借助了归化策略帮助中文读者更好地接受信息,译者的翻译惯习与彼时香港文学场的主流规范相契合。张爱玲的美国文学中译对当时港、台地区读者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甚至“时至今日依然是中文世界有关英美诗歌的最佳翻译及入门书籍之一”[7]。另一方面,张爱玲离港赴美后,曾先后从事英文写作与翻译,却始终未能如愿打入英美市场。这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张爱玲选择了早年的成名作进行翻译,希望以书中的东方文化来吸引外国读者,因而在翻译时不断地重现源语文化的特色,其间无论是作品中的人名、物名还是传统谚语均采用了直译的手法。而就读者的接受能力而言,这种几近异化的方式虽然忠实地传达了中国文化,却给西方读者的阅读造成了较大的负担。其次,在异乡经历了创作失败与生活坎坷的双重打击后,张爱玲在创作上选择回归中国传统的怀抱,其文学惯习“更追溯自身传统与人民记忆”[21],并在翻译时彻底打碎了西方想象中的中国形象。而张爱玲与美国文学场相悖的惯习也导致她在出走美国的40多年中始终放逐于主流之外。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80.
[2]BOURDIEU P.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essay on art and literature[M].Cambridge:Policy Press,1993:162.
[3]BOURDIEU P,WACQUANT L J D.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4]布尔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80.
[5]王悦晨.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J].中国翻译,2011(1):5-13.
[6]黄晓莺.多元视界下的张爱玲的翻译[J].中国翻译,2008(5):25-29.
[7]单德兴.翻译与脉络[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8]HEMINGWAY E.The old man and the sea[M].Beijing:The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9:80.
[9]海明威.老人与海[M].张爱玲,译.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2:68.
[10]林以亮.美国诗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53.
[11]游晟.美国文学场中张爱玲《金锁记》的自我改写[J].中国翻译,2011(3):45-50.
[12]张爱玲.张爱玲的英文自白[M]//高全之.张爱玲学.广西:漓江出版社,2015.
[13]张梅.《金锁记》改写的背后[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94-96.
[14]张爱玲.忆胡适之[M].张爱玲.张爱玲全集:第7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15]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张爱玲.张爱玲全集:第6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92.
[16]张爱玲.怨女[M].张爱玲.张爱玲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17]CHANG Eileen.The Rouge of the north[M].London:Cassell & Company Ltd,1967.
[18]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19]金凯筠.张爱玲的“参差的对照”与欧亚文化的呈现[M]//杨泽.阅读张爱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0]陈吉荣.转换性互文关系在自译过程中的阐释——《金锁记》与其自译本及改写本之比较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2):69-72.
[21]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