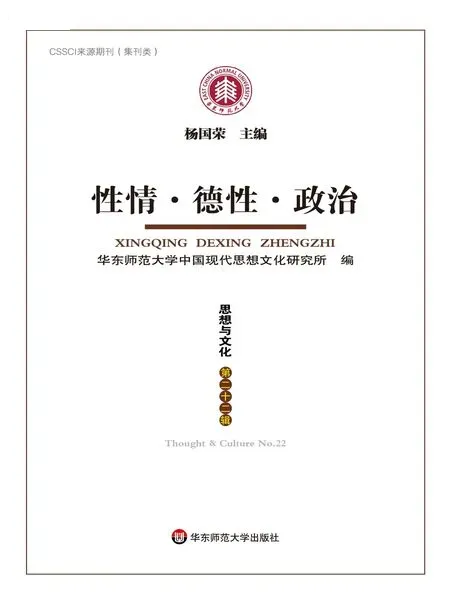身心之学的重建与自律道德的回归
——论朱子“尊德性”工夫的核心问题*
2018-04-02
●
一般而言,人们常常将朱子与其同时代的陆九渊加以对比,认为二人之间的一项根本性差异即在于前者强调“道问学”而后者强调“尊德性”[注]余英时先生认为,元儒吴澄对这一观点的流布负有主要责任。参见余英时 :《朱熹哲学体系中的道德与知识》,《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余英时文集》第十卷),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1—62页。,黄宗羲曾经对此作了更为明确的概括 :“先生之学(指陆九渊——引者),以尊德性为宗……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注]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 :《宋元学案》,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第1885页。余英时也指出黄宗羲的这一概括对后世人们对朱陆之别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影响。见余英时 :《朱熹哲学体系中的道德与知识》,《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第62页。如果说黄宗羲认定朱子之学“以道问学为主”已经忽略了尊德性在朱子为学工夫中的重要性,那么当牟宗三先生说朱子“工夫的落实处全在格物致知”时,尊德性在朱子为学工夫中的重要性就已经被完全淹没了。[注]牟宗三指出伊川朱子一系“工夫特重后天之涵养(‘涵养须用敬’)以及格物致知之认知的横摄(‘进学在致知’),总之是‘心静理明’,工夫的落实处全在格物致知,此大体是‘顺取之路’”。(见牟宗三 :《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3页。)林安梧先生已经注意到牟宗三的上述概括存在巨大的问题,他说 :“经由粗略的‘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区别,去讲明‘程朱’与‘陆王’,那是不足的。”(见林安梧 :《关于朱子“格物致知”以及相关问题之讨论 :“续别为宗”或“横摄归纵”》,见陈来、朱杰人主编 :《人文与价值 :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页。)当然,虽然相对陆九渊而言,朱子确实更加重视道问学[注]但这只是说,相对于陆九渊不重视道问学而言,朱子确实更加重视道问学;而不是说,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朱子更加重视道问学。实际上,就尊德性与道问学而言,尊德性在朱子那里无疑具有更为根本的地位。,但事实上,在朱子那里,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缺一不可。这在“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进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注]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36页。这一论述中得到明确的体现。不难发现,在朱子那里,尊德性的工夫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朱子那里尊德性工夫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然而,要具体地谈论朱子的尊德性工夫,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他对湖湘学派“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论的批判——实际上,朱子自身工夫论的建构正是在对湖湘学派的批判之中完成的。
一、 对湖湘学派工夫论的反思
作为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湖湘学派对工夫论有其独特的理解,即“先察识后涵养”。在中和旧说时期,朱子对此一工夫进路非常推崇,曾说 :“大抵衡山之学,只就日用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用功。”[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5册,第4747页。按陈来先生的考证,此书作于乾道元年(1165)。见陈来 :《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34页。而确立中和新说的乙丑之悟发生在乾道五年(1169),因此这显然是中和旧说时期的说法。然而,在乙丑之悟的中和新说确立之后,朱子对“先察识后涵养”这一工夫进路进行了一次翻转,从而确立了“先涵养后察识”的工夫进路。那么,朱子为何要进行这一翻转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首先弄清湖湘之学的“先察识后涵养”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湖湘学派关于“先察识后涵养”的论述首先集中体现在胡宏与彪居正的如下对话中 :
彪居正问 :“心无穷者也,孟子何以言尽其心。”曰 :“惟仁者能尽其心。”居正问为仁,曰 :“欲为仁,必先识仁之体。”曰 :“其体如何?”曰 :“仁之道弘大而亲切,知者可以一言尽,不知者虽设千万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举,不能者虽指千万事亦不能也。”曰 :“万物与我为一,可以为仁之体乎?”曰 :“子以六尺之躯,若何而能与万物为一。”曰 :“身不能与万物为一,心则能矣。”曰 :“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变万生,子若何而能与之为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问曰 :“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 :“齐王见牛而不忍杀,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间而见者也。一有见焉,操而存之,存而养之,养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与天地同矣。此心在人,其发见之端不同,要在识之而已。”[注]引自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60—3561页。
通过这一论述可以看到,湖湘之学将工夫的最终目标设定为“识仁之体”,而按照胡宏的说法,要达到这一境界,具体的工夫进路是在良心发现之时能够通过反省的方式自觉地意识到良心呈现这一经验性事实。由于良心即是恻隐之心,是作为性体的“仁”的经验性流露,对良心的察识实质上也就是通过对仁的经验性呈现这一事实的觉察而认识仁之体本身,因此,胡宏一方面说“必先识仁之体”,另一方面又说“要在识之而已”。所谓涵养,则是在察识到良知的存在之后,即在“一有见焉”之后,“操而存之,存而养之,养而充之”,实际上即是对良心的进一步体认、扩充。后来张栻将胡宏的上述观点概括为“学者先须察识端倪,然后可加存养之功”[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20页。,即“先察识后涵养”。在深受湖湘学派影响的中和旧说时期,朱子对工夫进路的理解基本与此一致,在著名的“人自有生四书”的第一书中,朱子写道 :
天理本真,随处发见,不少停息者,其体用固如是,而岂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虽汩于物欲流荡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尝不因事而发见。学者于是致察而操存之,则庶乎可以贯乎大本达道之全体而复其初矣。[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15—1316页。
这里的“致察而操存之”显然与湖湘学派“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进路是一致的。很显然,无论是胡宏、张栻,还是朱子自己对工夫进路的上述理解,都既包含察识的环节,又包含涵养的环节,那么朱子为什么在中和新说成立后却认为这里欠缺涵养工夫呢?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从胡宏和朱子自己的论述看,“先察识后涵养”中的涵养实质上不过是察识工夫的补充性环节,从根本上说,它仍然从属于察识工夫,而不具有独立的工夫意义,因为按照“先察识后涵养”这一工夫路径的安排,如果没有“先察识”这一先行的环节,则“后涵养”这一环节就无从下手。更为重要的是,“先察识”这一环节是建立在良心的呈现这一经验性事实的基础上的,无论是胡宏说的“良心之苗裔”,还是朱子说的“良心萌蘖”,都是指向良心(或恻隐之心)的呈现这一经验性事实。对察识工夫而言,如果没有良心呈现这一经验性事实存在的话,那么察识本身也就无从下手,更不要说察识后的涵养工夫了。然而,这里需要考虑的是,良心是永无停息地呈现在那里呢,还是其呈现需要特定的条件呢?事实上,在胡宏和朱子的上述论述中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良心的呈露并不是无条件的,它实际上是作为主体内在性体的仁在与特定情境相感通时才会呈现出来的。胡宏说的“齐王见牛而不忍杀,此良心之苗裔”,朱子说的“良心萌蘖,亦未尝不因事而发见”,都表明了这一点,即良心的呈现必须因事而发,或者说,仁之体必须感于物[注]在儒家传统中“物”的基本内涵即是“事”。朱子在注释《大学》的“格物”之“物”时,就明确说“物,犹事也”。而无论是郑玄,还是王阳明、王夫之,都是如此理解的。而动,倘若没有见孺子入井或者见牛觳觫这样的具体事件发生,就不会有良心的呈现这一经验性事实出现。[注]这一点笔者在《感通能力与“可以为善” :朱子对人性的理解》(载《问学——思勉青年学术集刊》第1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一文中曾经做了非常详尽的论述,这也是朱子区分性与情的根本性的问题意识所在。正如王夫之所言 :
意或无感而生(如不因有色现前而思色等),心则未有所感而不现。(如存恻隐之心,无孺子入井事则不现等。)[注]王船山 :《读四书大全说》(上册),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第23页。
良心的呈现不同于一般性的意识、思维,它只会在主体与特定的情境相遭遇时才会呈现。但问题的关键是,主体并不是一天到晚都会遭遇触动良心呈现的事件。实际上,能够触动主体内在的性体,从而流露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情境,在主体的日常生活中并不以常态的形式出现。那么,如果按照“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进路,在没有良心呈现的大多数时间内,主体的工夫显然无法安顿。正因如此,在中和新说确立后,朱子对张栻所说的“学者先须察识端倪之发,然后可加存养之功”提出了批判 :
所谓“学者先须察识端倪之发,然后可加存养之功”,则熹于此不能无疑。盖发处固当察识,但人自有未发时,此处便合存养,岂可必待发而后察、察而后存耶?且从初不曾存养,便欲随事察识,窃恐浩浩茫茫,无下手处,而毫厘之差、千里之缪将有不可胜言者。[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19页。
良心的呈现就是性体、仁体的发用,也就是已发,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自有未发时”。如果按照“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进路,在良心未发时,则无须工夫,也不知该如何做工夫。但对于朱子而言,“此处便合存养”,也就是说,真正的涵养工夫是在良心未呈现的那些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时间内进行的,而不仅仅是依赖于良心呈现这种特殊的、暂时的情境所进行的察识工夫的补充性环节。正因如此,朱子说 :“近看南轩文字,大抵都无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体通有无、该动静,故工夫亦通有无、该动静,方无透漏。若必待其发而后察,察而后存,则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81—1982页。之所以说南轩(即张栻)那种“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是“无前面一截工夫”,从而“工夫之所不至多”,根本原因在于良心的呈露是因事而发、感物而动的,因此就时间上说是短暂的,如果仅仅依赖先察识而后涵养,那么主体日常生活中做工夫的时间也就不会很多,日常生活的绝对多数时间内反而无须做工夫了。正因日常生活中良心的呈现是一种非常态的情况,而大多数时间内良心都不是处于呈现状态的,因此,“先涵养后察识”的工夫进路中的“先涵养”就是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时间内所进行的修养工夫,而“后察识”则意味着在良心呈现这特殊情况下所进行的工夫。如果说,在“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进路中,涵养工夫只是察识工夫的一个补充性的环节,因此,察识工夫才是工夫的根本所在;那么在“先涵养后察识”的工夫进路中,涵养工夫则具有更为根本性的地位,它在实际上构成了察识工夫的基础性前提。正如朱子所言 :
未发有工夫,既发亦用工夫。既发若不照管,也不得,也会错了。但未发已发,其工夫有个先后,有个轻重。[注]黎靖德辑 :《朱子语类》,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51页。
未发时的工夫显然是指涵养工夫,已发时的工夫则是察识工夫,而涵养与察识不仅“有个先后”,而且“有个轻重”,也就是说在“先涵养后察识”的工夫进路中,涵养显然比察识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朱子自己就曾经用“本领工夫”[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68页。一词来表达涵养工夫所具有的根本性地位。
二、 涵养工夫与身心之学的重建
不过,对朱子而言,涵养工夫之所以是根本性的工夫,不仅因为它在日常生活中所能够进行的时间长,更为重要的是,“先察识后涵养”与“先涵养后察识”两种不同的工夫进路中的涵养工夫在内涵上具有根本的不同。事实上,由“先察识后涵养”到“先涵养后察识”的转变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先后顺序的翻转,倘若如此,朱子就不会说张栻那里“无前面一截工夫”,更不会说他自己的中和旧说欠缺“平日涵养一段工夫”[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31页。。而欠缺“平日涵养一段工夫”则表明,在朱子看来,“先察识后涵养”中涵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涵养,因为它实质上不过是察识工夫的一个补充性环节。那么,朱子所说的涵养工夫的真正内涵何在呢?
如所周知,朱子那里的涵养工夫实际上是继承了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之说。[注]朱子中和新说确立后的工夫论是继承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从广义上说,无论是涵养还是致知都属于工夫的范畴,前者属于《中庸》所谓的尊德性,后者属于道问学。不过从狭义上说,尊德性属于更为具体的工夫,而道问学属于广义上的工夫,对朱子而言,道问学对于尊德性具有引导性、补充性的意义,而尊德性才是工夫的核心内涵。关于道问学与尊德性,或者说,致知与涵养之间的关系问题,笔者将另文再论,这里不再展开。当然,持敬工夫并非程颐的发明,而实质上是在孔子那里就已经存在的一种修养方式,在孔子那里已经将“敬”作为自我修养的方式而提出来了。《论语·宪问》中“子路问君子”,孔子首先的回答就是“修己以敬”。在这里,“敬”已经被看一种君子修己、成德的基本方式。此外,《论语·雍也》篇中也有“居敬”之说。对朱子而言,持敬工夫实际上是儒学最为核心的修养工夫,他甚至说 :“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成终者也。”[注]朱熹 :《四书或问》,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6册,第506页。那么作为涵养工夫的敬又该如何下手呢?在《大学或问》中朱子曾经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了这一点 :
曰 :然则所谓敬者,又若何而用力邪?曰 :程子于此,尝以主一无适言之矣,尝以整齐严肃言之矣。至其门人谢氏之说,则又有所谓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说,则又有所谓其心收敛不容一物者焉。观是数说,足以见其用力之方矣。[注]朱熹 :《四书或问》,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6册,第506页。
在这一论述中,持敬工夫被概括为四个方面,即 :甲、主一无适;乙、整齐严肃;丙、常惺惺;丁、其心收敛不容一物。甲、乙两者来自程子,实际上主要是程颐,而丙、丁则是来自程门后学。不过,如果全面地阅读朱子的文献,可以发现,朱子所强调的持敬工夫主要是主一无适和整齐严肃两个方面,这在《敬斋箴》一文中即得到明确的体现 :
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毋敢或轻。不东以西,不南以北;当事而存,靡他其适。勿贰以二,勿参以三;惟精惟一,万变是监。从事于斯,是曰持敬;动静弗违,表里交正。[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4册,第3996—3997页。
这里的“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足容必重,手容必恭”等主要涉及整齐严肃,而“不东以西,不南以北;当事而存,靡他其适。勿贰以二,勿参以三;惟精惟一,万变是监”则非常明确地属于主一无适的范围。这一点也体现在如下的论述中 :
“持敬”之说,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齐严肃”、“严威严恪”、“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此等数语而实加功焉,则所谓直内、所谓主一,自然不费安排而身心肃然,表里如一矣。[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72页。
从以上对于持敬内容的介绍又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整齐严肃与主一无适作为日常涵养工夫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涉及两个不同的层面。如果说整齐严肃所涉及的是对身体的调节,那么主一无适显然涉及的是对意识的调节;如果借用儒学的固有词汇,持敬涵养工夫实质上涉及身与心两个层面,正因如此,朱子说持敬工夫可以到达“身心肃然,表里如一”。在这一意义上,由整齐严肃与主一无适所共同构成的涵养工夫,实质上是包含身心两个层面在内的一种全方位的工夫进路。就这一点而言,朱子那里的持敬涵养的工夫,就与那种仅仅关注意识层面的修养工夫具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湖湘学派的“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就是一种仅仅关注意识层面的工夫,在那里身体层面的调节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此,朱子这种身心兼顾的修养工夫就值得特别注意。而且,如果将朱子的涵养工夫与西方思想中的精神修炼的传统加以对比,就更能显现出其独特性。在西方主流的思想传统中,身体往往被看作是灵魂的负担。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大部分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来说,哲学实践就是一个将灵魂从肉体中摆脱出来的过程”,因此其修养工夫也就成为一种“纯粹的精神修炼,其中并无身体的位置”。[注]彭国翔 : 《儒家传统的身心修炼及其治疗意义》,杨儒宾、祝平次编 :《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当然,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这种精神修炼的工夫植根于其根深蒂固的身心二元论传统。这一观念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到笛卡尔那里达到顶峰。赖尔曾经对这种被他称之为“官方学说”的理论进行了如下概括 :“可能除了白痴和怀抱的婴儿外,每个人都有一个躯体和一个心灵。有些人则宁愿说,每个人都既是一个躯体又是一个心灵。通常,他的躯体和他的心灵被套在一起,但在躯体死后,他的心灵可以继续存在并依然发挥作用。”[注][美]吉尔伯特·赖尔 :《心的概念》,徐大建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页。在赖尔看来,西方传统中以二元论为主流的对身心关系的理解,将一个具体的人假定为两个不同形态的存在的结合,它们分别是物理性的存在和心理性的存在,前者代表是身体,后者则是人的心灵;前者存在于时空之中,后者则是超越时空的。[注]参见[美]吉尔伯特·赖尔 :《心的概念》,第6页。这种对身心关系的理解,一方面将身心理解为两种完全异质的存在,二者如同两个不同的性质的物体一样机械性地结合在一起,无法相互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理解的背后又隐含着贵心(灵魂)而贱身(身体)的观念。从而反映在修养工夫上就是精神修炼,也就是仅仅从心上做工夫。但在朱子看来,心是“气之精爽”[注]黎靖德辑 :《朱子语类》,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14册,第209页。,因此心是身体的内在机能[注]朱子这种对心的理解与将心理解为一种实体化存在不同,而与现代科学对心的理解更为接近。在现代科学中,心的实质内涵即是意识,无论是理智、情感还是意志,乃至于潜意识都是意识的不同表现形式,而意识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参见[美]杰拉尔德·埃德尔曼 :《第二自然》,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第21页。)需要指出的是,前文曾经一再指出,在朱子那里,以仁义礼智为内涵的人性实质上也是身体的内在机能。这一点与心是身体的内在机能并不矛盾。在朱子那里,仁义礼智之性也是心的一个层面,即也是身体内在机能的一个层面。,因此身体层面的修养工夫与意识层面的修养工夫实际上是可以相互作用的。正如朱子所言 :
根本枝叶本是一贯,身心内外元无间隔。今曰专存诸内而略乎外,则是自为间隔,而此心流行之全体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动静语默由中及外,无一事而不敬,使心之全体流行周浃而无一物之不遍、无一息之不存哉?观二先生之论心术,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论主敬,不曰虚静渊默而必谨之于衣冠容貌之间,其亦可谓言近而指远矣。[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35页。
由此可见,朱子对修养工夫的理解建立在一种一元化的、身心互动的身心观之上的。正因如此,他不会将修养工夫仅仅理解为一种意识层面的精神修炼,而是对身体层面的修养工夫也非常重视。
实际上,朱子不仅非常重视身体层面的修养工夫,对他而言,身体层面的修养工夫比心灵层面、意识层面的修养工夫甚至更为重要。在他看来,身体层面的整齐严肃是持敬涵养工夫的最为核心的层面。他曾经多次谈到这一点,如 :
熹窃观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间,从容和易之意有余,而于庄整齐肃之功终若有所不足。岂其所存不主于敬,是以不免若存若亡而不自觉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圣学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固非谓但制之于外而无事于存也。所谓“既能勿忘勿助,则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为功效之名,恐其失之愈远矣。[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33页。
比因朋友讲论,深究近世学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裂灭。其言敬者,又只能说存此心,自然中理,至于容貌词气往往全不加工。……程子言敬,必以整齐严肃、正衣冠、尊瞻视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论。[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79页。
上述议论虽然都有其针对性,但如果考虑到朱子还有“夫子教人持敬,不过以整衣冠、齐容貌为先”这样的说法,那么丝毫不用怀疑身体层面的修养工夫在朱子那里所具有的根本性地位。事实上,在儒学传统中,身心之学中最为核心的工夫就被称之为修身,《礼记·大学》篇甚至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里的修身固然可以做广义的理解,即看作修养、修为的代名词,但这一名词无疑也体现了身体层面的修养在儒学修养工夫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可以说,修身最为直接的进路无疑是对身体的调节。而对于朱子而言,身体的调节构成了工夫最为核心的部分,正因如此,他对《礼记·玉藻》所说的“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速。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燕居告温温”,以及孔子所说的“君子有九思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类以身体的调节为核心的修养工夫非常重视,认为它们是真正的“涵养本原”[注]黎靖德辑 :《朱子语类》,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17册,第2965页。的工夫。
张载曾经说“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注]张载 :《张载集》,北京 :中华书局,1987年,第274页。。事实上,朱子之所以会给予身体层面的修养工夫以如此重要的地位,也与他对“变化气质”的重视密不可分。不过,对朱子而言,不仅整齐严肃这类直接的身体层面的工夫具有变化气质的意义,而且实际上,以主一无适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层面的调节也同样具有变化气质的意义。程颢曾经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指出 :“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注]程颢、程颐 :《二程集》,北京 :中华书局,2004年,第60页。这里的敬显然是从主一无适的角度说的,而这里的“学”显然是变化气质之学。朱子对程颢的这一说法非常肯定,并将其收入以“存养”为主题的《近思录》第四卷中[注]见陈荣捷 :《近思录详注集评》,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而朱子自己则作有《书字铭》对此加以阐发 :“只此是学。握管濡毫,伸纸行墨,一在其中;点点画画,放意则慌,取妍则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4册,第3997页。这里以主一无适为具体内容,持敬工夫更为具体地说就是专一,这从朱子反对“放意”就可以明确地看出。事实上,在朱子那里,主一正是以专一为核心内容的,他曾经非常明确地说“主一只是专一”[注]黎靖德辑 :《朱子语类》,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17册,第3240页。。无论是主一还是专一,它所强调的无非是现代人常说的专心致志,做起事来不三心二意。[注]钱穆也曾指出,敬“照现在话说,只是一个精神集中”。见钱穆 :《中国思想史》,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98页。正如朱子所言 :“做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头万绪。”[注]黎靖德辑 :《朱子语类》,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17册,第3240页。事实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很多事务需要处理,而处理事务的意识状态决定了效率与效果,因此意识层面的专一显然十分必要。但意识层面的专一并不仅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它同时也具有修身的意义。我们很难设想一个整日心猿意马,做起事来三心二意的人会是一个很具有修养的人。但正如朱子所发现的“今人做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头万绪”,这是一种衡诸古今都不变的基本事实,因此这种专一的工夫诉求就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意义,它虽然不具有直接的道德伦理的内涵,但仍然是变化气质、涵养本原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朱子也将其作为涵养工夫的重要内容。
在朱子那里,无论是对身体的调节还是对意识状态的调节,作为涵养工夫最终都指向变化气质。由于气质是每个人先天所禀,因此,气质的变化一方面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又非常困难。但在朱子看来,“气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注]朱熹 :《四书或问》,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6册,第863页。,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变化气质具有可能性[注]“气有可反之理”中的“理”是在可能性意义上说的,这涉及到朱子哲学中“理”的另一种内涵。在朱子那里,在作为人性的性理之外,作为一个概念的“理”还包含着可能性、必然性等内涵,关于这一点,需要专文作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主体也具有变化气质的具体进路,而上述所论的涵养工夫正是朱子对变化气质的具体进路的探讨。而通过上文的论述也可以看到,以整齐严肃、主一无适为主要内容的持敬构成了朱子所说的涵养工夫的基本进路。这一意义上的涵养工夫,与那种作为察识工夫的补充性环节的体认、扩充式的涵养工夫具有本质的不同,它不仅对主体的意识状态加以调节,同时也对主体的身体姿态加以调节。换言之,这一工夫进路实际上是将工夫安顿在身体与意识的不同层面,同时这一工夫进路也不依赖于作为道德意识的良知之呈现这一前提,从而能够将工夫安顿到日常生活行住坐卧的任何时空之中。因此,它既是对儒学传统中身心之学的自觉继承,也是对先秦儒学身心之学的重建。通过这一重建,使得儒学的身心之学能够以一种更容易为人们所把握的方式展现出来。正如有学者指出 :“朱熹在思想理论上通过对二程‘持敬’思想的创新阐释,而构成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中和新说’,其根本意向,就在于上至最高权力者下至百姓的所有成员,皆能在人伦日用之间得以实践。”[注]王健 :《在历史真实与价值真实之间》,上海 :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三、 察识工夫与自律道德的回归
正如前文所言,“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依赖于良心呈现这一具体情境,但不可否认,一些气禀非常差的人往往麻木不仁,而变化气质能够对气禀的不良加以克服,从而使得主体在遭遇孺子入井等具体情境时其人性能够更好地发用,这也就为良心的呈现提供了前提保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朱子指出 :
古人只从幼子常视无诳以上、洒扫应对进退之间,便是做涵养底工夫了。此岂待先识端倪而后加涵养哉?但从此涵养中渐渐体出这端倪来,则一一便为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养将去,自然纯熟。今曰“即日所学,便当察此端倪而加涵养之功”,似非古人为学之序也。[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80页。
由此可见,朱子之所以特别强调涵养工夫,正是因为涵养工夫构成了察识工夫基本前提,涵养工夫能够保证察识工夫更好地发挥其效用——如果气质不美,麻木不仁,即便见孺子入井也默然视之,那么察识工夫也就无法着手了。正因如此,在朱子看来,涵养与省察“诚不可偏废,然圣门之教详于持养而略于体察……夫必欲因苗裔而识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听其枝叶之自茂耶”[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62页。。对朱子而言,涵养工夫正是涵养本原、培植根本的工夫,只有气质得以变化,人性的功能才能够更好地发用,而察识工夫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当然,从上述论述中也可以看到,朱子虽然给予持敬涵养的工夫以非常根本的定位,但也没有否认察识工夫的重要性。不过,朱子在中和新说后所确立的察识工夫,实际上与湖湘学派的察识工夫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明确地体现在朱子对胡宏所说的“欲为仁,必先识仁之体”的批判上。虽然胡宏的这一说法源于程颢在著名的《识仁篇》中所说的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注]程颢、程颐 :《二程集》,第17页。但胡宏所言与程颢毕竟还是有所不同,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胡宏这一说法是对彪居正“为仁”之问的回答。对朱子而言,彪居正之问与胡宏的回答涉及知与行的关系 :“为仁”是行,而“识仁之体”是知,但胡宏之说中的一个“必”字,意味着为仁这一道德行动必须建立在知“仁之体”这一前提之下,那么就会产生如下的问题,即在未知“仁之体”的情况下,主体还是否应该践行道德行为。显然,按照胡宏的说法,主体的日常道德实践将缺乏可能,因为,对“仁之体”的体察、认知并非非常容易达到的境界。[注]正如陈代湘所言 :“湖湘学知先行后说的最大危险就在这里,识得仁体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这种境界不是人人都可以瞬间直悟的,但未识体之前还是要躬行践履,不能坐待识仁之后再践履。如果硬要等到识仁之后,那么道德践履就会出现未识仁而不践行的空缺时段。”见陈代湘 :《朱熹与胡宏门人及子弟的学术论辩》,《船山学刊》,2012年第3期。正因如此,朱子虽然并没有对程颢之说提出异议,但对胡宏则毫不客气地批判 :“‘欲为仁,必先识仁之体’,此语大可疑。”[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61页。对朱子而言,伦理道德实践无疑是人伦日用之中不可或缺之事,它不因主体未能“识仁之体”而减损其重要性与必要性。主体或许一生之中永远也不能达到“识仁之体”的境界,但不会对事亲、从兄之事一无所知,实际上,主体内在的人性总会在人伦日用之中有所呈露,见父则孝,见兄则悌,这是发之人心而不容已的,主体所该做的就是循而行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朱子批判湖湘学者吴晦叔道 :
大抵向来之说,皆是苦心极力要识“仁”字,故其说愈巧而气象愈薄。今日究观圣门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实践、直内胜私,使轻浮刻薄、贵我贱物之态潜消于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浑厚慈良、公平正大之体常存而不失是仁处。其用功着力,随人浅深,各有次第。要之须是力行久熟,实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盖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注]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12—1913页。
对朱子而言,既然作为人性主要内涵的仁实质上是主体内在的功能性存在,那么,只有在身体力行的行仁实践中,这种功能性存在才能够使得这种能力得到一步一步的提升。而且仁体作为一种身体的内在机能,它非一种实体化的存在,它不会以任何形象化的方式向人们展现,因此如果不能够身体力行,那么所谓的识仁、知仁不过是一种“想象臆度”罢了。不难发现,朱子对湖湘之学的上述批判正是出于对力行道德实践的强调。[注]朱子曾经批判程门高足谢良佐的学问是“以活者为训,知见为先”。朱子对“知见为先”的批判则与他对湖湘学派的批判密不可分 :谢良佐作为湖湘之学的鼻祖,其以“知见为先”的观念对湖湘学派“先识仁体而后可以为仁”的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就理论后果而言,它与湖湘之学一样都隐含着对道德实践进行消解的倾向,因而,朱子对谢氏以“知见为先”的观念的批判也与他对力行道德实践的强调密不可分。正因如此,朱子对谢良佐进一步批判道 :“其意不主乎为仁而主乎知仁……盖其平日论仁,尝以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但能识此活物乃为知仁,而后可以加操存践履之功;不能识此,则虽能躬行力践,极于纯熟,而终未足以为仁也。夫谓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可矣,必识此然后可以为仁,则其为说之误也。……然直曰知仁,而不曰为仁,则又并与其扩充之云者而忘矣。必如其说,则是方其事亲从兄之际,又以一心察此一心,而求识夫活物,其所重者乃在乎活物,而不在乎父兄,其所以事而从之者,特以求夫活物,而初非以为吾事之当然也。此盖源于佛学之余习,而非圣门之本意。”见朱熹 :《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614—615页。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识仁、见体为导向的察识工夫,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将人伦日用中的道德行为工具化。正如杨儒宾所概括的,“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进路中,“学者为学的首要工夫就是体认本体,等有所见了以后,再涵养此本体,而且涵养也不是静态的涵养、后天的涵养,而是人生的动态行为随时随地体证此‘理’”[注]杨儒宾 :《论“观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5年,第15卷(第3期)。。但如此一来,人伦日用之中事亲、从兄的道德实践不过成为体认本体的工具。这一点在胡宏门人张栻那里就有很明显的体现,尤其突出地体现在他的《癸巳论语说》之中,如在注释“志士仁人”章时,张栻说到 :“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亏其所以生,则其生亦何为哉?”但在朱子看来这一诠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说 :
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过处,不忍就彼以害此耳,非为恐亏其所以生而后杀身以成仁也。所以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后为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种意思,不以仁义忠孝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为畏天命、谨天职,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后为之,则是本心之外别有一念,计及此等利害轻重而后为之也。诚使真能舍生取义,亦出于计较之私,而无悫实自尽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说,自它人旁观者言之,以为我能如此则可,若挟是心以为善,则已不妥帖。况自言之,岂不益可笑乎?[注]见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79页。
从朱子的这一批判不难发现,在张栻那里存在着将日常的伦理道德实践工具化的严重倾向,毋庸置疑,这一倾向根源于其所继承的湖湘之学的识仁之说,它以识仁、见体为诉求,而将日常的实践行为都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但在朱子看来,对人伦道德的身体力行不过是“遂其良心之所安”,这是天理之自然,而并非是为了识仁、见体。如果“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后为之”,那么道德实践则成了“计较之私”,从而丧失了其道德性。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朱子又对张九成所说的“当事亲,便当体认取那事亲者是何物,方识所谓仁;当事兄,便当体认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识所谓义”[注]引自黎靖德辑 :《朱子语类》,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15册,第1303页。张九成虽然不属于湖湘学派,不过他这里所说的“识仁”、“识义”等工夫诉求与湖湘之学的识仁、见体之学具有极大的相近之处,从理论上说,这一工夫进路所包含的问题也是类似的。提出了批判,他说 :
顷年张子韶之论,以为 :“当事亲,便当体认取那事亲者是何物,方识所谓仁;当事兄,便当体认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识所谓义。”某说,若如此,则前面方推这心去事亲,随手又便去背后寻摸取这个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随手又便着一心去寻摸取这个义,是二心矣。[注]黎靖德辑 :《朱子语类》,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15册,第1303—1304页。
这里的“二心”与前述引文中的“本心之外别有一念”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其实质内涵就在于,本来事亲、从兄出于主体的爱亲、敬长之心,是人性感通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主体只要“遂其良心之所安”,尽其爱亲、敬长之心即可。但如果在事亲、从兄之时又要别起一念来反思“我”所以能事亲、从兄的这一本心是何物,并进一步借此达到识仁、识义的目的,那么事亲、从兄的行为实际上不过成为达到识仁、识义这一目的的工具,从而事亲、从兄的道德行为也就不再具有伦理道德内涵和价值。
而在朱子那里,察识工夫与湖湘学派这种借助于察识以体证本体的进路具有根本的不同。与湖湘学派一样,朱子那里的察识工夫也是建立在良心呈现这一基本前提之上,良心的呈现在本然的状态下可以直接指引主体当下采取行动,但主体往往会在这一当下考虑自己的安危利害而抑制了良心的召唤,这就是朱子所谓的天理人欲交战。对朱子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察识工夫意味着,当你察知到良心的召唤之时,就应该“遂其良心之所安”,换言之,真正的察识工夫,就是要在天理人欲交战之时,察见自己的本然之善心,并听从它的指引以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也就是朱子所说的“存天理,去人欲”[注]在这里可以看到,“存天理,去人欲”这一表述,虽然近代以来饱受诟病,但那是因为人们并不了解这一表述的实质内涵。而从本文的论述看,这一表述实质上是朱子工夫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可见,朱子那里的察识工夫实质上是通过对主体自身的道德本心的察知,进一步将其落实到具体的道德行为之中,即便自身的道德本心受到来自人欲的干扰、抑制,也要“遂其良心之所安”,而不可为人欲所夺。由此可见,与湖湘学派将察识良心作为体证本体的中介、工具性环节不同,朱子那里的察识工夫,强调的乃是力行道德实践本身的重要性。这从如下的论述中可以进一步地看到 :
只如一件事,见得如此为是,如此为非,便从是处行将去,不可只恁休。误了一事,必须知悔,只这知悔处便是天理。……道理只要人自识得,虽至恶人,亦只患他顽然不知省悟;若心里稍知不稳,便从这里改过,亦岂不可做好人?孟子曰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着这些子,存,只是存着这些子,学者所当深察也。[注]黎靖德辑 :《朱子语类》,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第18册,第3678页。
这一论述就清楚地表明察识工夫最终要落实在“从是处行将去”这一道德践履之上。而这里的“去,只是去着这些子,存,只是存着这些子”正是“存天理,去人欲”。由于从察识到践履的转化,存在着天理人欲交战的心理斗争过程,因此,这一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一个道德自律的过程。相反,那种将对良心的察知当作体认本体的工具性获得的察识工夫反而与他律道德很难划清界限,正如朱子所言,这种察识工夫骨子里正是“出于计较之私,而无悫实自尽之意”[注]正如康德所言 :“凡是在必须把意志的某个客体当作根据,以便向意志颁布那决定意志的规则的地方,这规则就只是他律;这命令就是有条件的,即 :如果或者由于一个人想要这个客体,他就应当如此这般地行动;因而它永远不能道德地,即定言地下命令。”(见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邓晓芒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5页。)事实上,在湖湘学派那里,以体证本体为目标的察识工夫,正是将本体作为工夫过程的目标,即康德这里所说的客体,而察识工夫作为一种行为,实际上是“想要这个客体”,因此察识工夫本身是工具性的,从而是他律的。有意思的是,牟宗三先生曾经认为朱子是他律道德,因此是别子为宗,而胡宏一系则是自律道德,是儒学正统所在。李明辉先生曾经将牟宗三的这一判教的依据概括为 :“他们是否承认孟子底‘本心’义,而接受‘心即理’的义理架构?如果是的话,则必属自律伦理学。不接受此义理架构,但有一独立的‘道德主体’概念,仍不失为自律伦理学;……若连‘道德主体’底概念亦不能挺立起来(如朱子),便只能归诸他律伦理学。”(见李明辉 :《儒家与康德》,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第45页。)但正如杨泽波先生所指出的 :“按照李明辉的划分,能否称为道德自律,主要是看其有没有一个独立的道德主体。孟子的道德本心自然属于道德主体……但我们知道,朱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天理或理,理必须在事中显现,落实在具体的事物之中而为事物之性,理是就总体而言,性是就个体而言,就此而言,性或性体就是朱子学理中的道德主体。”在这一意义上,杨泽波不同意李明辉从是否承认道德主体的角度判定朱子为他律道德,因为既然朱子那里确认了性体的实在性,自然也可以归入道德自律。不过他又进一步指出 :“朱子学理的问题不在有没有一个独立的道德主体,而在这个理没有孟子的心义,使理没有活动性,最后沦为死理。”(见杨泽波 :《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的困境及其出路》,《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然而,事实上,在朱子那里,以仁义礼智为具体内涵的天理或性体,不仅具有其实在性,从而是“存有”的,而且具有其功能性,从而是“活动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笔者《感通能力与“可以为善” :朱子对人性的理解》,载《问学——思勉青年学术集刊》第1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因此,朱子那里的性体实际上是“既存有又活动”的,因此,他那里的理或天理也不是死理,从而将朱子判为他律伦理学显然是不合适。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从自律、他律的角度来理解朱子哲学乃至儒家哲学都有其内在的限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理论的误置。(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唐文明 :《隐秘的颠覆 :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63—137页。)。有意思的是,如所周知,牟宗三先生正是以朱子的道德学说为他律道德,从而判定朱子是“别子为宗”,并肯定胡宏一系才是儒学正统所在。但在这里可以看到,实际上朱子那里反而存在真正意义的自律道德,而以胡宏为代表的湖湘之学的道德学说却与他律道德更为接近。在这一意义上,不难发现,朱子对湖湘学派察识工夫的批判,实质上正是从道德的他律化向自律道德的回归。
综上所论,不难看到,朱子的工夫论系统不仅包含着牟宗三所强调以“格物致知”为内容的道问学,也同样包含着尊德性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朱子的尊德性工夫,正是建立在对牟宗三所推崇的湖湘学派的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牟宗三以道问学为依据将朱子的学术形态理解为他律道德,但对朱子而言,湖湘学派的学术形态才是一种他律道德,而他正是通过对湖湘学派的自觉批判,在重建先秦儒家的身心之学的同时,也在实质上面上实现了向自律道德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