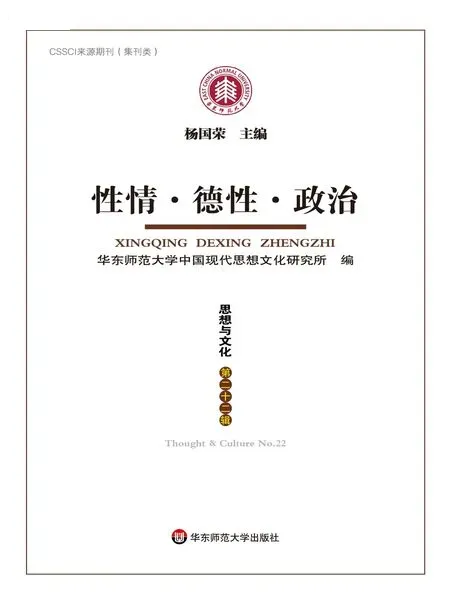“味道与中国哲学的生成”笔谈*
2018-04-02
●
作为哲学问题的“味”之来龙与去脉
贡华南
从我走上哲学思考之路开始,一直自觉沿着“重建中国哲学”这个大方向摸索。“古今中西之争”是思考的前提——重建中国哲学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而重新认识传统离不开了解西方,需要以西方为借鉴,通过西方这面镜子才能寻找到“中国”。
“寻找中国”这项工作,从上个世纪初就开始了。中国哲学家寻找中国哲学方法论找了百年。从梁漱溟的强调直觉、反对理智,到熊十力的弘扬性智、反对量智,再到牟宗三用智的直觉来概括中国传统,把智的直觉当作中国哲学的根基,这是一条显豁的思想路线。另外一条是由金岳霖开创、冯契发扬光大的思想路线,即强调思辨综合、理性直觉、德性自证之统一,进而以广义认识论标志中国哲学。我大体接着这两条思想路线思考探索。
从直觉出发,去追寻区别于西方的中国思想自身的方法论,这个工作既指向发现中国,在今天又能够给我们重建中国哲学提供根基。我接受牟宗三先生的这个观念,开始思考“直觉”问题。学界将“直觉”与理智、理性的对立,视之为直接性思想活动,尤其将其与中国哲学的根基同一化,这让我深深疑惑。接受这个观念即意味着接受中国思想杂乱、含混,不可言说。这些西方传入的“直觉”概念显然被引入歧路。“直觉”是如何活动的?直觉活动的内在结构遂成为我探究的焦点。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知识”为题,讨论知识的类型。这个选题乃是受古代诸子百家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现象之刺激,特别是儒家主“良知”、斥“真知”,而道家主“真知”、拒“良知”。这些对立的“知识”都将其根基措置于不同的生命存在之中以捍卫自我,此正是冯契先生所主张的“广义认识论”的第四个问题。受其启发,我开始尝试以生命存在来理解20世纪的不同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形上知识、常识,并将知识理解为不同存在者之间的交往方式。落实下去,将科学知识还原到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思想传统,回到欧洲人的生命存在中去理解科学。具体说,就是把主观、客观、感性、理性、对象、直觉等概念统统冠以主语“欧洲人”,视之为他们的生命存在之展开。以此反观先秦以来的中国典籍,一切都变得陌生与新奇。《知识与存在》带出了更多更难的问题。
在中国经典中,我没有找到“直觉”,而是找到了“感”。一说起“感”,大家总是与西方认识论的“感性”联系起来,认为感性低于理性。可是再回到中国传统,感性通于理性,而高于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理性。这样,我对“直觉”的疑惑就转移到了“感”。“感”如何展开,它的结构、运行机制如何?宋明儒常说的“感通”、“感应”,让我确信“感”在中国思想中异常重要,但在宋人那里,“感”同“直觉”一样让人难以捉摸。
为弄清楚这个问题,我只能继续往前追寻,由此到了《易》。《系辞》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说,结合《咸·彖》“咸,感也”,我隐约触及了“感”的内在结构与活动机制。在古代,“咸”指五味中的咸味,其本义指能够穿透、融入对象之味,进而转义为领会对象的方法。咸乃五味之首,于是,通过“咸”再反观,就追到了味觉。“味”,作为动词,它既指口舌之尝味,也可指对诗词艺文的品味、玩味,还可指对天理、大道之领会(味道)。作为名词,“味”既可指万物之滋味,也可指诗词艺文之意味,在形上之域,它还可指道味、理味。从直觉追寻到感,再追寻到味,我自认为找到一个更有解释力,同时也让我安心的根基 :中国人的感官活动、思想活动皆以味觉为原型展开,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方式。进而反观中西思想方法之差异,得出的结论如下 :西方思想是立足于视觉的,西方的感性和理性都以视觉为基本架构。而中国思想立足于味觉,视觉被味觉化,听觉被味觉化,思想也被味觉化。味觉思想以“象”为基本范畴,视觉思想以“相”为基本范畴。在2008年出版的《味与味道》中,我如蜘蛛织网般,以“味”、“感”、“象”为主轴,编织了一个中国思想网络。
《味与味道》勾勒出中国思想方法之基本面貌,其后,我进一步从“史”与“思”相结合角度揭示味觉思想的历史演变脉络。具体说,近几年勾勒出中国思想史中三条彼此配合的演变脉络。第一是感官选择的脉络,即揭示在商周时期形成了以耳口通达内外的认知传统;先秦时期,耳目被凸显,目一度被聚焦,但耳目之争,耳最终胜出;秦汉时期,耳舌相争,最终舌胜出。从早期耳口配合到耳目之争,耳胜出可以看作是对商周古老传统的回归。秦汉时期展开的耳舌之辩,舌胜出,实质上亦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口先隐而后以舌显,耳、舌的分别胜出也是认知思想的自觉推进。目、耳在诸感官之争中分别被压制,被味觉含摄,由此使中国认知思想与强调视觉优先、听觉优先的认知取向渐行渐远,最终确立了味觉优先的认知取向。味觉优先也确定了由味觉主导构成“道”等核心观念的文化路向,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味觉思想世界。第二是范式转换的脉络,从先秦的“形”范式,到秦汉的“体”范式,再到宋明的“理”范式,中国思想一直自觉摒弃纯粹视觉,而导向味觉思想。与形、体、理范式之嬗变历程相应,对道的领会相应展示为从形名到形而上、从体到本体、从理到天理。第三是方法论的几种历史形态,即与从形名到形而上演变脉络一致的“感通”,进至于从体到本体的“体味”、“体道”,再到从理到天理的“理会”。由感通、体会到理会则不断生成、强化着味觉思想。
从横向面看,中医药、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画论、书论、诗论、文论、道学等人文领域都以味觉思想为主导。从而使中国文化各个层面浸染着味觉思想,故我以味觉思想为中国文化之血脉。以上为即出《味觉思想》的基本思路。该书展示出,此血脉从远古流淌至今,虽历经千万劫而健进不息,在当代中国依然随时随地触之可及。当代意欲在中西古今之争视域下重建中国话语体系,重建中国思想、中国文化,味觉思想亦提供了最厚实的资源与最切身的选项。
深感近代以来视觉思想所带来人与万物之疏离,我努力从味觉思想出发,把握并解析当代生存状况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症状,尝试以此方式开展当代中国哲学。受我的老师杨国荣教授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即Being优先于Knowing,将后者确立为前者的一个维度,进而聚焦“具体的存在”。我自觉从存在论层面,将“意味”而不是抽象的、纯客观的本体视为对象;从方法论层面说,自觉追求以我手写我心,从自身痛痒处入手来书写自身的感受。依我的体会,“忙”是当代每个人最普遍的状态,“忙人”乃是我们时代真实的“主体”。可哲学界由于种种原因,一再错过这个问题。“忙”既是我感受至深的生存状态,也是对我意味深长的命运。由此意味入手,才真正把“味道”哲学坐实。当然,随着思考的深入,“我”扩展到“我们”, 我的切身问题即是这个时代的“我们问题”。由此人生意味入手,我将“忙”的时代病症与万物失味结合起来,将“味道”哲学坐实到现实体验而不是单纯的义理分析,这是2015年出版的《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一书之主旨。
将忙、累、烦、怕这些让每个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问题哲学化,努力把时代之痛表达出来,这是我所理解的“做哲学”的基本方式。忙、累、烦、怕、闲这些日常语言最贴近当代现实,或许它们在古典时代还不是中心问题。但是今天历尽生活的变迁,它们已经成为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切身的问题,这决定了它们注定会从精神的边缘进至于思想的中心。以此为主题,思想的开展才能真切厚实。这些问题之最终的解决不能止于人道,不管是人的目的、合理性,还是以人伦为大,都不足以解脱天人之厄。我的想法是,由人是目的扩展到万物皆是目的;在天道、地道、人道之外,确立物道观念;以天地万物构成的大场景为思考的大视域、大伦;突破合理性,确立合道性,等等。这些问题直接接着《忙与闲》展开,同时也是味道哲学目前聚焦之所在。
医药神话与本草味道
杨奕望
机缘巧合,拜读贡华南教授的大作《味与味道》,参加“味道与中国哲学的生成”雅集,对我这个中医人而言,实则是一次聆听、学习的绝佳机会。贡教授以中国传统之“味觉”为突破口,寻求阐释世界可能性与必要性,旁征博引,汇通中西,探索中国哲学研究的“味觉”范式。囿于个人学养和专业领域,可谓“哲学的他者”,仅对于论及的“味道”、“五味”等朴素概念稍有涉猎,自然而然想到的是医药起源及其神话传说。
神农(炎帝),被誉为我国农业、医药的发明者,他的传说在诸多典籍广泛流传。如西汉刘安《淮南子·修务训》载 :“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北宋刘恕《资治通鉴外纪》亦载 :“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神农氏可以理解为上古部落的代表人物,“神农尝百草”的神话传说则是先民群体初期医药经验日积月累的客观写照。而其中的“尝”、“味”,也成为早期人类了解、熟悉药效,乃至认识、感知世界的重要途径。
有“神话之渊府”之称的先秦典籍《山海经》,其所包涵的医药神话更加丰富精彩。就“味觉”而言,《山海经》记载了酸、甘、苦、辛四种滋味。例如“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西山经·次三经》)。再如“又西九十里,曰阳华之山,其阳多金玉,其阴多青雄黄,其草多薯蓣,多苦辛,其状如橚,其实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疟”(《中山经·次六经》)。[注]袁珂 :《山海经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4、140页。值得注意的是,咸作为五味之首,“且咸之入物既如水一般润下,而又如坚戈一般具有穿透性”[注]贡华南 :《味与味道》,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9页。,并未以滋味的形式在《山海经》出现。咸,或命以人物、国家的名称,如咸鸟、巫咸、巫咸国;更多地则以地名形式展示,如咸阴山、小咸山、大咸山、少咸山、咸山、不咸(山)等。若仅仅以当地自产盐、制盐加以说明,需要更多文史论证,也为后来学者拓展了研究思路。
东汉以降,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著作,《神农本草经》首次将“药味”的概念引入本草领域,产生的中药五味,与四气、毒性、七情等共同构建出中药药性理论的框架。《神农本草经》序录提出 :“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注]吴普等述,孙星衍、孙冯翼辑 :《神农本草经》,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书中更结合寒热温凉四气,几乎对所载全部药物的性味作出标识(基本为单一药味)。如“菖蒲,味辛温”、“天门冬,味苦平”、“五味子,味酸温”、“水蛭,味咸平”、“杏核仁,味甘温”等。据王家葵、张瑞贤两位教授的研究显示,若以日本考据学家森立之《本草经》辑本357味药为例,包含辛味99种、甘味78种、酸味14种、苦味131种、咸味14种。[注]王家葵、张瑞贤 :《〈神农本草经〉研究》,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78页。五行学说框架下,《神农本草经》进一步将“五味”与“五脏”紧密连在一起 :“五味,养精神,强魂魄,五石养髓,肌肉肥泽。诸药,其味酸者,补肝养心除肾病;其味苦者,补心养脾除肝病;其味甘者,补肺养脾除心病;其味辛者,补肺养肾除脾病;其味咸者,补肺除肝病。故五味应五行,四体应四时……”(《太平御览》引《养生要略》、《神农经》)[注]吴普等述,孙星衍、孙冯翼辑 :《神农本草经》,第122页。后世本草,大体延续着同气相求、药物归经、五行生克的思维逻辑。
回归原点,从《山海经》的医药神话到《神农本草经》的中药味道,由最初的口尝得味发展为五行配属理论、毒性反推、功效反推、以类相推等衍生判断[注]张卫 :《“五味”理论溯源及明以前中药“五味”理论系统之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58—159页。,从“真实滋味”演变至“理论滋味”,中医药理论始终与“味”紧密联系。[注]薛辉 :《中医药“味”理论源流》,杨国荣主编 :《思想与文化》第十四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0页。历代本草为“味与味道”理论提供了大量实证,也很好地印证了贡华南教授的“味觉”思想。
“味”之道——可感的中国哲学研究探索
朱 璐
“重建中国哲学”、反思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探索中国哲学研究的合理范式,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界须共同直面的重大问题。无论是重建“中国哲学”,还是重塑“哲学在中国”,均需中西哲学研究的视野交融。“汉化胡说”、“胡话汉说”还是艰难地复归“汉话汉说”,中国哲学的话语系统该如何重构?贡华南教授的“味”道体系,不失为“新鲜”的灵泉,大有会通六根、达于本体、道行天下之“象”,万物“合道”而“味”行天下。
一、 会通六根
六根,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净是超脱了大千烦恼,度越世间各种“忙”之后的大“闲”智慧。在贡教授看来,“味”道之学,始于舌尖,我们也可以说,这种可感的中国哲学,是始于“舌尖上的中国哲学”。
与古希腊、古印度始于视觉(“眼”、“目”)的认知秩序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将“味觉”放在六根之首。“心”开窍于“舌”,是中国哲学的感知秩序,即心性、智慧的获取,源于舌尖的味觉。“舌者,心之官也。”眼、耳、鼻、舌、身、意,皆是“味”觉的外化和 “味”之一偏,皆有所失。只有以“味”这一立体的、本质的、“可感”的“感通”形式,会通六根,才是“进入”万事万物的正确方式。“中国思想立足于味觉,视觉被味觉化,听觉被味觉化,思想也被味觉化。”“味觉”,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大全。
作为“可感”的“感通”世界的方式,“味”何以“可感”?六根认知中,最重要的是“意”,也就是“心”。 贡教授返之于《易》,沉潜其中,而发明 “感”义,交“感”于“味”。《系辞》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说,《咸·彖》又言 :“咸,感也。”贡教授以此触及 “感”的内在结构与活动机制。在古代,“咸”指五味中的咸味,其本义指能够穿透、融入对象之味,进而转义为领会对象的方法,即“咸”于心,则为“感”。咸乃五味之首,于是,他通过“咸”再反观,就追到了味觉。以“味”觉始,而“感”观中国哲学。
二、 达于本体
观乙未月庚子日“味”与“味道”雅集,感触最深也心存顾念之处,乃贡教授独辟蹊径,将“味”形上至本体之思。中西哲学本体之论,洋洋洒洒,蔚然壮观,或以理念、逻辑、神性、理性等为本体,或以仁、性、理、道等为本体。以“味”这一“感通”形式为识见本体的哲学思维体系,尚乏善可陈,贡教授开一体之先河。雅集当夜,群贤毕至,茶琴辅趣,斗室生馨。
首先,贡教授以“史”、“思”相契而梳络味觉思维演进历程。自商周时期,以耳口通达内外的“感官选择”认知传统始;至先秦耳目被凸显,目之被聚焦,耳目相争而耳胜;秦汉“耳舌相争”,终以舌胜。从早期耳口配合到耳目之争,耳胜出可以看作是对商周古老传统的回归。在此进程中,口先隐而后以舌显,耳、舌的分别胜出也是中国哲学认知思维的自觉推进。目、耳终被味觉含摄,由此使中国认知思想与强调视觉优先、听觉优先的认知取向渐行渐远,最终确立了味觉优先、以味觉为本的认知取向。味觉优先也确定了由味觉主导构成“道”等核心观念的文化路向,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味觉思想世界。
其次,贡教授认为,就中国哲学本体论范式转换脉络而言,从先秦的“形”范式,到秦汉的“体”范式,再到宋明的“理”范式,中国思想一直自觉摒弃纯粹视觉,而导向味觉思想。“味”兼具“所以然之故”、“所当然之则”的本体意味。就形下而言,“味”既指口舌之尝味,也可指对诗词艺文的品味、玩味;就形上而言,“味”是对天理、大道之领会(味道)。万物“玩”味,则万物得“体”,生机勃勃;万物失味,则“幽明”失序,“有无”失“象”。以“味”论道,以“味”论中国哲学的生成机制,探讨“味”觉的存在论意义、结构及谱系,丰富其形上、形下意味,从而建构“味”道本体论哲学,沉思“味”道哲学与中国文化血脉的生生之意,是贡教授近年来心力所向,成果丰硕。
就此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于贡教授。一、“味”之道,与传统心性、义理之学如何打通?“味”道哲学,是否能应接传统“卫道”之学的辩难与质疑?开一代体系之先,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恩师张立文先生自上个世纪首创和合学,一路走来,筚路蓝缕,饱受争议与攻讦。然而,本世纪始,自上而下对和合学体系的认同,终究证明了和合学的巨大理论价值。贡教授气象不凡,“闲”心学思,亦期待贡教授能迎“难”而上,解“味”、辨“味”,以待其时。二、“味”之为本体,在贡教授的考辨和梳理下,自本自根,自证自足,然而“味”如何能超越传统“仁”、“理”、“道”等范畴,而形上为中国哲学之本体概念?这可能不仅需要自证“味”之为本体,亦需要“他证”,即与“仁”、“理”、“道”等范畴比较研究,进而诠释“味”之超越性。三、综观“味”道体系,儒之“味”,尤其是道之“味”意,欣然跃于纸上。然则,佛之“味”说,亦充盈而不昧。如法华玄论上乘之“一味”之教,“一相一味”之说等。雅集席间,亦有南开小友明炎君惠补一二,值得关注。此外,禅“味”诸多叙事,论及春夏、生命流转、万法皆空,皆关乎生存本体,若能接引入“味”道体系,儒释道三教“味”道具足,当更为完满。
“味觉思想”在现代世界如何可能?
俞 喆
人类是灵长目的动物,我们的祖先穿荡在树林间觅食避害,仰赖于色觉和立体视觉。在心智觉醒的时代,有先贤圣哲将看的能力与知的能力相联 :譬如悲剧中的俄狄浦斯查明自己弑父娶母之后刺瞎了双目,他怨忿这双眼睛不辨真相;譬如柏拉图主张真知无法由感觉把握,却要人们用心灵的眼睛去注视理念。如今这种联系已在语言中积淀,在别人解释说明后我们用“明白了”、“I see”来表示知悉。
贡华南教授对“味觉思想”的阐释挑破了貌似自然而然、已成习惯的视觉主导性。贡教授指出 :中国文化在汉代确立了味觉中心主义,有别于西方古希腊传统的视觉中心主义,以味觉主导的思想方式并不把对象归于与质料相对的形式,人与对象之间没有距离、彼此交融。
“味觉”线索为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开辟出新的角度,比照之下又可凸显不同文化各自的特质。探索味觉思想不止于述古,对现代人、现代社会各种问题深怀关切的贡教授将之视为回归真实存在、重建天人关系的助力。于此,我却嚼出了些许苦味,不禁发问 :“味觉思想”的方式在现代世界如何实现?能在什么程度、多大范围实现?
日常味觉活动最密集之处是餐桌。如今,我们餐桌上的食材天南海北四季不断,餐馆食肆有本土传统、有异国新味,融合菜方兴未艾、分子料理最为时髦,味道可谓丰富。我们的餐桌上还有现成品、微波炉加热后的半成品,有些吃食甚至不必自备餐具,无须摆上餐桌。现成食品古罗马就有,但工业化食品生产的规模不是旧时小作坊能比,工业化带来了高度的便捷,也带来了标准化的味道。很显然,我们吃的东西变了,也就是说味觉活动的对象变了——入口之食是经过加工改造,甚至由人创造出来的东西。现代人的味觉对象是技术的成果。古人亦烹调腌渍,对象改变的要点并不是加工,关键在于 :今人的生活里难觅真正的自然,我们遇到的是人化之物,是我们自己。味觉思想求身心与天地万物感通,但万物已与天地疏离,即便我们能与人化的万物融通又如何回归真实的存在,如何重建天人关系?
或许味觉思想方式要求人回归自然,但技术对饮食的影响趋势是不可逆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厨房传出的饭菜香曾是家庭生活的一个核心,意味着一家人围坐桌旁一同用餐。而在个人原子化的社会,家庭规模缩小,家庭成员吃饭的时间也未必划一。城市人经常外食,用餐时间须配合现代经济活动。是现代生活方式让人们选择快捷,食品工业化带来的各种快餐店迎合了人们的需要。而随着人们对便捷食品的习以为常,即便在得暇悠闲一餐的时候也会有人去吃快餐。
当然,味觉思想远远不只是吃的问题。在我想来,“味”的最好的对象必定包括杰出的艺术作品。这个领域同样面临着现代世界对象改变,更确切地说是对象稀缺的问题。我们有如此之多的出版物、画廊、剧院、音乐人……然而读物未必是文学、故事未必是小说,文学、音乐、戏剧、造型艺术之中有多少是消费品,有多少是跟风庸作,又有多少是真正的艺术?
味觉思想方式需要匹配的对象,这样的对象现代世界中似已难觅。那么,我们现代人如何去“味”,以何去“味”?
感官与体察世界
朱 承
贡华南教授近些年来在中国哲学方法论和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方式领域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相继出版了《味与味道》、《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等一系列重要著作,拓展了中国哲学方法论、思维方式、处世方式研究的新领域,值得我们学习。今天,我们围绕“味道与中国哲学的生成”这一主题,对贡华南教授提出的“味与味道”相关观念进行研讨,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我们认知和体察世界,首先是从感官出发的,视觉、味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官能是我们把握世界的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方式。“耳听之为声,目遇之成色”,人对声色世界的觉知和掌握,往往从耳目开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感官对于我们体察世界具有最基础的意义。过去,我们理解中国哲学,最容易从阴阳、道、气、心、性等抽象的层面入手,而忽略了人最原始的感官功能,贡华南教授提出从味、感等角度来认知中国哲学,正是敏锐地把握了感觉对于哲学思维的原初式意义。贡华南教授认为,就感官而言,在中国哲学的认知传统中,有一个从目到耳到舌的演进过程,有一个从视觉优先到听觉优先,最后被味觉所统摄的过程。当然,这里的“味”不仅仅是指味觉,还有品味、玩味、体味的意义。“以味体道”这一新颖的诠释进路,可以说是“耳目一新”,为我们理解中国哲学思维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也可以说是提出了一种新的中国哲学思维范型,其学术意义自不待言。
在这里,结合个人的理解,向贡华南教授请教两个问题。
首先是日常经验与理论诠释的问题。实际上,就日常经验而言,感官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不同功能从逻辑上可以做层次区分,但从事实层面很难做这种层次区分。比如,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离坚白”学说坚称,面对一块白色的石头,我们眼睛看到的是白的颜色,并不能看到坚硬程度;而当我们用手去摸这块“坚白石”的时候,获得的感觉是坚硬程度,并不能摸出其颜色。从感官分离出发,“坚”和“白”并不是同时共存的,而是相互分离的、各自独立存在的,故而称“坚白相离”。然而,在实际经验中,我们面对一块石头,所形成的是统觉,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做这种感觉上的分离,只是为了突出某一点时,我们在语言表达上才会对其有所侧重。比如,我们看到一个“又大又红又香”的苹果时,为了突出“大”,我们说这是一个“大苹果”;为了突出“红”,我们说它是“红苹果”;为了突出“香”,我们说“这只苹果香”。在日常经验中,面对外在世界的信息,感官上其实并无高下之分,只不过有的是需要听,有的是需要看,有的是需要嗅,有的需要尝,分工不同而已。就此而言,如何从理论上更好地解释这种感官功能上的优先性问题?如果仅从文献里出现的感官词语的多寡上,或者从语词与“道”的远近来做层次上的判别,这种论证是否具有必然的合理性?
另外,关于“心知”和“口耳之知”的问题。王阳明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谕泰和杨茂》。杨茂是聋哑人,口不能言,耳不能听。王阳明与他以笔墨答问。王阳明问他耳不能听是非,口不能言是非,心能知是非吗?杨茂示意能。由此,王阳明说,只要心能知是非,所以依旧是个圣贤的心,而口耳不能言听是非,“省了多少闲是非,省了多少闲烦恼”,是件好事。所以王阳明告诉杨茂 :“我如今教你但终日行你的心,不消口里说;但终日听你的心,不消耳里听。”在这个故事里,王阳明主张“心知”是最重要的,“口耳之知”无益于“心知”,有时还徒添烦恼。当然,王阳明在这里表现出一定的反智识主义倾向。但是,这也反映了,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有另外一个重要传统,那就是“心知”优先于感觉之知,就像张载主张的“德性之知”优先于“见闻之知”一样。这其实说明,在中国古代哲学里,在体察世界的过程中,感觉要让位于理性(道德理性)认知。如果说,建构“以味体道”的感觉认知进路是恰当的话,那么如何理解它与“心知”、“德性之知”之间的分野?
以上,是我对于“以味体道”之感官认知范式的一点粗浅理解和疑问。在体察世界的道路上,各种思维方式“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历史地来看,各种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体察世界范式,都有其独特的意义,揭示和分析这些范式有益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这也是贡华南教授近年来学术工作的价值所在。
味道的感通与心体的通感 :贡华南教授的味觉中心论评议
王懷聿
贡华南教授对中国古代味觉思想的研究为我们认识与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特质与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与会通开拓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贡教授将中国古代的思维模式归结为“味觉中心论”,以期与西方文明的“视觉中心论”分庭抗礼。贡著立论恢弘,征引旁博,深入浅出而富于妙趣。限于篇幅,以下拟从汉语的某些特点出发,来考察中西思维模式的异同,并以此对味觉中心论这一命题作一个粗浅的评议。
钱钟书在《管锥编》首章拈出古汉语“背出分训之同时合训”的现象 :如“易”字含“变易”与“不易”二义,“乱”可兼训“治”,“废”兼训“置”等等。这些均可与黑格尔所标榜的德文Aufheben一词兼灭绝与保存二义比类相参,妙味相通。其实,除了相反意义同时合训的字例,古汉语中更多的可能是同一范畴内相对的两个义项或某种情事中相对的两个行为集于一字的现象。如《荀子·非相》中“观人以言”的“观”字,不作“观看”解,而是“展示”的意思。又如“闻”兼有“听闻”与“报告”二义;“理”可兼指个体的纹理与一般的理则;“体”可兼指手脚四肢(四体)与身体的全部,并进一步指示由全体统摄各部的规范与体统;“感”字包含感觉的激发(感动/感化)与接受(感受)两层意思等等。而“味”字本身,也蕴含了味道与味觉这两个相对的意义。
汉语的这一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对事物认知的深刻体验 :味道与味觉、施感与受感、客体与主体、物象与心识、一般的原则与个体的具象,既彼此对待,又相互交融,难以分划。按《礼记·乐记》的说法 :“人生而静,感于物而动…… 物至知知。”在古人看来,对事物的理性认知与感性觉受相反相成,不可偏废。大概物至而后心有所感,有感而后知。也就是说,人的知性对事物的认知必然基于心物之间的某种感通。值得注意的是《易经》中感卦的感字写作“咸”,依贡著的考证,古文“咸”、“感”二字可相通假。这也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味觉中心论的主命题 :古人对心物感通的体验来源于味觉这一特殊感受。
在贡教授看来,“中国人的感官活动、思想活动皆以味觉为原型展开,而西方思想是立足于视觉的,西方的感性和理性都以视觉为基本架构”。将中国文化定义为味觉中心,乍一听可能会让有些人觉得匪夷所思。但只要依照贡著的论证细心考察,就会发现这个说法不但持之有故,而且有典可依。贡著思辨严谨,见地深远,充分展示了味觉在中华文化与思想中的重要性。当然,味觉是否真是感官与思想的中心,以及味觉、视觉与听觉在不同文明体系中的独特地位,是非常有趣而复杂的问题。这有待学界进一步研究。本文希望借助中西学界对通感现象的讨论,对这个命题作个初步的权衡。
钱钟书有《通感》一文,专论中西经典及日常经验中对通感(synesthesia)现象的描写。五官的感受不但往往挪移错位,而且可以相互融通。前者如说颜色闹人、声音尖锐或宏亮,及味道精美,都借助他官的感受来描述某种特定的官能体验。后者则涉及心物通会的神秘经验,而常见于中西宗教家的论述。如《列子·皇帝篇》 :“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神释。”又如《成唯识论》卷四 :“如诸佛等,于境自在,诸根互用。”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西方哲人(如梅洛-庞蒂)更将通感的直觉体验看作人类感知活动的原型。以此看来,日常经验中各种官感的交错打通并不一定是五官功能逻辑分理的失调,而更可能是人类原初感知体验的一种回归与再现。这种原初的体验大概正是李笠翁在评议通感现象时所影射的“理外之理”。
这个理外之理姑且可以称作心体的通感。心体的通感印证了我们对事物的感知依赖于所有感官的综合体认。事实上,五官在对不同物象的感知过程中往往交替为主,相辅相成。因此,我们很难将任何感官的作用看作是凌驾他官之上的固定与唯一的中心。再者,古代经典对人类感知的中心其实有过明确的界定。这个中心不是味觉,而是人心。如《荀子·解蔽篇》所总结的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即便味觉作用本身,也必须受心主导 :“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 ” (《灵枢·脉度篇》)当然,汉语“心”的含义非常丰富,其功能总包万虑,集情感、思维与精神于一意。这与西文中对情感心(heart) 与智识心 (mind) 的分界恰成对比。语文关乎思辨。这也许是为什么西方哲学常以情感与理智等二元对反的张力与分争见著,而中国思想则更富中和通化的韵味。
话又说回来,正因为五官的感受可以相通,由味觉来理解甚至统领心体的感知过程是一条具有深意的进路。贡著通过味觉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进行整合与重建可谓独具只眼,发聋振聩。应该承认,味觉即便不是中国人感知与思想的唯一中心,大概仍不失为五官体验中的一个重心。中心只有一个;重心则可以依据不同的情境有所转替。我们对味觉文化的推崇,不必以贬低或忽略其他官感为前提。与西方的理性中心主义相比,中华传统的一个特色可能正是其多元性。总之,现代人要摆脱自我中心主义的困扰,所需要的也许并不是对味道的刻意执着,而是通过品味的修炼培养一种平静中和的心境。而达成这种心境的途径可以因人而异,不一而足。应该说,由身心修行所体证的工夫境界上的差异要比味觉、听觉与视觉这些不同进路间的差异更为重要吧!
好规范,使人闲
陈乔见
在中国哲学界,贡华南教授的中国哲学做法可谓自成一格,别有一番意味。贡教授早先从近代中国思想界的“科玄论战”入手,探讨“知识”的问题,由近代学人所讨论的“直觉”进一步找到中国思想自身中的“感”,进而追溯到了作为五味之首的“咸”,由是开启了对“味觉思想”的梳理、思考、诠释与建构。最近出版的《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则是把他对现时代的感受——“忙”——纳入哲学思考之中,由是坐实他所倡导的味觉思想。毋庸置疑,贡教授的研究不落窠臼,让人耳目一新,全无中国哲学研究中那些令人厌倦的“章法”。从实质上看,他的一些观点同样发前贤所未发。其中,于我个人而言,最富启发的是,他在即将出版的《味觉思想》中所勾勒出来的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三条线索 :其一是从“象”、“形”到“使形者”再到“形而上”的思想线索;其二是从散殊之“体”到类之“体”再到作为“故”之“体”的“本体”的思想线索;其三是从“类之理”到作为“故”的“理”再到作为“理”之理的“天理”的思想线索。这三条线索勾勒了从先秦到魏晋再到宋明这一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转捩性质的思维方式和核心概念的衍化。这种哲学与思想史的勾勒,绝非仅凭聪明才智即可臆想杜撰,它一定是经历了十几年的文献积累和反复沉潜思索而得。这种“重建中国哲学”的尝试和做法值得高度肯定。
不过,在贡教授的论述中,笔者对他的某些说法和观点,亦有于义未安处。首先一点就是大概很多人都会质疑的“味觉思想”。贡教授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域中论定希腊(欧洲)是“视觉中心主义”,希伯来是“听觉中心主义”,中国传统是“味觉中心主义”,这种概括难逃简单化约的危险。两希姑置不论,但就中国思想而论。贡教授梳理了早期中国思想中的“耳目之争”和“耳舌之辩”,由耳胜出到舌胜出,由是而奠定了味觉思想的基调。笔者以为,贡教授的梳理轻视了“心”的理性和意志功能这一维度。比如孟子说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说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无论是“大体”说还是“天君”说,都分明把“心”较之耳目口(舌)等看得更重,就其实,则是对思考、分辨、判断、选择等理性和意志能力的重视。荀子更是强调唯有“心”才可知“道” :“人何以知道?曰 :心。心何以知?曰 :虚一而静。”(《荀子·解蔽》)这些说法似乎明显与“味觉中心主义”相抵牾。如果说,从原先处于边缘的思想资料中发掘新的思想传统,这是十分有意义的;那么把边缘塑造为中心并描述为“中国文化之血脉”,则似乎有些过。反过来,这种过度又会影响到对思想本身的理解。比如把上述三条思想发展线索完全纳入“味觉思想”框架,至少有些地方稍嫌牵强,比如从“形”到“形而上”的思想衍化,脱离了抽象和思辨而仅凭“味觉”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其次,是笔者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即正义问题。贡教授在《忙与闲》第五章论述了“盗”与“道”。贡教授对现代世界的感受是一“忙”字,“忙是因盗而忙”,“忙人即盗,忙人盈街,可谓满街都是强盗”。相较于传统儒家“满街都是圣人”的说法,“满街都是强盗”的论断无疑是具有颠覆性的。不过,贡教授所谓“盗”比我们日常生活或法律用语中的“盗”更为宽泛。在他看来,人不经天地万物的同意而从天地万物那里获取衣食住行之所需,本质上皆为“盗”,今人所讨论的“分配正义”不过是使分赃变得更加所谓“公正”罢了。贡教授的出发点在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人大于天),不仅要尊重“人道”,而且更应尊重“物道”(天大于人)。按其说,则“盗”是人的本质规定,因为人要生存就必须“盗”取万物。那么,如何使“盗亦有道”?贡教授特别反对现代人的“以规律取物”,主张“以物道取物”,前者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和需要取物,后者是“依时取即依照日月之令取”。“万物有其时,招之取之非时即为盗。”问题是,把“规律”与“道”完全对立起来是否合适?人类诚然有掌握了一物之规律而创造出非时之“物”的情形,但就我们的日常观念而言,依时取物不就是遵循规律取物么?换言之,“规律”即是“物道”之一种。更何况,“依时取物”或“以物道取物”的背后依旧是人的意志和需要,其本质仍脱不了“盗”之名。
如何由“盗”返回“道”,贡教授开出了两个方案 :其一,自我改变,做自我净化的工夫,将人的占有性目的收回、退隐,不走出自身,不插手他者。其二,拒斥规范和法令,“自觉以法为令之非,松动法令构成的强大的盗之堡垒,拒绝以法为令展开自身,此亦摆脱盗的重要环节”。在笔者看来,第一个方案不啻一味精致化的心灵鸡汤,想想那些每天为生存生计而劳作忙碌的黎民百姓,你一有闲阶级跟他们说“自我净化”、“退隐”云云,这太没人情味,简直是拉仇恨。第二个方案也很难苟同。笔者很赞赏庄子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深刻洞见和批判精神。然而,如果人生在世注定为盗(根据贡教授对“盗”的理解),不可能有绝对的有道世界或公正世界,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即如何规范盗,以便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比较有道或相对公正,这就需要仁义礼法。如果没有仁义礼法的界定、约束、规范和制裁,人与人之间的盗行将变得无法无天,人对天地万物的盗取也将变得无法无天,如此,人与物都很难“闲”下来,“物道”根本不可能得到尊重。相反,惟有好的规范,方能使万物各正性命,“闲”下来。质言之,“物道”要得到尊重离不开“人道”的确立。
可感的语言和中国的哲学
刘梁剑
中国的哲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地做中国哲学。所谓“做中国哲学”,不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客观对象加以考察,而是以哲学的方式研究问题,同时这种哲学研究还带有某种中国的味道。这方面的成果包括 :杨国荣教授“具体形上学”的开放体系,陈嘉映教授对科学、说理、良好生活等问题的贴切思考,黄勇教授以庄子、程朱等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接着”西方当代哲学“说”出的道德铜律和差异伦理学,陈少明教授关于“做中国哲学”的具体实践及方法论反思,潘德荣教授关于“德行诠释学”的理念,如此等等。近十余年来,贡华南教授的研究独辟蹊径,相关成果总是令人耳目一新。依笔者之见,它们展示了做中国哲学的另一种可能性 :从感觉开始,更确切地说,从感觉中的味觉开始,思考中国人当下及传统的生活经验和运思经验,从而在挖掘中国哲学特质的同时,让自己的哲学思考带上中国哲学的特质。“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中庸》)同样,我们无时不用“味”这个概念,然鲜有人对“味”进行精细的专题考察。味,中国人的经验原型;意味,中国人的思想范式;味-道,中国人追求的极高明之境。由是,味——意味——味-道,一条“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哲学的开显之路。作为道-路,即通往道的路,也许它不是唯一的,但无疑是别致的。
我们如何做出中国的哲学?由于哲学和语言的密切关系,我们不能不关注语言,关注中国学人在其中做哲学的元语言。熊十力曾致函汤用彤,谈到亟需培养能够注疏佛经的人才,“务期以今日活的语言详释古经名义”[注]熊十力 :《十力语要》,《熊十力全集》第4册,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7页。。注疏经典需要“活的语言”,做中国哲学更需要“活的语言”。然而,何谓“活的语言”,它如何是“活的”?无疑,我们首先会想到它应该是现代汉语。但这点对于做哲学来说是不够的。哲学不免要用到术语,然而现代汉语常用的哲学术语往往有无根之弊。如所周知,现代汉语中的说理词大多源自西方近代思想的翻译。它们作为“人工”的译名得到理解,尚未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长”到一块儿,我们用起来不免有一种“隔”的感觉。再者,这些常用的哲学术语又是飘浮的大词。一般说来,一个语词要有意义,必须“十字打开”,在横向维度与其他语词发生意义的关联,在纵向维度与生活世界发生关联。作为大词的哲学术语先天不足,缺乏纵向维度,它们在彼此的相互指涉中所获得的意义充其量只是飘浮无根的意义。因此,活的哲学语言除了是现代汉语之外,还应该是扎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与当下生活世界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是比较可感的语言。中国哲学的创造有赖于可感的语言。
陈嘉映教授回顾早年自学哲学,尼采、杜威等人的书为他敞开了一条新的地平线 :“他们的生活世界是我了解得相对比较真切的世界,我比较能够把捉他们的表述和他们的世界经验之间的生动联系。”[注]陈嘉映 :《求真迷行录》,《无法还原的象》,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6页。尼采等人的语言是比较可感的,用这种比较可感的语言来做哲学思考,思考就容易贴切、实在。陈嘉映教授这里讲“可感”,着眼于哲学语言和生活经验之间的生动联系,把自己在“求真迷行”路上的重要感悟端出来,惠泽后学良多。不过,贡华南教授可能还会提醒我们 :当心!不要把可感之“感”理解偏了。随翻译而引入的西方近代思想似乎已经浸入我们的骨髓(受过哲学训练的人尤甚),看到“感”,我们很自然地把它理解为“感性”,一种与理性相对的较低级的认识能力。然而,依照中国人原本的思想经验,“‘感’不是西方近现代知识论意义上的感觉,‘感’之官是由心统摄的身之整体,它既指味觉,也指味觉化了的视觉、听觉,乃至嗅觉、触觉,感的特征即在于人的自觉参与”[注]贡华南 :《味与味道》,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在此意义上,要明白“感”,首先需要破除“感性”的理障。
试比较“感性”、“可感”、“感”。“感性”是哲学术语,承荷着很多理论,尤其是西方近现代认识论,同时它本身是不那么可感的大词。“可感”更像是日常语词,没有那么多理论负荷;而且,它和我们的生活经验有生动的关联,所以它本身还是可感的。如此一来,如果要做中国哲学,“可感”较之“感性”有不少优胜之处。日常语言是富矿,哲学家一项富有前途的事业,便是从中萃取语汇,通过自己的运思将其锤炼成意味深长的术语。其中一种锤炼术 :将现代汉语通行的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如“可感”)锤开,敲打锻炼其中的字(如“感”),仔细发现(抑或发明?)其中隐藏着尚未觉察到的意味;意犹未尽的时候,索性再用点力,把字也破开,追究造字的奥秘。这样做还有一个妙处 :字在古代汉语中往往是可以独立使用的单音节词,它们在历史长河中千锤百炼,积淀了丰富的意蕴;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字音韵学对字的音、形、义进行了持续的自觉反思;语词(或者进一步的“字”)打开之后重新合拢,我们可以把这些古老的丰富意蕴吸纳拢聚到现代双音节或多音节词之中去。《味与味道》充分运用此种锤炼术,对“味道”、“意味”、“回味”、“对象”、“象”、“感”等等的解释生意盎然。不过,某些地方似乎过了头,给人牵强附会之感。比如,为了说明美味意义上的“羞”如何转化为羞耻意义上的“羞”,《味与味道》言曰 :“羞”字展示了“以手举羊,欲抓未抓时游移不定的神态,引申为面对羊等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时有所感、有所思”[注]贡华南 :《味与味道》,第145页。。依笔者之见,字义的引申流衍有很多“不讲道理”的地方,如果一定要在这些地方给出说法、讲出道理,便只能自己“想出”一番理,进而不自觉地把这番理当作历史事实。在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理与事、思与史之间某种内在的紧张。贡华南教授的味觉思想颇多“思”的创获,下一步的工作将是以味觉之思返观中国哲学史,梳理中国思想发展的新脉络,衡定中国文化相对于两希文化与印度文化的特质。在此过程中,思与史之间的张力会不会更加突显?
味-道诸义——对相关问题的回应
贡华南
各位同仁提出的问题都很有挑战性,对我启发良多。下面我简略地谈谈我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一、 自然性感官与文化性感官
我一直把感官、感觉问题放到具体的文明、文化系统中考察,而不是抽象地讨论“人”的感官、感觉。作为生理性器官,诸感官不思想。不过,作为文化性器官,诸感官总与思想相互贯通。如我们所知,每个文明、文化系统都在自觉地选择、凸显特定的感官、感觉,而不是一视同仁。为什么不同文明、文化系统会选择某种特定的感官?如我们所见,各个文明、文化的集大成者都会为其选择而给出自己的理据,后世的思想家们也会自觉地传承,并结合各自时代的知识状况进行论证。比如,古希腊自觉选择视觉、凸显视觉。古希腊思想家会说,从认知上看,眼睛更可靠,口舌贪图享受而导致认知含混,等等。近现代欧洲思想家们区分了“机械作用的感觉”(视觉为代表)与“化学作用的感觉”(味觉为代表),持续强化着视觉的优先地位。
经过特定文化观念的选择与不断的强化,各种感官、感觉也就脱离了生理层面,成为文明化的感官、感觉。人皆有五官,但在不同文化传统中,五官的地位并不齐同,五官之中总有一个官觉优先于其他官觉,主导后者,并进而主导认知方式。这在一个文明内部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但在不同的文明的对照之下,各感官的地位差异便可清晰地显示出来。同样是视觉,在“非礼勿视”文化中展示的是人自身的教养;在“以道观之”思想系统中展示的是“道”对万物的统摄;在认知优先文化中凸显的是对客体的扫描、聚焦。虽同为“人”,同有“耳目”,但在不同文明、文化系统中,感官展开的方式都会依照不同的文明、文化观念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涉世未深的孩童、教化未达者之感官活动或许大同小异。不过,这恰恰证明,文化对感官的规训决定了不同文明、文化系统中,感官活动方式不可能同一。专注于“对象是什么”的文化,与专注于“对象对人意味着什么”的文化,在面对同一对象时,也随时在调动、引导不同的感官,为其提供所需的素材。自然性感官正是如此被“化成”文化性感官。
二、 感官与心
如何理解内在的心?心有无外在的通道?这个问题在几大文明中都被提起,其实质是对“反思活动”之“反思”。中国文化有“耳目,心之枢机也”、“心目”等说法,西方文化有“眼睛为心灵的要道”等说法。这表明,古人一直相信“心”有外在的感官与之对应,并试图通过外在的感官来理解内在的“心”与“心的活动”。 我在《中国早期思想史中的感官与认知》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有较为详尽的论述,现录之于下 :
心之官则思,心并不直接与外物接触,因此,在认知客观世界的时候,心作为思的载体并不拥有现实的思想内容与思想方式。思想活动之现实性源于人生命活动之展开,源于与其他存在者现实的交接与交往。一切现实的认知活动一方面会呈现出相近的思想品性,比如,区分事物的类别,寻求区分类的根据,等等;另一方面,不同文化系统的认知活动又总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比如,有不同的分类标准,有不同的确定标准的根据。这些差异根源于不同文化系统对心的不同理解,及相应对其活动方式的自觉塑造。
作为身体器官,“心”在内,但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都不约而同设定了相应的感官作为其外在的表现与通道。“心”在这些感官中直接呈现,感官活动与心的活动隐喻性地实现了同一。不同的文化系统对作为心外在表现与通道的感官的关注有不同侧重,由此使与感官活动相通的认知活动的内容与方式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感官与心直接相通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感官中发现心,可以从不同的感官活动了解心的活动在认知方面的多样品性。感官活动引导着现实的心的活动,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认知方式,也成为理解后者之不同的关键路径之一。每个感官与物交接的方式皆有显豁易见的差异,不同的感官与心的直接关联使与之相关的认知内容、方式、对象呈现出不同个性。正因为“心”与感官之间的内在直接的关联,因此,从感官入手找“心”,一直被认为是可行的思路。
从世界文明图谱看,视觉、听觉、味觉分别在不同天地间被凸显。在认知客观世界的道路上,视觉、听觉、味觉分别主导思想道路的塑造,分别成就了偏重视觉、听觉和味觉的文化与文明。这表现在 :视觉活动、听觉活动与味觉活动不仅分别为不同文明的认知活动提供了质料,也为其提供了原初的范型,比如思想者如何安置思想对象,如何调适与思想对象之间的距离,以及如何摄取对象(比如色声味),进而如何塑造对象,如何规定对象,等等。[注]贡华南 :《中国早期思想史中的感官与认知》,《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味觉思想并非强调生理性的味觉在思想,也非强调中国人不用“心”,而是表明,思想的原型是味觉。或者说,味觉作为原初经验塑造了特定的思想方式。同时,这些原初经验也为思想提供了实质性精神义蕴,“善”、“美”、“义”、“羞”等汉语思想核心观念语族与“羊”这种“可欲者”之间的直接关联皆表明了这一点。当然,如何在揭示原初面目之时保持思与史之间、异想天开与辨名析理之间的平衡,这始终是沉思者必须面对的难题。
三、 心者神明之主
从感官处寻求心的活动方式只是表明,在各个文明、文化系统中并非四海同心,也非万古同心。据我的浅见,中国早期思想史中,“耳目之争”所争的乃是耳目对心的塑造之主导权。耳胜出,乃是耳获得了塑造心之活动方式的主导权。继而,“耳舌之辩”所辩的乃是耳舌对心的塑造之主导权。舌胜出,乃是舌获得了塑造心之活动方式的主导权。这个历史过程的完成表明,如何塑造“心”,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一个文明、文化对心活动方式的塑造尽管一直在进行,但并非变化无常,甚至变化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多。感官的选择总会在历史过程中被定格在某个特定感官,从而使心的活动方式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并且在新的问题境域出现时,不断地回到此特定感官,以期获得新的源泉。不过,心的活动方式一旦被确定,它往往会自觉脱离其原型,而将其凌驾于众感官之上,甚至坚定地与之划清界限。比如,味觉思想通过“神农(尝百草)”、“黄帝(《内经》)”等神圣之味觉与心被确立。神圣之口舌与心则被当作庶众之标尺,而庶众之感官总是有待规训,其心也总是有待于匡正与拔高。
“心”与特定感官之间的直接关联,特定感官对“心”活动方式的塑造,并非抹杀“心”对感官的统摄。心的活动与耳目舌等感官活动确实不同。毋庸置疑,“味”主要是心在味,“感”主要是心在感,“体”主要是心在体,“理会”主要是身心在理会。广而言之,归纳、推理、抽象、演绎都是心的活动,由“形”到“形而上”也是心在运思、在超越。所谓“味觉思想”、“视觉思想”,无非是说归纳、推理、抽象、演绎、形而上这些心的活动在不同文化系统中具有不同的方式。比如,在味觉思想中,心以“立象”方式达到普遍性;在视觉思想中,心则以“抽相”方式达到普遍性。在味觉思想中,我们可以谈“感情”;在视觉思想中,我们才能谈“移情”。
味觉思想回答的重点不是“心何以知”的问题,比如,是否需要德性作为其前提,其重点落在“心如何知”上。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最大的差异是前者设定天下“无一物非我”,而闻见之知则是以“我”与天下之物之“非我”之间距离的设定为前提。心知、德性之知的展开自觉消除主客之对立,此即我说的“以味体道”或“味道”。
四、 通感
西方文学中的通感与佛学六根互用都是极其有意思的问题。通感之可能,其根据在于,对象乃色声味形等可感性质之统一体,同时,人自身乃诸感官之综合体。感官与对象之间不断交往而熟悉,诸感官共同参与,彼此之间交换信息,由此彼此之间可以互通、暗示。以此为基础,某感官得以捕捉到其他感官之对象。例如,眼睛可以看到声音,耳朵能够听到形色,等等。在某些感官障碍者那里,经过训练,其他正常的感官可以替代受损的感官,这也可以看作是通感之一种。
通感现象存在于各文明、文化系统中。但在对事物的认知过程中,各文明、文化系统并没有倚重通感。或者说,并没有以通感为认知事物的基本方式,亦不曾以通感为原型构建自己的文化理想。比如,参与对事物本质的设定,以及对通达事物本质的方法论的构建。如我们所知,古希腊视觉优先观念将“相”(idea)视作万物之本质,将“心眼”规定为通达本质的康庄大道。其文化观念都围绕视觉构建。怀特海将其后两千年的西方哲学视作古希腊哲学之注脚,这无疑挑明了视觉思想充当着西方文化之主轴或血脉。不可否认,通感在视觉文化中发挥过作用,但此作用绝非主导性的,目之为视觉思想之补充或许更恰当。在中国文化中,通感或六根互用现象亦大量存在。但经历耳目之争,耳胜出。继而,耳舌之辩,舌胜出。在舌最终主导和构建的味觉文化中,滋味、意味、道味被理解与规定为对象之本质,味觉的不同历史形态,如感通、体味、理会被规定为通达对象的主要方法。感通、体味、理会并非单纯的理智活动,身、心诸感官共同参与其中,就此说通感亦未尝不可。只不过,此通感明显以味觉方式展开。
五、 味与道
味道与中国传统核心观念之间的关系对于味觉思想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在我看来,味觉思想乃中国文化的血脉。它既是传统观念的基本特质,也是贯穿于这些观念历史形态的基本脉络。当然,最重要的是,味觉在这些观念构成过程中充当着主导作用。比如,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它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范畴 :不仅百家所论的“道”的内涵有差异,不同时代“道”的面貌也不同。
我在考察商周以来感官的历史选择时曾指出,先秦时随着“目”的凸显,视觉一度成为构建道的主导势力。比如,在兵家、法家、形名家那里,“道”都高高在上,与人保持着巨大的距离。随着耳在“耳目之争”中胜出,听觉又成为构造“道”的主导势力。相应,听觉所构造的“道”起先与人有距离,亦有高高在上之态。但听而闻的过程,却使得这个距离逐渐消弭,最终,人与对象相融相即。在孔孟老庄那里,我们可以发现“道”的听觉特征。随着舌在秦汉“耳舌之辩”中胜出,味觉成为构造“道”的主导势力。于此我们所见的“道”不再与人有距离,这就是后世所熟悉的“日用即道”思想。
如我们所知,“道”在中国文化中是最高的范畴。“道”与“人”之关系的历史变迁,以及味觉所主导的道的构造,也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核心范畴确立了基本基调。比如,从道到德,《老子注》到《庄子注》,从理(学)到心(学),以及20世纪由新理学到新心学,中国思想史中几个重要思想脉络的历史演进无疑都与味觉思想主导有关。当然,如何细致论述味觉思想与这些核心范畴、核心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六、 味觉思想在当代
在味觉思想者看来,当代最大的问题是万物及人的“失味”。其表现即是万物的图像化,其思想的根源则是视觉思想的现代泛滥 :人自居于万物之上,通过科学技术将万物化为图像,以图像为实在,从而最大限度地宰制万物,进而将万物从天地间拔根,使其失去自己的世界,远离真实的存在而失去自身之味。人在这个过程中,对物的控制使其亦从天地间拔根,失去自己的世界,远离真实的存在而失去自身之味。窃以为,以味觉思想扭转视觉思想,可以克服人、物之失味,及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扭转”之关键是人要柔软自己的身段,对万物放手,以天道为尊,这对于以己为尊的现代人诚然是个难题。尽管万物失味,人也因此败坏了自己的品味,但味觉思想仍不失为当代人希望之所在。堕落的路正是拯救的路,除非我们对这个世界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以我手写我心,写人生百味,尤其是自身的痛痒,这是在当代开展味觉思想的基本要求。一己之痛痒与一座城的痛痒、一国之痛痒、一世之痛痒相通,万物也不能免痛,“人忙万物忙”是也。忙乃以己加于物,取物归于己。忙即盗,忙人即强盗。不告而取谓之盗。我把“取”的宾语由“人”扩展到“人与物”,这并非一己心血来潮。看看我们的食物就知道恣意地取物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生来并不为盗,盗并非人的本质。在我看来,盗是在特定意识形态下(比如更高更快更强),通过法律、制度鼓励、怂恿、支持、赞美而成就的特定人格。我所做的不过是揭开当代忙人为盗之面纱,让世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人之所为对天地万物意味着什么。
正义问题既涉及人群之间,更关乎天人。人间的正义并不能保障天人正义之实现,相反,当代人习惯认为,“发展”才是解决人群正义的终极依靠。止于“人道”而求正义的光景至多是,人美天(物)不美。我们不应期待这个结局,其实现乃是我们所不能承受之厄运。因此,重建物道,以天、地、人、物构成的大场域作为我们思想与行动的基本视域,将“天人共美”作为我们终极愿景,这更有可能让物得其味,人得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