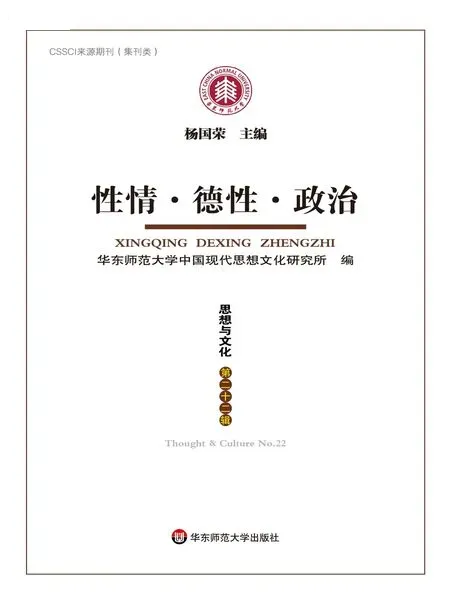发现内圣外王的庄子
——评陈教授的《庄子哲学的精神》*
2018-04-02
●
《庄子哲学的精神》是一部关于庄子哲学的论文集。在这部论文集中,陈赟教授对庄子的文本做出了别开生面的诠释。全书共分八章,包括《〈庄子·天下〉与内圣外王之道》、《〈逍遥游〉的鲲鹏寓言与人的自由》、《从“是非之知”到“莫若以明” :〈齐物论〉与认识过程的升进》、《“庖丁解牛”与养生的大义》、《“不知之知”与“非人之人” :〈应帝王〉与庄子的政治批判》、《“浑沌之死”与“帝”“王”政治典范的终结》、《由人而天的“机制转换”与新主体观》、《从“无体之体”到“与化为体”——庄子哲学的本体与主体》八篇论文。每章各有论旨,虽无形式上的系统性,实质上却有一贯性与整体性。如果说“化”字构成全书的潜在中心词,那么,“与化为体”就可以视为该书的“书眼”,也是该书抵达的结论。本文首先对此书作一简要介绍,然后再作一简要的评论。
一、 该书大要 :始于内圣外王,终于与化为体
陈赟教授通过“万化”、“造化”、“大化”等的分析,指出“化”不仅意味着存在的本身,而且也是存在的方式。世界的自我展开与呈现通过“化”进行,生生之德构成天地之“化”德。也就是说,天地在“化”的过程中彰显着“化”的伟大品质,即“生而不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的“玄德”——化化者不化,而让万化自化。与这种生生之意的造化相伴生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与化为体”,它要求的是一种以滋养、蓄养而不是消耗为特征的养生的生命政治学。这就意味着政教行动本身就是“化民”,上行其教,以成民俗,在不知不觉中引导人民自成其为人。以这样的方式,帝王的统治就转变为百姓的自我治理。而将“与化为体”的生存论与“化”的生命政治学加以连接就有了庄子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就是以“化”为机制的生命政治之运作[注]陈赟 :《庄子哲学的精神》,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导言第5—6页。,这就是该书的写作思路。该书把对《天下》篇的解读作为全书之首,这一方面呼应了《天下》篇作为庄子后序的传统看法,另一方面则是凸显“内圣外王之道”在庄子思想世界中的中心位置。《天下》篇乃是庄子综论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大文字”,陈教授认为对六家学术的讨论只是其“表”,其“里”则是中国政教生活的核心问题。“内圣外王之道”在《天下》篇首次提出,它给出了《庄子》一书的问题意识,也展现了整个中国思想的基本关切 :回应整个中国思想在周秦之变这一大时代面临的大问题,庄子才得以提炼出“内圣外王之道”这一本身就具有震撼性且极具思想潜力的概念。正是在此意义上,陈教授将对《天下》篇的阐释放置在全书之首,这种安排既源于《天下》篇与《庄子》内篇本身的内在体系性,同时开宗明义地点明整该书的核心问题。
《天下》篇以“道术”与“方术”之辩开篇,庄子通过对此二者关系的阐释,揭示了从方术开出道术的可能性,而道术的通达要求天道(神)、地道(明)、圣、王四者的连接与整合。在“神、明、圣、王”的大视域下,庄子将生命存在的类型划分为天人、至人、神人、圣人、君子、百官、民七类,从而揭示出政教文明的人性基础。在七类人中,圣人乃是人类政教文明的中枢,因为只有圣人能通达七种人性类型,从而承担起“圣者尽伦”、“王者尽制”的政教事业。
钟泰先生曾言 :“《天下》篇深致叹于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此内七篇,则所以反复发明内圣外王之学者也。”[注]钟泰 :《庄子发微》,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页。其中“《消遥游》之辨大小,为内圣外王之学标其趣也。《齐物论》之泯是非,为内圣外王之学会其通也。”[注]钟泰 :《庄子发微》,第2页。那么,小大之辨、是非之别在何种意义上构成对内圣外王之道的展开?《逍遥游》开篇的鲲鹏之化寓言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鲲鹏作为自由主体的象征被置放在《庄子》首篇,这意味着“自由问题”构成庄子哲学的始点与归处,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形而)上又抵达(形而)下的鲲鹏乃是作为能化者——自由主体的象征。以重言方式出现的鲲鹏寓言强调的是唯大者能化,唯化者能游。而这个“大”不仅指代鲲鹏本身之大,更重要的是带出了一个浩渺无涯而又时刻变化着的无穷境域。这个令人震撼的视域展现的是气化流行的宇宙论,也就是说世界的自我呈现方式是“化”。“化”的宇宙本体论为“自由”问题提供了背景视域与理论支撑。
《逍遥游》中的“化”,表现在从有功到无功、从有名到无名、从有己到无己的工夫过程。[注]陈赟 :《庄子哲学的精神》,导言第4页。这个“化”最终需主体去承载、去展现,因此陈教授分析了“我”、“吾”两种不同主体形态。“我”是与天地万物相对待的“主体”,也是眼耳鼻口不能互通的“主体”;而“吾”于内部意味着官能的相互通达,于外部则意味着天籁与人籁的统和与沟通。从“我”达“吾”之路,即是从认识上的是非彼此的错综构成返归“莫若以明”的清明状态。这就意味着只有“丧”去了“我”,才能“化”为“吾”,化掉教条化的“成心”,化去凝固化的“成形”,在艰难的人间世,人才得以展开自由的飞行。[注]陈赟 :《庄子哲学的精神》,导言第4页。
丧“我”化“吾”的动态生命行程,意味着以滋养而不是以消耗为其存在样式的生活形态,而“庖丁解牛”所蕴藏的养生大义便是这种生活样态的寓言表达。庖丁解牛的关键在于由“技”而“道”,以“道”辅“技”,而养生之理便隐藏在“技”、“道”关系之中。其内在的逻辑是,由解牛之技上达解牛之道,道周流六虚,旁通互成,故可因解牛之道体悟养生之理。而连接解牛与养生的关键是“缘督以为经”。“缘督以为经”就是“顺中以为常”,即不滞于上下左右,而能通达上下左右,是以顺中者无滞无碍、空空如也。这显示的是一种“虚静”的主体(在“庖丁解牛”中称之为“余”),主体之虚意味着给万物固然之天理预留了自我显现的余地,故而主体之“虚”恰恰带出的是天理之“实”。在以蓄养为特征的生活中,“余”成为这种生活中的新的却又更真实的生命形态。
一种以无执、通达、蓄养为存在样式的生活,意味着政教行动指向的是“养民”,其实现方式是“化民”,而不是“治民”、“统民”。由此而言,最高的统治是一种没有统治的统治,一种百姓不知统治者存在的统治,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此时,帝王对百姓的统治转变为百姓的自我治理,即“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对政治生活的思考集中于《应帝王》篇。从“应帝王”篇名可见,庄子面对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意识 :在以德与礼为政教实践的理念纲领的帝王时代已经不再可能的情况下,政教生活如何重新开端?即如何应对“帝”、“王”时代的终结问题。
《应帝王》开端啮缺问王倪之寓言给出了庄子对政治生活始点的思考,结尾浑沌之死的寓言则蕴藏了政治生活的归宿。出发点的差异既会直接影响到对政治过程及其本性的理解,也会导致不同的思想归宿[注]陈赟 :《庄子哲学的精神》,第144页。,因此陈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着墨最多,认为“四问而四不知”中的“不知”与“未始出于非人”中的“非人”构成了庄子政治批判的双重开端。“不知”不是知的“否定”,而是意味着更深层的“不知之知”。从“知”到“明”到“神”的层层深入,就内蕴在“不知之知”中。而恰恰是“神”、“明”构成了通达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帝王之德,与“不知”相对的“知”阻碍了认识向着天、地开放。需要注意的是“不知”并不是“反知”,也不是“非知”,而是知与不知的互动,“不知之知”与“知而不知”是其两种形态。因此,庄子以“不知之知”为起点的政治思考,通向的是天、地、人三才贯通的帝王政治类型。在此庄子批判了“王倪”所代表“王道”和“有虞氏”所象征的“帝道”。以“礼”为政教典范的三代王道造就了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战乱时局,同时处于王道上游、以“德”为政教典范的帝道亦不是庄子理想的政治,因为尧舜之道(帝道)虽安于一世,“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注]《庄子·庚桑楚》。。在庄子批判的眼光下,儒家所提供的最高理想仍内藏治乱之机,依旧无以逃脱治乱循环的机制。庄子试图直驱本根,跳出治乱的相互对峙,从而建立一种更具有原初意义的政治生活。理想之政治在《应帝王》中以“泰氏”的形象出现。“泰氏”这一圣人形象带出的是“相忘于江湖”的政治生活形式,相较于与民同体、与百姓同忧的“相濡以沫”,泰氏展现出来的是万物自生自化、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生活图景。圣人与物无隙,与世偕忘,淹没于万物之中,有化物之效而无化物之功,这时政治嵌入到了生活之中隐而不显,因此天下作为天下人之天下的可能性得以敞开,而“藏天下于天下”正是“泰氏”带出的政治生活的最高可能性。
帝道政治之所以陷于治乱循环之中,深层次原因是在“人禽之辨”的基础上界定人,这种在与“非人”对峙意义上建构起的政治生活将导致以理性化与秩序化的方式挤压未知性与混沌性,其最终指向的是片面化与支离化的人。而“泰氏”所象征的政治典范,以“非人之人”为根基,去消解秩序与混沌、人与非人的对立,从而支持政治生活去抵达那种整全的个人。正是在对人不同的理解上,最终导致两种不同的政治生活形式,而帝道之所以不能成为理想政治的原因在于立足于与物相隔的“人”,而不是大全之“道”。
在人禽之辨视角之外重思人的另类可能性,即所谓“非人之人”,而这与“与化为体”的新主体构思关联在一起。如果说《庄子哲学的精神》的第五、六两章给出的是“还天下于天下人”的返归式的政道,内在要求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治道,那么,“与化为体”带出的是养生性的政治生活形式,后者最终落实到人的身体之中。[注]陈赟 :《政—治、教—学与文—化——古代中国政治正当性思想的一个向度》,《学海》,2007年第2期。从对毕来德的《庄子四讲》的批评切入,通过从“人的机制”到“天的机制”的转换,陈教授构筑了一个新的身体-主体观。作者认为毕来德建构的主体观,意在应对今日生活在世界上的个人所面临的以下困境,即现代性社会所催生的一种为历史、社会与政治所设置的残缺主体,因此毕来德通过《庄子》而建构的乃是一套能解放这种被规训化了的主体的新身体-主体观。虽然毕来德把庄子带到了当下境域中,但问题是他却把庄子从中国传统思想与社会政治脉络中抽离出来,与真实的庄子失之交臂。如庄子曾以“通天下一气”揭示宇宙秩序与身体秩序之间的连续性,毕来德却将气局限在个人身体之中,从而与宇宙隔离。毕来德把宇宙秩序视为帝国秩序的自我论证或辩护的方式,政权与个体是对立的,个体为确立独立性,摆脱外在体制、规训的控制只能切断与宇宙秩序的联系。陈教授认为这又是毕来德对《庄子》的误读。在庄子思想中,天道不是绝对的超越者或形而上学的造物主,而是一种将秩序与浑沌包裹在其中的气化论宇宙观,它具有一种不为人的知能所穿透的浑沌性与未决性。天道在保持自己的浑沌无定与开放性的同时,还为人的自由思想与行动预留了巨大的空间。“无体之体”乃是天道的本性,这给出了一个没有终极的造物者而物各自造的存在论,由此天道将事物的根据与意义交还给了事物本身。“无体之体”的本体概念与浑天之旨相互构成,建构的是立足于气的基础上的大化流行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要求的存在方式是“与化为体”,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变化而参与天地万物的变化,甚至辅助天地之化。
总体而言,该书围绕着“天下”问题,以“化”为进路,形成了认识论、政治学、主体观的三重诠释交响曲。这既是陈教授对《庄子》的诠释,又根植于《庄子》的文本逻辑。
二、 陈书之“隐言” :“深度诠释”
近代分科之学建立之后,众多经典由于无法契合“学科”而处于游离的状态。幸运的是《庄子》并没有离开人们的视野,不同学科都试图对它展开不同阐释,然同时造成《庄子·天下篇》所言之状况 :“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作为整体性的对象被肢解,哲学视域带出的是《庄子》的思辨智慧,美学给出的是《庄子》的境界之美;这样《庄子》给人带来的仅仅是心智层面上的提升,而没有面向身体及其活动本身。在此意义上,庄子来到了当下,却没有对当下生活有指涉。陈赟教授在《中庸的思想》的自序中提出“深度诠释”,以这种方式所打开的汉语世界是一个基于历史,却对当下有意义,同时面向未来的活生生的真实世界。“深度诠释”似乎构成陈教授探索古典汉语思想的思路,它也贯穿在该书当中。如果说概念化、固定化了的文字是该书“显”的部分,“深度诠释”则属于该书“隐”的部分,是隐藏在“言”背后的“非言”,因此读者需要在“非言之言”中体察作者之思、之意。
“深度诠释”的研究方法,要求悬置那些在潜移默化中不自觉接受而未被反思的大概念,直面文本及其问题,并将这一文本置放在与同时代思想意识的其他文本的关联中去。诚如陈赟教授所洞察到“思想的本性是相互通达的,不同的文本不能被作为既定的不可逾越的封畛。所谓的以《庄》解《庄》毕竟是在思想的事情中人为地圈定封畛”[注]陈赟 :《中庸的思想》,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自序第3页。。古代中国经典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文”关系。穿越于其他的经典,方能更好地抵达《庄子》。因此在《庄子哲学的精神》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先秦“道家”的子学文本,同时看到作为“子学”的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经典的身影,更看到《庄子》与“六经”的一贯性。在不同文本之间自由穿梭,形成一种“大视域”,它为庄子的诠释开辟了更恢弘广阔的远景空间。陈赟教授将庄子置放在周秦之变、中国思想文化的轴心奠基这样的大脉络中,就内蕴了对这一远景空间的领悟。
其次,作为思想的事业,“深度诠释”带来的互动与穿越,最终指向人之生命。作为研究方法的“深度诠释”具有历史性的维度,“史”不止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式,同时指向现在、面向未来,因此“历史”成为“作为当下的过去”,“作为未来的过去”。该书对《庄子》的阐释根基于文本、历史,并由历史身处的文化形式更新、转换当代,从而使之朝向新的可能。由此,《庄子》被输送到了当下,同时指向了未来,成为了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化过程的思想,而不是仅属于先秦的文本。《庄子》被视为整个中国思想与文化在当代进行自我表达的“活文本”。由此,对于庄子的诠释与对时代处境的构思在该书中被关联在一起,成为陈书问题意识的主导方面。
三、 该书的推动意义与讨论空间
书中所选各篇论文,胜意纷呈,各具精彩,又直指核心。通读全书,深有启发。无论是该书的“明言”还是“暗语”,都展现了一个更全面、更深度、更有厚重感的《庄子》。陈赟教授的研究范围广泛,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与时代关怀,理论功底深厚,较强的思辨性又是其为文特点;由是此书往往能够在学术与思想之间保持贯通与平衡,耐人咀嚼,引人深思。本节先列举该书之成就,继而提出一些笔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疑问与感受。
(一) 该书的贡献
该书的首要贡献在于开启了研究庄子的全新视域,尤其看到“六经”、孔子与庄子的关系。“子学”的根柢在“六经”、在“经学”,在此意义上“子学”是“六经”离散的结果。《庄子》核心问题的产生就来源于六经,因此“六经”构成了《庄子》思想的潜在背景。然而,当司马迁的《老庄申韩列传》把庄子列于老子之后,而后世诸家又多囿于学派之见,于是庄子所生活的那个真实的历史世界在诠释者中隐退了,这就阻断了庄子与六经的关联。孔子对六经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使得上古政教文明得以谱系化,因此,孔子成为庄子面对时代问题绕不开的人物。然而,由于近代历史以及分科之学的影响,使得孔子不再是那个对六经进行典范性整理的,塑造了两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先圣,而是被降低为百家之一的儒家的开创者。种种的因素造成孔子与庄子的割裂,一些研究者未能注意到孔子才是庄子真正的对话对象。陈赟教授跳出以庄解庄的格局,直面庄子所面临的时代性大问题,由此呈现出了一个全新的《庄子》。这一庄子完全不同于精神哲学、人生哲学、审美哲学的庄子,而是一个面向政教整体生活的内圣外王的庄子。
在此,陈赟教授提供了全新的切入庄子思想的视角——六经、孔子。陈赟教授尤其注重孔子在《庄子》中的特殊意义[注]详见陈赟 :《庄子对孔子的消化 :以中国思想的轴心奠基为视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甚至由此判定庄子自处于子学之位,以尊经学。对孔庄关系的强调,容易使人误解为陈赟教授划庄为儒,然而,庄为儒为道并不是陈赟教授关注的问题,陈教授的贡献是,于经典之间的互文当中,于更广阔的总体性背景视域之中为《庄子》定位。当把六经作为庄子思想的背景,把孔子作为庄子对话的一个重要对象时,一个之前一直为人所忽视的维度被自然带出了——庄子思想的政治维度。考察庄子学史,会发现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庄子不断地被道教化、禅宗化、美学化、境界化,结果是《庄子》内存的政治向度被隐没了。由此庄子变成了道教式、美学式的庄子,他便不再是先秦那个面对中华文化的整体问题,对三代政教文明有着一贯与根本思考的庄子,去政教化便成了理解庄子的主导趋向。在此意义上,《庄子哲学的精神》还原了庄子的政教向度,开启了研究庄子的新领域。由此,庄子形象走出了仅仅关注个人心灵安顿的窠臼,展示出文明论意义上的魅力。因此,庄子不再是中国思想的例外[注]如毕来德将庄子作为中国思想尤其是帝制中国的例外。详见毕来德 :《庄子四讲》,北京 :中华书局,2009年。,与儒家一样,庄子也为华夏文明的自我奠基提供了思想能量。
(二) 进一步的讨论
1. 鲲鹏寓言是《逍遥游》的开端,也是《庄子》整本书的开端,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庄子哲学的精神》通过对鲲鹏形象的分析,引出了“人的自由”这一主题,这就会促使我们关注 :“自由”对庄子整体思想而言有着什么意义?或者说《庄子》为何以鲲鹏寓言作为内篇开端?在《庄子哲学的精神》中陈教授并未给出答案。这个问题在《自由之思与庄子哲学的出发点》一文中得到了解决。文中指出,庄子哲学的基本背景是对孔子仁道的反思,孔子以仁界定“人之所以为人”,着眼于通过学习的过程而达到伦常秩序。庄子在肯定伦常秩序的前提下,提出了异于仁道的新的切入点,就是自由。这样,自由问题成为了庄子哲学的出发点与目的地。[注]陈赟 :《自由之思与庄子哲学的出发点》,《齐鲁学刊》,2017年第5期。同时,对《逍遥游》文本的内部而言,鲲鹏的最后一次出场又将自由问题引向何方?自由是否仅仅局限于个人身心的安顿?这是《庄子哲学的精神》的结尾引发读者的思考。陈赟教授对《逍遥游》这个“大文本”的解读是全面、一贯而深刻的,认为鲲鹏与其他事物的比较已经将逍遥的问题引向了“正性命”的语境中。个人身心的安顿与政治生活有着密切关系,进而陈赟教授揭示出《逍遥游》中隐藏的政治向度。[注]如 :《逍遥境界的政治向度——〈庄子·逍遥游〉“知效一官”章的文本学释读》,《学海》,2009年第2期;《“尧让天下于许由” :政治根本原理的寓言表述——〈庄子·逍遥游〉的内在主题》,《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无用之用”与“至人无己”——以〈庄子·逍遥游〉为中心》,《哲学与文化》,2017年第2期;《自由之思与庄子哲学的出发点》,《齐鲁学刊》,2017年第5期;《〈庄子·逍遥游〉的文本逻辑与思想结构》,《人文杂志》,2017年第8期;《发现内圣外王的〈庄子〉 :〈逍遥游〉思想的政治向度》,《当代学术状况与中国思想的未来》,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1—168页。
2. 该书第六章,将“德”作为“帝道”的政教典范,将“礼”作为“王道”的政教实践的理念纲领,并分别对应大同与小康两个社会阶段,立意新颖,论据充分。陈教授写道 :“在礼的架构下,德已经不再是帝的政教理念,而转变为人伦的内在品质与规范。”[注]陈赟 :《庄子哲学的精神》,第210页。笔者并不否定“礼”在三代王道之政教上的典范意义,然“德”是否就囿于人伦领域?“德”的确是诸如宗教祭祀、婚丧嫁娶、游戏宴饮这种集中体现人伦的社会实践活动背后的精神价值及其原则,然“德”并没有失去在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
韩宣子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春秋》。曰 :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
先君周公礼制作乐曰 :则以观德,德以处事。(《左传·文公十八年》)
礼乐,德之则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成礼义,德之则也。(《国语·周语上》)
可见,“德”并不囿于人伦领域,它作为制度设计背后的人文动机依旧发挥着作用。在该书的第五章,陈教授提到周公制礼作乐,“天下一家”,“中国为一人”,实际上以小康的形式承载大同。[注]陈赟 :《庄子哲学的精神》,第167页。这就意味着以“礼”的形式去承载“德”。从这个意义上说,陈赟教授并没有否认“德”对“礼”的指引。那么,照此推论,陈赟教授将“德”限于人伦之域也有待讨论了。
3. 该书第五章言“‘不知之知’与‘非人之人’乃是庄子政治批判的双重开端”[注]陈赟 :《庄子哲学的精神》,第145页。,这就引发了读者的思考,这两个开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该书提到“在《应帝王》的文本中,‘不知’在前,而‘人’与‘非人’是由‘四问而四不知’导入的”[注]陈赟 :《庄子哲学的精神》,第145页。,这是从文本上言,仅具有描述意义,因此并没有系统地解释“不知之知如何导入非人之人”,更没有明确地回答作为开端的两者有何关系。陈教授在第五章第三节,论述了“泰氏的非人”与“其知情信,其德甚真”之间的关系[注]陈赟 :《庄子哲学的精神》,第196—199页。,但这并不是对“非人”与作为政治批判始点的“不知之知”的关系的回应,而是在呈现“泰氏”这个圣人形象所具有的“知”是怎样的。因此在该书文本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这样的论述 :“泰氏的‘不知之知’恰恰是循着‘由人而天’的次序,通过是非之辩还原为彼此之封畛,进而通过将彼此之封上升到有物无封,甚至未始有物,从而完成了‘由人而天’的上达之路。”[注]陈赟 :《庄子哲学的精神》,第197页。在这里,陈教授把“泰氏”当成“人物”,而没有揭示出作为政治最高可能性的“泰氏”与“不知之知”的关系,同时两个开端的关系问题也依然悬搁着。
4. 在此书中,我们看到了陈教授对历史尤其是中国轴心时代的深沉思考,也看到他如何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展开深度诠释。思想的深邃性以语言的形式表述出来同样是个艰难的过程,甚或思想的深度与语言的清晰本身存有张力,就像《道德经》首章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揭示的“名”与“道”之间无以绝对的契合。在《庄子哲学的精神》中,读者能很容易地察觉到,陈教授对问题思考得周遍、严密,同时也能感受到他对语言精准的高要求。当陈教授试图兼顾这两个标准时,不得不使用众多的定语去限定、修饰核心词汇,因此造就了诸多极其长的句子。从文章的严谨性来说,这种做法是毋庸置疑的,然表述上的不流畅无形中给读者设置了很多阅读障碍。思想与语言之间的紧张感或许对从事哲学思考多年的学者来说已经习以为常,然对于仍然走在回归真实存在之路上的未达者来说,这个障碍颇需花费精力去克服。从“教”的意义上说,文字上的晦涩无疑缩减了该书承载的“化”人的力量。
以上是笔者提出的几点个人浅见。整体来说,《庄子哲学的精神》是陈赟教授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于传统论述当中,开拓出不同于以往的角度,深有反思辩证之思考,饶富沉淀激情、辨析新意之用心。其立意虽然新颖,却有根柢。可以预期,该书亦将是日后研究《庄子》的重要参考材料,是值得与之对话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