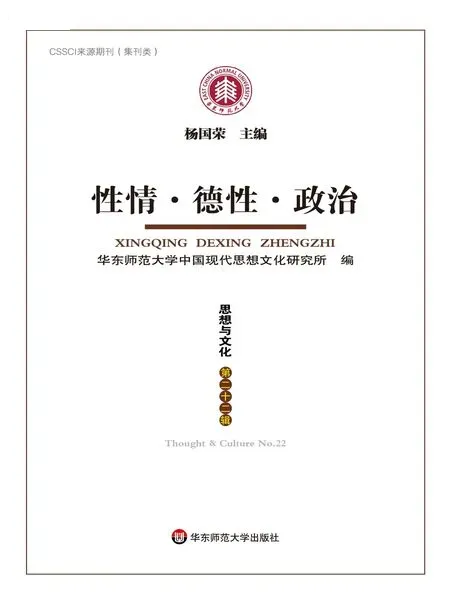政治的词源学
——从西方古典语言语源学来看*
2019-01-14
●
一、 πολι et civitas :古希腊人和拉丁人的城邦







二、 persona et auctoritas :人格与权威
城邦或国家的人格起源于哪里呢?柏拉图先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将城邦和个人都理解为肉体(欲望)、精神(激情)和心灵(理性)的统一体,实际上已经把城邦视作一个唯一的人格。只是,柏拉图仅仅停留在哲学层面,或者说形而上学的层面,这个城邦的形而上学就是正义,正义本身是一个完美的概念,正义下面的三种德性(智慧、勇敢和节制)同样也是完美的概念。正因为要符合这个完美的概念,统治城邦的哲学王、城邦卫士的共产共妻、欺骗平民的真实谎言,都是因概念的完美而来的理性必然性。尽管柏拉图似乎是从各个阶层的分工合作来说明城邦的起源,但最后实际上又把完美的概念视作城邦的起源,因为都是善的理念的模仿。

Persona到了古典时代开始意指人(homo)。与现在流行的作为法律主体的用法不同,persona一开始指的是法律客体或对象。在法学家盖尤斯(Gaius)时期,persona这个词所指的人范围比较广阔,甚至也可以指一个奴隶,因其在法学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作物,故而是法律的客体而非主体。这种理解的正当性就在于,奴隶也有购买法律主体资格的可能性。法学认为奴隶是潜在的法律主体,并且同时将其看作在所谓人格法(ius personarum)范围内的真正的、恰当的法律主体。Persona与homo不同的地方在于,persona是一个法学概念,一个人(homo)如果进入了法学范围,那么就总是以某种persona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每个人在所处的家庭、社会和国家当中都有其地位或状态(status)。
在用面具来指代人格之前,罗马法还用另一个术语来表达相同的含义,即caput(头、首)。Caput源于动词capio(抓),而不是像有些语法学家们说的,用头来代替人,是因为人使用头脑思考;因为古人并不见得明白这一点。之所以“头”用“抓到”这个比喻来指代,是因为人若看到某个人的头和面目,就抓到某个人的特征了。故而caput被视作人的主要特征,这是以部分来指代整体。无论自由人或奴隶,他们都有头,故而都有人格,指的就是在某一集体(无论家庭还是城邦)中的地位(status)。Caput转而又比喻任何事物的主要部分或本质、实质、精华,从而人格就是每个因其头首而相互区别的个体在社会关系当中的本质。这个本质就体现在其地位或状态(status)上面。单单直接去看persona,似乎难以看清其本质所在。在人格减等(capitis deminutio)这个法学术语中,我们可以看到persona到底包含些什么。
所谓人格减等,指的是自由人的某些法律资格的丧失;这些资格可以表现为自由权、市民籍或者某种家庭地位。罗马人甚至把人格减等等同于“市民法上的死亡”,并且根据所丧失的资格的重要程度将其区分为最大人格减等(capitis deminutio maxima)、中等人格减等(capitis deminutio media)和最小人格减等(capitis deminutio minima)。我们从最大人格减等就可以看出,被剥夺的部分就是人格的主要部分,即市民籍和自由权,以及其他附属权利。简而言之,人格就是自由公民。正因为自由公民就是人格的本质,所以后来的法学家就认为,奴隶没有人格(personam non habent),因为他们既没有市民籍,也没有自由权。现在可以看出,人格就是完整的公民法权的统一体。它是单独的、单数的,因为它是从头来区分的,头就代表着个体,人格是个体的人格。这些面具就是各项公民法权,故而人格就是法权,法权就是人在社会和国家中的面具。这些法权应该是完整的,要不然就意味着人格的残缺。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家庭、社会、国家等都是一个大的舞台,每个个体都在其中戴着面具,演着自己的角色,扮演着自己的形象;每个个体因其角色或形象而拥有自己的权威,这个权威就体现在其所拥有的三项法权当中,这三项法权又具体体现在其所拥有的物质财产、精神财产和自由意志,及其因而形成的种种社会关系当中。正如维柯所说 :“罗马人在法学中考察的不是人(homines),而是人格(personas);他们曾把人格说成是capita,即‘头’;任何一个罗马公民都有三种capita,即三种人格 :自由权、公民权和家族权;如果一个人没有人格,那么就引入他人的人格(alterius personam),家父的家子(filium familias patris),主人的奴隶(servum domini)等,就好像罗马法看起来就是诗歌,一种罗马戏剧。”[注]Giambattista Vico, Opere giuridiche, il diritto universal, a cura di Paolo Cristofolini, Sansoni Editore, Firenze, 1974, p.541。这就是罗马法中人格法的源泉。
继而人们还可以看出,既然人格只是个面具,是人们合法的虚构,最后它就可以独立于每个个体而存在。每个个体可以脱下面具,成为一个没有法权的动物或工具;也可以恢复自由,重新戴上这些面具进入社会,从而具有种种地位。这样就可以拟制(fingo)种种人格,或者说,将个体的种种形式的集合视作具有一个独立人格的法人单位,于是就出现了所谓“法人”(persona giuridica)。法人作为非个人性的、非物质性的,也就是说精神性的法律主体这个概念,实际上并不是由罗马法学家构思出来的,而是由教会法学家们构思出来的。不过,虽然罗马法学家并未构思出这个概念,但他们早在古典时期就已经承认了那些联合组织的法律主体地位,这些组织个个都被承认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的人格跟其成员的个体人格大相径庭。在这些组织中,包括罗马奎利蒂人民(populus Romanus Quiritium),包括自治市(municipium)和殖民地(coloniae),包括社团(collegia)和团体(sodalitas),慈善团体(piae causae),甚至还包括hereditas iacens(尚未继承的遗产)。这些创制中最伟大的虚构当属populus Romanus Quiritium,而且这个创制早在前古典时代就已经得到了承认。不过,最能显示这种人格与人身之分离的当属hereditas iacens,“尚未继承的遗产”,指的是等待继承人予以取得的或者尚未被任何继承人所接受的遗产。这种遗产属于无主物(res nullius),既非死者的,亦非未来的继承人的。尽管如此,罗马人仍然为之拟制或者虚构一个独立的人格,使它被视作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也就是说,它可以独立地享受有关的权利,并且承担有关的义务。这种人格拟制方式甚至可以为国有资产的人格拟制提供合法性,不过这并非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此处更关心的是罗马奎利蒂人民这个国家人格的拟制。在罗马法中,罗马奎利蒂人民被理解为一个具有清楚的政治意涵的抽象实体,因其至高无上性而不仅与个别市民区别开来,而且与附属的公共机构区分开来。早在前古典时代,它就被承认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法律主体,因此又象征着一种与其成员相互区别的个体单位。由于其公共性质,它属于公法范畴,区别于私法领域的市民关系。因为它取得了这样的人格,故而也拥有与个体公民类似的权威,亦即有其自己的所有权、自由权和保卫权;或者不如说,它因为拥有了类似的权威,故而也披上了人格的面具。国家人格虽是公共人格,但作为人格,它仍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实体。模仿个人(这里实际上是指家父)所有权,国家也有其财产,这就是aerarium populi Romani,“罗马人民财库”,也就是国库。到了帝国时期,罗马人民财库改称为fiscus Caesaris。Aerarium这个词源自铜币(aes),实际上意指币制的统一,其人格归属则在罗马人民,货币度量、发行以及赋税都属于罗马人民。罗马人民作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这个概念清楚显示了这个人格的虚拟本性。帝国时期改称为fiscus Caesaris,“凯撒财库”,仿佛是凯撒个人的财产;fiscus原意是篮子,而后衍生为柜子,最后比喻财库。正因此,在后古典时期,国家主权的人格就与专制君主的人格混淆起来了,因为所有国家大权都越来越集中到君主手中。如此一来,所谓罗马人民的主权就不再被认为是一个法人,而是被剥夺了独立自主的人格性。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即便是君主专制,罗马人民主权的人格并未消失,只是跟君主个人的人格合而为一罢了。这个证据就在于,凯撒财库完全不同于凯撒私人的家产,因为君主财库或者后来的皇帝财库虽然属于君主或皇帝,但在君主或皇帝死后,并不转给其后裔继承人,而是转给登基上位的新君主。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就如同“尚未继承的遗产”中的人格拟制一样,君主财库仍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人格的财产,是国家人格对其拥有所有权,即便是君主、皇帝,也只是这个公共人格的代表。
除了国库,法律、政府、军队、警察等公共制度和机构都归国家所有,是国家的proprietas。这种所有权主要体现为制度,in-stitutio,仿佛是从人民(populus)内部(in-)创建、确立起来的(statuo),因为取得了如此这般的独立自主的人格,故而稳固不变地立(sto)于世间,从而获得了其地位(status)。这种恒定的(consto)、不随人事变迁的状态(status)就是城邦或国家(civitas)的本性,所以国家在其政治地位和建构上也被称为status。实际上,即便是国家之内的城市,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的。日耳曼语作为比较古老的语言,保存了很多原始思想的遗迹。德语中的“城市”(stadt)和“国家”(staat)都跟拉丁语status具有相同的词根sto,正如拉丁语civitas既是指城市,又是国家,无论是画圈(cio)还是坐地(sto),都表明了其地位和状态;在德语中status是状态、情况、地位,而statut则是规则、章程、法规。
自然的个体作为法律主体是个人的,罗马法有云,特权是个人的东西,也就随着个人的消亡而消亡(Privilegium personale est et cum persona extinguitur)。[注]教皇博尼费斯于1298年整理出版了88条法律名言或准则,这是第7条,原文是 :“Privilegium personale personam sequitur et extinguitur cum persona.”Boniface VIII, De Regulis Iuris, No. 7, 1298.但这句话可以一般地来说,人格的东西就随着人格的消亡而消亡(quod personale est et cum persona extinguitur)。反过来,quod personale est et cum persona nascitur,即人格的东西随着人格的产生而产生。上述词源学阐释说明了persona从戏剧面具到个人人格再到集体人格的演变,但这个过程并非人格这个事物本身的产生和演变,因为persona只不过是讲了一个关于这个事物的寓言故事。这个故事背后的真相则是,政治社会实际上就是人格社会,政治演变无非就是人格的演变。一般而言,当出现独立自主的国家人格时,一个完整的政治社会也就出现了,不同的权威因其不同的所有权、自由权和保卫权在社会中相互关联,相互竞争。政治学(无论政治科学还是政治哲学)无非就是对于种种政治人格及其权威的研究,而政治实践不过是人类个体或集体创造、参与种种人格的一幕幕戏剧。
三、 ordo et respublica :秩序与国家
如果我们从纷繁芜杂的历史现象当中来看政治,那就眼花缭乱,不知秩序为何物。但是如果从人格角度来看,秩序就跃然而出了。因为一切法律实体,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社团、国家,都是具有自己特有人格的政治单位,进而,一切物(res)也都被人格化,故而人格社会转而涵盖了物的社会,或者更不如说,物作为自然的物在人格社会中成了社会的物。自然物有其自然秩序,但这种自然秩序(在生物意义上也包括人的自然秩序)是社会秩序的质料,政治秩序则可以作用于质料的形式,给予自然秩序以新的秩序。自然秩序是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围,政治秩序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


但我们这里关心的是政治世界中的物的秩序和人的秩序。自然世界中的物的秩序是从几何来理解的,因为直线是最简单最准确的;也可以用代数来理解,因为统一于“一”是最明确、最清楚的。政治世界中的物的秩序可以归结为人的秩序,也就是人格秩序。因为一切物都从有用与否来理解,有益、有用、满足人类需要的就是bonum(利益),就是善,法(ius)就是按照人格对利益的正当分配。这种分配遵循两种秩序 :在相互平等的人格之间,利益的沟通要采取交换律,也就是互通有无,进行代数的等价交换;在不平等的人格之间,利益的沟通则是自上而下的分配率,采取几何倍增方式。[注]Giambattista Vico, Opere giuridiche, il diritto universale, a cura di Paolo Cristofolini, Sansoni Editore, Firenze, 1974, p.75, p.7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法律主体的人格享有其独有的所有权、自由权和保卫权,亦即享有属于自己的不可侵犯的权威。因而,对于每个法律主体来说,他的权威,也就是他的所有权、自由权和保卫权都是他的res(物),但这种物不同于其人身和财物,因为它并非由肉体或广延等可见可触物构成,但却是物之为物的法律基础,或者不如说人格基础。同理,无论个人人格还是集体人格,都是独立自主的人格,都有同样的三种权利,个人人格和集体人格都同样可以支配种种有形物和无形物。这种人格对于物的支配就是政治社会中物的秩序,而人格与人格之间的等级关系(包括平等与不平等)就是政治社会中人的秩序,这两种秩序合起来就是政治社会的秩序。
但如果不是在人与人共存的社会中,人格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尽管哲学家们仍然可以假设一种没有社会的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自私的自由的个体。[注]霍布斯 :《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7页。很明显,罗马人是在戏剧面具所代表的角色中来体会人格的,剧场就是众多角色在其中演出的社会。只要是在社会中,最初是家庭,然后部落,然后城邦,然后国家,最后乃至人类共同体,人都处于种种角色当中,同时具有种种人格。所有的人都可以来了又走了,事物和事件都可以千变万化,但人格却不会变化,只不过是有些人格可能不再有人表演了,终止了,但在历史的某个时段,可能又有人去扮演那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