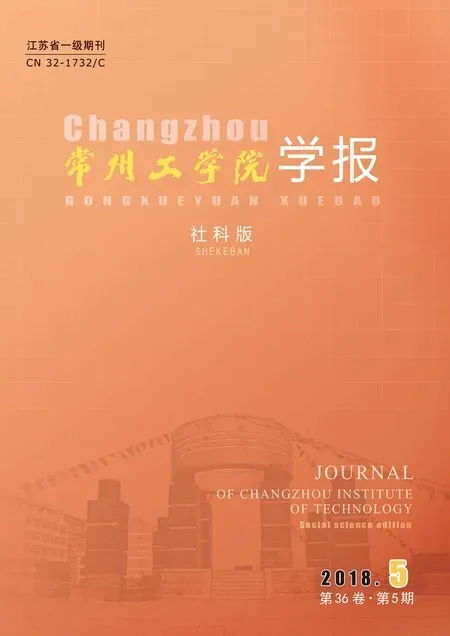论苏青小说的都市日常叙事
——以《两条鱼》为个案分析
2018-03-29钱亚玲
钱亚玲
(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
梳理中国女作家创作,活跃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的苏青,向来被归于散文家之列。苏青的文学之途始于散文,散文篇目远远超过她的小说,1935年她发表散文处女作《生男与育女》,距离1943年3月首篇小说《胸前的秘密》问世有9年之隔,这期间她倾情专事散文创作,完成了后来结集为《浣锦集》的诸多篇什。苏青散文的乡村风俗叙述、市民生活观照、女性心声的坦陈和言语的直白率性,为她赢得了众多读者,也奠定了其散文的文学史地位。当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面世后,读者将它与苏青散文并置比较便是情理中事,而身为同行兼闺蜜的张爱玲的评点代表了某种专业眼光:“我认为《结婚十年》比《浣锦集》要差一点。”①很难确定“张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苏青小说的阅读,但时至今日,一个普遍的共识仍是,苏青的小说不及其散文。
综观苏青的文字世界,笔者认为,其价值不啻于散文的直陈市民日常生活、现代母性妻性的撕扯和职业女子内外受夹的困境,苏青借助都市外来者的生存体验、个体敏锐的直觉和长年积淀的文学素养,于小说的舞台闪现过一片精彩。近十载散文写作,为苏青日后小说创作既做了题材上的储备,也做了一定技艺的训练,故苏青屈指可数的小说创作更能反映其艺术功力和思想深度。苏青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艺术地呈现都会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女性涉世”,更在于其对战时都市“底层”市民的深入体察。以短篇小说《两条鱼》为代表的都市“底层”叙事,既印证了苏青于小说疆域的掘拓,彰显出其未被读者领略的小说技巧,反映了苏青小说深广的思想意涵,更为现代女性写作如何叙述城市生活提供了经验与方法上的诸多启悟。
一、“底层”观照的叙述策略
与此前散文和日后《结婚十年》《蛾》《九重锦》《续结婚十年》《歧途佳人》等或多或少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相比,苏青1943年4月于《风雨谈》杂志发表的《两条鱼》是唯一不关涉家庭和婚恋、最少苏青个人印记的一个作品,讲述了一个由外乡人、娘姨、厨子司务、鱼贩、巡捕和瘪三等贫民、“小人物”“混搭”而成的上海“底层”故事:一个上海本地鱼贩,用新鲜小黄鱼做招牌,意欲卖掉做过手脚且已腐烂的大黄鱼;一个貌似外乡人的中年妇人,为给女儿买条鱼和鱼贩讨价还价;鱼贩和中年妇人发生激烈争吵,妇人的菜篮被扯坏;妇人为讨说法奔走呼告,中外巡捕先后处理纠纷;妇人到手的两条鱼遭抢,路人、鱼贩和中国巡捕因妇人的“倒霉”而开心不已。文本聚焦于都会的“底层”日常,于叙述策略上精心营运,无论是故事结构还是人物形象塑造,《两条鱼》堪称苏青短篇佳作。
(1)颇有意味的“菜场”场景设置。较之张爱玲钟情于“电影院”“剧场”“电车”等带有小资情调、适合浪漫邂逅的公共场地,苏青更偏爱“菜(市)场”“马路”“弄堂”等体现平民色彩、更具开放性的流动空间,适值战时沦陷,充溢、来往其间者多为“平民”中“贫民”。《两条鱼》选取“菜场”为故事舞台,投视于“黄鱼”交易情境,借助鱼市买卖织就了一个关联都市底层、各路看客和外来洋人的沪上“天桥”世界。在此,“菜场”成为透视上海都会的别一个“窗口”,透过它,一个着实热闹、传奇迭出、地域风情尽现的海派底层市民世界尽收眼底:柴米油盐垒就的一日三餐,混合着鱼腥肉臊、汗水唾沫,贯穿着粗野放肆的叫卖和赤膊上阵的论理;战时沦陷招致日常生活物资匮乏,广大底层市民苟延残喘。小说借“菜场”这一独特视镜,立体呈现了现代殖民统治下东方都会的街头别景,为读者重建一种有关上海都会的“文学想象”,上海不止是新感觉派笔下的流光溢彩与纸醉金迷,也非只有左翼笔下破败潮湿的“地狱”与困死其中的“机器的奴隶”,这个现代都市的“芯子”仍是普通、底层的市民及其柴米油盐。
(2)“外视角”为主的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视角,即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其变换会造成不同的故事风貌,带来不同的阅读感受。法国的兹韦坦·托多洛夫将叙述视角分为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三种形态,所谓“外视角”,指叙述者置身于事件进程之外向读者叙述人物的行为和语言,无法解释和说明人物言行的原因。“外视角”叙述的优点是带来叙述语言的戏剧性,造成叙事的悬念。《两条鱼》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主要运用“外视角”并借助一定的“全知视角”讲述整个故事。前半段是中年妇人和“麻脸”鱼贩之间的“价格战”,主要叙述人物之间你来我往的对答和具体的动作,呈现双方的强买强卖,暗示“中年妇人”的“外来者”身份、经济的拮据及难言的苦衷、幼女的纯真无知、鱼贩的奸诈,而鱼贩的不良居心、狡黠贪利、流氓无赖相,中年妇人的节俭、胆小怯弱又不失机警等,于对话语言和人物动作中得到鲜活展露。后半段的“官司战”则主要在“眼镜”巡捕、“麻脸”鱼贩和中年妇人三者间展开,文本运用类似电影的“跟拍”和“晃镜头”,动态记录了中年妇人奔走哭嚷、讨公道的过程与场景,小说除进一步运用人物自身语言和动作,同时还结合人物的少量心理活动,凸显“眼镜”巡捕、鱼贩和中年妇人三者间尖锐的利害关系,而人物形象随着“镜头”的“切换”得到更完满的呈现,让读者进一步看到中年妇人愤怒至极的疯狂决绝,张狂的“麻脸”于权力前的乞怜摇尾,“眼镜”的见利忘义与奴颜媚骨,洋巡捕的颐指气使与飞扬跋扈。最后,经由洋巡捕的“直觉”“裁定”,中年妇人意外买到“两条鱼”,风波平息。但故事没完,文本再次运用“外视角”,借街上“看客”之口,叙述中年妇人的“两条鱼”光天化日之下遭瘪三抢夺,这出乎意料的收场,俨然构成都会日常“传奇”的表征,凸显了都市现世的混乱。借助“看客”的“转述”,既营造了一种戏剧性场景,更赋予故事结局的“未定性”和“不知性”,带给读者无尽的遐想。《两条鱼》自由灵活、极富悬念的“外视角”,强化了上海都会的“传奇”色彩,无疑也暗合了作家苏青作为都市外来者的身份和眼光。
(3)情节结构上的“看/被看”模式。从苏青小说《歧途佳人》的男主人公提及鲁迅笔下“九斤老太”这一人物可断言,苏青熟识鲁迅的小说世界,《两条鱼》于情节结构上深受鲁迅小说的影响,明显存有三重递进式“看/被看”关系:“瞧热闹”的围观者与“麻脸”“中年妇人”“眼镜”等主要当事人构成了底层间实有的“看”与“被看”;自始至终俯视“菜场”的“太阳”(实为场外见证者)与“菜场”各路角色构成了具有宿命意味的“看”与“被看”;“菜场”外的叙述者(隐性作者)与底层人物之间构成了充满批判意味的“看”与“被看”。在多重“看/被看”的关系构置中,呈示国民无聊、麻木、冷漠的“看客”性格,呈现商业文明浸染下现代都市利己主义的处事态度与明哲保身的个体生存哲学。
二、国民性与海派市民性格反思
《两条鱼》叙事策略呈现出了上文所述特征,由此而致小说意涵丰实,于苏青其他文字也不曾多见。
首先,《两条鱼》的“菜市”叙事,鲜活地呈现了沪上日常生活的别样景致,使读者获得阅读审美的快感,也意外获取一种地域文化的认知。上文论及,小说的视点直抵现代都市最日常、最直观体现城市“市”之“城”本质的地带——菜(市)场,这固然与作家个体经验有关,也体现出苏青的匠心独运。作为生活资料的交易场,菜(市)场是现代社区保障市民日常生活的一种基础设施,更是一座城市最真实的文化名片,城市的地域风貌、发展水平、文化习俗、市民饮食习惯乃至素养皆可通过“菜(市)场”这一特定区域汇流而出,“菜(市)场”可谓天然的地理历史博物馆和人像展览馆,也是故事的生发地。种种俗白的叫卖,遍地的大小黄鱼,鱼肉腥味混杂着国语、外语、软糯的吴语和其他各地方言,这是《两条鱼》呈示的海派“菜市”景观,折射出近代以来半殖民化上海多元杂会、开放流动、商业铜味气息弥散等多重城市性格。娘姨、厨子司务、中年妇人、“眼镜”巡捕等在黄鱼摊位前的踯躅流连、挑肥拣瘦,甚至忍辱受屈,又让我们领略到沪上市民对“黄鱼”的情有独钟。这是基于天然的海岸地理而生成的地域饮食习惯,沿海地带的居民对鱼类普遍有着偏好,“黄鱼”是绝大多数海派市民的日常最爱,故人们在黄鱼摊前流连忘返,与其说是对一种食物的垂涎,不如说是对历史沿袭下来的生活方式的执念,于沦陷区国民更是一种民族认同心理和情感的慰藉。《两条鱼》折射出海派日常生活风貌和市民饮食趣味,蓄含着苏青文字惯有的社会民俗学价值。
其次,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不满现状与追求独立自主构成苏青现实的人生,将现实经验带入文学的世界,早期便是散溢于散文中的女性的种种负气——叹气、怨气与戾气,对女性苦难的叙述折射出苏青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热切的人生担当。当营生的卖文遭逢战争与沦陷,作家的窘迫可想而知,此时苏青的文字“没有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事实,但字里行间却可以找到由于日寇侵略造成民族苦难的描写”②。上海文化人谢蔚明先生曾替蒙冤的苏青作如是辩,《两条鱼》可谓是一个最好的注脚。只是随着思想和文字技艺的成熟,苏青对苦难的叙述和对现实的批判不再作表层的浮游,也不再作主观琐细的絮叨,而是冷眼旁观,用忠实的文字和近乎戏谑的笔调,细致入微地再现都市底层的生存“保卫战”,引发人们对现实的深思。随之而来的困惑是,作为沪上家常的“黄鱼”何以成了奇缺的美味?何以就成了普通市民的奢想?答案存于故事自身——外族入侵造成的生活物资稀缺、无良商贩的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中外强权势力的相互勾结和巧取豪夺。《两条鱼》生动而宏阔地展示了上海底层市民的生活样态,艺术地揭示了造成底层苦况的深广的社会因由。对外在社会的关注、对现实的冷嘲热讽以及叙述姿态的淡定含蓄,赋予苏青小说深沉的批判力度,也见证了苏青文字艺术的日臻完善。
较之上述两个方面,笔者认为《两条鱼》透射的对国民性的反思和对海派市民文化性格的批判尤为珍贵。张爱玲对近代以来海派市民性格如是总结:“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③换言之,传统乡土文化造就的畸形国民性,于非常时期非常地带因俘获了新的质素往往混合出更为复杂的精神面相,表现得更触目惊心,苏青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两条鱼》的风波跌宕,源自现代都市金钱驱动下“鱼贩”“良心”的丧失,起始于他的“瞒”与“骗”的初心,“烂了肚子”流出“腐臭黑水”的“大黄鱼”极其妥帖地隐喻了“黑心”的“鱼贩”。显然,在洋“巡捕”等象征现代殖民势力的胁迫和商业文明浸染下,海派市民在承袭传统文化造就的匪气、流氓气、无赖气与奴隶气之外,又添加了市侩气和油滑气,苏青的高妙在于,她写出了这种种“凌人”之“盛气”,最终在洋人的“霸气”面前都“泄”了“气”。国民这种“疲软”的精神长相和苏青带有黑色幽默的表达,反映了苏青对海派市民性格的深度体察与难言的忧愤,引发我们对传统国民性和沦陷时期历史现状的再度深思。
三、现代女性写作如何叙述城市生活
与散文“牵手”多年后,苏青意兴于小说并将眼光投注于“菜市”和底层,映照出苏青试图走出耽溺其中的“她”世界,意欲将文学视界扩展而至身外广大的社会,显示了她在文学体例和小说题材上的双重探索,而《两条鱼》所蕴含的社会批判和国民性反思、富有地域特色的底层群像、多变灵活的表现手段和简洁练达的叙述语言,综合见证了苏青这种双重尝试的成效——作为散文家的苏青不仅有驾驭小说的功力,且能把短篇做得很纯粹很精致。苏青创作路途上的这种探索,不仅赋予创作主体某种特别的意义,也演绎出“现代女性写作如何叙述城市生活”这一深层而现实的问题。
城市(生活)与女性(写作)之间关系诸多问题,曾为很多学人探涉,较为一致的观点有:是城市给了女性自由的生存空间;城市文化空间的包容性和公平性,使女性获得自由抒发的写作权利;女作家天然属于城市。苏青的文学之路是其中最好的诠释,城市召唤着苏青一步步走出宁波浣锦村,上海都市文化让苏青最后走出家庭走上文坛。回望20世纪初以来的女性写作实践,由早期抒写追求恋爱婚姻自由和性的苦闷、30~40年代关注外在的社会解放,到当代强调男女“性别差异”,女性写作路向的每一次转变,都受制于生活其间的城市文化,反过来女性写作又融为城市的文化元素,成为城市文化的又一表征,这是就女性写作的整体状况而论的。事实上,真正的写作历来都是写作者个体的行为,每个作家创作的路途千差万别。换言之,城市为女性写作提供了一定自由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在此基础上,一部好作品的诞生,依仗作家个体生活历练的沉淀、对人生的体悟反省和写作技艺的孜孜以求等多重因素的整合。苏青从散文到小说的跨界探路,给现代女性写作至少提供了两点有益的启示。
第一,女性写作要重视有限的城市生活经验,更要重视如何将现实经验植入文学世界成为创作的“专属物”,从而生成自我的创作“名片”。城市化进程固然给世界女性带来了自由的生存空间,不可否认,基于自然(生理)性别的差异和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现代中国女性的生活空间较之男性依然有限,女性视界和个体经验依旧不如男性开阔和丰富。苏青早期散文大多感喟女性之苦、女性之累与女性之惑,感叹都市柴米油盐的精贵,可谓一部“女性市民”的“苦经”,折射出步入都市后苏青生活空间和视界的狭窄。显然,作家苏青又极其珍视这些单调的城市居家经验,反复的絮叨强化了读者有关上海都市生活的印象,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阅读审美的疲惫。直到小说《两条鱼》的出现,才又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依旧写上海,写都市的日常,用“菜场”替换“舞场”,用“小人物”替代女主角的“她”,用潜心旁观替换往日的指手画脚和强行“入场”,苏青用全新的叙事策略构建了一个“菜场”世界,也给现代文学提供了一幅完全不同北地的沪上市民生活图景,“菜(市)场”由此成为苏青有关上海城市叙述的一张“名片”,如同北京的“胡同”是老舍文字世界的“专属物”。文学创作离不开直觉和激情,面对浮华、变动不居的都市现实,似乎更需要作家隔岸观火,潜心体悟,滤掉主观的情绪,借助运思巧构,完成一次理想的文学旅程。这些于以直觉和感性见长的女性写作者尤其不可或缺。
第二,有关城市的叙事,要刻画出富有鲜明个性和人性深度的形象。文学以展现人性的复杂性为其终极目的,城市因其生活方式的异质性、多样性与开放性,把人性中过度的善与恶都展示出来,现代城市较乡村地带更有利于作家对人性的抒写。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伴随生存自由的获取,直至上个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大多“发声”急切而忽视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度观照,普乏思想的深度和鲜活的人物,譬如20世纪初涌现的“问题小说”,因滞于突出“问题”短于人物形象塑造而为人诟病,即便是作为其中主力的冰心,此时的小说也乏善可陈。苏青前期散文和后来的一些自叙传长篇明显也有这一通病,除张扬女性立场、追求个性自由的女性“类型”外,人物多数面目模糊,性格单一,难见人物心理和精神生成史,谈不上人性的高度。短篇《两条鱼》俨然是个例外,国民性中普存的“阿Q”气和沪上特有的市侩气、精明完美地统一于鱼贩、厨子、巡捕等众生中,浓郁的地域气息赋予人物格外鲜活的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记,再度引发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城市地域文化的反省。人作为文化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产物,如何通过对人物的捕捉和对人性的挖掘达到对文化的反思,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作家理应坚守的心理暗示,而对于长期囿于传统文化泥沼的现代女作家及其创作而言,正视这样的问题或许更有意义,其作品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也将越发地久远。
四、结语
承受着政治与文化的高压,面临“言”与“不言”的两难,沦陷的都市生活虽苦,但日子总得要过,忍辱负重抑或风风火火,皆成为人类历史续延的真迹,也是古往今来的一种永恒,故《两条鱼》的“底层日常”切入,固然展示了散文家苏青于小说写作上的超凡技能,更映射出她对人类生存历史的一种真切的把握和素朴的体悟。回望20世纪新文学的历程,不难看到,苏青正是以《两条鱼》这样的短制佳构,参与到20世纪40年代上海都市日常叙事的整体性建构中,因而,无论于苏青自身的文学活动,还是于现代文学史,以《两条鱼》为代表的苏青都市日常叙事都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
注释:
①张爱玲:《我看苏青》,见《苏青文集》(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460页。
②蔚明:《一个女作家的沉浮》,见《苏青文集》(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491页。
③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见《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