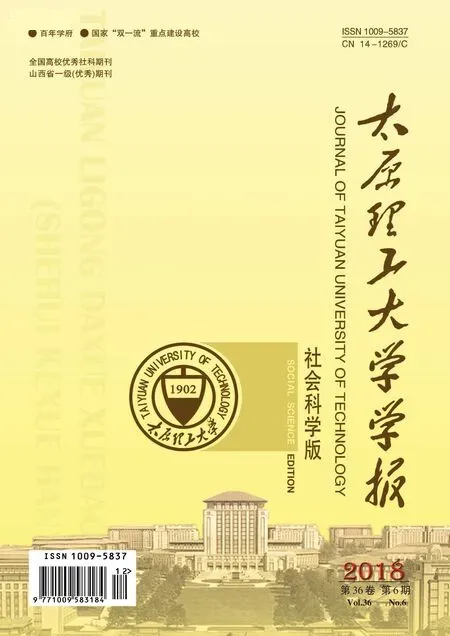试论清代京畿商人与灾荒救济
2018-01-24董志磊
张 燕,董志磊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所谓京畿一般代指京师与其附近所辖地区,清代京畿地区时称“直隶”,所辖范围涵盖今河北、天津及山东、内蒙古一小部分区域。清代京畿地区作为畿辅重地,由于地理上靠近政治行政中心,往往受到政治史、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关注。灾荒救济是清代京畿地区社会史关注的重要内容,以往学界对该问题的探究大多重视其救灾制度和行政力量等[注]主要研究如下池子华,李红英.晚清直隶灾荒及减灾措施的探讨[J].清史研究,2001(2);王彩红.清代康雍乾时期洪涝灾荒研究——以直隶地区为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s1);池子华,李红英.灾荒、社会变迁与流民——以19、20世纪之交的直隶为中心[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王洪兵.清代顺天府与京畿社会治理研究[D].南开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9:359-463;王洪兵,张松梅.清代京畿灾荒与秩序控制——以乾隆朝顺天府通州告赈案为例[J].齐鲁学刊,2011(2);王洪兵,张松梅.清代京畿灾荒与祛灾仪式探析[J].东岳论丛,2011(7);曹琳.明清直隶灾荒及救助制度述论[J].兰台世界,2015(36);毕静丽.清代直隶州县灾荒救助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7.,而对参与救灾的主体研究明显不足,忽视商人群体的参与。考察清代京畿灾荒救济中商人的参与活动,是对畿辅地区灾荒救济参与主体多元性的重新审视,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清代京畿地区商人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一、清代京畿地区主要的灾荒与救济体系
清代京畿地区拥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从地貌上看包括围场高原、丘陵、冲积平原等;海河、滦河作为两大主要河流流经此地,山岭、河谷交错其中,地势构造十分复杂。气候上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极易出现暴雨、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复杂多样的地形及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导致了清代京畿地区在历史上以干旱、洪涝、雹雨、地震为主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自然灾害中以水旱灾害为最,据统计 “仅海河流域从1368年至1948年的580年间,就有旱灾407次,涝灾383次,平均每1.4年发生一次旱灾,1.5年发生一次涝灾”[1]。频繁的水旱灾害极易引发饥荒,以地处京畿西南太行山麓平原的邯郸为例,邯郸县“道光十六年大旱。十七年二月始雨,夏无麦。六月大旱。十八年夏无麦,秋禾歉收”,导致邯郸县连年“西乡荒旱尤甚,人有流离饿死者”[2];此外还有雹灾、霜灾、雨灾、瘟疫、蝗蝻灾害等,这使得京畿地区不得不应对复杂多样的灾荒。
京畿地区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频发的自然灾害极易引起饥荒、动乱,也直接威胁京师的安全。这不得不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在京畿地区各个州县灾荒的赈济上,形成了颇为完备的赈恤体系,具有较为完备的灾荒救济运作程序,灾荒发生后各受灾州县上疏请赈,经由各级官员层层上报,经勘查核准后放赈[3];而在灾后救济内容上,以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畿南旱灾为例,直隶总督方观承总结天下赈饥成法以备参考,其中包括了赈钱、赈米、平籴、安流民、贷牛种、节省运耗、广种宿麦、召兴工作、赎农器、劝富民捐输等几个方面[4],基本涵盖京畿赈饥的主要内容。在灾荒赈恤的主体上,国家权力与地方民间力量相互作用;以官府为主导,以地方官员、乡绅富户、商人等民间力量共同参与为特点。政府作为赈恤主体,制定政策方针,而绅商民间力量则响应地方号召,广泛参与京畿地区的灾荒救济。
二、京畿商人参与灾荒救济的方式与特征
清代京畿地区频发的自然灾害,往往引起该地多个州县连年的灾荒,极易引发社会秩序混乱。由于其地理位置上靠近政治中心,畿辅重地的灾荒往往受到政府的极大重视,故而形成了以地方政府官员为主导的相对完善的灾荒救助体系,参与灾荒救济的主体中,除地方行政官员外,士绅、乡绅、商人群体襄助也不可忽视,使得其灾荒救助主体呈现多元性的特点。而清代京畿地区的商人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参与到灾荒的救济当中来,其救助方式主要有钱财募捐、赈粮施粥、参与赈恤机构建设等方面。
钱财赈济。钱银捐赠是商人参与灾荒救济最为直接的方式之一,灾荒发生后,地方政府发放一定数额的赈济银两,当地官员、富户、富商往往率先出资抚恤。清末时局动荡,政府赈济派发钱银数量不足,而商人钱银的募集和捐赠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灾荒救济中政府赈济的缺额。霸县商人王化南,于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设钱肆于独流镇”,独流镇发生灾荒后,“政府派员施赈,所发官欵,约缺数百缗,饥民又嗷嗷待哺。该员拟暂假欵,赈后归还,本镇绅商恐无把握,均莫之应”,面对这种情况,王化南“独慨然出任借欵”[5]资助地方政府放赈。在捐赠的数量上也十分可观,沧县商人卫正身,“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旱,其杰捐万金,煮粥以赈,邻民闻之,麕至全活一万六千余人”[6],捐赠数额巨大,后来还得到直隶巡抚于成龙的旌奖。另外京畿商人的救助参与亦延及临近省份灾荒,光绪庚寅(公元1890年)年,临近河北的山东“山左大水,津人捐输者众,而付托难其人”,在天津经营二十余年起家的商人金汝琪“既出资,复身任之,跋涉三千里艰危弗恤”[7],他不仅自己出资捐输,更是亲自运送山东抚恤。京畿商人在灾荒救济中的钱银捐赠,弥补了地方政府赈济的缺额,协助地方政府放赈,也是除政府赈银、地方官员捐俸及乡绅捐赠之外灾荒救济钱款的另一个主要来源。
赈粮与施粥。清代京畿地区灾荒的救济内容以赈饥为主,粮食捐赠和设置粥厂施粥是其直接参与灾荒救助的方式。频发的自然灾害极易引发严重的饥荒,粮食是救济中的主要赈灾物资。虽然京畿地区在仓储和备荒上有较为完善的机制,但由于粮食的需求量十分巨大,仅凭地方政府的仓储是不够的。杨继盛《上少师徐少湖翁救荒书》中记载了灾荒时期京师之地“城中饿殍死亡满道,人人惊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师之民,各有身役常业,何以顿至于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因为“各处司民牧者无救荒之心,而京师有舍米、舍饭、减价卖米之惠,故皆闻风而来,当其事者又不肯尽心,鲜有实惠,故每冻饿以至于死”[8]。绅商、富民在赈饥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富商王镇在道光十二年(公民1831年)旱灾,“镇出粟赈饥,不计数,不责偿还”[9];营商海店的任邱县商人边大发“康熙间岁饥,在海店设厂施粥三月,活人无算”,“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大水施谷五十石煮粥济与乡里,赖以生存者甚众”[10]。清代京畿地区富商、绅商面对饥荒大规模捐赠粮谷、棉衣,广泛设置粥厂施粥,与地方政府协作,极大地推动了清代京畿的灾荒赈济的开展。
参与赈恤机构的建设。除了捐资、赈粮、施粥等直接参与外,商人们亦参与到地方官府灾荒赈恤机构的建设和管理中。清代京畿地区赈恤机构主要有育婴堂、养济院、暖厂、粥厂、普济堂、功徳林,以及各地士绅创办的善堂等,如光绪四年(公元1908年)荣禄在《遵旨会议疏》中有:“京师地面向有普济堂、功徳林留养穷民,及五城官饭厂,随处赈济。近又迭荷皇仁,添设六门、四镇等处粥厂,其资善堂、崇善堂、百善堂等暖厂,及朝阳阁长春寺等粥厂,亦均蒙恩赏米石,俾资接济。此外,民捐粥尚不下二十余处,小民赖以全活者其众”[11]。可见畿辅之地赈恤机构形式多样,官民协作较为完善。虽然此类机构多系官办,但其建设往往也得到商人的捐赠。清末天津从事盐业的绅商严克宽“以才望推为总商”,在任总商期间,“若育婴堂、施馍厂、牛痘局之属,其费取给于芦纲者,向以总商董其役,克宽事必躬亲不辞,劳怨成效”。盐行对当地育婴堂、施饝厂、牛痘局之类机构的捐赠,都由大盐商严克宽负责管理。同时,他们还大力支持地方慈善活动,“凡官绅所兴举,輒以相属,克宽亦视为义所当然,未尝推诿”。光绪初年爆发饥荒,“畿南饥民就食兹邑,克宽分任芥园粥厂,尝以分棚防火,与主者意见,鉏铻力争”[12]。因粥厂防火事宜还与主事者据理力争,作为盐行总商,对当地赈恤机构的建设做出很大贡献。
清代京畿商人除了钱财募捐、赈粮施粥、参与赈恤机构建设,还施药治病、助死者入殓等,作为地方民间赈济力量,他们联合地方绅富,协助地方政府。京畿商人参与灾荒救济的行为体现了明显的主动性特征,以官商、封建大地主商人或富商为主,多为财力雄厚的巨商大贾。商人们自发参与到灾荒的救济中来,虽然有受到地方政府劝解呼吁的影响,但往往是非强制性和非制度性的,他们依靠自身财富和乡间的声望奔走倡捐,主动捐赠大批物资钱财,协助地方政府赈恤百姓,以身作则,引领更多地方绅富主动参与到灾荒的赈济中来,对抚恤灾民给予强力的支持。
三、京畿商人参与灾荒救济的动因分析
作为京畿灾荒救助的主体之一,京畿商人在赈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明清商品经济大发展的环境下,京畿地区商人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群体组成多为外籍客商的复杂性,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但京畿地区良好的消费环境和商贸往来,使天下客商云集此处,由于靠近政治中心,其在经营文化上兼容并包,并广泛参与到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当中。考察清代京畿商人参与灾荒救济的动因,不仅仅包括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有其对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追求,也是商人群体本身的责任使然。
(一)社会影响
京畿地区作为清代畿辅重地,其社会秩序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京城的安危,直隶地区灾荒频发,极易引发饥荒和动乱,危及社会秩序,清廷极为重视灾荒的赈恤工作,组织形成了一个颇为完整的灾荒救济和赈恤体系,而在这种救助体系中商人便作为民间力量参与到灾荒的救济中来。另外明清时期的商人阶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商人价值观、道德观念逐步形成[13],商人群体也成为影响地方民间社会的重要因素。在经济上,京畿地区是京师的中心商贸圈,本地商人、外籍客商云集,进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的京畿商人群体,清末时局动荡,清政府对地方控制趋于薄弱,商、绅作为地方精英,在清末社会秩序的维稳中发了重要作用。
(二)响应地方政府的劝谕
灾民等待官府赈济的同时,地方政府会颁布文告开展劝谕,号召地方绅衿富户助赈,京畿商人参与灾荒救济很大程度也是响应官府的劝谕。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旱灾波及二十七个州县,受灾面积巨大,《劝谕助赈示》中:“尔绅士商民人等,有谊笃桑梓者,或将裕存粮食减价平粜,或就本地穷民径行施给,或设厂煮粥使之就食,或捐备棉衣以御寒,事出乐施,情殷助赈,即呈报地方官听其自行经理。事竣之日,将用过银米数目申报督院核酌,从优旌奖与例符,即予题叙。又或邻省富户、侨寓士商有乐于捐助者亦一体呈报,转详核办”[4]。劝谕地方绅商参与赈恤工作,并标明不准地方官员过度干涉,核准后予以旌奖。而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旱灾赈饥工作普遍开展的同时,亦展开棉衣劝捐,以解灾民寒苦。《劝捐棉衣谕》中呼吁商人“即如当商,平时取利于穷格小户,今捐值十两八两之棉衣以恤灾困,宜无吝情”[4]。为响应劝谕,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旱灾中商人捐赠了大批棉衣,旱灾最重的十六个州县,均有商人捐赠棉衣的记载,部分州县甚至商人捐赠棉衣占据了多半,如河间县“职官捐棉衣一百件,绅士捐棉衣二百件,商捐棉衣七百八十件”[4],商人响应捐赠为灾民御寒做出了极大贡献。政府对赈恤中的商民参与不做过多干涉,并在劝谕中指明奖励办法,得到商人广泛响应。
(三)对提高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追求
京畿地区特殊的政治环境给一直处于“四民”末端的商人群体提供了提高社会地位、获取名望的机会。对京畿地区灾荒赈济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商人,政府也会不遗余力地给予匾额、花红,甚至授予顶戴品衔等褒奖。参与灾荒救济成为京畿商人实现政治目的难得的机会,可以受到皇帝亲自传旨嘉奖。总督陈辉祖的家奴蔡永清,同时也是足迹遍布全国的著名巨商,嘉庆年间参与京师赈恤,得到嘉庆皇帝嘉奖:“蔡永清向在京城居住,每岁经理收养老病贫民及婴孩等事,今年夏秋曾捐资散给被水灾民,兹又凑办棉衣,种种义举,殊堪嘉尚,着顺天府堂官备办匾额、花红,传旨赏给蔡永清,以示奖励”[14]。蔡永清不仅得到皇帝褒奖,更是因赈济“叙五品职衔,出入舆马,揖让公卿”[15],一度名誉京师,风光无限。他身为巨商,又有总督家臣的特殊身份,凭借赈济之功得五品职衔,达到了作为商人难以实现的政治高度。另外参与地方灾荒救济,也使京畿商人实现了自身价值和追求声望的愿望,文安县大商人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复筹赈有功,经李文忠公鸿章奏奬五品衔”。赈恤有功得五品衔,死后墓志铭曰“浮云富贵,为寿几何,立身后,名千古不磨,亦既有名,而又有子瓜瓞,绵绵本支百世”[16],相比一生富贵长寿,似乎更在追求留名后世。枣强县商人孙廷祥“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岁大饥,出所积谷,赒济乡里,全活甚众”,为表彰其一生善行,“乡里请县祝以《鸿德颐寿》匾额”,而他的儿子孙兴魁同样秉承父志,遇“光绪庚子凶年,出所积粮周济贫困,次年又出谷以补仓粟”,后得到乡里请奖“长孙庆椿六品顶戴同父,并封奉直大夫”[17]。祖孙三代都受到政府褒奖,成为乡里颇有名望的家族。商人参与灾荒救济也是其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和声望的一种实践。
四、京畿商人参与灾荒救济的影响
清代京畿商人广泛参与到灾荒救济中,对商人群体本身及京畿地方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京畿商人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嘉奖,获得良好的社会声望,甚至得到官府授予的品衔,极大地提高了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商人作为民间力量,通过多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参与京畿灾荒救济,极好地协助官府开展赈恤工作,与地方社会其他参与力量一起推动了灾荒救助工作,为维护灾后社会秩序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对商人群体本身而言,提高了其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由京商、津商、冀商及客商组成的京畿商人,不具有明显的“帮”的血缘和地缘特征,没有形成诸如徽商、晋商等具有全国影响的商帮,但京畿特殊的政治和贸易环境,吸引天下客商云集此处,形成了兼容并包和显著的政治性文化特征。如此靠近政治中心,给商人提高政治地位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参与灾荒救济,成为其提高政治地位的重要途径。许多商人凭借在灾荒中的赈济功劳,得到极高的政府褒奖,荣耀乡里,获得极好的声望,甚至能得到官方的品衔和封典。如京畿地区天津巨商宁世福,闻名中西商界,光绪年间总理天津商会,“其间黄河决口,畿东旱灾,直隶水灾,东省防疫,诸义举率倡先捐资以恤民,所保全者甚众”,清末发生灾荒时以身作则,带领地方绅商保全百姓,后来“大府具奏请奖,得旨以知府用后,又以覃恩,授一品封典”[18]。作为清末津地商业巨擘,得到极高的一品封典,还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影响。
另外京畿地区商人作为民间力量,直接参与到灾荒救济中,对推动灾荒赈恤工作和维护社会秩序做出了极大贡献。京畿地区频发的灾荒往往直接危及京师重地社会秩序的稳定,商绅富民作为民间力量对灾后社会秩序的维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清末政局动荡,地方政府财政亏空,无力承担高额的赈济费用,地方绅衿商富在官府的呼吁和控制下平籴平粜,响应政府劝谕赈钱、赈米、开设粥厂、捐赠棉衣,弥补了官府赈恤资金的空缺,与地方社会其他参与力量一起,对清代京畿地区灾荒救济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