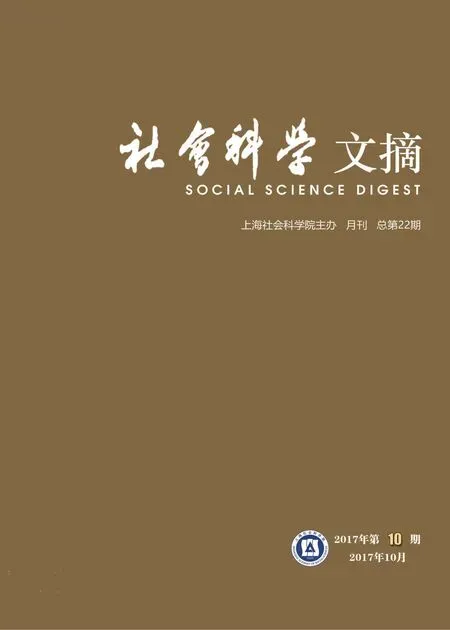论礼的近代命运
2017-11-21张昭军
文/张昭军
论礼的近代命运
文/张昭军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也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毫无疑问,礼含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养料。比如《礼记·礼运》篇所提出的大同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今天读来,仍能强烈感受到一种理想的力量。然而,理想毕竟不等于现实,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礼记·大学》说:“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本文拟从现实层面考察礼在近代的命运,希望为较全面地认识儒家文化有所助益。
天崩地解:礼秩的丧失
礼秩,即以礼为原则确立的社会秩序,涉及到人与人、家与家、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兹谨从宏观上来看儒家的天下秩序在近代是如何解体的。
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是与儒家所建立的礼治秩序相统一的。在与西方接触之前,中国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世界”与“国家”概念。“天下”观念是中国古人关于世界秩序的核心观念, “天下”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它以京师和中原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以朝贡体制为例,它在形态上呈同心圆之状,“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又可分为内藩和外藩。中国作为宗主国,与藩属国不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为了显示“天朝上国”的富有、大度和友好,中国统治者总是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尽可能给予朝贡者以赏赐,所以,各藩属国多是甘愿来华朝贡。而且,在藩属国处于危难之时,中国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和帮助。
当然,华夷双方不是对等关系。儒家主张华夏中心主义,认为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文明与周边的蛮、狄、夷、戎比较,存在文明与野蛮之别。华夏中心主义实质上是儒家文化中心主义,它维持天下秩序的理论基础就是儒家的礼。正如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所指出:“《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均以礼为标准。
步入近代后,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和礼治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里试以地理学为例予以说明。
客观地说,中国古代地理知识并不落后,但没有引起士大夫的足够重视。到清代中叶,这种状况无根本性改变。魏源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但他仍然没有突破传统的华夷观念。他提出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不具备“学习西方”的现代性。因为,他“师夷长技”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提高自我、超越自我,而是为了“制夷”,仍是古代以夷攻夷的权宜之计。日本明治初年,日本著名学者重野安绎曾讥讽魏源说:“自外来者皆帆于海,遂目以海国,而自称曰中土,是井底之蛙耳!”他认为魏源所秉持的依旧是华夏中心观,而非现代意义的世界观。实际上,直到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士大夫的科学知识仍相当贫乏。1898年,皮嘉祐撰写了一首《醒世歌》:“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意在向国人传播近代地理常识。然这并不能为守旧士大夫所接受。大学者如叶德辉等人对《醒世歌》“中国并不在中央”的观点不以为然,引经据典,严辞驳斥。在他们看来,中国是否在中央,不单是地理方位问题,而是关乎华夷秩序。由此可见西学对中国人观念世界和文化秩序冲击的现状。
然而,较之于思想观念,现实要残酷得多。西方人借助铁与火的威力,强行摧毁了中国人沿袭数千年的礼治秩序。清代疆域形势变迁图,直观地展现了华夷秩序的解体过程。清鼎盛之时,藩属国东有朝鲜、琉球,南有安南、南掌、暹罗、缅甸,西南有廓尔喀、哲孟雄、不丹,西有浩罕、哈萨克、布鲁特,等等,达数十个之多。晚清几十年间,他们相继落入列强之手,维系上千年的朝贡体系随之瓦解。即便治内之地,清廷也无法做主,任人宰割。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通过侵略战争及不平等条约,蚕食鲸吞,至少割走33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列强还通过强占租界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等手段,对中国进行了野蛮的殖民统治。而且,京师两次陷落于西方列强手中。到清末,天下已不再是中国人的天下,甚至连与西方人平起平坐的资格也没有了。1900年夏,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朝的太后携天子仓皇出逃。八国联军不仅在天朝的首善之区烧杀抢掠,而且公然在紫禁城阅兵扬威,联军头目还放肆地坐在天子的龙椅上留影。乾隆帝接受大英使臣马戛尔尼的跪拜礼仿佛就在眼前。前后对比,形如隔世!慈禧所面对的局面可谓天崩地裂。素有“礼义之邦”之称的中国,被对方视作未开化的野蛮国家。从此,历史上的华夷文野之分失去合法性,以礼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和意义世界分崩离析。
礼崩乐坏:礼教的衰败
顾名思义,礼教即以礼为教,其内容因应时代而有所调整。孔子主张扩大受教范围,把周礼运用到庶民阶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还提出“正名”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化伦理教育。汉代尊崇儒术,明确提出三纲五常说,礼教走上细密化和程式化。宋代以降,纲常名教与程朱理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礼教之风大为流行。清末有人甚至称:“吾人舍名教纲常,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可以说,从孩提时代的《童子礼》《三字经》等启蒙读物,到身后的牌坊、碑传,均是礼教的体现物。
以礼为教,彬彬有礼,初衷是使人由野蛮走向文明。然而物极必反,明清时期,礼教走上了极端,扭曲了人性,呈现出严重的病态。步入近代后,这种状况并无多少改善。
礼教病态之一:单向化。从本源上说,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对双方都有要求。然而,现实生活中,礼教却是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妇的欺压工具,造成了君权、父权、夫权绝对化,即便英君、名儒也不例外。康熙帝以“尊儒重道”著称,重视纲常教化,但他所看中的仅仅是臣下的忠诚。曾国藩被尊为“一代儒宗”,他所理解的纲常也是单向化的。他教导长子纪泽说:“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从上到下,他们普遍把三纲上升为最高道德原则,强调的仅是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绝对服从。
礼教病态之二:愚民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对于忠臣义士、孝子节妇来说,礼教代表了人生的意义,寄托了人生的信仰。他们甘愿为名教而献身,他们去世后,又进而成为他人宣传的教材和学习的榜样。近代社会动荡、战祸频仍,甘为名教殉身者数目惊人。仅同治二年七月,安徽六安获准旌恤入祀的殉身绅、民、妇女就达1887名,山东莱州则有3282名。据《徐州府志》记载,从清初至同治年间,夫亡守节者达4151人,遇变捐躯者1381人,夫亡身殉者918人,未嫁殉烈守贞者146人。入清以后,安徽桐城节烈妇女增长速度惊人。该县烈女祠在明代祀有93人,至道光中叶,所祀妇女已达2774人。福建福州一带,“凡女已字人,不幸而夫死者,父母兄弟皆迫女自尽。先日于众集处,搭高台,悬素帛,临时设祭,扶女上,父母外皆拜台下,俟女缢尽,乃以鼓吹迎尸殓归。女或不愿,家人皆诟詈羞辱之,甚有鞭挞使从者”。此类记载在史书中不胜枚举。
可以说,至晚清,礼教已陷入了严重病态。病态不是礼教的发展,而是礼教的败落。败落的礼教是中国文化的负担,是中国文化腐朽、落后、愚昧的象征。
另一方面,礼教又受到了新思潮的大扫荡。无论是维新派、革命派,还是新文化派,均把礼教作为重点批判对象。
维新派首举义旗,向礼教发起了猛攻。他们把礼教比作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桎梏”“囹圄”和“网罗”。康有为从个性解放出发,控诉礼教压制人性:“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夫之专制其家,鱼肉其妻孥,视若奴隶,恣其凌暴。在为君、为夫则乐矣,其如为臣民为妻孥者何!”谭嗣同所著《仁学》明确提出要“冲决网罗”,认为礼教并不是神圣永恒的“天理”,而是君桎臣、官轭民、父压子、夫困妻的工具。
革命派对礼教的批判又前进了一步,认为礼教是野蛮时代的象征物。他们说:礼者,“此野蛮时代圣人作之以权一时,后而大奸巨恶,欲夺天下之公权而私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从也,于是借圣人制礼之名而推波助澜,妄立种种网罗,以范天下之人。背逆之事,孰逾于此”!他们指出礼教乃制造社会不平等的渊薮,养成了中国人的奴隶性:“重礼则养成卑屈之风、服从之性,仆仆而惟上命是听,任如何非礼,如何非法,而下不得不屈从之。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是重礼者之代表也。卑屈服从之奴性,呜呼极矣!”数千年来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礼教,在革命家笔下变成了野蛮和罪恶的代名词。
新文化派把礼教与吃人联系在一起,抨击力度空前。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吴虞在《吃人与礼教》中发挥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他们把吃人和礼教画了等号,彻底改变了礼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近百年中,反礼教运动愈演愈烈,以至于“礼教”变成了上上下下口诛笔伐的贬义词。
道不在兹:礼义的败落
礼义是对礼本身所蕴含意义的阐释。清代以来,包括理学、朴学在内的儒家各派对礼之大义无所发明,导致礼义严重扁枯。从与礼相关联的角度,笔者把清代士大夫分为四种类型,以说明礼义学说的状况。
其一,假道学。儒家讲究实体实行,知行合一。而假道学者,则是满嘴仁义道德,背地却为非作歹,甚至丧尽天良。当时,假道学、伪君子不在少数。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这两位塾师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具有代表性。方宗诚系晚清名士,实则是假道学。据记载,他剽窃方东树“未刻之稿,游扬公卿间,坐是享大名。初客吴竹如方伯所,有逾墙窥室女事”。他任枣强县令5年,敛财40万金,以致离任之日,乡民聚集城门,具粪秽以待。同光年间的大学士徐桐也被人目为假道学,不过,他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官至尚书,位高权重,却能洁身清廉,勤谨任劳,按儒家的标准,应该算是忠臣和清官。问题出在他不识时务,逆违潮流。他嫉恶外国事务如仇,戊戌时期极力反对变法。义和拳起,禁咒召神,他信以为真,鼓动朝廷对外宣战,主持了攻教堂、围使馆、杀洋人等排外事件。他自以为能灭洋人,靖国难,结果适得其反,京师陷落,大局糜烂,只好自缢以谢天下。正是这样一位誉满天下的理学名臣,却“崇奉异端,贻毒海内”,人们认为他称不上有真才实学,故此,他也被奉以“假道学”之名。
其二,株守派。清代还有“真理学”的说法。所谓“真理学”,就是真心实意崇奉程朱理学者。他们奉二程、朱子为神明,甘愿匍匐于脚下,声称“天不生尼父,万古矇其视。天不生紫阳,百代聋其声”。这类人是礼教的产物,又是礼教在现实社会中的维护者和践行者。清前期的名臣李光地、中期的陈宏谋、晚期的倭仁,均恪守程朱之道,以宣传和践行礼教为职责。李光地,系康、雍两朝公认的理学名臣。康熙帝曾三次授予御匾,表彰其功,雍正帝也对他欣赏有加。李光地对孔孟程朱之道表示由衷服膺,他在康熙帝面前表示:“然臣之学,则仰体皇上之学也,近不敢背于程、朱,远不敢违于孔、孟,诵师说而守章句,佩服儒者,摒弃异端。”陈宏谋,被尊为乾隆朝“理学名臣之冠”。他对理学也无所创新,只是株守前人成说,宣称:“讲学人不必另寻题目,只将《四书》《六经》发明,得圣贤之道,精尽有心得,此心默契千古,便是真正学问。”倭仁,曾任同治帝的师傅,时人称他有圣贤气象。他对理学的诠释也完全是以程、朱为转移。他本人对此高度自觉,在日记中表示:“孔、孟大路,经程、朱辨明后,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理学的尊奉,并未停留在理论或口头上,而是在日用伦常中身体力行,将思想信仰与道德实践切实结合起来。如倭仁,作为清廷重臣,他思路明确,即严格遵照程朱理学的道德要求来治理国家。他的名言“治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后人引以为顽固派的证据,从渊源上说,这句话恰恰来自于儒家传统,与《礼记》所说“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一脉相承。
其三,书斋派。
应承认,有清一代,礼经研究成就突出,不仅官方编有《大清通礼》《三礼义疏》等典籍,而且涌现出一批专家学者。如秦蕙田、凌廷堪、胡培翬、黄以周、孙诒让等,都对礼经有深入的研究。据此,有学者认为清代乃礼学复兴时期,但礼学在何种意义上复兴,值得分析。因为,他们的著作偏于考据,内容主要表现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整理和总结,而不是思想理论的创新。即便有学者力图重释一些礼学命题,也并未带来根本性突破,且不说其中夹杂有较浓的门户之见。
简言之,汉学家的礼经研究与现实距离较远。正如钱穆所批评:“社会性的礼乐是该与时俱变的,专靠考据古礼,创兴不起今礼来。”与新派人物相比,汉学家往往缺乏一种宽阔的世界视野,他们无法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在所难免。
其四,记诵派。
此派又可称为考试派,人数最多。《礼》是科举考试必考的内容。读书人虽自小读圣贤之书,但主要是为博取功名。他们以记诵、科考见长,对礼义学说缺乏深刻认识,甚至把读书与做人判为两端。罗泽南描述湖南的情形说:“近日之士以作文掇科为急务,语以身心性命之要,莫不以为迂而笑之。”陕西学者贺瑞麟也称:士人浸淫于举业,不讲正学,以致“一有守正之士,例遭指目,不诽笑,即诋毁”。清代中后期,此类专注利禄之途而不问圣贤之道者大有人在。
世易时移,步入近代后,儒家文化因不能适应“中西大通之局”,大势已去。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的价值取向已发生根本性改变。陈独秀绝决地表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20世纪的中国人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局面:包括礼在内的儒家文化已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摘自《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