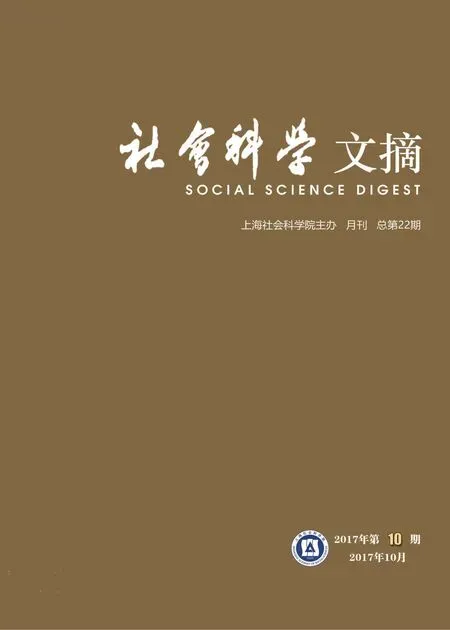“文学是人学”再续谈
——贺钱师百岁寿诞
2017-11-21陈伯海
文/陈伯海
“文学是人学”再续谈
——贺钱师百岁寿诞
文/陈伯海
业师钱谷融先生今年正步入百岁华诞,刚好又是其震惊文坛的大作《论“文学是人学”》发表60周年。母校为其庆寿,嘱写一篇文字,但不属纯纪念性的,要重在究明学理。作为亲炙教益的门生,固自义不容辞,遂不恤年迈笔衰,勉力从事,仍以老师倡扬的“文学是人学”为题,试加阐释如下。
“人学”观的历史定位
从历史源流上看,我们当承认,“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以人为本”的文学本原观的确立,同时也便是具有鲜明现代性的文学本体论趋于成熟的表征。这样说,并不等于否定传统文学创作中的人的本原作用(人永远是文学活动的主体,文学作品也必然镌有人的生命的印记),而意在表明由于传统社会中的人普遍地处于从属地位,其本原意义常受压抑,难以得到彰显,只有待到近现代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下具有独立自主人格的人的出现,“以人为本”的文学观方有可能明确树立。
我们知道,西方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是“摹仿自然”说,“自然”(指整个对象世界)成为文学的本原(柏拉图更以“自然”为“理念”的影子,于是“理念”成为文学艺术的最终本原),其中自亦包括现实世界中的人及其相互关系在内,但在“自然”的大背景下并不显得特别突出。中世纪教会以人为上帝的仆从,文学的神圣功能在于“光耀主恩”(所谓神学本原),尽管这“上帝”的形象无非是人的希望与信念的投影,而异化了的神圣终于掩抑了人自身。待到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大力标举“人文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发扬开来,文学的“人学本原观”始得到初步树立。之后古典主义者高标人的理性精神,浪漫主义者推重人的情感生命,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生命哲学、意志哲学、心理分析学派以及各种现代主义潮流又大力鼓吹非理性的作用,总体说来仍不离乎“人”这个本原。现代思潮中也有以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为代表的以宣扬“文本”的核心地位来取代“人本”的主张,更有像解构主义乃至消费主义那样将“人本”与“文本”一并打破,使文学艺术活动完全融人日常生活及符号游戏的种种试验,待拭目以观其效。
再来看我国的传统。自古以来,在我们的文学领域中也出现过“诗言志”“诗缘情”“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乃至“以情志为本”诸种提法,形成了传统文学中的“人学”内核,足可珍视。但古代中国人所肯定的“志”或“情志”,实属一种与宗法礼教人伦紧相关联的“怀抱”(参见朱自清《诗言志辨》所述),传统伦理关系支配着人的思想感情,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的训导,故“情志为本”仍须归结于“文原于道”,而文学也就成了礼教、政治的工具。政教工具论的文艺观支配中国社会达2000余年之久,至晚明“童心”说、“性灵”说的兴起,始有“以人为本”的思想萌芽产生,而仍不成气候。“五四”时期率先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明确宣示以“人学”本位来取代政教本位,体现现代性的文艺思想方告正式诞生。当时虽有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有关文学使命的争议,但前者的“为人生”固然凸显着“人本”观念,而后者的“为艺术”,落脚于表现自我,实际上也还属于特定的人学本原观。于此看来,“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正是直承“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理念发展而来的,其思想内涵与理论形态则更为博大、深厚且成熟得多,故能成为当代中国文艺思想演进上的一个独特的亮点,值得人们悉心关注与大力推进。
“人学”观的现实意义
“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的提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为长时期来在革命文学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左”的倾向而发的。如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间兴起的左翼文学运动,以“革命文学”的口号取代了“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革命文学”主张文学创作为革命事业服务,表现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理想和斗争生活,这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尝试用人民本位的文学观来丰富和拓展“五四”时期有关“人的文学”的理念,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文学为革命斗争服务,一味地让文学从属于政治,又不免割裂了人的多样化的社会存在,扭曲其血肉丰满的生活实践,进以削弱甚至丢失了文学的“人学”本根,使之蜕变为单纯从事宣传、说教的工具。长时期因袭下来的将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与故事用为图解政治、粉饰生活的手段,就是这种“工具论”恶性膨胀的表现,导致文学创作严重脱离人的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坠入假、大、空的窠臼而不能自拔。“文学是人学”的申言正是为针砭时弊而发,它在大力反对“工具论”的同时,高扬了文学活动的“人学”本原,在那个时代实起到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与此同时,《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对“五四”以来的“人学”传统也作了进一步提升,它既不像“人的文学”一说所鼓吹的那样偏重在“自然人性”和“个体本位”,亦不同于后来梁实秋诸人着力标榜的“普遍人性”及全人类的“共通性”,而是切实地主张自然人性与社会人性的统一、普遍人性与具体人性的结合,并以“人道主义”(即“把人当作人”的信条)用为人学本原观的价值尺度,联系相关论题,建构起一个更为圆融而开阔的理论体系,其实际意义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的。
遗憾的是,这一理念提出后,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立即遭受严厉打压,成为思想批判的众矢之的,而被沉埋达20年之久。直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历经“文革”浩劫,人们回过头来清算“左”的遗毒,才又将其重新发掘出来并加以肯认。实际上,“以人为本”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新时期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恰是沿着这条路子不断展开其行程的。从70年代末对于“工具论”的反拨,经80年代前期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到80年代中后期主体论文艺思想的建构与传播,以至90年代中叶就“人文精神失落”危机所发出的警示性召唤,这一系列理论思想领域的探索与建树,不都是奠立在“人学本原观”基础之上的吗?可以说,“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文艺思想战线建设上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至今未曾消歇。
犹可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以来关于“人学”本原问题的探讨,虽有多方面的深入开展,却并未穷尽这个命题的全部内涵。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只触及人学本原观的若干重要方面,完整的理论形态尚待系统梳理与整合。主体论文艺思想虽形成了一个纲领,仍有将作为文学本原的“人”置于主客二分的境地且予以实体化的倾向,未能充分揭示“人学”的本原意义。而有关“人文精神”的热切呼告,亦只是在价值论层面上发扬了“人学”的追求目标,其对激情的诉求远远大过于理性的思考。甚至20世纪90年代之后陆续兴起的各种“后新潮”文学观如形式本体论、文本建构论、语言符号游戏论、意义消解论,以及21世纪以来大众消费文化和休闲文艺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也都需要有“人学本原观”及时作出有力的回应。据此而言,“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自仍有大力拓展的余地,要求我们为其开辟出更为远大的发展前景。
“人学"观的未来建构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进一步发扬这一具有强劲生命力的理念,使其获得更为广阔的解释空间和更为坚实的立论根基呢?我以为,这样几个方面或许是可资探询与思考的。
首先是作为文学本原的“人”的内涵界定。“文学是人学”一说的核心在于“人”,“人”是文学的主体,也是文学的本根。只有对当今时代所需要树立的“人”的内涵有明确的把握,文学的发展才会有牢靠的方向。然而,“人”又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一种存在物。它既有自然的生命,又有社会的生命;既属于个体的存在,又属于群体的存在;既有感性的需要,又有理性的追求;既会有现实功利的计较,又会有精神超越的向往;乃至既常有“主客二分”的设置,又时须步入“天人合一”、与万物一体的境界。对这样一种最具复杂多面性的生物体,该当如何来领会其实质,方足以为当今文学的演变确立切实可行的航向呢?依我之拙见,尽管“人”在不同时际、不同境遇下会侧重展示其不同的方面,但从总体上说,我们所须推重的当是向着全面发展而不断生成着的人,而不应是单面的人、封闭的人以及凝固化了的人。就立足于当前已然达到高水平的现代文明和开始向“后现代”转型的时代潮流而言,亟须树立的也当是那种既具有独立自主性而亦能与他人、与他物乃至与整个世界和协共生的人格精神。这样的人才足以开创未来,才能担当起全面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并进以营造“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社会的职责,也才有可能引领我们的民族新文学稳步走向繁荣与复兴。人道主义者鼓吹“把人当作人”,我们自不能停留于19世纪时那种单纯同情弱者的胸怀,也不能追随尼采式的一味仰望强者的眼光,须有我们自己面对当今世界的选择,这或许将成为眼下拓展文学的“人学本原观”的第一要义。
其次要看到,“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中必然蕴含着一个“人”与“文”的关系问题。把“文学”归结为“人学”,意味着“人”是文学的本根,但本根并不同于芽卉,文学作品仍须以文本的形态呈现,这里就有一个由“人”到“文”的转化过程。比如我们常说,文学是写人的,是写给人看的,这都不错,但前提乃文学为人所写,“人”是文学的创作者。人凭什么来创作文学作品的呢?一是要凭他在其生命活动中长期积累的生活素材和所形成的生命体验,二是要通过审美想象将这些素材与体验转化为艺术构思,三还要借助语言文字符号将其艺术构思体现于文本形态。这一个个转化的步骤都需要分别作研究与解析,“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方能真正得到落实。再比如,文学作品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符号系统,被人称作“有意味的形式”,其表层文本结构中实涵有深层的审美心理与文化意蕴在。这形式中的“意味”、表层下的深层,实即文本内涵的“人本”,如何将不同层次的因子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让语言符号、审美心态、文化意蕴三者之间相互渗透与映射的关系得到阐释,“文本”与“人本”得以会通,也是尚待解决的问题。还要看到,文学作品产生后,文学活动其实并未曾终止,更须有一个读者对作品的解读与接受的环节,这又构成了由“文”向“人”的转化过程,而转化中的双向交流与互动,包括如何由艺术符号生成新的审美体验与思想共振,亦尚可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总之,上述几方面问题均涉及“人”与“文”的对立统一关系,逐一梳理清楚,有一个全面的观照,“文学是人学”的原理才得以充分展开并确立不移。
界定“人”的内涵与正确把握“人”与“文”的关系,属“文学是人学”一说的基本内核,除此之外,涉及问题尚多。如:文学活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之一,与人的其他存在方式之间关系如何?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活动的结晶,与人的其他审美形态及意识形态产品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何在?甚至像传统所云“人品即文品”或“人品不类文品”,这样的说法该当如何对待?诸如此类的问题,要追根溯源,都常会触及“文”与“人”之间的内在关联。立足于“文学是人学”的理念,从人学本原观上来看待各种文学现象,便于高屋建瓴式地来营构文学理论的大厦,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也是崇奉“以人为本”信念的文学工作者今后所当致力的方向,愿与同好者共勉!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