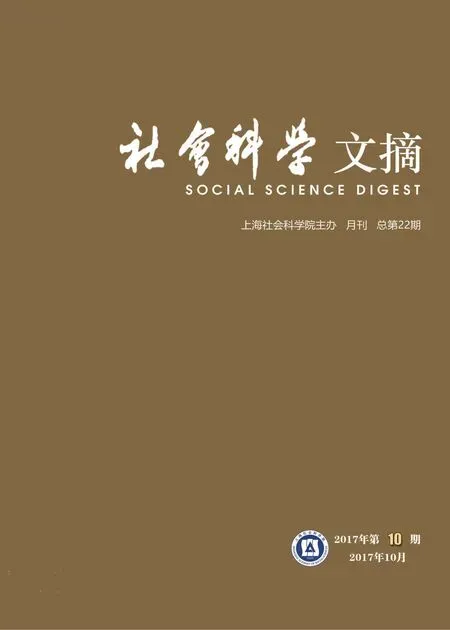石黑一雄小说中的怀旧与身份认同
2017-11-21魏文
文/魏文
石黑一雄小说中的怀旧与身份认同
文/魏文
引言
在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作品中,怀旧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石黑一雄的主人公大多是在现代社会中被边缘化的“无家可归者”,面临着由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动荡所造成的身份危机或存在焦虑感。身处困境的主人公往往诉诸于怀旧,力图通过对往事的怀想和对曾经短暂存在过的那个“家园”的回忆,从而重新认识自我,稳固并重申自我身份。
然而在其不同的作品中,小说家对自我身份的强调却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例如《长日留痕》的主人公史蒂文斯试图建构一个单一、静止、排外的身份,这个身份有两个核心要点:尊严和英国性。然而他的怀旧叙事却充分暴露了这种身份模式的内在悖谬性。小说叙事实际上解构了他所信仰的“尊严”和“英国性”,从而彻底否定了那种一层不变的固定身份认同模式的合法性。不同的是,在另一部小说《群山淡景》中,叙事者悦子通过自反性、反讽式的叙事,重构自我身份。这种身份实则是一个永远在被言说、被建构的过程,一个永在进行中的叙事话语实践;它永不完结,也没有排他性,而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现代社会中的怀旧与个体身份
怀旧的英文“nostalgia”来自两个希腊语词根:“nostos”意为“返乡”,“algia”意指“怀想”。因此怀旧的大意是指对往日家园或往昔时光的怀想。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和情感体验,怀旧是古往今来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社会现象。传统社会中人类通过祭祀活动所表达的对先祖的崇拜可以看成是一种怀旧;当今社会中诸如黑白照片、复古音乐、历史题材影视剧等大众文化产品所引起人们对往昔岁月的回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怀旧。因此可以说,怀旧是无时不在和无处不在的。
而在现代性语境下,人类的怀旧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怀旧是现代个体维持自我身份稳定和统一的重要方式。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看来,现代人普遍面临着“本体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存在的焦虑”这两大问题。对于处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变迁中的现代个体来讲,若要维持自我身份稳定、缓解“存在的焦虑”,就需要回溯过去,通过从传统与往事中寻找确定性,从而为生活在当下变化中的自我树立信心和安全感。在这个意义上,怀旧为个体探寻自我之源、维持自我意识的统一提供了可行的途径。为了应对现实情境中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和存在焦虑感,主体通过回溯过去,挖掘存在于往事中的个体形象和生存经验,从而为当下的自我提供应对困境所需要的信心和确认感,从而避免处于不断变迁的现代社会中的自我被分裂、被异化的命运。总之,怀旧就是个体在当下的混乱中用来不断建构、维护和重构自我身份重要方式。
与此同时,美国俄裔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将怀旧现象划分为两大类:复原性怀旧与反思性怀旧。复原性的怀旧者往往不承认怀旧叙述中的虚构成分。他们在某个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力量的驱动之下,通过有选择性地恢复某些传统、重构一个神话式的本源,从而试图为当下的世界树立某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因此,复原性怀旧的个体总是试图通过构建一段共同的历史,回溯一个稳定不变的起源,从而为集体中的所有个体确立一个本质主义的、单一化的身份。与此相反,反思性的怀旧所关注的并非某个存在于过去的绝对真理,而是对历史和时间的思考。此类怀旧并不企图重建某个神话般的家园,而是借助关于过去的叙事探索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因此,反思性怀旧者所重申的身份也不可能是一种固定僵化的实体,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身份认同的过程。
怀旧同样是石黑一雄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他的所有长篇小说均探讨了记忆、怀旧等话题。此外,除了《被埋葬的巨人》之外,其余六部小说的情节皆是以主人公对过去经历的怀旧叙事为基础而展开。因此,本文以《长日留痕》和《群山淡景》为例,探讨石黑一雄对怀旧与个体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复原性怀旧与英国性的悖论
《长日留痕》是石黑一雄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89年。小说的叙事者史蒂文斯是一个“典型的”英式老管家,他所工作的地点也是一栋“典型的”英国乡间府邸——达灵顿府。小说的故事始于1956年,此时的达灵顿府如同大英帝国一样,早已失去昔日的辉煌。“二战”后英国社会经历的剧烈变化使得史蒂文斯这位迟暮之年的老管家对现实倍感困惑。随着自己效忠多年的主人达灵顿勋爵的离世,史蒂文斯和达灵顿府一起被打包售给美国富商法拉戴先生。对现状的失望迫使史蒂文斯只能诉诸于怀旧,借旧日的荣光慰藉当下的苦难。个人身份的困惑让他回望过去,企图通过回归本真的起源、恢复现已遗失的某种绝对真理并将其作为最高价值和道德的判断标准,最终构建一个封闭且排他的、个人和集体高度一致的英国民族身份,或英国性(Englishness)。
按照博伊姆的定义,史蒂文斯的怀旧属于“复原性”的。博伊姆认为,“复原性怀旧体现于对过去纪念碑的完美重构”以及“对传统和习俗的重新发明和复原”。而史蒂文斯企图重建的“纪念碑”便是曾经的达灵顿府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传统价值和道德标准。此外,达灵顿府还是史蒂文斯理想中的那种英国民族身份的基石。在他的怀旧叙事中,作为民族身份的英国性由三个基本方面构成:达灵顿府、绅士阶层以及男管家。这三者共同蕴涵的传统价值和道德标准被史蒂文斯总结为“伟大”和“尊严”。
在史蒂文斯看来,达灵顿府即是英国的象征。他骄傲地告诉自己的美国雇主法拉戴先生:“这些年来我十分荣幸,能够欣赏英国最美的风景,就在这四周的高墙之内。”实际上,在英国文学传统中,乡间庄园通常被认为是定义英国性的最佳地点,因为其建筑结构象征着严密而整齐的社会结构,其经久不衰的历时性则暗示着“民族身份连续性的幻象”。他们作为一种关于英国民族身份的怀旧话语,让过去重新显现于当前,同时也让现在能够重新创构过去。正因如此,史蒂文斯才试图从往日岁月中寻找到达灵顿府所体现的价值和理想,从而复原某个已逝的民族身份。除此之外,如果说庄园府邸是英国民族身份的物理表征,那么居于其中的绅士以及男管家则承载着关于该身份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伟大的英国绅士阶层是人类文明进步之重任的承担者;而男管家之伟大则体现于他们为伟大的绅士服务,从而也就是为人类之福祉而服务。此外,这两者又与“英国”这一概念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在史蒂文斯看来,“只有英国才有真正的男管家......一个伟大的男管家,根据定义,一定是一个英国人”。
不幸的是,史蒂文斯并未意识到,他试图重构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却被自己的怀旧叙事所颠覆和解构。他的复原性怀旧叙事非但没有重构一个理想化的英国身份,反而暴露了这种身份神话的在内悖谬性:这种单一化、排他性的本质主义英国民族身份只不过是一个自身充满悖论的幻象。
首先,达灵顿府早已沦为某种文化商品,无法表征具有本真起源的民族传统。在小说中,美国人法拉戴买下达灵顿府后,曾邀请友人韦克菲尔德夫妇前来做客。这对夫妇询问史蒂文斯:“这个拱门看起来像十七世纪的。它不会是最近才仿造的吧?”他们最终得出结论:“我觉得是仿造的。技术很好,但依然是仿造的”。而法拉戴先生也曾以相同的方式质询史蒂文斯:“你是正宗的老式英国管家,而不是一个假装管家的服务员。你是真的东西,对吧?”这一情节的反讽意义在于,当史蒂文斯把达灵顿府视为表征民族身份的神话而与之认同时,美国人法拉戴却把这种神话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形式将其挪用。在英国文学传统中,庄园府邸之所以被认为是英国民族身份的象征,是缘于其物理结构的完整性表征着社会的高度统一性;然而在《长日留痕》中,作为文化商品的达灵顿府却因为本身的流通性和易变性被切断了与历史起源的关联。它不再通过继承或传承而见证历史交替,相反,它现如今只能在资本市场进行流通和转移。
其次,史蒂文斯所宣扬的“伟大”和“尊严”的本质乃是对贵族阶层的愚忠和奴性。在他看来,对雇主的绝对忠诚就意味着男管家没有必要具备独立批判性的思维能力。以这种方式,他将道德价值判断的责任让渡给诸如达灵顿勋爵这样的绅士。换言之,高贵的绅士们不仅是英国民族身份的象征,同时还是知识和道德方面的权威专家,以及国家命运的裁决者。具有讽刺性的是,达灵顿勋爵对“二战”前的政治时局作出了错误判断,支持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最终将英国推向了战争的深渊。此外,为了讨好来访的纳粹特使,达灵顿勋爵要求史蒂文斯解雇府邸里两名犹太女佣,尽管她们“一直都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员工”。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顾公平、正义等道德原则,这说明达灵顿勋爵根本算不上是一位谦谦君子。
可见,晚年的史蒂文斯试图在对往事的怀旧中寻找并复原一个稳定不变的个体身份和民族身份,并重新发明与此身份相关联的传统价值和道德标准,从而应对当前所面临的身份危机。然而他的怀旧叙事却反讽式地颠覆和解构了自己试图重建的价值观和传统。他所引以为豪的“尊严”只不过是对贵族统治阶级的盲从;而他所试图证明的关于英国民族身份的“伟大”实际上是一个极其空泛的概念。
反思性怀旧与身份重构
与史蒂文斯的复原性怀旧不同,《群山淡景》中的叙事者悦子的怀旧则是反思性的。小说的叙事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叙事者悦子是一位寡居英国的日本女性。一方面,她由于大女儿景子的自杀而感到愧疚和痛苦;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亚裔移民,她还是文化偏见的受害者。有研究者指出,“错位(displacement)”是小说的重要主题。而英文里,“displacement”还有“驱逐、离家”之意。因此,悦子的遭遇不仅是各种层面的错位,更是远离精神家园的放逐。被流放至社会边缘的她,只有借助于对往昔岁月的回顾与怀想,才能够找到认清现状、化解危机的可行方案;也只有求助于怀旧,她才能想象性地重构已经丧失的自我身份。
然而,悦子并没有试图去恢复记忆中那个虚幻而美好的家园,因为她深知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故土日本长崎早已被战争摧毁;她也没有企图通过回忆的想象去建构某种排他性的民族身份神话,因为在她看来,东方和西方“有着如此多的共同点”。简而言之,她关于过去的叙述是“讽喻性的、碎片化的、非终结的”。反思性的怀旧使得悦子能够想象性地重构一种并非固定僵化,而是处于动态建构中的身份;或者说,悦子的怀旧是一个始终处于进行之中的、关于自我身份的叙事过程。这种叙事具有以下两大特点:
悦子的怀旧叙事摘除了父权思想为女性贴上的柔弱、温顺的标签,并逆转了“男性/女性”二元对立中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在对往事的叙述中,悦子巧妙地借用另一位母亲幸子的故事,颠覆了“男性作为欲望主体,女性作为幻想客体”的性别神话。根据悦子的描述,幸子是她在长崎生活时所结识的友人,一位叛逆、独立、勇敢的女性。读者不难发现,悦子和幸子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例如,两人均有一段不幸的婚姻以及一个性情孤僻的女儿;幸子一直希望美国大兵弗兰克将自己带到美国,而悦子则是同英国记者谢林汉姆结婚并移民英国。此外,当悦子劝说幸子的女儿真理子跟随她母亲幸子移民去美国的时候,她误将“你们”说成了“我们”——“如果你(真理子)不喜欢那里的话,我们可以随时回来”。也就是说,悦子似乎并不是在对别人的女儿讲话,而是在向自己的女儿景子作出承诺:如果你不喜欢那里(英国),我们可以随时回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幸子的经历填补了悦子关于自己的叙事中的空白,还原了被省略的信息,并揭示了被叙事者刻意隐藏的秘密。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幸子坚强独立、敢于挑战传统道德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叙事者悦子本人的所作所为。她的怀旧叙事假借她人之口颠覆了性别神话。悦子实际上将自己对命运的不屈抗争“投射”到幸子之上。在这两位女性难分彼此的故事之中,男性(悦子的英国丈夫谢林汉姆以及幸子的美国男友弗兰克)不再扮演拯救者的角色,而是沦为女性为达成目标所借助的手段。被凝视的客体(女性)逆转成为能动的主体,而欲望的主体(男性)则成为了女性为达成目标所利用的工具。
除此之外,悦子非线性的怀旧叙事所呈现的内在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意味着她身份的重构永不完结。在《群山淡景》中,悦子的叙述总是在“现在”与“过去”之间频繁无规律地跳跃,这使得她的怀旧叙事呈现出非线性和碎片化的特征。而悦子和幸子两者之间模棱两可的关系也印证了她的叙事的内在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叙事中的意义空白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随着悦子碎片化的回述缓慢展开,读者自己也经历了伊瑟所说的“连续修正的过程”。正如作者书写了悦子的故事那样,读者也通过自我的阅读策略重新创造了相同的故事,建构了一个由角色和情境所组成的网络,推动情节走向最终结局。值得注意的是,悦子关于自我的叙事永远不会终结。在小说里,悦子的小女儿尼基告诉她,“我的一个朋友正准备写一首关于你的诗”,并要求悦子提供“一张照片,或其它东西,关于长崎的......这样她能够了解所有的事情”。悦子却不知道该给女儿什么,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展示“所有的事情”。正如悦子本人的怀旧一样,尼基的朋友所要书写的诗歌同样是关于悦子的叙事;同样,如同没有什么可以展现“所有的事情”一样,没有什么叙事能够展示关于主人公的一切。个人的身份与其说是一种从过去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稳定不变的实体,还不如说是一段通过怀旧来书写的、永未完结且需不断修正的叙事。
结语
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时,石黑一雄认为自己接受了“典型的英式教育”,但同时又否认自己“在文化意义上完全是英国人,因为(他)由日本父母抚养长大”。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经历使意识到了自己的特殊身份,他曾声称自己“既不是英国的,也不是日本的”。这并不是在否定自己所继承的文化遗产,而是对身份作出有别于传统的阐释。正如他在自己的作品《群山淡景》和《长日留痕》里通过主人公的怀旧叙事所证明的那样,“身份”不可能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或者排他性的概念,也无法简单地置于某一个单一的框架内去定义。它只能是一个开放性的动态概念,永不完结,一直在修正。
(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讲师;摘自《外国语文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