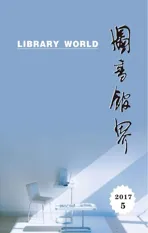“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图书馆知识创生新形态研究
2017-11-16
(枣庄学院图书馆,山东 枣庄 277100)
“互联网+
”时代的数字图书馆知识创生新形态研究
张红梅
(枣庄学院图书馆,山东 枣庄 277100)
“互联网+”时代为数字图书馆的知识创生提供了条件,知识创生将成为数字图书馆知识创新的新形态,数字图书馆以及用户所蕴含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将转换为碎片化知识、关联知识和知识集合,并形成一个循环的系统。在数字图书馆用户的知识需求以及数字图书馆的理念要求的基础上构建了数字图书馆知识的创生模式。本研究具体地阐述了知识创生的概念以及知识创生的缘由,以此满足了用户知识的需求以及用户的个性化知识服务,为后续数字图书馆的知识创生服务提供了借鉴。
知识创生;数字图书馆;互联网+;用户需求
1 引 言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数字图书馆在信息推送和信息竞争环境的迅速变化中也面临着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爆炸越来越明显,数字资源整体无序的状态越来越严重,从而出现了所谓的“被数据淹没,却饥渴于知识”的现象。人们对于知识的需求却不断增加,简单的查询、统计、检索信息已经不能满足于人们对更深层次知识的需求。为了满足自身的学习以及工作的需要,那么寻求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转化成为在互联网时代获取重要信息和知识的当务之急。知识创生过程即是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相互转换并不断循环互动的过程,这是由日本知识管理专家野中郁次郎和绀野登提出来的。该过程是由四个知识转换模式组成的,即社会化(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外在化(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组合化(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和内在化(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其轨迹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螺旋上升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共同创造了新的知识,实现了知识的自我超越,有效地满足了用户对于知识的需求,并解决了目前“信息丰富而知识贫乏”的现象。知识创生为科学交流带来一场变革,图书馆作为科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卷入这次革新的浪潮。因此,知识创生为数字图书馆中用户知识的需求以及知识的再生产提供服务。笔者从知识创生对数字图书馆的影响着手,挖掘数字图书馆中用户对于知识的需求以及数字图书馆中用户的新理念,进而结合知识创生的特点构建数字图书馆的知识创生模式,为以后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提供借鉴。
2 知识创生:数字图书馆的新使命
以往,知识来源于书本中,或者图书馆的馆藏书目中,然而现在处于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在线交流平台以及在线图书馆来传播、发表、获取和利用信息。在整个使用过程中,知识的创生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显性知识被记录下来,而是知识的习得来源于用户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参与,分析加工一个一个的碎片化知识,使相关联的知识集合起来。为了更好地实现用户对于数字图书馆的使用,通过知识创生的形式将知识进行整合,为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开辟新的途径。
2.1 知识创生的概念
在我国,钟启泉教授最先提出“知识创生”,他认为知识创生的主体不是一个组织或者一个团队,而是一个个体,它通过不能显示出来的隐性知识与能够通过语言或者形态体现出来的显性知识相互交换,并不断循环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本质发生着质的改变。也就是说,知识创生,创造出了新的知识,促进了新知识生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有益于个体发展的、动态的、循环的新知识。其实质就是使个体达到自我超越的程度,成为一个新的个体。
吴燕在《泛在知识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发展研究》中指出:数字图书馆是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知识中心。那么在“互联网+”时代,数字图书馆对于知识的需求也不再是简单的电子资源的需求,而是对于数字资源建设的需求。需要对知识进行再加工也就是知识进行创生。用户在个人图书馆的使用中形成知识之间的链接,使数字图书馆成为知识的中心。
2.2 数字图书馆的知识创生
探究数字图书馆知识的创生问题,是本研究的核心。数字图书馆知识创生是通过用户的学习实践,生产出有利于图书馆知识体系中新知识的生成过程。数字图书馆知识的创生与用户个人原有的知识、经验、心里认知水平有关,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用户在数字图书馆中形成新知识的动态循环也与用户的自身对于知识理解的能力以及教育机制和创造性有关,因此,需要不断地创生实践性知识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2.2.1 数字图书馆用户新需求。首先,是对数字图书馆用户的定义,展晓玲等在《数字图书馆的服务转型》一书中指出:数字图书馆用户是指在网络环境下,为了实现自身的信息需求,利用数字图书馆来完成科研、生产、管理、技术、新闻、艺术以及各项社会活动的个人或团体。它不仅包括亲自来到图书馆满足自己需求的用户,比如通过借阅证或者被授权或者未被授权的用户,而且还包括通过互联网远程登录访问的用户。
“读者第一,服务至上”一直是图书馆的服务宗旨,用户的需求也一直是改善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源泉与出发点,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用户的需求也将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并产生新的需求。根据泰勒(Taylor)的信息需求理论,将用户的需求划分为四类:内在的需求(用户真正需要却无法表达出来的信息——隐性知识需求),意识到的需求(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转化的部分,用户可以感觉出来,但是比较模糊),表达出来的需求(显性知识,用户可以用语言描述,并需求帮助),折中的需求(显性知识,最后呈现出的修正的知识)。对于用户在检索过程中检索出来的单个文献或者文献集以及各种检索方式的使用,这些都是显性知识。然而,在检索中用户还可能需要与之相关的PPT、视频、博客以及相关的专家评论等,这些都属于潜在的知识。用户真正需要而意识不到的知识,属于意识的需求。用户在浩瀚的信息中检索出了信息,但是无法完全保证用户能够获取到准确的信息,并对大量超载的信息做出选择也很困难。用户需要的是经过筛选以及整合过的信息,这属于折中的需求。用户需要的不仅仅是相似度匹配的检索结果,还需要与之相关的无形学术交流而得到的网络化知识,这就是内化的需求。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数据库记录,而是一个无形的网络,辅助用户更深入地科学研究。这些数字图书馆用户的新需求,呼唤着数字图书馆知识进行创生并形成一定的模式。
2.2.2 数字图书馆新理念的要求。信息时代,数字化图书馆应该与时俱进,坚持新的理念,科学创新,并服务用户。在图书馆的工作中,每一个环节都是围绕着人来开展的,为此,读者作为图书馆的真正需求者,数字图书馆的理念要满足读者需求,为读者着想,设身处地地为其提供各种方便,这是图书馆发展的最新理念。
首先,图书馆需要开展人性化的服务,要求图书馆应充分考虑读者的个人特点和独特的信息需求,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信息环境服务。它的内容包括:个性化的检索方式、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个性化的用户界面以及个性化的信息处理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把“用户第一”的思想理念牢记于心,为后续展开服务打下良好的基础。
其次,在为读者提供服务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提供知识的创新。读者对文献资源的利用需求变得更综合,这需要更加全方位的信息保障。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用户需要的知识更加集成和高效,这就需要数字图书馆将文献信息深层次整合,将分散的知识集中整理,这些都需要将知识进行重组,创生。
最后,提高读者增加值是数字图书馆在竞争中谋求发展的核心。图书馆的发展开始由被动服务转换为主动服务,将读者的需求转换为动力,增强对信息的分析重组,采用更高的附加值产品来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同时采用知识服务来创新性的对知识进行抽取、分析、整合,创造出一种更加人性化的服务,满足各个知识网中不同用户的知识交流,让知识在网中流动,并不断的加入新的知识,形成知识的内化,满足各种类型读者的需求。
数字图书馆是知识的场所,用知识来调节数字图书馆的用户需求。数字图书馆不仅应该知道用户的需求,而且应该不断地从用户的行为中整合形成新的知识。这种知识的获得就是通过数字图书馆中用户对于知识的创生。数字图书馆的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在某一特定的服务方式上,设定信息的来源方式、表现形式等;同时,数字图书馆也可主动记录用户的阅读习惯,用户的个体特征以及用户阅读活动的方式和用户阅读内容的选择,以便最为便捷地从数字图书馆中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这种将用户需求化被动服务为主动推送服务的发掘用户隐藏需求信息的方式,能更好地吸引用户对于数字图书馆的使用,使图书馆服务达到质的飞跃。
3 构建数字图书馆的知识创生模式
为了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数字图书馆的知识创生应运而生,它是在传统图书馆的基础上融入了互联网,并且以用户的个性化服务作为基础,既强调了个体在其中的建构过程,也强调了知识在知识网中关联的重要性。为此,基于以上对数字图书馆中用户的需求以及图书馆新理念的要求的分析,继而构建数字图书馆的知识创生模式,如图1所示。为了凸显其中的关联性,并未完全展示,而是着重展示其框架结构,在后续的研究中再一一展示。

图1 数字图书馆知识创生模式图
“互联网+”时代,数字图书馆中的知识既有显性知识也有隐性知识,其中显性知识更多的是来源于互联网中的知识以及数字图书馆中的电子资源,而隐性知识则是经过用户头脑内化的知识,同时在数字图书馆中用户的行为也生成了隐性知识,以这些知识为基础,不断地汇集累加完成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转化。“互联网+”时代,数字图书馆的学习使用就是让知识通过用户的行为在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不断地转变,从而创生出数字图书馆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通过不断的改写、融合,然后逐渐整合起来,并且与数字图书馆用户本身原有的知识体系完成对接,最终通过数字图书馆进行知识的创造性重构,从而实现知识的创生。数字图书馆知识的创生过程就在于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的不断循环,实现数字图书馆知识体系的重构,完成知识的创新。在数字图书馆的使用过程中,用户对于知识都是基于需求、基于兴趣以及基于用户实际工作或者任务中的需求,在互联网时代,数字图书馆中用户的知识创生其实也是一种新型的知识建构,在建构中蕴含着创新,知识的创生也就是知识的创新。
新知识的形成往往是由原有知识进行内化而形成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互联网中,知识与知识之间以互联网为桥,形成连接数字图书馆内的各个节点。知识的分布也变成碎片化知识与知识集合和与之相关的关联知识,并以开放的形式得以存储。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主要就是这些碎片化知识、知识集合以及关联知识相互转化。下面呈现的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的关联,如图2所示。

图2 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内部创生的路径图
数字图书馆时代,知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本知识,载体也不再是仅仅依靠纸质书本,互联网时代的图书馆知识存在着碎片化、关联性以及集合性的特征。碎片知识、关联知识、知识集合这三种知识都存在于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中,并且是共生共存的。碎片化知识是基础,通过协商形成关联知识,对关联知识不断的叠加形成知识集合,知识集合被分享给各个用户又形成碎片化知识,在数字图书馆中,这三种形态之间不断地转变,形成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内部创生。
3.1 通过协商形成关联知识
在数字图书馆内,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交流是通过协商进行的,而传统图书馆中,对知识的掌握则是单纯的书本知识,不能进行有效的意义建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数字图书馆内用户之间的交互行为也得到了关注,通过用户之间的互动,对原有的知识内容不断地增加以及改写,使原有的碎片知识积累形成关联。这一过程实现了用户与用户之间知识的传递与接收,从而达到知识的一种聚合状态,建立数字图书馆内用户知识之间的动态传递,形成知识之间的内部关联,获得关联知识。同时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自主地选择学习内容、学习资源,并且根据自身的爱好与兴趣相投的用户建立联系,形成关联性知识,这个过程知识的获取也成为主动的生成,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在这个过程中,知识不断地被整合,产生新的知识,形成社会化网络。
3.2 重构是形成知识集合的关键
在数字图书馆中,用户都可以看作一个一个的单元,用户所拥有的知识在互联网中非常的碎片化,这就为我们对知识的重构打下一定的基础,由于碎片化的知识之间有着关联性,为此,我们按照一定的逻辑法则对其进行梳理,抽取出来的知识则是知识集合。重构在知识的创生中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用户往往通过已有的知识寻找其中内部隐含的逻辑将碎片化的知识进行系统化组织,这是知识创生的关键性步骤。没有重构则知识之间不能形成体系,不能完成知识的创生,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则无法进行转化,完成循环过程。
知识的重构不仅满足了用户的信息需求,而且对于用户的检索模式、借阅行为都可以进行关联的规则分析,从而可以优化检索路径,提高用户的检索效率,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服务,数字图书馆也能得到众多用户的使用,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3.3 通过分享生成碎片知识
知识的传授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分享行为,在数字图书馆的学习过程中,用户将自己阅读的成果在网络中展示,其他用户则可以获得阅读的内容、阅读的评论以及其他用户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通过推送的形式引起其他用户的关注与参与,同时这背后蕴含着其他用户进行分享的动力。所有有意义的建构都是个体的主动分享,用户的主动分享促进知识集合生成碎片化的知识。在互联网中形成的碎片化知识包含着用户的一些客观数据和非客观的材料,对于这些知识可以采用话语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来探究更深层次的意义。知识创生的方式就是主动分享,在不断的分享过程中不断地产生新的知识,满足数字图书馆用户的不同需求,实现个性化的知识服务。
4 反思与评价
知识创生本是知识管理中关于知识创新而引出的,现引入数字图书馆中,使原有的数字图书馆知识更加丰富,同时也准确地揭示了在数字图书馆中知识生产的全过程。这种自我超越的全新模式,正是我们以往在使用数字图书馆时所忽略的部分。在数字图书馆内进行知识创生,这是首次提出来的并且对于知识的获取以及知识的再生产也将非常有意义,同时也将使数字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更上一层楼。数字图书馆的知识创生模式也将使用户更加清晰地明白知识的内部转换,使知识更加个性化,同时还可以促进用户间的交流。
5 结 语
关于知识创生的过程有很多不同的表述,然而知识创生在其他的领域中已经有着丰富的经验。随着互联网的变革,也慢慢进入数字图书馆中,知识创生已然成为“互联网+”时代数字图书馆的新的形态。关注知识创生的过程能够将数字图书馆的知识服务进行调整,以达到数字图书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推动了“互联网+”时代信息经济的发展。将数字图书馆中碎片化知识、关联知识以及知识集合之间的互动循环形成一个系统将更好地为数字图书馆用户服务。在“互联网+”时代,数字图书馆的知识创生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需要继续探索,本研究只是一个开端,希望后来者能够更加深入地探究数字图书馆知识创生的研究,并给予关注,那么知识的成型将是有可能的。
[1]靳晓恩.数字图书馆的知识发现研究[D].湘潭大学,2008.
[2]梁松林.SECI(知识创生理论)对于教师实践性知识生成、共享和创新的启示分析[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11).
[3]王 帆,舒 杭,蔡英歌,等.“互联网+”时代众传知识的创生与实践——智慧教育新诉求[J].电化教育研究,2016(4):42—48.
[4]崔冬敏.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中实践性知识创生问题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
[5]姚小娇.数字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1.
[6]张为江.基于用户需求分析的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系统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9):83—85.
[7]魏思廷.结合替代计量学的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新模式[J].图书情报知识,2015(2):87—92.
[8]党卫平.高校图书馆服务在信息时代的新理念[J].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08(2):143—145.
[9]龚孟伟.数字图书馆的理念变革与运作策略[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4):15—18.
[10]余肖生,周 宁,张芳芳.数字图书馆中个性化服务的用户需求模型研究[J].情报杂志,2006(5):116—118.
G250.76
B
1005-6041(2017)05-0074-04
2017-06-01
张红梅(1990—),女,硕士,枣庄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