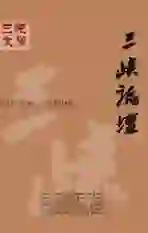认同、想象与表达:华安高山族的文化重构
2017-10-20林钰琼董建辉
林钰琼 董建辉
摘 要:华安县是大陆高山族同胞聚居最多的縣份,而华安高山族在近几十年的生活中经历了在地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地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为高山族文化重构奠定良好基础,高山族文化逐渐获得发展,产生了以舞蹈和服饰为主的文化内容。高山族以集体或个体不同形象主动参与文化重构,其主体性意识逐渐提升,不断加强了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
关键词:华安高山族;文化重构;认同
中图分类号:A1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7)05-0025-07
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频繁进行,有关台湾原住民族的研究成为一个小热点,至今已产生诸多成果。这些原住民族除主要分布于台湾外,仍有一小部分居住在大陆,被统称为“高山族”。大陆高山族因为人口规模小,居住分散,聚居区少,在地化明显,所以较少被学术界所关注。福建华安县是大陆高山族的一个主要聚居地,高山族的人口数量、聚居程度在大陆高山族中均位居前列。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华安高山族中出现了明显的文化重构现象。本文拟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对华安县高山族文化重构的社会背景、详细过程及其后续影响等进行分析,进而尝试从理论的层面加以反思。
一、华安高山族的在地化
据《华安县少数民族族谱》记载,在华安定居的第一代高山族共有9位,他们来此定居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从军及经商。[1]国共内战时期,一些高山族同胞被国民党征召到大陆参战,战败后又加入解放军。解放后,他们多数被安排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厂矿工作,少数因文化程度较低,则主动要求到农村地区务农。闽南地方语言及文化习俗与多数台湾汉人社区近似,所以厦、漳、泉和潮汕一带就成为了他们的定居首选地。在这9位高山族同胞中,林忠富、范金华、严谷长是排湾族,高文贵、黄清发是阿美族,林富是布农族,田大作是卑南族。另有2位女性,刘阿休是阿美族,高玉兰是噶玛兰族。其中,刘阿休与仙都镇赴台经商的汉人陈树烈相识而结成夫妻,抗战时期为躲避战祸,携子女回到大陆。从第一代高山族迁移至华安定居距今已近70年,而在早期的数十年中,华安高山族经历了一个文化认同的在地化过程。
台湾原住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多以狩猎、采集为主,兼及小米种植,而华安高山族及其后代的生计方式多种多样,但就是没有狩猎和采集,也不种植小米。一方面,第一代高山族退伍老兵被分配到华安等地,部分进入政府部门工作,退休后都有政府给予的离退休津贴;另一方面,华安境内虽山峦叠嶂,但大型河流稀少,人们多生活在平原地区,以务农为主,主要种植水稻、甘蔗等农作物。尽管如此,第一代高山族中仍保有少量原住民山地生活技能的痕迹。据陈树烈的后代CYB回忆:“在家里,我伯父陈龙福会做(鱼篓),(他)有教我做,(鱼篓的样式)跟现在的差不多,因为靠近河边(还能够用这种方式抓鱼)。也有捕鸟,是用鸟吊吊,带一点鱼(做诱饵)。(我们)用一块石板,然后弄成一个小灶,把鱼放在上面煎。”高山族后代多为个体户,或经商、务农、行医、外出打工、教学等等,其中务农人口最多。
台湾原住民各族群多有宗教信仰及圖腾崇拜,据说阿美族的刘阿休就曾保留有一张蛇图腾。其后代回忆,此图腾由刘氏从台湾带到大陆,之后被全家奉为民族圣物。每年丰年祭时节,全家人都跪拜在图腾下,口念民族吉祥语,以示慎敬,并祈赐子孙好德行善,能读书,会做事。[2]该图腾毁于“文革”, 此后图腾信仰也逐渐淡化。现在,高山族家庭中既无图腾,也无严格的信仰禁忌。因闽南地区居民多信奉民间神祇,受其影响,高山族后代中也以民间信仰为主,如土地公、妈祖、保生大帝等。他们也过清明节,但各个家族的扫墓时间不尽相同,分为清明和冬至两个时段。高氏家族在先辈的忌日也举办祭祀活动。
台湾原住民各族群语言差异较大,相互间难以沟通。第一代高山族在华安定居后,因生产生活需要,习得闽南话与普通话。只有在以民族代表身份出席各级人大会和政协会时,或小范围的聚会中,他们才会使用本族群语言交流。这些高山族当年生活在台湾时,正值日本统治台湾,并在高山族地区强制推行日语教育,所以多数人都会使用日语。相聚时,他们偶尔也会用日语交流。据后代回忆,改革开放后,每逢过年过节,高山族老兵都会邀约在一起,到彼此家中串门,其中还包括一位定居在华安县良村乡的日本人。他们聚集在一起,举杯换盏,喝完酒就开始跳舞,拼命地跳,边跳边唱,激动时还会禁不住落泪。
在“文革”期间,不少高山族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他们被视为特务、“反革命”,当众遭受殴打,并被挂上各种屈辱性牌子游街示众,有的还被抓去批斗、进学习班等。某些个人因为担心受到官方、地方人群的迫害,甚至偷偷更改民族身份,只字不提与本民族相关的任何文化信息,其民族文化在代际间的濡化也被迫中断,民族性被迫隐匿于当地汉人社会之中。学者陈建樾在调查河南邓州的“台湾村”时,也曾经发现类似的现象,他对这种族性的隐匿做出了解释:“对于一个移入异质社会文化的弱小族群而言,它首先要面对的不是族性的张扬,而是族性的隐匿。惟有融入主流社会,并获得有效的发展空间,它才有可能开始逐渐回味、展示乃至张扬那些曾经因生存需要而被主动藏匿起来的群体文化特征”。[3]尤其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之下,表明自身的高山族民族身份已然威胁到个人的基本生存,对主流社会的政治形态及主流族群的恐惧迫使高山族将标示本族身份的任何信息隐匿起来。在此期间,因为两岸关系紧张,华安高山族与台湾亲属间的联络也被迫中断。因此之故,第二、三代的高山族除了知道自己的家族来源外,对于本民族的族语、风俗习惯、仪式禁忌、宗教信仰等均知之甚少。
在地化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高山族后代身上的民族文化表征已所剩无几。他们多交叉使用闽南话和普通话,根本不会讲各自的族语,甚至也不会听,生活方式已与当地汉人无异。据华安县民宗局统计,2016年户籍保留在华安县的高山族共45户,141人,而实际在地居住的人口不到其中一半,主要分布在仙都镇和县城的华丰镇。仙都镇的仙都村、送坑村、大地村、云山村、下林村等多个行政村,几乎每个村都只有一两户。因为高山族人口本来就少,又散居在各个村落,加上通婚对象又都是汉族,所以代际间的文化传承缺失,高山族的文化表征逐渐消失。
正因为如此,所以到了20世紀90年代,高山族的文化传统基本仅留存在他们的口述和传说之中,只是凭借历史记忆和血缘纽带,维系脆弱的高山族族群认同。然而,族群认同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首先,文化是族群认同的基础和天然边界;其次,历史记忆为族群认同提供了合法性,并且必要时可以成为认同本身的组成部分;再次,文化和历史记忆都会接受社会因素的改造。[4]本来,高山族的历史记忆出现了模糊,文化传承也已中断,再往前发展,其文化就可能逐步消失,族群认同也会随之消解。但幸运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随着两岸高山族来往互动的日益增多,这种残存的历史记忆非但未能消失,反倒和对家族来源的认知一起,被“改造”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华安高山族开展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重构的基础。
二、高山族文化重构的社会背景
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社会大环境逐渐改变,为华安高山族拓展生存空间进而开展文化重构提供了契机。具体而言,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的扶持、对台交流的开展、媒体的宣传报道等等,在扩大华安高山族的社会文化影响,提升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同时,也促成了高山族文化的重构。
在国家政策方面,为了保障少数民族享有民族平等权利,尊重少数民族成员正确表达本人民族成分的自由,1981年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份的处理原则通知》,提出:“凡属少数民族,无论其在何时出于何种原因未能正确表达本人的民族成份,而申请恢复其何种成份的,都应当予以恢复。” [5]在此背景下,一些高山族又陆续将户籍上的“汉族”身份改成“高山族”,其民族认同感得以逐渐复苏。1987年,台湾解除了持续38年之久的“戒严令”,大陆放宽台湾居民以探亲名义到中国大陆,两岸民间交流渐见繁忙。由于福建和台湾只有一水之隔,地缘关系使很多台湾人到福建探望被分隔多年的宗亲。1991年,年近七旬的林忠富几经周转,也踏上了台湾探亲之旅,并在朋友的帮助下,与台湾亲人相认。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大陆与台湾实现了“三通”,閩台高山族亲人间的联系更趋热络,华安高山族的民族身份也日益突显。这些变化的发生,都与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密不可分。
以国家的政策为依托,地方政府也对高山族进行多方面的扶持。20世纪90年代,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部分高山族开始办理回台定居或探亲手续等。进入21世纪,地方政府开始关注每户高山族家庭的生计生产,包括帮扶修建新居、开办印刷厂、经营餐厅等。茶叶经济是华安县的重要产业之一,诸多高山族家庭投入到茶叶种植生产中,地方政府则帮助他们添置制茶机械、开办茶园、购买门店经营茶叶等。2010年,华安县设立“民族团结进步创业基地”,并在该基地成立高山族首家茶叶合作社——山海茶叶专业合作社,注册“山胞”牌铁观音商标。2011年,合作社又与台湾原住民合作,在仙都镇市后村建立“海峡两岸(福建华安)少数民族生态茶叶基地”,共同开发建设300亩“海峡两岸(福建·华安)少数民族生态茶叶基地”项目。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国家实施“扶持到户”政策,华安高山族每户每年获得补贴3000元。仙都镇送坑村、大地村、市后村、云山村、下林村,和华丰镇大燕村、沙建镇沙建村等7个村,被国家民委列入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享受整村推进的优惠政策。在文化方面,地方政府重点发掘高山族文化,组建高山族舞蹈队,并在当地举办各类文化展演活动,邀请高山族队伍参加演出。同时鼓励高山族舞蹈“走出去”,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茶叶博览会等活动,不断提升华安高山族的知名度,并着力将其打造为华安地方重大特色之一。地方政府的这些帮扶举措,使高山族同胞获得了经济上的实惠,感受到民族身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也无形中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两岸关系缓和之后,华安高山族的对台交流互动出现了更多的形式,从探亲访友、经贸交流到文化展演、参观考察,两岸高山族人往来愈发频繁。其中,文化展演是华安高山族最经常参与的一项活动,展演以舞蹈为主。华安高山族曾多次参加两岸共同举办的“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丰收节”活动,地点或在大陆,或在台湾。地方政府还组织高山族专程赴台开展考察、交流。2014年,华安县政府组织乡镇对接交流团等5个团组赴台,走访多个台湾原住民部落,切身感受他们的生存状态,并参与他们的仪式活动,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祭典节庆、风俗习惯等,将之前对原住民的文化想象转变为贴近现实的文化认知。台湾原住民有时也会组织到华安参观交流。2016年,在全国台联的组织下,由台湾原住民多位部落长老及原住民舞蹈教员组成的台湾考察团,到仙都镇送坑村参观。华安高山族为考察团展示了本地的高山族舞蹈,之后双方又围坐在华安高山族家中,举行非正式的茶话会。
出于对台工作的需要,新闻媒体对高山族的宣传报道也逐渐增多。漳州市电视台、天津电视台、福建日报等多家媒体都曾对高山族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做出报道。如福建日报于2016年5月6日9版视点刊登《高山常青 涧水常蓝——华安县传承和发展高山族文化》,对高山族舞蹈的发展及挑战进行详细报道。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恰逢天津交响乐团到华安土楼演出新年音乐会。演出前夕,几位交响乐团的演奏家在媒体与当地组织单位的安排下前往高山族家庭进行慰问,高山族人严丽贞与高燕均穿着他们特有的民族服饰,接待到访人员。在随后的音乐会中,主办方也邀请这几位高山族代表出席观看演出。中场休息时,高山族同胞接受了多家媒体记者采访。新闻媒体作为对外宣传的主渠道,在引导社会大众对高山族及其文化认知的同时,也在不断形塑华安高山族的社会文化。
高山族的民族认同意识也在文化实践中不断增强。在政府的组织和鼓励下,他们积极参与各类文化活动,活跃于文化舞台上。通过参与活动,他们深切地感受到高山族的生存和发展受国家与地方社会重视,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他们不仅认同自身的民族身份,而且开始注重个人及本民族利益诉求的表达,为高山族争取更多的权益。其个体主动性不断增强,从而使得其族性由之前的隐匿转变为现在的积极主动显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群体以民族身份(小集体)融入地方社会(大集体)并获得话语权,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在上述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本已明显在地化的高山族,透过身份认同、文化想象与主体表达,开启了文化重构的社会历程。
三、高山族文化重构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开始,华安高山族的文化重构逐步推进。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高山族对自己的民族身份逐渐认同。他们开始以高山族的身份,参与各种文化实践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高山族舞蹈表演,既有外出的参赛和演出,也有在本地的排练和展演。服饰也因各类演出要求的不同,呈现出差异化的样式,且不同时期互有变化,近年来则渐趋定型。20世纪后,因旅游业在地方社会收入中的比重增加,地方政府尝试从旅游的视角,进一步发掘高山族的文化资源,并通过对高山族社区空间的改造,吸引海内外游客,以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各种高山族文化元素不断被想象与表达,整合到高山族社会文化中,从而塑造出一种新的“融合型”高山族文化。
1.舞蹈的引进
舞蹈是华安高山族文化的显性标志之一。他们开始接触舞蹈,除了第一代高山族青少年時期在台湾社会的生活实践外,则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深圳的特殊经历。深圳的“锦绣中华民俗村”是我国第一个荟萃各族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和民居建筑于一园的大型文化游览区。因为华安县聚居有较多的高山族人口,所以该景区负责人于1991年底亲自到华安,招募了一批高山族同胞,前往民俗村表演高山族舞蹈及其他技艺。1992年初,在第一代高山族林忠富、高文贵的带领下,他们组团前往深圳。同行的12人中,有9位是高山族,3位是汉族。因为多数人都没有舞蹈功底,所以景区聘请专人对他们进行培训。景区还给他们免费发放高山族服饰,其样式以阿美族和排湾族的服饰为主。这些服饰连同他们在景区习得的舞蹈及手工技艺,后来都被带回华安,成为高山族文化构建的早期元素。
至1997年底,这批前往深圳参加表演队的成员都相继回到华安,分别进入不同行业工作,但基本都与舞蹈无关。不过,因为在深圳民俗村的经历,他们成为高山族文化重构初期最主要的一股力量。90年代末至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届,当地政府都会组建一支高山族代表隊参赛,而且每届都获得奖项。运动会召开前夕,所有参赛队员都要暂停各自手头的工作,前往集训地接受封闭式训练。地方政府会聘请当地经验丰富的教师,为高山族队员编排舞蹈,并指导技巧性项目的训练,最终以舞蹈表演和体育项目(抛陀螺)参赛。1999年第一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时,高山族代表队的参赛主力就是赴深圳民俗村表演的成员。他们表演的舞蹈及穿着的高山族服饰,均主要源自民俗村。
高山族居住较为分散,且当地交通不便,这使得他们相互间平时联系较少,大部分族人都互不熟悉。运动会的定期举办,使高山族队员打破了村落的地域限制,建立起人员往来的常态机制,彼此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增加,共同的民族身份认同感也随之增强。以高山族的名义参赛,让本族人直接参与其中,也在不断形塑族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主观认知。在比赛中,为了替团队及所代表的高山族争取好的名次,队员们团结协作,也在无形中凝聚了他们对本民族的向心力。而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又令他们增强了本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通过参加少数民族运动会,高山族同胞逐渐建立起对本民族及其文化的认同。
除外出参加全国性运动会外,华安高山族也参与当地的诸多活动,如商业演出、高山族广场舞表演赛、华安县新年团拜会、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丰收节等。这些演出活动对参演人员的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也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组织。从90年代至今,华安当地已陆续成立多支舞蹈队,其中既有官方筹办的,也有私人组建的,每支队伍中都同时有高山族成员和汉族成员。舞蹈队有专门的指导者,主要来自当地富有经验的舞蹈教师。他们负责对舞蹈的曲目、动作、音乐以及服饰等进行编排,借鉴之前或其他舞蹈队的经验,再结合新发现的视频资料加以整合。此外,因为华安高山族曾多次往来台湾开展交流,所以也有机会从台湾购买原住民族舞蹈的影像资料,带回来观摩后再加以消化吸收,这也使得不同的舞蹈队各有其不同的特色。
2.服饰的采借
民族服饰是彰显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其样式、色彩、材质、配饰等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在华安高山族中,服饰成为区别高山族与闽南人的重要标志。
如今,华安高山族每人都至少有一套高山族服饰,但这些服饰在样式、色彩、材质上略有不同,其原因是获得服饰的途径不一。一些人是当年从深圳民俗村带回的服饰,少数人是在返台探亲时亲友所馈赠的服饰。例如,林忠富从台湾所带回的排湾族服饰,上面布满由琉璃珠编缀而成的百步蛇蛇腹、蛇肋、蛇背及陶罐、人头纹、勇士等图案,对襟圆领背心形短褂,下身系绣有百步蛇蛇腹纹的后敞裤,并配有野猪獠牙头冠。也有人是请当地的裁缝,参照别人的服饰,再结合网络图像资料制作。多数人的服饰是参加运动会或加入舞蹈队后,由组织者统一订制和分发的。最晚近的应该是送坑村表演队的服饰,于2016年表演队成立时才制作,由政府出资,一套花费700多元。这套服饰与2011年高山族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时大体相同,差别只在头饰上做了少许改变。女性的羽冠右上方插有一束彩色羽毛,男性的头饰改为头冠且比女性的小,头冠顶上倒插五六根褐色长羽毛,上沿和下沿绣有各色绒球。头冠后面用黑色弹力带缝紧,以防表演时掉落。长袖蓝色上衣改为五分袖短上衣,饰以白边,右肩斜跨一只与女性相同的红色槟榔袋。服饰属夏装,若是在冬季演出,女性需在短袖里面再穿一件黑色打底衣,下身穿上黑色打底裤后再穿围裙,而男性则是在穿上日常裤子后,再系上无背绑腿裤。
华安高山族服饰的主要功能是舞蹈表演,因此在设计与制作上注重轻盈美观,以便实现较好的舞台效果。但是,他们的服饰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及人们审美观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在参与每届少数民族运动会之前,当地的组织者都会要求高山族的表演项目要有所创新,无论是舞蹈还是服饰,都必须不断改进,由此也促成了高山族服饰的革新。目前他们的服饰样式多以阿美族的服饰为主,部分吸收排湾族的服饰元素。一方面,阿美族能歌善舞的民族特征更符合华安高山族舞蹈的表达诉求,其服饰更能满足舞台效果;另一方面,华安高山族后代中阿美族人口居多,排湾族其次,主要采借阿美族服饰再结合排湾族服饰的元素,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除了舞蹈表演,高山族服饰也出现在其他一些重要场合,如参加各级会议、出席重要庆典、接受媒体采访等。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着装与当地汉人完全相同。对部分高山族而言,只有在特定的场合穿着本民族的服饰,才能显示出他们民族身份的特殊性。但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穿着本民族的服饰,则会被人视作是另类的行为。这种思想观念缘于他们长期处在汉人社会中,并且在生活实践中已经完全在地化。换言之,在华安高山族社会中,民族服饰已失去了实用性,仅仅是特殊情境下的一种象征符号。
3.社区空间的改造
近年来,为了因应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当地政府尝试通过改造民族社区空间的方式,将高山族的居住空间与旅游空间融合起来,以此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21世纪初,华安县就先后投入400多万元资金,在距离县城主城区不远处的“竹种园”旁,建成了面积500多平方米的高山族舞蹈表演场地和高山族民俗风情园,园内建有工作室、起居室、表演厅、瞭望塔、餐厅等,并聘请高山族在专门的场地上表演舞蹈。当时,华安县政府曾计划将县里的高山族全部集中起来,在风情园附近选择一块居住用地,将他们安置于此。但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该计划束之高阁。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华安县所属的漳州市政府响应中央号召,于2006年推出《漳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五年规划》,为该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指导,并先后评选出4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为他们提供资金扶持。在此背景下,华安县高山族文化建设再次被列入当地的旅游规划。其中,仙都镇送坑村因为毗邻福建地方特色建筑——二宜楼[6],而被授予“漳州市第四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2012年12月,作为全国高山族的一个试点,送坑村规划建设高山族特色民族村寨,总投资2000万元,计划建设19幢34户高山族特色民居、停车场、生态公厕、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高山族文化博览园、风情表演会所、风情广场、风情小街区、特色村寨山门、观景台、瞭望塔等,建成后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大地土楼群”(涵盖二宜楼)的景区旅游配套项目。至2017年初,社区内已建设完成高山族演艺舞台,其他基础设施仍在紧张修建之中。在此基础上,在地高山族联合附近部分汉族人士,组建送坑村高山族舞蹈队。舞蹈队挂靠送坑村委会,并利用广场及舞台进行舞蹈排练和演出。2016年舞蹈队成立至今,已在当地进行多场高山族舞蹈演出。
已建成的高山族演艺舞台占地面积300平方米,由专业设计院规划设计。设计过程中,曾委派专人到台湾的九族文化村实地取材,在此基础上对高山族文化进行适当的想象与整合,采借其中的一些文化元素,再通过社区空间的改造加以展示。演艺舞台顶部采用与闽南古厝屋顶相似的斜坡设计,上面加盖褐色木板。正面顶端悬挂橙色兽面图腾,图腾下方分布“高山族演艺舞台”字样,舞台背景主体为排湾族百步蛇图腾。舞台前方有一延伸平台,顺着平台两侧的台阶可走下舞台,台阶两旁则饰以半包围状的竹栅栏。平台前端两侧是深色的人形图腾柱,据说是阿美族的图腾标识,图腾脸部五官、头饰及手脚部分关节都被刷上红白相间的颜料。舞台前方是广场,广场地面的各色地砖呈现出不同造型,正中心是由黄褐色地砖铺成的百步蛇造型,与舞台背景上的图案基本一致。舞台周边是高山族住屋,主体采用框架结构,柱子用自然的石材装饰,屋顶类似中国古代的九脊顶,整体的风格为中西合璧,住户可根据需要修建两层或三层的楼房。
社区空间改造后,部分高山族人生活在具有本民族色彩的空间里,日复一日接触本民族的文化元素,族人的民族认同感不断得到强化。
4.个体的想象与实践
以上文化重构实践多为高山族普遍参与,虽然背后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意志和力量,但其中也融入了高山族个体对本民族文化的想象与塑造。例如,2017年刚当选为市人大代表的高山族同胞王雅琼,有感于目前华安高山族仅以舞蹈和服饰作为其民族文化展示的主要内容,向市人大提交建设高山族博物馆的提案,意在推广高山族文化,丰富民众对高山族文化的认知,并深化族人对高山族文化的了解。也有高山族同胞在自家茶园修建“台湾岛”,通过开发具有高山族特色的旅游休闲农庄,来增加个人经济收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少高山族同胞有意識地利用高山族文化元素,作为个体经营中的亮点,无形中对高山族文化起到了宣传和推广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自我对本民族文化的参与感与认同感。
民族及其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民族中个体的努力,个体也通过对本民族的归属与认同获取更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资源,并透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渠道,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阿伯乐·库恩认为,人是双向度的,既是象征的人,也是政治的人。[7]153并且,族群认同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经济、政治现象,族群的形成、变化和发展最终必归结到政治、经济等社会条件的基础上。例如,族群之所以强调传统文化,是因为传统文化能够激发和增强一个族群的政治内聚力。[8]在華安高山族的文化重构中,个人的想象与实践往往不是直接建构高山族文化,而是在国家的大背景下,通过政治、经济等各种不同手段,去重新塑造本民族文化,以间接的方式影响文化重构的进程。
四、结论与思考
从几个人到华安定居,到如今已繁衍三、四代人,华安高山族人口达到了100多人。其间,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华安高山族经历了一个在地化过程,最终融入了闽南地方社会,以致其整体文化表征逐渐消失,族群性湮没于汉人社会之中。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民族政策的落实,高山族的社会地位逐渐提升,其民族身份得以彰显,从过去的被迫“隐匿”逐渐过渡到有意“张扬”。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的扶持、对台交流的开展、媒体的宣传报道等,既扩大了华安高山族的社会影响,提升了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华安高山族的文化资源逐渐被挖掘,并以文化重构的方式向外展示,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经过20多年的努力,华安高山族最终形成了以舞蹈和服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高山族文化,并透过社区空间的改造,进一步拓展民族文化的显示空间。
必须承认,在华安高山族文化的重构过程中,地方政府一直作为主导性力量,扮演着决策者的角色。但是,高山族在其中也并非是完全消极被动的,而是以配合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其中。从早期舞蹈的引进、服饰的采借,到后期民间舞蹈队的创设、社区空间的改造,都离不开华安高山族群体或个人的支持,其中也融入了他们对高山族文化的想象与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安高山族文化的重构是地方政府和高山族群体共同促成的结果。当然,部分汉族民众也有一份功劳。因为高山族人口总量少,所以在整个文化重构过程中,一直就少不了汉族民众的协助,他们充当了高山族文化重构的支持者。
经过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以不同方式的参与,华安高山族文化以一种杂糅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其中既有阿美族文化的元素、排湾族文化的元素,也有当地闽南文化的元素,还有一些甚至是纯属想象与发明的元素。如果从所谓的“文化本真性”来看,华安高山族所重构的文化无疑是失真的,因为首先,以舞蹈和服饰作为高山族文化的主要表现载体,无法涵盖高山族文化的整体;其次,舞蹈和服饰仅仅是一种舞台展示,而非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华安高山族的饮食起居、风俗习惯、民间信仰、价值观念等和当地汉族并无二致;第三,台湾本土的原住民族包含十来个不同族群,其内部的文化差异性极大。即使原封不动地照搬其中某个或某几个族群的文化形式,也不足以代表整个原住民族。
尽管如此,这种文化重构仍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一方面,华安高山族从过去隐匿自己的民族身份,到現在主动配合政府开展文化重构,这种转变本身就体现了国家对高山族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视,以及高山族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借由文化的重构,华安高山族从单纯依靠家族来源、血缘关系及历史记忆维系对本民族的认同,发展至现在能够通过具象的文化形式来展现其民族身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民族主体意识逐渐提升,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不断增强。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民族文化若要实现良性发展,就应该与文化主体紧密结合起来,因为华安高山族才是文化的真正主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赋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激发他们对文化的自觉意识,并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使这种经由重构产生的文化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注 释:
[1]华安县少数民族族谱编委会:《华安县少数民族族谱》,2004年。
[2]施沛琳:《閩南社会下之大陆高山族探析——华安陈姓家族的高山族观察》,《东南学术》,2013年第6期。
[3]张海超:《微观层面上的族群认同及其现代发展》,《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4]陈建樾:《“台湾村”:一个移民村落的建构、想象和认同——河南邓州高山族村落田野调查报告》,《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
[5]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份的处理原则的通知》,(81)民政字第601号,1981年11月28日。
[6]二宜楼于2008年与其他福建土楼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7]董建辉:《政治人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
[8]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责任编辑:刘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