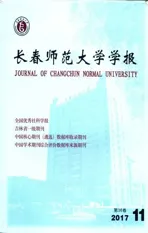加地拉船被劫案析论
2017-03-28张家丽
张家丽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116)
加地拉船被劫案析论
张家丽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116)
1854年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加地拉船被劫案是中美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刑事案件。这一案件的协商和处理前后持续数年,折射出中美早期外交的若干面相。根据《望厦条约》所确立的不赔偿原则,美国就此案件通过正常的外交交涉难以获得赔偿。然而,美国通过战争讹诈、歪曲条约等方式,获得了中方的赔偿。
加地拉船被劫案;中美刑事案件;《望厦条约》;中美关系
1854年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加地拉船被劫案(下文简称为“加案”),是中美近代外交史上重要的刑事案件。这一案件的协商和处理持续数年,折射早期中美外交关系的发展轨迹和演变趋势。学术界关于道咸时期中美外交关系中的刑事案件以及由此带来的修约影响的研究极少,无专文探讨加案①。本文根据南京大学图书馆藏英文本《美国外交公文:美国与中国(1842-1860)》(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842—1860))以及其它中美相关文献,对加案的发生、交涉过程及影响作具体的论述。
一、中美早期有关海盗案件的法律依据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抵达广州,拉开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序幕。此时,美国正值肇建之初,与拥有强大海军力量的英国相比实力相去甚远。故至鸦片战争前,中美之间主要侧重于商业贸易上的友好往来。中国官员与商人视美商“最为恭顺”,美商亦深感“现在和中国人相处得真是再好没有”。[1]海盗问题是影响中美两国贸易发展的重要障碍,美国商船多次遭受其害。1805年8月,美国人多贝尔(Dobell)和比德尔(Biddle)乘坐官艇由澳门往广州的途中被劫[2]8。1809年,美国船“阿塔瓦尔帕号”(Atahualpa)被“一大队海盗小艇”围攻[2]107。这些案件大多不了了之,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清朝水师软弱无能,水师力量过于分散,缺乏熟悉水上作战的官兵,巡哨制度形同虚设,没有强大的战船,且腐败现象丛生[3]。东印度公司委员会对此亦有同感:“这个政府不能说是畏怯,实在是缺乏力量,由于他们可诅咒的轻率,竟然向皇帝隐瞒当前海盗扰乱沿海,这可能是最可怕的情况——如果这种可诅咒的行为长久保持下去,就无法将公款拨充装备一支适当的武装力量,剿灭海盗或将其从沿海赶走,这是显然的。”[2]8在当时以中方为主导的中美关系格局中,美国政府对海盗案件的频发和中方的处置不力虽有不满,但未提出外交抗议。
中美两国海盗问题处理的无序及无法状态随着《望厦条约》的签订而被打破。借助第一次鸦片战争及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之机,美国政府决议任命顾盛(Caleb Cushing)为驻华专使,与中国谈判签约事宜。顾盛、耆英于1844年7月3日签订了《望厦条约》,美国依片面最惠国待遇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有的特权,甚至攫取了更广更深的权益,如在海盗问题上获得了外交协商机制和条约法的判决依据。《望厦条约》第26、27条规定:美国商船在中国内洋被劫,中国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应严拿强盗照例治罪。凡属收缴赃物,经美国领事馆,物归原主。万一正盗不能缉获,或有盗无脏,及起脏不全,中国地方官例有处分,不能赔还赃物。若美国商船在中国洋面触礁搁浅,遇盗致有损坏,或在外洋损坏漂至中国,中国地方官应设法拯救,酌加抚恤。第19条规定:中国地方官应保护美国人在华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在内地放火烧楼抢夺财物的不法匪徒,须严加查办,按例治罪[4]54-56。
《望厦条约》英文本与中文本一致,皆明文规定:中国政府应保护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若遇损害,美国人可以报官。中国政府应迅速缉拿匪徒并按例严惩,给以适当的抚恤,但无赔偿之责任[5]。
中美《望厦条约》所确立的不赔偿原则在两国早期的海盗案件如娄礼华案的交涉处理中得以较好地履行。1847年8月16日,美国传教士娄礼华(Walter Macon Lowrie)与中国仆人和信差乘船从上海前往宁波,途中遭遇海盗抢劫并丧命。中国官府在接到仆人报案后表示将立即查办抓捕海盗,并救济其些许财物。8月29日,美国代理领事贝茨(Bates)就此案照会上海道台咸龄。8月31日,咸龄复照称,他已将此案向上级报告,同时分别悬赏300美元和100美元捉拿主犯及其他海盗。[6]9月13日,美国副使伯驾(Peter Parker)就娄礼华案照会钦差大臣耆英,催促其办案。9月16日,耆英复照称,已咨文浙江巡抚,让其转饬地方官严加查办。11月15日,耆英照会伯驾称,已抓获名叫华坤元的海盗。1848年7月8日,伯驾照会两广总督徐广缙,促其尽快结案。7月11日,徐广缙复照称,曹四老大等多名海盗已被抓获,正在接受审讯。9月22日,徐广缙照会伯驾称,抓捕到的9名海盗已被定罪,其中曹四老大、华坤元和张苏春被判斩首示众,其余6人被判流放新疆。刑部已核准,等待皇上勾决。[7]此案终算了结。从娄礼华案的交涉始末可见,这一时期中美两国官员遵从《望厦条约》精神,对涉及海盗案件的条约并无歧义。中方官员在接到报案后及时处理,捉拿海盗,按例严惩。美方官员恪守职责,敦促中方办案,并无要求赔偿等逾越条约的行径。
二、加地拉船被劫原委及中美初次交涉
1854年中美两国对加案的交涉处理,使双方在海盗案件上首次打破《望厦条约》的精神,促发了重要的外交后果。
1854年10月5日,智利船加地拉由船长鲁尼(Matthew Rooney)率领从香港出发前往旧金山。船上附搭贵重货物,约值价银十万圆[8]211,尽归美国承保会承保。此船向东行驶,当夜遭遇飓风,致船体损坏严重,须觅处遮障。10月7日,此船至高蘭猪牯尾海岛(the islands of Koolan and Choo-koo-me)地面浮动抛锚。船员修整船只时,海盗从舢板上向其投掷臭罐和易燃材料,对其进行占领并抢夺财物。10月9日天亮时,大帮海盗船驶来,将船上之物尽皆抢去,所存只有石块及些微食物,晚上八点离开。之后,其他海盗又占领此船,拆毁船舱,撬烂船面,将剩余伙食、乘客水手的行李和船上器具等物抢去,不许船员下船,且放火烧船,幸得及时救灭。其后,又有一批海盗船驶来,“将前各帮取剩之物擕去,撬取铜片,拆毁船胁各木,以致该船全被毁拆无余。”[8]213
案发后,船长鲁尼设法到达澳门,“方到之时,即达知该处官宪,但不得帮助,随往香港”[8]213。10月13日,鲁尼抵达香港,随即呈明官宪,并雇佣客船“玛丽伍德女士”号(Lady Mary Wood)前往事发地点,“但见该船已被烧毁沉溺,以致尽皆毁烂无存。”[8]213同行的“斯巴达”(Spartan)号在附近村庄觅得装有茶叶和糖的包装袋,其上载有与加地拉船有关的名字和记号[9]28。10月16日,“玛丽伍德女士”号返港,将所发生之事禀告美国驻华官员。同日,美国驻粤副领事斯普纳(Spooner)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告知此案,并要求派兵助剿海盗。19日,叶名琛复照称:将严惩这批海盗,且已饬令事发地所属新宁县地方官展开调查。[9]31中方于11月11日派两艘战船抵达香港,与英、美、葡三国联合组成远征军,于次日前往事发地,预剿灭海盗并夺回财物。此后,远征军在高蘭岛上寻得了船上载运的茶叶、属于船体的金属片和经过船长鲁尼确认的其他货物[9]41,但终因距案发时间许久,所得之物价值不大,遂未将其带走。
根据《望厦条约》第26条款,中国政府对海盗应按例严惩,此例指《大清律例》。《大清律例》强盗律文第二条规定:“其江洋行劫大盗,俱照此例立斩枭示”[10]。然而,此案中的一支海盗队被清政府地方官员借机招安,使其非但没有被立斩枭示,反而逃脱了联合军队的剿灭。美国军人和承保商人对地方官员的这种做法深感不满,进而要求中国政府赔偿损失。他们致函美国驻华全权专员麦莲(Robert Milligan McLane),控诉中国地方官员纵容海盗,使其数量在过去四年里愈发众多;在此案中始则与海盗勾结,未将被劫货物在附近村庄发现一事上报,继则在四国联合行动中一再迁延,使海盗趁机转移赃物,甚至招安部分海盗[9]35。他们要求赔偿的主要依据是美国外交官顾盛对《望厦条约》的解释。在就《望厦条约》进行谈判时,美方曾试图就条约第19条引入赔偿原则,然在中方官员要求加税的抵制下终未得逞。原草约为“假如无赖、暴徒焚烧美国公民的房子,或者伤及他们的人身,应赔偿所遭受的损失,中国的高级官员有责任过问此事,并负责赔偿损失。”顾盛公使方面力持“居住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应该受到保护,如果由于政府的疏忽使他们遭受损害,中国政府理应负有责任。这个原则在1842年已被认可,并作了赔偿。”②这一赔偿要求遭到中方官员强烈反对,“黄阁下(黄恩彤)承认远道而来的人民应该受到保护……但不能赔偿……潘仕成建议从每担茶叶中收取附加税七两,政府就能承担这一责任。”[11]因此,据本条款及中美《海关税则》③,美方最终同意中国政府不予赔偿。
在《望厦条约》签订后,顾盛致函当时美国国务卿约翰·尼尔森(John Nelson),将《望厦条约》划分为16条并加以自己的解释,其中第9、11条对应《望厦条约》第19条和第26、27条。第9条大意为:中国政府必须保护生活在这里的美国公民不受侮辱和伤害。如果没有履行这一职责,理应接受美国政府的控诉,并为所有的后果负责。第11条大意为:中国政府要设法保护和救济在中国洋面搁浅或因不可抗拒原因进入中国口岸的船只,并且需要追回(restitution)在中国洋面被海盗抢劫的财产[9]13。顾盛在提到“追回”时用了restitution一词,在英文语境中有两个解释:一是归还原主,二是指金钱方面的赔偿④。但不管是何种含义,都只能代表顾盛个人的意见,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换言之,美国商人的赔偿要求缺乏条约法的法律依据,在中美两国正常的外交协商中很难得到通过。1854年10月16日,驻粤副领事斯普纳照会叶名琛,要求中国政府对加案损失赔偿时[9]29-30,被后者以《望厦条约》的明文规定加以拒绝。对此结果,美国使臣麦莲表示谅解。他在11月27日复函美国商人时称:据《望厦条约》第26条款,“没有依据中国政府需要赔偿”[9]9。他希望受害者获得赔偿,但首要责任是将此案的法律解释如实告知,而非轻率鲁莽地交涉,如此才尊重中国政府。他会将此案汇报回国,等待指示。不久,麦莲因患疟疾而离开中国。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美交涉
美国对加案的赔偿要求在正常的外交谈判中无法实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则使本没有法律依据的无理要求有了实现的可能。美国伙同英法对中国进行外交、战争讹诈的重要表现就是新任驻华使臣伯驾的上台。
伯驾(Peter Parker)是美国马萨诸塞州人,于1834年作为传教士来华,随后在广州设立眼科医院,因医术高明在当地颇有威望。他于1844年担任顾盛的翻译官,参与《望厦条约》谈判,次年担任新设美国使馆的秘书兼翻译官,此后十年间未曾中断对华交涉事务。因伯驾具有丰富的对华外交经验,美国政府赋予其与中国修约的重任。1855年9月,伯驾正式被任命为使华外交委员。十余年的对华外交经验使其认识到古老的天朝只有在船坚炮利之下才肯屈服,增派美国驻华海军是修约不可或缺的条件。为达到修约目的,他甚至在给国务卿马西的报告中建议使用最后手段,即占领台湾。[12]
伯驾将加案与修约联系起来,着手歪曲《望厦条约》,尝试扩大法律特权。1855年12月3日,美国人吉定(Cutting)代纽约及波士顿承保会各商禀呈伯驾,请其代为向中国政府索赔因加案而损失的10万美元⑤。伯驾复函称:中国政府对此案损失的赔偿,洵属必然,他将尽快与两广总督交涉。但因美国在华海军力量薄弱,所以对能否获得赔偿并无把握。[9]531856年3月31日,伯驾照会叶名琛,称:“着将本国民人所列智利国加地拉船一案,请中国国家办理,照该民人所失讨取银两赔偿……不得籍端托故久延等因。”[8]211为避开条约第26条“中国地方官例有处分,不能赔还赃物”,伯驾竟狡辩:“奈因该船加地拉之事,如果系在海面遇盗,照该条款所载,即毋庸议及。但却不然,该船被劫,并非在洋面,乃在新宁县属界内中国官员治下之所,足能捕获盗贼,追出赃物。按照公义,中国国家必须偿还所失者,系因不肯沾手办理之故。加以第二十七款条约所载,确然特为似加地拉之案,倘果遵行,即无可告与夫讨取赔偿之事,但因该条款未有遵行,是以中国国家必任其事。”[8]211伯驾要求赔偿的解释颇为牵强。首先,加案的发生地即使并非在海面,而是在新宁县官员治下之所,也只能影响到中国官员的办案力度和从海盗手中追回损失的程度。其次,叶名琛等官员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加案的前期调查、围剿海盗等,谈不上“不肯沾手办理”。即使伯驾的指控属实,那也只涉及中国官员的失职责任。根据《望厦条约》,无论依据案发地还是对中国官员的失职指控,皆不能导出中国政府代为赔偿美国商人损失的法律解释。
叶名琛因忙于应付英、法、美的修约要求,并未复照伯驾。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疲于应战,此案暂被搁置。随着战事的推进,清政府接连战败。美国以此为契机,利用清政府的畏战心理,加紧扩大对华的条约权利,以攫取更多的利益,其重要体现便是将加案的赔偿要求从外交官个人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1857年11月,美国首任驻华全权公使列卫廉来华谈判修约事宜。国务卿卡斯(Lewis Cass)在给他的训令中,“要求中国遵守条约保障在华美国公民生命财产,并偿付其损失”[13]。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在给麦莲、伯驾等外交官的训令中,均未涉及美国商人的财产损失和赔偿问题⑥。
1858年5月8日,列卫廉向直隶总督谭廷襄递交了酌定条款11条,其中包括“合众国人控讦中国国家讨取赔偿各款。或因妄行监禁。或因抢夺破坏船只货物。或被焚毁房屋行栈。或被匪劫。与夫地方官员经涉之事,多有久历年所。屡经照知两广总督部堂。总皆未蒙清结。此时必要立行伸理。倘朝廷肯派专员自当将一切所控证据呈验。并将为数若干逐一列明,约银不过六十万两之则耳。”[14]次日,谭廷襄将美使递交的酌定条款上奏。当日,咸丰帝发布上谕:“其赔偿银两一条,该国被劫被焚船货等物,均应于失事之时,遵照合约所载办理,为日既久,岂能逐款清理。况如前年被英夷放火所烧货物,岂能向中国清理,亦应驳斥。”[15]16255月13日,谭廷襄照会列卫廉,按旨意拒绝赔偿。5月20日,英、法以清政府未派“全权大臣”为由,占领大沽炮台,继而向天津进军,美国使节亦随同赴津。咸丰帝因清军败绩,只得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授予“便宜行事”,前往天津海口谈判。6月7日,中美双方进行了首次谈判。桂良对美方的态度甚为不满,在奏折中称:“讵该夷语言傲慢,借英夷为恐吓。坐间将要求各款。哓哓置办。所开款目。亦较谭廷襄所议者加增过多。”[15]1880-1881照例对赔偿一款未曾允准。
此时,咸丰帝及相关官员尚能依据《望厦条约》对美方提出的无理赔偿要求予以拒绝。但随着战争、外交事态的演变,咸丰帝的态度有所动摇。1858年6月12日,咸丰帝在给桂良等人的上谕中称:“如与中国无甚伤碍。另有可令该夷获利之处。仅可酌量饵之。以免他患。如桂良等去时所定条款内。有咪夷所求五六十万。未曾允准。如必恳求。即照从前上海免税之例。俟广东开市后。酌免按月税银。此条可以饵咪夷。”[15]1913-1914所谓“他患”,主要是指“公使驻京”。咸丰帝不愿“因小失大”,故同意美方索赔之款。而列卫廉则宁愿“将赔偿一款删去,暂为宽缓”[8]299,以换得咸丰帝一再抵制的“公使驻京”权利。最终,双方均作出让步,美国获得了“公使驻京”最惠国待遇⑦,而赔偿一款却未写入《天津条约》。
随着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的签订,中美两国有关美国在华商民损失索赔的交涉再次启动。按照中英《天津条约专条》、中法《和约章程补遗》的规定,中国政府需赔偿英国白银四百万两,赔偿法国白银二百万两。基于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列卫廉于6月23日照会桂良:“务要将本国控告赔偿之款,与英法国一体商酌办理,并要定立确据。”桂良于6月25日复照称:“今大清国大皇帝已知大合众国当粤省动兵,各事毫无沾插,自应准其民人照别国一样办理,是以情愿将大合众国商民所控六十万两赔偿之款,于通商各港内,归于广州、福州、上海三港,按每年所收船钞及出入口税饷,以五分之一扣抵,以为赔偿。”[8]303列卫廉对此办法并未满意,在上海谈判时与桂良重新磋商,建议由上述“三港海关银号立行发给银票,照数分摊,则广东居其半,上海三份之一,而福州只六份之一。”[8]312如照此行,愿将赔款减为52.5万两。桂良等人经核查后,主张减为50万两,由广东承担30万两,上海、福州各承担10万两。11月8日,中美签订了《赔偿美商民损失专约》,共计50万两,合735238.97美元[16]281,其中包括加案损失的10万美元以及船长鲁尼个人损失4750美元。[16]283至此,中美两国交涉数十年的赔偿问题终告解决。
11月29日,列卫廉将专约签订一事报告了美国总统布坎南(James Buchanan),并推荐宁波领事朴莱德(Charles W. Bradley)和香港领事罗伯茨(Oliver E. Roberts)组成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美国商民索赔的实际数目。列卫廉认为“加案乃纽约承保会要求赔偿,在美国提供的证据毫无疑问,所以这项赔款最容易操作。”[16]289其卸任回国后,由华若翰(John Eliott.Ward)接任。1859年5月5日,国务卿卡斯在给华若翰的训令中称:根据《望厦条约》第26、27款规定,中国政府应该针对加地拉船被劫采取措施,但并没有这么做,所以受损失的美国承保会有权利要求赔偿[9]59-62。华若翰来华后,就加案赔偿一事与朴莱德和罗伯茨进行了沟通。11月,委员会在澳门听取了索赔之人的申述,通过了因加案而请求赔偿的104750美元。
四、结语
1854年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加地拉船被劫案是一桩涉及金额较大的中美刑事案件,双方对案件的处理轨迹折射出早期中美外交的诸多特征。清政府之所以向美方赔偿加案造成的损失,除了因其恐惧列强的武力威胁之外,还源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清朝官员对加案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案件的处理中存在疏失,给了美方索赔的借口。另一方面,清政府缺乏近代外交观念,在拒绝公使驻京和拒绝无理赔偿的抉择上重前者而轻后者。咸丰帝认为,施与“恩惠”便可使贪图小利的美国放弃公使进京的要求。美国在利用加案扩张其条约权利时,多藏匿于英、法的背后,巧妙地借助英、法之武力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益⑧。美国为博得清政府的好感,甚至愿作调解之人,中美《天津条约》第一条便规定“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4]90。
[注释]
①参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吴孟雪:《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1842年,美国海军副少将加尼以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炮击一艘美国商船,造成舍理之死和数人受伤以及清军拘留并重伤五个美国商人等事件为借口要求赔偿,最终取得了约25万元的赔偿金。此赔款与本案无可比拟。参见(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79页。
③清政府并未收取美国每担七两的茶叶出口附加税。参见王铁崖编著:《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页。
④“追回”在英文本《望厦条约》中对应的词为“recover”,指重新获得。参见:Jules Davids, ed.,AmericanDiplomaticandPublicPapers:theUnitedStatesandChina(1842—1860) , Vol.2, Wilmington 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73,p.126.
⑤中文翻译文件来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8年版,第213页。英文文件来自Jules Davids, ed.,AmericanDiplomaticandPublicPapers:theUnitedStatesandChina(1842—1860) , Vol.11, Wilmington 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73,pp.50-52.
⑥美国政府在给麦莲的训令中,要求其协助英国进行修约谈判,从而使美国在两年后依据“最惠国待遇”得到相同的利益。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给伯驾的训令为:(一)准许外交官员驻扎北京;(二)无限制扩大贸易的范围;(三)取消一切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参见(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42页。
⑦“嗣后无论何时,倘中华大皇帝情愿与别国,或立约,或为别故,允准与众友国钦差前往京师,到彼居住,或久或暂,即毋庸在再行计议特许,应准大合众国钦差一律招办,同沾此典。”王铁崖编著:《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0页。
⑧中美《天津条约》第13条将《望厦条约》第26、27条加以融合,在此基础上添加:“……倘若地方官通盗沾染,一经证明,行文大宪奏明,严行治罪,将该员家产查抄抵偿。”王铁崖编著:《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2页。
[1]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M].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27.
[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三册[M].区宗华,林树慧,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3]张雅娟.清代嘉庆年间东南沿海海盗活动高潮成因分析[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3):61-70.
[4]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北京:三联书店,1957.
[5]Jules Davids.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842—1860):Vol.2[M]. Wilmington 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1973:126.
[6]Chinese pirates:death of Mr.Lowrie[J].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7(9).
[7]Official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death of the Rev.Walter.M.Lowrie[J].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8(9).
[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8.
[9]Jules Davids.AmericanDiplomaticandPublicPapers:theUnitedStatesandChina(1842—1860):Vol.11[M]. Wilmington 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73.
[10]马建石,杨育棠.大清律例通考校注[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685.
[11]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214.
[12]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38.
[13]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41.
[1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四国新档(美国档)[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131.
[15]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9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
[16]Jules Davids.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842—1860):Vol.15[M]. Wilmington 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1973.
TheCalderaCase
ZHANG Jia-li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The Caldera Case took place in China in 1854 is an important criminal case that influenced the modern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consultation and treatment of this case lasted several years and reflected many aspects of early Sino-US relations in diplomac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non-reparation established by the Treaty of Wanghia, this case was difficult to obtain compensation through normal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However, the US used the war threat to distort of the facts, and obtained compensation.
the Caldera Case; criminal ca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Treaty of Wanghia;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K254.3
A
2095-7602(2017)11-0063-06
2017-07-25
张家丽(1992-),女,硕士研究生,从事近代中美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