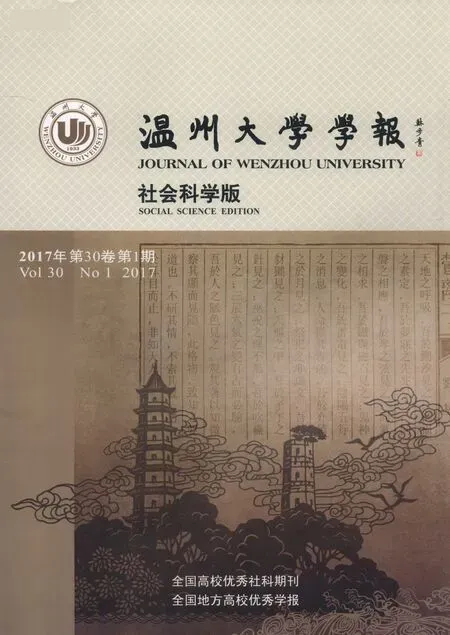《刑法修正案(九)》视角下的死刑立法改革
2017-03-08何立荣徐翕明
何立荣,徐翕明
(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
《刑法修正案(九)》视角下的死刑立法改革
何立荣,徐翕明
(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情节恶劣”和“期限重新计算”规定,进一步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作出限制,并取消了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等9个适用死刑的罪名。此修正案彰显了我国政府和立法者对死刑问题的高度关注,符合我国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是中国死刑立法改革的又一重要进步。我国当前死刑的立法改革应当适用“最严重的罪行”的标准;扩大“特殊主体”免死的范围;放宽“老年人免死”的年龄;逐步废除“非暴力”类犯罪的死刑。
《刑法修正案(九)》;死刑;改革
近代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早在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废除死刑的理念,他认为没有人愿意将操纵自己生死的权力赋予他人行使[1]。美国学者约翰·列维斯·齐林在《犯罪学及刑罚学》中提到:美国联邦政府于1890年通过一项联邦法律,将死刑罪名缩减至叛逆罪、谋杀罪和强奸罪三种[2]。此外,日本学者团藤重光在《死刑废止论》中提到:逐步推进死刑的废止是“宪法精神”和“程序正当主义”的宗旨所在[3]。不难看出,在世界范围内法律制度较为科学完善的国家大多主张死刑废除论,即便存在死刑的也只是极少数罪名。目前,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通过,中国保留死刑的罪名已经下降到了46个,死刑制度改革已经迈入了限制、减少死刑的良性发展轨道。本文通过对《刑法修正案(九)》的解读,通过现象看本质,结合我国国情,对未来我国死刑的走势做出大胆预测,并且提出为符合这一趋势我国应当采取的立法措施。
一、《刑法修正案(九)》对死刑的修改
(一)对刑法总则的修改
《刑法修正案(九)》修改的条文总计达到52条,在中国的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次修改的重点落在对分则罪名的相关规定,总则部分的修改只涉及了4个条文,与死刑相关的只有一个条文,即修正案第2条对死缓犯的规定。死缓制度虽不同于死刑立即执行制度,但在一定程度能有效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此次修正案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调整体现为新增“情节恶劣”和“期限重新计算”的规定,以此限制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
(二)对刑法分则的修改
《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1997年《刑法》的分则部分进行了大刀阔斧改革,进一步废除了分则中9项罪名的死刑①这9条被废除死刑的罪名分别是: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和战时造谣惑众罪。。关于死刑罪名,我国经历了一个“少-多-少”的过程。1979年的《刑法》只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推进,社会的转型必然伴随着不安定因素迸发,以至于在1980年代末不得不在某些领域实施严打,以正法纪,此举导致在1997年《刑法》中死刑罪名多达68条,位居世界之首。与此同时,我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和执行死刑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无人能及的,这一现象与国际社会逐步“去死刑化”的刑罚潮流是相背离的。之后,中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达成应当“逐渐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共识,并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取消了13种犯罪的死刑[4]。此次修正案的通过最终将保留死刑的罪名定格在46种。
二、死刑争论及评析
(一)死刑的争论
1.提高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对限制、废除死刑的实际意义
《刑法修正案(九)》将现行刑法典中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进一步限制在“情节恶劣”,应当说在理论上具有积极影响。但是,却遭到学界不少学者的质疑。首先,依据目前中国死缓犯的服刑情况,在死缓期间去实施故意犯罪的少之又少,立法又在此基础上增设“情节恶劣”的规定实属多余。其次,“情节”的表述过于抽象、概括,难以区分是定罪情节亦或是量刑情节。再者“恶劣”的描述包含了浓厚的主观因素,无法具体到量的判断。最终,对于何谓“情节恶劣”只能由人民法院根据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客观表现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综合判定,容易造成司法实践的扩大处罚。故此,“情节恶劣”的规定对死缓犯最终被执行死刑的影响甚微[5]。最后,由于未对死缓犯死缓执行期间的起算点加以明确,因此在理论上将起算点理解为故意犯罪之日或者最高院不予核准死刑之日都未尝不可。
2.分则中死刑罪名的废除对社会的影响
《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9种罪名的死刑,有人认为刑法分则中取消了这几种死刑罪名会削弱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作用,使尚未犯罪的人有了经济犯罪的企图,从而使经济类犯罪陡然上升;使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更加猖狂、肆无忌惮,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威胁人民生活。这些都是因为其他刑罚的震慑力和阻吓犯罪的效果远不如死刑,因为死刑剥夺的是人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中国自古就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谚语,何况被判处死刑显然也不能认为是“好死”。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巴哈认为,死刑可谓是刑罚中的极刑,一旦受到死刑惩罚,人生的一切便不复存在,这迫使行为人在犯罪时会慎重考虑,而大多数人都不会冒着被处死的风险去享受犯罪的快感。而废除上述几种罪名的死刑,意味着给了犯罪分子一块“免死金牌”,难免不令人担忧。
(二)死刑争论的评析
根据上文的分析,对《刑法修正案(九)》死刑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死缓犯执行死刑门槛的提高对限制死刑带来的效果以及取消死刑罪名对社会的影响。
1.对增设“情节恶劣”的分析
不少学者认为,增设“情节恶劣”的规定实属多余。他们的论证理由是增设“情节恶劣”的规定虽然在形式上对故意犯罪的情形作了进一步的限制,但实践中运用的机会却非常少,不免有画蛇添足之嫌。
笔者反对上述学者的论证理由,但对其论证结果又持肯定态度。首先,我们不能根据案情的特殊性去评价制度的一般性。死缓考验期内故意犯罪的情况确实非常少,但绝不是不存在,直接得出“规定”多余的结论在逻辑上说不通;再者,当故意犯罪确实发生时,用“情节恶劣”加以限制应当值得肯定。然而,笔者也认为,“情节恶劣”的规定确实没有必要,其实质是对“故意犯罪”的重复性评价。论证之前,我们必须对“故意犯罪”做缩小解释,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是故意犯罪就一律执行死刑。例如,故意伤害致人轻伤较过失致人死亡的危害性更小,但如果按照“故意犯罪”的文义解释,最终故意致人轻伤的死缓犯被执行死刑,而后者在两年后减为无期徒刑,这明显违背了罪行相适应的刑法原则,更有悖于常理。因此,这里的“故意犯罪”应当解释为“严重的故意犯罪”,而“严重”与“情节恶劣”的内涵在犯罪论领域内基本相同,所以笔者认为“情节恶劣”的规定实属多余。
再者,假设“情节恶劣”的规定确实有设立的必要,那么笔者也同多数学者有相同的疑问:何为“情节恶劣”?众所周知,“情节”包含的内容多种多样,“恶劣”字面可解释为坏到极点,在犯罪论领域内可解释为罪大恶极、罪恶滔天。但无论做怎样的解释,都自然包括了价值判断因素,因此要清楚界定其内涵,必须依赖于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因此,就现阶段的立法而言,笔者依然持“规定多余论”。
2.对增设“缓刑考验期重新计算”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50条第1款作出修改,增设了死刑缓期执行期间重新计算制度,但对起算时间未予明确,司法解释中也没有作出规定。学界有观点认为:应从最高院不予核准执行死刑之日起重新计算;如果不需要报请最高院核准的,应从查实之日起重新计算①参见《〈刑法修正案(九)〉49个重要问题逐一解》,网址:http://www.acla.org.cn/html/lvshiwushi/20150915/ 22789.html.。其理由是,死缓犯固有的两年缓刑考验期排斥了期间从故意犯罪之日的起算点,否则有悖于立法本意。
笔者认为,死刑缓期执行期间重新计算制度的本质与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相似,诉讼时效的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进行中,因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致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无效,待时效中断的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起算。根据条文的字面解释,死刑缓期执行期间重新计算制度的中断事由就是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那么重新计算的时间应当是最高院不予核准执行死刑之日,而不应当理解为故意犯罪之日。
3.对分则死刑罪名进一步取消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九)》总共取消了9种死刑罪名,不少学者担心这样成批量的取消死刑罪名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笔者认为,这样的担心既没有法律根据也没有实践根据,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第一,上述罪名的死刑在立法上基本是处于闲置状态。其中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和战时造谣惑众罪的死刑基本变成了一种摆设,而组织、强迫卖淫罪和伪造货币罪的死刑也是鲜有适用的余地[5]。因此,取消这些犯罪的死刑不但不会造成立法上的漏洞,而且能使分则中繁杂的罪名更加精简,同时对司法审判的影响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二,根据以往的实践经验来看,即使成批量的废除死刑罪名,也未必会产生负面影响。《刑法修正案(八)》取消的涉及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死刑条文远大于此次修正案,但从近4年间的实施效果来看,应当说,社会治安形势总体稳定有序,一些严重犯罪稳中有降,社会各界对减少死刑罪名的改革措施反响积极。
三、完善中国未来死刑立法的建议
(一)总则关于死刑适用的条款应当进一步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仅仅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情形作了限制,而对其他涉及死刑的条文没有作修改,让笔者颇感意外。首先就增设“情节恶劣”的规定,根据本文上述的分析,虽然笔者主张该规定确无必要,但依然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情节恶劣”作出明确的界定,达到限制死刑执行的预期效果。再者,笔者主张将最高院不予核准执行死刑之日作为期限重新计算之日,并建议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另外,对此次修正案没有涉及的关乎死刑的条文,笔者同样提出以下建议。
1.明确“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
有关“罪行极其严重”的内涵,在刑法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通常将其解释为犯罪的性质、情节,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客观危险性均达到极其严重的标准,但对该标准所映射的具体内容,仍然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6]。笔者认为,关于死刑的适用标准,应当与联合国公约接轨,该公约用“最严重的罪行”来替代“罪行极其严重”的表述,指的是所有犯罪中整体性质最为严重的犯罪。那么在未来的立法改革中应当对犯罪的整体性质进一步细化:应考虑到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否严重,犯罪手段是否残忍、恶劣,犯罪次数是否多、持续时间是否长,是否使受害人遭受巨大痛苦而致死亡,掩盖罪行的手段是否丧失人性,违背伦理道德,极其狠毒等。
2.扩大排除适用死刑的主体范围
根据现有刑法规定,只有犯罪时未满18周岁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方可排除适用死刑,故笔者建议,将精神障碍人群,处于哺乳期的妇女纳入排除适用死刑的主体。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关于保障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措施》和《对保障措施的补偿规定》的规定,都将精神病患者(也有称智障者)和哺乳期妇女排除在死刑适用之外。因这两类主体在心理和生理上的特殊性,对其犯罪后处以死刑这样的极刑,恐怕既不符合刑罚人道主义的情怀,也不符合国际化死刑发展的趋势。
3.放宽老年人犯罪的免死年龄
现行刑法将老年人免死的年龄规定为审判时年满75周岁,且不存在“手段特别残忍致人死亡”的情形。笔者建议,将老年人犯罪后不适用死刑的年龄放宽到70周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于2013年5月15日在日内瓦发布的《2013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6岁[7]。但是以平均基准去衡量犯罪特例并不科学,并且在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中,《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70周岁以上即可认定为老年人。与此同时,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都将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年龄规定为70周岁甚至更低。另外,从《刑法修正案(八)》实施的四年间,并没有出现70周岁以上老年人被判处死刑的案例。
(二)分则中应当进一步废除不适用死刑的罪名
《刑法修正案(九)》虽然进一步废除了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但是仍然有以下几点需要完善。
1.进一步废除贪污贿赂类犯罪的死刑
此次修正案已经对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适用予以严格限制,不过,就推动死刑立法改革而言,中国有必要进一步考虑在下一步的刑法修正中适时取消严重腐败犯罪的死刑[5]。笔者赞同赵秉志教授的观点,理由如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于贪污贿赂不设置死刑,废除全部的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有其深远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社会原因,死刑无法有效遏制其发生,例如明朝时期朱元璋曾采取过“重典治吏”的政策,用来惩戒官吏的贪污受贿行为,但最终却导致贪污贿赂犯罪愈演愈烈;上文提到,我国死刑的改革应当与国际公约接轨,应当适用“最严重的罪行”的标准,贪污贿赂犯罪远远够不上“最严重的罪行”的性质。
2.进一步废除其他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笔者认为下一步我国立法可以废除运输毒品罪的死刑。首先,运输毒品与制造、贩卖毒品相比,运输行为只是整个毒品犯罪的中间环节,而制造行为属于毒品犯罪的源头,贩卖行为属于毒品犯罪的终结,权衡三者,很明显运输毒品的社会危害性比制造、贩卖毒品小得多,没有适用死刑的必要;再者,运输毒品与走私毒品相比,运输行为仅限于国内流通,相较于走私这一跨国运输,也不及后者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性。并且,近些年我国对打击毒品犯罪已经取得较好的效果,大多数公民对于毒品犯罪已经形成清醒的认识,顶格适用无期徒刑已经可以达到人道化地惩治和遏制犯罪的效果。故,可以在保留走私、制造、贩卖毒品罪适用死刑的前提下取消运输毒品罪的死刑。
3.全面废除经济类犯罪的死刑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顺利通过,《刑法》分则第3章的罪名中,保留死刑的只有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与其说上述两种罪名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还不如说是对公共安全的破坏,因为假药和有毒有害食品已经威胁到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符合《刑法》分则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征。因此,笔者建议将现行立法体例作简单调整,把这两罪归为《刑法》分则第2章,从而实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零死刑”化。
《刑法修正案(九)》掀起了中国死刑立法改革的高潮,也与世界刑罚发展趋势接轨。但是,鉴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目前的社会发展程度,中国死刑的立法改革必定是一项漫长且浩大的工程,而且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去死刑”化道路,盲目照搬国外立法是行不通的,这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法律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1] 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M]. 黄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9.
[2] 约翰·列维斯·齐林. 犯罪学及刑罚学[M]. 查良监,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75-376.
[3] 团藤重光. 死刑废止论[M]. 林振彦,译. 台北: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7:90.
[4] 高铭暄,苏惠渔,于志刚. 从此踏上废止死刑的征途:《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死刑问题三人谈[J]. 法学,2010(9):1-13.
[5] 赵秉志. 中国死刑立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主要视角[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1):5-20.
[6] 赵秉志. 中国死刑制度改革前景展望[J]. 中国法律,2012(1):28-42.
[7] 刘素云. 中国人均寿命达76岁[N]. 新民晚报,2013-05-16(A18).
Study on Legislative Reform of Death Penal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mendment 9 of Criminal Law
HE Lirong, XU Ximing
(School of Law,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China 530006)
In Amendment 9 of Criminal Law, provisions of “wicked circumstances” and “term recalculation”are added so as to further limit the range of death penalty execu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9 kinds of crimes related with death penalties, such as crimes of smuggling of counterfeited currency, crimes of Counterfeiting Currency, are removed from it. This amendment not only shows the great attention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legislators attach to the issue of the death penalty, but also is in line with the policy of killing less and cautiously. So it is an important progress of the reform of the death penalty legislation. The standard of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should be applied to the legislative reform of Chinese current death penalty through following measures: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pardoned “special subjects”, reduction of the age of “pardoned old people” and gradual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for the crime of “non-violence”.
Amendment 9 of Criminal Law; Death Penalty; Reformation
D924.12
A
1674-3555(2017)01-0078-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7.01.012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付昌玲)
2016-03-09
何立荣(1970- ),男,广西桂平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