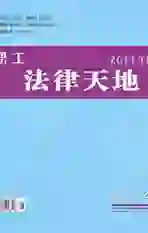浅析虐待罪的行为
2017-06-07刘松铭
刘松铭
(100081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北京)
摘 要:行为是犯罪的核心,残害身体型虐待行为用暴力和作为的方式直接作用于被害人身体,具有持续、连贯经常性的特点,其和家庭暴力行为既有相似又有不同;断绝衣食型虐待行为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行为方式,虐待罪和遗弃罪的主要不同在于犯罪客体;涉性侵型虐待行为的受害者多为女性和儿童,情节严重的婚内涉性侵犯型虐待行为应该用刑法加以规制;精神侵害型虐待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亚于肉体虐待行为,针对儿童的精神虐待应单独立法加以规制。
关键词:虐待罪;虐待行为;情节恶劣;家庭成员
网络描述:虐待是一个人以胁迫的方式控制另一个人的一种行为模式。虐待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造成身体上的伤害和心理上的恐惧,它使别人不能做她想做的事,或强迫她以不情愿的方去做事。虐待包括使用人身暴力和性暴力、威胁和恐吓、情感虐待和经济剥夺。通常对虐待的理解,是行为人为了满足自己欲望和意志,通过给被害人的身体和心灵两方面施加恐惧和伤害的方式,让被害人违逆自己的意志做或者不做一定的行为。在虐待罪中,可以理解为家庭中占据主导、强势的成员为了控制其他家庭成员而对其进行心理和身体双重伤害和折磨。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时代的迁移,刑法始终没有对虐待罪中的“虐待”进行定义。我国刑法学界从多角度对“虐待”进行定义。比如从行为方式的角度划分,“虐待”可以是暴力和非暴力的,被害人受到的伤害可以是身体和精神上的[1]。从时间角度进行划分,“虐待”是持续性、经常性的损害行为[2]。若是将“虐待”行为剥丝抽茧进行细化,虐待可以表现为殴打、冻饿、不给治病、限制人身自由、强迫超体力劳动、侮辱人格[3]。在司法领域中,关于什么是“虐待”虽然没有直接的定义,但是可以参照一下“家庭暴力”。2001年12月24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的行为”是为家庭暴力。那么比较有说服力的虐待的定义可以是持续性、经常性的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的行为。下文中,笔者将虐待行为划分成四类,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浅析虐待行为的本质。
一、残害身体型虐待行为
身体残害型虐待行为指的是行为人将身体残害行为施加到受害人身上,使受害人身体功能受损,甚至导致死亡、重伤的结果发生。这种虐待行为用暴力的、作为的方式,直接作用于受害人身体。残害身体型虐待行为可以采取徒手的方式,即不借助于外界的工具,例如扇嘴巴子、拳打脚踢;残害身体型虐待行为也可以借助一定的工具实施,比如用针刺、用刀划伤、用热水浇烫。1979年《刑法》虐待罪位于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1997年《刑法》虐待罪被置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由此可见,对公民身体健康权的侵犯是虐待行为的本质之一。
残害身体型虐待行为应该是持续、经常、连贯的,偶然的一次性的残害不应理解为虐待罪中的“虐待”。根据学者刘慧霞的观点,行为人的虐待行为具有周期性,这一次的虐待行为和下一次的虐待行为之间会间隔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平静。虐待行为的慢性特点,决定了虐待行为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受害人会对施害人的虐待行为产生习惯性和适应性,甚至会失去戒备性。
家庭暴力和虐待罪中的残害身体型虐待行为相比较,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根据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包括性暴力、身体暴力和心里暴力,殴打、辱骂、奸淫、性凌辱、切除阴蒂等行为都是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女性居多,也有男性,且仅限于配偶和伴侣之间。但是虐待罪中虐待行为的主体范围则相对来说大的多,不仅仅包含在配偶之间,而是涵盖了所有诸如父母子女之间关系的家庭成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虐待是持续性的、经常性的家庭暴力。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家庭暴力行为除了可以用虐待罪来规制,也可以用非法拘禁罪、侮辱罪、遗弃罪等刑罚规制手段。由此可见,对待家庭暴力行为的反制手段要多于残害身体型虐待行为。
二、断绝衣食型虐待行为
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的表现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一种是不作为。如果残害身体型虐待行为更多以作为形式出现的话,那么断绝衣食型虐待行为则更多的是不作为。什么是断绝衣食型虐待行为?顾名思义,就是行为人用不给衣服穿、不给食物吃的方式达到其虐待的变态心理。
虐待罪和遗弃罪的不同之一在于犯罪客体。遗弃罪的犯罪客体在于行为人想要摆脱其应尽的义务,而虐待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则是人身权。单纯的不作为行为是否应用虐待罪加以规制,这在学界是有争议的。断绝衣食型虐待行为应根据其行为的恶劣程度并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分析。这其中应该主要分析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内容。因为断绝衣食型虐待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既可以是为了逃避抚育赡养义务,也可以是想要造成被害人身体健康受损的结果,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遗弃罪的犯罪主体是本应该对被遗弃者应该负有抚养义务的同时具有履行能力的人,在这一点上与虐待罪要求的主体为家庭成员不同。从主观故意的内容角度看,虐待罪的故意内容里更多的是折磨,伤害被害人,这种折磨和伤害是直接的显性的;而遗弃罪的故意内容里则是逃避责任和义务,这种逃避是消极的、隐性的。从客观行为的特征上看,断绝衣食型虐待行为的外在表现往往是持续、连贯、经常、多次,从而使得受虐人苦不堪言,在施虐人的控制之下备受折磨。
在这里,笔者比较赞同学者刘慧霞的观点,单纯的不给东西吃、不给衣服穿的断绝衣食型虐待行为是可以构成虐待罪的。举例来说,如果被害人是行为人的家庭成員,同时行为人又对被害人负有应尽的抚育赡养义务,而且施害人不给东西吃、不给衣服穿的行为又是经常性施加的而且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考虑用虐待罪来规制的[4]。
三、涉性侵犯型虐待行为
涉性侵犯型虐待,指的是通过束缚、拘禁、性报复等方式为了满足自己在性方面的满足感、占有欲而伤害、折磨他人,给他人肉体和精神施加痛苦的行为。涉性侵犯型虐待行为究竟是一种正常的人类行为还是一种病态,这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至少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性虐待不是正常的,这一点从它的别称就可以看出来——虐恋、虐淫、痛淫。严重的性虐待施加者会采取极端的方式剥夺被害人的生命,碎尸、食尸都是这一行为的组成部分,而类似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涉侵犯型虐待行为具有痛苦行、侮辱性特征。常见的涉性侵型虐待行为还包括痛打、撕咬、捆绑、鞭打、尖锐物刺痛、踩踏、灼烫。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国一直是一个谈性色变的民族文化,性话题的神秘性、难以启齿性决定了涉性侵犯型虐待行为具有隐蔽性。这就决定了在现实生活中,一方家庭成员如果收到了另一方家庭成员的性虐待,受害的一方的维权通道莫名地受到性畸形文化的束缚,宁可选择退避、忍耐也不会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正是基于虐待罪告诉才处理,使得涉性侵犯型虐待的受害人往往走向两极,要么选择在沉默中死去,忍辱负重,身心饱受摧残;要么选择在沉默中爆发,即因不堪忍受性虐待暴力,而采取极端行为报复施虐者,走向私力救济犯罪的境地。
涉性侵犯型虐待行为的受害者多为女性和儿童。由于生理原因和社会原因,在家庭关系中,女性和儿童往往处于弱势的一方。涉性侵型虐待行为极大损害了女性的性自主选择权和身体健康权,而性自主选择权时我们作为人生而拥有的[5]。涉性侵犯型虐待行为和强奸行为之间如何界定是一个疑难。二者相似之处都是对女性性选择权和人身健康权造成了伤害。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强奸是一种违背被害人的意愿,使用暴力的非法手段,强制与被害人进行性交,但是涉性侵型虐待往往身披婚姻这一合法的外衣,给施害人以涉性侵犯型虐待行为之名行强奸之实。女性在受到涉性侵型虐待行为的时候,自身性器官如阴道、乳房、阴蒂等会受到伤害,这极大破坏并伤害了公序良俗也违背了正常的社会伦理道德。在受到涉性侵犯型虐待行为的成年女性当中,大部分在其童年时也受到过涉性侵犯型虐待。儿童也是涉性侵犯型虐待行为的重灾区。而涉性侵儿童型虐待行为大多是非接触型性行为,比如施害人故意窥探阴部、强行注视阴部、暴露自己性器官。总的来说,施害人就是在儿童面前不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涉性侵儿童型虐待行为有的是接触性性行为,比如施害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恋童癖而故意抚摸儿童,亲吻儿童,更有甚者触摸儿童的生殖器甚或和儿童性交[6]。这其中男性家庭成员如继父和父亲巨大多数,而母亲和男性家庭成员的情人也占了一部分。
针对婚内涉性侵犯性虐待行为的定性问题一直是学界的难点和争议的焦点。一来婚姻关系给夫妻双方在性行为方面赋予了很多合法的权利和自由。再者,夫妻家庭生活本身就具有私密性,而且施害人侵害的部位更是难以启齿的私密部位,因此外人很难察觉。有的学者对婚姻存续期间的性强迫行为持否定入罪的观点,认为配偶权包括夫妻之间满足对方性行为的忠实义务,在正常情况下,夫妻任何一方都不能拒绝履行同居这项义务,夫妻间在性行为方面的摩擦冲突都应该只停留在道德上,不应该用刑法加以规制。笔者比较赞同学者刘慧霞的观点,婚姻豁免与当下的社会现状不符,婚内的涉性侵犯型虐待行为如果真如刑法规定的那样情节严重,那么用刑法加以规制是完全有必要的。
四、精神侵害型虐待行为
人们在精神上的需求以及关注是以往任何时代任何时间所不能比的。这一方面是有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慢慢地从物质层面转移到精神层面。以往我们提及虐待更多的是侧重于关注暴力行为,但是新情况新案例揭示,很多虐待行为对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比肉体型虐待行为更严重。然后包括刑法在内的我国法律,对公民精神层面的保护的条文甚少。
精神侵害型虐待行为是指施害人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对被害人的精神和心灵进行折磨造成伤害的行为。主动的精神侵害型虐待行为包括对受害人使用语言、表情、神态等达到其嘲弄、威胁、侮辱、贬损的目的;被动的精神侵害型虐待行为通常是冷暴力、冷战,即通过故意冷漠、疏远等方式造成被害人心里得落差產生的不平衡从而对被害人造成伤害。在精神侵害型虐待行为当中,家庭成员里的儿童和老人是受害最多群体。孩子在家庭教育当中,可能会刻意或者非刻意地被家长的显性言行或者不作为中伤。而被公认为弱势群体的老人在精神侵害型虐待行为当中更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为年龄的原因,老年人在生理方面的机能日益衰退,头脑智力等方面也和过去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子女将老人视为负担,对老人的一些幼稚的行为冷嘲热讽,有的甚至把老人关起来、封闭起来,对老人漠不关心不闻不问。上述现象在当下的社会越来越普遍,对老年人和儿童的权益保护值得深思。
那么精神侵害型虐待行为是否构成虐待罪呢?有学者认为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摧残和压迫,如果情节恶劣,其对人身心健康所造成的伤害绝不亚于残害身体型虐待行为,因此如果家庭成员受到精神上的摧残和压迫情节严重的,是可以以虐待罪加以规制的[7]。精神侵害性虐待行为因为是在精神层面的侵害,所以在取证过程中不像残害身体型虐待行为那样容易。但是刑法不能因为实然层面的操作困难就在应然层面放弃对这一具有隐性社会危害性并且有可能诱发显性危害的行为加以规制。在当下,精神层面的暴力或者说冷暴力已经超越身体侵害和性侵害而成为频率最高的虐待行为方式。女性在经受精神层面的暴力伤害之后易患抑郁症和焦虑症。如果指望道德约束来限制精神暴力,恐怕超越了道德应有的能力。偶尔的家庭精神冷暴力可以用道德来约束,但是长期的、严重的精神侵害型虐待行为还是需要上升到法律、刑法的高度对其加以约束。
笔者认为,针对精神侵害型虐待行为应该充分发挥妇女联合会、社区街道、居民委员会以及法律援助中心的力量加以疏通调解。儿童处于生长发育阶段,三观不成熟,简单的行为就可以对其终生产生影响造成阴影,长久下去甚至有可能形成反社会人格。对于儿童的虐待行为,笔者认为有必要单独立法,或者在现有法律中用单独条文和内容加以规制。
参考文献:
[1]刘慧霞:《虐待罪若干争议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2]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刘白驹:《性犯罪:精神病理与控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本。
[4]巫昌祯,杨大文:《防治家庭暴力研究》,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5]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6]黄列:《家庭暴力从国际到国内的应对》,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春季号。
[7]储兆瑞:《共同抵制性虐待》,载于《祝您健康》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