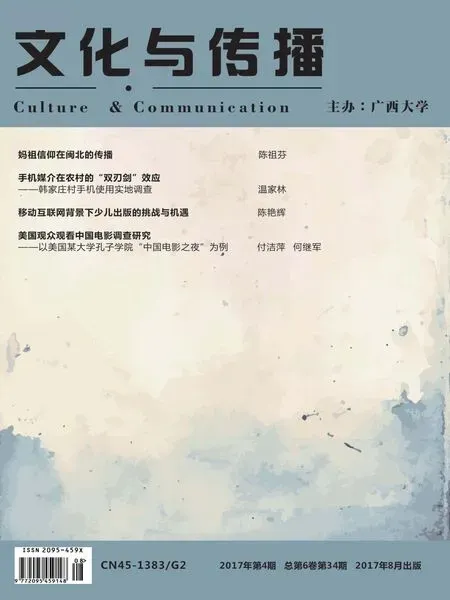魔是鹅的另一面相
——比照名为《利维坦》的名著与电影
2017-02-15晋振华
晋振华
在2014年戛纳电影节上,俄罗斯天才导演安德烈·萨金塞夫(Andrey Zvyagintsev)拍摄的电影《利维坦》初次亮相便斩获嘉奖。2015年,该片又获得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并在同年获得第72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及第35届伦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2016年,英国广播公司(BBC)评选新千年以来最伟大的100部电影,《利维坦》位列第47名。《利维坦》的成功,除了该片凸显人类普遍处境之主题及其寓言式的表达方式之外,恐怕还和作为语言符号的“利维坦”印刻在人们脑海中的惊悚画像及其政治意蕴不无关联。
一、利维坦的故事
“利维坦”原本是《圣经》中所记载的一种海中巨兽,“它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箭不能恐吓它使它逃避,弹石在它看为碎秸……在地上没有像它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它无不蔑视,它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1]833在接受采访时,不谈利维坦的宗教印象,导演安德烈·萨金塞夫却坦言他拍摄电影《利维坦》的灵感源于他阅读英国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的同名政治哲学名著《利维坦》。霍布斯在这部著作中将利维坦比作为强势的国家,是处于自然状态之下的人们走出丛林法则之后的秩序权威。
至于作为国家的利维坦的具体形成过程,霍布斯是这样描述的:“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就等于说,指定一个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每一个人都承认授权于如此承当本身人格的人在有关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为、或命令他人做出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这就不仅是统一或协调,而是全体真正统一于唯一的人格之中;这一人格是大家人人相互订立信约而形成的,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与这人或这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与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2]131-132后来,在《利维坦》的第二十八章,霍布斯又进一步阐发了这种国家的由来,由于“人类的天性,他们由于骄傲和其他激情——被迫服从了政府;此外又说明了人们的统治者的巨大的权力,我把这种统治者比之于利维坦。”[2]248
当然,萨金塞夫所拍的电影《利维坦》不会像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那样抽丝剥茧般地对现代国家的特征进行条分缕析,他只是不紧不慢地拓展了一个发生在俄罗斯的寻常故事以诠释他对霍布斯所刻画的利维坦的个人体悟。
电影《利维坦》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俄国西北部巴伦支海沿岸的一个边陲小镇。主人公科里亚(Kolya)是一位退伍军人,他和前妻的儿子罗马(Roma)以及年轻貌美的妻子利里娅(Lilya)过着悠然恬静的生活。在自祖辈就生活的地方,科里亚有一栋精致的小楼,小楼依山傍水,且离市中心不远,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被当地市长瓦迪姆(Vadim)所垂涎,市长遂以市政需要为名强行征收科里亚的房屋,科里亚的悲惨生活就此开始。市长野蛮骄横且无所不能,从警察局到检察院再到法院,他手法老道地裹挟国家机器而怙恶不悛。最终,市长通过罗织罪名让科里亚锒铛入狱、家庭破碎。他自己也达到了目的:权力巨兽利维坦要踩死一只蝼蚁,也可以做到程序上的合理合法。
简单地讲,萨金塞夫的《利维坦》展示了科里亚这个原本属于国家机器当中的一员与强征土地的市长所构成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种对立与冲突是现代政治的一种普遍处境,它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及这个国家之中的任何一个个人之间发生。换言之,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萨金塞夫所要探讨的主题,正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它(电影《利维坦》)所讲述的是人的命运,不仅是俄罗斯人,也不仅仅是发生在俄罗斯,它讲述的是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着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3]
事实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与冲突也正是霍布斯的《利维坦》所要辩解的难题。这个难题能否在他搭建的利维坦式的国家中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我们需要回顾霍布斯对其利维坦的形塑与设计。
二、鹅是利维坦的最初面相
在《利维坦》的书信体献辞中,霍布斯如此描绘利维坦的面相:“我谈论的还并非是人,而是抽象意义上的权位。就像是罗马卡普托利山上(Capitoline Hill,罗马七座山丘之一,这是最早的罗马城堡,相当于古希腊雅典卫城)那些没有党派之私的生灵(圣鹅,sacred geese),用它们的叫声就保住了山上的人,不是因为它们是它们,而是因为它们在那里。”①需要指出的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利维坦》将其英语原版中的书信体献词删掉了,这实际上不利于汉语读者对《利维坦》的准确理解。[4]3
依据古罗马的民间故事,[5]霍布斯所讲“圣鹅”的故事情节大概如下:公元前390年,一大群凯尔特人从北部意大利向南进发,摧毁了罗马军队,将罗马城洗劫一空,有一小撮守兵能坚守在卡普托利山上,并安然无恙,只是因为山中养了一群圣鹅,当凯尔特人试图往山上爬时,半山腰上的圣鹅就拼命地的嚷叫,圣鹅的叫声警示山上的人拿起武器进行防卫并击退凯尔特人。圣鹅保护住了山上的人,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圣鹅,而是因为圣鹅所在的位置。
很显然,圣鹅就是霍布斯想要赋予那个坐拥利维坦主权权位的统治者的应有形象,其原型或许就是那个缔造都铎王朝黄金时代的伊丽莎白一世——擅长权力平衡而维护了英格兰统一的“圣洁女王”(又称“童贞女王”)。把主权者刻画为一只不偏不倚的圣鹅,是因为在霍布斯进行学术创作的164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对派开始公开地质疑国王的权力,他们认为自己是生而自由的公民,而不是国王的臣民。也正是在这个年代,现代政治竞技场上的两位伟大主角——个人和国家——开始面面相对,且要分出高低位阶与先后次序。此时,亦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言:“当国家的政治权力受到威胁时,有一群鹅唤醒了沉睡的哲学家,这就是霍布斯。”[6]72
出于对国家眼前灾难的悲伤,在《利维坦》开篇伊始,霍布斯便陈述了自己的创作缘由:“在一条熙熙攘攘的路上,众人互相争斗,一方要求过度的自由,另一方要求过度的权威。欲求两不相伤而安然通过,殊不可得。然依我之见,提高国家权力的努力,不应受到国家权力的谴责,也不应受叫嚣此权力过大的私人的非难。”①这几句话同样出自《利维坦》英语原版中的书信体献词,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利维坦》所没有的。此处引文采用王利先生在其专著《国家与正义:利维坦释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中的译文。[4]3简言之,霍布斯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对国家的权利和臣民的责任进行更为刨根问底的探讨以最终实现国家和个人关系的条理化。
在《利维坦》中,为摆正个人与国家的层级与关系,霍布斯押注在主权代表者的角色定位上。因为,在霍布斯所生活的时代,人们也开始认为,主权权力(sovereign power)的持有者不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而是作为国家的代表来行使的,也即,作为自然人的国王只是国家法人的人格代表。只是在理论铺展的过程中,霍布斯似乎忘记了这样一来国王就有了两个身体,这就是霍布斯的后辈学人康托洛维茨(Ernst H. Kantorowicz)所概括的“君之两体”(The King’s Two Bodies):即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作为国王职位的政治体,一个是作为国王个人的自然体,政治体不会死,可以无限延续,自然体会死,可能犯错。[7]霍布斯坦承:一方面,“国家不是(自然)人,除开通过代表者以外也无法做出任何事情”;另一方面,“人(person,希腊文不作“人”而作“面相”讲)的意义和演员的意义相同,代表就是扮演或代表他自己或其他人”。[2]123毫无疑问,国王的政治体需要由他的自然体去扮相。那么,问题出现了:如何保证国王的自然体不会冒犯和僭越国王的政治体?毕竟,国王的身份不只是一种,政治体和自然体同为国王的两种人格(面相)。国王有两种面相,政治社会中的其他人物也概莫能外。看看电影《利维坦》里渐次出场的各个人物:市长、律师、法官、主教、警察等等,他们所拥有的不仅仅是社会(政治)身份,他们还扮演着父亲、丈夫、妻子、朋友、邻人等自然角色。社会身份与自然角色之间的扞挌与纠缠显而易见,就像霍布斯把自然(意味着野蛮)和社会(意味着文明)看作是人类生活极易滑入的两个极端一样。显然,如何避免两种面相之间的翻转所带来的不幸和苦难被霍布斯忽略了。
三、鹅到魔的翻转
霍布斯在西方学界被称为是现代国家理论的奠基者,他推崇理性、悬置道德、批判宗教和彰显世俗权力。其中,为了摆脱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桎梏,他在《利维坦》中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揭露教会的腐败、黑暗、贪婪与虚伪。在霍布斯的笔下,上帝(神)的圣洁与尊崇,教会的威严与神秘,都荡然无存。“从霍布斯开始,‘现代性’的神学政治就取代了基督教的信仰作用,国家代替了上帝,成为价值的创造者,它认为自己存在的正当性并不是通过与某一个上帝的交流,而是将自己与终极真理同化。”[8]换言之,用人权调换神权,现代国家的神话发端于霍布斯的利维坦的登台亮相。
人性的自私自利是霍布斯建构利维坦的出发点,在霍布斯看来,众人之所以要赋予利维坦以垄断性的绝对权力是因为人的权力是他取得某种未来利益的现有手段,而全人类的普遍倾向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种“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力欲”。[2]72霍布斯也承认,人和其它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有理性。理性提示人们,建立拥有绝对主权的利维坦是避免人与人之间进行“狼斗”的不二法门。的确,人虽然不是天使,但也不一定非得要做魔鬼。但霍布斯的困难在于:利维坦建立后,他无法阻挡应该表现为天使的人(掌权者)却表现为魔鬼。关于这种风险,只要扫一眼霍布斯所罗列的主权代表者的权力清单就知道了。并且,霍布斯还声称主权者一旦获得授权,其权力就是绝对的。大家都必须听从他的意志和判断,就像是听从自己的意志和判断一样。换言之,在授权完成之后,对主权者的任何反抗和革命都是违背契约,在道义上是不义之举,在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
霍布斯是通过观察人性并推演出国家存在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因为主权者是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他就理应超越于规则之上而不受规则制约。这样一来,“霍布斯笔下的国王,只是一个教士……这样的国王不仅无法完成霍布斯所指派的主权者的工作,相反地,他只会利用手中的权柄完成自己的利益。”[9]因为,霍布斯为身为主权者的自然人留存了可以“假汝之名”的广阔空间。即使我们把利维坦看作是公意的代表,但“国家没有意志,除开具有主权的某一个人或多人的意志所制定的法律以外也不能制定任何法律”。[2]287虽然霍布斯一再强调主权者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公职,但霍布斯从未否认这种公职也需要由自然人去承担。有意或无意的,霍布斯用代表概念模糊或淡化了主权者的自然体和政治体之间的殊异。
恩格斯曾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程度之间的差异。”[10]67揆诸《利维坦》(英文初版)的卷首插图,①遗憾的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利维坦》没有英语原版中的卷首插图。霍布斯赋予利维坦以神(宗教的)之左手、魔(世俗的)之右手,把兽性作为工具去实现人(神)性的目的在霍布斯那里就在所难免。基于对霍布斯利维坦的这种认识,福柯就认为,(利维坦的)主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与死的权力,这种权力能维持生命仅仅因为它随时都可以将它夺走。主权者是用他剥夺生命的权力来行使他维持生命的权利。[11]154没有界限和防护,在兽性和人性之间变幻莫测,主权者的公正与偏私就在乎一念之差,利维坦从鹅到魔的翻转也只是弹指瞬间的事情。
以宗教为例,宗教虽然劝人向善,可是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公义对任何时代任何教会来说都有巨大的解释空间,而教会因为是由人组成的,因而也就不可避免的因为人性的软弱而产生各种腐败乃至罪恶。在电影《利维坦》中,教父的职责虽然是摆渡灵魂,但收受市长的好处后便闪烁其词、左右逢源。类似人格(也即希腊文所指的“面貌”或“面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电影《利维坦》中还有很多:法官的职责是讲究证据、依法判决,但为了体现上级领导的意志,却做出明显的有罪推定;交警八面玲珑、阴奉阳违,警车驾驶座的前方,既贴着几幅圣像图,又贴着几张裸女的艳照;代理律师的职责是伸张正义,初战告捷便引诱当事人(也是朋友)的漂亮妻子。综合起来,萨金塞夫对霍布斯《利维坦》的感悟应该是:亦神亦人的主权者无异于一个暴殄天物的魔鬼。这个时候,人们还能向国家寻求庇护吗?电影《利维坦》的最后,主教说,自由是找到上帝的真理,而上帝的真理,就是上帝自己。当国家拆了科里亚的房子,让他身陷囹圄、妻离子散,并占有了他的房屋作为教堂,国家俨然已是上帝,它垄断了真理。
实际上,霍布斯的同时代人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就对其心怀不满:“霍布斯的帝国既不存在于文明人那里,也不存在于野蛮人那里,我认为他们既不可行也不为人们所喜欢——除非那些必须享有至高权力的人生来就拥有天使般的美德。因为人们为统治者的至高智慧和能力所折服对于人们完全放弃其自身意志是必不可少的,只要此点做不到,人们就将会遵循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争取福利。因此霍布斯的论证只在上帝做国王的国家才能成立,因为人们只对上帝抱全部的信任。”[12]153可见,提防利维坦就应该是随时随地的事情。
四、提防利维坦
康德曾认为,人类最困难的问题就是,人是一种动物,人对人总会滥用自己的自由,当人类组建一个共同体(国家)时,就需要有一个主人用一条法律来规定大家的自由界限。但人的动物倾向性却极力把自己排除在界限之外,主人也是动物,他也需要有一个主人,主人的主人……如此循环,没有终点。[13]10所以,康德悲观地认为人类的这种困难直到最后才能解决。
然而,自信满满的霍布斯,虽然在时空上比康德还早了近半个世纪,他却笃定可以给康德的循环链条打个死结——一个使人畏惧的共同权力。但根据霍布斯的代表理论,他想必也明白:“‘国家’是一种抽象物;它并不会感受到痛苦或快乐,它没有任何希望或者恐惧,我们认为是国家目的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掌控国家的那些个人的目的。当我们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思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特定的某些人取代了‘国家’,他们拥有的权力比大多数人所享有的要多得多。”[14]94
比照《圣经》(或霍布斯《利维坦》中的相关引文)和电影《利维坦》中的类似场景:神(或神的代表神父)以利维坦可怕的特征诘问约伯(或科里亚):“你能用鱼钩钓上利维坦吗?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你能用绳索穿它的鼻子吗?能用钩穿它的腮骨吗?它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它永远作奴仆吗?”[1]832约伯(或科里亚)不能作答,即默认不敢惹它。实际上,人类的普遍处境,就是约伯(或科里亚)的处境。这种处境或如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所说的:“我们人类脆弱得要命的那种状况的天然不幸;它又是如此之可悲,以至于当我们仔细地想到它时,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安慰我们。”[15]73在电影《利维坦》中,我们看到,无望无助的科里亚只能借酒消愁,他的律师朋友被市长恐吓之后便逃之夭夭,对科里亚深感同情的邻人也只能借助尼古丁(抽烟)来做选择性的记忆。
可见,即使建构利维坦是必须的,但霍布斯的利维坦也仅仅是脱离最坏自然状态的最初政治设计,而不是走向历史终结的最好政治架构。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在《驯化君主》中所言,“既维护自由又具备阻吓敌人、保障公民安全的强有力政府,是近代的一项发明…这项发明仍不是十分可靠,维护自由的政府往往倾向于变得软弱,而强大的政府倾向于放弃或践踏自由”。[16]我们应该明白,萨金塞夫拍摄的电影《利维坦》是在强调启蒙时代的一种政治理念:“政府的存在,正是人性的最大耻辱,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或内在的控制。”[17]264
总之,即使利维坦是一只鹅,也不要忘记魔是鹅的另一面相,代表神性的鹅和凸显人性的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种意义上,霍布斯的《利维坦》和萨金塞夫的同名电影讲的是同一种寓言。
[1]《圣经》[M](简化字新标点和合本),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5.
[2][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延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利维坦:公权怪兽下的蝼蚁小民》,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6&id=11352051,凯迪网络,2016年9月10日.
[4]Hobbes, Thomas, Leviathan, ed., by Richard Tuc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影印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pitoline_Hill,2016-9-10.
[6][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7]晋振华. 主权抑或主权者——论“利维坦”的政治意旨[J].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2014(3).
[8]曾庆豹. 利维坦与政治学:一个现代性的批判[J]. 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2003(5).
[9]梁裕康. 既“可怕又谬误”却“公正且真确”——论卢梭对霍布斯宗教理论的评断[J]. 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14(6).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法]伊夫·扎卡尔. 权力的形式[M],赵靓、杨嘉彦,译.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12][徳]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政治著作选 [M],张国帅、李媛、杜国宏,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13][德]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4][英]罗素. 权威与个人[M],储智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5][法]帕斯卡尔. 思想录[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6][美]哈维·曼斯菲尔德. 驯化君主[M],冯克利,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17][美]汉米尔顿、杰伊、麦迪逊. 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在汉、舒逊,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