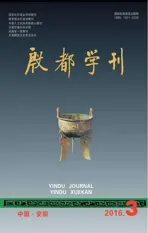赋体生成与屈辞赋体论证
2016-11-09张世磊
张世磊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99)
赋体生成与屈辞赋体论证
张世磊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99)
赋体文学盛于汉代,体式多样,题材丰富。作为文学文体之一类,赋至宋玉正式标题成体。世人在追溯赋体形成时,都会提及屈辞,或径直将屈辞认定为赋体。这缘于屈辞的创作同样是采用讲求言辞文采的雅言写作。而雅言的言说、创作形式,正是赋成体之前,作为动词时赋的基本内涵。屈辞的创作虽是采用赋法,但一些作品的创作已有明确的文体归属,并非全为赋体。可称赋体的只有《卜居》《渔夫》与《招魂》。
屈原;宋玉;屈辞;文体;赋
一、问题的提出
赋体文学盛于汉代,是最能代表汉代文学成就的文体。综观全汉赋,不仅文体样式不尽相同,而且内容题材十分丰富。文学史著作,及专门的赋史,都曾对汉赋文体样式作过具体划分。文学史一般分为骚体赋、汉大赋与抒情小赋;专门赋史著作,如马积高《赋史》,则分为骚体赋、文赋和诗体赋。足见汉赋的体式并不统一。
从篇章内容上看,赋的表现范围非常广泛。有表伤悼之赋,如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有言志之赋,如刘歆《遂初赋》、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有游猎宫苑之赋,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有京都之赋,如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有抒幽情之赋,如司马相如《长门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诸如近些年出土的《神乌赋》等俗赋、故事赋。这足以证明赋体文学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不论幽情、壮彩、爱物、悲愁,皆可以赋展现。
基于汉赋体式的多样性,题材的丰富性,决定了其所本必然不唯一。清人章学诚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1](p152)章氏此论,便不拘泥一端,能就赋体之不同体式、内容,各自溯其源,其眼光是敏锐的。
但是又要看到,从文章体类上说,赋毕竟只是一种文体类别,既然在《诗》、《骚》、战国诸子、《庄》、《列》中,都可找出赋体的一些特征,这说明赋体与它们之间的某些篇章、段落,必然存在一种共性。我们以为这种共性,在于这些作品皆采用西周以来所提倡的,讲究文采的雅言创作。这也是赋在成体之前,作为动词时,它的基本内涵,即雅言的言说、创作形式。
同时也应注意到,章氏此论和其他论赋体之源者,存在一个共同点,即都会提及“楚辞”。如章氏所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刘勰所谓“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等等,都指出了楚辞在赋体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其实不止此二者,凡论赋体渊源者,都会论及楚辞。那么楚辞更准确地说是屈原辞,何以影响赋的形成与发展呢?我们以为,这缘于屈原辞的创作同样是采用赋法,文辞十分艳丽。但同时又要注意到,屈辞的创作虽是采用赋法,然而一些作品的创作已有明确的文体归属,并非全为赋体,可称赋体的只有《卜居》《渔夫》与《招魂》。但若从篇题上看,最早明确以赋名篇的,是宋玉作品。这足以证明,宋玉已有明确的赋体创作意识,赋至宋玉正式标题成体。
二、宋玉的赋体意识及赋体创作
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2](p3020)。并且在宋玉赋中,多涉及与楚顷襄王在一起,可知宋玉与屈原大体是同一时代,仅稍后而已。那么,宋玉作品何以称赋呢?
宋玉赋主要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大言赋》、《小言赋》、《登徒子好色赋》、《讽赋》,以及上世纪70年代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御赋》。仔细研读这些赋作,不难发现,在每一篇赋文的篇首,皆以问对开篇,事实上,问对的内容完全可视为该赋创作的缘由。如《登徒子好色赋》篇中,登徒子以宋玉好色而短之于楚顷襄王前,“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3](p79)于是宋玉为此展开了一番辩说。这种辩说,因为要有足够的说服力,自然讲究语辞文采,及言说技巧。最后,因宋玉说辞精美,“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讽赋》的创作缘由与此完全相同,“唐勒谗之于王曰:‘玉为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大王,愿王疏之。’玉休还,王谓玉曰:‘为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3](p117)于是宋玉又为自己展开一通辩说。这种辩说将宋玉善文辞的特点充分展现出来。
《高唐赋》的表现更直接。在宋玉与楚顷襄王游云梦之台时,宋玉讲起巫山神女的故事,说到了其来去飘逸、丽靡,且有“愿荐枕席”之事,这勾起了本就好色的楚襄王对高唐神女强烈的好奇心,“王曰:‘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3](p51)这里楚顷襄王直言“试为寡人赋之”,不同于“亦有说乎”,不再是让宋玉简单开脱了,而是提高到要求对方创作的高度。“赋”在这里虽是“作”的意思,但绝不是一般的创作,而是意指一种讲究言辞文采的雅言创作。《神女赋》的创作,可以做进一步的证明。
《神女赋》是《高唐赋》的姊妹篇,所述内容是,宋玉为楚顷襄王赋完高唐神女后,夜里楚顷襄王果然梦见了那位神女,第二天就告诉宋玉,宋玉问神女长相,襄王自己描述了一番,大体向宋玉讲述出了自己所梦见神女的形象。但或是因为神女太美丽,自己的言辞不足以描绘她,楚顷襄王显然不满足于自己刚才的那番叙述,于是“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3](p69)楚襄王让本没有梦见神女的宋玉根据自己的描述,为艳美的神女,作一篇赋。足可见赋法创作并非人人可为,楚襄王之所以选择宋玉赋神女,所看重的也正是宋玉是他身边最善文辞的人,即司马迁所谓“好辞而以赋见称”。由此可见,赋绝不是一般的创作,一般的语辞。不然襄王自己的那段并不短的铺叙何以不尽兴呢?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在宋玉赋中,楚顷襄王多次表示“试为寡人赋之”,可知赋是动词,译为作、创作,或是口头上的或是书面的。这种“作”不是一般创作,而是讲究华美文辞、谋篇技巧的有文采的雅言创作。那么,赋即是动词,正常逻辑来说,《高唐赋》《神女赋》应该是“赋高唐”、“赋神女”才对。那么它何以成为名词而作为篇名,进而直指文体性质的呢?
吴承学说:“在先秦时期,文献一般是成篇在前,命篇在后,且命篇的主体以文献的整理者、编撰者甚至抄写者为主。”[4]但战国末期的宋玉创作,已不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宋玉赋的成篇,首先有源于君王的命题在先,或是让其状物摹人,或是让其解同僚掐口之难。同时宋玉的创作又有被命体的意味,即明确是让“赋”之。宋玉完全明白楚顷襄王所谓“赋”的内涵要求,因而完篇之后,合以主题内容,以赋命篇。因此《高唐赋》、《神女赋》的篇名当时就已经存在,非后人所加。宋玉《大言赋》、《小言赋》对此能给予证明。
《大言赋》、《小言赋》是楚顷襄王为满足声辞之需,让宋玉等侍臣所赋的纯粹的文辞游戏,《大言赋》创作在先,《小言赋》在后。其中《小言赋》的开篇有这样一段叙述:
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毕而宋玉受赏。王曰:“此赋之迁诞则极巨伟矣,抑未备也。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小大备。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细,非妙工也。然则上坐者未足明赏,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3](p110)
这段叙述,明确提到了之前所作的《大言赋》,并且楚襄王对这篇赋还作出了评点,可证《大言赋》篇题当时已定。吴承学说:“对篇章的命名,也是文体认定与命体的前提,所以命篇是文章学与文体学发生的基础。”[4]如果说“赋毕而宋玉受赏”之“赋”还是动词,那么“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以及“王曰:‘此赋之迁诞则极巨伟矣’”之“赋”则为名词无疑,且已具有文体之意。由此可以认定楚襄王与宋玉皆已有了初步的文体意识,已开始称谓所作的篇章为赋。这段文字的最后,楚襄王又说“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就可看作是完全的命题、命体作文了。
通过以上所论可知,宋玉相关赋篇的创作,在当时已有篇题,并已自觉认定所作篇章为赋体,可以说这开启了文体之赋的创作,使赋作为一种文体类别进入到中国文学之苑囿。当然这与楚顷襄王“好辞”是密不可分的。楚襄王“试为寡人赋之”之“赋”是渊源有自的,并不是其所造,但将“赋”指向享乐,满足声辞之需,从可信之史料记载看,他确实有“开创之功”。那么作为动词的赋,在先秦有着怎样的渊源及内涵要求呢?
三、赋的内涵及其写作、言说要求
赋作为动词使用,始于西周中前期,其义项主要有诵读、传述、布政等等。这些义项的使用,有一个前提,即建立在语言统一的基础之上,有了一种流行的通语存在。语言学者认为西周在代商统一天下后,为方便国家治理的需要,推广了一种通用的语言,并且普遍认为,这种语言即是《论语》中提及的孔子所使用过的雅言。《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5](p180)雅言即是西周推行的通语,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的普通话。清代刘台拱在《论语骈枝》中即说:“‘雅言’,正言也。……然而五方之俗,不能强同,或意同而言异,或言同而声异。综集谣俗,释以雅言,比物连类,使相附近,故曰‘尔雅’。《诗》之又《风》、《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国之音不尽正,故以‘风’名。”[6](p293)可见当时确实存在一种与方言相区别的雅言。朱正义甚至指出,西周王畿之地的镐京话“以其优越的地位而被人们认可,担当起了雅言的角色”[7]。
王国维在《<周代金石文韵读>序》中说:“余更搜其见金石刻者,得四十余篇,其时代则自宗周以讫战国之初;其国别如杞、郐、邾、娄、徐、许等,并出《国风》十五之外。然求其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8](p46)两周金文的使用场合通常比较正式,所记内容多为祭祀、训诰、赏赐、颂祖等。既然这与包含不同地域十五国风在内的《诗三百》用韵“无乎不合”,只能说明两周确实存在一种通用的规范了的语言。
《周礼·秋官·大行人》载:“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9](p1177)属,郑玄《注》曰:“属,犹聚也。”象胥,即翻译官。即是说每七年行人会召集各诸侯国的翻译官,向他们普及语言,统一他们的辞令;每九年召集各诸侯国的乐师和史官,向他们普及文字,统一声调读音。这可以看做是西周王朝推行雅言的具体措施。因为只有有了一种通用的语言,才方便中央王朝同地方的联系、沟通,才方便政令的颁布、执行。
西汉刘歆在《与扬雄书》中曾提到,“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戏”[10](p518),轩车使者与遒人使者相当于周代行人。代语是方言中义同而词异、音异的语词,整理风诗时可以代换。这对周代曾做过统一语言的工作也是一个旁证。这里对各地采集而来的风诗歌谣,会由专人做统一的雅言化,班固对此有过清晰的叙述。《汉书·食货志》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11](p1123)即是说行人采集各地方言音的歌诗谣谚,献给大师,大师更定其音调,将其雅言化,再由专人(瞽矇)诵给天子。可见大师在此起着重要作用。大师是怎样的官呢,《周礼·春官·大师》载:
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大祭祀,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朄。大飨亦如之。大射,帅瞽而歌射节。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大丧,帅瞽而廞;作柩,谥。
凡国之瞽矇正焉。[9](p714-722)
大师是掌管音律的乐官,行人从各诸侯国采集来的歌谣都要经过他们的加工处理,以使之合声、雅言化,各地风歌谣谚,就转变为诗。大师再教授瞽矇,然后用于祭祀仪式,或君王观政等各种场合。
其中大师所教“六诗”,是六种不同的说诗、言诗形式。诗,如闻一多先生所言,是“志”,是史,是事件、怀抱。自西周统一以来,君王、公卿、大夫创作了许多记叙西周战争、建国、兴盛乃至衰败的诗,加上从各地所采集之诗,这共同构成了《诗三百》成集之前,诗的存在面貌。西周制礼作乐后,实行严格的礼乐制度,根据《周礼》的记载,祭祀、典礼、教育、宴享等等仪式活动,都会伴有相对应的乐歌、乐舞,不同场合,会使用不同的诗乐舞,诗乐舞的表现形式也会不同。大师所教“六诗”,即是从表演、传述或传播等形式上所说的诗的六种不同表现形式。
其中风与赋相对。风指地方音调,即采诗官所采集的地方原生形态的歌诗。而经大师雅化、文化后,教授瞽矇,然后由瞽矇传诵给天子,以观地方之政。这时用雅言的形式诵读风诗,即称为赋。王小盾在《诗六义原始》中通过论证后即指出:“如果说‘风’、‘赋’二法在周代宫廷由不同的瞽矇乐工分司,以实现不同的功能;那么,‘风’的目的便是保存各地的风歌,故用方音背诵它们;‘赋’的目的则是以诗言志(事),故使用不同于风歌的雅言来吟诵它们。”[12](p10)可见赋是一种用雅言言说、诵读的形式。《国语·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弥谤》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3](p10)其中“瞍赋”,即是以雅言的形式向天子吟诵地方风诗。
西周王朝确定好通语,即雅言后,便向全国推行,上文我们引《周礼·秋官·大行人》,“七岁属象胥,谕语言,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就是一种定期向诸侯国推广的具体活动。可想而知,在通语雅言制度推广后,西周在政令的颁布,纳谏进言等各种场合都会使用雅言,因而也就往往称赋。如《诗经·大雅·烝民》所载:
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是赋。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
这里仲山甫“赋政于外”,即是将王之政令以雅言的形式向四方传达。
进入到东周,雅言通语在诸侯国,至少在其统治阶层、贵族阶层应早已普及开来,根据《左传》的记载,春秋早期诸侯国就已有赋(作)诗记事的现象了。如《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左传》闵公二年,卫国为狄人所败,“许穆夫人赋《载驰》”。又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又如《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足可证春秋早期,各诸侯国已可自由地运用雅言作诗记事。
对于各诸侯国来讲,能够掌握周王朝官方语言,并且能够运用其记事言理、表情达意,显然算得上是一种才能。班固说,“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随着周王朝的衰落,确实已无力再颁布政令或是组织起会盟,赋与布政的联系逐渐式微。但随着诸侯国间的交流日趋频繁,各国之间“赋(引)诗言志”,以微言相感,多了起来,有学者甚至认为,《诗三百》最终成集的目的正是在于方便言语交流、称引方便的需要。雅言化了的《诗三百》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庞大的文辞语库,因而成为了士大夫学习、征引的对象。《论语·季氏》篇中,孔子就问其子孔鲤“学诗乎”,对曰“未也”,孔子便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当然不是说不会说话,而是说话没有文采;没有文采,便没有说服力,即其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春秋士人的“赋诗言志”,正能说明这一点。因为引诗往往不是根据“诗”之义,而是根据自己表达的需要断章取义,所看重的正是《诗》之言辞的文采,追求一种有文采的且隐晦的表达。从“赋诗言志”开始,赋即和辞之文采逐渐联系在了一起。据董志安先生《从〈左传〉、〈国语〉看“诗三百”在春秋时期的流传》一文的统计,《左传》、《国语》中的“赋”诗达70余处。这无疑强化着“赋”与讲究言辞文采之间的关联。这一时期,因周王室无力向诸侯国颁布政令,赋作为一种雅言的言说方式,其含义渐渐向两点集中:作诗与引诗。能够掌握赋法,也逐渐成为士大夫外交官是否有才华的体现,所谓“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即是对这一现象最好的说明。
同时春秋以来,行人出使他国,大夫劝谏君王,除了引诗之外,其它相关辞令,也往往会有意修饰、雕琢。《论语·宪问》载:“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叙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5](p357)可见造一则外交辞命,都要经过几人的讨论与雕琢。《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孔子语,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也可见对于辞令文采的重视。
也因此,春秋时期出现了许多善言辞的人,这些人多是行人。这与行人的职业属性有关,行人要出使专对,应对王侯,这决定了他们在言辞上必须要讲文辞、讲技巧,如齐国晏子,鲁国叔孙豹,郑国子羽等等。《晏子春秋》载:“晏子将至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14](p292)《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对行人子羽(公孙挥)的一段记述:
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子羽,且使多为辞令。
可见行人不光会使用雅言,而且还要善用,具体来讲,即是指向言辞的华美与表达技巧。
从另一面来说,不论他们是出使应对他国君臣,还是向本国君主谏言,所述言辞都是在与君、与同僚的问对中展开,而当这些问对言辞被史官记录下来时,便形成一篇篇史料文本。而正是史官对君臣问对的实录,奠定了我国文学作品中的问对体例模式。在各国史官史料基础上编写而成,主要载录春秋史实的《国语》和《左传》,保留了大量这样的问对文辞。
到战国时期,随着纵横家的兴起,凭口舌取富贵的他们,为能使诸侯王采纳自己的策谋,更加注意修饰自己的言辞,甚至虚拟想象着与君王对话,来演练自己的说辞。《战国策》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战国纵横家们的这种行为,是在史官真实记录君臣问对的基础上,开启了假设问对的先河,这已非常接近文学创作。至此,以问对开首,继之引出自己所言之辞的创作模式已经形成。这种创作因为同样是用雅言,且强调文辞的华美,因而也便与赋联系了起来。以致后来,问对开篇继之以引出所赋内容,也成为了赋体的一种标志。
四、屈辞赋体论证
屈原活动于战国中后期,与纵横家苏秦、张仪等同时,是楚怀王时期的左徒。左徒是何官呢,赵逵夫先生通过论证左徒即左登徒,而登徒是参加外交活动的官员,即“行人”,进而指出“楚国之左徒相当于中原国家的行人”。[15](p149)准此,那么屈原左徒之职也就类似于行人之官,如上文所述,行人之官一项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讲雅言,善文辞,即善赋。《史记·屈原列传》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司马迁这里对屈原官职的描述正符合行人之官的特点,且明确说屈原“娴于辞令”。屈原虽然生活在战国时代,但依然秉持着传统士大夫的气质与情怀,在遭遇谗害后,并没有选择离开楚国,而是将“娴于辞令”的才能转向了赋法创作,以抒情、明理、言志、讽谏。
那么屈原之赋(创作),是否有文体意识呢?我们以为是有的。屈原在一些篇章中,有过自己的创作自述,如《抽思》篇中,他说“道思作颂,聊以自救”,颂即是诗;《悲回风》中,则明确说到“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可见屈原显然清楚自己是作诗,以明志、抒情、安抚心灵、申辩自身清白。屈原用“赋诗”二字,则表明他虽处于战国中后期,但仍采用春秋以来传统士大夫赋诗言志的传统。屈原清楚“赋”有着怎样的内涵和写作要求。因此可认定屈原作品皆是采用赋法创作,这与其任左徒时的个人修养是分不开的。但屈原大部分创作都有明确文体指向,一些明显是采用赋法作诗,如《离骚》《九章》《天问》;并改作了《九歌》,去除其俚语鄙辞,使其雅言化,这类似于周大师的工作,即将风歌雅化,但《九歌》的文体性质不会变,《九歌》还是歌体。此外,他还创作了《卜居》、《渔夫》、《招魂》。《卜居》、《渔夫》、《招魂》这三篇文章,篇首都以问对引起,这与春秋以来行人外交辞令以问对开篇,战国纵横家以问对引出言辞的创作模式是一致的。在这三篇文辞中,屈原没有创作自述,因而没有明确的文体归属。我们以为若稍后的宋玉在楚襄王的命题下,强调采用“赋”法创作,以问对开篇,或描摹人物,或解掐口之难,而创作的作品可称为赋体,那么屈原这三篇同样是以问对开篇,采用“赋”法而创作的文辞,何以不能称为赋体呢?
《卜居》、《渔夫》明确以问对开篇,引出所言之辞,以述己志。篇首的问对呈现出口语化、散文化特征;而阐述道理的主体部分,有文辞的铺排,且合乎韵律,已是韵散结合。如《卜居》中:
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絜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乎,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
这一部分一连出现了数组“宁……,将……”句式,形式固定且呈现出铺排的特点。从韵律上讲,又是合乎韵律的,除去句子末尾的语气词“乎”,其用韵情况如下:
耕(耕部) 名(耕部)
身(真部) 生(耕部)
真(真部) 人(真部)
清(耕部) 楹(耕部)
驹(侯部) 躯(侯部)
轭(锡部) 迹(锡部)
翼(职部) 食(职部)
由此可以看出,这部分句子用韵是非常规整的。就正篇文辞讲,已是韵散结合,句子短长结合,散化特征明显。《渔夫》篇的体例与之相似,已符合后世对赋体的认识。
《招魂》开篇同样叙述创作缘由,以问对形式引出招魂之辞,其文辞之精美,罗列之广丰,已开汉大赋之先,如:
天地四方,多贼奸些。像设君室,静闲安些。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实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谖些。光风转蕙,泛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砥室翠翘,挂曲琼些。翡翠珠被,烂齐光些。翦阿拂壁,罗帱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
这也完全符合赋体的体式规范。姚小鸥在《赋体文学源流与〈招魂〉的文体性质》一文中,就把《招魂》文本与《艺文志·诗赋略》和《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有关“赋”的理论加以观照,认为《招魂》完全符合有关赋的理论界定,也认定《招魂》为赋体。因而,我们以为屈原辞中《卜居》、《渔夫》、《招魂》可以定为赋体。
屈原将自己善文辞的创作才华用于讽怨、抒情、明志以及自慰郁结之生命;而宋玉将这种才华用于君王的声辞享乐。这只是所赋内容的不同,相同的是,都是运用讲究言辞文采的创作形式,即“赋”。这也是《诗》、《骚》、战国诸子、《庄》、《列》中,都可找出赋的某一体征的原因所在。杨雄曾言“诗人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丽是赋法创作的共性,因为它们都需讲究言辞文采。不同的是,屈原用于言志、讽谏、抒情,因此称则;宋玉等汉赋作家用于铺排消遣、娱乐,为赋而赋,因此称淫。但不论怎样,赋由作为一种讲究文采、讲究华美文辞的雅言创作方式、言说方式,作为动词,在用于诗歌创作,外交辞令创作等等之后,终于在战国后期,经屈原而至宋玉,迎来了自己独立成体的时刻。赋独立成体之后,因其体式阔大、自由、言辞量大,描述事物及表情达意充分,因而被广为采用。于是便形成了多题材、多内容表现的现状,因而蔚为壮观。
班固在《艺文志·诗赋略》中的概述可谓基本描述出了赋体的形成过程:

班固对于春秋时期“赋”与《诗》的关系的讲述是比较客观的。讲到屈原时,他说:“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他能看到屈原一些作品有古诗之义,这是可贵的,但认为屈原作品全为赋,就片面了,是对赋法(写作方式)创作与所作文体的认识混淆。
[1](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吴广平编注.宋玉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1.
[4]吴承学.命篇与命体—兼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发生[J].中国社会科学,2015,(1).
[5]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清)刘台拱撰.论语骈枝(一卷)[M].续修四库全书第1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朱正义.周代“雅言”[J].渭南师专学报,1994,(1).
[8]王国维著,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M](第四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8.
[9]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清)钱绎撰集,李发舜、黄建中点校.方言注疏[M].中华书局,1991.
[1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王小盾.诗六义原始[A].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3]陈桐生译注.国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4]孙彦林,周民,苗若素译注.晏子春秋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1.
[15]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康邦显]
2016-05-02
张世磊(1986— ),男,山东梁山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
I206.2
A
1001-0238(2016)03-006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