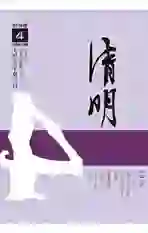诗歌中的“在场”与“不在场”
2016-07-19王士强
王士强
诗中的“在场”与“不在场”是一对颇为有趣、值得玩味的范畴,有时不吝笔墨连篇累牍所书写的,其实并不是作品真正要表达的;有时全篇无一字提及,却是须臾未曾离开的焦点与重心。有时浓墨重彩下笔千言但却基本无效、约等于零;有时寥寥数语却值得用千倍、万倍的篇幅来阐释且依然阐释不尽。诗歌以形象见长,需要“在场”,如此诗歌才能够成为“实有”,而同时,诗歌真正要表达的又往往是“不在场”的,是在言说之外的,它是穿行于语词的缝隙但却看不见摸不着、不可把捉的精灵。诗歌妙在于“在场”与“不在场”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也就是说,“在场”的各部分之间应该发生化合反应而产生出召唤性、开放性的“不在场”,否则作品便不能引起人的兴发感动,造成艺术上的失败。阅读中我们会遇到,许多的作品并没有对生活特别的发现与感受,而只是在说一些寻常的、人云亦云的话,诗意、诗味寡淡甚至意味全无。还有一些作品,诗中“在场”的只是一些各不相干的材料、意象,彼此缺乏有机的、非如此不可的关联,不能结构为一个整体,也不能形成有效的“不在场”的艺术空间,这同样是一种艺术上的失败。
总的来说,诗歌中应该既有实又有虚,实中应有虚,虚中亦有实,同样,诗歌中应该既有“在”又有“不在”,在而不在、不在而在,应该写出在之不在、不在之在。这么说并不是玩语言游戏,而是指出,诗歌作为一种高级的语言活动,它必然是辩证、复杂的,有的部分是不可知、不可解的,是在悖论、在对于表象的逆反与逃逸中产生的。
李寂荡的《生的两面》典型地体现了“在场”与“不在场”的关系,一方面是通过对于生存境象的观照体悟到“生的坚忍,生的艰辛”,颇具现实之关切,另一方面写了在复杂世相背后个体的孤独处境和世界“虚无的一面”,类似于鲁迅所说的“唯黑暗和虚无乃为实有”,由之而体悟到“生的苦痛,生的不堪”,这里便写出了实有(在场)背后的虚无(不在场)以及虚无(不在场)之为实有(在场),如此也与佛教关于“色”与“空”的阐释相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由之全诗打开了一个极为丰富的诗性空间。而《厄运》全诗所写也正是“不在之物”:“命运”,它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与个体的生存形成紧张关系,却又全无踪影,无从对抗,仿佛陷入“无物之阵”:“当我忍无可忍挥刃刺向他/他却了无踪迹”,而这样的命运“终与我如影随形”,其中的情状,让人思之不尽、品味再三。《响水潭》更多的是从正面、从在场的角度来写自己所追求、热爱的事物,笔触具体、细腻、生动,而在如此的繁复、细腻的“在场”背后,呈现了一种静谧、优美、和谐的意境,以及安静、淡泊、自然的生命形态,实际上,并不在场的后者才是诗歌所要表达的重点,它由前者生发,却又超乎其外,构成了诗之为诗的最为重要的部分。
殷常青的《云烟》所写是他所生活的“平原”,其所体现的不仅是身体的“在”,同时也是精神的、灵魂的“在”,表达了主体与环境之间的融洽、和谐状态。与“生活在别处”不同,《云烟》所表达的是生活在此处、生活在这里,如全诗起首所写:“如果在平原上行走,/你要一再放慢速度,/要从远方收回目光——”,全诗也正是“放慢速度”“从远方收回目光”的,关注的是眼前、身边,发现并欣赏其中的“美”与“秘密”:“我心里有春风,有种子,/我诗里有小青河,/我羞于向枕边人开口,/说出这样隐秘的欢欣,/因为平原上依然有着——/更多的美,更多的秘密。”平原上的生存安然、平淡,其中的事物“平凡、无奇”“庞杂、繁乱”,“在这里,爱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爱着,/依旧还在平原,形色匆忙,/舍不得离开这乏味的世界。/是的,一年一年过去了,/岁月无情,唯一的奇迹——/你还在这里坚持爱着。”如此,他的爱是富足、从容、宽阔的。在主人公这里,“平原”即是他的“祖国”:“我把祖国搬到平原上,/从此不出门,哪里也不想去。”而“祖国”实际上也意味着世界,意味着一切,诗中的“平原”即是一种世界图景、生存范型。全诗所真正要表达的是其中所显现的淡泊、豁达的生存状态,这是诗歌的“在场”之后所提示、指向的“不在场”,显示了一种通达、睿智的人生智慧。当然,这里的“平原”本身既可以看做是一种“在场”,也可能是理想、远方,是一种“不在场”,是在反向上对于“在场”的反写。
阿成的《云水谣》写身边的风雨,写在风雨之中道路上的艰难行进,但其念兹在兹的却是不在场的“你”,这与海子《日记》中“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的“姐姐”有同工之妙。与海子诗歌不同的是,这首《云水谣》所表达的情感更为隐晦、复杂,包含了多种的理解可能,有着更复杂的人生感喟。《山水课》一诗则很大程度上是以山水为师,从而还原、建构一个更高、更合乎理想、“比原来更妙的世界……”。《唯有黄花和青草可以信赖》写老屋坍塌、村庄陷落、故人老去,同时也写了在“残垣断壁、古木砖石之上”所生长的“漫无边际的野花和青草”,写出了与衰朽、败落相对比的成长与生机,写出了生命的顽强与生生不息,由此,诗歌不但表达了对具象、在场事物的关切,同时表达了对更具普遍性的、生命本体的一种态度。
马端刚的《阴山笔记》对其所身处的“阴山”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书写,阴山既是客体对象,同时也是主体的外化,诗中包含了丰富的人生感悟,在并不长的篇幅之内,却包含了关于个人与世界、个人生活的巨量经验,体现着复杂而深沉的关切。“阴山”是在场的,却同时勾连出了整个世界与人生,成为一个具象与抽象结合、有着超越性的审美空间。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的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到诗歌中来描述一个永恒的悖论,言说永远是不到位的、言不及义的,一句话说出时它已变形,其最为真切的意义已经远走,正如“道”“可道”,然而一经道出已非“常道”。所以,“在场”与“不在场”必将是一对天生的密友与冤家,两者之间辩证性的遇合,是诗意产生的前提。
责任编辑 赵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