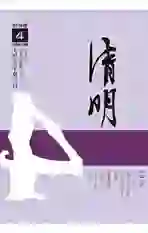食物十记
2016-07-19徐迅
徐迅
白 菜
中国人喜欢以“大”自居。什么大中国、大上海、大运河……说起这大,都有自豪之感,但一叫大白菜却有轻蔑之意。物以稀为贵,可见大白菜在所有的菜疏中是个大路货,是稀松平常之物。说所有的菜蔬,我能想到的有辣椒、莴苣、茄子、黄瓜、豆角、芹菜……辣椒,我们那里又叫大椒。比如,大椒炒肉、大椒炒毛鱼什么的。白菜炒肉有,但没有白菜炒鱼。白菜炖粉条、白菜豆腐,还有白菜氽肉。我长时间不认识“氽”字,吃一回便问一回,吃完又忘。
小白菜,地里黄,三岁四岁没了娘……南方的白菜似乎适宜叫“小”。小时候,我不知道白菜有大、小之分,以为只有小白菜。妈妈手里时常提着一捆小白菜,水淋淋、绿茵茵的,鲜亮得很。特别是小白菜的茎白嫩得透亮。因看一本书里有一个女人外号叫“小白鞋”,好像是个地主婆,我还总把小白菜与小白鞋混淆在一起。后来知道有一出戏叫《杨乃武与小白菜》,在加深对小白菜记忆的同时,我这才发觉自己的知识和记忆早已混乱不堪。小白菜嫩嫩的,有人就叫“嫩白菜”——说起来,白菜就是这种菜蔬,可以从“嫩”吃到老,吃到只剩下白菜帮子。有人借此骂女人“老白菜帮子”,那是骂老了的女人。皮肤白皙、漂亮水灵的小姑娘熬到老,熬成干巴艰涩的老女人,就被人说成是白菜帮子。但这只能骂别人家的女人,一骂自己家的女人,肯定就有一场海陆空大战。
那时,我家里油水有限,总觉得妈妈炒的小白菜很“柴”。柴是土话,是说白菜有些干巴,像是没蘸油。但别无他物,妈妈总变着戏法让我吃。或把白菜洗净做成一锅白菜汤,绿莹莹的,让我喝;或挖出白菜洗净晾干,然后腌起来,等到没菜可吃时,做一碗腌白菜,酸溜溜的吃着下饭。后来吃到韩国泡菜,我心里一愣,小时候,我妈妈也腌制过这种菜,妈妈何曾去过韩国?她连县城也只去过有限的几次。白菜能做许多菜,醋溜白菜、白菜肉丝,还有让我总念,又总念不全的白菜氽肉……几乎有上百种吃法。但吃了很多白菜,我还是忘不了小时候母亲给我们炒的菜。那样的白菜叶子,盛在碗里青葱葱的让人怜爱。现在有人一说起青葱岁月,我立马就想起小白菜。那用稻草扎着的一束小白菜,绿盈盈、水灵灵的,骨子里就透着清爽,像某位南方才子的文字,干净、养眼。
我从南方到了北方生活,发现小白菜被人称作油菜。有一回,到一位朋友家里玩,看他家阳台上堆放了许多白菜,说是入冬储藏的大白菜。这时,我才知道,还有一种白菜叫大白菜,是可以储藏的。旧时,北京人家总爱把大白储藏在地窖里。现在没有了地窖,只能凑合着放在阳台上。新鲜的带着根和老叶的白菜,能储藏一整个冬天。冬天里,要吃那大白菜,就拨去大白菜外边青黄的老叶,露出那被裹着的柔嫩嫩的菜身子——北方人家都把冬天储藏大白菜当一件大事。我当时听了就觉得新鲜——因为,在我们南方,白菜是白菜,油菜是油菜,白菜根本不用储藏。想吃,就会跑到地里随便掐上几把,简单得很。冬天下雪,薄薄的一层雪不用管它,一旦大雪盖住了白菜,白菜努力伸出的绿茸茸的叶片,就像是白雪的耳朵。看主人来掐白菜,就像是揪白雪的绿耳朵了。
北 瓜
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中国地理上把这一带称为江淮之间。江淮之间虽然土肥物丰,但人的身份却有些尴尬。北方人当他们为南人,南方人把他们当成北人。当事人自己百口莫辩。当然,有不东不西,就有不南不北。不南不北无妨,不东不西就是骂人了。偏偏有不南不北的人,就有不南不北的瓜。比如南瓜、北瓜。
“北瓜”这瓜名我从小叫到大,可能还要叫到老。突然被人改叫成了南瓜,我听了心里老大不舒服。感觉就像人到中年却无端地把姓名改了。改姓名的也有,但人家心甘情愿。北瓜改成南瓜,就有点让人不情不愿。有一回朋友请我吃饭,听他说上一盘南瓜饼,待端上桌,我看是我熟悉的北瓜饼,不解地盯着他。他也不解地盯着我,好像我就是那瓜——南瓜也有叫倭瓜的。我虽不是倭瓜,但在他眼里分明读出了“倭”字。无话可说。结果,是他吃他的南瓜饼,我吃我的北瓜饼,各自心猿意马。
东、西、南、北的,奇怪的都有对应的瓜。但落在实处的只有三样:冬瓜不是东风的东,是冬天的冬。冬瓜长得横竖一般粗,好看得像枕头。淡青色的瓜面上一层薄薄的霜,似霜降的霜。西瓜好认,我二十几岁才认识。那时,父亲说种西瓜比种稻好,心血来潮地种了一田西瓜,结果让一场洪水淹得烂透了,气得父亲整天唉声叹气。剩下就是北瓜了——北瓜颜色黄爽爽的,有的长得像大葫芦,有的像磨盘,还有的像一口金钟。金钟敲起来声音当当的,北瓜声音却闷闷的,响而不亮。
北瓜饼、北瓜粥、北瓜粑、北瓜饭、北瓜疙瘩、北瓜糊,煮北瓜……在乡下,北瓜被翻做出许多吃的花样。但在我记忆里,北瓜更多的是用来做了猪饲料。我们那里人喜欢米饭,也喜欢蔬菜,北瓜顶多用来灾年救荒时吃。不过,有一种叫北瓜丝的菜,我小时候特别爱吃。北瓜青嫩嫩的,嫩得能掐得出汁来。摘下嫩北瓜,洗擦干净,用刀切,切成条丝状。绿皮黄心的,用热油炒炒,吃在嘴里,鲜嫩可口,还有一种粉粉的味道。后来在北方,我偶尔也吃过南瓜丝。至于像南瓜饼、南瓜粥、南瓜粑、南瓜饭、南瓜疙瘩、南瓜糊,煮南瓜……尽管姓氏早已南辕北辙,但吃法却是南北一统了。
有几年时兴说什么浑身都是宝,北瓜也是。北瓜子就是个宝。剖开北瓜剥开瓤子,里面就有星星点点、大小一样的籽粒,把这些籽粒掏出来,洗净,放在太阳下晒晒,就是白净净的北瓜子了。白白的瓜子,炒在锅里香喷喷的。吃在嘴里,上下牙齿一嗑,脆脆的,还有一种“吱”的声音。过年时,北瓜子是上好的招待客人的东西。主人热情,客人也乐意吃。有女人嗑北瓜子,“滋溜”一声,壳在她嘴里就“噗”地弹出,面前就有一道醒目的弧线,妩媚得很——说女人长了一副瓜子脸,漂亮。那瓜子便不是葵花子,也不是西瓜子,说的就是白净净的北瓜子——葵花子尖尖的,黑黑的;西瓜子黑黑的,瘪瘪的……女人的脸若长得像那样的瓜子,不跑到美容院里整容才怪!
人们在地里收拾干净了北瓜,总会留下特别健康壮实的瓜籽粒儿,到第二年种在地里,让它发芽。待长出绿绿的秧子,就在山边地头辟开一条条土埂子,叫北瓜埂子,学名北瓜垄。再把北瓜秧栽到垄上。北瓜秧在垄上生根一长开,牵藤挂蔓的,就开着一朵朵金黄色的花儿。花儿鲜艳艳的,像是一只只大喇叭,在地里喧闹得很——吾乡作家说这种黄花,招蜂惹蝶,热闹得就像小报娱乐版的明星绯闻。
山 药
在名人的故乡难见到名人,但在名产的故乡肯定能吃到名产。名人有时是故乡荒腔走板的传说,但名产却是故乡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一见面就要寒暄、唠叨。有一回我到了山药的产地河南焦作,在餐桌上听几个人窃窃私语,然后又哈哈大笑起来,那神情好像是背后说人坏话——当然,很快我就知道他们不是说人坏话,而是说山药的坏话。说什么坏话,这里卖个关子。
山芋、山楂、山药蛋、山粉圆子……在姓“山”的能吃的特产里,我认识并吃到山药的时间应该很迟。原因便是吾乡不生产这玩艺。后来工作到北方,第一回吃山药似乎是“山药拔丝”。那东西用筷子夹,轻易夹不动,好不容易拉出一条,油光闪亮、状若发丝。朋友看我吃拔丝的一筹莫展,就教我把那东西放进桌上预备的一个盛满清水的碗里。顷刻间,那发丝晶莹剔透的就凝固了起来。吃在嘴里脆脆,甜甜的,因此印象深刻。后来,我知道拔丝类的菜还有苹果拔丝、地瓜拔丝、香蕉拔丝……这些拔丝味道大同小异,山药拔丝并没有显出什么特别。
山药与山芋差不多,轻车熟路的吃法是洗净、去皮、切片,放在米里一起煮粥。煮大米、小米粥都行。两种山药粥各有所长。白片状的山药隐在大米粥里,用筷子或勺子一翻,山药立即现出身子,仿佛“浪里白条”;小米粥里的山药,在黄米里显得有些异样,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不合群。再就是用山药蘸糖吃了。这种吃法一般都在饭店里。山药洗洗干净,连皮也不刨,就剁成一节节的香蕉状。山药一上桌,毛须须的,似有水意,让人感觉它是刚从地里挖出来的,有些自然、乡土的滋味。当然,山药吃在嘴里都是粉粉的、柔柔的。我说“山药怀乡”就是想说这两层意思:一是说山药生长在怀乡(现在焦作一带,即古时怀庆府,称怀乡);二是说,在城市里餐桌上猛然见到毛须须的山药,让人会陡然平添一种怀乡的感觉。
梁实秋先生写过一篇《北平年景》的散文,回忆吃年饭。他说:“……年菜是标准化了的……一锅炖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一一管够。”山药有许多的做法,有醋溜山药、蜜汁山药、山药炒肉片,等等,但他说山药又是一碗,我私下里认为该是山药煲汤才好。妻子用山药做菜,最拿手的就是用山药煲鸡鸭、排骨的什么汤。切好刮了皮的山药,又切好排骨或者鸡鸭,再把这些东西一起放进砂锅里,用文火慢慢煲制,直煲出汁味来。那汤轻轻喝一口,口味鲜美,再咬一口山药,山药粉团团的,回味绵长。人们都说舌尖上的美味,我觉得山药煲汤算是一味。
山药本为食物,叫薯蓣,根形似芋,其甜如薯。《神农本草经》上将山药列为药之上品,谓“薯蓣味甘温,主伤中,补虚赢,除寒热邪气,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红楼梦》里也有山药制作的名叫“枣泥山药糕”的美食,说是秦可卿在病中所服的一种滋补品——但这么好的滋补品,名字叫得不仅土,还很曲折:先是唐太宗名豫,避讳而改名薯药;后遇宋英宗,又避讳其名曙,这样才改名为山药——刚才,我在前面说,有人说山药坏话,其实是一个段子,那段子是说“男人吃了女人受不了,女人吃了男人受不了,男女都吃了床受不了。”这段子有点像谜语,它让人猜着,也让人在不知道山药复杂的身世情况下,就知道了它的暧昧。
土 豆
对于土豆,我是先知道山药蛋,后来才知道土豆名字的。这就如同村里一块长大的朋友,我是先喊他的小名,然后才喊他的大名。但没想到,土豆的名号很多,广东人叫它“薯仔”,江浙一带人叫它“洋山芋”,还有地蛋、马铃薯、荷兰薯什么的……这也好比一位作家起了许多的笔名。说来,我知道山药蛋就是因为喜欢文学,那时文坛上“荷花淀派”“山药蛋派”流行,我由荷花淀而知道孙犁,由山药蛋知道了赵树理。
在没有见到过山药、山药蛋时,我总是把它们当作是同一物种。山药、山药蛋,怎么看,它们也像有紧密的血缘关系,像一对父子或是一对母子。但后来一见,才知道它们风马牛不相及。山药出自本土,山药蛋却是舶来品。就是入菜,山药也是没有人切成丝的。刨了皮的山药粘粘糊的,痒人,切片已属不易。但土豆能切成丝。据说,人们吃土豆一般都从吃土豆丝开始,在土豆制作的菜肴里,最难做的就是土豆丝。土豆去皮、切片,再切成丝,要刀工好;炒土豆丝时,酱油配料要调配得好;土豆丝下锅出锅,还要火候掌握得好,不然土豆丝就炒成了黑糊糊的黑浆糊。
我同事里有山西人,我们一起吃饭时,他必点土豆丝。清爽爽的一盘土豆丝端上桌,他就急不可耐地倒上醋,吃得津津有味,通体舒泰。除了土豆丝,他爱吃土豆炒肉片、土豆炒青椒、醋溜土豆片……等所有与土豆有关的菜什。土豆,在我是若有若无,于他,却是必不可少。有一段时间我喜欢吃尖椒肉丝,我们一起吃饭时,我为他点一个土豆炒肉丝,他就回报我一个尖椒肉丝。两盘肉丝,惹得饭店里的老板娘一脸的糊涂。我们相视一笑,一种温暖各存于心。或者为了迁就我,他就舍了点土豆,点了我能接受的菜。于心不忍,我慢慢念一句伟人的诗句“土豆烧好了,再加牛肉。”自己径自喊老板娘点一盘“土豆烧牛肉”。有趣的是如此几番,我居然喜欢上了土豆烧牛肉。
“山药蛋开花结疙瘩,圪蛋亲是俺心肝瓣。半碗豆子半碗米,端起了饭碗就想起了你……”同事不仅喜欢吃土豆,还喜欢唱山西民歌。唱得很地道。受了歌声的感染,我就以为土豆产自他们山西一带。有一回,我俩莫名其妙吃了回肯德鸡,我见到洋餐里有薯条、土豆泥的菜,就私下咕囔,说怎么外国人也有土豆,他笑着说,土豆本来就产于南美,后来是经欧洲引入中国的。“土豆”是它的中文名字,这就像“大山”“夏克立”之类的明星,到了中国以后起了中国名字——当时这两位洋人在荧屏上正火。我一听,大快朵颐,吃土豆而增加了学问,这是我第一回吃洋餐的好处。其实,我们南方有很多豆子,比如,黄豆、蚕豆、绿豆、豇豆……但南方的豆子似乎如南方人一样,小巧玲珑,温顺可人。拿土豆跟南方这些豆子一比,就有点憨憨,朴拙的样子。后来,我看英国电视剧《憨豆先生》,看到憨豆先生搞笑的样子,我就一乐,我觉得土豆到底有洋基因。憨豆说的一定是土豆。
现在想来,土豆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吃的。但现在却能接受,也时常地吃上几口。这里面好像有那么一个过程。我的能吃土豆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然人被驯化为社会人,南方人被驯化成北方人的过程,这里面不仅有味蕾的变化,还有人的胸襟、见识和包容。
茄 子
人多嘴杂,有人们爱吃的菜,也有人不爱吃的菜。有人偏食,就有人挑食。比如我的兄弟姐妹中就有不吃莴笋的,还有人不吃黄瓜。这与家族遗传基因是否有关,我没有研究。一位堂弟不吃葱蒜,有一次我们一起到人家做客,主人弄了一桌菜,他一口不吃,惹得主人心里很忐忑。我挑食比他好一点,原来不吃茄子,现在吃了。我把这例子说出来试图说服堂弟。但兄弟姐妹们听了,眼睛都愣愣的盯着我,好像我说得是一个笑话。
我以前不吃茄子,不吃就是不吃,也没什么理由。从南方到北方工作,我多年吃的都是公共食堂。这公共食堂也是一家部委食堂。不久前,网上有人列举部委食堂吃饭的大便宜,我觉得那时候的情形比现在要好。那时不像现在这样吃自助餐,菜的品种也不多。在食堂里吃饭要排长长的队。这样排着排着,轮到谁,碗一伸进打菜的窗口,师傅不容分说就将一勺子菜倒进碗里。某一回,我的碗里就这样装上了茄子。我当时不知道是茄子,猛一看有点像红烧鱼,用了不少的酱油或蚕豆酱,酱糊糊的。吃完了,问人,想不吃都来不及了。只是吃在肚子里,倒也没什么反应。
吾乡的茄子是时令菜蔬,一年只一季。不像现在大棚茄子,一年四季菜市场上都有。妈妈栽茄子时,总喜欢将茄子与辣椒栽到一块地里。一排大椒,一排茄子。茄子大椒栽下地都要精心管理,每天傍晚还要浇水,施肥。小时候浇水施肥这两种活计我都干过。我也因此在菜地里看到茄子和大椒的生长。两种植物开始冒绿叶,渐渐的,茄子在绿叶里开出紫花,花谢时,茄树上便打起紫色的果实。一种紫色代替另一种紫色;而大椒也由开始的绿,变成绿红,变成红色。同一块地里,茄子圆溜,大椒细长,绿叶掩映着紫茄和红辣椒,让人就有一种眼花缭乱的喜悦。特别是清晨,菜园里湿漉漉、水灵灵的,色调格外醒目……大概到了七八月份,茄子能采摘了。茄子好油,妈妈烧茄子主要是煮,妈妈好像与大椒一直较劲,把茄子也与大椒一起放在饭头上蒸。饭好了,茄子也好了,然后把它们一起放进锅里用油烩。茄子烂烂的,其实用手撕开,蘸点什么佐料也可以吃。还有一种炸茄盒,做法也简单,就是把茄子割肠剖肚,里面放进肉馅,蘸蘸面粉,然后放进油锅里炸。茄子盒很多人爱吃。我却对这名字不理解,也不喜欢。先入为主,我只对红烧茄子感兴趣。尤其是机关食堂里的红烧茄子,仿佛落寞的公子忘不了初恋。
朋友胡竹峰写过一篇关于茄子的文字,说他有段时间不敢吃茄子,吃到就吐。他比我不吃茄子时的情形厉害。他说茄子像一位“紫袍将军”。妙而有趣。想那茄子挂在故乡的菜园里,挂绿披紫,俨然就是一位披胄带甲的戍边将军。现在,我知道茄子还有很多的别名,比如紫茄、白茄、落苏、昆仑瓜、矮瓜……一个个都非常好听,文字写起来也美。只是人们还是叫惯了茄子。尤其是在拍照时,人们齐声喊一声“茄子”,脸上都露出灿烂的微笑。当然,这算是茄子的一种异秉,是瓜果菜蔬里的一桩美谈了。
萝 卜
萝卜如人参,亦如人生。说萝卜如人参,是民间的经验老到。说萝卜如人生,也有很多民谚俗语。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拔出萝卜带出泥”“花心大萝卜”等。美食家汪曾祺先生写到萝卜时说:“我们那里说在商店学徒(学生意)要‘吃三年萝卜干饭,意谓油水少也。学徒不到三年零一节,不满师,吃饭须自觉,筷子不能往荤菜盘里伸。”这也是拿萝卜说事。三年萝卜饭不好吃,但被人家说成花心大萝卜,恐怕那人也好受不到哪里去,起码他的爱情观就让人可疑。
萝卜在《尔雅》有记载,称为“莱菔、葖、芦萉”,《说文》中唤作“芦菔、荠根”,《诗经》里叫做“菲”。像个老古董,播种的历史久远得吓人。但从种子下地到发芽破土、长大成形,它的生长过程人们一览无余。收获起来也很容易。拽住叶子,稍稍一带,叶子带萝卜的就到了家。收获后的萝卜可以从头吃到尾。叶子切碎,用盐拌拌,或放锅里炒炒就能吃;小而嫩的萝卜收拾干净,圆滚滚的不用管它。大的,再用刀切成两瓣,放在阳光下一晒,腌成萝卜干或萝卜枣。有人把萝卜枣和辣椒酱放进玻璃瓶里腌制,白白的小萝卜挤在红红的辣椒酱里,有品相,也有嚼头,早晨伴着吃稀饭,脆脆的,香喷喷的。现在我回老家,朋友还会把萝卜枣当作礼品送我。萝卜枣,有人说是“萝卜鲞”。我觉得小萝卜形状似枣,吾乡方言说“萝卜枣”,一定是指这个。还有,萝卜的叶子绿茵茵的,吾乡人叫它“萝卜缨子”。
到了北方,我知道萝卜也是北京人冬天爱吃的一种美食。过去的北京街头有各种各样的小吃摊子,卖萝卜的小贩叫“萝卜挑儿”。在数九寒冬的日子,无论白天或夜晚,那“萝卜挑儿”总是吆喝着“萝卜赛梨,萝卜赛梨”穿街走巷地卖萝卜。乡贤张伍说老北京有一种卖水萝卜的,在胡同里吆喝着“水萝卜赛梨,辣来换!”声音凄婉哀怜,其父恨水先生听了总是百感交集,因此填了一阙词:“谁吆唤,隔条胡同正蹿。长声拖得难贯。硬面饽饽呼凄切,听着教人心颤。将命算。扶棍的,盲人锣打叮当缓。应声可玩。道萝卜赛梨,央求买,允许辣来换。”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与文人的哀痛之情跃然纸上。
说萝卜赛梨,又说萝卜赛人参。看来吃萝卜总是没错的。我在冬天里吃萝卜能吃出一头汗来——冬天里,外面白雪皑皑,大雪封道,与几个好朋友一起在屋里围着火锅,听着萝卜羊肉火锅烧得咕噜噜地响。其时,佐以小酒,推杯换盏,吃羊肉萝卜,是人生惬意不过的事。羊肉沾了萝卜的鲜嫩,萝卜吸了羊肉的膻腥,萝卜入口即化,羊肉也绵软滑溜。我本家有一位小爹爹喜欢荤肉,口头禅是“喜精爱肥腥不怕”。萝卜的性子好像与他似有一拼。萝卜炖牛肉、炖羊肉、炖排骨、煮鲜鱼都是美味。萝卜鲫鱼汤,那萝卜与鲫鱼一起用文火一起慢慢熬,熬出的汤如乳白色,其味鲜美无比。
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提供过一份菜单:说用萝卜丝炒鱼翅,那萝卜丝要放在鸡汤里先后焯两次,才能和鱼翅一起炒。以“令食者不能辨其为萝卜丝、为鱼翅”为最高境界。我家也做过萝卜丝,萝卜用刨子刨成细丝,放在太阳下晒干。晒干后的萝卜丝白白净净的,真的形似银鱼。但妈妈只用萝卜丝拌饭吃。平常人家只信青菜萝卜保平安,不可能天天吃鱼翅的。人们说萝卜如人参——那人参能补肾、补血、补肺、补气,是人们益寿延年的上等补品,萝卜有如此同等身份,也算是前世修来的福份。
丝 瓜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这是因为地里的白菜都要下市了。白菜下市,地里就腾出了空。乡村四月闲人少,一般农家总是自己闲不住,地也是不让闲的。空地一出来就要种瓜点豆。凑巧,应了节候的就有黄瓜、北瓜、丝瓜、茄子、大椒、葫芦……这些菜蔬都是种子播种栽培。妈妈收藏这些菜种,总喜欢用玻璃瓶。这样,什么瓶装什么菜种一目了然。到了播种的时候,妈妈拿出这些菜种子,就像拿出什么宝贝。
如同戏曲里的生旦净末丑,这几种菜蔬虽然都要粉墨登场,但播种也各有各的戏法。比如大椒、黄瓜和茄子,只用撒在一块平整好的地里,而北瓜、葫芦和丝瓜则要在地头专门挖出一条土埂,即垄。因为这两样菜都是葫芦科的攀援植物,都需要牵藤绕蔓的。不同的是北瓜、葫芦可以大片的播种栽插,但丝瓜不用。妈妈栽培丝瓜,先用温水浸洗丝瓜种子,然后找一个破废的瓦钵或者瓦缸,在里面装上细土和草灰,再把丝瓜种子小心地放下去。等丝瓜种子发芽,也不是成片的栽播,而是找院墙的角落或棚架,或者干脆就搭一个丝瓜架子。只栽那么两三棵,有点像给什么人烧小灶似的。丝瓜秧苗长出土,就生出纤细的藤蔓,藤蔓带刺,一寸一寸顺着棚架或墙角往上直蹿,碧绿的藤蔓爬满棚架或整个院墙,就像一道绿色的瀑布。风掀着绿叶哗哗响,瓜棚架下浓绿荫凉,凉风习习。
丝瓜开花结果时,黄灿灿的花儿长在藤尾上,像是小姑娘盘在头上的蝴蝶结。清香四溢的,惹得蜜蜂成天赖在瓜棚里不是采蜜,就是嗡嗡乱叫。丝瓜花分雄雌,雄花不结果,是谎花,只有雌花结果。绿藤、绿叶、黄花交织在一起,在瓜棚里不仔细看,是看不到丝瓜的——猛然看到弯曲的藤蔓上挂有丝瓜,这时丝瓜已经长在瓜棚的顶上了。瓜越长越长,身子也愈来愈重,直挺挺地悬垂在半空,碧绿碧绿,就像是一个天外来客。这时,想吃丝瓜就可以随手去摘。记得小时家里有客人来时,妈妈就会拿丝瓜与鸡蛋烧一锅丝瓜汤,我们跟着也能美美地吃上一顿。丝瓜能清炒,能炒鸡蛋、炒青椒、炒毛豆……城里有人还将丝瓜去皮凉拌,作凉拌丝瓜,也很好吃。
吾乡方言叫丝瓜为“满瓜”,因丝瓜有藤蔓,我自以为是,纠正为“蔓瓜”。其实不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丝瓜“始自南方来,故名蛮瓜。”我叫丝瓜为“蔓瓜”那一定是误叫了。看丝瓜绿绿的样子,很是可爱,我想说丝瓜是菜蔬里的“小鲜肉”,还想给它取个笔名叫“小青”。但都没有叫出名。冬天到了,丝瓜的绿叶散尽,瓜棚往日的繁华与喧闹都已过去,偌大的瓜棚只剩下稀疏的几根褐色的瓜藤。老了的丝瓜,被人弃之如敝履。有人抖落老丝瓜里面的籽粒,丝瓜便成了软软的丝瓜瓤子。丝瓜瓤子利用起来,用来刷锅或刷茶缸,非常好用,起码比现在人家用的钢丝球好。陆游说:“丝瓜涤砚磨洗,余渍皆尽而不损砚。”看来,丝瓜制刷古己有之,陆游就知道用它可以擦洗砚台。
丝瓜能入画,齐白石到九十多岁还喜欢画丝瓜。三笔二笔的,他就画了两根绿绿的丝瓜,瓜蒂上有一些欲开未开的黄花。画取名叫《子孙绵延》,画面喧欢。“新种葡萄难满架,复将空处补丝瓜。”据说在蔬果中,齐白石除了白菜,最爱吃的就是丝瓜了。据说,他在他所住的四合院里的种满了丝瓜、葫芦——丝瓜谐音“思挂”,表示思念和牵挂。他画丝瓜蚱蜢、丝瓜蜜蜂、丝瓜螃蟹、丝瓜蝈蝈、丝瓜乌鸦、丝瓜昆虫、丝瓜小鸡……想必就是对自然的思念与牵挂?
蚕 豆
除了人家房前屋后栽的桃花、杏花、梨花、栀子花,菜地里许多蔬菜也会开花的。比如葫芦与辣椒的细白色小花,丝瓜、北瓜和黄瓜开的金黄色的花,茄子与蚕豆开的紫花……在乡村里长大,总能目睹到一些植物的生长,也能欣赏一些植物盛开的花朵。我说,蚕豆花开在田埂上,把稻田镶上一道紫色的金边……走在有露水的蚕豆花丛里,偶尔沾在裤腿上的紫色花瓣,仿佛小女孩咯咯的笑声。
蚕豆的生长周期长,生命力很顽强。俗话说“蚕豆不要粪,八月就在土里困”。蚕豆一般在头年的八月或秋天里下种,在稻田或小麦间套种都行。与油菜、小麦一样,蚕豆要在地下过一个年,到第二年春上才开始露头。露了头的蚕豆一遇到春风,很快绿叶疯长,开花结果。蚕豆的花冠呈蝴蝶状,白嫩嫩,内有微黑色和紫色斑。春风几度,满园花香,蚕豆紫色的花瓣和那些菜花次第开放时,菜园里蜜蜂嘤嘤,蝴蝶翩翩,使人感觉就像是一群游园的美女,不知惊醒了谁的春梦。
有人说“蚕豆开花黑着心”,用戏词为证:“春二三月草青青……豌豆花开九连灯,菜花落地像黄金,萝卜花开白如银,蚕豆花开黑良心。”戏词出自《庵堂相会》,一部锡剧电影。写的是金秀英和陈阿兴的爱情。金陈两人青梅竹马,幼小订下婚约,但金秀英的父亲金学文发了横财,想赖掉这桩婚事,陈家不肯……戏剧写两情人分别年久,路遇却不相识,终于看出端倪,相识相爱,一起想点子对付嫌穷爱富的父亲……这戏词就是陈阿兴唱的。我看这戏,故事老套,没有听黄梅戏亲切。但由此却知道陈阿兴说蚕豆黑心,是境由心生。
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说:“新蚕豆之嫩者,以腌芥菜炒之,甚妙。随采随食方佳。”我就剥过新蚕豆,新鲜的蚕豆温婉如玉,放油锅里爆炒,豆子绿绿,油嫩嫩的。但蚕豆出园,妈妈似乎没炒过腌芥菜,她喜欢用蚕豆做鸡蛋汤。淡黄的鸡蛋,清清的汤水漾着绿色的蚕豆,喝进嘴里鲜美无比。蚕豆粉团团地嚼在舌尖上,更是口齿留香。新鲜的蚕豆一时吃不完,妈妈就用竹器盛着放在太阳下曝晒,存放到来年春荒时,用水泡酥,煮成五香豆。或者干脆晒干,干得没一丝水分,然后在烧红的锅里炒。那蚕豆在滚烫的锅里活蹦乱跳,隔着几里路都能闻到蚕豆浓浓的香味。炒好的蚕豆冷却一下,吃在嘴里嘎嘣脆,清香沁人。逢年过节,妈妈就用这招待客人。有一年,妈妈把选好的蚕豆种放进一个布袋里,吊在房梁上。趁妈妈不在家,我和小伙伴们把那蚕豆偷偷炒吃了。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妈妈知道后,不停地责备我:“你这伢,你这伢……”不知说什么好。
江南一带,因蚕豆在立夏时节上市,所以称蚕豆叫“夏豆”。还有一种说法,说蚕豆食在春蚕吐丝的时候,所以称“蚕”。蚕豆又叫胡豆、佛豆……叫法很多,让人糊涂。朋友陈琳因我在文章里说过蚕豆种在田埂上,对我把蚕豆与水稻秧苗弄在一块耿耿于怀。他的指摘,我自觉温暖而汗颜。吾乡有一笑话说,当年有人戏问下放知青粮食从哪里来,知青回答说从麻袋里长的。段子没有人证实。但下放知青都是在城市长大的,下乡本来就是接受再教育,闹出这样的笑话不算什么。我自幼在乡村里长大,若闹出笑话,不该。
辣 椒
在瓜果菜蔬中,辣椒算是一道普通而又并不普通的菜肴。说它普通,因为它在各地的菜园里随处可见。说它并不普通,是说它下至平民百姓,上至达官贵人都喜欢。伟人毛泽东接见苏联的米高扬,让厨师炒了一盘红辣椒,那米高扬嚼上一口,辣得泪水直冒,嘴里不停地呵气。伟人笑着打趣道:在我们这里,不吃辣椒就不算革命。看来,辣椒能够成就革命者,而且能成就不普通的革命者。
辣椒,我们那里叫大椒。在早春的菜园地里,它和茄子、黄瓜、豇豆、豆角几样菜几乎同时栽培。几种菜秧子落地生根,就得浇水、施肥。所以一段时间,菜园的主人总要每天傍晚往菜地里跑,勤快而辛劳。浇了水、施了肥的菜在春天里摇头晃脑,撒欢般地成长,就有点“茁壮”的意味。很快,菜园里或红或绿、或黄或紫,一片姹紫嫣红。大椒在青青菜地由小长大,由绿转红,脱颖而出,就像一串红灯笼照亮了人的眼睛,菜园主人一眼就看到了它……那时候,正是农村的双抢季节,繁重的农活需要人吃饱肚子干。大椒炒肉、大椒炒鸡蛋、大椒炒鱼……便是最好的下饭菜。当然只有家庭殷实的人家才会天天有鱼肉。
吾乡河道生产一种小河鱼,逮起来洗干净、晒干,伴着青大椒丝一炒,鱼白椒绿,赏心悦目。煮好的鲢鱼汤,在上面撒上点剁碎了的红辣椒,好吃又好看。现在有一道菜叫剁椒鱼头,美其名“鸿运当照”,其实就是由此延伸的一种,红红的大椒象征着吉祥。除大椒炒肉,乡村过去有的人家腌了腊肉有异味,舍不得扔,也会用大椒炒着去味。乡村里,新鲜大椒可以磨成辣椒酱,晒干的大椒壳子能磨成辣椒粉……在我的记忆里,大椒一直是做菜时用的调味品、一种普通的佐料。只是当我吃到“虎皮尖椒”“大椒瘪”这两道菜,我才知道大椒是可以独自成菜的。妈妈喜欢用菜刀把大椒去掉籽粒、拍瘪,然后放在饭头上与茄子一块蒸,这蒸熟的大椒伴以油盐,叫作“大椒瘪”。
“四川人吃辣椒,不怕辣;江西人吃辣椒,辣不怕;湖南人吃辣椒,怕不辣。”这几个省份的人都以能吃辣椒为荣,出语惊人,很有刺激和挑战的味道。但各地竞相与辣椒为伍,实际上对大椒的劲道要求却不一致。辣椒因为品种、地点和生长气候的不同,也生就了不一样的辣劲。南方的大椒因种植的生长期适逢酷夏,天气炎热,日照光线足,大椒就辣,从朝天椒、尖椒这些辣劲十足的名字上就能知晓。北方种的是菜椒或说甜柿椒,大多为大棚种植,日照少,肉质肥厚,品性温和,辣劲当与南方不可同日而语。况且,北方人很少像南人那样吃大椒。初到北方,我看一位朋友喝酒,喝着喝着,要了一碗大椒壳蘸着酱油当饭吃,吓得瞠目结舌。还有一回,陪一位朋友吃饭,他喝一口酒,就咬一口大椒。我看他辣得满头大汗,我就急得满头大汗。只是不用打听,他们都是一只只来自南方的狼。
我见陕北窑洞那土墙上经常挂的红大椒也是一景。那些用麻绳串起来的红大椒,一串串的挂在墙上,经过太阳的照射,很快晾干。晾干了的大椒不仅保持了原味,而且红艳艳的,保持了原色。到吃的时候,取下来放在清水里洗一洗就可以了。那一串串红红的辣椒,人们远远地望去,就像是一串熊熊燃烧着的火焰,不仅显示出农家红红火火的日子,让人还莫名其妙地想到革命两字。
自然,当辣椒以革命者的面目出现时,人们的语言有可能就与它息息相关。那语言不仅褒贬不一,而且开始泾渭分明。比如说某某人泼辣,那一定是表扬某某人具有雷厉风行、行事果断的风格。这大多数时用作表扬女人。而说某某人心狠手辣,若你站在一位革命者的立场上,就会对他(她)愤恨、鄙视和横加鞭挞。
责任编辑 鲁书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