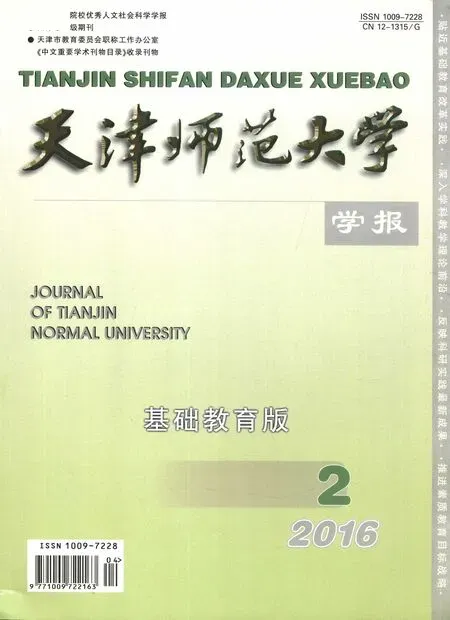合作学习的理性分析与改进策略
2016-05-06董裕华
董裕华
合作学习的理性分析与改进策略
董裕华
合作学习是一种古老而又新鲜的教育观念和实践。我国开展大规模的合作学习已历时十多年,究竟实际成效如何,发展趋向如何,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就目前情况看,合作学习特别要关注其适用范围、条件和情境,关注合作的内容、方法和流程。教师不仅要重视相关的理论学习,还要注意选择恰当的方法,设计切合的问题,把控合作学习的时机,合作学习才能更具实效。
合作学习;历史沿革;理性分析;改进策略
一、合作学习的历史沿革
早在公元1世纪,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Quintilian)就曾指出:学生可以从互教中受益。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则主张“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互相受益”,不仅肯定了学生之间合作的必要性,也肯定了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合作的重要性。由于教育家帕克(Park,F.)和杜威(Dewey,J.)的积极倡导,美国在19世纪初也开始尝试合作学习,并一度占据了美国教育界的主流地位。但在强调人际竞争的观念主导下,合作教学法又逐步被边缘化。20世纪70年代,在斯莱文(Slavin,R.E.)、卡甘(Kagan,S.)、约翰逊兄弟(Johnson,D.W.& Johnson, R.T.)等学者的推动下,合作学习的观念又再次复兴,并且迅速形成和发展成为一系列原理与策略体系,占据美国教育界的潮头。[1]1997年,美国著名教育评论家埃利斯(Ellis,A.K.)指出:“如果让我举出一项真正符合‘改革’这一术语的教育改革的话,那就是合作学习。”“合作学习如果不是当代最伟大的教育改革的话,那么它至少也是其中最大的之一。”[2]
我国合作学习的思想也有悠久的历史。孔子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1932年陶行知发表的《小先生》:“有个学校真奇怪,小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描述的就是我国私学教育“高业弟子转相传授”的情况。检索发现,1987年第2期《外国教育资料》上发表的前苏联教育家雷先科瓦等人所著的《合作的教育学》(朱佩荣译),可以说是我国最早介绍国外合作学习理论的文章。部分省市的研究者、教育者进行了实践和理论探索,并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研究群体。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鼓励合作学习,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促进师生教学相长。”随后,教育部出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纲要》又进一步明确指出:“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是新课程大力倡导的三种主要学习方式。”这标志着我国的合作学习迈上了大规模、系统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展开了“本土化”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反思。
二、合作学习的理性分析
(一)合作学习的目的
在美国,合作学习的兴起虽然源于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但其主要目的还是反对种族隔离,让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学生拥有的学习机会均等。正是由于合作学习的外在性,也就普遍缺乏内在的合作动机。从学习过程看,竞争是绝对的,而合作只是相对的。合作学习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组间的竞争,即使组内成员能真心合作,但小组之间的竞争依然非常激烈,合作的基础依旧非常脆弱。合作学习虽然改善了课堂氛围,促进了学生良好非认知品质的形成,但来自混合学校的报告却表明:合作学习策略对不同种族儿童之间关系的改善收效甚微,不同种族的孩子仍然在自己所属的种族内发展同伴关系和友谊关系。[1]因此,仅仅依靠合作学习来达到比较高的教育理想、缩小种族间的差别确实难以实现。合作学习对提高学习成绩的帮助还没有太多令人信服的证据,参加PISA2012测试的上海学生感觉数学题目超简单、做题很享受,而欧美学生却感到苦不堪言。以合作学习见长的美国学生的平均得分为481分,低于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而上海学生平均得分为613分,高出第二名40分,高出OECD的平均分119分。但合作学习对增强合作意识、竞争意识,培养合作精神、创新精神,发展交往能力、主动学习的能力,对人终生的发展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美国奥数国家队主教练冯祖鸣东西方教育都经历过:他14岁考取北京大学少年班,18岁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学硕博连读,博士毕业后他却选择到埃克塞特的中学教书。他曾感慨地说:“一直以来,亚洲人或者华人似乎有一个误区,认为我们的数学很好,其实那只是到中学为止。进入大学以后,我们的能力可以说很差。因为太习惯被动去等老师给问题,给公式,不能自己创造。”[3]
(二)合作学习的分组
学生的分组是合作学习的首要问题。卡干的合作学习理论把合作小组分为四种类型:异质性小组、同质性小组、基于学生选择的小组和随机小组。[4]一般认为合作学习要“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编排时由教师依据学生的知识基础、兴趣爱好、性格特征、学习能力和性别等差异进行分组,尽可能让不同特质、不同层次的学生优化组合,均衡搭配,使每个小组都有各个层次的学生。组内异质促进了小组成员间的互相帮助、共同提高,而组间同质又为各小组创设了公平竞争的宽松环境。这种观点表面看来合情合理,但异质小组不是学生自愿组合,成员彼此间缺乏共同语言,合作交流的程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基础好、能力强的学生往往能控制小组的局面,容易独断专行,以自己的见解代替全组的想法,抢夺了别人思考、发言的机会;内向的组员不敢也不愿表达思想,懒得动脑、动手、动口,甘心情愿地担当沉默的听众。特别是规模大的班级,更难保证每个学生平等参与小组活动,合作学习常常名存实亡。如果长时间得不到调整,这种小组就会成为“懒人”的避风港。研究发现:把女生从其他女生中独立出来,或者把有色人种的学生从其他有色人种中孤立出来,不利于个体获得学业成功。[1]因为这些人在小组内显得微不足道,容易孤独自闭,只能扮演模式化的角色,缺乏主动积极的精神。研究合作学习的代表人物穆里安研究全班及小组合作教学过程中的学生行为时发现,学生在合作性的学习小组情境中比在全班情境中显示出的参与行为要多很多。但是,在合作的小组中,学优生比学困生显示出更高质量的参与行为,学困生在合作小组的大部分情景中被淘汰出局,尤其是集体中的弱势群体往往被忽略。[5]
(三)合作学习的条件
美国与中国的国情不同,小班化的教室里,小组间在合作学习时的干扰少,教师可以参与到每个小组,及时掌控学习的情况。而我国绝大多数中小学的班级规模都比较大,有人认为合作学习可以解决大班额的班级老师不能顾及到每个学生的问题,每个学生学习中出现的疑惑不一样,有些可以通过互帮互学得到解决。的确,合作学习突出了“兵教兵”,让学生参与到“教别人”和“向别人请教”的活动中,但教什么、怎么教、以什么方法教,特别是同组学生的差距过大时怎么“教”,却是很多人没有关注的问题。对合作学习的评价,理应突出学习过程中组员的参与度、合作度以及思维的发散度,给不同层次的学生设置不同的评价标准,通过评价增强小组的凝聚力,提高倾听、分享、归纳、整合的能力,但遗憾的是,这方面也很难拿出行之有效、简单可行的操作办法。在合作学习中,教师很难照顾到每一个小组、每一个人,很难了解到每个学生在合作学习中获得了多少进步的问题,也就容易出现合作学习的“死角”。在汇报学习成果时,也不是每个小组的代表都能有机会发表意见,教师收到的信息也可能会比较片面和局限,容易出现教学的盲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优势学科,国内分组的方法通常只能看总分,“组内异质、组间同质”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并没有顾及到每一门学科。而国外大多是学生走班制,教师有固定的教室,学生每门课参与的合作学习小组是不同的,每门课的学生个体间的差异也是较小的,这些都是合作学习的有利条件。再看看我国开展的合作学习、同伴互助活动,确实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
(四)合作学习的流程
有些学科需要学生独立思考,许多有价值的学习成果都是学生静静“悟”出来的。学生带着深思和感悟形成的独立见解参与研讨,合作学习才会有效果。如果把控不好合作的时机,学生的思维还没有完全展开,就已经被别人的观点同化,人云亦云、随大流。这种在他人提醒帮助下获得的知识,远不及经过自己思考得来的深刻和持久,热热闹闹的背后可能意味着学生认知水平的原地踏步。有些教师为了赶时髦,不管是不是真问题,都喜欢拿出来“秀一秀”,似乎只有合作讨论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一些没有思维含量的问题充斥其中,学生感觉不到合作学习的必要,懒得合作;一些复杂的问题在大多数人还没理清头绪的时候就匆匆讨论,致使大多数小组的讨论处于盲目混沌状态,大大降低了合作学习的效率。有些教师为了突出合作学习和学生主体地位,一上课就安排合作学习的任务,自己则退至教室的角落耐心等待,或如蜻蜓点水般游走在各学习小组间。教师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感觉,到时间就依次听取各组的汇报。而学生汇报时常常是完成得快的组抢了头筹,后面的班级没有新意也就不了了之,难免有的组会滥竽充数。汇报完毕,整个教学活动便算完成。有的课堂看似讨论热烈,却是活而无序。这种合作学习,学生并没有真正掌握合作学习的方法,不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做;教师也没有掌握合作学习的技巧,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该合作、怎么合作,更不清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需要帮助、引导和点拨学生。师生都是为合作而合作,违背了合作学习的初衷,浪费了大量的教学时间,合作学习的优势自然不够明显。
(五)合作学习的内容
如果学习任务体现了较多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或者人际交往品质与能力的培养目标,包含了较为复杂或较高层次的认知过程,或者需要分工合作才能完成的探究实验、研究性学习等,合作学习的方式较为适宜。但合作学习并不是所有的学科、所有的学习内容、所有的学习阶段所共有的最佳的学习方法。每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要求,用合作学习的方法组织人文科学学习时,大多侧重于小组成员相互交流信息,碰撞智慧火花,共享思维成果;而自然科学,则侧重于小组成员分工协作,共同完成作业,共享合作乐趣。国家层面上已经注意到学科间的差异。比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无论是2001年版,还是2011年版,课程基本理念都强调“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2003年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课程基本理念是“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而把“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作为教学建议。2001年版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课程基本理念强调“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而2011年版的课程基本理念则强调“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等,都是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接受学习对数学学习的作用在新版本中得到了肯定。新版本的课程基本理念还要求“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处理好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并不排斥教师讲授知识。2003年版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课程基本理念是“倡导积极主动、勇于探索的学习方式”。学生的数学学习活动不应只限于接受、记忆、模仿和练习,高中数学课程还应倡导自主探索、动手实践、合作交流、阅读自学等学习数学的方式。由此看来,强调合作学习在学科学习中的作用是正确的,但合作学习不是万能神器,不能过多地依赖某一种学习方式,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遗憾的是,有些地方在推进合作学习的过程中“一刀切”,所有学科、所有年级“齐步走”,为了统一的模式而舍弃了教学应有的规律。
三、合作学习的改进策略
(一)选择分组合作的恰当方法
合作学习必须具备5个基本特征: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各尽其力、交流互动、团体历程。没有经过训练的合作小组是散乱的,这样的合作学习就是假合作,合作学习的价值就不可能凸显。合作学习方法的掌握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教师长期不懈的训练和引导。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学科,讨论一个热门话题、做一个分组实验、解决一个数学难题,学生合作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方法、担任的角色都是不一样的。合作交流的形式,能在2人同桌完成的,就不在4人小组内解决;4人能解决的,就不在大组中解决;不是疑点、难点、重点的问题,尽量不在全班展示。为了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小组成员可以定期交换分工。并不是每个学习内容都需要通过合作学习来完成,也不是所有的合作学习内容都能在一节课内圆满解决,有时还要向课外延伸。比如,高中数学中有些综合性较强的内容,仅仅依靠课上时间完成整个合作学习的流程基本不可能,必须在课前先做准备。因此,合作学习既要有基本的方法和程式,又不能僵化教条,囿于模式,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常用的分组模型还有:(1)问答模型。学生之间互相提问、互为解答、互作老师。(2)调查模型。可以按兴趣爱好分组,可以按感情友谊分组,也可以按特长搭配分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研究性学习。(3)拼盘模型。将学习任务分割成几个部分,各小组合作学习后在课堂上汇报,达到全班学习的目的。(4)编号模型。各小组合作学习以后,教师要求某一编号的学生回答问题,组内其他成员先补充,其他组再帮助。卡干研究发现每种类型的小组都有自己的优势与缺陷[4],教师要掌握每个类型小组的特点,选择最适合当时教学情形的小组类型,不能千篇一律,生搬硬套。
(二)设计合作学习的切合问题
合作学习的问题应当对学生具有挑战性,个体是不能独立完成的,必须依靠团队协作才能解决。一个高质量的问题应当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一个能使学生通过合作在原有基础上取得突破的问题。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懂得他人和社会群体在个人生存和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从而以更积极的态度投入合作。问题过于简单,难以激起学生的求知欲,学生会觉得无聊而消极应付;问题过于复杂,离学生思维“最近发展区”太远,学生会觉得无所适从、束手无策而逃避。因此,问题的切入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的实例:
同样是求面积,我们的常用处理方法就是记公式、套公式,讲究熟练掌握。而PISA测试的思路就不一样。PISA测试给出了下列样题[6]:
这是一幅南极洲地图,请你利用图中的比例尺估计它的面积,并解释你是如何得到的。
【评分标准】
(1)对结果与方法均正确的解答的评分

凡属下列情况,均可获得满分2分。
情况1:用正方形或长方形来估计,答案在12 000 000与18 000 000(km2)之间(对单位不做要求,下同);
情况2:用圆来估计,答案在12 000 000与18 000 000(km2)之间;
情况3:分成几个规则的几何图形,将各个部分的面积加起来,答案在12 000 000与18 000 000 (km2)之间;
情况4:用其他方法,答案在12 000 000与18 000 000 (km2)之间。
(2)对结果与方法部分正确的解答的评分
凡属下列情况,可得1分。
情况1:用正方形或长方形来估计,但结果不正确或不完整(计算错误,没有进行比例转换;没有最后结果等);
情况2:用圆来估计,但结果不正确或不完整;
情况3:分成几个规则的几何图形,将各个部分的面积加起来,但结果不正确或不完整;如果计算的是周长而不是面积,则不能得分。
【评注】:本题虽然是一道测试题,但作为合作学习的载体也是非常不错的内容。在以考试为中心的课堂,这一内容可能会一带而过。这里所提供的几个思路,涉及的范围覆盖了学生已有知识、能力的方方面面,既考查了学生建模、运算、估算、面积公式多方面能力,也考查学生的思维过程,评分方法和尺度也比较人性化,这种“宽容”给学生更多的思维空间和自由,为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放开手脚解决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真正体现了既让学生学会,更让学生会学的教育理念。由此看来,易混概念的辨析、规律性知识的探究、开放性问题的解答,都是合作学习的最佳切入点。
(三)把控合作学习的关键时机
各学科的课程标准都把“合作”放在“自主”之后,这一细节说明: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是合作学习的前提和基础,即使在大力倡导“合作学习”的今天,培养与锻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依然不可忽视。合作不是目的,要让学生通过合作学习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仅仅依靠教师预先的设计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教师把控好合作学习的“度”。什么问题需要合作学习,合作学习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需要教师点拨,什么人代表小组发言,很多时候是动态生成的,靠的是教师的课堂驾驭力。整个课堂就像牵在老师手上的风筝一样,既能放出去,又能收得回。教师不仅是合作学习的组织者,更应是合作学习的参与者,合作学习不单是学生相互之间的事情,师生平等合作的心态也是合作学习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的问题,需要教师及时发现、指出并帮助解决。教师的课堂驾驭和调控能力很重要,遇到个别问题可以个别处理,遇到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可以在小组汇报环节共同探讨。对于表现出色的小组和个人可给予适度的表扬,对处于弱势的同学取得进步时,要给予充分的鼓励。这些鼓励、表扬可以是公开的、全班性的,也可以是私下的个别交流,可以是一句赞美的言语,也可以是一个眼神,甚至一个微笑,都可能激发学生合作学习的热情。
合作学习的成功实施离不开小组建设的优化、自由时空的创建、积极互赖关系的形成、挑战性学习任务和实质性评价的践行。[7]要想让合作学习更有效,教师不仅要加强相关理论的学习,注重理念的更新,还要重视方法的优化,要因时、因事、因地制宜。只有从整体上把握合作学习的发展,才有可能处理好合作学习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1]王凯.论合作学习的局限性[J].香港教师中心学报,2004 (2).
[2]施阳.略谈课堂小组学习活动的有效性策略[J].浙江教学研究,2013(6).
[3]周一妍.专访美国奥数队主教练冯祖鸣:中国学生数学优势止于中学[J].中华少年,2014(1).
[4]牟尚婕,盛群力.合作小组的组建策略[J].课程教学研究, 2015(4).
[5]杨朝军.英语教学中应用合作学习的缺陷及对策[J].教学与管理(理论版),2010,27(9).
[6]张景斌,彭刚.PISA对我国数学教育评价改革的启示[J].数学通报,2004(8).
[7]葛绍飞.翻转课堂视域下的合作学习[J].浙江教育科学, 2015(2).
[责任编辑:况 琳]
Rational Analysis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DONG Yuhua
Cooperative learning is an ancient but fresh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practice.The large-scale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China has last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It’s urgent to summarize and rethink of the actual result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special attention is required to be paid to the scope, conditions and situations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as well as the content, methods and learning processes.Teachers should constantly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hoice of appropriate methods, the design of relevant question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opportunities.Only in this way can cooperative learning be more effectively applied.
cooperative learning; historical evolution; rational analysi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G632
A
1009-7228(2016)02-0037-05
10.16826/ j.cnki.1009-7228.2016.02.009
2016-01-25
董裕华,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江苏226600)副校长,中学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