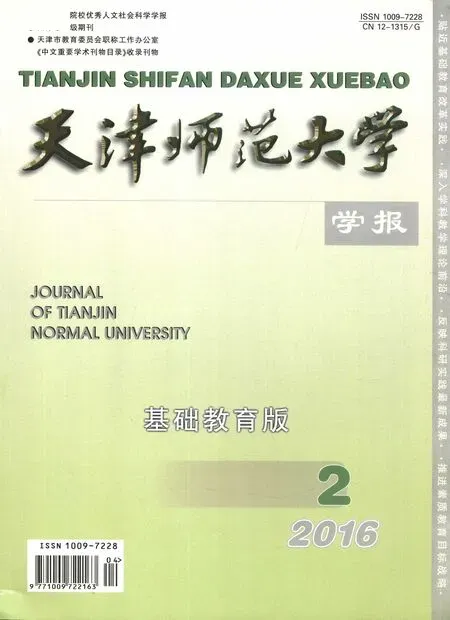国外核心素养研究及启示
2016-02-13刘义民
刘义民
国外核心素养研究及启示
刘义民
核心素养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形成比较系统完善的内容结构、课程体系、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核心素养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推动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支柱性理念。核心素养研究是一种国际共识。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以终身学习为目标的素养研究,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个体的成功生活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的核心素养内容结构框架研究,有欧盟组织的核心素养研究和美日为代表的以能力为目标的核心素养研究。核心素养研究包括核心素养概念、内容指标、课程体系、质量保障指标体系四个方面。核心素养研究对我国有重要启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契合个体和社会发展需要,课程变革要强化对教育信息的快速反应,要建构一体化的课程研究机制。
核心素养;多维演进;特点;启示
核心素养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形成比较系统完善的内容结构、课程体系、质量保障体系,并已成为推动西方发达国家课程教学改革的支柱性理念。我国2001年开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素质教育,时至今日基础教育面临深化改革难题。2014年3月30日,《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正式印发,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研究制订中小学各学科学业质量标准”的新任务,为以核心素养为目标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明了方向。因此,梳理国外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对推进我国核心素养教育研究,建构课程,制定教育质量指标体系,深化课程改革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一、核心素养研究的多维演进
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国际教育改革的交汇期。国际组织、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对教育改革取向虽然理解不同,但却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核心素养研究。代表性的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以终身学习为目标的核心素养研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以个体的成功生活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的核心素养研究、欧盟组织的核心素养研究和美日为代表的以能力为目标的核心素养研究。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学会生存”报告,认为人的发展目标是“人的完整实现”,是人之个性丰富内涵的“全面实现”,反对仅仅侧重于技能培养的教育观念,提出全面教育的主张。199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学习:财富蕴藏其中》一书,指出21世纪公民必备的四大核心素养: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提出“学会改变”的教育主张,并将其作为终身学习和发展的第五大核心素养。[1]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经合组织”合作出版研究成果《发展教育的核心素养》报告,明确核心素养是使个人过上理想的生活和实现社会良好运行所需要的基本素养。2013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美国著名智库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发布“学习指标专项任务”研究报告——《向普及学习迈进》,从身体健康、社会情绪、文化艺术、文字沟通、学习方法与认知、数字与数学、科学与技术7个维度,为基础教育阶段0~19岁的学生构建了学习目标体系,突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思维能力和工作方式培养,强调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重视信息技术能力培养,凸显教育的社会内涵,并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发展特征明确了不同的学习重点:哪些方面的学习最为重要,如何检测。[2]
1987年,“经合组织”启动了“国家教育系统发展指标”项目(INES),组织了5个国际工作小组,分别研究项目的某个特定领域,为其成员国搭建交流与共识平台,改进教育信息搜集和报告方式。1997年12月,“经合组织”启动“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论和概念基础”项目(DeSeCo),尝试在国际跨学科背景下,与科学界合作开展“素养”内涵的界定、概念化和测量研究,建构核心素养总体概念参照框架,统一核心素养概念和研究指标,解决其成员国之间的教育研究分歧问题,指导各成员国开展教育输出信息的搜集和报告活动,促进相互借鉴和发展。
欧盟深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主张的影响,2000年3月发布“发展适应知识经济需求的‘新基本能力’”研究报告,强调终身学习应该具备IT、外语、技术文化、创业精神和社会互动5项基本能力。[3]2002年,欧盟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核心能力(Key Competencies)概念,并对5项基本能力进行分析,提出了8项核心素养教育主张。2003年又对8项核心素养进行文字表述修饰。2005年11月,欧盟委员会向欧洲会议和欧盟理事会提交8项核心素养提案,并于2006年12月18日通过。之后,核心素养方案成为欧盟成员国引领本国终身学习和教育与培训改革的参照体系。
“二战”后,美国也持续进行教育改革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其核心素养研究主要是通过核心课程研究来体现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发布《帕地亚建议》报告,转变过去过分注重选修课程的做法,为所有学生提供相同的课程。1983年4月,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布《国家处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研究报告,认为高中毕业生必须具备英语、数学、科学、社会、计算机5门学科基础。[4]1985年,美国民间科学团体科学促进协会,自发组织美国上百名科学、数学和技术界知名专家与部分教育实践者,研究设计美国基础教育中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于1989年形成《2061计划:为了全体美国人的科学》,呼吁美国基础教育要加强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是“教育的中心目标”,任何事情也没有比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改革更为紧迫了。1991年,布什总统签发《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文件,制定了4项教育改革战略和6项全国教育目标,要求政府为学生创办更好、更有成效的学校,使学生在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地理五门学科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1993年,克林顿政府签署全国性教育改革法案《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确认1991年的6项全国教育目标,另外增加外语和艺术两门学科,使核心素养课程增加至7门。步入21世纪,美国企事业和教育界提出了“21世纪型能力”(21st Century Skills)的研究性课题,核心能力主要包括学科与21世纪课题研究能力、学习及革新能力;信息、媒体及技术能力;生存及职业能力。[5]
日本以“教育立国”著称,其核心素养研究是以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改革体现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议提出学校贯彻基础和基本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和创造性发展,尊重文化传统,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6]90年代,日本将上述教育主张进一步具体化。1996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布《关于面向21世纪的我国教育》报告,提出培养学生“生存能力”的教育改革目标,并就改革方针、课程建设、教育内容等重大问题进行研讨。1998年,日本教育课程审议会在答申报告中具体阐述了以“生存能力”为目标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宗旨:培养丰富的人性和社会性;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日本人;养成学习和思考的自觉能力;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充分发展个性;推进特色教育和特色学校建设。[7]2002年,日本中小学开始实施新的学习指导纲领,标志着以能力为核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展开。进入21世纪,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构建了本国“21世纪型能力”框架,从以“生存能力”为核心向“思考力”为核心转变,强化语言力、数理力、信息力和实践力,形成日本独具特色的核心素养理论。[6]
二、核心素养研究内容
(一)核心素养内涵与功能
“经合组织”的“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论和概念基础”项目认为,“素养”是一个动态的、整合的概念。它是基于行动和情境导向应对复杂要求成功开展工作的能力,比知识、技能的意义更加宽泛。核心素养是覆盖多个生活领域促进成功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的重要素养。[8]其目标是实现个人生活成功和促进社会良好运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是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基于人的教育的顶层设计。它改变了传统教育以学科知识结构培养人的课程体系,是目前国际性和地域性组织、各个国家分析研究教育改革的核心概念。
(二)核心素养内容结构
“经合组织”的“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论和概念基础”项目认为,核心素养内容结构包括3个一级指标和9个二级指标。[8]一级指标包括互动地使用工具、自主行动和在社会异质团体中互动三类。二级指标是对一级指标的细化。互动地使用工具是个体实现与世界相互作用而行使的社会文化工具,包括使用的语言、符号和文本,知识和信息,新技术等。自主行动是根据自身需要把愿景转化为目的行动,包括复杂环境中的行动,形成并执行规划的行动,维护自身权益和自我监控活动等。在社会异质团体中互动强调个体与他人,尤其是与异质于自身的他人的互动,包括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团队合作、管理与解决冲突。各项素养都有具体内容详细说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认为核心素养内容结构由5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包括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和学会改变5个方面。二级指标由5个一级指标细化而成。学会求知包括学会学习、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品质;学会做事包括职业技能、社会行为、团队合作、创新进取和冒险精神;学会共处包括认知自身和他人的能力、有同理心和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学会生存包括丰富人格、促进自我、多样表达、责任承诺;学会改变包括接受、适应、主动、引领等改变。[9]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发布了《全球学习领域框架( the Global Learning Domains Framework )》报告,把核心素养划分为身体健康、社会和情感、文化和艺术、语言和交流、学习方法和认知、算和数学、科学和技术7个一级指标,以及与其相对应的从学前、小学和小学后3阶段划分的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又进行下一层次指标划分,各指标都有比较详细的内容说明。[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素养内容结构包括以终身学习为导向的素养内容结构框架和以学习领域划分的素养内容结构框架两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学习素养的研究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核心素养的研究对欧盟有重大影响。欧盟2000年启动核心素养研究,2006 年12月通过核心素养建议案。该核心素养由3个一级指标和8个二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包括人与社会、人与自己和人与工具三个方面,二级素养指标由一级指标细化而成,包括使用母语交流、使用外语交流、数学与基本的科学技术素养、数字素养、学会学习、社会与公民素养、主动意识与创业精神、文化觉识与表达。每项二级素养指标又分别从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个维度描述阐释。[10]这为欧盟各成员国制定教育政策,进行课程改革提供了方向指导和框架参照。
其后,其他国际组织,如国际文凭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格兰、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参照“经合组织”的“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论和概念基础”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者欧盟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在分析本国、本地区个体成功和促进社会良好运作的基本国情、区情的基础上,形成了适应本土的核心素养内容结构框架。框架以培养什么样的人为核心教育目标,以具体层级指标划分为枝脉,构建可操作的科学化的课程体系,为世界各国课程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行动路径。
(三)核心素养课程体系
核心素养教育目标的实现凭借是课程。参照“经合组织”的“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论和概念基础”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者欧盟核心素养内容结构框架研究成果,世界上多个国家形成了适应本国国情的核心素养内容结构框架,并构建了相应的课程体系。
依照核心素养与课程体系相对独立的程度,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核心素养体系在教育教学实践领域的应用模式大致分为三类[11]:第一类,分项研究,逐渐融合模式。核心素养研究独立于课程体系之外,由专门机构研制开发,然后,逐渐实现核心素养与课程和教学相融合,最终达成核心素养教育目标的课程体系化,主要代表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第二类,以核心素养框架统辖课程体系建构。根据国际核心素养内容结构框架指标,厘定本国课程体系中蕴含的核心能力和素养内容指标,以此指导课程内容选择、组织与实施,形成课程体系,主要代表国家是芬兰。第三类,间接体现核心素养模式。学生的核心能力和素养没有单独的体系规定,但是,国家课程体系的建构无意识地部分体现了培养核心能力和素养的宗旨,主要代表国家是日本和韩国。
(四)核心素养质量保障框架
核心素养课程体系的形成为课程实施奠定了基础,但是课程实施需要质量监控,以保障课程目标的有效落实。
2000年,联合国全民教育大会评估了1990年以来世界全民教育进展情况,指出应该将教育质量作为全民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强调教育质量。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Draft: Life Skills: The Bridge to Human Capabilities》一书,提出教育质量框架和支持教育质量的10个方面的标准。其中学习结果是质量标准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学习者达成基本认知成绩水平所需要的知识;理解、尊重、团结、平等、包容、尊严等所秉持的价值;解决问题、团队精神、与他人相处、学会学习等所需要的技能以及学以致用的能力。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2005:教育质量势在必行》一书,对教育质量作了系统论述,并制定了教育质量整体框架。[12]框架以学习为核心,分设学习者和教育体系两个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是由两个一级指标细化而成的。学习者包括寻找学习者、学习者知识与经验、学习内容、过程和环境5个二级指标;教育体系包括行政和管理体系、良好政策的实施、支持性法律框架、资源和学习结果测量5个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又进行具体划分,指标框架全面立体地体现了基于人权的学习、终身学习、可持续发展学习的人本教育理念。质量框架作为一个整体,面向各级各类教育的所有人。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面向基础教育的质量分析框架项目研究,该项目以核心素养概念为标准作为对教育质量分析、监测和诊断的依据。[10]
2000年后,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侧重于核心课程实施的质量保障研究。主要成果有小布什政府出台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和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改革蓝图》两个法案,根据这两个法案的主要精神分别制定了《2002-2007年战略计划》和《2007-2012年战略规划》,作为核心素养教育目标有效落实的法律保障。[13]
欧盟也积极探索建构教育质量保障框架。2001年5月,欧盟委员会教育和文化总司发表“欧洲学校教育质量报告”,提出学校教育质量评估的4领域16指标。2002年,欧盟委员会组织31个欧盟成员国专家、国际组织代表评估欧盟成员国核心素养目标达成进展状况,分析成功实践范例,最终厘定了包括教师、高校数学理工科毕业生、知识社会技能、教育投人、开放学习环境、学习吸引力、外语学习、教育流动等8个关键领域29个评价指标。2007年2月,欧盟委员会起草“监测里斯本教育和培训目标进展的指标和基准的统一框架”文件,对29个评价指标进行调整,最后敲定并批准16个监测教育进展的核心评价指标,具体包括学前教育参与率;特殊教育;早期离校生;阅读、数学和科学素质;语言能力;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公民素养;学会学习能力;高中教育完成率;教师教员专业发展;高等教育毕业生;高等教育跨国流动;成人终身学习;成人能力;人口教育成就;教育培训投入[14],指标涵盖终身学习的整个系统,体现了教育质量的全程全面监测特征。
三、核心素养研究的特点及启示
我国关于以核心素养为目标的课程改革研究还刚刚起步,核心素养的目标厘定、内容细化、课程建设和质量保障指标都需要深入研究。国外关于核心素养的研究成果为我国以核心素养为目标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核心素养研究要契合个体和社会发展需要
核心素养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是在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核心素养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个体成功生活和社会和谐发展,具体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则又有不同,如何根据本国、本地区特点确定核心素养内容结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终身学习目标出发,确定学生个体需要的五大核心素养,以供各国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过十多年的研究,界定了核心素养概念,拟定了遴选原则和操作方式,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框架参照;欧盟以核心素养内容结构框架建议其成员国根据国情具体实施,都充分体现了个体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研究和采纳特征。
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发展基本走向正轨,但是在教育与个体和社会发展契合性方面依然存在严重不足。改革开放阶段,教育需要培养的不仅仅是有知识的人,更是有能力的人,但是教育实际上却走向“重知识”的应试教育,严重影响了学生个体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世纪之交的素质教育,志在扭转“应试教育”造成的弊端,附和国际教育改革的浪潮,尽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从当前世界性的核心素养教育改革来看,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依然存在严重不足,素养教育改革缺乏勇立潮头的国际视野,没有真正伴随中国大国地位的崛起,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机遇和挑战,培养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具有领导力、创新力、实践力和正确价值观与人生观的符合时代需要的精英人才的先进意识。
而更为遗憾的是,我国的教育改革历来都是“哲学取向”的改革。这种改革能够对教育实践提供一般性指导原则,反映教育教学规律和社会需要,但是在概念、原理上却含糊不清,缺乏可操作性,难以具体指导教学实践,也不利于教师专业培训和发展。[15]2014年3月30日《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核心素养培养目标,对于指导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化有重要意义,但是素养目标是否适合个体成功生活和社会发展还需要具体论证,如何把核心素养内容结构细化为终身教育体系,细化到学科课程和教学体系,依然需要深入研究。特别是当前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已经由简单模仿借鉴发展到探索、创新、引领阶段,核心素养研究与实践要具有世界前沿性、引导力,更需要具有前瞻性和领导力的研究者,以解决我国目前教育发展的个体、国家和社会的困局。
(二)课程变革需强化对教育信息的快速反应
教育变革是一项旅程而不是一张蓝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同时,教育对个体和社会的效能是后续的,有的甚至十几年后才能清楚,因此,教育必定不断处于变革之中,而且每次变革也要力争能够最大限度地除旧布新,发挥变革的正效应。在以核心素养研究推进的教育改革中,美国、日本两国对教育信息的反应是比较迅速的。国际教育变革信息反应的是全球性教育变革主流取向,国内教育信息反应的是地域性问题,地域性教育变革要以国际教育变革为导向。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对国外教育变革信息的反应过于迟缓。从对国外文献资料的研究看,译介到国内的资料比较陈旧,有些甚至还是国外20世纪70年代的;所谓最新年代标签的教育研究成果实质上也是“新瓶装旧酒”,内容大多是20世纪末的旧作。从教育机构对国际性教育改革信息采纳的行动看,意识不足,动力不够。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教育改革还处于追赶阶段,教育变革几乎都以发达国家教育变革主流为导向,准确适度把握教育改革主流趋势,及时吸收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经验促进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乃是学者之职、政者之任、教者之勇,要团结一心,快速应对、敏锐觉识。这取决于以下方面:一是研究机构,二是教育行政机构,三是研究者。研究机构主要是信息搜集研究,教育行政机构主要是信息传递、政策制定和监督实施,研究者是基于自觉自发和兴趣之上的摸索者、探索者、“盗火者”。没有信息的搜集、研究,就不能准确把握教育发展的动向,没有协同一致的快速反应就没有有效的执行力度。同时,研究机构之间、教育行政机构之间以及研究者之间还要及时沟通交流,以保障新的教育信息能够上通下达,彼此周知,更好地服务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更需要铭记的是,中国教育并不仅仅需要一直追随他国的教育改革。中国教育研究和改革需要放弃“卑者心态”,剔除“媚骨”,睁开双眼去观察,迈开双脚去体验,敞开心胸去容纳,立足于“自我”去思考,去建构具有引导力、创新力、自适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三)建构一体化课程研究机制
所谓“一体化”课程研究机制,从纵向看,指课程制作的一体化,即集课程目标内容结构、课程标准、课程(教材)建设、教学质量评价等于一体的教育变革活动。这是课程变革的必备环节,需要深入研究。研究应该全面有序,并保障目标与内容、教材和质量评价标准的一致性。这种一体化的课程研制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加快课程改革的进程,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课程改革的效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各自根据当前学生个体成功生活和社会程度发展需要确定了核心素养目标,然后细化核心素养内容形成结构框架,再建构相应课程体系,最后以可操作的质量指标监控实施,从而形成了由核心素养到内容结构,由课程目标到课程体系,再到评价监控体系的一体化,保障了课程的有效建构和课程目标的有效落实。
我国课程变革历来存在着研究不足,匆匆上马,生搬硬套,简单模仿等问题。尤其是当前关于核心素养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核心素养到底包括几个方面?如何细化?如何课程体系化、学科化?如何监测评价?这是核心素养教育的根本,如果这些问题还都没有研究清楚,就要匆匆开编课程,就要实施教学,那简直就是“过家家”!
鉴于此,核心素养课程体系应该建构一体化研制机制。首先,以“大数据”、“云计算”为工具厘清当前和未来几十年我国教育现状和核心素养的本质内涵与维度,这是关键,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潜心研究,尽管国外有相当成熟的研究成果,但是本国的核心教育素养内涵与维度需要“亲躬”研究而不是简单地“拿来”和浅显地随意“言说”。其次,解决核心素养目标内容结构与课程体系以及学科化之间的有效承接问题,使核心素养目标与课程体系、学科内容结构相一致,避免脱节,避免泛化。第三,建构基于“目标——评价”相一致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避免课程和教学的随意性和课程评价的过分多样化,保障核心素养目标的有效落实。
[1]成尚荣.学生核心素养之“核心”[J].人民教育,2015(7).
[2]滕珺,朱晓玲.学生应该学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基础教育学习指标[J].比较教育研究,2013(7).
[3] European Council.Lisbon Eropean Council 23 and 24 March 2000 Presidency Conclusions[EB/ OL].(2000-09-04)[2013 -09-01].http: / / www.europarl.europa.eu/ summits/ lisl_ en.
[4]孔锴.浅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J].外国教育研究,2006(2).
[5]钟启泉.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发展:挑战与课题[J].全球教育展望,2016(1).
[6]彭寿清.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及特点[J].当代教育科学, 2004(18).
[7]李协京.对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考察[J].教育评论, 2003(1).
[8]张娜.DeSeCo项目关于核心素养的研究及启示[J].教育科学研究,2013(10).
[9]裴新宁,刘新阳.为21世纪重建教育——欧盟“核心素养”框架的确立[J].全球教育展望,2013(12).
[10]张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素养研究及其启示[J].教育导刊,2015(7).
[11]辛涛,姜宇,王烨辉.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课程体系建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12]董建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质量框架探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7(11A).
[13]付谢好,和学新.新世纪以来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及其启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5).
[14]李建忠.欧盟教育质量监测的指标和基准[J].比较教育研究,2009(10).
[15]皮连生,吴红耘.两种取向的教学论与有效教学研究[J].教育研究,2011(5).
[责任编辑:陈 浮]
Research and Enlightenment on Foreign Key Competencies
LIU Yimin
The research on key competencies began in the 1990s, and thorough content structure, curriculum system, and security system of quality of education have been formed.Key competencies have been the leading idea of promoting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And the research on key competencies is an international consensus.Researches have been conducted by UNESCO on lifelong learning, OECD on individual’s successful life and soci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EU, and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America, Japan.The research on key competencies includes concept, content, course system and quality assurance.It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o the basic education reform which should correspond to the need of individual’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inforce the reaction to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nstruct integrative curriculum research system.
key competencies; multidimension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 enlightenment
G631
A
1009-7228(2016)02-0071-06
10.16826/ j.cnki.1009-7228.2016.02.016
2016-02-29
刘义民,嘉应学院(广东梅州514000)文学院讲师,博士。